冯老头
2022-04-29刘香筠
刘香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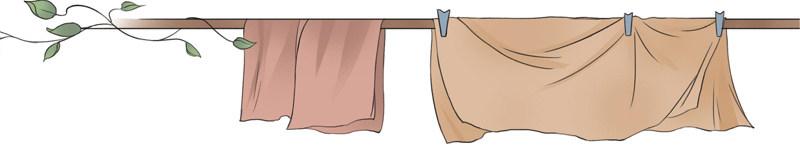

窗外面是一片空寂,天空已经好久没有泛蓝。那些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员才从小区喷洒完消毒水离开,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上午10点,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我发现她准备了四个人的饭菜。“可我们家只有三个人啊?”我问妈妈。“香香乖,这是给隔壁冯爷爷做的。”妈妈一边切菜一边对我说。冯老头?我感到有点疑惑。
冯老头是一年前搬到我家隔壁的,平时穿着一身唐装,喜欢搬一条小板凳、拿一张报纸在走廊里坐一上午,不时还哼一首小曲,只有午饭时间回去,然后又出来坐着。有几次从他身边路过,一股浓浓的草药味刺激着我的鼻子,那种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所以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听妈妈说,他之前是一位中医,现在已经退休在家,老伴早一步离他而去,有一儿一女,平时喜欢在走廊里坐着等他的儿子回家。他的儿子在市第一医院上班,女儿是个护士,已经嫁人,只有周末才会回来看望老人。
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一对儿女匆匆地来又匆匆地离开。临走时,老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眼里满是坚决,还一个劲地叮嘱儿女要注意安全。儿子应付了几句就离开了,似乎有很急的事要去做,毕竟他是医生。女儿抱了一下老人也匆匆离开了,可我明明看见她眼角泛着泪光。
从那以后,老人就再没有在走廊里坐着,妈妈则开始每天做好饭送到他的门口,敲门让他出来拿。
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已经无人敢上街,消毒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甚至晚上还有无人机在空中喷洒药水。
妈妈除了出门给冯老头送饭,已经不出门了。每天都有小区的物业人员给每家每户送食物。这天下午,我坐在阳台看着无人的街道出神,我们两家的阳台之间只隔了一道防护栏。突然听见隔壁传来阵阵抽泣,是冯老头。难道他出了什么事?我悄悄走到防护栏边上,只见冯老头抱着一张照片,肩膀不停地抖动。怎么回事?我很疑惑,一大把年纪怎么哭得像个孩子似的。突然,我感到身后有人拉我的衣服,是妈妈。她把我拉回客厅,我问她怎么回事,为什么冯老头会哭得如此伤心。妈妈低声说道:“冯爷爷的女儿在看护病人的时候不小心被感染,不幸走了。”脑海里一道霹雳轰下,我有点不敢相信。怪不得冯老头会哭得那般伤心。自己最亲的人走了,换了谁都会痛哭一场,更何况白发人送黑发人。
自那以后,小区有专门的人员给冯老头送饭菜。直到疫情第三个月的时候,妈妈出门买菜回来说:“你冯爷爷要重操旧业了。”我急忙跑到阳台,果然平时本该在阳台藤椅上读报的他此时并不在那。转身一看,他已经朝着小区外面走去,在那里有一辆救护车在等他,而他那有点驼背的身影此时在我心中无比高大。
两个月时间眨眼就过去了。两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去阳台看看冯老头回来没有。也许这是疫情期间唯一期盼的一件事了。时间飞逝,又过了一个月,冯老头的儿子回来了,他的脸上全是被口罩勒出来的痕迹,多少有些“可怕”。这天,我看到冯老头的儿子坐在他之前坐的藤椅上,手里是一张照片。突然,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难道冯老头……
那之后我不敢再去阳台,我怕听见隔壁传来哭泣的声音。一次晾衣服时不经意一瞥,我发现那张藤椅上坐着一个人,头发有些花白,是冯老头。只是不再如之前那般神采奕奕,想来是因为他失去了女儿吧。我鼻子一酸,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这个非亲非故的老头,不经意间已经成了我心里解不开的结。妈妈说,冯老头回来已经十几天了,只是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隔离,所以我才没能看见他。原来如此,那之前冯老头的儿子看的照片是谁的呢?
疫情缓解后,冯老头又成了我家的常客。两个月里,每次妈妈要去送饭,我都抢着要去给冯老头送。一来二去,我俩之间也变得亲密。我经常邀请他到我家来吃饭,虽然每次他都有些推辞,但奈何不了我的热情,只好跟着我进了我的家门。有时,我还跟着他下楼去散步,人们碰见了直说他的孙女真乖。冯老头和我听了,对视一眼后都哈哈大笑……
6月,天空的乌云摊在天空,乌沉沉的。暴雨下个不停,有些地区受到洪水的侵袭。我家楼下也不例外,到处都是浑浊的泥水,虽然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还是让我们担惊受怕。在这期间,我一无聊就跑到冯老头家去摆弄他的那些草药。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草药味是难闻的,反而觉得有些清香。冯老头总会耐心地收拾被我弄得一片狼藉的草药,每次看他细心地挑选、辨别、归类这些草药,我都有一种好像他就是我的爷爷的感覺。就这样,在他的陪伴下,虽然疫情与洪水期间不能出去,但也不是那么无聊。
洪水终于过去,天空放晴。这天,我在阳台睡了一个午觉后,去冯老头家找他下楼散步,可是平时敞开的门此时闭得严严实实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丫头,爷爷去散步啦,就在楼下。
跟我玩捉迷藏。哼,好你个冯老头!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职业大学)
(插图:石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