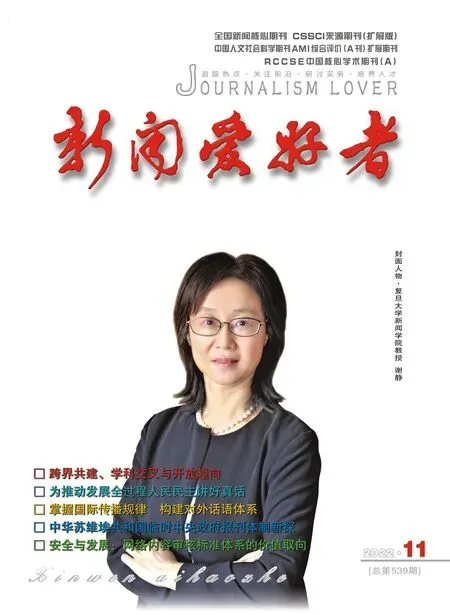关于主流媒体污词治理的思考
2022-04-29郭克宏
郭克宏
【摘要】网络污词由“民间舆论场”侵入“主流媒体舆论场”已经日久,且仍保持扩散之势,汉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包括媒体行业在内的一些人对污词的本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媒体自律和社会他律的治理效果不够理想。要充分认识污词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善污词治理手段,多措并举阻断污词进入“主流媒体舆论场”的通道。
【关键词】污词;舆论场;主流媒体;治理
“两个舆论场”概念是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首次提出的,他认为“民间舆论场”是靠口头传播和自媒体平台形成的民众意见汇聚地,“主流媒体舆论场”是国家主流媒体营造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舆论平台。[1]打通“两个舆论场”一直被视为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努力方向。在我国主流媒体积极拥抱“民间舆论场”的过程中,污词现象沉渣泛起,虽几经努力,但扩散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媒介环境被污染,社会风气被毒害。2021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污词泛滥再次提出警告并提出治理意见。目前,“治污”的当务之急是对其在“主流媒体舆论场”做好屏蔽。
一、污词及其传播态势
“污”即脏,污词是指内容污秽、低级下流、给受众心理带来不适感的词语。这种词语一般用于诅咒、吐槽等宣泄情绪的小众语境。污词由来已久,新媒体环境里的污词泛滥是近年来借助网络流行的一种语言现象,与传统污词相比有着独特印记。
(一)污词的特点及本质
网络上流行的污词有三个特征:一是污词语义比较“污”。这类词主要有两个来源:由生殖器名称或者相关谐音词合成,如“撕逼”“装逼”“傻逼”“牛逼”“逗比”“懵逼”“屌丝”“傻屌”、SB;描述性活动,如“操蛋”“我靠”。二是附着时尚的外表。“我草”“卧槽”“我擦”“草尼玛”等,因为谐音双关修辞而趣味十足,从而受到热捧成为流行语。三是起源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因其语义的“污”一般仅用于小众语境。
污词的流行迎合了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的标新立异和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符合他们以蔑视崇高来消解正统的非理性愿望,是他们摆脱现实世界制度和规则束缚的心态表达,具有亚文化典型的反叛性、边缘性和颠覆性的特质。
(二)污词对主流媒体的侵入
污词从“民间舆论场”侵入“主流媒体舆论场”的突破性标志是“屌丝”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人民网在2013年3月1日转文《给大家自称屌丝的权力》对此表示肯定:既然“二逼”“苦逼”等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媒体就只能“与时俱进”了。从此,污词在主流媒体上从以往的犹抱琵琶走向理直气壮。
1.从自媒体侵入主流媒体
污词从自媒体的“民间舆论场”进入“主流媒体舆论场”,在传统媒体实现了“身份漂白”和“角色转正”,包括中央级党媒在内的传统媒体及所属网站纷纷放下身段去蹭污词热度,都市媒体更是不甘落后,播发的资讯里污词遍布,惨不忍睹。
2.从“软新闻”入侵“硬新闻”
如果说污词对传统媒体甚至权威媒体的成功入侵是媒体行业语用的理性不足,那么从“软新闻”到“硬新闻”的突破则是整个行业的底线沦丧。比如,金融分析文章《戴志康带不走金融科技的“高光时刻”》(央视网,2019年9月5日)中使用的“屌丝死于P2P”,科普信息《让科学也变得更屌丝一点》(《杭州日报》,2013年2月3日)、国际文化新闻《日本屌丝团上街抗议情人节》(《海南日报》,2015年2月16日)、教育新闻《成都“史上最萌”中考作文题 考生点评“很逗比”》(人民网,2014年6月13日)等不一而足。更不可思议的是,“屌”字竟然出现在东北一家出版社的幼儿读物上。[2]
3.污词扩散“进行时”
早在2000年,《文汇报》题为《网络语言不规范引起关注》的文章对污词传播吹响了“哨子”,但是并没有真正引起关注。据考察,污词媒体泛滥集中在2013年至2014年前后。2015年6月,国家网信办主持召开的“净化网络语言”座谈会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纷纷予以介绍,旗帜鲜明地反对污词使用,这可视为主流媒体正式对污词集体抵制的标志,污词传播扩张之势由此在主流媒体上得到一定遏制,但并没有禁绝。2021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污词治理提出明确要求,一些主流媒体认真落实,效果明显。截至2022年4月上旬,“屌丝”等污词已经在新华网销声匿迹,但在其他一些中央级传统媒体网站的资讯中“污词依旧”。
目前,影响力巨大的商业网站仍是污词重灾区。用“搜狗搜索”在某影响力巨大的网站“资讯”板块搜索,含有“撕逼”“屌丝”“卧槽”的信息都在万条以上。
4.从小众渗透大众
污词起初仅在自媒体的小众里流行,后经主流媒体持续助力已全面渗透进公众生活。北京大学一研究机构竟然在全国范围内搞过一次“屌丝”调查,评出国内“最屌丝的省份”“最屌丝的城市”“最屌丝的行业”及最盛产“屌霸”省份,还发布了一份“屌丝”地域分布榜单。[3]社会生活中靠“蹭污”博取眼球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相声作品《屌丝青年》,有走紅视频节目《屌丝男士》,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在某卫视主持的一期国际政治问题分析节目的题目居然是《屌丝辛格的逆袭路:十年一“梦”褒贬参半》,可见污词对社会浸淫程度之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教育专家张黎曾撰文批评污词传播现象,他警告说:网络语言规范问题已经超出语言的范畴,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4]
二、污词传播的认识误区
(一)媒体行业对污词修辞属性的错误认知
社会上“污词无害论”颇有市场:一是认为污词本身不污,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污词自行“脱污”了;二是污词是受欢迎的时尚用语,主流媒体也要改变看污词的老眼光。某出版社一位副总编曾对媒体表示:“‘屌丝这个词没什么不雅观的,如果它不雅观,那‘厕所更不雅观。”他认为“屌丝”描述功效比传统词语更准确,具有其他词语的不可替代性;使用时间长、使用群体大也是媒体不应拒绝它们的理由。[5]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也持相似态度,认为“屌丝一词传播至今已非贬义”。[6]有人甚至拿“屌丝”登上中央党报作为污词使用正当性的“一个突出例证和缩影”,认为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7]这些观点是社会上对污词特殊属性错误认知的典型代表。
污词的魅力除了来自自身形象附加标识功能以外,时尚特性也很鲜明。但是,考察污词的语义,其态度倾向明显属于贬义,用于责骂和贬损;污词对生殖器官的炫耀和对交媾愿望的表达决定其使用语境的特殊要求:仅限于微观语境的私人场合或者文艺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特殊需要。在大众传播领域,尤其是主流媒体,满眼“屌丝”“撕逼”无异于有身份的人在公共场所污言秽语骂街。
必须承认,词语的语义和态度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但是,审视当下的流行污词,它们能指的变动表现在原先生殖器官名称谐音字的替代,所指的改变也仅局限于比喻意义的引申。但在口头传播时,污词的能指几乎没有变化,比如“操”“草”“肏”读音基本相同。换言之,污词自诞生起,能指和所指两方面都没有改变“污”的本质。说“屌丝”和“厕所”一样污的观点更是荒谬。从所指来看,“屌丝”是个人隐私的范畴,厕所虽是“藏污纳垢”之所,却是可以在公共场域谈论的东西,它们的使用语境迥异。使用时间长、使用群体大更不能成为污词进入主流媒体的理由,千百年来百姓骂街的污言秽语绝不能成为主流媒体承载日常信息的工具。
(二)对媒体政策“贴近性”的误读
“三贴近”是党对媒体提出履行使命的重要工作原则。为此,“破防”“给力”“洪荒之力”“月光族”“作秀”等一大批深受人们喜爱的流行词语的吸纳,使媒体产品的表达形式更加丰富,更接地气,提高了媒体的传播力。但是这不能成为污词进入“主流媒体舆论场”的借口。
党和政府在强调“三贴近”的同时,更强调媒体的“引导”责任,要求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媒体“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8],坚持传播正能量,成风化人,澄清谬误,明辨是非[9]。这说明党和政府对媒体“贴近群众”的要求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履行对群众错误认知的纠正和引导义务。无条件地贴近就成了迎合,那就丧失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清华大学王君超教授对社会纵容污词泛滥的现象表示痛心,认为对粗俗鄙劣的语言文化现象的包容心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不幸。他警告说:“如果网络世界变成一个充斥着脏字儿的虚拟空间,不仅网络文化会被污染,而且整个语言文化系统也岌岌可危。”[10]
(三)对自律和他律的无视
从媒体自律看,新华社之前做过努力。2017年11月,《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明确禁止使用的词语中,就包括“傻逼”“我靠”“玛拉戈壁”“草泥马”“装逼”“撕逼”“特么的”之类的污词。从行业自律看,2015年8月,中国记协向全行业发出《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倡议书》,并组织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召开专题评议会,倡导新闻媒体和网站抵制不文明用语的歪风。[11]在污词治理的他律方面,我国并不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条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不仅对媒体用语规范提出了要求,更强调媒体精神价值导向,要求媒体在弘扬优秀道德文化和时代精神、展现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方面履行主体责任。罔顾法律法规对媒体传播的用词要求,有业内人士居然认为“没人规定党报可以用什么语言,不可以用什么语言”。[12]这不仅反映出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对行业规范的无知,也从侧面暴露了污词治理效果欠佳的根源。
三、对主流媒体污词治理的思考
(一)主流媒体肩负屏蔽污词的社会责任
我们党和政府对媒体工作一贯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特别强调在媒体融合中“传播正能量”。[13]这里的“各个方面”理所当然地包括文明的传播语言。所以,在新的传播技术语境下,主流媒体应发挥其社会“瞭望塔”职能,监督包括网络平台在内的失范行为,“扛起文化责任和价值引导责任的大旗,塑造正能量的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14]主流媒体在言辞上不能把自己和普通群众等同起来,更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二)主流媒体污词治理的建议
第一,法治治污必须有“良法”可依。法理学认为,“良法”除了目的价值追求的正当性之外,还表现为可靠的形式价值。诸多形式价值要素中包括“实用性”和“明确性”,即法律规范不应华而不实、含混不清。[15]对于污词治理,国家广电部门治理电视广告乱象的做法值得借鉴,即根据现实乱象有针对性地出台具体明确的规范要求,让执法活动有清晰的依据和尺度,用“硬控制”手段高筑污词进入“主流媒体舆论场”的隔离墙。第二,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治污”原则。现实的媒体行业治理中,监管部门对政治性差错和非政治性差错往往表现出“硬”“软”不同的两种态度,治理效果也截然不同。对此,建议相关部门借鉴治理政治差错的决心和勇气,加大对污词传播的监管威慑力。对于违规使用污词的主体,监管主体要敢于“一针见血”;对于屡教不改影响恶劣者,要果断“一剑封喉”——吊销当事媒体的经营证照,追究当事人的相应责任。第三,在法治框架内多措并举。“当前,全面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已经成为提升政府监管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力的重要举措。”[16]作为市场主体,政府可以考虑把信用监管手段纳入媒体治理体系,对不守规矩者给予信用降级。同时,污词治理有必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让那些热衷于污词传播的主体经常在社会舆论中“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当有助于他们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
四、结语
主流媒体的污词治理是当前全行业甚至全社会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清污”的前提是对污词的本质和传播危害的深刻认知。统一社会认识,创新治理手段,把高度的责任担当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屏蔽污词在“主流媒体舆论场”中的传播,为信息传播营造风清气正的媒介环境。
参考文献:
[1]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打通“两个舆论场”[EB/OL].人民网,2011-7-11.
[2]幼儿早教书现不雅文字,还组词“屌丝”?哈尔滨出版社回应[EB/OL].光明网,2021-11-28.
[3]屌丝生存状况报告出炉:平均薪酬2917.7元[EB/OL].光明网,2014-10-29.
[4]张黎.网络语言,到底该规范什么[N].光明日报,2019-07-13.
[5]桂杰,等.网络时代悄然改变的“主流表达”[N].中国青年报,2012-11-11.
[6]屌丝生存状况报告出炉:平均薪酬2917.7元[EB/OL].光明网,2014-10-29.
[7]屌絲生存状况报告出炉:平均薪酬2917.7元[EB/OL].光明网,2014-10-29.
[8]习近平的这“三问” 媒体工作者要谨记在心[EB/OL].央视网,2019-2-21.
[9]郑保卫.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J].新闻爱好者,2021(9):17-25.
[10]王君超.低俗用语,且慢包容[N].光明日报,2015-06-14.
[11]中国记协举办网络文明用语专题评议会[EB/OL].中国记协网,2015-10-27.
[12]桂杰,等.网络时代悄然改变的“主流表达”[N].中国青年报,2012-11-11.
[13]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M].展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11-112.
[14]包国强,宋钦章.民营网络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机理与推进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2(1):12-16.
[15]张文显.法理学[M].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14.
[16]徐敬宏,袁宇航,巩见坤.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平台治理:关键议题、现有模式与未来展望[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14-120.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