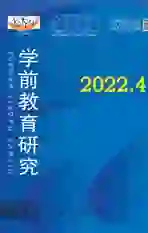儿童早期教育“托幼一体化”的国际向度及本土镜鉴
2022-04-28刘国艳詹雯琪马思思范雨婷
刘国艳 詹雯琪 马思思 范雨婷



[摘 要] 为0~6岁儿童提供一体化的保教服务已成为国际学前教育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破解我国当前“幼无所托”困局的有效策略。瑞典、新西兰等国通过行政、课程、师资整合以及多方协作实现“托幼一体化”的先行经验,可以为我国探索“托幼一体化”的中国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未来我国应架构整合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制定贯通性的学前教育课程标准,构建一体化的托幼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形成多元一体的0~6岁早期教育服务供给格局。
[关键词] “托幼一体化”;早期教育;托育服务;学前教育
公共托育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养育成本的增加以及女性就业意识的觉醒,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逐渐提升,城市双职工家庭比例也随之急剧增加,这极大冲击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刺激了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然而,相比于广大群众对优质儿童照护与早期教育服务的热切期盼,我国3岁以下社会托育服务供给却十分短缺,供需严重失衡,且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与质量隐忧。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0~3岁婴幼儿数量约4 200万,其中30%具有较为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实际供给仅为5.5%左右,供给缺口超1 000万以上。托育难、托育贵、托育质量参差不齐等多重难题使城市双职工家庭陷入“工作—家庭”平衡的困境,强化了夫妻间因育儿产生的矛盾冲突,并影响了家庭内部和谐。此外,在社会性别文化的规制下,不少职业女性被迫“舍业归家”或降低职业目标追求,承担起婴幼儿照料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育龄女性就业权益的充分实现,成为限制女性职业发展的桎梏。随着2021年5月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我国生育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较少的优质婴幼儿托育服务势必成为导致新时代社会压力与生育焦虑的重要因素,托育服务供给的压力将空前凸显。由此可见,在生育政策变革的背景下,加快完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不仅关涉儿童健康成长,是对新时代体现妇女权益、维持家庭和谐稳定的直接回应,更是增强三孩生育政策效能的基础工程与解决民生之需的民心工程。
一、破解困局:“托幼一体化”
(一)“托幼一体化”的意蕴阐释
“托幼一体化”意味着教育视线的延长与视域的扩展,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解读:就纵向之维而言,指转变0~3岁与3~6岁教育之间脱节割裂的状态,将0~6岁幼儿教育进行整体性思考及系统性规划,在管理体制、投入机制、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督导评估等层面均实施一体化,进而实现“托”龄和“幼”龄的有机联系、有效衔接;就横向之维而言,指促成托幼园所与家庭、社区、社会相关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个责任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结,共绘幼儿发展的最大同心圆,谋求协同教育的最大公约数,凝聚为互通、共享、协作的教育共同体,为0~6岁幼儿提供连贯协调的保育与教育服务。(见图1)其根本目的与价值取向在于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与教育规律,既重视0~3岁婴幼兒发展的特殊性,又兼顾到0~3岁与3~6岁保育和教育的连贯性、衔接性,寓教于保、保教融合,并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形成合力,建成横向贯通、纵向衔接的0~6岁托育服务体系。
(二)“托幼一体化”的现实呼唤
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儿童抚育通常被看作是家庭私领域的事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鼓励女性更好地从事社会化生产的目的,我国借鉴苏联的经验,建立起较为全面的托育服务网络,形成了“国家—单位—集体—家庭”四者合力的托育服务模式,以大集体公社(农村)和单位、社区(城市)为基础的集体照顾模式成为家庭儿童照料的有力补充。[1]然而,随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城市、农村的国有和集体组织逐渐萎缩,公办托儿所几近消失,公办幼儿园因资源有限而定位于只招收3~6岁的儿童,3岁以下儿童入托机会急剧缩减。3岁以下儿童托育的责任除了回归核心家庭,也被推向市场。改革开放后,“重社会、重市场、轻政府”成为我国政府托育政策的基调,《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1992)和《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2003)都提到了以“社会力量”办园。这里所指的“社会力量”包括政府自身以外的其他力量,核心主体力量即市场。特别是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一大批早期教育企业先后创立,提供机构式托育。[2]托育服务行业发展迅速,但也存在过度市场化的倾向,目前0~3岁托育服务机构在服务标准、课程质量、师资资质、卫生安全、园所环境等方面均缺乏有效的规范与监管,各类教学、安全、卫生事故频发,难以有效承载科学育儿的重责。
随着国家和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及普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为起点,0~3岁早期教育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属性再次凸显,为家庭提供公益性、普惠性的早期教育服务成为新时期努力的方向。2019年2月,《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2021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将托位数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2020年的1.8个增加至2025年的4.5个”,并明确了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因此,加快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确保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满足广大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与向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的信任感与获得感已是迫在眉睫。
二、他山之石:“托幼一体化”的国际向度
随着脑科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推进,0~6岁儿童托育的重要性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普遍共识,为0~6岁儿童提供一体化的保教服务已成为国际学前教育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学前教育”的概念范畴已由3~6岁向0~6岁拓展延伸,随后“托幼一体化”的理念应运而生。[3]英国、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日本等国作为先行者纷纷于20世纪90年代将“托幼一体化”理念落实于政策实践中,建构起相应的法律、财政与监督保障机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力倡导“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一体化”(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并在其2006年出版的《强势开端II》(Starting Strong II)调研报告中一再重申“托幼一体化”对普及优质幼儿教育的战略意义,倡议各成员国启动托幼整合。[4]根据OECD《2020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提供的最新数据,超过70%的成员国正积极推行托幼整合的托育模式,并由单一部门(通常是教育部门)主管所有类型的托育服务。[5]相较而言,瑞典及新西兰的“托幼一体化”模式实施历史更长、程度更高、效果更显著,探索经验相对成熟,因此也更具有典型性。立足本国教育的现实土壤,观照“托幼一体化”的国际实践进路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对拓展我国托育服务的理论视野、提高托育服务的实践水平大有裨益。
(一)瑞典“托幼一体化”的实践与成效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瑞典的“托幼一体化”制度、课程体系以及师资建设等逐渐健全及完善,托育服务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1. 实践经验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瑞典学前教育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建设密切联系,由国家健康与福利董事会(The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负责。自1996年起,幼儿保育的管理权逐渐从福利部门划归至教育与科学部,承担0~6岁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全国性政策的制定和儿童照看、教育管理的职责。1998年,国家教育部(the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全面接管国家健康与福利董事会的幼儿保育相关事宜,成为瑞典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行政管理部门的统合使得学前教育机构和人员在办事上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效率得到大大提高,满足了学前儿童保育和教育方面的发展需要。基于有不断健全的政策法律保障及明确的管理监督机构,瑞典托幼公共服务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效运行的体系。瑞典的幼教机构绝大多数由政府设置,以公立机构为主,以非营利机构为辅。虽然近年来市场也开始参与少量托育服务供给,但其供给的服务仍属于政府购买的范畴。[6]
瑞典“托幼一体化”的托育服务是以高昂的政府公共经费支持为基础的。20世纪70年代,瑞典经历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失业率骤然提升,经济持续下滑。为了积极推动妇女就业,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大力扩建托幼一体幼兒园,扩大了“托幼一体化”学前教育的覆盖面。瑞典政府制定了托育服务的最高收费标准,即婴幼儿托育服务费用不得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3%,家庭缴纳费用约占托育服务机构运行经费的8%,[7]有效地减轻了家庭的养育负担。2015年,瑞典家庭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为3.54%,其中大部分开支用于为婴幼儿提供福利保障,其开支占比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占比最高的。[8]由于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人力成本较高,为确保托育服务的规模和质量,瑞典用于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财政经费高于学前教育阶段,如2015年托育服务财政经费投入占GDP 的比例为1.1%左右,是世界范围内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学前教育的投入仅为0.5%左右。[9]由于托育服务长期获得大力的认可和公共财政支持,有效分担了婴幼儿家庭育儿经济成本,使得托育服务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是可获得、付得起、有质量的。
1998年,《学前教育课程》(Curriculum for the Pre⁃school Lpfö98)出台,从法令的高度对全国学前教育课程做出了标杆性指导。该课程框架不仅涉及“保育”,也涵盖“教育”,旨在将保育与教育融为一个整体,提高不同阶段之间衔接的连贯性与相关性,为1~5岁儿童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10]此外,框架强调以游戏为主要活动形式,并根据幼儿的需要开发全面的课程,促进婴幼儿在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该课程框架还突出了家长参与的重要性,增加了对家长的引导与支持,使家长有机会参与国家框架的设计并对幼儿园活动产生影响,强化了幼儿园保教工作与家庭的密切合作。可见,该课程框架“一体化”的设计思路不仅体现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更贯穿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一体化”的课程框架,不仅仅使得保教形成了良好的衔接,使儿童获得连续性发展,也为行政管理机构更好地管理学前教育事业铺平了道路。2004年,《学校法案》(The Pre⁃school Bill)取消了托儿所与幼儿园之间的区分,规定1~5岁幼儿进入幼儿园或家庭日托中心,采取混龄编班。目前幼儿园(Preschool)是提供公共托育服务的主要机构,面向1~5岁婴幼儿,其托育服务正是在《学前教育课程》的指导下开展。
师资队伍建设也是瑞典“托幼一体化”建设的一大着力点。2004年9月,瑞典国会出台了一项学前教育法案(The Pre⁃school Bill),法案提出自2005年1月1日起,国家将拨款给各政府5亿克朗,用于招募幼儿教师及保育员,这使得早期教育的师资队伍扩充了10%。[11]此外,瑞典实施了“促进学前教育”(The boost for preschool)项目,对幼儿教师和保育员不分专业方向均实施一致的职前教育课程培训,课程涵盖的年龄范围为1~5岁儿童发展的相关内容,且注重保育人员与幼儿教师的交叉培训。幼儿教师除了完成三年大学教育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外,还要学习儿童发展心理学、教学方法、家庭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保育员除了要完成三年中等学校的专业课程学习外,还要学习儿童保育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据统计,2012年至2014年期间,瑞典政府已为早期教育师资的专业进修提供总计约1.2亿瑞典克朗,用于这一期间的跟进和评估领域。[12]幼儿教师与保育员无论是在职前教育,抑或是专业发展上都逐步趋同,托育服务的师资队伍质量和社会地位均得到进一步提升。
2. 实践成效
瑞典“托幼一体化”的治理模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第一,瑞典“托幼一体化”普及程度非常高,2017年,瑞典有84%的1~5岁婴幼儿入园,与一般发达城市的入园率对比相对较高。[13]“托幼一体化”的模式为托育服务注入了义务教育普惠、免费和公平的原则,使托育服务的获得和父母就业脱钩,成为儿童权利的一部分。第二,瑞典“托幼一体化”的质量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主要强调延续连贯课程体系,不仅从制度上向前延伸至1岁,还使得学前教育融入整个教育系统中,突出了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的地位,进一步加深构建了国家终身学习体系。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获得了社会和家长的普遍好评,对托育服务质量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14]第三,瑞典的“托幼一体化”由于较好地实现了托育服务的高水平和高质量供给,进而较好解决了性别平等、儿童贫困等诸多社会问题,使女性就业率达到83.3%,儿童贫困率仅为9.1%。[15]此外,瑞典“托幼一体化”实践对提升生育率起到了积极影响,2006—2016年瑞典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16]在低生育率发展为全球性社会问题的背景下,瑞典“托幼一体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托幼一体化”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二)新西兰“托幼一体化”的实践与成效
新西兰是世界上整合保育和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延续至今,其改革开端早、历时长、改革范围广泛,涉及行政管理转移、幼儿教育国家课程标准、师资培训以及财政投入这几个主要方面。
1. 实践经验
新西兰自1986年起逐步探索托幼整合的管理体制改革,以期克服原有早期保育与教育分权而治的弊病,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中的统领作用和首责定位。其具体做法是将儿童保育从社会福利体系中剥离并入教育系统,由教育部集中管理。[17]此举不仅提高了学前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有效解决了分权结构下幼儿保育与教育行政治理的平行、重叠或冲突,随后其改革被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所效仿。1989年,新西兰《教育法》出台,该法案将幼儿教育和保育中心定义为“用于教育或照顾6岁以下的儿童的场所”,表明学前教育是为儿童提供教育和保育服务,从国家层面保障0~6岁儿童获取保教服务的权利,促进了“托幼一体化”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新西兰对0~6岁学前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在2002年颁布了对新西兰学前教育中长期发展具有全面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政策《未来之路——幼儿教育十年战略规划》后,0~6岁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系建设更是驶入了快车道。2001—2019年,新西兰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从0.28%提高到0.68%,占整个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从5.6%提高到14.19%,生均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从5 392新元增长到9 254新元,分别增长了约143%、153%和72%。[18]得益于学前教育经费来源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模式,新西兰“托幼一体化”体系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机制,大大增强了发展实力。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早颁布幼儿教育全国性课程标准的国家之一,1996年新西兰教育部制定了适用于0~6岁儿童的《编席子:学前教育课程纲要》(Te Whāriki: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以下简称《课程纲要》),并于2017年结合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进行修订。Te Whāriki是毛利语,意指“编织的草席”,引申为《课程纲要》与毛利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原则、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实践像草席一样相互交织而组织起来,象征着课程的一致性与连贯性。[19]《课程纲要》涵盖了健康幸福(Wellbeing)、归属(Belonging)、贡献(Contribution)、交流(Communication)和探索(Exploration)五大学习领域,每一领域又包含不同的课程目标和学习成果,成为全国保教人员的纲领性行动指南。[20]《课程纲要》覆盖了0~6岁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并根据儿童的年龄划分学习阶段,体现出分段式的一体化课程设计思路,既突出了儿童课程的整体性,也照顾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发展特点和需求,有效促进了儿童的连续性发展。
新西兰还聚焦保教人员的专业发展与支持条件。1985年起,新西兰幼儿保育和教育论坛大力支持延长并整合幼儿教师教育的培训课程。[21]幼儿园教师需接受两年的培训,为了提高早教人员的专业素养,教育部也为保育员提供一年的培训课程,此时的两个政府工作小组分别关注幼儿园和儿童保育。论坛结束后教育部加强了对政策变革方向的思考,教育部长指示延长幼儿教师的培训时间,并为保育工作者和幼儿教师提供综合培训,从1987年开始引进为期三年的综合培训课程,三年制的早期教育文凭被认为是幼儿园和儿童保育中心的“基准”资格证书。[22]此外,《未来之路——幼儿教育十年战略规划》明确规定早期保教人员薪资水平不得低于小学教师薪资标准,在此规划实施期间,政府通过加大公共支出以推进教师薪资平等的实现。[23]这一系列举措改善了保教人员的工作条件,提升了师资保留率,有利于建立优质的保教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保障儿童保育和教育质量。
2. 实践成效
自“托幼一体化”改革以来,新西兰全国范围内参加教育和保育中心以及家庭服务的儿童人数大量增加,幼儿托育服务的参与度越来越高,0~6岁婴幼儿积极参与各类保教服务,各个年龄段儿童的入学率、出勤率稳定增长。2007年“20小时免费ECE”计划实施后,新西兰有98%的四岁儿童及20%的两岁以下儿童参加各种幼儿教育计划。在该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教育成本下降了5.2%,父母的幼儿教育花费下降了32.4%,更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幼儿保教服务。[24]经合组织对各成员国的幼儿教育进行监测评估发现,2013年,新西兰3岁以下儿童参与率高于大多數经合组织国家,并且在2003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8%,有41%的0~2岁儿童参与正规托育服务。2009年至2018年间,0~4岁儿童在许可服务机构的入学率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18年为64.4%。[25]
(三)“托幼一体化”建设的国际经验之维
上述国家的“托幼一体化”服务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促进儿童发展、提高女性就业率及总和生育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和社会公平,都起到了良好作用,各国经过时间考验以及各界政府接力式的传承改革,取得较大成效,其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1. 行政之维:强化政府职能,构建一体化管理体制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即国家统筹与组织学前教育事业的基本体系、工作制度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它既是教育体制与教育管理体制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26]理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既要明确各层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关系,也要厘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托幼分离的“双轨制”模式明确区分了学前教育中的“保育”和“教育”,其特征是针对婴儿与幼儿采取不同的治理体系,遵循不同的教育/保育传统、财政投入、员工标准和质量标准。法国的托育服务和3~5岁学前教育长期以来分别属于教育部和卫生与社会事务部门管理。(见表1)这种区分治理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国家行政结构的沿袭,另一方面是其教育观坚持认为应当将婴儿教育和幼儿教育进行适度区别。[27]“双轨制”模式导致法国0~3岁与3~5岁学前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差异:第一,幼儿园的入园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托育服务却长期处于供需失衡的状态;第二,幼儿教育长期以来获得充足的公共拨款,而托育服务长期以来缺少公共拨款;第三,幼儿教师的学历要求不断提高,而托育服务员工的资格要求相对较低,居家照顾人员仅需要满足数小时的培训要求即可上岗,导致师资力量良莠不齐。[28]此外,家长长期面临着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女性就业权益的充分实现。一些联邦制国家受分权制度和传统习惯影响,将学前教育治理交由多个部门协同完成,包括社会福利部、家庭事务部、教育部、妇女和儿童工作部、公共健康部、劳动力保障部等。[29]美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见表1)与瑞典、新西兰相比,美国由于缺少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系,各州托育服务治理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相对而言,美国托幼关系复杂的“分散化”模式为托育服务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甚于积极影响。[30]第一,由于缺乏全国性治理框架,托育服务政策和供给仍然严重碎片化,为家庭的选择带来困难;第二,增加托育服务的供给与公共投入未成为政府治理重心,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儿童入托率低于OECD平均水平;第三,托育服务的市场主导特征明显,由此带来了托育服务费用上升较快、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托育服务队伍质量低工资低等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
为破除横亘在0~3岁婴儿保育与3~6岁幼儿教育之间的壁垒,改善托幼分离所滋生的政出多门、职责交叉重叠、管理效能低下等一系列弊端,瑞典、新西兰相继采取措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将0~6岁学前教育管理结构由“多轨制”向“单轨制”变革。(见表1)经合组织较为推崇的正是托幼整合的“单轨制”模式,特别是由国家教育部门主持下的一贯制治理体系,认为其是扩大学前教育可获得性、公平性以及减少儿童在不同阶段间多次转化适应的理想选择。[31]将学前教育服务归由教育部门单一负责,一方面提高了学前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解决了分散行政结构下学前教育政策不连贯的问题。
2. 课程之维:制定国家标准,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
课程标准是对一定学段课程的基本规范与要求,是规定课程目标、内容框架、课程实施与评估的纲领性文件。整合设计课程标准是支持儿童连续性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各国落实“托幼一体化”的战略之举。正如OECD《强势开端V》(Starting Strong V)中所強调:课程标准的制定和规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服务条例和司法之间的一致性,并确保各地区学前教育目标和具体实施层面上的相对公平,且有助于儿童的可持续发展与教师专业成长,增进教师与家长的沟通。[32]瑞典、新西兰均将研制课程标准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予以充分重视,且课程标准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即年龄范围覆盖从出生至义务教育学龄前的全体儿童,保育与教育的课程体系相互衔接、相互贯通,课程实施具有整体性取向。(见表2)
瑞典及新西兰的学前教育课程标准覆盖整个学前教育阶段,使0~3岁教育有了统一的规定和执行标准,有效避免了托班课程小班化趋势,即用幼儿园小班课程的模式来实施0~3岁教育。同时,将0~6岁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纳入有机联系、共同发展的体系中,更能体现课程的综合性与整体性,更有利于整体规划课程内容和儿童的全面发展。我国现行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针对在园幼儿,分年龄段、分领域地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保教质量指标做出了详细规定,为广大家长与幼儿教师提供了具体、易操作、权威性的指导与参考。然而,0~6岁一体化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还未跟进,难以兼顾到0~3岁与3~6岁保育与教育的衔接性,无法支撑儿童实现全面持续发展。
3. 师资之维:淬炼师德师能,构建一体化培养模式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教必先强师。师资建设是“托幼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师资队伍及其素质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在“托幼一体化”的背景下,幼儿保育人员与教育人员的整合渐成国际趋势。师资一体化培养模式涉及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模式、考核评估等诸多要素,旨在打破幼儿保育人员培养与教育人员培养之间相互割裂的藩篱,变“分割式”培养为相互衔接、前后连贯的系统性培养。整体而言,瑞典、新西兰的一体化师资队伍培养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促进早期保教人员资质的提高与趋同。不同于各国对保育员与幼儿教师的学历要求、资历认证施以分轨限定,瑞典、新西兰均对两者的资质要求做出同等规定,构建起一体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体系以及资格认证标准。获得教师资格认证并通过审查登记的教师方可跨幼儿园、全日托中心、家庭日托、托管机构任教。[33]调整保教师资职后培训结构,构建覆盖所有托育从业人员的培训体系,实现了托育机构从业人员规范化。
第二,促进早期保教人员培养课程的整合。0~3岁与3~6岁这两个阶段,儿童的保教服务需求十分相似且具有连续性,因此应促进“托”与“幼”的对接,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特点来实施保教工作。培养课程的融通与整合能够帮助保教人员获得“托幼一体化”教育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保障其胜任0~6岁年龄跨度如此宽广的幼教工作。瑞典、新西兰通过整合托幼师资职前培养体系,建立起一套具有核心技能、知识体系的师资培养标准,从而提高了“托幼一体化”的整体质量。
第三,优化保教人员薪酬待遇。瑞典、新西兰政府致力于改善早期保教人员的工作条件,通过立法明确保教人员的地位,对保教人员的工资待遇做出具体规定,分阶段提高保教人员的薪酬标准,并建立起完善的对侵犯幼儿教师权益行为的惩罚机制。加大财政投入以促进保教师资质量的提升,通过立法对幼儿教师财政拨款的数额、拨款的审批、款项的实际运用与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严格的规定。以上举措有效提升了保教人员的职业满意度与社会地位,增强了高质量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4. 协作之维:凝聚内外力量,构建一体化合作机制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学前教育被纳入开放的社会体系。儿童的发展受到与其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学前教育既要注意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又要面向社区,整合优化社区资源。“托幼一体化”是以托幼园所为核心,并横向整合家庭、社区、社会相关机构等多方资源合作共育的开放式系统。为实现早期教育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瑞典及新西兰都大力倡导建立起多方协同的一体化合作机制,为幼儿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智力支持以及时空便利。
鉴于婴幼儿的发育特点和生理特征,家庭始终是婴幼儿最主要的照料主体和中心场域,在托育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核心性地位。因此,在瑞典和新西兰,政府十分重视家长在托育服务中的作用,以社区为资源集散点,指导家长参与托育服务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提高家长参与的意识和理念,从根本上提高早期教育的质量,促进托育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归纳分析可知,家长参与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4类,包括政府为家长提供信息和支持材料、提供家庭上门指导、给家长充分的参与权、鼓励家长经营托育服务机构。[34]此外,儿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父母和托育机构,也与社区环境息息相关。因此,瑞典和新西兰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致力于为儿童提供一个“连续的服务”。社区的参与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一种额外和扩展的服务,同时也为家长的参与和合作提供了空间。尤其对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家庭来说,社区参与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强有力的社区可以作为“社会网络”,给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支持,从而有效分担家长的育儿压力。
三、本土镜鉴:国际向度对我国的启示
鉴于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借鉴国外托育事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文认为0~6岁“托幼一体化”学前教育体系正是突破“幼无所托”困境,使托幼互惠共生的有力举措。
(一)“托幼一体化”是破解我国托育困境的有力举措
在“托幼一体化”这一发展路径中,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办托班是最好的“托幼一体化”形式。该体系具有以下优势。
1. 兼顾0~6岁儿童发展的特殊性
3岁以前,个体的发展不仅涉及生理发育、动作发展,更有心理发展,是各种社会性学习的奠基性时期。同时,0~3岁婴幼儿发展任务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的教育和保育所占的比重应有所不同。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显而易见,教育的成分会越来越多。[35]因此,在儿童5~6个月后,特别是1岁后,家长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照料看护”,对高质量保、育服务的需要更为迫切,其需求呈现出“保教融合”的偏好特征。[36]在“托幼一体化”保教整合的模式下,婴幼儿的饮食、饮水、如厕、盥洗、睡眠、游戏等一日生活与活动均得到合理安排,其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之中,在生活和游戏中获得经验,从而促进生活自理、认知探索、社会互动、身体协调、语言表达等能力的全面发展。[37]
2. 满足0~6岁儿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0~3岁与3~6岁这两个时期,儿童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我们可以把“托”“幼”两个阶段视为一个整体,施以一体化的思考与规划。以年龄作为入园准入要求确有其历史性与实用性,但同时也将儿童个体的发展水平用阶段界限一刀切、均质化,造成0~3岁与3~6岁教育的分层,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38]“托幼一体化”体系则将学前教育由3~6岁向0~3岁拓展延伸,作为有机联系、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有利于促进“托”龄与“幼”龄的良好衔接,且益于儿童的整体发展。[39]
3. 明晰相关部门权责边界
我国尚无专门的托育服务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目前的托育行政管理工作分散于两个业务部门。教育部门主要围绕学前教育的相关内容开展行政规划和管理工作,卫生部门主要围绕免疫接种、疾病防控和妇幼卫生等内容开展业务指导与健康督导工作。由于多部门统筹协调与有效合作的工作机制缺失,故而在政策落实与执行上并未取得显著效果。[40]“托幼一体化”模式则具备统一且清晰的管理主体,能够在大局上对托育服务进行通盘考量,且厘清了各相关部门、机构的职责,从而保障托育服务政策的制定以及推行。[41]
4. 汇集软硬件资源优势
在幼儿园附设托班将会克服0~3岁与3~6岁早期教育设施重复添置、资源利用率低、设点布局难以统筹规划、保教人员无法融通且学术科研无法形成合力等弊病,最大限度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效益,[42]实现0~3岁与3~6岁教育之间资源共享。
(二)我国“托幼一体化”的实现进路
参照世界各国“托幼一体化”的实践进路并结合我国现行托育服务的问题所在,本文就推进我国0~6岁“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1. 立法建制促规范,明确职责抓落实
加快学前教育的立法进程,以法律形式确立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地位,对“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宏观层面(国家学前教育发展方向、理念等)、中观层面(儿童发展指标、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等)、微观层面(师幼比、从业人员等)的各项标准作出统一规范与要求,保障其在法律框架下行稳致远。
具体而言,一是建议将学前教育立法适用范围明确为0~6岁学龄前儿童,以“托幼一体化”为立法理念并将其贯彻于法条内容中,从总则到附则均贯穿托幼整合的精神,体现保教融合的原则。如深圳拟将《深圳经济特区学前教育条例》列入2021年度立法计划,探索延伸学前教育的年龄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幼儿中心)利用现有资源或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研究将不少于8托位/千人的标准纳入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并据此增加新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规模,用于设置适当比例的2岁至3岁幼儿托班。《深圳经济特区学前教育条例(草案)》在专项规划、公共服务配套、民办幼儿园扶持等条款中,都增加了关于幼儿园托班的规定,以更好落实国家政策,满足人民群众关于2至3岁幼儿托育的需求。
二是建议改革双轨制的学前教育治理格局,逐步将0~6岁学前教育职能划归单一部门主管。经合组织一直倡导在教育部门的統一主持下对全年龄段儿童进行闭环管理,将托育服务的主管部门由卫生/福利部门转移至教育部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43]从我国发展现状来看,短期内可以采取增强部门间协同的方式改进治理效能,长期来看则应当将学前教育职能逐渐划归教育部统筹,以解决现存的批管分离、责任交叉、管理留白、管理效能低下等一系列问题。[44]如2021年6月,深圳市以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评审认定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选取40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作为试点园,面向2~3岁幼儿开设托班。未来,教育部门主管的公共托育服务治理体系将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并全面铺开。
三是以立法形式保障政府对“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的财政性投入。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扶持力度,为学前教育设置专项进行独立核算,将托育服务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步均衡0~3岁与3~6岁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通过提高生均经费、减免租金、划拨用地、水电气优惠等补贴措施对开设托班的幼儿园予以扶持。
四是加强托幼一体园服务质量控制。制定幼儿园增设托班、新增托育机构的国家及地方准入标准,如2021年深圳市卫健委结合实际制定《深圳市托育机构设置指南》及《深圳市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强化对办托条件、从业人员资质、备案登记等环节的审核。加快研制0~6岁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囊括园舍建筑、设施设备、卫生保健、课程建设、人员配备、园所管理等维度,将0~3岁与3~6岁保教机构共同纳入考察评估范围。建立健全精细化监督管理体系,设立托幼一体园托育服务专职督导人员,定期赴实地排摸查访,进行安全防控、卫生保健等专项检查及巡查指导,形成对托幼园所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的常态监管网络,促进托育服务合法化、合规化发展。
2. 多元主体齐参与,凝聚合力扩供给
当前,我国“托幼一体化”托育服务供给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前期需发挥政府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满足庞大的婴幼儿入托需求。鼓励尚未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积极创设条件增设托班,鼓励有条件的民办幼儿园开设普惠性托班,进一步明确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按一定比例开设托班。多途径扩充普惠性托育资源,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机构为补充、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多元一体的托育服务供给格局。
其次,发挥场地保障、税费优惠、减免租金等政策杠杆作用,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应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强政策扶持,推动普惠托育机构、企业自办托育园建设;通过新建、租赁、合作等途径设立高品质的普惠性托育点,借鉴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丰富有效经验,提供全日制、半日制、计时制、临时制等灵活多样的服务模式,以满足家长多元化、多层次的托育服务需求。
再次,激发市场潜力,鼓励具有合法办学资质的晚托、暑托、寒托、亲子中心等市场化托育机构继续发展,并转制进入幼儿日托服务领域,转变为托幼一体机构;或考虑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扩大市场化供给的覆盖范围,以良性竞争盘活托育服务市场。
此外,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始于家庭,家庭是儿童照护的核心主体与关键场域,故而应始终将增强家庭的科学育儿能力作为落脚点。应通过为婴幼儿家庭开展宣传教育、新生儿访视、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新生儿疾病筛查、膳食营养、生长发育、预防接种、安全防护、疾病防控等公益性服务加强对家庭的支持与指导。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现有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背景下,隔代照料、父职照料也是弥合托育供需缺口的一剂良方。
最后,充分发挥社区服务效能,为家庭育儿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协助。应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大力推进全市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母婴室建设,在工作场所建设“爱心妈妈小屋”,为婴幼儿出行、哺乳等提供便利条件,营造友好的婴幼儿照护环境。整合社区综合资源,打造环境友好、设施完备、服务优质、可及便捷的“15分钟托育服务便民圈”,按需为适龄幼儿家庭提供嵌入式、菜单式、分龄式等形式多样的服务。
3. 严把从业入口关,多措并举强师资
针对当前我国托育从业人员数量相对短缺、队伍流动性大、专业性有待提升等痛点,应综合施策,加强托育服务人员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第一,严格限制托育从业人员职业准入门槛,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标准与行为规范,以“零容忍”“严查处”的态度对肆意践踏道德底线的虐童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研制从业人员资格审查办法与考核评价机制,做到全员持证上岗。如深圳市规定托班班级婴幼儿与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的配比不高于7 ∶ 1,托班教师应当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取得适用的教师资格证,并接受托育保教方面的相关培训;托班保育员应当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取得保育员上岗证,并接受托育保教方面的相关培训。
第二,统整0~6岁学前教育师资培育体系,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增设幼儿保育相关专业,并在扩招专项工作中将其作为重点环节予以推进。学前教育本科生培养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制定贯通0~3岁与3~6岁教育的专业培养方案,锻造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托育人才队伍。未来我国还可开展“1+X证书制度”(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多证培养试点工作,并借鉴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开发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深化复合型保教实用人才的培养模式及评价模式改革。
第三,畅通职前培养、入职教育与职后培训路径,形成可持续的专业发展机制。成立0~6岁学前教师发展联盟,凝聚院校、托育机构、幼儿园等多方合力,在实践教学、实习实训、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形成联动。此外,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培训机制,涵盖法律法规、安全防护、膳食营养、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基础内容和实务操作内容,重点突出职业道德培养。将托育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
第四,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健全薪酬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学前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为其安心从教提供有力经济保障。分阶段消除保育员和幼儿教师的不平等待遇,在职业地位上予以同等对待。完善职业晋升通道,畅通职称、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渠道,并强化社会支持,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提升保教师资的职业荣誉感及职业吸引力。
4. 统一标准优课程,保教融合重衔接
国际经验表明,基于保教融合的理念,整合设计并实施0~6岁学前教育课程标准,是推进“托幼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刚性保证。鉴于此,我国应加快研制科学合理、统整保教的0~6岁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一方面,使课程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实现教育内容的循序渐进与教育手段的前后衔接,最大限度满足儿童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为家长科学育儿和保教人员科学施教提供理论参考与方向指引。值得关注的是,提高特殊儿童受教育普及程度,是“十四五”期间特殊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也是保障特殊儿童合法教育权益的必然要求。因此,0~6岁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也需对特殊儿童群体予以关注,注重保教与康复相结合。此外,制定课程标准的同时需配套研发系统性的课程评价体系,具体包括课程内容设计评价、课程实施评价、课程效果评价机制等,将儿童、保教人员、家长、社区納入评价主体,并综合运用正式评价与非正式评价、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等多元评价模式,为课程的落实保驾护航。
注释:
①美国为联邦制政体,不同州的托育服务治理结构存在差异,本文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例。
参考文献:
[1]洪秀敏,陶鑫萌.改革开放40年我国0~3岁早期教育服务的政策与实践[J].学前教育研究,2019(02):3-11.
[2]赵建国,王瑞娟.我国幼托服务供给模式选择及实现路径[J].社会保障研究,2018(03):84-91.
[3]但菲,索长清.“保教一体化”国际趋势与我国学前师资培育改革[J].教育研究,2017(08):96-102.
[4]OECD. Starting Str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B/OL].(2006-09-14)[2021-07-20].https://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starting⁃strong_25216031.
[5]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EB/OL].(2020-09-08)[2021-07-20].https://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education⁃at⁃a⁃glance⁃2020_69096873⁃en.
[6]Swedish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politics of pre⁃schol⁃intentions and decisions underlying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the Swedish pre⁃school[EB/OL].(2015-06-01)[2021-11-10].http://sweden.se.
[7]NEUMAN M J. Governance of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politics and policy in france and swede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2007:64-111.
[8]LEE S, DUVANDER A Z, ZARIT S H.How can family policies reconcile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comparison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sweden[J].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16,22(03):269-288.
[9]OECD.OECD Family Database[EB/OL].(2021-10-16)[2021-12-13].https://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
[10]GORDON C S. Integration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in canada:a comparison with sweden, new zealand, england and wales[J].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Dordrecht,2013(45):178.
[11]OECD: Quality matter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sweden[M]. Paris: OECD Publishing,2013:47.
[12]杨雪燕,高琛卓,井文.典型福利类型下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人口与经济,2019(02):1-16.
[13]GARVIS S, LUNNEBLAD J.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in sweden [J]. Munich: ICEC Working Paper Series,2018(13):27-28.
[14]European Commis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B/OL].(2008-04-03)[2021-11-10].https://eacea.ec.
[15]江夏.儿童福利视角下瑞典学前教育公共支出政策内容、特征及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18(03):3-12.
[16]CEIC. Statistics Sweden[EB/OL].(2015-01-01)[2021-12-13].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sweden/vital⁃statistics.
[17]ANDERSEN G, BILLARI F.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5,41(01):1-31.
[18]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tistics[EB/OL].(2019-12-31)[2021-05-13]. https://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finances.
[19]CARMEN 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 current issues and policy developments[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1990,64(01):61-70.
[20]徐鹏,胡恒波.新西兰学前教育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与改革趋势[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8(01):73-79.
[21]Ministry of Education. Te Whāriki: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EB/OL].(2021-03-30)[2021-08-03].https://www.education.govt.nz/early⁃childhood/teaching⁃and⁃learning/te⁃whariki/.
[22]Ministry of Education. New Zealand.Early Childhood Teac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2017[EB/OL].(2016-07-01)[2021-11-10].https://www.teachnz.govt.nz/assets/Uploads/Thinking⁃of⁃Teaching/Qualifications/2017⁃ECE⁃Qualifications⁃Guide.pdf.
[23]OEC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ate Country Note—New Zealand[EB/OL].(2016-10-28)[2021-11-10].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ECECDCN⁃NewZealand.pdf.
[24]HELEN M. Towards the Right of New Zealand Children for Fre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Policy,2008(02):78-84.
[25]Ministry of Education. Overview of attendance at licensed ECE services in 2018[EB/OL].(2018-10-16)[2021-11-10].https://www.educationcounts.govt.nz/_data/assets/pdf_file/0009/192942/ECE⁃Summary⁃page⁃1 Attendance⁃in⁃2018.pdf.
[26]KAGAN S L, COHEN N E. Reinventing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a vision for a quality system[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6:5.
[27][33]范昕,李敏谊,叶品.托幼服务治理模式国际比较及中国路径选择[J].比较教育研究,2021(01):104-112.
[28]KHERROUBI M, PLAISANCE E. Making a modernist pedagogy: changs in elementary and pre⁃elementary school[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2000,15(01):83-91.
[29]HOTZ V J, XIAO M.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on the supply and quality of care in child care marke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05):1775-1805.
[30]OECD. Starting str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M]. Paris: OECD Publishing,2001:125-134.
[31][39]OECD. Starting strong II: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6:45-56.
[32]OECD. Starting Strong: Transitions fro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to Primary Education [EB/OL].(2017-06-21)[2021-08-03].https://www.oecd.org/education/starting?strong⁃v⁃9789264276253-en.htm.
[34]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EB/OL].(2013-09-09)[2021-08-04].https://www.oecd.org/education/Sweden_EAG2013%20Country%20Note.pdf.
[35]庞丽娟,王红蕾,冀东莹,等.有效构建我国0~3岁婴幼儿教保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5-11.
[36]高琛卓,杨雪燕,井文.城市父母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20,44(01):85-98.
[37]赵琼.托幼一体化是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01):122-123.
[38]虞永平.全面理解托幼一体化教育体系[J].早期教育(教师版),2008(06):4-5.
[40]刘中一.我国托育服务管理职责体系建设:兼论托育服务行政主管部门的确立[J].行政管理改革,2019(02):8-15.
[41]洪秀敏.婴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66-96.
[42]汪黎明,陆建国.郊区“托幼一体化”教育的实践与认识[J].上海教育科研,2003(07):44-46.
[43]OECD. Starting strong III: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M]. Paris: OECD Publishing,2012:217-219.
[44]樊晓娇.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的发展态势:基于经合组织国家经验的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21(05):15-27.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Kindergarten with Nursery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Enlightenments for China
Guoyan Liu,1 Wenqi Zhan,1 Sisi Ma,1 Yuting Fan2
(1Faculty of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on of kindergarten with nursery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arly education and is also a good way to solve the predicament of “children without care” in China.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kindergarten with nursery education” i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Sweden and New Zealand from their four⁃dimensional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integratio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eacher integration,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alize such integr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kindergarten with nursery education”, early education, childcare service, preschool education
稿件编号:202109130003;作者第一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11-28;作者第二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12-18
基金项目: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2020 年建设专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现状与专业化、规范化研究”(编号:2020WQYB061)、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课题(教育综合改革专项)“广东省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批准号:2021JKZG026)
通讯作者:刘国艳,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E-mail:szdxlg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