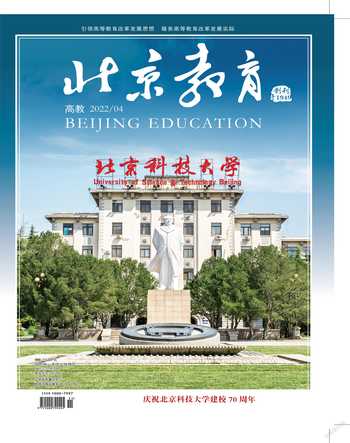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现实困境、 逻辑遵循与实现路径
2022-04-27刘宝存商润泽
刘宝存 商润泽
摘 要:高校科研评价是高校学术管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构成,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落實直接相关。然而,我国现行高校科研评价却面对着科研评价标准制定忽视科类差异、科研评价主体与方法多元性缺位、盲目追求绩效产出致使评价流于形式以及科研绩效奖励制度致使评价价值取向异化的现实困境,高校科研评价改革势在必行。我国新时代的高校科研评价应基于“提升科研质量水平”这一逻辑基点,依循“价值—目标—实践”的逻辑理路,以“贡献”引领价值,以“内涵”重构目标,以“多元”指导实践,进而构建起以“质量”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以“效力”为旨归的灵活式评价机制、依托于学术共同体的多元主体参与评价机制以及多向度评价方法组合应用的精准评价机制。
关键词:高校科研评价;分类评价;评价主体;评价方法;科研贡献度
高校科研评价,即高校基于国家和本校战略与目标,按既定原则、条件及程序、方法,对教师科研行为、过程和结果的表现所做出的价值判断,[1]是高校学术管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构成。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应“改革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制度”,教育部继而于2016年9月发布《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从评价的导向、机制、办法及周期四方面对高校科研评价做出指导。2020年10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发布,其中将“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作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方面。虽然相关文件的出台表明国家十分重视高校科研评价工作,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中的种种沉疴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与改观,但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仍处于现实的困境中,严重阻碍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落实。破解制约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重重现实积弊,则须厘清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逻辑理路,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政策引领实践的效力,为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改革的深化推进探寻可行之策。
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现实困境
教育评价改革是我国新时代教育深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有教育评价体系下,高校科研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存在着科研评价标准制定忽视科类差异、科研评价主体与方法多元性缺位、盲目追求绩效产出致使评价流于形式以及科研绩效奖励制度致使评价价值取向异化等现实困境,极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科研评价的成效。
1.科研评价标准制定忽视科类差异
高校科研,即在高等院校中进行的在“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旨在探究真理的普遍理智创造性活动”[2]。由于不同学科门类的高校科研活动在研究对象、方法、手段、过程、成果及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质,因此评价标准与学科门类特质相契合应是高校科研评价的基本逻辑遵循。尽管教育部曾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应“针对不同类型、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并进一步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再次对“落实分类评价”做出强调,但反观现实实践,我国部分高校在制定科研评价标准时对不同学科门类仍是一概而论,忽视了由于学科门类不同而导致的科研性质、内容及成果形式的差异性,科研评价标准整齐划一,并未充分体现学科门类特质,高校科研分科类评价尚待进一步的深化与落实。
2.科研评价主体与方法多元性缺位
目前,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的主体通常是由行政管理人员与同行专家构成,受人际因素影响,一方面行政管理人员与其所赏识的小部分科研人员之间相互理解并产生“默契”,从而形成一系列“潜规则”已是中国学术界心照不宣的事实[3]。另一方面,同行专家在科研评价过程中亦会受到所谓“熟人圈子”的规制与影响,[4]评价结果难免有失偏颇,以致我国高校科研评价面临公信力缺失的现实困境,受到多方质疑。而这一现实困境的出现,其实归根结底在于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主体较为单一。虽然同行评议的实施打破了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以行政评议结果为绝对依凭的单一性局面,但不可否认同行专家的选取极易受到行政因素的挟制,以致现阶段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仍然是以行政管理人员为主导,缺乏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制衡。
与评价主体相同,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在方法方面亦面临多元性缺位的现实问题。我国高校现行科研评价方法通常是由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论著、专利、奖项等量化指标对教师的科研绩效进行评定,属于定量评价的范畴。但正如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所言,现今的大学教师“从事并提供多科目的教学与研究,从非功利学科、纯学术学科到接近于职业教育的学科”,致使高校成为“一个由学者、专业取向的教师与着眼于实用技术的人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5]高校科研类别亦由此日益多元,概而言之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类,而我国现行的以数量来衡量教师科研水平的单一化评价标准则未能全面反映出不同类别高校教师科研活动发展规律的多样性、成果贡献以及社会服务的复杂性、差异性。[6]因此,我国高校将定量评价作为科研评价的唯一方法用以衡量多向度的研究势必会阻碍高校科研的发展,亦有悖于其“求真”的本质。
3.盲目追求绩效产出致使评价流于形式
科研绩效评价是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制度的核心内容,虽然我国政府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中曾多次就“改进科研绩效评价”做出强调,我国高校亦纷纷做出响应,针对科研绩效评价进行了诸多创新性的探索与改革,但事实证明,对于改进后的科研绩效评价,诸多高校教师依然表示无所适从。[7]我国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现实挑战,主要表现为科研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提升教师科研水平是高校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旨归,但反观实际,我国高校科研绩效评价在行政制度逻辑的影响下却呈现出显著的绩效工具化倾向,“数字游戏”成为高校科研评价的隐喻,而隐藏于数字背后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却鲜有问津。[8]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中以“科研数量”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僭越和以“科研质量”为导向的价值理性成为主导高校科研发展的指挥棒。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通过科研绩效评价迫使教师加速学术生产,部分高校教师为追求绩效达标,在研究过程中盲目追求“短、平、快”,对研究本身的社会需求与学术价值置若罔顾,高校科研绩效评价的精神内核为行政管理人员对其促进绩效产出这一浅层功能的盲目追求所遮蔽,难以彰显其“提升科研质量水平”的真正价值,流于形式。
4.科研绩效奖励制度致使评价价值取向异化
近年来,将科研成果“貨币化”,即通过明文规定将科研产出与经济收益直接挂钩的科研绩效奖励制度已然成为我国高校中的普遍现象。作为高校科研评价的重要环节,科研奖励制度有助于高校充分调动教师科研积极性与创新活力,从而提升高校的整体科研水平与影响力,但同时亦不可否认其经济利益驱动的价值导向是对高校科研评价价值取向的异化,极易导致学术功利主义的滋生,生产出大量并无多少学术价值的“复现型”的学术泡沫。据《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学者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共计发表论文59,867篇,占国际份额的31.4%,排名国际第二,排名于首位的美国学者国际占比仅略高于我国,为32.9%,但在“高被引论文数量”方面,我国学者在国际占比为23.0%,而美国学者则高达46.4%,从侧面管窥该数据,我国学术泡沫之泛滥亦从中可见一斑。
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逻辑遵循
“质量”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规定性与永恒主题,[9]“提升科研质量水平”应是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的逻辑基点。因此,欲要在新时代做好高校科研评价,高校应基于“提升科研质量水平”这一逻辑基点,依循“价值—目标—实践”的逻辑理路,明确科研评价的价值意涵,厘清科研评价的目标理性,构建科研评价的路径样态,为本校的科研评价机制架构起以“贡献”引领价值、以“内涵”重构目标、以“多元”指导实践的逻辑框架遵循。
1.价值逻辑:以“贡献”引领价值遵循
“大学的使命”是高等教育领域亘古不变的话题,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使命应是对高深学问的探索与发展,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指出“大学将科学视作一项未完全解决的难题,因此其亦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中”[10],蔡元培亦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1],另有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做出补充,认为大学亦应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如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便指出大学在“对发展真理负有无限责任”的同时“仍有必要充满现实感”[12],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亦提出“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13],克尔(Clark Kerr)则认为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有若干个目标,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为多种市场服务并关心大众”[14]。
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科学研究无疑是大学用以履行其自身使命的基本手段之一。因此,高校科学研究的开展须契合于大学的使命,高校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应时刻以增进人类文化知识与社会知识,并利用知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目的,为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切实贡献。由此,作为高校科研发展的指挥棒,高校科研评价须将“贡献”视为其价值遵循,摒弃其现阶段所奉行的计量导向的绩效逻辑,将研究的知识生产创新价值、社会价值作为其评价标尺,重构自身价值逻辑,以“贡献”引领高校教师的科研价值取向,明确高校科研的正确方向,促推高校科研规范有序发展。
2.目标逻辑:以“内涵”重构目标导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科学研究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因此推动高校科研基于质量与效率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势必有助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现,[15]这就要求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应以“内涵”重构其目标导向,将科研内涵评价作为评价的主体内容,由以“科研产出数量”为主导目标向以“科研产出质量”为主导目标转变,从而有效纠偏我国现行高校评价的过度量化倾向,实现高校科研评价“提升科研质量水平”本心的复归。
3.实践逻辑:以“多元”指导实践路径
“多样性”是现阶段高校科研的基本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研类型的多样性。学科门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群,因此随着高校学科门类的日益丰富,高校科研亦衍生出诸多不同的类型,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可以将其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三类,不同学科有其不同的研究类型适应域,如工学类学科的研究主要指向实践领域,需要考虑某一特定的实际目标,与应用研究的主旨相契合,而理学类诸如数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世界基本规律与更高深学问的探索,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二是科研相关主体的多样性。随着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已然不再是中世纪的“象牙塔”,现代的大学“需要与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密切接触,且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社会环境”[16],高校科研亦不再仅仅是“志同道合之人对于真理之事业的追求”,而是与社会不同群体产生交互,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社会公众等群体均被纳入其中,高校科研相关主体日益多元。三是科研成果呈现形式的多样性。随着科学发展进入开放科学时代,大学科研成果的呈现形式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术出版物,“卓越”与“非学术影响”逐步成为高校科研评价的新常态与转型发展的新向度。[17]
综而言之,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现实实践的单一化样态显然脱节于现阶段高校科研发展的多样性路向,高校科研评价实践亟待多向度、多视角、多方面的实践路径规划。由此,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的实施应以“多元”为逻辑前提与指导遵循,在科研评价方法方面应用多向度方法进行评价,在科研评价主体方面引入多视角参与评价,在科研评价标准方面参考多维度予以评价。
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要实现上述价值逻辑和目标,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建立以下机制。
1.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
“提升科研质量水平”是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的逻辑基点,因此我国高校科研评价改革首先应构建起以“质量”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一方面,我国高校应将“质量”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目标,明确科研评价应是一种复杂的价值研判活动,而非机械的事实统计活动,在制定评价标准时应以“是否合乎构成真理的技术性、学术性要求以及其所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性”[18]为框架遵循,着重关注科学研究的创新性与内涵;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则应意识到分类评价的必要性,其实对于建立科研分类评价,我国政府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已明确作出“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的指示,因此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应基于对不同学科与岗位教师科研特点的梳理,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多维度评价标准,从而充分体现出对于科学研究多样性的基本关切。
2.构建以“效力”为旨归的灵活式评价机制
以“贡献”为价值引领,我国高校科研评价首先应构建起以“效力”为旨归的灵活式评价机制。所谓“效力”,即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有利的作用,将“效力”作为科研评价的旨归,可以促进高校科研实际贡献度的切实提升。该理念亦为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所秉持,如英国便在其高校科研评估项目“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中特别设有科研影响力(Impact)模块,并将科研影响力界定为“科研成果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环境、生活质量等各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变化或收益”[19],美国亦在其“美国科学技术再投资—测度研究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STAR METRICS)项目中将科学研究的影响力(Effect)作为其测度的重点,旨在评估科学研究在经济增长、知识生成、社会发展以及国民健康保障方面的价值功用[20]。
在加强“效力”评估的同时,我国高校亦应明确不同类型研究成果呈现形式的差异性,杜绝以往单纯以论文发表、课题立项等科研成果数量为指标进行评定的刻板式评价,提升科研评价的灵活度,可以在合理量化评价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学科门类教师设置评估单元,进而制定与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特质相契合的评估标准,教师通过提供代表性科研案例参与评价,评价则主要采取“评议+调研”的方式,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从而实现对高校教师科研的灵活科学评价。
3.构建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多元主体参与评价机制
多元化评价主体架构的建立对于我国现阶段由于行政逻辑主导而导致的高校科研评价绩效管理与过度量化倾向的纠偏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虽然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但在实践层面却缺乏具体落实,因此我国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应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式的评价机制,引入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政府相关部门、科研受益群体、第三方评价机构、同行专家等多视角参与评价,充分发挥不同评价主体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优势互补,相互制衡,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与公信力。此外,为保证评价主体选取的科学性与完善度,高校相关部门应在评价后面向部分被评价教师代表公布评价流程与参与主体并征询其意见,教师若对评价有所质疑须陈述与之相应的有说服力的理由,通过相关部门与教师代表的反复论证,促进高校科研评价主体架构的日臻科学与合理。
与此同时,我们亦应明确高校科研评价是一项专业性较强、具有较高门槛的工作,评价者如若缺乏一定的学术资质,势必难以胜任评价工作。而作为特定领域交流的学术共同体组织,我国各学科专业学会汇聚了高校教师、科研机构人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政府部门人员以及相关行业人员等多方面的专业性人员,可以为高校科研评价主体的选取提供有效资源。因此,我国高校应积极与各学科专业学会合作,以专业学会这一学术共同体组织为主要依托完成多元主体参与式科研评价机制的构建。
4.构建多向度评价方法组合应用的精准评价机制
评价方法是高校科研评价赖以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评价方法的适切性之于高校科研评价质量而言至关重要。国际现行的科研评价方法主要有定量评价方法、定性评价方法以及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三类,而无论何种评价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局限性,如“文献计量法”作为一种定量评价方法,虽然其确实为高校科研评价提供了一套更为直观、科学的客观标准,但其极易导致科研流于形式,学术功利主义滋生的弊端长期以来亦备受质疑。
因此,对于科研评价方法的应用,高校首先应对不同评价方法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定位形成准确的判断,明确各种评价方法的适应域,进而根据所评价教师科研的具体特质,选取与之相匹配的多向度评价方法加以组合应用,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从而实现对高校科研的精准评价。例如:在高校教师聘期考核中,其目标之一是评估教师是否胜任自身科研工作,如若单向度地应用同行评议法,基于同行专家所给出的定性意见做出评价难免过于主观,缺乏客观性,而如若仅依凭论文发表篇数、课题立项数等计量学指标做出评定又难以对教师科研内涵与贡献度做出准确判断,但如若将二者相结合,即在整合同行专家评议意见的基础上,以h指数、类h指数等量化数据作为参照,二者相互印证,从而形成综合性的评价意见,这种综合性的评价结果毋庸置疑会帮助高校对所评价教师能否胜任其科研工作做出更为精准详实的研判。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优先关注课题“当代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编号:BEBA1703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顾海波,赵越.高校科研评价规则变革问题研究[J].科研管理,2017,38(8):126-133.
[2]谢安邦. 比较高等教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263.
[3]SHI Y G, RAO Y.China’s Research Culture[J]. Science, 2010, 329(5996): 1128.
[4]刘梦星,张红霞.高校科研评价的问题、走向与改革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1):117-124.
[5]劉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307, 322.
[6]靳玉乐,张良.论高校教师的分类评价[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7):8-14.
[7]方宝.基于访谈视角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9,42(2):69-75.
[8]邹太龙,张学敏.论我国科研评价体制中的“二律背反”—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引发争议的再思考[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4):76-82.
[9]朱军文,刘念才.高校科研评价定量方法与质量导向的偏离及治理[J].教育研究,2014,35(8):52-59.
[10]彼得·贝格拉.威廉·冯·洪堡传[M].袁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4:79.
[11]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917~1919)[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5.
[12]刘宝存.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教育理念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03(8):60-64.
[13]FLEXNER A.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5-6.
[14]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M]. 陈学飞,等,译.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96.
[15]刘兴凯,梁珣.英国高校科研评估的制度改革、效应及其借鉴意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6(3):82-88.
[16]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 徐小洲,陈军,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98-99.
[17]武学超,罗志敏.开放科学时代大学科研范式转型[J].高教探索,2019(4):5-11.
[18]GASTON J. 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Sci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0, 35(4):718-732.
[19]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Decisions on assessing research impact[EB/OL].(2011-03-11)[2022-02-22].extension://bfdogplmndidlpjfhoijckpakkdjkkil/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dera.ioe.ac.uk%2F%2F2004%2F1%2F01_11.pdf.
[20]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TAR METRIC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s Reinvestment-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cience[EB/OL].[2022-04-02].extension://bfdogplmndidlpjfhoijckpakkdjkkil/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sites.nationalacademies.org%2Fcs%2Fgroups%2Fpgasite%2Fdocuments%2Fwebpage%2Fpga_057083.pdf.
(作者單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