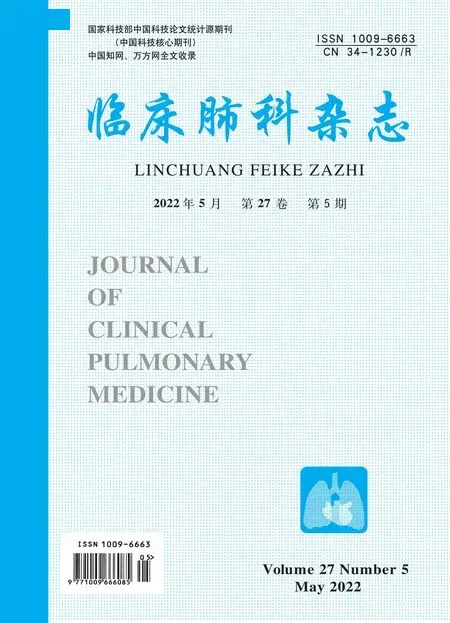吸气峰值流量在COPD中的研究进展
2022-04-26祁子歆柴燕玲
祁子歆 柴燕玲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慢阻肺)是常见的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肺部疾病。最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8.6%,4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13.7%,由此来估计全国患病人数接近1亿[1]。慢阻肺已成为我国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2013年我国慢阻肺死亡人数约达91万[2],而至2017年,慢阻肺死亡人数达3千万人(42.2/10万人),在非传染病性疾病中排第七位[3]。
慢阻肺以持续气流受限、气道阻塞为特征,患者的呼气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大多数学者致力于对慢阻肺呼气能力的研究,并对慢阻肺诊断的标准达成共识即FEV1/FVC小于0.7。然而关于吸气能力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但在临床上我们发现慢阻肺患者由于长期高肺容量、缺氧、感染、营养不良等因素,常伴有吸气肌的功能障碍,尤其吸气肌疲劳,因此患者吸气能力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2020慢阻肺全球创议(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GOLD)中推荐对慢阻肺患者进行抗炎、平喘治疗,常使用的药物包括β2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或糖皮质激素等,为更快、更低剂量、更少副作用的达到治疗效果,对以上药物均推荐吸入途径给药[4]。但因患者吸气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以至于在进行吸入疗法时出现药物吸入不充分,进而不能最大程度的改善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因此了解不同吸入装置的特征并个体化的为患者选择理想的吸入装置,对于临床医师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本文主要就吸气峰值流量(peak inspiratory flow,PIF)在慢阻肺中的应用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吸气峰值流量的测定
众所周知,慢阻肺特征性的病理生理改变是持续的气流受限导致的肺通气功能障碍,但随着对慢阻肺认识的不断加深,慢阻肺患者的吸气能力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检测慢阻肺患者吸气能力的指标最常见的是吸气峰值流量,即在用力吸气时产生的最大吸气流量,亦称最高吸气流速、最大吸气流量。测量装置最先起源于1960年代的Wright峰值流量计,如今在标准肺功能测试或采用肺活量计即可测出,在临床上非常普遍、经济、迅速。
此外,关于PIF的测定,一些文献推荐了手持式设备即In-Check DIAL®和后期经过改进的新型In-Check DIAL G16®,测量范围为15~120L/min(±10L/min)[5]。它们带有可调节的刻度盘,通过旋转上面的转盘来调节流量仪的孔径大小,从而改变吸气阻力。因此可用于模拟不同吸入装置的内部阻力来检测患者的自身吸气流量,并能评估该患者能否带动装置,进而将药物颗粒最大化沉积在肺部[5]。但是,由于它的可及性及价格的限制未能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吸气峰值流量对装置的选择
目前,吸入是许多用于治疗慢阻肺的药物的首选给药途径,而吸入装置是有效输送吸入剂的主要工具[6]。如今我们常用的吸入装置有干粉吸入装置(DPI)、压力定量气雾吸入装置(pMDI)和软雾吸入装置(SMI)。每一种吸入装置由于形成气溶胶的方式不同,对病人的适用要求有所不同,它们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由于吸入药物在肺部的沉积受到吸入药物输送系统和剂量混合系统的严重影响[7],而确保药物输送到相应靶器官与患者的吸气流量息息相关。因此,在为患者选择吸入装置前需要深入了解各种装置的特点及评估患者的吸气能力。
pMDI是常见的一种输送装置,激发速率为2.0~8.4m/s,喷雾持续时间仅有0.15~0.36s[8]。患者必须在加压罐体的同时吸气,这要求患者达到高度手口协调性。而慢阻肺的患者大都为老年人,难以做到手口高度配合,无法连续操作激发和吸气的步骤。而最近新起的SMI,如常用的能倍乐®,其操作原理是通过旋转底座产生弹簧机械动力,将15ul的内置药物溶液推送至单向阀喷嘴系统,产生两股特殊交叉角度喷射的液体,从而形成流速缓慢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软雾[9]。对于高龄患者来说,有更多的时间来反应完成吸入。且能倍乐®的吸气流速仅10~30L/min,吸气努力程度远低于DPI,轻松吸入[10]。因此,对于吸气流量不足但手口协调好的患者推荐次序为SMI、pMDI。
目前,全球公认DPI是较为理想的吸入装置,但相对于pMDI和SMI,DPI内部具有不同的阻力。DPI的使用通常在初始需要进行快速吸入并达到最佳吸气流速维持2~3秒[11],以产生湍流来分解药物颗粒,从而将细颗粒(通常直径小于5um)沉积在下呼吸道中[12]。因此,产生最佳的吸气峰值流量的能力是成功使用DPI的主要要求。目前临床上最常使用的DPI包括准纳器®、都保®、比斯海乐®和易纳器®等,由于装置内部阻力不同,患者需达到的吸气流量也各有不同,以下是不同DPI所需的最小吸气流速及最佳吸气流速表(表1)[13]。但要评估患者最佳使用设备能力的关键呼吸参数是通过设备检测的吸气峰值流量(PIFdev)[14]。由于检测方法复杂,不易在临床中开展,且数据不易获取,一些研究者用肺活量计或常规肺功能检测PIF后,将其与PIFdev相联系。Seheult等[15]发现PIF与PIFdev存在一定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将受试者分为健康组、哮喘组、COPD组及神经肌肉疾病亚组,发现当PIF达196L/min时,84%的准纳器®测定的吸气峰值流量测定值,能对应准纳器®自身所需的最佳吸气峰值流量,即60L/min,而需达到准纳器®自身所需的最小吸气峰值流量30L/min时,对应的PIF为115L/min。Farkas等[14]也分析了都保®、比斯海乐®和Genuair®的吸气峰值流量,在其研究中,若需达到都保®本身的最小PIF和最佳PIF,在肺活量测定法中相对应的PIF分别为135L/min和295L/min。同样,如果患者的吸气峰值流量分别超过143L/min和183L/min,则可以超过比斯海乐®(50L/min)和Genuairde®(40L/min)的PIFdev。以上研究均为临床医师个体化的选择吸入装置提供了依据,即只需对慢阻肺患者常规行肺功能检测PIF,由此来对比患者的PIF是否达到装置所需的最小和最佳吸气流速。

表1 国内现有DPI所需吸气流速
此外,在临床上我们意识到,许多慢阻肺患者难以生成DPI所需的最佳吸气峰值流速以实现有效的药物输送并因此获得临床收益。Kawamatawon等[16]对139名慢阻肺患者检测吸气流量,结果显示21名(19.3%)使用都保®的患者的最低吸气流量低于60L/min,10名(9.3%)使用准纳器®的患者的最低吸气流量不能达到其适宜的吸气流量,从而使得慢阻肺患者的肺功能、临床症状及急性加重次数无法得到改善。因此,为使药物通过吸入装置在肺部达到高效沉积,吸气流量的评估成为了选择合适吸入装置的关键步骤。
吸气峰值流量的影响因素
一、年龄和性别
相关文献有报道,慢阻肺患者中,年龄和女性是PIF降低的重要临床预测指标[17-19]。在纳入170名研究对象的试验中,低吸气峰值流量的队列与正常吸气峰值流量的队列相比,患者年龄较大(66.2±10.04)岁vs(62.1±9.41)岁(P=0.006),女性的可能性更高(61.2%vs42.4%,P=0.014)[17]。Malmberg等[18]也对年龄和性别与吸气峰值流量做了相关性的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与PIF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0.004),且女性的PIF明显低于男性(P=0.004)。此外Alexander等[20]也证实了性别和身高是吸气峰值流量不佳的独立因素,然而当将两者加到同一个模型中时,效果不显著。解释以上原因,可能因为年龄、性别及体重会引起呼吸肌疲劳和/或存在呼气末正压有关,这使得患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吸气流量。因此针对女性患者,尤其是身材矮小、营养不良且高龄的慢阻肺女性患者,为其选择吸入在装置时,吸气流量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二、肺功能参数
大多数文献支持慢阻肺患者中PIF与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缺乏一定的联系[17-19, 21]。这可能是由于在吸气过程中,胸膜压力低于大气压,发生气流受限的可能性较低。这提示我们在选择DPI装置时FEV1并没有预测价值,无法根据FEV1的大小来预测患者的吸气流量大小。但Prime等[22]和Chen等[23]表示PIF与FEV1在统计学上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r=0.73,P<0.005),尤其是极重度的慢阻肺患者中两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在慢阻肺的极重度期,患者的气道严重阻塞,导致其吸气功能受到了影响,表明了慢阻肺的吸气气流一直保持到疾病的晚期。当然,PIF在肺功能的其他参数上也有着相关联系。Alexander等[20]证实了PIF与吸气量及残气量与肺总量比值(RV/TLC)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且PIF与吸气量之间的相关性(r=0.40,P<0.0001)比PIF与RV/TLC之间的相关性(r=-0.19,P<0.002)更强。深吸气量(IC)的降低是肺恶性膨胀的一个标志,这将会影响呼吸肌肉力量的作用,从而降低吸气峰值流量[24]。对于吸气峰值流量和呼气峰值流量(PEF)的联系,也有文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22, 25-27]。PEF不仅关系着气道的通畅性,也关系着呼气肌肉的功能是否良好。同样的PIF检测不仅需要良好的气道通畅性支持也需要吸气肌肉的配合,患者才能最大程度的从残气位快速吸气至肺总量位。
吸气峰值流量的相关因素
一、临床症状
慢阻肺患者由于气流阻塞,导致气道陷闭引起肺过度充气,久而久之出现呼吸困难、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进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无论在疾病的稳定期还是急性加重期,呼吸困难一直是慢阻肺疾病严重程度的指标及治疗的主要目标。研究发现CAT评分对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的病情严重程度、健康状况起到了很好的评估作用[28]。而mMRC也是评估呼吸困难的主要工具,它的有用性在GOLD中得到了高度强调,以上两种方法因其简单、方便,在临床得到医生的广泛使用。因此,有学者也致力于吸气流量与呼吸困难这一症状关系的研究。Harb等[26]证实了与最佳吸气峰值流量队列相比,低吸气峰值流量队列显示出统计学上更高的CAT分数(20.46±7.93vs15.06±7.77,P<0.001),但是mMRC在两个队列间无统计学意义。对于呼吸困难、评分低而无法行肺功能检测的患者,可推测其吸气峰值流量因肺部过度充气受到影响,在选择药物时应考虑,如比斯海乐®内部阻力较小的吸入装置。正如文献所述,不论年纪、性别、COPD严重程度,相比其它吸入装置,使用比斯海乐®只需通过最小的吸气努力即能达到最佳的PIF值[29]。
而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情变化与PIF之间的联系还未得到确切肯定。一项研究纳入了50名伴或不伴急性加重的哮喘及慢阻肺患者,他们发现这些纳入者中有50%的急性加重患者,不能达到都保装置的适宜吸入流量(定义为PIF<60L/min),而对于不伴急性加重的纳入者来说,只有5%没有达到(P<0.004)[30]。而在另一项纳入123名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的研究中,未能达到适宜的PIF的患者占有52%,但这项研究中的PIF中位数并无差异[21]。目前两者的关系有待考究,还需更多的数据来证实PIF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二、住院率及合并症
Loh等[21]首先提出PIF与住院率之间的关系,并证实了低PIF(<60L/min)的患者有着更高的住院率及更短的住院间隔天数。该研究一共纳入123名慢阻肺患者,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因慢阻肺入院(65.5天vs 101天,P=0.009)或全因入院(63.5天vs144天,P=0.002)的患者,相比适宜PIF组,低PIF组有着更高的小于90天的慢阻肺入院率(28.1% vs13.6%),且更短的住院间隔天数。究其原因,考虑低PIF的慢阻肺病人吸气能力低下,患者在行吸入治疗时,无法将药物传输至肺部,导致肺部药物颗粒沉积率低,降低药效,并将激素等药物残留至咽喉部或口腔,增加真菌感染的几率。
也有研究结果表明,肺炎和缺血性心脏病与PIF有关。Sharma等[17]研究纳入了170例患者,他们发现在低吸气峰值流量的患者,肺炎是更常见的合并症(38.8%vs22.4%,P=0.020),且低PIF队列人群诊断为肺炎的患者更多(10.6%vs2.4%,P=0.029),有着肺炎病史增加的趋势(28.2%vs16.5%,P=0.066)。这警示临床医师对于低PIF的慢阻肺患者,及时的预防性抗感染治疗能够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减少肺炎发生的风险。同样的,缺血性心脏病在低PIF中也更普遍(14.1%vs3.5%,P=0.015)。但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支气管扩张症、结核、房颤等疾病,两组队列之间并无统计学意义。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吸气峰值流量与慢阻肺息息相关,它不仅为慢阻肺患者选择合适的吸入装置提供价值,也为慢阻肺疾病的进展及预后提供重要信息,临床医师应在关注患者气道阻塞程度的同时也要评估患者的吸气流量。有学者建议,将模拟特定干粉吸入器阻力测量的吸气峰值流量作为慢阻肺疾病中“新兴生物标志物”[31],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吸气流量在慢阻肺疾病中的诊治地位。并且研究表明吸气峰值流量与性别、年龄、肺功能参数及疾病发生发展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为慢阻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但基于目前相关文献报道不多及样本容量小,还需更多的研究来证实和探讨吸气峰值流量在慢阻肺及其他疾病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