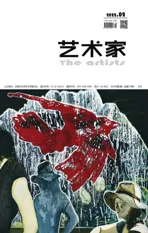以张式《画谭》论王蒙《花溪渔隐图》
2022-04-24黄艺璇
□黄艺璇
(黄艺璇/福建师范大学)
王蒙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而张式作为清朝善于绘画的文人,深受前朝先辈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对清代文人张式的画论《画谭》中山水画创作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以其中的理论来分析王蒙的山水画作品《花溪渔隐图》,以探索山水画创作中的思想形态与认知范式。
一、张式《画谭》中的山水画论
张式为清代著名文人画家,字报翁,一作报生,号荔门,夫椒山人,今江苏无锡人,长期隐居于江阴。其擅长诗古文辞,书法方面师法褚遂良,山水画则师法元朝各大家,其山水画作品有澹远苍秀之风。张式著有画论《画谭》一篇,“五千余言,阐尽笔墨之妙”。本文所分析的是《画谭》中关于山水画的一段阐述。
从《画谭》中张式对山水画创作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创作一幅山水画的理解。《画谭》山水画论中第一句是“画山水以气韵生动为主,才能使笔墨”。开篇即提到“气韵生动”这一理论,可见张式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这一理论自六朝谢赫在其《古画品录》提出后,就一直是中国古代画论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美学命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式继承了谢赫的这一理论,他强调只有注重画面的“气韵生动”,才能够使笔墨技法在画面中得到展现。
这篇画论对一幅山水画的创作过程也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张式首先强调“全幅局势先罗胸中”,即一幅画在还未下笔前,其构图全势就应了然于胸。作画时应先从树入手,从树的中心分干发枝的地方下笔,然后画枝干再到树根,最后画叶子。张式以写文章进行类比,提到写文章要从“理”顺,而画树大概也要像写文章一样,遵循树本身的疏密向背、曲折参差来表现;画完树后,先画出坡石山岚的轮廓,到桥彴宇舍和人物,再画远处的树;接着为皴染山石,再渲染山石并设色,然后叠上苔点。在这样从“理”而顺的步骤下,进而反复循序渐进、衬浅提深,以体现画面空间感,最后通过笔墨丘壑的经营来表达画者的情思,这即是张式对一幅山水画创作基本步骤的阐释。虽然不同的画体,画法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想要表达的东西,因此张式还在文中提出“以主为先”的观点,即作画时应从大的地方落墨,而不从一些琐碎的地方开始。这也就是说,作画时要么在画面中大约安排好位置的经营,要么先使用碳条朽笔在纸上大约勾勒出画面全局轮廓。在构图上,张式认为要将画面分为前、中、远三段,然后再一层一层往里深入画面。深入过程中,画面中有些地方的浓淡需要交加叠润,使之干枯相宜,而有的地方则落笔后就不应再重复勾勒。
在《画谭》中,张式强调“气韵虽曰天禀,非学力不能全其天”。他认为绘画虽然需要有一定的天赋,但更重要的是勤奋学习,勤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天生的缺陷。而学画者如果可以通过古人的墨迹领会他们的作画思想,就能在作画时达到熟能生巧、毫无阻碍的境界,使自己的画面自然生动。张式还强调“详审古人墨迹,自有分晓,断不可依俗手为入门路径”,即画者需要仔细研习古人的墨迹,方能够知道其中的道理。这是因为人总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在临摹古人画迹时绝对不能够将普通俗手作为入门学习的范本,否则画者一旦接受了这样的学习就很难不受其影响。在作画的过程中,张式认为画者要在作画前就将画面整体局势罗列于胸,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全局罗列于胸”。依照这样的“全局”观念,画者在作画时所画的每一笔才能做到前后都有所联系、有所交代,从最初的到最后的结笔都还是“一笔”,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笔画”。
张式这段关于山水画创作的内容,从对古人墨迹的学习到对一幅作品的笔墨经营都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下面以王蒙的山水画作品《花溪渔隐图》为例,结合张式的山水画论,进一步探究张式对山水画论的理解。
二、王蒙与《花溪渔隐图》
王蒙是元代十分著名的一位画家,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为“元四家”,也是开元朝画坛“古意”之风的赵孟頫的外孙。王蒙的山水画,尤其是他所创造的“水晕墨章”技法,不仅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还对元朝以后的明清及近代中国山水画有深远的影响。
在《画谭》原文中,张式说到了“说者不能凿空,学者亦不能凿空”。也就是说,学习绘画和叙述一样,不能够凭空无据。因此,学画者须向前人学习,临摹古人画迹。当然,学习古人的墨迹不能随意选择一些不入流的作品,这也就是张式接下来所提到的“断不可依俗为入门路径”,习画者在临摹前人画作之时,需要谨慎选择。因此,王蒙必然也是从许多优秀的先辈前人中获得经验。王蒙的山水画艺术自幼就受到其外祖父——人称“元人冠冕”的赵孟頫的影响。当然,王蒙对古人墨迹的研习不止于此,他还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唐宋大山大水式的复古风格,并结合了同为“元四家”黄公望的艺术语言,以及董源、巨然等大家的绘画风格。这样融合多家的绘画风格在王蒙的这幅《花溪渔隐图》(如图1)中也能够体现出来。
《花溪渔隐图》的整体构图中,王蒙以三段式划分全幅局势,又以“S”形的构图形式,利用山石与溪面的虚实差异形成强烈的对比,以及山势如“龙脉”的走势,使画面的律动感和空间感更加强烈。王蒙从右下角近景的树入手,利用前后错落有致的树石,营造出郁郁葱葱的景象,利用平静的水中漂浮着一支渔父垂钓的小船,营造出一幅“有我之境”;接着向后依次经营中景的山岚流水、房屋宇舍,然后顺着画面走势接入远处的山巅远树的位置;经营好位置后,才开始为山石布皴并渲染设色。此图就是以这样的顺序反复循序渐进、衬浅提深,以加强整个画面的空间感。在这样逐层递进的过程中,画面达到了客观、可居、可游的效果。

图1
从整体上看,《花溪渔隐图》的画面中,处于中景的草堂影影绰绰坐落于成排的树木之间,房前淌着蜿蜒的河口,与画面右前景缓缓驶来的渔船及画面后方高低跌宕、连绵不断的山峦相呼应,整体呈现出一幅蜿蜒悠远的景象。在这里可以看出王蒙对董源、巨然山水画风格形式的吸收与转换,而画面中王蒙所表现的山势内部的结构线条与山体外部的轮廓线条相呼应,画面前后景致相互呼应,是受到了北宋山水画的影响。
除此以外,画面中有许多细小的破笔皴法,这些皴法可能是取自北宋画家燕文贵,而其中重笔勾勒的粗笔线条又接近于北宋山水画家李成、郭熙的笔法。正是通过对古人墨迹的深入研习,王蒙才能够达到张式《画谭》文中所说的“读得破古人墨迹,则触处透空,自然生动”的境界,从而能够运用自己的笔墨语言经营出一副气韵生动的画作,来表达自己隐逸的心境。
《花溪渔隐图》是王蒙绘画生涯中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是元朝末年,此时的王蒙一直隐居于浙江一带的山林中,不问世事,但他始终保持着与江浙一带的文人在艺术上的交流,尤其是同为后人称道的“元四家”间有着艺术上的交流,因此从他的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出其受到黄公望、倪瓒等前辈的影响。而在这幅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匿于山林溪流间的草堂以及一叶扁舟上的渔父形象,这正是当时文人画家所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最真实的精神状态的写照,画面也体现着画家所营造出的“有我之境”。在这一时期,王蒙的用笔风格是从董、巨的皴法中发展而来的。董源创造了“披麻皴”技法,以表现温润的山体和土质,而后又在山顶作矾头,这种表现风格成为江南画派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王蒙在此基础上又通过自己对自然的感悟,将董源所创造的“披麻皴”进行转换,创造出“解索皴”法,以表现出浙江一带山势的松动温润,这也更加符合王蒙所表现的江南景物。这样的技法在《花溪渔隐图》里处于中、远景的山峦中可以见出,王蒙正是使用这种“解索皴”来表现浙江一带的山势连绵氤氲之势。
在行笔上,《花溪渔隐图》中的每一笔都做到了有所交代,每一笔的前后之间都能够做到“笔断意连”,它们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画面连贯的气韵,这就是其所说的“下笔时是笔笔生出,不是比比装去,至结底一笔亦便是第一笔”。这与清初画家石涛所提出的“一画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说,画者在作画时应达到一气呵成、无须顾及细枝末节的境界,画面首先呈现出一个整体,然后各个部分才依次展现。换言之,并非多个细节构成“一”这样的整体,而是“一”先构成自身,并在这个整体中展示多;不是以多表现整体,而是将“一”作为创造整体,并在其中表现自身。这是一种画者达到与宇宙万物的灵性沟通,物我通达的境界,也就像王微的著名画论《叙画》一文中所提到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是一种自然与艺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作画的人就是通过与自然的沟通和相互交融,将所见所想,以及对宇宙万物的哲学思考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画面中,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合张式《画谭》的山水画论和王蒙《花溪渔隐图》的图式,我们可以具象化地了解到张式对创作一幅山水画的理解。首先,张式提出山水画的临摹学习绝不能从普通俗手入门;其次,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注重“气韵生动”,以“理”为先,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笔墨经营。张式的这一山水画论为我们总结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山水画创作方法,为后世山水画习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