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浪潮下的知识分子精神图谱与思想突围
——试论阎真小说理性叙事的类型考察
2022-04-23袁姣素
□袁姣素

作家阎真
阎真在中国现时代文学的特征色彩应该是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有着自觉的理性认知。与大多数作家们探寻的陌生化道路不同,他更善于将新儒学注入思辨的力道,厘清现实与理想化的距离,以生命的温度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真理性。在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有着特定的背景与生存环境,他们见证历史,铭刻时代印记。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敢于直面现实,批判自我,在精神层面,有着高度的精神自省与自觉。四部长篇小说中,《因为女人》写了知识女性的情感危机,《曾在天涯》《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写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窘境,四部长篇小说集中反映了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与思想突围。
在这些小说传达的中国故事中,阎真以在场的感官经验和绝对真实的书写,重现知识分子的古典精神,探寻与开掘儒家精神脉络的现代性。他理性而敏感的视角与先锋性路数不同,也与现代性的儒家心性叙事不同,阎真站在历史的角度冷静而理性地讲述时代进程中的中国故事。他悲悯而本真的写作态度造就了了其文学作品的高度真诚和心灵震撼,其敏锐的情感触角、绵密的生活细节,赋予了作品真实的时代镜像,更见出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道。基调平和朴素,气韵沉稳内敛,遵从内心,以小见大;于平凡见真理,以普通见特殊,笔力遒劲,思想踏实;在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具有现实的骨感与时代的纵深。在以“人”为本的现实社会,生命的终极关怀与价值取向决定着人们思想上的高度,阎真骨子里的文人情怀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漫溯而上,以道德尺度与传统文脉塑造了一个个具有“士大夫”精神的傲骨形象。《曾在天涯》的高力伟,《沧浪之水》的池大为,《活着之上》的聂致远,他们演绎的人间故事与命运在精神和价值的道路上殊途同归。鲜活的现实凸显出他们在经济变革与价值坍塌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名利物欲之时的思想突围。小说中的人物有道德底线的坚守,有现实生活的沉沦,有精神苍茫的迷失……他们是如此地鲜活和真实。
黑格尔说:“哲学的真正的实现是方法的认识。”阎真在叙事的熨帖,对人性的挖掘中,是将普遍性、特殊性融合统一的。他以深情而理性的笔触透析时代问题,见情见性发人深省,有着不可抗拒的震撼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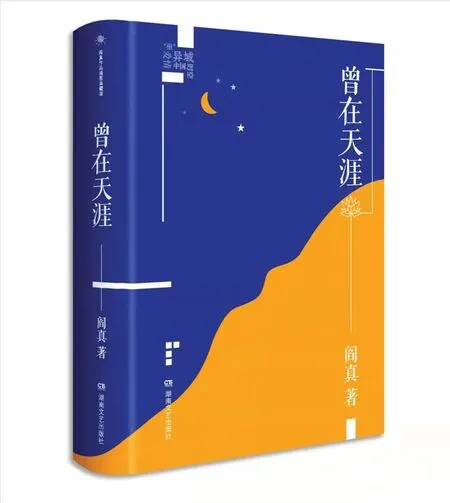
郁达夫式的忧郁情调
《曾在天涯》是阎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上世纪80 年代海外学子的命运遭际与灵魂漂泊。当时,出国留学是许多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以致国内形成了一股留学风,绿卡潮。小说将高力伟的海外经历与情感波折交相杂糅,描摹了他在北美的一系列遭遇,展现了当时国内学子追崇海外生活的心理态势与迫于现实的无奈心境。在矛盾与取舍中,在情感的痛楚纠结中,高力伟始终沉浸在自我的悖反冲动中。在爱情难以为继的尴尬中,林思文的女权意识又刺激着他敏感而强大的自尊心。很显然,生活与爱情的狭路相逢为高力伟的撤退埋下了伏笔。而现实生活的严峻更让他警醒,这个知识分子们所向往的“天堂”并不是他高力伟理想中的“天堂”。尽管有爱人林思文的百般挽留,有恋人张小禾的百般柔情,仍难以阻止他一心回国的坚定决心。
诚然,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时代进程的发展中,《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们渴望出国拿绿卡,如沈湘平所言“在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当代中国,价值观问题特别是核心价值观问题被愈益凸显出来”。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80 年代,当时正值国内改革开放,社会大变革刺激着社会每个行业的神经。一批走出国门的学子选择了拿绿卡在国外定居,有的人放弃了学术研究,开个小饭馆当个小老板,或经商或打工,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回国的寥寥无几。但高力伟的思想和价值观不同,他已在北美生活了几年,绿卡唾手可得,却毅然选择了回国,在许多走出国门的学者中,高力伟无疑是个异数。炙手可热的绿卡和才貌双全的爱人、恋人都无法留住他,而林思文、张小禾、孙则虎、周毅龙、葛老板等等这些留在北美的人与他不同,都对绿卡心向往之,但这些挚爱亲朋并不能阻挡他的回归之路。有人觉得荒谬,有人替他惋惜,但这却是高力伟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做出的选择。他的“老派”与新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形之中把中国文化底色渗透进了现代生活之中。《人民日报》对《曾在天涯》的评论是:为北美留学生活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也为历史留下了真相。浪漫的异域传奇不再是作品的精神重心,对文化品位的追求在情节进展中被强烈地凸现。
小说较其他文体之所以能承载更多的思想与文化,是因其中强大的包容性、多样性、总体性,这些丰富的文化元素能够构建诸多故事阵场。故事的人物形象既要典型立体,还要折射出不同凡俗的光芒,这些个性地塑造更要依赖于小说叙事的魅力。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特点在于传达感情”。可见,小说中的情感铺垫、展开、打动人心也是至关重要的。阎真的《曾在天涯》在叙事上是侧重感性基调的,有着郁达夫式的忧伤情调与“情”之本真。而且,在小说的情感意境上,他们也有着相同的悲凉底色。郁达夫的作品颇具诗意,追求真诚之美。而阎真的坦率表现在初心之真,从《曾在天涯》的叙事基调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种真诚,触摸到他悲凉的灵魂。他骨子里的民族感情、文化基因在召唤他漂泊的灵魂,这在小说中,也体现在高力伟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上。
小说的尾声与开头有着遥相呼应的悲情因子,重逢与离别都充满了忧郁的色彩。在细节的铺展上有着看似“柔弱”实际却“暴力”的轨迹。这在林思文多次对高力伟施以暴力中体现,情感的脆弱,生活的凶狠,一览无余。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异域他国,高力伟的灵魂如无根的浮萍,无所归依。他不得不一边忍受着妻子的折磨,一边坚持着打工赚钱,他做过洗碗工,搞过烧烤,卖过豆苗,还做过炒锅师傅……小说以真实的镜像效果再现了海外留学生的窘迫境况,他们在国内的留学光环与国外的现实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从另一视角反映出知识分子矛盾的性格特点。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上,林思文的形象也达到了逼真的效果,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有着好强与倔强的狠劲,在追崇虚无光环的过程中,把自己逼入了感情孤苦无依的境地。
高力伟无意间遇到了张小禾,两人都陷入情网,但都理性地坚守着最后的底线。这种感情不同于与林思文的感情,两人都试图努力挽留对方,但现实还是让他们分手了,情感最后都没能战胜双方执守的信念。正如《中华读书报》上的评价,“小说触及了生命无可逃遁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对知识分子来说尤为痛切。
无疑,阎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无论是小说的叙事还是结构,或者阎真式的风格塑造,都深沉老道,驾驭自如。其高度的理性自觉,标志着具有“阎真”符号的长篇小说正以迅雷之势为读者所熟知。
经验之上的现代心性儒学的开掘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崛起,乡土的凋敝等等诸多时代进程构建了中国复杂多样的现代格局。孙犁在《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中提到:“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可见作家在社会中的使命和担当。当然,文学也亟需丰富的养分来使其焕发新的色彩,这就要求中国文学在既往的繁华上,探寻更为恰当的创新性途径。
阎真的《沧浪之水》融合个人的感官经验,洞见时代背景下的道德形态与生命终极的追问。从创新性的意义上看,《沧浪之水》以遵从内心的真情叙事来体现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性综合元素,在文化形态与人格塑造上有着高度的自省与自觉,将池大为这个知识分子与现代儒学充分融为一体,发掘出小说艺术的精神导向、人性观照。主人公池大为在社会进程的发展中是有着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在与马垂章的几次接触中,池大为深切感知到权力的微妙作用,又从丁小槐、任志强等人的生活经历中体味到他们审时度势的小聪明带来的利益与物欲的诱惑。而深受儒学影响的池大为并不为这些外物所动,他的道德理想时常与父辈的追求交融在一起,在现实的社会中屡屡碰壁,这个血性青年的耿直与可爱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他的抱负与志向眼看要灰飞烟灭,在他敬重的晏老师的点拨下,池大为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清高,决心“杀死过去的自己”,成为了权力的“圈内人”。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故事的尾声中,池大为虽然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却隐隐流露出心无皈依的茫然与无奈,他在父亲坟前烧毁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是忏悔还是召唤?那种复杂的情愫冲击着他的内心,价值与信念失守的懊悔,都体现出深刻的警世意味。正应了儒家经典《中庸》里的“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可见池大为的内心还是很懊悔自己为取悦世俗而改变了初衷,最后让虚无主义将自己吞噬。如此,在这个精神“多元”的时代,培育健康的精神,正确化解“现代性危机”是迫切的时代需求。而《沧浪之水》的底蕴气质,及其理性自觉的时代价值诉求,正是阎真的小说辩证法。正如张兴国所言,“当科技理性成为价值理性桎梏,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一类问题不屑一顾甚至有意‘躲避崇高’的时候,精神便失去其本有的超越性、能动性特质。因此,那种被物质欲望所绑架的、被科技理性所窒息了的精神,必然因自我偏狭而导致封闭和专断,失去健康精神应有的开放与包容的博大胸怀。”

价值失守的悔恨与渴望精神救赎正是对池大为的深刻写照。《沧浪之水》有着宏大叙事的气场与魄力,更是理性精神的思维过渡。站在道德价值的尺度考量,池大为最后的放手一搏,并没有完全泯灭内心的道德和良知,他的内心还是希望做个现代“包拯”,只是再美好的初衷也难逃社会环境与规则的制约。恰如雨果所言,一片树叶受到阳光照耀,它的背面一定是阴影,阳光越亮,阴影越深。如此,池大为的内心隐痛就能够被理解了,屈子情结成为他的束缚,却又学不来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淡泊超然。以致这场灵魂的挣扎和思想突围历经了时间的洗礼,逾越了道德的鸿沟,无形中构建了一张巨大的欲望之网。在社会潮流中,命中了“放下容易,坚守很难”的现实性逻辑。池大为从坚守的防线溃败,到寻求精神支撑的矛盾纠葛,酝酿的是一场矛盾的“精神僭越”。其哲学意味与深刻内里,在现实主义的河流中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美学经验。譬如在故事进程的发展与人物渐进的模式中,作者擅于把控人物精神的磁场,心理描摹细致入微,有着开掘现代心性儒学的价值。这在思辨哲学的范畴中,有着探寻“现代问题”的积极意义。如此,《沧浪之水》的现实主义精神超越了现代思潮的本身,有着更新传统、精神皈依的意味。
美国学者安敏成在其《现实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召唤,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是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问题。”
阎真的《沧浪之水》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中,体现的不仅仅是遵循与回归,更是把故事中的典型人物和时代浪潮合二为一,以现时代凸显的“精神危机”问题微观社会,更见其创作的精神与力道。就如文学批评家雷达所言,《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与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在它面前,诸多同类题材的小说都会显得轻飘。池大为、马垂章、丁小槐这些人物被写活了,写透了,其复杂内涵令人深长思之。
在人物塑造的细节上,阎真是用“情”至深的。比如池大为第一次到省卫生厅报到的时候,见到马厅长,因为知识分子的那份自尊、使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跟他打招呼,倒是马垂章主动喊了他一声“小池”。这让池大为心里有了震动,多年未见,堂堂的厅长大人居然还记得他这个小人物,感动之余又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心理暗示。池大为当然懂得这轻轻的一声“小池”背后给予他的期待,而因性格使然,池大为的感动封存在他的内心,以致后面多次碰见马垂章,也没能在嘴上表达感恩。此类细节还有如他帮助了那个跪在门口得了绝症的赤脚医生,不想丁小槐一句“我知道大为他其实也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这句刀片式的话刺伤了他的神经,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丁小槐人性递进式的各种片断镜头的特写,以及点到即止的心理摹写都展示了小说中巨大的细节能量,点睛传神,催熟灵魂,达到了引人入胜的共鸣效果。
在小说的真实性问题的阐述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就提倡现代文学必须注视真实的人生经验,阎连科也提出过“神实主义”,但阎真却更关注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直面“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彰显真情叙事的魅力与风采。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言——“始终去寻求和阐释活的文学,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这是我们对文学的一种态度”。
诚然,故事的发展和推波助澜还需要人物的对立和矛盾。小说中见风使舵、急功近利的丁小槐起到推动矛盾冲突的作用。池大为和丁小槐在前途命运上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心理鸿沟。但在表面上还得维持同事间的那种和谐局面。揭示池大为心灵细节还有关键的一幕:他儿子被开水烫伤,为了赶时间送往医院,他求到马厅长安排司机大徐送他们去医院。到了医院,又因为要缴纳两千元的住院费费尽周折,最后打了丁小槐的电话,才办理了住院手续。这段有惊无险的求助经历让池大为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的作用力与优越性。在人物心灵轨迹的变化中,这无疑也是关键的一笔。诸多的生活磨难与感官刺激不断地累加,给人物的灵魂扭转点燃了引线。而始终贯穿在小说中的精神暗线也在并轨同行,作者专注于现代化语境下的实践逻辑和思辨逻辑的哲性思考,凸显出社会中的道德主体性的价值和意义。与现代心性儒学不同的是,阎真虽然追崇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却更关注个体心性精神在社会中的无奈性与无力感。就比如池大为的初心与价值信念的坍塌,一切的发生都不是由他本人把控的,而是在必然的过程中,一步步开启了他的人性贪欲。在高贵与世俗,物欲与精神的较量中,以池大为为代表的另一类知识分子面临着精神的僭越与尴尬。
无疑,阎真的思辨逻辑并不依赖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而是以个体经验的精神复活延伸到小说叙事的哲性思考中去。小说的尾声池大为一方面快速地处理马垂章留下的“烂尾”工程,突出自己的政绩,一方面以疗养身体为由送马垂章夫妇出国,处事有条不紊。这种全面把控、运筹帷幄的能力,充分说明了这个知识分子的睿思,以及处世之道的成功。
阎真风格的真情叙事与哲性意味是富有个性魅力的,既基于传统又创新传统,通过一系列人物的演绎,成功地塑造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与心灵蜕变,展现出生命的终极意义与安宁回归,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缩影。在文学的审美路径上,文本中表现的另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回到文学本身”,还是重返现实的河流,所折射出的艺术光芒都有着特别的意味。
精神危机下的理性从容
在阎真的四部长篇中,《活着之上》是理性精神的延展和沉淀。阎真的长篇小说一步一个脚印,一部聚焦一个典型,可谓“步步莲花”。回顾阎真笔下的代表性人物,从《曾在天涯》的高力伟,到《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到《因为女人》的柳依依,再到《活着之上》的聂致远,阎真塑造的人物都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演绎着相同的社会角色,展现了终极的时代价值和诉求。阎真以饱含真情的笔触激活尘封的历史烟云,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照亮那些小人物卑微而不屈的灵魂。
《活着之上》的聂致远以最后的坚守者形象区别于池大为最终的价值失守。聂致远虽然平凡朴素,却也散发着自己的光芒,立于天地之间。他在精神上杀出重围之路,正如清风送香,宁静致远。阎真小说的人物故事都不是特别悲情,没有大苦大难的悲剧命运。但这些普通的人物却演绎了人世间的万家灯火,展现了现实生活与价值诉求的时代命题。这几部小说整体合一地化身为“阎真”符号,把脉时代,予人深思。也显示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与探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艰难探寻与坚定守望,在小说中发自内心的真情,真爱在时代进程的“精神危机”下,始终不减,在理性中从容,于不可能中探寻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
众所周知,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高峰猛浪之中,诸多的批判也应运而生。在波澜壮阔的现实世界中,中国的社会变革亟需“有难度的写作”。诚然,文学的嬗变与社会思潮的涌现,正是从社会转型期间脱颖而出的。阎真的《活着之上》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赢得了社会潮流的青睐,其直击中国高校学术反腐等真实的书写产生了巨大的效应。阎真以锋利的笔触一层层剥开学术腐败的隐形外衣,坚持以传统文化的“老派”树立典型,以现实的世俗烘托理想的崇高。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大胆超越,也是知识分子以“文学介入”的方式体现社会担当与挽救“精神危机”。
文学评论家陈骏涛曾说过:“搞文学的人,其目光绝对不能仅仅止于文学,而应该关注文学以外的广泛的问题。首先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这些每一个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特别是搞文学的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就知识领域来说,还应该涉猎除了文学以外的其他门类——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
而这些哲学的,美学的,历史的等等,恰恰印证了陈骏涛对《活着之上》的精神旨归的描述:“……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
聂致远用他那点艰难的人格坚守,照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这样的“活着”是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的,是高于现实、超越灵魂的。
与余华的《活着》中徐富贵的悲情、苦难、坚韧的生命不同,《活着》诠释的生命是“是人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而《活着之上》的聂致远思考的是人活着,还应该有着活着之上的牺牲精神。二者体现的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生命不同的灵魂观照。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阎真不仅擅长书写知识分子的领域,也是提炼生活经验的高手。聂致远是游弋在生存之痛中的平常人,从与蒙天舒互换了导师开始,他的人生就进入到了颠沛流离的状态。在现实的生活中,一身清高有着文人酸气的聂致远显然不是蒙天舒的对手,他辛辛苦苦撰写的论文被蒙天舒几句天花乱坠的话就哄骗去了,成了蒙天舒开启仕途前程的钥匙。如此种种,都让善于钻营的蒙天舒占尽了上风。这在两人的精神疆域中有了明显的分水岭,一个追求利禄,一个景仰风骨。聂致远在物欲利诱面前扼守心灵的净土,代表的是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是经济社会中的暖色与闪光,也是传统文化与功利主义的交融碰撞。而更让人惊艳的是阎真笔下的思辨力道,与《沧浪之水》不同的是,《活着之上》的叙事更为简约有力,大胆犀利,其直击现实的锋芒更见出理性之中的淡定从容。这是一种对时代精神与文化哲学的突破,“换言之,正是精神的问题和作为问题的精神,成为一个带有时代性意义的课题”。
在人物塑造的典型上,阎真笔下的女性人物刻画也颇具代表性,有着鲜明的人物个性。比如《曾在天涯》中知识女性的代表,要求严苛的林思文、浪漫灵性的张小禾,《沧浪之水》中高傲美丽的许小曼、不甘人后喜欢攀比的董柳,《因为女人》中迷惘而焦虑的柳依依,《活着之上》中现实平庸、渴求解决编制的赵平平,她们在阎真的笔下也是各具特色,与现实生活对照,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活着之上》中,阎真叙事的个体经验更侧重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窘境。比如聂致远与赵平平结婚时买不起房子,也没有能力在省城操办一场体面的婚礼。甚至,在考上博士以后,也没有经济能力在省城买下一套房子,让聂致远在岳母面前尽显尴尬。在回到鱼尾镇的老家后,家人以为博士是个多大的官,却发现还不如在镇上当办公室主任的弟弟有经济能力。面对父母的疑惑,聂致远心有愧疚,却无从解释。这些生活细节,都充分地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生存困惑与精神窘境。生活的困顿让聂致远一次次陷入精神的“桎梏”,妻子赵平平的编制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让他备受煎熬。编制问题深入展开,竟然还深藏着潜规则,这让聂致远从震惊到愤怒,却又无力改变。在现实的利诱面前,聂致远努力坚守自己的底线:他成家之际,也是最需要钱的时候,一个矿老板要为自己的爷爷立传,请他来写这部书,当聂致远发现矿老板说的资料完全与事实相悖时,坚决拒绝了这笔收入可观的交易。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都有着以小见大的力量。叶圣陶说过:“写文章不是生活的点缀和装饰,而就是生活本身”。阎真善于把哲理融入简单庸常的生活中。文中聂致远以一次次地拒绝抵制心灵的腐蚀,维护着高贵的尊严。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聂致远还面对诸多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窘境,更显可贵。
《人民文学》的主编施战军评介说:“《活着之上》是现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遭遇史。没有拔高也没有虚饰,内心有着执着和向往,但伴随着妥协、挣扎、痛苦。在梦中的曹雪芹和世上的聂致远之间的虚衔处,恰恰是我们精神的生机所在。”
一部好小说的评判标准在读者的心里,不在炫技,不在多情,不在矫饰,而是能与读者共鸣。譬如聂致远站在那棵熟悉的老槐树下感慨万千,思量人生。这时,他突然发现,曹雪芹的生卒年以及父亲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永在,留给了历史和未来无限的思考。从开头到结尾,聂致远对曹雪芹的难以割舍,顶礼膜拜,始终贯穿其中。这不只是一种心灵默契,更是一种精神的融会贯通。正是在这种文化道统的耳濡目染下,在伟大先贤的力量驱使下,阎真笔下的聂致远用自己的行为准则冲破世俗的樊笼,始终遵循着内心的真诚,用他景仰的精神高标给出了时代性的命题,也是对生命之上的终极追问——“我觉得历史中藏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秘密,关于时间,关于人生,关于价值和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阎真叙事有着哲人的先知先觉,从知识分子的命运抗争与精神坚守的矛盾纠葛中洞见思辨之下的理性认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特征标识上,语言的辨识度自成一体,精神疆域执着而旷达,其秉持内心坚定的文化自信,塑造了一个个不屈的精神形象,传承和深化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的神来之笔总见于细微之处,善于用细小和平凡的事物检阅生活真相,没有人世间的大喜大悲,却能从平淡与琐碎中发现人生宝库的钻石,诠释真理,升华境界,重塑精神。
站在价值和艺术审美的立场看,阎真叙事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他以干净的灵魂寻找着文学的灯火,无论是《曾在天涯》,还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抑或《活着之上》,整合的是时代浪潮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精神上高度统一,不媚俗当下,不将现实功利化,始终遵循强大的内心,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增添了“阎真”符号的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