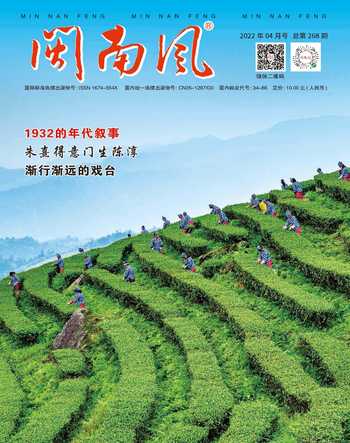渐行渐远的戏台
2022-04-22林进结
林进结
很怀念乡村的节日,怀念乡村的戏台。
有戏台,就有戏看。农历十月,乡村陆陆续续过起了平安节,社戏唱起来就没有停下来。
许多乡村都在唱戏。在我们这里,唱的是潮剧。对东山人来说,潮剧就是自己的戏剧,潮音,便是乡音。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还是黑灯瞎火的,更不用提文化生活。年轻人精力充沛,夜间在县里四处转悠,哪里有演出电影就奔向哪里,几十里地的来回那根本不在话下。县里的有线广播拉到乡下,中午和傍晚广播机播放“革命”、天气和“样板戏”,偶尔也播放潮剧。潮剧唱腔圆润,美妙动听,村庄里的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老人们说这是唱“白字”,因为他们把闽南语系中的潮汕话叫做“白话”,白话不是普通话,是自己听得明白的方言。京剧“革命样板戏”的基础是普通话,大多是文盲的老人们听不明白。
村里演戏,我们从小就喜欢。我起初对它的喜欢很朴素,演戏,就有节日,就很热闹,就可以吃点好的。我们村一般在农历十月份的平安节演潮剧,名义上是酬神,实际上凡夫俗子也能过过眼瘾。戏还未开,戏台下面就摆满密密麻麻的长条板凳,大家纷纷占据好位置,以至许多人家吃饭要站着,没有凳子坐了嘛。演戏的时候,台下人头攒动,那种热情的劲头,就是种渴望了。平安节,年前祈求平安,年底就要还愿答谢,除了家家户户要摆果品牺牲祭拜上天,还要请答谢地头神一年来保佑村庄的辛苦。我们村的护佑神叫西方玄天上帝,大家一起集中在村外的神田里祭拜,神田的地面早早平整好,一家一张桌子摆着供品,这夜鞭炮焰火的声音此起彼伏。祭拜完成后,戏才能开锣,否则便是不敬。神田后来盖了小学校,祭拜的场地改在各家各户门口,大家也很顺从,只是劳烦了神明,要各家各户走吃了!平安节在秋季,一年的收获大多已经入仓了,时间空闲,吃的丰足,各个村庄过节,你来我往,相互请客,亲情融融,乡情满满。小孩更是欢天喜地,在夜色下闯来蹿去,尽情地贪玩。
除了平安节,有时候,三月三也演戏。
农历三月三是我们村重要的时节。其一是古清明节,其二是西方玄天上帝诞辰。我们村子过清明节有讲究。祭扫旧坟墓,就在三月三,称古清明节;上新坟墓,就等到清明的那一天。当然,清明节四乡八里都不会演戏。但是三月三是“西方玄天上帝”的生辰日,要祭拜,偶尔也演戏。诏安林家潮剧团来村义演的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
那一年的三月三演戏,一演就是三天。戏班是诏安县的林家(或是林厝),他们是我们林姓本家,新学了戏,想展示展示,所以就不请自来了。村里说农忙太累太忙,拒绝了他们,没想到林家班一定要来,不要工钱,不要车钱,伙食自己解决也要来。亲人嘛,这么坚决,村里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只得在农忙时节抽调后生搭戏台。那时,我们的村庄很穷,没有固定的戏台。凑齐搭戏台的杉木柱子、椽子、台板很不容易。几个后生,几个木匠师傅忙碌了两天,戏台还没完工,演员们坐着拖拉机先到了,大家赶紧帮忙,戏台终于搭好了。戏笼未到,还在后头,村里的小朋友们压抑不住兴奋纷纷爬上戏台玩耍。戏锣还没有开,热闹就开始了。
村里其实也不冷淡,既然人家来了,便安排了食宿。我家那时已经建起了新楼房,有几个女演员住在我家。女演员比较金贵,分散到一些房子比较宽敞的人家住,至于男演员,本来就是泥腿子,没什么讲究,都挤在祠堂的大厅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
白天,演员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参加插秧。傍晚回来,洗洗,吃了饭,化了妆就上场了。戏的好坏现在也无从想起,但快乐的就是我们了,忙碌的是大人,要招待来看戏的亲戚。经此一演,每年的平安节都请林家班来演戏,直到林家班散了才请别的剧团。林家班不管别处有没有戏分,都来。至于报酬什么的,大家都是“亲人”,熟头熟脸,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开戏以后,胆大的孩童会偷偷溜上戏台角,坐在帷幕后,演员的脚步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他们得意的时光。情窦初开的二牛,装成大队的人,溜进后台看,看戏,看女演员,不过,结局是被民兵队长拎着耳朵扔到戏台下,十六七岁的人,羞得要钻进地缝里去。

演戏总是和节日联系在一起,不是节日,哪个村也不会吃饱撑着演戏。但是,有例外。我们的邻村下湖村他们有潮剧团,经常在排练完节目以后向村民们汇报演出,没有过节村子也演戏,演戏就能吃干饭,让我们很是羡慕。演员也都是村民,男男女女,白天在田间脸朝黄土背朝天,晚上就你是帝王我是将相,出将入相,驰骋舞台也一慰平生。或我扮书生你扮小姐,郎情妾意,假戏往往也成真,令许多正当年华的男女青年很羡慕。邻村与我们只有一路之隔,姓氏相同,有一大部分人是我们村的后裔。他们村子有专门的戏台,有潮剧团,我们村没有戏台,没有潮剧团,让我们心里很不甘。不甘归不甘,锣鼓一响,还是忍不住,一群人纷纷投奔他们的戏台去了。
看久了,听久了,听人家唱,嗓门就痒痒的。渐渐地,我从喜欢看戏的热闹上升到喜欢潮剧。至今,还记得许多剧目,像《井边会》《陈三五娘》《穆桂英挂帅》《秦香莲》《杜王斩子》等。也记得许多名角名人,比如红妙、仙花,姚璇秋、方展荣、马丽端等。红妙是潮剧大师,男扮女装演青衣,真是妙不可言。仙花老师原名陈华,是我们东山人,许多好听的曲调出自他的手,我们都觉得很骄傲。我听说广东潮剧一团、潮剧二团及潮州潮剧团是最好的,心里很是钦羡,直到多年以后,戏剧已经式微,我到潮州还特意到潮州潮剧团所在地走了一趟,在它的台阶上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一直都在想,如果要排列对我启蒙的顺序,那么,潮剧一定是位列前茅。我对世界的许多认知,许多做人的道理是从它那里获得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戏剧兴盛的时代。改革开放了,物质丰富,生活好了,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娱乐的方式也没有那么多。乡村也好,城市也好,还有大片的戏迷。那时,我们这里有许多潮剧团,县里的潮剧团最为正宗,演艺炉火纯青。其他的都是乡村自行组织的潮剧团,像什么“青年潮剧团”“实验潮剧团”“第二潮剧团”一系列,名称虽然好听,但是演艺还是粗糙。平安节如果哪个村庄能够请到县里的潮剧团,就让人觉得特别有面子。东山潮剧团,一年里大多在潮汕地区演出,难得有回东山的机会。回东山总免不了要安排在人民会堂演出。买票要买前排的,拿票得有人脉。对于一个喜欢看戏的人,位置很重要,一定要前面。前排看得清,听得明。演员的神态,表演的细节才能细品。那时,东山人对潮剧团的演出有着莫大的热情,一千多个座位的人民会堂,座无虚席。许多人还买不上票,通过各种方式挤进来,站在门口的,趴着窗户的,各个角落都有。静静地听,静静地看。散场了,每个人都在谈论戏、谈角色、谈剧情、谈情绪,总之,潮剧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在外读书时,我喜爱的剧种多了起来。像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我都喜欢,有时也能来两句。参加工作后,我给家里买了一个录音机,买了许多潮剧磁带。母亲晚上空闲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大门口听潮剧。我家门口的空地、巷子坐满了人,大都是中老年的妇女,她们闻声而来。
我现在住在县城里,家临着大街,对面住着一位老人,七十多岁了。他会弹扬琴,声音悦耳动听。经常和几位老人一起在家门口合奏。月下,扬琴、二胡、三弦,弦音汇合,潮曲声声,引行人驻足围观。这样的生活情景其实很美妙,可惜我们的生活中保留的太少了。
现在,我几乎不看戏了,不管是电视机还是戏台。但在老家,还有人在看戏。我的父亲喜欢把电视的声音调到最大,不知道是耳背还是故意要让潮剧的声音在街巷里飘荡。几个邻居老太常来厅堂坐坐,听潮剧,到点了才回家煮饭。一个休息日,我回老家,本要陪陪父亲,但父子相对也没有太多的话说,于是陪着父亲看完了《红鬃烈马》全剧。《红鬃烈马》讲的是薛平贵的故事。我发现还是喜欢,漫长的几个小时,一点烦躁也没有。我在暗暗感叹也许是生活的节奏太快了,让我们没法停下来欣赏它。也或许它经受不住各種快捷的文化样式的冲击,一步一步地后撤了。
县城的剧场,也基本上不再演戏,确切地说,不再演潮剧大戏。偶尔有,也是文艺汇演中的戏曲小品,那种万人空巷看戏的情景不再了。乡村里,平安节依然演戏,可是戏台下几乎空荡荡的,观众很少,钟情于戏剧的老一辈粉丝已经消亡殆尽,没有受过戏曲熏陶的年青一代几乎天然地拒绝了戏曲。
也许有一天,村庄的神明会成为唯一的观众。我在漳浦县新港城庙群参观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每个村庄新建的戏台都对着修建得辉煌无比的庙门,戏是神的戏,戏台是神的戏台。戏曲的命运直落千丈,曾经风光无限的东山潮剧团就已经被解散了,成立了个潮剧传承中心。我不知道芗剧、歌仔戏、莆仙戏甚至各种大剧种现在的命运如何。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在保护名录上才能见到它们,那真的是百感交集了。它们是我们的,民族的,我们爱它们,太想它们复兴了。
如何复兴呢,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