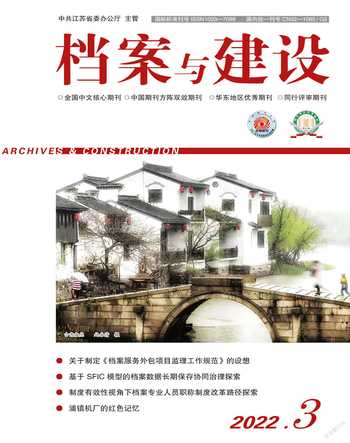信仰与秩序:1935年徐州城隍信仰风波探微
2022-04-21刘晗王亚民
刘晗 王亚民
摘 要:民国时期的徐州,城隍信仰已然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一种共有习惯,既具有满足民众日常需求的工具效用,亦起到了稳定基层秩序的“安全阀”作用。铜山县基层官员忽视民众日常生活中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需求,违背上级不得“骤行废除”的指示,做出了烧毁神像之举,导致官民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官府对传统信仰习俗的改造不应采取激进手段,而应将民众的基本诉求作为解决问题的核心。
关键词:民国徐州;城隍信仰;官民冲突;基层秩序
囿于阶级与思维逻辑的差异,民间城隍信仰常被民国的书写者以自身经验出发,冠以“愚昧无知”之名,民国时期徐州地方政府亦是如此。目前,学界对于民众视域下的研究相对薄弱,故拙文在解读多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出发,结合民众心理与官府行为,力图就“1935年徐州城隍信仰风波”略加探析,进而揭示其背后的内在逻辑。
一、 城隍信仰习惯的形成与民众日常生活
徐州城南门外一里(旧城隍街)的城隍庙,相传为奉祀汉臣纪信之址。至明清时期,城隍已作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掌控人民,“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1]
随着生产力发展,庙会的宗教功能逐渐向商业功能转移。徐州民众形成了“有神必拜,拜则成会”的风俗,每逢年关,“聚众赛会,锣鼓喧天,闹市招摇”,[2]游人成千数万,舞狮杂耍,宗教表演,应有尽有,颇有一番繁华景象。城隍庙周围的店铺尤受其利,逐渐形成以城隍庙为中心的商业街道。据调查,在徐海地区90处庙会中,交易买卖与游艺娱乐的比重占61%,而求神拜佛仅有23%,曾经商业对象“大部分不过是城镇里一般的市民”,[3]而乡村的定时市集逐渐与庙会相融合,逐渐变成了交易什物之所。由此,庙会成为了缓解农村破产压力的必要途径,城隍庙亦演化为民众日常生活重要的公共空间。
总体看来,城隍庙会被赋予了宗教、商业与娱乐三大功能,在民间信仰根深蒂固、娱乐相对匮乏的民国时期,城隍庙会起到缓解民众生存精神压力之作用。在官方与民间的双重促进之下,城隍神已然深入徐州区域的社会文化之中,几成当地文化符号。
二、 城隍信仰风波与官方的话语书写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渐入人心,故而提出“(前清祀典)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4]此后,在西学东渐与新思潮的加速传播下,彻底消除旧信仰、构建新社会成为民初政治的重要议题。民国元年(1912),粤军在克复徐州后“为破除民众迷信起见”,即毁除两廊神像,但城隍“幸未遭及”,事后该庙经过民众修葺,仍于朔望与会期“香烟缭绕”。[5]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力求破旧立新,“反迷信”亦被规划进国家制度建构体系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声称,祀神礼节系“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之余毒”,迷信民众将会“锢蔽其聪明、贻笑于世界”。[6]在地方党部的积极推动下,各地的破除迷信运动如火如荼。北伐军二次光复徐州(1928)时,国民党铜山县党部在“破除迷信,彰扬党义”的旗帜下,分两路捣毁了该庙,将大殿改为总理纪念堂,余则用作公安局消防队驻所与教练所之讲堂。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在科学昌明时代,城隍实无存在之必要”,[7]饬令各市县公安局“随时劝导人民破除迷信”,[8]城隍神亦在被废之列。表面上,徐州旧时城隍神早已在北伐军破除迷信声浪中灰飞烟灭,但城隍庙的主持道士却暗将神像移至西关的城隍行宫中,并重塑金身。平日有附近民众组成烧香会,对城隍神进行拜祀。
1935年正月,乡间民众“静极思动”,城隍竞赛又在远近各庄及城庙展开。此次迎神赛会上各种表演及游戏如跑旱船、大头娃娃舞、舞狮、踩高跷等层出不穷。有报道称,此欢闹场景实乃多年不遇,街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城隍巷内终日“几无立足之地”。[9]
力主革除封建迷信的铜山县县长王公玙闻城隍复活后,惊愕道“竟有人开倒车”,遂以影响治安、关系地方秩序为名,授意骑兵分队队长郭玉标封锁各要道,以隔绝民众,并令西关镇长程子良于二月十五日夜[10]实施了烧毁城隍神像的计划,城隍木像在主持道士“哭天抢地,苦苦哀求”声中被焚为灰烬。
1928年北伐革命军破除城隍时,民众不过“烧香焚銖诅咒”抑或“泪涔涔下”,而无实际之反抗。然而,此次事件发生于正月,民众恰有余暇,又在奉祀神像与开展庙会的热情高涨之时,故而民众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起巨大的反抗动能,这显然是铜山县府始料未及的。
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抵抗分为两个阶段,即风潮开始时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抵抗,游行示威与打砸镇公所,后期有意无意地制造舆论,实施间接反抗。从“有声”到“无声”,反映了民众在与地方政府博弈时不同的反抗形式。
在第一阶段,民众得知城隍神像被焚后,即组织了数千人的示威运动。保甲长先行辞职,交出甲牌以作抵抗。“保甲长尤为接近民众,直接影响民众的地方更多,改造风气,转移人心的力量更大”,[11]由此有力地推动了风潮的发展。
随后,城隍信众所组成的烧香会“加以扩大”并暗携武器,试图与政府对抗,以烧香会为代表的民间宗教组织迅速转化为抵抗的有生力量。信众认为政府烧毁城隍神像的行为,“已犯神怒,以后人民生活将更臻困苦”,因而认为政府此举,实系故意为民“召祸”,[12]渐由信仰对立逐渐上升至官民对立。民众高呼“城隍能焚,镇长亦可焚”,[13]随即冲入镇长程子良家中,“喝令打倒”,并质问,欲破除迷信缘何镇长家中仍供奉祖先?遂将程家三代祖龛肆意“满涂粪污”,以作羞辱。“一时万众喧嚣,西关一带,途为之塞”,[14]程子良在护卫之下逃往县府躲避。
在浩大而激昂的抵制行动中,民众不断对县府进行施压,要求交出纵火镇长。同时,各种“迷信游艺”层出不穷,街市一时“鸣炮示威、锣鼓喧天”,县府虽然抓捕数人但旋即释放,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派出军警维持秩序。民众不畏强暴,进而提出重塑泥像、“令两镇长奉祀,并革其镇长职”的诉求。
在抵制运动的后期,惮于传统政治权威,民众采取分化战术,即将县政府与涉事官员相分离,将主要矛头对准涉事官员,给县政府留有周旋的余地。其标志是,坊间开始传闻,程子良于年前向该庙道士借洋二百未遂,此次事件只是出于私心,假借破除迷信而企图报复。无论该事件是否真实,民众通过匿名手段施加舆论压力,借以要求严惩“罪魁祸首”镇长程子良。地方民众非暴力的反抗形式不仅达到打压政府之目的,更有效地规避了公开抗争所受处罚的风险。
此次风潮持续了数日,参与民众达数万人,地方仍以破除城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借口,坚称“系奉省令”“迎神赛会尤在严禁之列”,直至县长王公玙答应对程子良调查处理后,又经“数日疏导,示威群众方告平息解散”。
作为处理城隍信仰风潮的主要官员,王公玙所载此次事件与之前所述迥然不同。他将此次风潮的发生全然推诿于地方党政内部“相互倾轧”“壁垒分明”,自称“兼顾不易,取舍尤难”,直言“此番阳借迎神之名,实含有党争意义在内”。[15]
王氏认为民众之所以暴动,在于西关镇长程子良在迎神赛会前夕藏匿城隍头像,民众以“无头之神既不可迎,即迁怒于该镇长”。[16]他指出,1935年春的迎神赛会是有“同志”在其中撺掇,又得到津浦路警备司令王均的支持,程子良“原系某一派系斗士,为敌对者所仇视”,[17]亦反对迎神赛会,因而被“政敌”借刀杀人。
这次风潮的主要处理者是县长王公玙,“推诿”与“掩饰”不得不说是其世故的表现。他在自述中使用“据传”“嗣知”等模糊性的字眼,一方面旨在与程子良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试图掩饰风潮的某些真相。他在自述中建构了虚拟事实,将风潮的导火索由“烧”改为“藏”,暗示民众对于“藏”反应强烈,顺势将风潮的责任转嫁于“愚昧无知”“蛮横无理”的民众,试图掩盖县府破除城隍计划的纰漏以及对城隍信仰风潮带来的恶劣影响。
三、 城隍风波背后内在逻辑的深层分析
首先,信仰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失效致使风潮发生。民国时期的徐州地区,“第以连岁天灾人祸相逼而至,农民生计困苦极矣”。[18]通常情况下,生活极为困苦的徐州民众并未“揭竿而起”,而是将“城隍”作为其心灵寄托。此时的城隍信仰已然被赋予了“社会安全阀”之职能,是防止地方社会秩序失范的一道精神屏障,其安全阀功能如若失效,民众的不可控感随之出现并加深。从表象看,徐州城隍信仰风波是民俗信仰与政府治理的冲突,但若寻其根本,冲突则是生存压力与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具象化。“土地之集中”“赋税之畸重”“田赋之增高”“高利贷”“币值及度量衡之紊乱”“水利的废弛”“匪患”[19]等等,直接导致徐州地方民众长期处于压抑与紧张的状态,而民众的精神压力本可通过城隍信仰活动中的“进香”“祈祷”“赛会”等予以排解。同时,庙会中的农贸活动亦可舒缓民众物质方面的压力,一旦内生于民间社会的城隍信仰活动被革除,而外部又无有效渠道予以接替,那么疏解紧张情绪的安全阀门即被阻塞,演化为现实中的民众风潮。
其次,官方过激的反迷信行为与民间信仰习俗的尖锐对立,导致“除旧布新”无法实现,反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反迷信”“现代国家建构”话语下,提出宗教“妨碍国民塑造独立自主的态度”,然而,民间信仰根植于地方社会文化,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故而在反迷信运动中受到了来自地方信众的强大阻力。在数百年历史中,徐州城隍信仰逐渐臻于一种地方性习俗,官府骤然强力地以“反迷信”方式将其破除,无疑会导致官民冲突,继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
铜山县政府破除城隍神庙的过程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在破除迷信的政策上,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明令取缔城隍之地位,但也仅限于“见诸佛经”的虚妄而无历史渊源的神祇,徐州城隍神以纪信为原型,不在破除之列。其二,在破除迷信的具体实施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提出缓进的策略,若“骤行废除,不但启民众误会,亦且易滋纠纷”。[20]其三,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制定的《民俗改善运动大纲》明确要求,“以诚恳和善之态度纠正民众不良习俗”,抑或加以劝导,“使其停止或乘机改变其集会之意义”。[21]显然,铜山县政府未采取缓进策略与“诚恳和善”的态度,这无疑使民众陷入了政府“招祸”的错觉中,是引发城隍信仰风潮的原因之一。
最后,通过透视庙会的宗教职能向商业与娱乐职能的转变,可以发现徐州城隍庙以及周围地界已然变为重要的商业空间;再者,“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剥削”,[22]徐州民众通过游艺表演等,已然将其作为转嫁心理压力的主要娱乐形式。徐州官府外部强制性的文化改造,不仅阻断了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更与内生的民间信仰相抵牾,弱化了地方政府执政权力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明)吕本:《明宝训》(卷四),明万历刻本,第14页。
[2][9]《徐埠破除迷信》,《中央日報》1935年2月20日,第6版。
[3]杨汝熊:《徐海十二县庙会调查报告》,《教育新路》1933年第23期,第2页。
[4]《内务教育二部为丁祭事会同通告各省电文》,《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32期,第11页。
[5]莘盫:《粉身碎骨之城隍老爷》,《申报》1928年5月22日,第21版。
[6][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3、514页。
[10]《新闻报》《时报》言系二月十五日焚毁,《中央日报》及其他言为二月十六日夜焚毁。本文取二月十五夜为焚烧时间。
[11]徐西明等编:《保甲长须知·序》,铜山县保长训练所1935年版,第1页。
[12]悟生:《徐州城隍风潮详记》,《福尔摩斯》1935年2月27日,第2版。
[13]《徐州西关镇长焚毁城隍 民众反对到县府示威》,《大公报(天津)》1935年2月18日,第4版。
[14]《徐州西关两镇长宅被捣》,《申报》1935年2月18日,第3版。
[15][16][17]王公玙:《畸园残稿》,新文化彩色印书馆1984年版,第214页。
[18]《徐属农村生活调查》,《中央日报》1932年9月6日,第6版。
[19]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6期,第77页。
[20]《党务:打毁神像与破除迷信问题》,《江苏省政府公报》1928年第64期,第47页。
[21]《民俗改善运动大纲》,《教育部公报》1934年第6卷第19-20期,第37页。
[22]润之:《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向导》1926年第179期,第18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