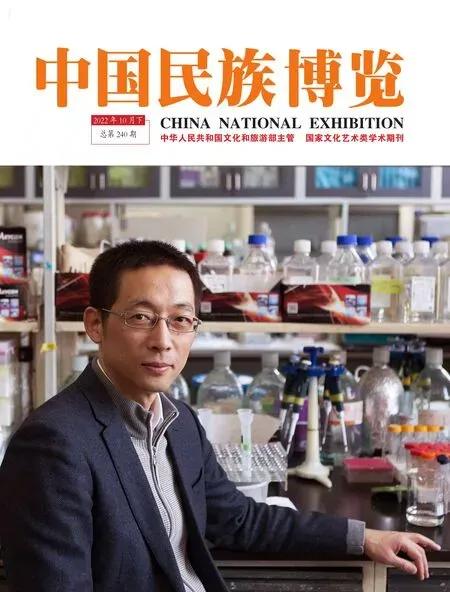从《源氏物语》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以“文图论”中的“虚”与“实”为视角
2022-04-18戴鑫源
戴鑫源
(外交学院,北京 100037)
全球化时代,“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这种战略的成效很不乐观[1]。而战略不乐观的核心在哪里?其次,我们当下面对的是传媒时代新危机,“图像”的袭来让“文学”的地位面临挑战,新世界的“语图危机”到来[2]。文本由静变动,传统的纸张书籍依旧存在,但是它时刻面临着被“超文本化”的可能。“语图危机”归根到底是“图像”对于“语言”的战争。文章以《源氏物语》为平台,以“语图论”中的“虚”与“实”为视角切入,探寻千年前以平安朝为背景创作的《源氏物语》中“文本文字”与“图像绘画”二者的关系,并从二者“语图关系”中透视出中日文化的互动特点,以史为镜,再回看全球化下“文化走出去战略”。
一、文字的出现:诗文“实指”
如若谈诗文,就离不开组成诗文的文字。中国的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汉民族的“自源”字。而日本的文字离不开中国文字影响,是由汉字和假名两套符号形成。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前,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日本作家河野六郎指出,日本人已经无法离开有魅力的汉字,这种文字已经与日本人紧密相联[3]。笔者认为这里面的“魅力”是指汉字的出现,让日本可以从“口语时代”更顺利过渡到“书面时代”。文字出现了,并且富于文字“一串声音”,变身为纯粹的书面语能指。
《源氏物语》第二回《帚木》卷中,藤氏部丞讲述他到一位文章博士家里去,发现他的书牍,一个假名也不用,全用汉字,措辞冠冕堂皇,写得极好。[4]”可见“汉字”与“假名”两种符合各自承担不同的作用。第三十四回(上)《新菜》卷里明石道人给老尼姑写信:“我看惯汉文经典,阅读假名书信颇费时间。”可见当时文字文本采用“汉字”渗透到平安朝的知识分子生活中。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在“原样移植”汉字的时代,中国文化对于自己民族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中国对于彼时的日本是先进发达的理想的超我。同时,彼时“唐土”的文字能在日本民族中流传至今,使之融为日语的一部分。这个体现出了汉字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表现出日本人善于学习他国优秀文化[5]。
由上述可知,平安朝的文学载体文字受中国文字影响颇深,那么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学也必然受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强调明志载道,相比之下,日文文学重点也多放在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上,即更注重“人生况味”的抒写[6]。
但是,无论是“言志载道”还是“人情况味”,都是借助语言文字所抒发。这似乎是无需论证的道理。正如有学者提出:言说是我们的本性,而人是靠本性才拥有语言一样[7]。同时还有“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8]?”先有言说,使语言意指世界成为自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精准的意指提供了先决条件。而“精准”一词便与“文字”相关,也就是文字的“实指”。文字出现以后,书面语社会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之前的口语时代。因为书面语可以让人们的“言说”能够在时间以及空间上进行传承,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以及文化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从而进行“对话”,语言便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的语言”。“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二者孰轻孰重的明证。也有学者指出:“语言成为文字的过程就是语言成为语言的过程。[9]”
《源氏物语》中,作者紫式部用文字呈现了很多中国诗词,因为文字的“实指”,让我们能立刻知道所指。比如,文中采取直接引用的有很多,引用痕迹比较明显,读者看后能马上联想起原诗。第四回《夕颜》卷源氏公子对夕颜说:“长生殿的故事是不详的,所以不引用‘比翼鸟’的典故。”“比翼鸟”便是引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第四十九回《寄生》卷中,匂亲王口中诵着“不是花中偏爱菊”元稹的古诗。除了很明显的直接引用之外,引用某句诗或者典故,却已融入作品中,不经仔细研读不容易发现。比如第十八回《松风》卷中,紫姬说的话中,出现了斧头柄也烂光这一词语,其实这便是引用了《述异记》里的烂柯山典故;第十五回《蓬生》卷中,太宰大弐的夫人来看末摘花。提到了“三径”。[4]此处的“三径”来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指通门、通井、通厕的径;还有第三十四回(下)《新菜续》卷提到的“不惜挂冠悬车,身无官职”里面的“挂冠悬”就是辞官的意思,来自《后汉书·逢萌传》。
由此可以看出,所固定到纸面上的文字文本不能让我们思绪“任意”而为,因为文本文字的能指和所指二者的“胶合”所达到的效果就是“精准”指代,否则文字的实用性就会尽失,文字也就失去了意义,就会造成“言不达意”的尴尬境地。翻看平安朝文学,这些文字会让我们精准追溯到它的来源,同时印证中国文化对于彼时日本的巨大影响。
二、图像绘画之“虚指”
上文所述,文字不过是一种简化了的图像,那么文字来自图像并演变成书面语言的能指之后,图像和语言文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图像的意义来自其图像本身,需要我们“凝视”甚至有时候要“定睛观赏”去细品其中奥秘。比如我们以日本传统美学之一的“幽玄”为例子。比如日本画《月下溪流图屏风》就是“幽玄”审美的一个代表作,画中月的光华是由溪流来表现的。在观赏这幅画作之时,观者需要驱动自己的现象力,加入与作画者时空联动的共创之中。可见,对于图画的欣赏离不开“驻足观赏”,这个与文字的“幽玄”二字比,本质有很大不同。
莫里斯曾经说过:“符号具有隐喻性。把汽车叫做‘甲虫’,或者把一个人的照片叫做一个人,这就是隐喻地应用了‘甲虫’和‘人’这两个语词”[10]。
所以,语言“幽玄”和图像“幽玄”都作为意指符号,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幽玄图具有隐喻性。具体来说,面对文本文字,只要认知文字,便可在看见文字的同时就明白所指,“反复”只是为了“强调”。而图像因为其“隐喻性”,在“驻足观赏”时,我们必须“反复”来解读其奥秘,对于它的认知方可达成。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文字是“幽玄”的能指和所指“胶合”在一起,可以精准意指。日本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盆景趣味”。简单说来,日本人喜好将自然和人生做缩微化的处理。究其根本,图像作为二维平面之物,尤其是放到日本如此“微缩”文化的语境下,想要表达三维的宽广世界,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语言文字的精准表达。这就是图像作为隐喻性符号的结构形态及其虚指性效果。
如上文所述的语言文本之“胶合”特点,图像因其本身的隐喻性也就是其本身的“虚指”想要精准表达其意时,便离不开文字的辅助。将莫里斯与赵宪章教授所论述的”甲虫“之喻进行结合思考。把汽车称为“甲虫”,就是在实物汽车身上加上一层隐喻之意,以此来说明汽车和甲虫相似。而“甲虫”本身就有实际意义,是一种实指,此刻变为了语象虚指。由此可以看出来,语言由实指滑向了虚指。而这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由“语象”所图绘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世界。文学语言就是这样通过“语象”中介和图像发生了必然联系[2]。
三、“虚实结合”中的“语图互仿”
上文谈了日本文本文字,我们不妨谈谈日本图像,也就是日本的绘画。日本早期的绘画是以佛画为代表的,毫无疑问,是从中国东渡而来。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便是:佛教绘画还有用图画解释佛经这一形式[11]。
由上文所述,文字的出现,人类摆脱“口传”走入“文本”,以文字强大的“实指”准确表达其意,这个是“虚指”的图像所做不到的。于是文字书写记录成了日本当时一个基本的形式。但是并不意味着图像退出历史舞台,如秋山光和所述图像在彼时的日本开始模仿文字。赵宪章教授论述道,“文本时代”语图关系的基本特点是“语图分体”,外在表现为图像对于语言的模仿。然而图像作为语言符号的记忆和叙述功能并没有消逝,它只是降格为文本语言的“副本”而存在。[12]即,文字的出现,我们进入了“文本时代”,这个时候文图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语图互仿”。
在《源氏物语》成书的平安时代,住宅内部都有隔板作用的滑门(日语汉字标记为“障子”)以构成房间,障子的内外两面都糊以纸或绸。房间的大小则可以用屏风来调整。这些形成家庭生活布景的屏风及障子上都饰以图面,起初是受中国感染的,用几句诗或是一段经文作为画题,并将诗句也一同书写在画幅上。其后日本式的诗和歌很快就代替了中国的主题,因此日本国内的一般生活及精神面貌也都反映在墙壁及屏风画上了。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献记载加以研究后,知道此种装饰墙壁的绘画在当时即被命名为“大和绘”,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形式的艺术称之为“唐绘”。
诸如《源氏物语》,这类小说从开始就有图画解说,以迎合当时贵族们的审美趣味。具体来说,这些贵族对于个人对图画欣赏力以及能正确地把她们自己描绘出来的绘画才能,都是非常自豪的。《源氏物语》中便有把物语故事制成绘卷欣赏的例子。
第二十五回《萤》卷中,紫姬看了《狛野物语》的画卷并称赞画工精良[4]。第十七回《赛画》卷中,藤壶母后出主意:将物语鼻祖《竹取物语》中的老翁和《空穗物语》(又名《宇津保物语》)中的俊荫这两卷画并列起来,教两方辩论其优劣。由此可以看出,“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在一个平面上虚实结合,也就是做到了“语图互仿”,其结果必然是和谐的。因为从《源氏物语》中还可以看出语图合二为一于一个平面上,已经融入彼时平安朝人们的生活中。
在第十三回《明石》卷中,源氏公子为了紫姬而不去见明石姬,源氏公子把日常感想题在自己所作画上,这些画中渗透了源氏的情思,很让人感动。巧妙的是,紫姬寂寞无聊的时候,也做了许多画,并将日常生活状况写在画上,集成一册日记,这或许就是心灵相通吧。大家可以想象两个人在生活中此般题画场景,由此可以看出,感想以文字的形式“题”写在画上并且看了又让人感动的力量,这必然是在“和谐”下才可以做到。第二十五回《萤》卷中,写到六条院内诸女眷寂寞无聊,每日晨夕赏玩图画故事。再到第四十七回《总角》卷,匂皇子看见大公主正在静静地观赏图画。……拿起散放在身边的画幅来欣赏。都可以看出来,“语图互仿”的形式以融入人们平常生活中。甚至,在第三十二回《梅枝》卷中,出现了诸如“歌绘”一词,“歌绘” 在日本平安时代很流行,是表现歌意的画,文字与画并行混合是其一大特点。
至于,图像和文字是哪家“仿”了哪家。《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中描写近来皇上晨夕披览的《长恨歌》画册背后隐藏着答案。文中后面还记载:这是从前宇多天皇命画家绘制的,其中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4]《长恨歌》画册属于“唐绘”,平安时代(794—1192)“唐绘”的实际作品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但各类文献中的记载却俯拾皆是,可称之为“文献中的唐绘”。《菅家文草》是日本平安时代以才学著称的诗臣菅原道真的作品,收录了468 首诗歌。《菅家文草》卷二和卷五的屏风诗诗序中还可看出日本制作“唐绘”屏风的过程。即先从《列仙传》《幽明录》《述异记》等中国典籍中摘抄出“本文”,再由画家巨势金冈作画,菅原道真作汉诗,书法家藤原敏行书写[13]。
由此可以看出,“文”与“图”之间的互动,即中国诗文为“唐绘”屏风提供了绘画内容,在中国诗文与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交融于“唐绘”屏风的过程中又催生了日本诗人的汉诗文,“唐绘”成为中国诗文和日本汉诗文之间的一种媒介[14]。所以可以得知,图文关系在文本时代是“图文互仿”“和谐统一”。
文字文本的“实”与图像绘画的“虚”相统一于一个平面上所表现的“图文互仿”是和谐的,但这份“和谐”不仅仅是形式上那么简单。千年之前的平安朝,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学习和大力输入中国文化的时期。从跨文化阐释角度看,能够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往往是被其他民族所阅读、理解和认可的[15]。上述提到的“唐绘”也好,“汉诗文”也好,其实本质上都蕴含两层意思。“唐绘”既指中国传来之绘画,也可以指日本绘制的中国题材画;同样“汉诗”既可以指中国传来之诗文,也可以指日本人用汉文创造的诗文。这两个词本身就蕴含着古代中日两国互动的历程。《桐壶》卷中,长恨歌画册是有中国题材的唐绘,在唐绘基础上还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可见,在《长恨歌》这一本属于“唐”的绘画空间中融会了和歌与汉诗两种文化符号[16]。
那么“和”文化与“唐”文化之间是以什么关系相处呢?我们可以从《源氏物语》中窥知一二。《赛画》卷中,称赞起《空穗物语》画卷,作者描述这画的笔法兼备中国、日本两国风格,趣味无可比拟之丰富,最后此画获胜。可知,在《源氏物语》中“和”“汉”两种文化符号构成了一种和谐美。这个现象与《源氏物语》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源氏物语》成书时代,“唐”文化依旧是一种权威,而“唐”依旧是彼时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未去过的异国,是一种超我的“理想美”。但同时,随着唐朝战乱,以及日本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源氏物语》的成书时代“国风文化”抬头,作品往往对“tíつfkし”的亲和美更为赞赏,对具有女性气质的“和文化”表现出亲切感和归属感。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与认知,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17]。如上文所述的“唐绘”以及“汉诗文”那样,“唐文化”的内涵已经远超其字面意思,本身也代表着一种“和”文化,即“唐文化”既是“他者”,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我们不妨用日本学者千野香织的图形(如图2)来解释:

图2
A 是唐文化,B 是和文化,而a 是和文化中的“唐文化”,b 是和文化中的“和”。而a,b 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互影响的。即便894 年,遣唐使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由此中日两国官方交流结束,日本汉文学逐渐呈现衰退趋势,但并不代表“汉文学”退出历史舞台,其在幕后依旧发挥着“唐土”的强大影响力。
语言符号的实指,让我们看到了文字,文学对于彼时日本人的强大影响。图像符号的虚指让绘画在文字面前处于“辅佐”的地位,但依然可以做到“虚实结合”统一于同一平面,在《源氏物语》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长恨歌》画册。画册表面是“文图互仿”,背后是“和汉并立”两种文化符号互相影响,这也构成了平安朝人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审美特点。
同时,在“和”与“汉”的互动中,我们也应该看出,日本人面对强大的唐文化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选择取舍,在本民族的思维体系中咀嚼消化,这个过程就是两种异质文学相互“对话”的过程。而在当今21 世纪,“对话”可以为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危机进行解答。当下,语图危机值得我们重视,同时自身的文化要想传播出去,真正的是要靠“影响”。只有通过“对话”而不是单方面“发话”,加深彼此间的了解,进而才会做到“影响”,中国文化才会主动“走出去”而不是“送出去”。语图危机,信息时代对于文字的“驱除”,我们需要重新坐着时光隧道,聚焦在过去作为“微型胶卷”的文献再构建“语图和谐”的世界,并伴随中华文化自信地“走出去”,“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飞向“和而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