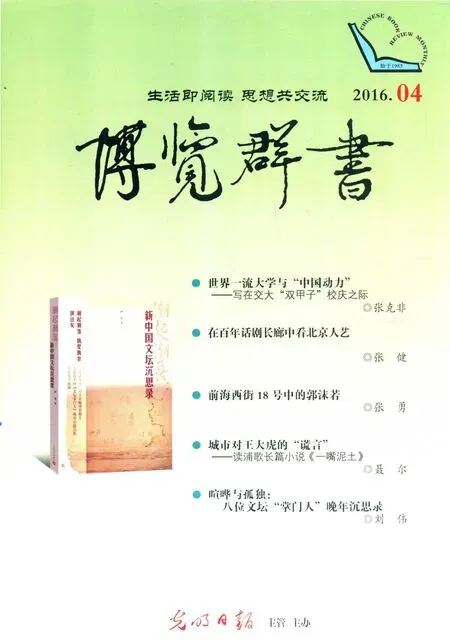和平年代再读《苦菜花》
2022-04-18咸立强
咸立强

长篇小说《苦菜花》是冯德英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加上后来出版的《迎春花》和《山菊花》,就是备受赞誉的“三花”。“三花”为作者赢得了无数荣耀,在特殊的年代里也因小说中男女关系的描写、人道主义的思想等受到了批判。冯德英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鲁迅在《小杂感》中寓言般描述出来的一种革命困境:“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歷史证明,冯德英的“三花”不是毒草,而是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就像作家自己说的那样,“因为比较真实,有感情有激情写的东西,这样打动了读者。”即便在当下和平的年代里,《苦菜花》也有让人一读再读的价值。
“三花”写的都是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的斗争生活。《苦菜花》开篇以诗意的笔触描写山东昆嵛山一带的四季美景。初读,我以为作者只是借景抒情,礼赞大好河山,以大地与植物隐喻生生不息的劳动人民,读着读着,发现作者另有目的。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任意在肥沃的山地上,繁密的草木中,埋上一块石头,做下一个记号,就可以庄重地宣布:这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山岭,属于他私有了。从此,别人再休想去动一草一木,掘一筐土、搬一块石头。
大自然的馈赠,自然里生长出来的财宝,本来应该为所有人共有共享,结果却并非如此。荒山有主!冯德英在《苦菜花》中说,“奇怪得很,就是有。”让人感到奇怪的不是没有荒山,也不是荒山有主,而是冯德英的那种感慨渐渐消失了,没有多少人为荒山有主感到奇怪,若是什么自然资源无主,才会让人感到奇怪。
1958年1月,《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初版发行。1959年,《收获》第4期刊登了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迎春花》。《迎春花》与《苦菜花》一样,开篇叙述的是昆嵛山美景,不同的则是《迎春花》从还乡团汪化堂偷偷溜进村开始写起。两种开篇,都是革命小说尤其是土改小说最常见的叙述模式。1959年,《收获》杂志第6期刊登了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创业史》第四章对任老四的叙述,与《苦菜花》的开篇很相似。任老四一家生活困窘,住的是草棚屋,东墙上破了一个大窟窿。在修补房屋的季节里,任老四却没有工夫修补自家的东墙,而是忙着给别人家打土坯,挣几个钱买粮吃。小说第四章叙述任老四走在街门外的土场上,“贪婪地吸着早春清晨的新鲜空气”,“他理直气壮地吸空气,因为眼前空气还没被什么私人所占有,不需要掏钱买,他怕什么?”接着又以饱含诗意的抒情文字写道: “温暖的初春的阳光啊!你从碧蓝的天空,无私地照着所有上身脱光的庄稼人打土坯。”让冯仁义和任老四痛苦的社会,就是一个资源被剥削阶级瓜分完毕的社会。占有资源的阶级,就有了剥削底层人民的资本。
阅读《苦菜花》《创业史》,看到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民只有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的权利,我的心就会为那些挣扎着生存的人民感到心酸,就想起孩子的图画书上讲述的狼和小羊的童话故事。狼想要吃小羊,就故意找茬,说小羊把他喝的河水弄脏了。小羊吃惊地说:您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弄脏呢?狼毕竟还是比人低级,没有宣布河水是他家的。《苦菜花》和其他革命文学经典相似,所有权问题都是作品表现的重心。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士大夫苦恼的是穷,底层老百姓痛苦的是贫。“物各有主”的社会里,“取之无禁”从来都是梦,穷苦人想要靠劳动换口饭吃,都要地主老财们的施舍,更让穷苦人心寒的,吃了地主老财们的施舍,无不加倍地还了回去。《苦菜花》叙述地主王唯一霸占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有讨饭的老太婆来要饭,女儿不给,儿子说:“给她吃点吧,反正她吃了,拉屎也要拉到咱地里,给咱当粪料。”讨饭的老太婆听了很生气,决心走出王唯一家的地盘,坚持走了一天半,实在憋不住才拉屎,原以为不会再便宜王唯一家了,结果一问,那里还是王唯一家的地!无产阶级想要避免当“粪料”的命运,靠走(逃避)是不行的,要像冯秀娟、冯德强一家子那样闹革命,翻身当家作主人,才有开始新生活的希望。
革命是浪漫的,浪漫的革命总是伴随着爱情。
最早的革命者,往往是社会的叛逆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由而不容于社会。《苦菜花》里的冯秀娟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的不容于社会,倒不是因为先有了革命的思想,而是因为她身体生长发育很“自然”。小说中写道:“为她高高丰满的胸脯和厚实的脚板,母亲忍受过许多风言风语的责难。”冯秀娟不裹小脚,这是她的罪过;冯秀娟不把胸脯束得平平的,也是她的罪过;冯秀娟背着枪和男人并排站在一起,也是她的罪过。冯秀娟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恋爱,但是像她这样的女子,不革命怎么能够得到爱情呢?即便是爱情降临,若是不革命,也必定只是悲剧。革命与爱情,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代表的却是人们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
人类社会的每次大变革,往往都肇端于男女两性关系,爱情便是男女两性关系最重要的体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一个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男女两性关系的变化。一百年前,倡导个性解放的国人,将自由恋爱视为个性解放的重要标志。《伤逝》中的子君终于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后,她就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叛逆者,和父母决裂了,与涓生同居了。尝过了自由与爱情的味道,子君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即便是回到从前的家,她也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自由恋爱就是对包办婚姻制度的背叛,就是传统社会和家庭的叛逆,也就成了新的一代踏上革命旅程的导火索。《苦菜花》等革命小说翻转了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传统叙述模式,讲述革命才有真正的爱情,革命旅程中发生的同志爱才是伟大的真正的爱情。与革命者炽热真挚的爱情构成对照的,则是王唯一、王竹等地主老财们赤裸裸的兽欲。不仅如此,《苦菜花》还特别塑造了杏莉母亲的角色。杏莉母亲深爱的情人是自家的长工王长锁,她的丈夫王柬芝则是小说中的头号大反派:
和第一个人在一起,她是活人,有灵魂,有理智,全身流动着血液。可是她时常不得不痛心地支开他,而去接受另一个的强迫。在这时,她是死的,没有了灵魂,也没有了感觉。
爱情属于有理想的革命者。
满身油垢身体消瘦的纪铁功抽空来寻赵星梅,他们两个走在乡间堤坝上,景色如画,几个挖野菜的孩子用银铃般的嗓子唱着歌:
柳树叶儿嫩又青
桃树花儿鲜又红
一个俊姑娘得了病
样样医生都请过
各种药儿也吃净
就是治不好她的病
哎吆吆
她得的是相思病……
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无上美景,都被作家用来衬托两位革命战士的深情:
纪铁功紧紧地搂抱着她那窈窕而健壮的腰肢。他感到她的脸腮热得烤人。她那丰满的富有弹性的胸脯,紧挤在他的坚实的胸脯上。他觉得出她的心在猛烈地跳荡。他领会到她体贴爱护他的一脉深情。只有在这时候,他才深深感到他们正在用血汗争取的幸福,他自己得到的比别人要多得多。
但接下来,《苦菜花》却让两个动了情的二十几岁的青年发乎情而止乎礼,讨论了结婚生孩子与革命斗争需要的关系,最后强化了“现在不能结婚”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强调两人不能发生男女两性关系。
舍小家为大家,把个人的爱情放在一边,先投身于国家民族的革命斗争中去,《苦菜花》这类革命文学的故事叙述既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再现,也是特定时代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思政要求。于是,我们看到冯秀娟和姜永泉入了洞房后,两个人紧紧地搂着对方,男的说:“想想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穷汉子,连个媳妇都说不上。而现在,你,你比谁都疼爱我!”女的说:“还提这些做什么呢。永泉!我还不是有你来才走上革命的路吗!这些都是有了党才有的啊!”然后,两个人共同回忆赵星梅等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最后决定“往后要更加劲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死去的同志”。
然而,《苦菜花》等小说创作在特殊的年代里遭到了批评。冯德英回忆说:
《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一些人认为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
警惕的结果,便是小说写得越来越干净。据冯德英、俞春玲《〈苦菜花〉及其他——冯德英访谈实录》可知,“文革”后,小说也经过了一番修改,“感情的東西都要删掉,不改出版社就不能出。”性并不肮脏,男女爱情本就美丽。当年被批为自然主义与色情的部分,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写出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人的多种面相。事过境迁之后,本能方面的文学书写出现了强烈的反弹,王安忆的“三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让性回归性,爱情中夹杂的空洞说教随同秦波那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都成了历史。有真挚的理想做底子,理想就是激情,让爱情超越兽性,获得升华,因志同道合而尽显高尚可贵。
《苦菜花》的结尾,八路军救出了被鬼子抓去的母亲。冯德英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太阳、旗帜和苦菜花:一轮红日从朝霞中欢笑着跳出来,万道金光普射着暴风雨后清新的原野;火红的旗帜在半空中哗哗地飘扬,红旗那艳丽血红的光芒向四外普射开来;在母亲眼中,最吸引她的不是那粉红的月季花,暗红色的芍药花,而是加在这些大花中的金黄色的苦菜花,看着看着,母亲觉得眼前一片金光,到处都开放着苦菜花。太阳是红日,旗帜是红旗,大花都是红色系,然而,红日放出的是万道金光,红花中夹着的是金黄色的苦菜花,苦菜花让母亲觉得眼前一片金光。浩然写的长篇小说就叫《金光大道》,社会主义的大道就是金光大道。红色中透出来的是金光,红色寓意革命与牺牲,金光代表的则是幸福与美好。借景抒情,万物皆著我之色,冯德英通过小说中母亲的视角,写出了光明的未来。
革命的目的就是驱逐暗夜迎接光明。光明是革命的许诺,这个许诺也得到了验证。革命小说往往以革命的胜利作为结尾,这既是理想的寄寓,也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事实的客观陈述。始以悲剧,以正义获胜结束,这样的叙事带有乐观主义的精神。面对未知,迷茫、绝望与虚无于事无补,精神上的内耗更容易让人坠入深渊,适度的自信与乐观精神有助于人们从原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中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悲剧是好的,革命中有数不清的悲剧,但红色经典大多并不选择悲剧式结尾,而是选取光明式的结局。革命追求胜利,革命文艺往往也以光明的结局指引人民前进的方向,胜利与光明便是依然热爱生活的象征。无论是《白毛女》,还是《小二黑结婚》,都对故事中人物原型的命运进行了加工处理,悲剧变成了喜剧。革命是要让人活的,革命文艺的结尾处理便是给革命的人民以胜利的希望,这是黑暗社会里透进来的一缕光。贵妇人们总是喜欢悲剧,自以为高雅,有时只不过是因为早已麻木的心灵需要强烈的刺激。凄惨的打工者们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并不只是为了麻醉自己,更多的是坚信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身在泥淖,依然仰望美好,以便让自己继续热爱生活。世上最厚的障壁,是人心与心之间的隔膜。喜欢悲剧的,认定光明式的结尾廉价,一些搞喜剧的喜欢恶搞光明式的结尾,实际上借此遮蔽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与奋进,将革命的人民之革命的根源和理想一并虚化掉了,这是我们今天重读冯德英的《苦菜花》等作品需要自醒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