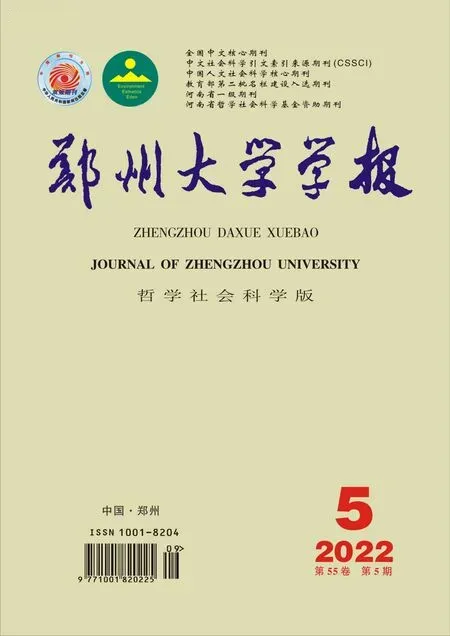作为文化共同体标识的“美国亚裔文学”
2022-04-16刘向辉
刘 向 辉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美国亚裔”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概念,其创造者为美国日裔学者市冈裕次(Yuji Ichioka)和艾玛·吉(Emma Gee)。1968年夏,在“你是黄种人吗”大会召开之后,时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的市冈裕次和艾玛·吉牵头成立美国亚裔政治联盟(AAPA),首次公开使用“美国亚裔”一词,以便取代对亚裔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东方人”称谓。从诞生伊始,“美国亚裔”便是一个极具活力和鼓动性的术语,它迫使人们重新定义自己和正视身边的政治议题,也在许多不同领域为人们看待世界和改变世界开启了新方式[1](Piii)。在社会政治层面,它标志着美国亚裔作为一个泛族裔和种族集体身份的出现[2](P821)。作为一个概念,美国亚裔暗含着一种共同的意识和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亚洲文化,也不是美国文化,而是美国亚裔文化。在界定自我身份和文化的过程中,美国亚裔把之前针对压迫亚裔共同体的孤立无效抵抗联合成一致的泛亚社会变革运动[3](P1),并激发了黄色权力运动的兴起[4](P8)。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的现实条件下,泛亚意识并没有在美国亚裔族群中得到广泛传播,只是停留在一些致力于族裔政治学的美国中产阶级亚裔的理念中, 并成为族裔社团领袖维护本集团利益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策略[5](P81)。而与“美国亚裔”这种具有政治联合意义的泛族裔化标签对立的“东方人”称谓依然存在。新旧两种声音的并存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美国亚裔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在文学批评领域,一方面,以“美国亚裔”为标识的文章和文学选集开始出现,并有不断增加之势;另一方面,以“东方人”为标识的文章和族裔文学选集仍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学界对“美国亚裔”与“东方人”两种标签的并置使用说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美国亚裔文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传统势力的博弈中曲折前进的,是对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构建的一种文学化折射。
一、“他者”言说: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萌发
自1968年被公开使用以后,“美国亚裔”逐渐进入到了文学领域。较早使用“美国亚裔文学”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杰拉德·哈斯勒姆(Gerald W. Haslam)。他不仅于1969年在《亚利桑那季刊:美国文学、文化和理论杂志》上发表了使用“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微妙的脉络:美国亚裔文学》,而且于1970年编写了一部设有“美国亚裔文学”板块的美国族裔文学选集《被遗忘的美国文学篇章》。在这部涵盖美国印第安文学、美国非裔文学、美国犹太裔文学等众多族裔的综合性文学选集中,哈斯勒姆收录了早川一会(S. I. Hayakawa)、艾米·李(Amy Lee)、金恩国(Richard Kim)、林语堂(Lin Yutang)等11位美国亚裔作家的作品,并把他1969年发表的文章《微妙的脉络》作为亚裔文学部分的标题和导言,这是“美国亚裔文学”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文学选集中。
在《微妙的脉络》中,哈斯勒姆对亚裔作家与美国主流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评价。他认为,美国文化向来很少受到亚洲作家成就及其传统的影响。这种对亚洲传统的忽视,以及对亚洲语言文化差异的明确承认,致使美国文学对某些世界最古老、最优秀文学的影响产生一种不良的迟钝感[6](P79)。为此他呼吁美国主流文学关注被长期忽视的亚裔文学,并通过编选少数族裔文集来补充和丰富传统的美国文学研究,以证明美利坚是一个多样化、兼收并蓄的民族[7](Pvii)。哈斯勒姆还指出,与美国的其他“少数族裔”群组成员不同,亚洲血统的美国人与他们伟大的亚洲文化遗产保留着某种联系,尽管他们难以具备充分融入亚洲文化的条件[6](P79-81)。哈斯勒姆点出了亚裔依恋祖籍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但他认为大多数美国亚裔文学作品并未脱离欧洲的影响,这也正是哈斯勒姆后来在赵健秀的文章《唐人街牛仔的自白》中被谴责为“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重要原因。在赵健秀看来,哈斯勒姆等人完全把亚裔文学当作没有自我独立声音的边缘文学,最多是美国知名作家在酣睡中构建美国梦的小拼图[8](P58-70)。
哈斯勒姆对“美国亚裔文学”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亚裔”和“美国亚裔文学”的社会辨识度,对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仍然有一批学者在论著中继续使用“美国东方人”“美国东方文学”等话语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他者”化建构,如麦伦·西蒙(Myron Simon)的文章《族裔作家和主流文学》、梅尔文·戈德伯格(Melvyn Goldberg)的文章《美国族裔文学:高中课程的一种新路径》等。这些学者与哈斯勒姆一样“呼吁关注亚裔文学等族裔文学”,也希望“少数族裔文学成为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9](P1318),但却在有意无意中把亚裔文学习惯性地称为“美国东方文学”。这种现象在1969年莉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和芭芭拉·布拉德肖(Barbara Bradshaw)编写的教科书式文集《为我们自己代言:美国族裔文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前言中,两位学者指出该书的目的是向大学生全面系统介绍不同族裔背景的美国作家,并试图通过与美国主流代表作家的对比来展示族裔作家的贡献。在她们看来,这些少数族裔群体都面临着适应美国生活的重要问题,其中不少族群的身份被贬损为一种污蔑性称谓[10](Pxii-xiii)。但悖论的是,在她们为少数族裔遭受的贬损与蔑视伸张正义的时候,她们仍然把费里斯·高桥(Ferris Takahashi)、山本久枝(Hisaye Yamamoto)、张粲芳(Diana Chang)、林语堂等亚裔作家称为“美国东方作家”。尽管如此,“美国亚裔文学”作为一个名称已经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借助亚裔文学作品的集中编选等手段,证明了“美国亚裔文学”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存在,为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的萌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自我”言说: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亚裔学者的“自我”言说是指站在自身族裔立场来构建美国亚裔文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美国亚裔的社会地位,而这正是“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意识觉醒的表现。自1969年旧金山州立学院设立第一个美国亚裔研究项目,特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于1969-1970学年成立美国亚裔研究中心(AASC)之后,广大亚裔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著述中使用“美国亚裔”这一概念,以便在学术层面推动美国亚裔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是艾米·立木(Amy Tachiki)等编写、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亚裔研究中心出版的《根:美国亚裔读本》(以下简称《根》)。作为美国亚裔研究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11](P43-44),《根》的目的在于探究美国亚裔面临的“根源”问题,鼓励读者基于人类状况的语境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去思考对比美国亚裔的经历,进而满足美国亚裔的特定需求[12](Pvii)。虽然《根》是一部主要关注美国亚裔身份和历史的综合选集,但对美国亚裔文学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关注。在《美国亚裔的响应与变革:检视美国亚裔文学》中,布鲁斯·岩崎(Bruce Iwasaki)不仅以“美国亚裔”身份明确使用了“美国亚裔文学”名称,而且从“美国亚裔”的立场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美国亚裔经历一直是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因此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不为人知的事实不足为奇。……但是从过去到现在美国一直都有值得关注的亚裔作家。美国亚裔的文学主题可以反过来阐明美国亚裔文学的接受过程……正如对美国亚裔(实际上是所有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研究是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对美国亚裔文学的检视可以揭示美国白人的排外性文学传统。”[13](P89)岩崎一方面指出了美国亚裔文学不为人知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指出了美国亚裔文学不仅在整个美国文学语境中没有关注度,而且与同为少数族裔文学的犹太裔文学、非裔文学和本土裔文学相比也明显处于下风。为此,检视美国亚裔文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挖掘美国亚裔文学的独特价值去批判美国主流文化传统的排外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代言”。首先,他通过介绍野口米次郎(Yone Noguchi)、何塞·加西亚·维拉、金恩国、赵健秀等21位作家来证明美国亚裔文学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借以说明美国主流社会排斥美国亚裔文学的不争事实。其次,他通过呈现诸多美国亚裔作家的多样化书写来反映不同类型的亚裔经历。当然,岩崎没有停留在只是肯定美国亚裔文学的层面,也指出了美国亚裔文学面临的问题。比如他认为语言问题是了解劳森·稻田(Lawson Fusao Inada)和赵健秀作品价值和局限性的关键。因为劳森·稻田和赵健秀都反对使用白人主流社会期待的矫揉造作言辞,主张使用一种符合亚裔社会生活实际的创造性语言。这固然体现了两位作家鲜明的族裔立场,但最终会陷入模仿东方经典、黑人修辞和白人俗语的困境。因此,他们只是在回应主流文化的成见,而没有正视解决美国亚裔共同体真正的根源性问题[13](P97)。
继布鲁斯·岩崎之后,第一部对“美国亚裔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当属1972年许芥昱(Kai-yu Hsu)与海伦·帕鲁宾斯卡斯(Helen Palubinskas)合作编写的《美国亚裔作家》。该书第一次以文学选集的形式集中呈现了之前已有近80年发展历史的美国亚裔文学,不仅为之后“美国亚裔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发出了重要声音,而且为后来诸多美国亚裔文学选集的编写提供了重要借鉴,更重要的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践行了亚裔行动主义思想,有力声援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亚裔运动[14](P82)。该书的最大意义不只在于收录了刘裔昌(Pardee Lowe)等22 位“美国亚裔作家”,更在于第一次对“美国亚裔作家”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即“具有丰富美国生活经历的亚裔作家”。这些作家依照“优先顺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作家;第二类是指年轻时移居并常住美国的作家;第三类是指创作始于菲律宾但在美国通过出版英语作品成名并经由美国人推介给菲律宾人的菲律宾作家。许芥昱和帕鲁宾斯卡斯同时指出,限于空间制约以及其他因素,他们的选集只能收录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作家的作品[15](P1)。至此,“美国亚裔文学”不再是一个缺乏具体所指的名称,而是一个有具体范围和特定标准的文学类别,这对美国亚裔文学的独立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不管是岩崎在文章中对“美国亚裔文学”的主题内容进行概括,还是许芥昱等在选集中对“美国亚裔作家”的范围进行界定,都是站在美国亚裔自身的视角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积极言说与主动构建,其主要目的在于借助文学手段挖掘呈现具有整体意义的美国亚裔文化,而这充分彰显了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三、共时言说:文化共同体意识的确立
在《美国亚裔作家》出版之后,被称为“唉咿!集团”的赵健秀、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劳森·稻田和徐忠雄(Shawn Hsu Wong)在《亚洲问题学者通报》上联合发表了论文《唉咿!美国亚裔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唉咿!》)。在这篇慷慨激昂的论文中,“唉咿!集团”把许芥昱和帕鲁宾斯卡斯在《美国亚裔作家》中界定“美国亚裔作家”的实践进行了深化推进。他们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亚裔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包含美国华裔、美国日裔、美国菲律宾裔等几个族群的联合体。”[16](P34)他们界定的“美国亚裔”虽然只包括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三个族裔类别,但增强了“美国亚裔”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意义。他们强调了美国亚裔的感情特点,认为这是一种既与亚洲人和美国白人有关但又与他们明显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凝聚着亚裔在美国长期被主流社会压抑和忽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惨痛经历。在需要通过甄别作家的实际出生地和情感出生地来界定“美国亚裔”身份时,“唉咿!集团”倾向于情感出生地[16](P34-35)。这种既注重作家出生地又注重作家美国亚裔感性的标准凸显了“美国亚裔作家”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正是构建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的核心纽带,也是美国亚裔用来抵抗白人种族主义压制的重要武器。在“唉咿!集团”的界定框架下,只有雷霆超(Louis Chou)、张粲芳等切实反映“美国亚裔感性”经历的作家才被称为“美国亚裔作家”,像林语堂、黎锦扬(C. Y. Lee)、野口米次郎、卡尔·贞吉·哈特曼(Carl Sadakichi Hartmann)等只是美国化的亚洲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只是利用东方新奇元素短暂影响了美国文学,而根本没有提及“美国亚裔”[16](P36)。
作为一篇论文,《唉咿!美国亚裔文学导论》在深入分析美国亚裔历史与美国种族歧视机制的基础上对“美国亚裔”“美国亚裔作家”进行了独创性界定,为“美国亚裔文学”的独立建制提供了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思想路线。1974年,“唉咿!集团”历尽艰辛出版《唉咿!》后,《唉咿!美国亚裔文学导论》这篇论文作为《唉咿!》的序言和导论不仅迅速成为学界热议的对象,而且几乎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的代名词。正是《唉咿!》序言和导论引发的热议,促使不同族群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共时言说,进而强化了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共时言说并非意味着不同族群对“美国亚裔文学”概念、范围等具体范畴的一致性认可,而是说他们都在承认“美国亚裔文学”存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多元化言说,其中既有褒奖之词,也有诋毁之语。
1975年美国非裔学者伊斯梅尔·里德(Ishmael Reed)在春季号《党派评论》上的书评中把《唉咿!》序言誉为“美国亚裔文艺复兴的宣言” [17](P319)。同年,科罗拉多大学的菲利普·海斯(Philip L. Hays)在书评中认为“唉咿!集团”为美国亚裔文学创作发布了一个宣言,而这个宣言赋予了入选作品力量和生命。他们的序言和导论不仅追溯了美国亚裔文学传统,而且有力揭穿了文化同质化的文学主题[18](P124)。由于批判精神过于犀利和文风过于辛辣,《唉咿!》也遭到了不少攻击。1975年11月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的书评中不仅对《唉咿!》中的历史谬误进行了嘲讽,而且对全书的结构安排、族裔涵盖范围、作家收录范围、学术规范、语言措辞等进行了严厉抨击[19](P57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对《唉咿!》的评论不管是褒还是贬,都是在承认“美国亚裔文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即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美国亚裔文学”的合法性。最具说服力的是,费德曼和布拉德肖1975年再版《为我们自己代言:美国族裔文学》时把1969年版本中的“美国东方作家”一律改为了“美国亚裔作家”。
学界对“美国亚裔文学”的承认与接受离不开“美国亚裔”学者的集体努力,特别是1974年几部“美国亚裔”文集的集中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亚裔文学”的崛起和独立,使得美国亚裔文学从沉默走向了发声[20](总序P8)。在《唉咿!》出版之前,华裔学者王燊甫(David Hsin-Fu Wand)已经编选了《美国亚裔传统:散文与诗歌集》。徐忠雄和赵健秀则借助里德等人创办的杂志《菜鸟读物》合编了一期美国亚裔专刊,即《菜鸟读物(第三卷)》。这三部文集遴选“美国亚裔作家”的标准虽然存在差异,甚至对“美国亚裔”本身的界定也有分歧,但这只是美国亚裔的“内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诸位编辑“在大历史中融入个人” [21](P61)的书写观,并不影响他们对“美国亚裔”“美国亚裔文学”的集体无意识认可与宣扬,因为他们拥有“在美国文学中确立‘美国亚裔’声音”的共同使命。相比较而言,虽然《美国亚裔传统》和《菜鸟读物(第三卷)》没有像《唉咿!》一样把编选作为一种力量在文学中去构建属于美国亚裔传统的意识或自觉,但这三部文集在同一年集中出版产生的合力却对“美国亚裔文学”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都是美国亚裔以文学为媒介构建文化共同体的见证。正是这三部选集的接连出版,促使“美国亚裔文学”达到了某种成熟水平[22](P135),而这种成熟是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确立的重要标志。
四、结语
自从1968年“美国亚裔”一词出现以来,作为其衍生词的“美国亚裔文学”历经几个阶段终于得到确认。1969年哈斯勒姆在论文《微妙的脉络》中使用“美国亚裔文学”一词,为从文学层面构建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契机。1972年许芥昱和帕鲁宾斯卡斯出版的第一部美国亚裔文学选集《美国亚裔作家》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了初步界定,为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做出了表率。1974年出版的《唉咿!》以热议的形式为“美国亚裔文学”赢得了广泛关注,增加了“美国亚裔文学”的社会辨识度与认可度,为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的确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与“美国亚裔”一样,“美国亚裔文学”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被美国主流社会长期忽视的文化传统,因此“美国亚裔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重新发现的,是被以亚裔为主的广大学者构建的。
重新发现与构建“美国亚裔文学”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而是一个涉及种族、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关乎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虽然1974年之后学界基本承认了“美国亚裔文学”的用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对“美国亚裔文学”本身的认可与接受。“美国亚裔文学”要成为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美国亚裔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