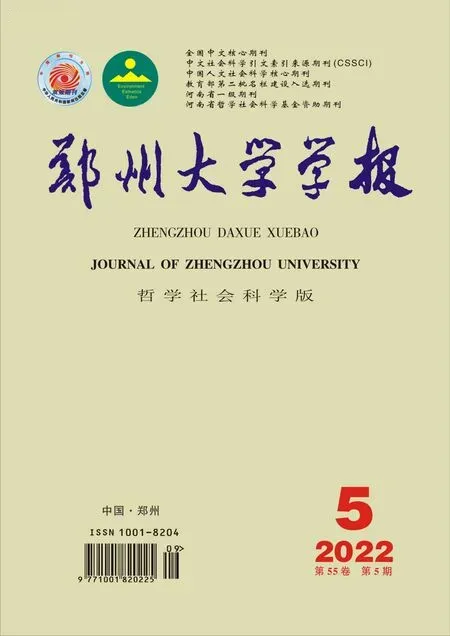论《楚辞》在汉代的接受与经典化
——以《远游》相关争议为中心
2022-12-10孟莉莉
王 允 亮 孟莉莉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在汉代文坛上,《楚辞》是众人关注的热点。《楚辞》一书以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为核心,附之以汉代士人的拟作,经刘向汇总编纂为十六卷定本,后经扬雄、班固、贾逵、马融等人的推阐,直至王逸集大成式的《楚辞章句》出现,其在汉代文坛上的经典地位终于确立。《楚辞》的接受与经典化,与屈原形象的确立有密切关系。作为楚国的宗臣,屈原因其清忠洁白的品格及自沉汨罗的悲剧命运,深受汉人的敬重与同情。随着屈原地位的逐渐上升,由于丰富其人物形象的需要,很多《楚辞》中无确定作者的作品,被有意无意地归之于屈原名下,成为确立其崇高形象的佐证,这一情况以《远游》一篇最为典型。《远游》旧传为屈原所作,然其文中透露的信息却显示此文当作于西汉时期,它之所以被归入屈原名下,与《楚辞》在汉代经典化的大背景有关。因此,本文拟从此入手,梳理《远游》的作者与写作时代,并结合汉代《楚辞》接受的大背景,剖析其被认定为屈原之作背后的原因及意义所在。
一、《远游》的作者问题
《远游》为《楚辞》中的一篇,其主题与《离骚》相类,多表现主人公神游四海八荒之意趣,历来认为是屈原所作,如汉代王逸即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1](P1925-1926)
因《远游》一文与司马相如之《大人赋》语言上多有雷同,故历代学者在以《远游》为屈子所作的前提下,多有认为《大人赋》为模袭《远游》而成者,如宋洪兴祖:“司马相如《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其妙处相如莫能识也。”[2](P415)又如明汪瑗:“《大人赋》非独不能窥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闯其门也,况升堂入室乎?其所述远游杂乱靡统而又剽袭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读者有凌云之意,盖未尝读《楚辞》故也。使武帝曾读《楚辞》,则读相如之赋如嚼蜡耳,吾见其昏昏唯恐其卧之不暇也,安得有飘飘凌云之意乎?若张衡《思玄赋》其命意措词文体间架是全篇学夫《远游》者也。”[2](P416)又如清朱乾:“屈子《远游》为游仙诗之祖。君子重其志而玮其词,谓其才可辅世,而忠不见谅于君,无所控诉,托配仙人,东南西北入于无何有之乡,千古悲之。相如拟之而为《大人赋》,志在于投世主之好,其文则丽,其志则淫。此邪正之分也,学者于此可以识去就矣。”[3](卷14)但以《远游》为屈原所作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先不说《远游》文中有非屈原能作的矛盾之处,就以《史记·司马相如传》载汉武帝览《大人赋》而“飘飘有凌云之气”来说,《汉书·淮南王刘安传》载,武帝初年,刘安朝见武帝,武帝命其作《离骚传》,可见武帝接触楚辞类文学甚早,远在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之前。如《远游》真为屈原所作,武帝应该早已见过。若其与《大人赋》高度雷同,武帝再看《大人赋》的时候怎么还会有“飘飘有凌云之气”这么大的反应呢?如果说汉武帝作为帝王都没有见到的《远游》,却为司马相如得到并拟之成文,这种逻辑是很难讲得通的。
故而,后之学者转而认为《远游》乃模拟《大人赋》之作,如清吴汝纶:“此篇殆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其文体格平缓,不类屈子。世乃谓相如袭此为之,非也。辞赋家展转沿袭,盖始于子云、孟坚。若太史公所录相如篇数,皆其所创为。武帝读《大人赋》,飘飘有凌云意。若屈子已有其词,则武帝闻之熟矣。此篇多取老、庄、《吕览》以为材,而词亦涉于《离骚》《九章》者,屈子所见书博矣。《天问》《九歌》所称神怪,虽宏识不能究知。若夫神仙修炼之说,服丹度世之旨,起于燕齐方士,而盛于汉武之代,屈子何由预闻之?虽《庄子》所载广成告黄帝之言,吾亦以为后人羼入也。”[4](P495)
《远游》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不同之处,也被学者注意到,并成为否定其为屈原所作的证据,其中以清人胡浚源为最力:“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虽《天问》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蜺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旧列为原作,非是。”[4](P491-492)
胡氏以此为据,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怀疑:“史明谓读《招魂》《哀郢》,又谓作《怀沙》之赋,《哀郢》《怀沙》俱在《九章》内,则《招魂》与《九章》皆原作可知。惟《远游》一篇,史所不及载,《汉志》屈原赋二十五篇,计二十五篇之数,有《招魂》则无《远游》,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其数乃合。大抵《远游》之为辞人所拟,良是。细玩其辞意亦然。”[4](P492)他甚至认为:“《远游》一篇犹是《离骚》后半篇,而文气不及《离骚》深厚真实,疑汉人所为。此亦如《招魂》之与《大招》,细玩知有不同。此篇若以赋游仙,则深洞玄旨,后世谈修炼家言断无能出其右者。若道屈子心,似反达怀,忧解愤释矣。朱子病其直,非惟直也,病乃太认真。盖《离骚》之远逝,本非真心,不过无聊之极想,而兹篇太认真,转成闲情逸致耳。”[5](P1898)
除胡浚源外,怀疑《远游》非屈原所作者还有近人姚永朴和今人王泗原。姚永朴认为:“太史公《屈贾传》赞云:‘读《离骚》诸篇,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又云:‘读《服鸟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按:《远游》与《服鸟鸟赋》同一旨趣,扬子云《反离骚》云:‘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观于《远游》,又何尝弃由、聃之所珍乎?” [5](P1902)王泗原认为:“辞句呢,袭《离骚》的不少,有的整句抄,并大仿司马相如《大人赋》。《史记索隐》引张华云:‘相如作《远游》之体,以大人赋之也。’这是因果颠倒。相如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若《远游》前此已有,汉武的飘飘然就不待《大人赋》。汉武帝于辞赋是内行,下过功夫的。相如蒙不过汉武帝,当然更不敢蒙。《大人赋》而袭《远游》,这个天子绝不会大悦。所以这篇不但不是屈原作,也决不是先秦的文辞,如《卜居》《渔父》之比,断然是汉人所作,且在司马相如以后。即使在汉人的楚辞中,格调也是卑的。”[6](P310-311)除这些学者之外,当代学者刘永济、胡小石等也都认为《远游》不是出自屈原之手,乃是后人的伪作(1)刘永济以为《远游》所言与屈原思想不合,乃后人伪托之作,见刘永济《屈赋通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页;胡小石以为伪托当出汉武之世,见胡小石《远游疏证》,收录于《胡小石文录》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103页。。
除了逻辑上的推演外,《远游》文本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对认定它为屈原所作非常不利。如《远游》中曾言“奇傅说之得星辰兮,羡韩众之得一”,此处“韩众”为谁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对于韩众的身份,王逸在《楚辞章句》里并没有解释,只是说了一句:“众,一作终。”[7](P164)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引《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 [7](P164-165)但是,《列仙传》一书的来历其实也有问题,虽其旧题为刘向所撰,但《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所撰书目不言有《列仙传》,故《四库全书总目》撰者疑其为魏晋间方士所为 [8](P1248)。因此它关于韩终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人因仙人传说附会出来的,可信度并不高。其实,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名为韩众的人,他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9](P319)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又载:“始皇闻(卢生等)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9](P325)《史记正义》云众“音终” [9](P326),则两处所言韩众、韩终实乃一人。顾颉刚认为,韩众是围绕在秦始皇身边为他求药的燕齐方士之一,后来畏罪逃亡,不知所踪,后人因而附会出仙去的传说,他其实就是《远游》中提到的“韩众”[10]。顾氏的这种推测是合理的,梁刘孝胜在具有神仙色彩的《升天行》诗中曾写道“少翁俱仕汉,韩终苦入秦”,足证仙人传说中的韩终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韩终实为一人[11](P920)。因此,《远游》一文的写作年代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后。
近来有学者论证《远游》中的韩众跟《史记》中所载的韩众并非一人,因为历史之韩众为人所恨(见谷永之上书),《远游》韩众为人所羡,故各是一人[12]。但这种观点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历史形象与神话形象上的不同,并不能否定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最有名的如《离骚》引傅说为殷贤相,《远游》复引傅说以为仙人,如此不同用法,难道是说傅说有两人吗?更典型的则是刘安,他在历史上因谋反自杀,后世也有他成仙而去的说法,故而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的传说,我们难道可以认为传说中的刘安和汉朝的淮南王毫无关系吗?其他像汉武帝、东方朔这一类由历史人物而被附会神话的人物甚多,所以,以此来否定《远游》韩众与《史记》韩众毫无关系并不能够成立。因此,从韩众这一信息来看,《远游》不可能出现于屈原时代,应该是秦以后的人拟作。
二、《远游》的写作时代
《远游》因和《大人赋》高度雷同,经常被拿来作对比。对于二者的关系,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大人赋》乃模仿《远游》而作。另一种则认为《远游》实出于《大人赋》之后,为模仿《大人赋》而作,如清吴汝纶等即持此种观点。郭沫若因《远游》和《大人赋》相类,甚至提出过《远游》为《大人赋》初稿的说法[13](P205)。以上种种,足以说明《远游》和《大人赋》间的密切关系。
从武帝看到《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的反应来说,我们认为《远游》不可能出现于《大人赋》之前,再从两处细节上来看,《远游》更应该是模仿《大人赋》之作。
首先,《远游》在描述主人公周游天下时曾有“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一句,这是主人公结束南方巡游转往东方漫游的一环,但这一句却极易滋生误解。明人汪瑗在解读此句时说:“太皓,东方之帝也。自南方而北面视之,则东方在右,故曰右转。……或曰,‘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二句,是言自南方而游东方,下三句是言将自东方而游西方也。自南而东乃曲行,故曰右转。自东而西乃直行,故曰径度。下文‘风伯为余先驱,氛埃辟而清凉’即申‘前飞廉以启路,阳杲杲其未光’二句之意耳。其说亦通。”[2](P406-407)从汪氏所言的“或曰”来看,因表述上的含混不清,《远游》这句话的解读并不确定。“太皓”即“太昊”,于五行属东方之帝,作者在主人公结束南方巡游时,明明说“吾将过乎句芒”,句芒为东方之神,则是准备往东方游历,自南视北,东方居右,故有右转之言。但太昊本居东方,又何须右转呢?“历太皓以右转”一句,不仅方向不明,也和上句“吾将过乎句芒”所言自相矛盾。汪瑗虽引或曰之说进行补充,却掩盖不了这句话晦涩难通的事实。《远游》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实原因应该是,它出自对《大人赋》的生硬模仿,《大人赋》有“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一句,两篇文章里都有“以右转”的描述,但是《大人赋》先是在北方游历,由南视北,东方居右,由北方右转正好到东方,其下所描写的也是在东方所游历的景象:“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湟。厮征北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而《远游》在模仿《大人赋》时,却忘了和自己上下文的协调,故而造成相互违戾的结果。
其次,《远游》中还有一例类似的情况,文章主人公在南方巡游时,作者有这么一句描述:“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一句话也颇令人费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说:“海若,海神之号,《庄子》有北海若。冯夷,河伯也,一曰水仙也。《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亦曰:‘冯夷得道,以潜于大川。’盖海若尊而冯夷卑,故令海若而命冯夷舞也。或曰,本谓令海若冯夷舞耳,曰‘令海若舞冯夷’,错文以成章也。”[2](P412)汪氏对此处提出了两种解读方式,一种认为作为神灵海若尊于冯夷,所以“令海若舞冯夷”即为通过海若命令冯夷而舞也;另一种则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句法结构方式,认为“令海若舞冯夷”即为令海若冯夷舞。但这两种解读均属推测,并无十分可靠的证据。所以也有其他学者觉得汪氏这句话解读有问题,认为“令海若舞冯夷”之“冯夷”为舞名,与上文“使湘灵鼓瑟”相对[14](P585-586),但冯夷为河神之名众所周知,解为舞名虽新人耳目却于古无据,所以这种解释也不能让人信服。种种歧见表明《远游》这句话本身就存在着问题,而之所以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存在着对《大人赋》的机械模仿。《大人赋》中有与此句相似的一句:“奄息葱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远游》的“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与此句有着直接联系。但是在《大人赋》中“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灵娲、冯夷各司其职,表述得明明白白,《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虽然将《大人赋》中的一句拆分成两句来表达,却反而更加夹缠不清,迂曲难通。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大人赋》和《远游》在字句上虽极相似,但在同样的地方,《大人赋》用的自然明白,《远游》却存在逻辑矛盾、表述含混等问题,这足以说明《远游》作者在创作时存在着对《大人赋》的刻意模仿,所以才会出现顾此失彼、词不达意、表述含混等毛病。换句话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是《远游》模仿了《大人赋》,而不是《大人赋》模仿《远游》,《远游》的出现应在《大人赋》之后。
这就牵涉到《远游》的作者和创作时间。首先,《远游》作者应为淮南王刘安身边的士人。《楚辞》与淮南王国关系密切,因淮南都城寿春曾为先秦旧楚之都城,故其地多楚文化之遗存。武帝亦因其故,当淮南王刘安入朝时,命其为《离骚传》。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楚辞》一书的产生与淮南有着密切关系。章太炎即言“《楚辞》传自淮南”[15](P549)。姜亮夫亦言“自《离骚》至《招隐》为书,必刘安之所为”[16](P398)。汤炳正也认为淮南王国文士之撰作,乃《楚辞》成书过程中之关键一环[17](P97-102)。同样,《远游》一文,也和淮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远游》中有“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一句,对于其中涉及的乐曲《咸池》《承云》《九韶》等,一直众说纷纭。王逸于此句下注云:“思乐黄帝与唐尧也。《咸池》,尧乐也。《承云》即《云门》,黄帝乐也。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时还车,将即中土,乃使仁贤若鸾凤之人,因迎贞女如洛水之神,使达己于圣君,德若黄帝、帝尧者,欲与建德成化,制礼乐,以安黎庶也。美尧二女,助成化也。《韶》,舜乐名也。九成,九奏也。屈原美舜遭值于尧,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内之大麓,任之以职,则百僚师师,百工惟时,于是遂禅以位,升为天子。乃作《韶》乐,钟鼓铿锵,九奏乃成。屈原自伤不值于尧,而遭浊世,见斥逐也。”[1](P2045-2047)宋洪兴祖于此句下注云:“《周礼》有《大咸》,尧乐也。《乐记》云:‘《咸池》备矣。’注云:‘黄帝所作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为言施也。言德无不施也。’又《吕氏春秋》云:‘帝颛顼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淮南》云:‘有虞氏其乐《咸池》《承云》《九韶》。’注云:‘舜兼用黄帝乐。’御,侍也。《孟子》所谓‘二女婐’也。《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周礼》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7](P173)朱熹则云:“《咸池》,尧乐。《承云》,黄帝乐,又曰颛顼乐,又曰有虞氏之乐,无所稽考,未详孰是。二女,娥皇、女英也。”[18](P110)汪瑗解曰:“张者,设而陈之也。《咸池》,王逸、朱子皆注为‘尧乐’。奏者,举而作之也。《承云》,王逸曰:‘即《云门》,黄帝乐也。’又曰颛顼乐,又曰有虞氏之乐。朱子亦莫能考定也。瑗按:《礼记》注曰:‘黄帝乐名《咸池》,尧乐名《大章》,舜乐名《韶》,禹乐名《夏》,汤乐名《大濩》,武乐名《大武》。’与此又不同,未知孰是。二女,娥皇、女英,尧之女、舜之妃也。御,侍也。《九韶》即舜乐。歌,歌咏也。言使二女侍侧以歌咏《九韶》之乐章也。《离骚》曰‘舞《韶》’,此曰‘歌《韶》’者,盖乐有歌有舞,单言之者,盖举此以知彼,而文互见也。”[2](P412)可见,关于《咸池》《承云》《九韶》的归属莫衷一是,至于这些乐曲为何会被作者联系在一起,更是无法考校,二女为何在此出现也令人困惑。其实,《淮南子·齐俗训》里有一句话,对于这句话的解读有直接的作用:“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但传统认为《远游》乃屈原所作,对它与淮南文化之间的联系往往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存有这种先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远游》这句话用了《淮南子》中舜的典故,不仅乐曲的名字一模一样,不需要臆测转换,而且舜娶尧之二女娥皇、女英为妃在这里也对应得上。由于忽视了这一点,所以过去的解释往往迂曲难通,无法令人信服。

“间维”之外,正如陆时雍在《楚辞疏》中所言,《远游》结尾“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儵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的表述,在《淮南子·道应训》中也能找到相类似的表述“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瞩”。从二者的表述来看,《远游》无疑是在《淮南子》的基础上做了增饰,前者由后者转换的痕迹非常明显。又《淮南子·道应训》中曾载:“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毂之上。”高诱注云:“(卢敖)秦时燕人,始皇召为博士(即诸生),使求神仙,敖亡而不反。”此处高诱以卢敖为秦始皇之博士,因求神仙亡而不反,至汉时被附会为神仙。有意思的是,《远游》曾提到的另一个神仙韩众,其原型也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因求仙不返,至汉时被附会为仙人。两人身份相似,经历相类,后世形象也相差无几。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作为仙人形象出现的时间也大致相近,《淮南子》中卢敖作为仙人出现的同时,韩众也作为仙人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远游》与《淮南子》代表的淮南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远游》与《大人赋》内容上虽较相类,思想基调上却大相径庭。《大人赋》主要表达人间君主高升远引的仙游想象,故其思想基调多夸奢靡丽,想象浪漫宏伟。《远游》虽也以仙游为主题,其缘由却在于躲避世间之迫阨,同屈原一样,《远游》作者也有对尘世生活的诸多不满。此外,由于《远游》同淮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武帝时期淮南王国周围的士人群体,一方面因刘安自身与中央皇室之间有两世血仇,隔阂甚深,处于惴惴不安之中;另一方面随着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加强,宾客游遨于诸侯王之间已引起武帝侧目,淮南宾客之盛更为当日中央所疑忌,故而这群人虽附庸于刘安,表面上以探求方术为生活,精神上却顶着巨大的压力。《远游》开篇“悲时俗之迫阸兮”,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由《远游》与《大人赋》之关系看,《远游》当出于《大人赋》之后,故其文有对《大人赋》之模仿。《大人赋》约作于元狩五年左右(公元前118年)[20],而刘安于数年前(公元前122年)已自杀身亡,因淮南王谋反案在当时影响巨大,武帝以此为契机对诸侯王势力穷追猛打,淮南宾客此时之生存环境可想而知。刘安在世时这些人尚有朝不保夕之感,等到他因谋反而畏罪自杀时,作为失败者的关联群体,这群宾客的处境更可想而知。在这种压抑紧张的氛围之下,借抒写仙游以抒发精神压力亦属自然。由此看来,《远游》应出于淮南宾客之手,表现的是这个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压力。因淮南文化的熏染,及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影响,使得《远游》呈现出一种杂糅的特色。这些失意群体赋写篇章只为抒发愤慨,本无意于扬名,故其文字并不讲求工拙,多与《离骚》《大人赋》等相同,也没有留下更多的作者信息,使得作者暗眛不彰。直到刘向编录《楚辞》时,因其与《楚辞》文风接近,才将这样一篇无名氏的文本编选进去。后人出于篇章解读的需要,不免要为其拟定作者,讨论起创作缘由,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其为屈原所作渐成共识。
三、《远游》与《楚辞》的汉代接受及经典化
王逸的《楚辞章句》中,除了他自己的注解之外,还吸收有汉代的旧注。这些旧注最为特殊的地方,是采取韵文的形式作注,被后世称为韵体注。这些注解基本四字一句,两句一韵,节奏整齐,特色鲜明。《四库全书总目》已注意及此,其卷一百四十八集部“楚辞类”《楚辞章句》下云:“《抽思》以下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韵。如‘哀愤结縎,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结屈,如连环也’之类,不一而足。盖仿《周易·象传》之体,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陈鸿图更从音韵学的角度将此认识推进一步:“传统以来,一般认为韵文注出自东汉王逸之手,但上文各例只得阳、耕同用倾向于东汉,但如鱼部家、华的合用则表现出西汉时期的押韵特征,这是东汉以后难以模仿的用例。这些部分如果照小南一郎楚文圈的传承,就可能是前人遗留的旧训,值得加以重视。”[21](P293)在对韵体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学界逐渐认识到它是流行于王逸之前的民间旧注。
《远游》中韵体旧注贯穿全篇,与王逸的注文有明显区别。如“奇傅说之托辰星兮”,下注云:“贤圣虽终,精著天也。傅说,武丁之相。辰星、房星,东方之宿,苍龙之体也。傅说死后,其精著于房尾也。”其中前面“贤圣虽终,精着天也”属于韵体旧注,后面对于傅说和辰星的注释用散体语句,为王逸附加的注释。相同的情况还有“绝氛埃而淑尤兮”,下注云:“超越垢秽,过先祖也。淑,善也。尤,过也。言行道修善,所以过先祖也。”前面八字来自韵体旧注,后面的散体文字出自王逸之手。这种情况说明在王逸之前,《远游》已经有了不少注解,而且按照注解用韵的特色考察,这类旧注可能出自西汉中晚期,比王逸生活的时代要早很多年。
在这些旧注中,《远游》已经被和屈原联系起来了,如“悲时俗之迫阨兮”旧注云“哀众嫉妒,迫胁贤也”,“遭沈浊而污秽兮”旧注云“逢遇暗主,触谗佞也”,“免众患而不惧兮”旧注云“得离群小,脱艰难也”,“忽临睨夫旧乡”旧注云“观见楚国之堂殿也”,“仆夫怀余心悲兮”旧注云“思我祖宗,哀怀王也”,其中文句注释所提及的楚国、怀王、暗主、被嫉妒等关键词,都和屈原的生平及作品所言一致,这种做法显示出以《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潜在逻辑。
拟定作者的过程是作家形象建构的一部分。古代篇章多不著录作者,故对篇章作者的拟定多出后人之手。对于这一现象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如余嘉锡即云:“古书既多单篇单行,刘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为若干篇,作者既不自署姓名,则虽同题为某子,本非一人之笔,其间孰为手著,孰为口传,孰为依托,必有不可得而辨者。”[22](P219)“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22](P157)书既如此,赋亦宜然,所以很多赋的作者序言之类信息都是后人添加的,清人王芑孙即云:“西汉赋亦未尝有序。《文选》录赋凡五十一篇……两汉赋七篇,其间有序者五篇。《甘泉》《长门》《羽猎》《长杨》《服鸟鸟》,其题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自序之作, 始于东京。”[23](P336-337)而《远游》之所以被认为是屈原之作,一方面因其文风与屈原相类,另一方面则是由汉代的屈原接受所决定的。熊良智先生曾经描述过这种现象:“《史记》所载《招魂》《渔父》的作者与《楚辞章句》不同,以及《楚辞章句》中《惜誓》《大招》的作者传说的不同,可以看出早期著述的特点和传播特点。著述不自署名,又多先后成于众人之手,流传又多单篇别行。”[24](P267)又言:“作品单篇别行,又不自署姓名,则编纂结果只能依据成书者的认同与判断。《招魂》因司马迁认同而为屈原作品,因王逸认同而为宋玉作品,《渔父》因司马迁、刘向之书而成屈原事迹,因王逸而成屈原著述。”[24](P250)与此相同,《远游》被定为屈原之作,也与汉人对屈原的接受有关。他们出于对屈原的崇慕与认同,不自觉地将作者不明的作品附会于屈原身上,以丰富其文学创作的内容,构建其仙游不息、上下求索的形象,抬高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行为。
屈原是《楚辞》文学形成的核心,汉代的《楚辞》接受,也围绕着屈原形象的构建而展开。曹建国通过考察汉代的咏屈赋、拟骚作品等,归纳出了汉代屈原形象变化的脉络:“西汉的屈原更像是神仙家的形象,在遭受不公待遇之时,便可以远游辞世,沉身汨罗也只是成仙之人的蝉蜕而已。到了东汉,随着思想一致时代的来临,屈原及屈赋解读的神仙之思逐渐淡化,甚至如班固以儒家经义为标准,对屈赋中所体现的神仙观念进行了批判,屈原之死也成了彰显君恶的罪状。最终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标志,对屈原及屈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于是神仙之思变成托物比兴,‘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的神游变成了‘怀念楚国,思慕旧故’的陪衬,这都是为了凸显屈原的‘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与之同时,《离骚》称‘经’,而屈原之死也被赋予了大勇大德之儒家伦理意义。”[25]纵观整个汉代,屈原形象有从神仙向忠臣变化的特点,这说明屈原形象在汉代的接受并非固定僵化的,而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被形塑构建,诚如熊良智所言:“屈原的历史地位,虽是由他的诗歌创作决定的,却是在汉代的文学思想中发生的。”[24](P206)正是屈原形象的日益崇高化,成为《远游》被归于屈原名下的大背景。
汉代的屈原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今可考者来说,对屈原及其作品有明确接受的人包括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傅毅、王逸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刘向与王逸二人。刘向以屈原作品为核心,将相关作品汇总并编纂为十六卷本《楚辞》,据王逸《楚辞章句》所述,这个是最早的《楚辞》文本。除了屈原的作品之外,《楚辞》还收录了宋玉的《九辨》、贾谊的《惜誓》、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作品,体现出了一定的编纂宗旨。这个经典文本的出现,为汉代《楚辞》学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相传《楚辞》古本《离骚》篇题后有“经”字,很多学者都认为《离骚》称经为刘向所为。明王世贞曾经评价过刘向的这种行为:“梓《楚辞》十七卷,其前十五卷,为汉中垒校尉刘向编集,尊屈原《离骚》为经,而以原别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东方、严忌、王褒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调者为传。”[26](P166)
当然,《离骚》称经是否刘向所为,今天已无法详考。但《离骚》称经是汉代《楚辞》学史上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刘向被与之联系起来,足见其在汉《楚辞》学中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出现了汉代《楚辞》接受史上集大成式的作品《楚辞章句》,此书当为王逸任东观校书郎时所作[27](P200)。据其《楚辞章句序》所言,之前的《楚辞》学虽有一定的成绩,然也有各种不足:“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当代学者蒋天枢曾经评价过王逸所做的工作:“叔师依十六卷本《楚辞》作《章句》,叙不依例列全书后,而厕《离骚》之末者,《离骚》旧题曰‘经’。统贯全书;而作叙之意主在屈原,与‘缵述其词’者无预也。自谓‘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所识所知’‘楚人以相教传’之旧说,其说出自屈原赋流传以来所积累之笺识,亦即《章句》中所备采之说,而‘稽之旧章。合之经传’,则于‘所识所知’之外,更参考刘安、班固、贾逵各家《章句》,并博考群书,以定著十六卷《章句》。”[27](P200)
可见《楚辞章句》是王逸在吸收前期《楚辞》学基础上的汇总之作。除了作《楚辞》学知识上的融汇整理之外,王逸还在《楚辞章句序》里对当时存在的以班固为代表的贬低屈原及《离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一方面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另一方面讲到屈原的作品,他也极力赞扬:“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可以说,虽然均持儒家之义进行裁决,但班固和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王逸的观点表明,即使不那么符合儒家经义之道的屈原及其著作,经过长期的磨合、接受、阐释,在东汉时也已经被确立为士人之楷模,成为大家效仿学习的对象了。
综而言之,《楚辞》之所以在汉代能发生巨大影响,端因其核心作者屈原及其核心作品《离骚》正好契合了汉代士人的心灵需要。徐复观曾总结其原因:“《离骚》在汉代文学中所以能发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出身于丰沛的政治集团特别喜欢‘楚声’,而不断加以提倡。另一方面的更大原因,乃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象征着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投汨罗以死’的悲剧命运,象征着他们自身的命运。”[28](P253-254)
随着《楚辞》在汉代的接受与经典化,它也被时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解读、阐释,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及《楚辞》的经典意义也逐渐被阐发出来,汉代士人“不遇中的焦虑,胁迫中的凄惶,失落中的抗争,期待中的回望,在屈原的遭遇和楚辞中都有了异代知音的共鸣与同情,这几乎成为古今中国社会知识阶层共通的人生情结。由此表明,文学传播是一种历史的构成,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历史也是现实构成的一个平台”[24](P360)。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作家的经典形象被逐渐建立起来,相应的增饰与附加自然必不可少,与之相关的经典文本也逐渐形成。《远游》本来是西汉中期无名士人对《离骚》及《大人赋》的拟作,但因屈原的巨大影响力,它在被收入《楚辞》之后,继而又被认定为屈原所作,成为形塑屈原形象的有力资源。《远游》在汉代的出现及解读,正是经典作家推动经典文本形成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