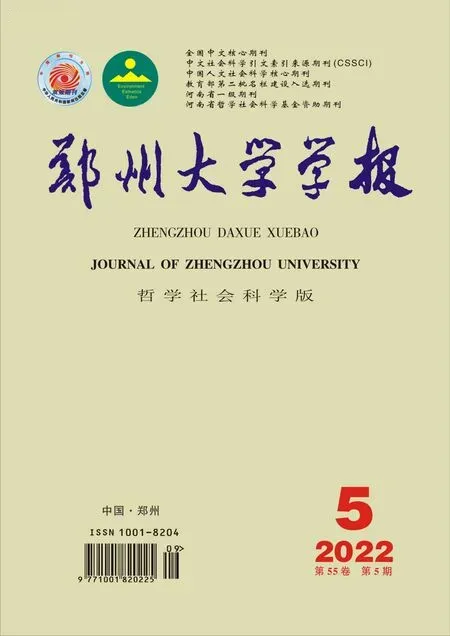百年《城堡》 漫漫长路
——卡夫卡《城堡》主题新论
2022-04-16曾艳兵
曾艳兵 李 爽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2.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3.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卡夫卡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有原创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城堡》则是卡夫卡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卡夫卡最有厚度和力度的作品。人们通常认为,《城堡》写于1922年1月至9月,迄今恰好百年。叶廷芳先生说:“《城堡》是卡夫卡创作风格成熟和定型的标志,在哪个意义上讲都堪称作者的‘压轴之作’。”[1](第3卷,P1)像卡夫卡其他两部长篇小说一样,《城堡》也没有写完,并且在卡夫卡写给布罗德(Max Brod)的遗嘱中,该小说也在应被焚毁之列。然而,布罗德慧眼识珠,将卡夫卡杂乱无序的手稿整理出来,于1926年出版。此时卡夫卡已经去世两年了。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论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说:“一本像《堂吉诃德》这样的书脱离了作者的意图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它对每一个喜欢它的时期都展现出一幅新面孔。”[2](P419-420)卡夫卡的《城堡》恐怕更是如此。一百年来,它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传播,也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对每一位读者和研究者几乎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一、众说纷纭的《城堡》
我们并不知道卡夫卡创作《城堡》的确切起止日期,因为没有确切的材料加以证明。我们只知道,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给布罗德朗读过《城堡》的开头部分,由此证明该小说应该写于1922年年初,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卡夫卡应该在1922年9月停止写作这部小说,因为9月11日卡夫卡在写给布罗德的信中明确表示:“看来我必须永远地撂下那个城堡故事了,自赴布拉格一周前发生那次‘崩溃’以来,再也无法衔接,尽管在普拉纳写下的篇章并不完全像你读的那么差。”[1](第7卷,P50)卡夫卡的疾病再次爆发,他的思路和精力显然已经难以衔接,顾不上这部小说,只好彻底放弃了。
如今,一百年过去了,就像《城堡》中的主人公K.毕其一生之努力就是想进入城堡一样,卡夫卡的读者也殚精竭力想走近《城堡》,进入《城堡》,成为卡夫卡的朋友和知音。那些卡夫卡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更是试图进入《城堡》的中心,洞察和把握《城堡》的精髓,揭示和阐发《城堡》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不停地阅读、解析、阐释、研究卡夫卡,呈现出多重图像交叉重叠、相互渗透、变幻多端、色彩纷呈的情景。
《城堡》显然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小说,它的故事非常简单:自称为土地测量员的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城堡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关于小说的结局,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在该书的《第一版后记》中写道:“结局一章卡夫卡没有写。”当布罗德问卡夫卡小说将如何结尾时,卡夫卡说:“他(K.)不放松斗争,但却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时总算下达了城堡的决定,这决定虽然没有给予K.在村中居住的合法权利,——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村里生活和工作。”[1](第3卷,P335)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仅此而已。与小说的故事情节相比,主人公K.七天里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活动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小说共20章,主要描写了K.七天里的思想意识活动。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前七分之一是描写前三天半的时日,后七分之六是描写后三天半。“这意味着K.和读者将以每天15~20页的篇幅等待着,尔后在第七天突然加快速度,以一天100多页的篇幅了结这次等待。”[3](P340)
《城堡》的主题是什么?小说中的城堡,“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式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许多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城镇。”[1](第3卷,P8-9)“城堡”的寓意是什么?卡夫卡为什么要写作《城堡》而最终又没有完成?一百年来人们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法国学者梭拉(Denis Saurat)认为:“《城堡》是一部寓言,我认为这部作品远远胜过他的其它作品。但是故事中并没有片言只语透露寓言的意义。它没有提供任何哲学的暗示;有的只是一系列不可理解的事件,文笔极其简明,写得非常令人信服。读者的心一下子被故事的荒诞性吸引住了,并想象出一幅与故事平行发展的梦境。”[4](P45)追求《城堡》的真正寓意正如追求终极意义一样,往往最终会失去真正的意义。美国学者考夫曼(Walter Kaufmann)说:“当我们一读再读《城堡》一书的开头,并把它和印在书尾的变化多端的开头相比较,事情就变得十分的清楚,那就是卡夫卡用尽他的方法去排斥单一注释的任何可能性。暧昧就是他的艺术本质。”[5](P122)《城堡》既在排斥注释,又在呼唤注释。
如何阐释卡夫卡的作品?美国当代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反对阐释》中写道:“卡夫卡的作品一直经受着不下于三拨的阐释者的大规模劫掠。那些把卡夫卡的作品当作社会寓言来读的批评家从中发现了卡夫卡对现代官僚体制的层层阻挠、疯狂及其最终沦为极权国家的案例研究。那些把卡夫卡的作品当作心理分析寓言来读的批评家从中发现了卡夫卡对父亲的恐惧、他的阉割焦虑、他对自己性无能的感觉以及对梦的沉湎的种种绝望的显露。那些把卡夫卡的作品当作宗教寓言来读的批评家则解释说,《城堡》中K.试图获得天国的恩宠,而《审判》中的约瑟夫·K.经受着上帝严重而神秘的法庭的审判……”[6](P10)相对于桑塔格所说的“三拨阐释者”,美国杰出文学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说得更加简洁清晰:“卡夫卡的主题,无外乎以下三种:俄狄浦斯情结或自惭形秽的内疚感;官僚专政或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上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或我们与上帝缺场的关系。”[7](P145)《城堡》的主题当然也不外乎是这几个方面,只是前后的顺序似乎正好可以颠倒过来。
二、“城堡”是天国或上帝的“恩宠”
“城堡”就是天国或者上帝的“恩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他将卡夫卡的遗作整理发表,也是最早解读阐发卡夫卡作品的人。他将卡夫卡的作品看作是宗教式的神谕。他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侯,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是有效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8](P292)卡夫卡的“城堡”在于表明:尘世和宗教世界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永远也无法走近或理解上帝,就像K.永远也无法走进城堡一样。人类愈思索,上帝离他就愈远。
犹太神学家格索姆·索勒姆(Gershom Scholem)将卡夫卡看作是一个超越神秘主义的犹太神秘主义者,是36位先知之一,杰出的犹太哲学家。他说:“尽管他本人没有意识到,(卡夫卡)作品是卡巴拉世界观的世俗再现。所以,今天的许多读者都从这些作品中看到耀眼的宗教光环——暗示了已经变成碎片的绝对。”[9](P128)卡夫卡俨然成为了一位犹太神秘主义小说家。
德国当代思想家、艺术家汉斯·昆(Hans Kung)和文学评论家瓦尔特·延斯(Walter Jens)认为,《城堡》里面并没有什么宗教——“城堡”不可能是“天堂”,不能与神恩相提并论;村子也不可能是“人的世界”。但是,《城堡》虽然不是一部直接关涉宗教的作品,却是一部宗教意味浓郁的作品。“《城堡》这部作品旨在描写一个人,即土地测量员K.想在一处以前‘从未有人居住过’(恩斯特·布洛赫语)的地方获得居住权,也就是说,他想居住在一个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相互和解的世界里。”[10](P311)也就是说,《城堡》关涉的是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关系。卡夫卡表达的是一种神秘的超验体验,一种走进神或接近神的体验。“超验始终是神秘的,讳莫如深的,令人恐惧的,但它仍然向人敞开了一条道路,并没有使希望成为不可能。”[10](P292)
卡夫卡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但他是一位坚定的信仰者,一位祈祷者,准确地说,是一位怀疑的祈祷者。“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11](P364)他将写作当成一种祈祷方式。在犹太教中,“祈祷是一种‘仪式’——‘内心’的仪式,这与在圣殿里通过牺牲举行的仪式是相互对照的,祈祷词教导我们通过每日的祈祷来‘尊崇’上帝。……祈祷需要内心的投入,是心而不是嘴唇,祈祷不仅仅是话。按《诗篇》的语言讲,它是一种‘心灵的洋溢’,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呼喊’。”[12](P76-77)“祈祷改变着祈祷者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希伯来语‘祈祷’(tefilla)一词的词根是‘判断’的意思,因此,‘tefilla’一词本身就有‘自省或反省’的意思。在祈祷中,人们会更好地了解自身并取得精神上的发展。”[12](P80)卡夫卡的祈祷更多的不是面向上帝、面向神,而是面向自我、面向内心。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反对从神学角度诠释《城堡》,他认为:“这种诠释忽视了上层世界令人厌恶而又令人恐惧的方方面面,所谓‘得天独厚的王国’。”卡夫卡不是一位先知或者是某种特殊智慧的恪守者:“卡夫卡没有成功地将虚构变为学说。毋宁说卡夫卡是道德箴言的创造者,他将‘无以复加的神秘与无以复加的纯朴融为一炉’。”总之,卡夫卡的作品是“一种个人和艺术的毁灭”[13](第7卷,P334)。
三、“城堡”是官僚专制机构的隐喻
许多学者将《城堡》看作现代社会的寓言或者官僚专制机构的隐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考夫曼认为,卡夫卡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卡夫卡所描写的就是上帝死亡之后个人的存在,普遍意义失落后人类对意义的追寻。《城堡》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寓言。法国当代作家丹尼尔-罗普斯(Daniel-Rops)说:“卡夫卡深深根植于人类生活的悲剧之中,他那无比清晰的作品,足以描摹出人类彻底破碎的形象。较之于仅仅停滞在心理意义的普鲁斯特,或总是试图用神话术语和语言魔力进行创作的乔伊斯,卡夫卡的探索无疑又前进了一步。正因为极度的痛苦吞噬了他,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痛苦,卡夫卡才成为了与虚无抗争的现代人的最忠实的、悲剧性的见证者。”[14](P184)美国作家奥登(W. H. Auden)认为,卡夫卡的《城堡》是描写现代人的危机——现代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从不留意世界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世界只不过是个人意图与欲望的投影而已,所以他只听从他自己。
还有学者指出,《城堡》描写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叶廷芳说:“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看起来就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它的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15](P81)小说的主题就在于对“城堡里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暴虐和腐化荒淫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描写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15](P82)。《城堡》是批评官僚制度的:城堡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仅仅是对我们世界历史状态的现实的比喻。城堡是权力,它不是“双面神的王国,在那里上帝可以扮演魔鬼,魔鬼可以扮演上帝”[16](P59)。城堡是一个清晰可见的统治制度,其目的是保证权力的稳固。在这里,每个阶层都不愿作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地绕着,绕到最后又绕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正如小说中村长所说:“对一个像伯爵衙门这样的大衙门来说,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个部门发出这一项指令,另一个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相不通气的事,虽然上一级的监督检查是极为严格的,但检查很自然地往往晚到一步,于是总会出点小差错,当然毫无例外都是在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事上出错……”[1](第3卷,P54)城堡是一个迷宫式的机关,人们既逃不出来,也进不去,并且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秘密。
这座地上的“城堡”其实非常类似于地下的“地洞”,正如语言的迷宫非常类似于世界的迷宫。“他(卡夫卡)常常自认为是一个不健全的人,这种不健全导致了他对极端的寻求:高度和深度,围墙和地洞,阁楼与昆虫。在这方面,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测量员,实际上是《城堡》中的K.所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3](P335)卡夫卡就像一个探测人类灵魂的测量员,他进入了这座灵魂的迷宫,但却无法进行明晰精确的测量。城堡是一个封闭的迷宫,正如灵魂的容器总是有限的,但进入城堡的路却是无限的,正如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灵魂的最深处。“可以说,《城堡》虽指向无限界,但仍不愧为一部描写内心世界的意识流小说。”[13](P339)“在一个重新建构的时间和空间之内,自由与监禁的如此混合标志着内封闭的特点,这显然是《城堡》的主题。”[3](P341)
四、“城堡”是精神分析的寓言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城堡》就是一部精神分析的寓言,一部自传性作品,就是卡夫卡的精神成长史。在心理分析学家看来,卡夫卡完全可以作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学说的病案例证来分析论证。卡夫卡的著作都是一些密码,只有通过弗洛伊德式的钥匙才能破译这些密码。“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城堡”与K.的关系不过就是“父与子”的关系。小说不仅表现了父子冲突,还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既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敬爱。就卡夫卡而言,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自传体作品。
《城堡》的中心思想就是目标无法抵达,理想难以实现。城堡矗立在山上,高高在上,阴森庄严,可望而不可即。当K.来到山脚下的村庄时,城堡已经在眼前了。“K.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K.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1](第3卷,P3)K.当晚寄宿在桥边客栈。第二天早晨,K.走出客栈,他在明澈的空气中看清了城堡的轮廓。K.动身前往城堡。因为下雪,同时又因为通往城堡的路绕来绕去,因此,城堡虽然近在眼前,但K.却始终无法抵达。K.自称是城堡聘请的土地测量员,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承认,实际上他也没有土地可以测量。他既不能进入城堡,也不属于附属城堡的村子。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改变现状。他始终就是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
这种“目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也许就是卡夫卡对自己爱情生活的概括和总结。最初在与菲莉斯·鲍尔(Felice Bauer)的爱情关系上,卡夫卡就曾哀叹目的不可能达到。卡夫卡曾将自己比作一个攻克不下城府的“可怜的将军”,而菲莉斯有时就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1913年4月1日,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害怕我们手拉着手走过整个世界,看上去亲如一人,但到头来全为虚幻泡影。简言之,我害怕的是,虽然你可能冒着危险深深弯下腰来靠近我,而我却还是永远被拒于您的门外。”[1](第8卷,P266)菲莉斯是柏林一家公司的职员,卡夫卡认识她时她24岁。卡夫卡与菲莉斯有五年的恋爱史,曾经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1917年7月,卡夫卡因肺结核病发作而解除婚约,他与菲莉斯从此各奔东西。1919年3月,菲莉斯与卡夫卡分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她嫁给了柏林的一位富商。卡夫卡与菲莉斯渐行渐远,最终彻底分手。菲莉斯就是卡夫卡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城堡”。
1919年1月22日,卡夫卡认识了28岁的捷克犹太姑娘尤丽叶·沃利切克(Julie Wohryzek)。尤丽叶是布拉格鞋匠、镇上的犹太教堂仆役的女儿。她从商业学校毕业后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工作。尤丽叶应该属于卡夫卡理想中的妻子形象,他们认识不久就订婚。正当卡夫卡准备和尤丽叶共同生活时,1920年1月4日卡夫卡收到了一封署名密伦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的来信,后者准备将卡夫卡的《司炉》翻译成捷克语。随后卡夫卡与密伦娜进入热恋之中。密伦娜给布罗德写过八封信。布罗德认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恩斯特·波拉克)。”[17](P220)密伦娜曾经告诉布罗德,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她产生兴趣。小说中弗丽达在奥尔加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嫉妒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尤丽叶·沃利切克的态度。所以,在某些传记学家看来,《城堡》中的弗丽达就是卡夫卡的密伦娜,她的丈夫波拉克则成了小说中的克拉姆,而阿玛利亚则是卡夫卡的第二位未婚妻尤丽叶。
1920年4月卡夫卡写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城堡》的雏型,或者说是《城堡》的一段试笔:“当你想要有人引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时,你会先去找一个共同的熟人,请求他帮个忙。如果你一个都找不到,你会忍耐,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地方,这种机会是不会没有的。如果今天没有,那么明天一定会有。如果不出现这样的机会,那么你也不至于就这样动摇了世界的支柱。假如一个家庭能不在乎没有你,那么你至少不会更在乎没有这个家庭。这些本来是不言自喻的,只有K.无法理解。最近他心血来潮,想要闯入我们的地主家庭去,却不是通过社交的路线,而是愣干。也许他觉得通常的那条路太迂回漫长,这是对的,可是他想要走的那条路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此并不想夸大我们的地主的作用。他是个善于理解人的、勤劳的、值得尊敬的人,但也仅此而已。K.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呢?他想被雇佣在地主庄园里吗?不,他没有这种想法,他自己是富有的,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是爱上了地主的女儿吗?不,不,他跟这种怀疑丝毫沾不上边。”[1](第4卷,P140-141)
K.想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一个地主之家,但他不走社交路线,不走平常路,而是径直走去。平常路虽然绕道较远,但直道却是一条死路。卡夫卡的《城堡》就是这个小故事的拓展和延伸——渴望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寻找一个安宁祥和的归宿。写这则小故事时,卡夫卡与密伦娜正情投意合,他唯一怀疑的是自己是否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一年后卡夫卡开始写作《城堡》,此时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走到了尽头,卡夫卡建立家庭的愿望彻底落空,于是,通向城堡的路也就被彻底阻断了。在卡夫卡看来,明明有通向城堡的路,但是却无法抵达城堡。
1921年4月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结束,也就在这时或稍早一些时候,卡夫卡开始写作《城堡》。这个月中旬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写道:“有一半姑娘的身体引诱我,我寄予希望的那个姑娘的身体根本不诱人。只要她(F)摆脱我,或者只要我们是一个人(M),这只是来自远方的威胁,说远也根本不远。一旦发生任何一件小事,就完全破裂。为了我的尊严,为了我的高傲,显然我(虽然他看上去还如此恭顺,是一个点头哈腰的犹太人!)只能爱高高在我之上、我够不到的东西。这自然就是整体的核心,这整体可怕地增长着,直到叫人‘恐惧得要死’。”[1](第6卷,P303)
卡夫卡在这封信中总结了他与菲莉斯、密伦娜等人的爱情关系。卡夫卡认为,他所爱的人总是高高在上,摸不着,够不到。目标虽有,有时尽管近在眼前,但又遥不可及,生命就在这种蹉跎中悄悄逝去。所以说,《城堡》就是这一情感和思想的结晶,是卡夫卡从一系列失败尤其是爱情生活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核心。
五、结语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卡夫卡《城堡》进行阐释和分析,其中每一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但未必充分;每一种说法都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当然,将所有的观点综合起来也未必就是《城堡》的全部意义。《城堡》还是那座“城堡”,它屹立在山顶,看得见,似乎近在咫尺,却永远也无法触及,更不用说进入城堡中心了。法国哲学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认为,《城堡》写的就是“一个在陌生国度的人徒劳地寻求工作和家庭安定幸福的故事”[18](P203)。而在这一寻求过程中,寻求本身成为了目的,以往的目的则变成了手段。游荡的需求变成了主人公生命的极限。所以,每当有机会留在村庄或接近城堡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而使他离城堡愈行愈远。如此看来,《城堡》仿佛就是一部人类漂泊历史的缩写。
总之,《城堡》是一部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小说过渡的作品。它在表现形而上欲望、表现我们时代的精神苦难和困境以及从这种困境中救拔出来的理想上,就像是《浮士德》的现代版。当然,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共同倾向。但比较其他现代主义作品,《城堡》的绝望似乎来得更为彻底和绝决。K.为争取进入城堡,争取社会的承认,自始至终不懈地斗争,尽管几乎没有希望和任何可能,但他从未屈服,绝不放弃。《城堡》的主题虽是悲观的,但并不绝望。目标之路虽无法可循,但并不放弃寻找、探索和奋斗。
美国作家乔伊斯·欧茨(Joyce Carol Oates)在《卡夫卡的天堂》一文中写道:“这部作品(《城堡》)出色地反映了意识的头脑对无意识无望的斗争,也反映了理智为了认识自己的灵魂如何进行漫画式的奇特搏斗。许多读者猜不透这部作品的用意,也对它不满意,这只能说明作品的基本论点同我们时代的基本论点大相径庭。不过,在《城堡》中可以说卡夫卡同样表现了老子叫作道的原始力,所不同的,卡夫卡是从欧洲人的、历史的观点,以晦涩、阴沉的笔法来表现。城堡显然就是处于永恒的、静态的或者无目标的真理,只有在静止了的、不知进取的思想中才得以认识。”[19](P696-697)在欧茨看来,《城堡》的精妙之处在于表现了中国老子的“道的原始力”。这样一来,那些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读者岂不是更容易理解《城堡》的深意和精髓?比较文学学者,由于“所关注的东西与其他文学专家所关注的东西有所差异”[20](P112),他们对于卡夫卡研究不仅具备独特的优势,而且还可以开拓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