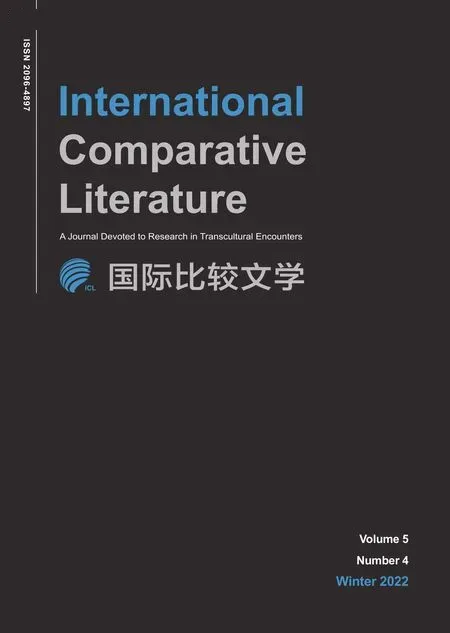文本主义者构想的声音: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
2022-04-15姚云帆华东师范大学
姚云帆 华东师范大学
并未交叉的开端:翁和德里达对书写问题的讨论
汉语学界对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思想的讨论已经较为成熟,对其赖以成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讨论曾经十分热烈,也开启了对中国汉字中有无“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系列探讨。1参阅周荣胜:《中国文明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求是学刊》2011年第3 期,第27~32 页。[ZHOU Rongsheng,“Zhongguo wenming zhong de luogesizhongxinzhuyi wenti”(The Problem of Logocentris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Qiushi xuekan (Journal of Qiushi)3(2000):27-32.]总体而言,上述研讨往往是内在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脉络之中,这种脉络所由来的类比或对比思维十分接近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2按:比较典型的研究有郑敏:《汉字与解构阅读》,《汉字文化》1997年第1期,第35~39页。[ZHENG Min,“Hanzi yu jiegou yuedu”(Chinese Characters and Deconstructive Reading),Hanzi wenhua(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1(1997):35-39.]以及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ZHANG Longxi,Dao yu Luogesi(the Tao and the Logos)(Chengdu:People’s Publishing Press,1998.] 这种基于类比和对比的中西比较模式在最近仍有对话者,参阅赵奎英:“从‘名’与‘逻各斯’看中西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21年第1 期,第39~49 页。[ZHAO Kuiying,“Cong ‘Ming’ yu‘Luogesi’ kan zhongxi wenhua jingshen”(Insight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from Ming to Logos),Wenxue pinglun(Comments on Literature)1(2021):39-49.]当学者们以“名”“道”等概念严肃的区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本源”意义上的差异时,逻各斯的幽灵就仿佛德里达引述《斐德若篇》中的“坏文字”那样,如蛆般依附于研讨者的文字之中。3Jacques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Of Grammatology)(Paris:Minuit,1968),26-27.而在20世纪西方思想界,对德里达的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在德里达声名鹊起之时,以塞尔(J.R.Searle,1932-)为代表的英美哲学家彻底否定德里达的学术价值,4按:德里达对塞尔的批评,中文评述参阅冯庆:《理论的节制:重审德里达与塞尔之争》,《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第154~160+197页。[FENG Qing,“Lilun de jiezhi:chongsheng delida he sai’er zhizheng”(Restraining in Theory:A Review of the Debate Between Derrida and Searle),Wenyi lilun yanjiu(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5(2014):154-60+97.]。更多集中评论文献,参见Raoul Moati,Derrida/Searle:Deconstruction and Ordinary Langu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而在现象学传统内部,德里达的地位则得到了相当的尊重。最近十多年来,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的讨论已经越发深入,即便是匹兹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兰顿(Robert Brandom,1950-)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也是在承认其论述正当性的基础上进行,而并非激烈否定其学说的思想价值。5Robert 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43.按:布兰顿认为,成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基本上是哲学不可避免的宿命,但哲学家可以经由对语言“意义和用法,概念内容和话语时间”的关系的描述,描述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正当性。
上述对于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的讨论,具有如下两个特点。首先,这些讨论将“逻各斯中心主义”看作一种思维方式,或是一种思想的表征方式来讨论的。其次,这些讨论关注的重点,基本不关心“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置于中心地位的“逻各斯(logos)”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也不关心这些表征,甚至解构这一中心的各种媒介在经验和质料层面的特殊性。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无论是逻各斯本身,还是表现逻各斯的“声音”,亦或再现声音,让声音自我解构的“文字”或“书写”,都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可感知、可把握的某种具体存在。这一理解,在早期德里达那里已经有了一定踪迹可循,尽管他试图用“踪迹”这样的概念,将“书写”这一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力量质料化,但他描述逻各斯、声音和书写的等级制逻辑仍然高度依赖德国观念论和现象学等哲学资源。
因此,在对德里达思想的批评中,媒介研究者翁(Walter J.Ong,1912-2003)的声音显得弥足珍贵。相对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伊尼斯(Harold Adam Innis,1894-1952)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等学者,翁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不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虽然何道宽对翁重要著作《口语与书写文化》的译本早已传播多年,而国内学界亦有相关研究专著出版。6按:国内研究界对翁的相关专著为丁松虎:《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瓦尔特·翁媒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DING Songhu,Kouyu wenhua shumianwenhua he dianziwenhua:wa’erteweng meijie sixiang yanjiu(Oral Culture,Written Culture and Digital Culture:On Walter Ong’s Media Theory,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7.];该书对翁和德里达的关系描述相对简明,并未当成重要主题进行深入剖析。相对于麦克卢汉思想的广为人知,翁的其它重要著作几乎未见翻译。而在文学研究界,尽管翁同样建树卓越,他的论述也遭遇了相对的冷遇。这部分是因为其更接近天主教保守派的立场,让关心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不甚欣喜,更可能是因为翁对现代媒介思想的研究颇为“古典”,不了解学术史变迁的文学研究者也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
但是,翁的相关研究恰恰决定了他与德里达在对待“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上的差异,也为他后来对德里达的批评打下了基础。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翁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拉米斯(Peter Ramus,1515-1572)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正因为拉米斯和其追随者的出现,人文思想的表达媒介才开始剧烈地从声音为中心,转移到以书写-印刷媒介为中心。按照翁的研究,拉米斯消解了中世纪自由七艺中“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的差异。7Walter J.Ong,Ramus,Method,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29-35.在此之前,沿袭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世纪修辞学和逻辑学都属于论证理论,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依靠论证获得自身的胜利,后者强调依靠推理获得真理。由于拉米斯相对较弱的学术基础和试图胜过经院派逻辑学的好胜心,他将修辞学中的论证理论并入了逻辑学,而将修辞学转化为修饰文辞的技巧,即辞格论。8Ibid.,272-79.这一改造鲜明地体现为传统逻辑学依赖线性时间推移展开的三段论论证被改造为更为简化的二分法逻辑图式,而且应用于包括哲学和文学作品在内的一系列印刷文本化的思想形态。9Ibid.,200-202.翁试图证明,之所以拉米斯的思想获得了有效传播,并战胜了经院逻辑学,不仅因为其学说简明,而是因为经院逻辑学的某种内在困境与现代印刷媒介的发展相互叠加的效果。
翁指出,中世纪经院逻辑学的经典文本是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所著的《逻辑大全》(Summes Logicales)。在这一著作中,彼得遇到了亚里士多德论证理论中一个不可克服的难题,即对逻辑可能性的展示。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中,前项、中项和结论的周延只能在一维线性的时间展开中完成,它只能指向一种必然结果。但是,许多逻辑问题在前项阶段就必须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从而导向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中世纪逻辑的讲授和使用中,口语表达只能在线性时间中进行推理,故而在呈现可能逻辑的推理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10Ibid.,62-63.按照翁的研究,彼得在他的话题学说(De Locis)和假设理论中都以放松三段论推理的方式,来克服这种表达可能逻辑时所遇到的疑难。11Ibid.,64.但是,限于口头语言离开具体时空的线性配置,就无法展示推理进程的局限。彼得的这样一系列论述虽然在学理层面得以成立,但在教学层面却无法得到落实。这一教学上的困难恰恰导致了中世纪经院逻辑在传播和接受上的困难。
按照翁的说法,拉米斯利用二分法图表,让中世纪逻辑学对可能逻辑的演绎得以用清晰而简明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恰恰有助于逻辑学对所有学科更为强大的影响和统治。而这种影响和统治与印刷-书写媒介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发展最终让知识的基本单元从稍纵即逝的声音转化为了可以普遍客体化的词语,而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可见的图标结构加以描述,且能通过严格的可复制性加以传播。而在声音为主要媒介的知识传播方式中,知识要素的关系必须依赖特定的情境而得以明细,而稍纵即逝的语音序列,也依赖特殊的记忆方法,才能在特定的场景和人物关系中得以把握。某种程度上,拉米斯的工作并非对中世纪逻辑学和修辞学知识的颠覆,而是激发了这两门学问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人文学科各门类的统摄,并得以更方便的向大众传播。但是,这种传播模式的改变却又实现了思想的某种转型,依靠声音媒介无法展示的可能逻辑理论,恰恰借助印刷文本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完善了古典逻辑学说,并对文艺复兴至18世纪的人文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经由早年学术生涯对拉米斯和拉米斯主义的研究,翁对书写-印刷媒介对思想史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看法包含了如下特点。首先,声音是一种线性的,高度依赖于时空处境的传播媒介,在表征多种模态、多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的思想形式时,它有其局限性。而相对于声音来说,书写媒介能将思想客体化,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思想的最小单元以“词语”通过符号表征出来,从而能表达更复杂的思想运动模式。其次,在拉米斯和拉米斯主义的案例中,一种重要的思想想要实现自己的效力,并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就必须等待恰当媒介的出现。而媒介的出现也能更清晰、更有效地整理这种思想的形式,让它得以真正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把握,进而改造人们的知识形态和思维模式。因此,在翁看来,印刷媒介让语音媒介仍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逻辑学中尚不能完全呈现,且不具影响力的可能逻辑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完全清晰地表征出来,这充分体现了书写-印刷媒介对语音媒介的优越性。
这显然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有着暗合之处。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是通过声音中心主义得以表征的。在《文字学》中,他引述亚里士多德《论解释》中“声音是灵魂的表征,而文字是声音的表征。”这一论述,并将之看作西方形而上学确立精神/声音/书写三重等级制最为原初和经典的表达。12Jacques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Of Grammatology)(Paris:Minuit,1968),21.在德里达看来,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所有思想家都在这三重等级制的影响之下,却不得不承担这一等级制自我解构所带来的悖论: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一切文字表述能够忠实地让思想最原初、最本真的形态在场;另一方面,为了超越这一文字的障蔽,把握原初、本真的思想,他们必须诉诸文字,从而进一步稳定这一等级秩序。通过这一悖论的揭示,书写得以超越语音,成为在思想得以表征唯一的机制,尽管也是一种不断自我批评、自我解构的机制。
德里达和翁都批评了声音在表征人类思想形式的局限,从而肯定了书写作为一种表征机制的重要作用。但是,翁和德里达早年学术道路的差异,导致他们肯定书写背后的意图并不一致。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来源于他早年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通过对胡塞尔先验还原学说中指明(Hinzeigen)和证明(Anzeigen)功能差异的区分,德里达发现了胡塞尔哲学中依赖现象得以还原,却又外在于还原过程的原初声音所蕴含的悖论。13Jacques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Voice and Phenomenon)(Paris:PUF,1967),25.在《文字学》中,这一悖论转化为试图垄断思想表征唯一中介的声音形式,和总是试图将这一声音形式转化为可理解内容的书写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德里达那里,“听不见的声音”,或者不在场的口头表达不仅在起源意义上优先于对这一表达的书写,也在价值上优越于这种书写。但是,在翁那里,声音媒介和书写媒介在表征能力和价值上处于平等地位,而在拉米斯主义的传播中,书写媒介在表征思想的能力上甚至比声音媒介更为优越,表达的效果也更直观、更清晰。这显然不同于德里达在批判声音形式在表征思想的过程中,仍然策略性地维持了语音形式之于书写形式的优越地位。
不仅如此,翁对拉米斯主义与中世纪逻辑学关系的研究,甚至成为了一个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例。不同于德里达利用文本解读策略,让声音/语言的等级制自我解构的工作,这个例子似乎直接让书写处于对声音的优势地位,从而构造了一种思想/书写/声音的等级制。书写-印刷文本可以清晰而完美的表征可能逻辑推理的形式,而声音形式反而会扭曲书写形式很容易驾驭的逻辑思想。考虑到“逻辑学”正是古希腊“逻各斯”概念最为严整清晰的表达,在翁所研究的例子中,逻各斯中心主义似乎应该彻底改名为“书写中心主义”。
最后,与德里达不同,翁对声音和书写-印刷媒介的理解并非止于一种思想形式,而是一种内在于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之中的物质性存在。他并非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从媒介史和思想史的视野中看待思想、语音和书写的关系。一旦进入了这一视域之中,德里达试图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相应于其存在的思想/声音/书写的等级制策略,反而让这一等级制强化为一种形而上学图式。在这一图式的限制下,书写和声音位置的互换并不能动摇等级制本身的意义。而在翁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书写”和“声音”的形态并非单纯的思想形式,而是被历史和社会处境规定的实在媒介。
因此,正如翁所述,虽然他在60年代之前并未接触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等法国思想家对话语和文本问题的论述,但他早年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与德里达思想的分歧和对立。在他接触了德里达的学说之后,他自然会采取批判的立场。
一、“文本主义者”造出的声音:翁的德里达批判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系列法国思想家的作品开始影响美国的人文学界,德里达自然是其中最为炙手可热的学者。与英美分析哲学界不同,在学术渊源上偏向文学和思想史的翁对德里达的抵触并不激烈。他并未将这些思想家打入另册,而是在全面阅读其思想后,进行了审慎的评价和辨析。
翁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都是根植于书写-印刷媒介这一基础之上。具体而言,他将这些批评理论粗略地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五个子类别:“文学史理论”“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本主义和解构主义者”“言语行为和读者反应理论”。其中,在“文学史理论”与“言语行为和读者反应理论”,对口传媒介的讨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文本主义和解构主义者”的学说则完全与书写-印刷媒介的核心产品:文本,有着根本的关联。14Walter J.Ong,Orality and Literac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154-57.在他看来,开启这一关联的学说是英美新批评这一文论潮流:“新批评思潮将语言艺术作品吸纳进文本的视觉-客体世界,而不是口耳相传的事件世界”15Ibid.,157.,而结构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特点在于,将本来高度依赖口传文化而得以构造的“原始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文本化转写,而口语媒介与事件和特殊场景的联系在这样一种转写中被边缘化了。16Ibid.,161-62.随着结构主义的发生,对整个社会体系的描述被文本化了,文学批评理论和现代印刷媒介的关联程度达到了顶峰。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翁对德里达和解构主义者的态度极为独特。一方面,他将解构主义直接定位为一种“文本主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文本主义者中,德里达确实发现了声音对于文学批评独有的作用。这使得他对德里达的批评不仅对理解翁与德里达的差异有所帮助,而且成为理解翁把握书写-印刷媒介理论和声音媒介理论差异的一条重要线索。
那么,翁是怎么理解德里达对声音的论述呢?他认为,德里达确实发现了声音形式和书写-印刷形式之间无法完全进行对称而透明的还原,从而确立两者确实是两种无法通约的思想表征方式。不仅如此,德里达还发现,声音形式的表征意义的基本单元无法严格对应于书写媒介表征意义的最小单位。因此,翁认为,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文本主义者”,打破了18世纪哲学家卢梭开启的对语言和书写关系的巨大偏见。“这一偏见以如下形式出现:人们假设外在世界的每一事物和口语中的单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后者和书面语中的单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一点似乎拓展到了印刷媒介之中,文本主义者似乎把书写和印刷看作一类事物,甚至冒险将这一对应关系拓展到数码媒介之中)。”17Ibid.,163.正因为语音形式无法以“词”为单位彻底还原为书写形式,声音媒介和书写-印刷(甚至数码)媒介对思想的表征与声音-口语媒介成为本质上不同的表征媒介。
这一点是翁认为德里达的思想与自己思想的相似之处。但是,在他看来,德里达未能更进一步,他虽然拒绝了书写媒介与声音-口传媒介之间的等价关系,但是,这种拒绝并非是为了探索两种媒介之间的差异,从而把握声音-口语媒介和书写-印刷媒介在实质上的特质,而是为了捍卫书写媒介的正当性,从而以驱逐书写(乃至声音形式)表征思想和客体的能力。因此,德里达构想出思想的声音形式,并不是人类历史文化中真实出现的声音形态,而是为了证明书写-印刷媒介不具有表征功能而树立一个虚拟的靶子。这个像康德“物自体”一般不可知、不可感的声音,只有通过书写形式对这一虚拟声音形式的抵抗、消解和拒斥,进而隐遁其在历史中的存在方式,才具有真正的理论意义。
在翁看来,这种对声音的理解并不能真正把握声音-口语媒介和印刷媒介真正的差异,也没法理清两者在具体历史-社会语境中的联系。而且,这只能说明,德里达看似捍卫“声音”和“书写”各自正当性的策略,实际上只是捍卫书写-印刷文本在塑造和表征思想的过程的独断地位。因此,翁指出:“即便说出了A不等于B,并不能说A就什么都不是。”18Ibid.,1.换句话说,德里达虽然指出了书写-印刷媒介不等于声音-口传媒介,却不再讨论后者到底具有什么性质,这实际上是一种懒惰行为。
不仅如此,翁还重新解释了德里达在论述逻各斯中心主义时,所涉及的柏拉图的思想。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所涉及的心灵中的“好文字”和可见的“坏文字”的区分是柏拉图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却又导致这一立场的自我解构的鲜明例证。但翁却认为,柏拉图之所以使用这一类比,恰恰是因为由于拼音文字的使用,书写媒介取得了对声音-口传媒介的优势。通过引用古典学家哈弗洛克(Havelock,1903-1988)的成果,他指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之所以驱逐诗人,是因为后者代表了
依靠技艺和口传传播思想的旧世界,在其中,模仿、集体组织、迂回表述、口才宏富、更传统、更富人性和参与感的因素,被柏拉图塑造的“理念”世界中分析性的、冷感的、隔绝的、精确而不变的特征所代替。19Ibid.,164.
因此,在翁看来,柏拉图创造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是声音中心主义,而是以声音的优先性为策略而塑造的一种文本主义,而柏拉图所推崇的“声音”,并不是声音-口传媒介中现实存在的声音,而是文本主义者刻意虚构出来的一种声音,它来源于对文字的模仿,却刻意伪装成文字的来源、模范和理念,仿佛后者是自己的模仿一般。由此可见,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是柏拉图这位文本主义先驱的当代模仿者,而翁则认为,他早年研究的拉米斯主义早已经成为这一文本主义谱系中远比德里达更优越的版本:“在其辩证法和逻辑学说中,拉米斯提供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为不可超越的典范。在《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衰败》(Ramus,Method,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1958b,pp.203-4),我并不将之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把它叫做‘微粒态认识论(corpuscular epistemology)。’”20Ibid.,165.换句话说,在翁看来,真正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恰恰是严格的文本主义,只有在印刷媒介得以有效使用的时刻,如拉米斯主义的传播时刻,逻各斯中心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而在此时,德里达刻意虚构出的“声音”也不再需要出现,印刷和书写已经彻底代替它将思想明晰地表达和传播出来。
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可谓理据充足,论述严密。但是,这一批判的完成有赖于一个问题的澄清,即翁何以把握声音-口传这一媒介真实而独立于书写媒介的存在方式,这一存在方式能否有效地摆脱文字-书写媒介的“污染”,而具有其固有特质。
二、词语-事件:翁对口传-声音媒介特质的界定
翁对声音-口语文化的研究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Lord)对口传史诗中套式(Formula)理论的研究,而古典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则将这套理论拓展到古希腊时期口传文化对政治、社会和思维形式的影响之中。基于上述学者的贡献,并参考世界诸多文化对口传-声音媒介的应用方式,翁提出了对口传-声音媒介本质特征的某种描述。他指出,真正的声音-口传媒介具有如下特点:1)累赘性而非类属性;2)聚集性而非分析性;3)重复性;4)保守和传统主义气质;5)封闭于人的生活世界;6)怼腔怼调(Agonistically Toned);7)共情参与而非间离客观的;8)超稳态的文化环境;9)境遇性而非抽象的。21Ibid.,36-49.
这八个特质中,前三个特质描述出声音-口传媒介的信息组织形式的特征,后四个特质则描述出这一媒介在传播形态的特点。翁认为,声音-口传媒介是一种声音在时间的线性序列中单向排布的媒介形态,因此,它无法描述复杂的类属关系,而倾向于将事实用“和(and)”连词缀列的方式累加讲述。他认为,《圣经》中的王族世系,《荷马史诗》中英雄出场的方式,就是典型的口传媒介在后世书写文本中的痕迹。而在民间艺人的史诗中,这种表达更是比比皆是。22Ibid.,37.其次,声音-口传媒介往往依靠固定的修辞格式,而不依靠单个词语来表述事情,比如,《荷马史诗》中内斯托尔总是和“智慧的”连用,奥德修斯总是伴随“聪明的”这个修饰语。这一特征源于翁对帕里-洛德理论中的“套式(Formula)”概念的借鉴。23Ibid.,39.这两位史诗专家认为,为了方便记忆,不能阅读文字的史诗吟诵者往往利用一系列固定的修辞搭配来表达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因此,声音-口传媒介带来了一种高度格式化,但信息表述量极为凝缩的表达形式,许多民间谚语、顺口溜和传说故事往往具有这一特点。24Ibid.,39-40.而且,与书写-印刷媒介不同,人们在口头表达中无法回过去检索和重复记忆之前的信息。所以,口传-声音媒介往往按照特定节奏不断重复重要讯息,以加深和强化听众的记忆。与此同时,口传-声音媒介很重视信息传达的密度;所以,往往对传播对象的描述极为细节化,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量的信息通过口语表达出来。
野黄芩苷对血管紧张素Ⅱ诱导的新生大鼠心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及ERK1/2、p38 MAPK信号通路的影响…………………………………………………… 辛 博等(5):629
上述四个特征最终指向了声音-口传媒介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的特质。这种特质服从于如下的传播策略:以让听者很快熟悉内容为目标。由于声音以一种单向一维且不可逆的方式传播,在单位时间内最大限度的传播信息,而非清晰表达所传播的信息要素之间的关联,成为传播的主要任务。
但是,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如果听众不理解信息之间的关联,也就无法清晰完整地理解信息的意义。那么,声音-口传媒介如何表现声音之间的关联呢?声音-口传媒介依靠自身的传播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声音-口语媒介并不以整理和推演新的内容和知识为目标,而是以保存和应用既有的知识为目标。所以,它所表征和传播的内容往往是传统规范和古代英雄事迹等“传统”知识,其功用在于保存传统,从而确保社会规范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与此同时,口传-声音媒介的听众往往与传播者相互熟悉,并潜在地共享某种知识传播的共同社会-文化语境。例如,游吟诗人讲的故事往往是部落民大概了解的祖先知识,布道者的演说往往是教徒潜在赞同,却对细节不甚明了的宗教教义。只有对部落民和同一教会的教众演说时,这些表达才会激发他们潜在的“共识”,起到传播效果。口传媒介讲述的话题往往激发着听众生活世界的各种经验,才能让他们理解。过于抽象的知识和话题,既无法让听众明白所传播信息所蕴含的复制逻辑联系,也无法让他们真正地感同身受,从而阻碍了信息的传播效果。
除了传播文化语境的限制,声音-口传媒介对具体传播方式的要求还体现在传播者语气姿态斗争性的要求。虽然翁认为,声音-口传媒介只能在一个超稳态文化环境中传播,但传播者为了申明自己的意见,达到极好的传播效果,往往必须以一种竞赛者和论争者的姿态,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听众才能被传播者的表达和言辞吸引,从而达到信息的有效传播。这也是声音-口传媒介占主导的社会,往往修辞技术优秀的人不仅能成为重要的传播者,而且能凭借这种技术,掌控巨大的政治和社会资源。由于传播方式与修辞说服技术的巨大关系,声音-口传媒介更强调听众情感的调动和行动的参与。因此,被声音-口传媒介主导的听众,比被书写媒介主导的受众,更不“理性”,更容易受到演讲者口才、姿势和情绪所激发的“共情”,被这种传播媒介所操控。但是,这种依赖共情得以传播的媒介也有其局限,它无法准确有效地表达某种“抽象”的知识,也无法清晰表达传播内容中相关信息之间清晰的逻辑关系。人们只能依赖对共同体“既定共识”的记忆,借助文化语境的约定性规范,才能模糊的“把握”声音-口传媒介传播出来的信息。
基于上述信息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描述。翁最终确立了声音-口语媒介与书写-印刷媒介在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一种依靠“事件-词语”为中心的媒介,后者则是一种以“符号-客体”为中心的媒介。翁指出,在许多声音-口语媒介占主导的社会中,“词语”并不被用来指涉客体,而是用来表征一个事件。例如,“希伯来语dabar 的意思是词语,但他的意思同样是事件,而且直接用来指口语意义上的词。”25参阅Walter J.Ong,Orality and Literacy,74.在他看来,当口头传播者说出一个词的时候,他表征甚至激发了一个事件的发生,从而激发听众参与到这个事件的发生之中,他的诉说和传播是这个事件的延续,而言说的终止也是事件的终止。
这让声音-口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包含了一种内在张力。一方面,“事件-词语”的呈现不可逆转,随着声音的终止而消失,体现了事件的瞬时性和不可重复性;另一方面,通过传播过程中的重复,对传统知识的回顾和共情效应的激发,“事件-词语”又呈现为传统和权威的永恒在场和不断复活。翁对《圣经》所蕴含的口传媒介的解释体现了这一点。
在三位一体神学中,上帝所有的第二位格是词语,而人与之相应的词语并非书写词语,而是口语意义上的词。圣父上帝对耶稣说话,他并不写上话,给他看。尽管作为上帝之言,耶稣既能说话,又能写字,但他没写下只言片语(路加福音4:16)。当我们读《罗马书》时,‘听到的才能信’,“字义让人死,精神让人生。”26Ibid.,74.
在这段话里,翁借助《圣经》的例子,呈现出声音-口传媒介不同于书写-印刷媒介的特性。上帝的声音通过耶稣的训导呈现出来。随着耶稣死亡-得救这一事件的完成。这一言说也就随之结束,却通过路加、保罗等人的口传得以不断在场,并赋予听者以“生命”。这显然是翁心目中口传-声音媒介最为典范的呈现。因此,翁认为:“德里达指出,‘书写之前没有语言符号’。但是,即便书写发明了,它涉及的那些口传信息也没有相应的语言符号。”27Ibid.他进而指出,印刷符号系统与声音-口传媒介主导的“词语”在源头上毫无交集。在翁看来,“符号(Sign)”这个概念,来源于古罗马军团借以区分敌友的军旗和徽章图案,在文艺复兴之后印刷媒介发展趋势之中,才得以用来指涉词语,进一步激发了词语客体化为一种符号。28Ibid.,75.这种词语的客体化形式本身最终取代了“词语-事件”的作用,从而标志了书写-印刷媒介对口头-声音媒介的胜利。
至此,翁找到了声音-口传媒介在“实证”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并通过以事件方式发生的“词语”和作为客体化形式的符号将口传-声音媒介和书写媒介彻底区分开来。这是否意味着翁对德里达的批评无懈可击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翁指出了声音-口传媒介与书写-印刷媒介的差异。但是,他证明这一差异的证据,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批评德里达构想声音所依赖的载体:文本。尽管翁依靠哈里-洛德在“无文字社会”中的史诗传唱研究,也多援引人类学家在这些社群中的田野调查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当翁试图证明声音-口传媒介固有特质具有普遍性时,他相当程度上诉诸于书写-印刷文本。这部分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主要的文明形态中,很难到找到无文字的社群,人们也就无法超越书写-印刷文本的中介,直接把握口传-印刷媒介的特质。但是,即便如此,翁也无法证伪,已经呈现于书写-印刷文本中的“声音”形态的残留29Ibid.就一定包含着不同于书写-印刷媒介的特质。因为,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书写媒介都能以各种方式表征声音-口传媒介试图通过“词语-事件”加以表征的信息。
例如,翁对《圣经》中“词语”问题的论述就使得他对声音-口传媒介的界定陷入了危机。我们已经无法听到耶稣真正通过口传-声音媒介传递出的声音,但恰恰是《圣经》文本这个死去的文字媒介,使我们得以确信,存在着这个转瞬即逝,却又可以在文本中再临的“词语-事件”。因此,《圣经》也许并不能直接用特定的符号以客体化的方式将词语表征出来,它却用让“词语”不在场的策略,让文本指涉词语,从而同样将“词语-事件”在书写文本中呈现出来。
这一德里达式的反批评并非不能找到其它的论据支持。文化记忆理论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1938-)在讨论书写系统与文化记忆的关系时指出,至少在古典西方文明、埃及文明和以色列文明中,书写媒介并不以符号形式让知识客体化,而是试图详尽地再现曾经出现的重大仪式情境。这也让书写体系拥有声音-口传媒介一样的特点:如重复性和保守性等特点。30参阅Jan Assmann,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Cultural Memory)(Muechen:Verlag C.H Beck,2000),93-97.这一例证说明,翁将“词语-事件”和“符号-客体化”区分出来的实证主义企图,在根本上并不成立。即便书写-印刷文本在历史上并不与声音-口传媒介同时出现,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两者的关系是互渗而共生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的关系。
这种互渗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翁批评的另一种局限。他将符号-客体化形式作为书写-印刷媒介的本质特征。这不禁让人发问:难道符号-客体化形式是书写-印刷媒介的唯一属性吗?翁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论断中,文本对声音的表征仍然成为他最为关切,却又最为矛盾的论述。他似乎将口传媒介主导下,试图完整再现“词语-事件”的文学风格看作一种“模仿式”的风格,却将书写-印刷媒介下的文学风格看作一种“反讽式的”风格。31Walter J.Ong,Orality and Literacy,102。以及Walter J.Ong,Interfaces of Words:Studies in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272-304.显然,这一划分恰恰与他对上述两种媒介本质的论述产生了矛盾。翁认为,为了准确的再现“词语-事件”,在口传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完整传承口传知识的传播原则和基于共情的参与性传播方式让趋向于同一性的“模仿”原则成为文学的主导原则;但在书写传播媒介中,激发怀疑,并让读者与客体化的文字信息产生距离的反讽原则,成为文学的主导原则。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首先,按照翁对书写-印刷媒介的界定,通过符号的转化,信息被严格对应为客观而准确的知识,从而让人们超越时空距离的限制,更准确忠实地理解信息内在的逻辑关系,这构成了书写-印刷媒介重逻辑,强调分析思维的特质。这种特质也更强调符号对信息要素一一对应的严格表征。这就意味着,书写-印刷媒介比口传-声音媒介更强调一种“模仿原则”(尽管这一模仿原则去除了参与性和共情机制)。但是,反讽原则恰恰要求读者质疑符号与信息要素的一一对应,而在翁看来,这种质疑和批评导致了读者和符号的视觉距离,却又客观上阻碍了信息传播的精确性。这让“模仿式”原则和“反讽式”原则形成了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书写-印刷媒介的特点并不一定能用符号-客体化来概括:显然,反讽造就了信息与读者的视觉距离,却不能导致读者通过符号分析有效地把握信息,反而造成了信息传递的困难和复杂。
其次,翁指出,反讽本来就是一个口传-声音媒介中的修辞技法,在书写媒介尚未发达时,作为一种韦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所谓的“稳定反讽(Stable Irony)”广泛存在于口传文学作品中,32Walter J.Ong,Interfaces of Words,288.直到18世纪现代印刷媒介发展之后,反讽造就视觉距离的潜能才得以明显地呈现出来。尽管翁用一种演化论论述,将“稳定反讽”和书写媒介中的反讽区分开来。但是,即便在所谓的“稳定反讽”中,听众对声音临时性的困惑和最终获得“谜底”的解谜快感,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时间差”。书写媒体中仅仅是将这种时间差通过视觉形式空间化了,从实现出传播过程中“知者和求知者的对立”转化为“学习者与知识载体的区别”。33Ibid.,112.
这一看法恰恰忽略了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口传媒介中继承下来的反讽技术,在书写-印刷媒介中,人们不可能在承认信息以视觉符号客体存在的同时,怀疑这一客体传达出的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书写-印刷媒介中反讽技术的使用,恰恰是在这一媒介中恢复口传-声音媒介在场性的努力,而非这一媒介在演化进程中被替代的标志。这也进一步证明,翁经历了诸多实证工作,试图区分口传-声音媒介和书写-印刷媒介的“实证”工作,仍然是失败的。
某种程度上,这一失败反而凸显了德里达论断更为有力的一面。翁认为,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界定窄化为词意/词的声音形式/书写符号之间等级关系。他则将词语看作一种与视觉符号平行无涉的意义表征媒介,从而将声音-口传媒介和书写-印刷媒介在“实证”和物质层面区分开来。我们发现,通过这种区分,尽管意义/声音/书写符号的等级制不再具有效力,一种“语词-事件”为中心的“保守”媒介即声音-口传媒介和一种以“视觉符号”为中心的“现代”传播媒介之中的对立呈现出来。有趣的是,为了确保上述两种媒介之间的地位界分和前者从传统演化为现代的路径,翁最终不得不混淆这两种媒介的特点,这种混淆再一次确证了德里达的基本企图:声音和书写无法独立的表达意义,在意义生成中,存在着书写出的声音踪迹和凭借声音写出的文字,两者不可分离,混而为一。
三、声音的特权和书写的霸权:翁媒介学说中的“政治无意识”
因此,翁并不能真正从“实证”工作中把握到声音-口语媒介和书写-印刷媒介中的区分,从而呈现一条客观的媒介演化史线索。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翁对德里达的批评时,就不得不反思翁的学术立场和其学术工作的潜在策略。
相对于同属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老师麦克卢汉,翁的学术工作有其潜在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判断。翁的博士导师佩里·米勒(Perry Miller,1905-1963)是著名的美国文学史学者和当代“美国研究”的代表人物。米勒的代表作品《新英格兰精神》(The New England Mind)对美国文化与欧洲文明的关联,进行了“修正主义”阐释,强调新教文化在连接两希文明和美国现代文化精神中的枢纽作用。米勒的学术工作有着为鲜明的政治倾向:为美国梳理承接西方文化天命的正当性提供“背书”。34参阅John Hartley为翁《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纪念版所写的前言,Walter J.Ong,Orality and Literacy,xv.他自己深度介入了美国的全球文化价值输出之中,在二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战略服务局(OSS)”,介入了美国文化冷战策略的顶层设计。
翁受米勒的影响极为深刻。他虽然是天主教徒,但他的研究开端于改宗新教并对英国新教神学和文艺复兴文学影响深刻的拉米斯,并依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拉米斯著作版本整理作为基础材料。35Ibid.,xvi.以及Walter J.Ong,Ramus,Method,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v.这些著作曾成为殖民地修辞和逻辑教育依赖的基本教材。我们可以发现,翁的拉米斯研究潜在地将书写-印刷媒介的变革与宗教改革和美国文化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翁在圣路易大学建立修辞和传播专业也受到了政治形势的激发,其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厨房辩论”。36参阅John Hartley为翁《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纪念版所写的前言,Walter J.Ong,Orality and Literacy,xx.在这场辩论后,翁发现,随着电视和电脑的出现,口传媒介在捍卫美国与西方文明价值中的作用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
这种政治倾向最后渗透到翁对声音-口传媒介的研究之中,成为这一研究背后的政治无意识。翁依据声音-口传媒介和书写-印刷媒介的区分,形成了一套清晰的媒介演化史脉络。在这条并不客观的脉络中,翁对上述两种媒介的论述包含着他对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在全球传播中的媒介正当性所进行的捍卫策略。这种策略最终组成了翁媒介理论中潜在的政治倾向。
翁将声音-口传媒介看作一种捍卫传统知识和文化关系的传播媒介,他既具有传统主义和保守风格,又依靠论争来捍卫这种传统规范和价值。而书写-印刷媒介则是一种跨越了时空和文化限制,将信息转化为视觉客体,从而传播“普遍”知识的媒介形态。通过对前者向后者转化进程的分析,翁试图呈现如下两个事实。首先,正是希伯来-希腊文化主导的西方文明,塑造了声音-口传媒介的发达形态,成为了西方文明得以捍卫其传统价值和规范的源泉所在。这在他对荷马问题和《圣经》中“发现”声音-口传媒介的踪迹得到了体现。其次,恰恰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媒介转型”产生了最有传播效力的书写-印刷媒介形态,这一转型的推手不仅包含媒介技术的变化,而且隐含了清教-美国文化的潜在影响。正是这种文化环境的培育,让西方文明和其当下代表清教-美国文化,成为书写-印刷媒介得以跨越社群、空间和文化的积累,成为主导现代全球文明的文化形态。
这就意味着,翁同时在张扬两种媒介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他坚持着现代西方文明(实际上是清教-美国文化)主导书写-印刷媒介的霸权;另一方面,他坚持着西方文明传统中声音-口传媒介对保存自身文化特权的重要作用,这种基于共情和参与机制,以保存文明传统为目标的传播媒介才能真正捍卫这一文明得以主导全球传播的重要因素。
这样一种试图在霸权和特权两者间维持动态平衡的理论使翁的德里达批判变得顺理成章。他部分赞同后者对“书写”在意义增殖过程中的传播效力的描述,但反对后者通过书写文本构拟声音的解构策略。因为,德里达的策略意味着印刷-媒介脱离其文化语境的声音-口传媒介的宰制。因此,翁必须发现“真实”的声音特权,而正如上文所述,这一勾勒“真实”声音的努力仍然不能脱离文本进行,反而构成了西方思想传播中最为保守的“声音”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