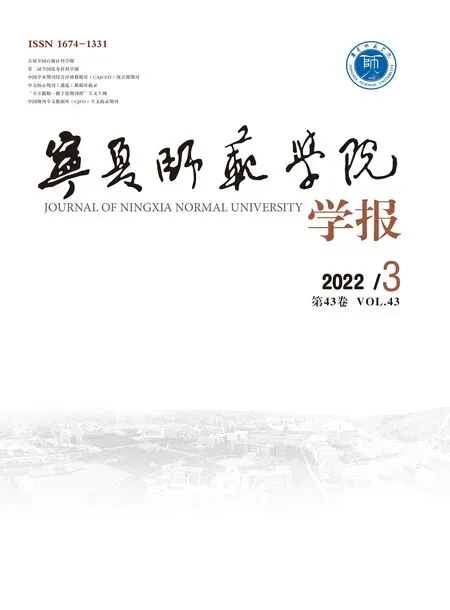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期宁夏戏剧运动考述
——围绕《宁夏民国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2022-04-14王方好
王方好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主要的攻占目标,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进而将掠夺的爪牙逐渐伸向我国的中部地区。与此同时,不少东部地区的文化机构开始西迁,直接带动了我国文化重心的西移,这主要表现在高等院校、出版社、科研院所、文化名人等领域。文化重心的西移,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夯实了基础,这集中体现在陕甘宁文艺的迅猛发展。
作为陕甘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重心的西移让宁夏地区的文艺事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集中体现在该地区戏剧事业的繁荣。这一时期,戏剧运动在宁夏地区如火如荼的进行,这集中的反映在《宁夏民国日报》这一区域性的报刊之中。《宁夏民国日报》是民国时期宁夏地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区域性报刊,创刊于20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该报首任社长为张子美。“《宁夏民国日报》创刊后,不断刊载戏剧理论、戏剧活动、剧本、表演艺术等方面的消息和文章。”[1]其中刊载了大量有关抗战时期宁夏戏剧运动的珍贵史料。遗憾的是,目前《宁夏民国日报》中的戏剧史料还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未有系统性的文章对其进行研究,因此,这一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西部少数未受日寇侵犯的区域,其中多个地区的文化活动呈现出繁盛的态势,尤其是在戏剧方面。由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使得其成为教化启迪民众、传播信息最为广泛的一种媒介。笔者通过查阅《宁夏民国日报》的相关材料,发现其中的戏剧史料多集中在1937-1945年这一区域间,且大多数与当时宁夏地区所开展的戏剧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也集中反映出当时宁夏地区戏剧生态情况,纵观《宁夏民国日报》之中的相关戏剧史料,笔者发现这一时期的宁夏地区戏剧运动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一、戏剧社团的蜂起与演出活动的兴盛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东部地区文化资源的西迁,宁夏一带的文艺活动开始兴盛起来。抗战时期宁夏地区戏剧运动繁荣的一大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戏剧社团。这些戏剧社团往往从抗战现实出发,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系统性的文艺活动,并且对传统的戏曲进行革新,使其为抗战的现实所服务,成为当时宁夏地区文艺活动的主要阵地。
宁夏地区的戏剧社团在抗战之前相对较少,抗战日期则出现了数百个戏剧社团,如贺兰剧团、军话剧团、同心剧团、觉民剧社、联谊剧社等。这些戏剧社团为宣传抗战、驰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剧团主要演出的剧种以话剧、秦腔为主,并且创演大量配合抗战宣传的剧目,成为抗战的重要的宣传阵地。
贺兰剧团成立于1940年,是抗战时期宁夏大后方影响较为深远的大剧团之一,主要以话剧演出为主。“由省教育厅和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十服务团联合组建。”[2]该剧团在建立之初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实施社会教育,发扬民族意识,加强抗战力量为宗旨。”[3]并且有着明确的分工与组织安排,在组织方面设有团长一人,团务委员五到七人,并且设有剧务、总务两部。剧务部下设编导、化妆、道具、装置、灯光、效果等六大部门,总务部则是设文书、事务、会计三大部门。贺兰剧团成立后,成为宁夏大后方宣传抗战重要的工具之一,定期排演抗战剧作,从而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演出剧目有《夜光杯》《国家至上》《征服》等剧目,这些剧目在思想上大多呈现出鲜明的抗战意识。如《国家至上》原为老舍先生于1940年创作的一部回族题材的话剧,该剧最先在山城重庆公演,随后引发轰动效应,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始演出。1941年十月起,贺兰剧团开始排演这部剧作,并筹划在宁夏地区公演。该剧一经上演就受到了宁夏地区民众,尤其是回族民众的广泛好评,公演次数不断增加,而所获收入也全数概作劳军物资。
觉民剧社是抗战时期影响较为深远的剧团之一,该剧团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由魏鸿发、刘小石发起,仿易俗社并聘请沈和中、何振中、王庚寅、康正中、席子才等著名演员,以当地“葫芦班”老艺人孙广乾、刘晏奎、李长青为骨干组建。”[4]由此可见,觉民剧社的形成受到了易俗社的影响,所以演出的剧目大多以秦腔为主。在抗战时期,觉民剧社为了配合抗战宣传工作,在宁夏各地区组织多次巡演,尤其多次排演历史题材戏曲,先后排演了《双诗帕》《三滴血》《新忠义侠》《对银杯》《吕四娘》《左宗棠》等剧目,对于宣传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35—1946年,觉民剧社先后招收学生二百余名,分甲、乙、丙、丁、戊五班。在抗战时期,丙班学生成为当时演出的主力军,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该剧团的演出“市民备极欢迎,每晚票价收入均在一万五六千元以上,十一日晚公演,收入竟达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元。”[5]所演出的历史剧目,对于唤起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宁夏地区戏剧社团的蜂起与演出活动的兴盛,为宁夏地区的戏剧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大大推动了宁夏地区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为宁夏地区的抗战文艺活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报刊出版与宁夏本土戏剧理论的建构尝试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6]相较于其它传播媒介,报刊凭借着其自身的优势,成为当时宁夏边区地区宣传动员群众的重要媒介。伴随着文化重心的西移,宁夏地区的文化出版事业的开始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专业的报刊。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宁夏地区的报刊数量达到了几十种,其中以《固原日报》《扫荡简报》《三边报》《贺兰报》为代表,其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还是要数《宁夏民国日报》。《宁夏民国日报》之中刊载了大量系统化的戏剧理论,这也成为宁夏本土戏剧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极具戏剧史价值。
为了能够对抗战时期《宁夏民国日报》所刊载的戏剧理论刊载情况更加直观的分析,笔者对其刊载的主要戏剧理论文章做了不完全的分类统计,见表1。(1)由于部分日期的报刊原件已经损毁,因此笔者所统计的为现存保留完整《宁夏民国日报》中的相关戏剧理论文章。

表1 《宁夏民国日报》主要所载抗战戏剧理论文章统计
《宁夏民国日报》刊载了多篇戏剧理论的文章,这些理论文章是宁夏本土戏剧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大多直面于当时宁夏地区的抗战戏剧运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其中的一些文章因未刊发单行本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纵观《宁夏民国日报》刊载的戏剧理论可以发现,其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旧剧的探讨。《宁夏民国日报》对于旧戏探讨的理论性文章数量众多,这些理论性文章大多对旧剧的起源、发展以及剧本、演出情况等进行了细致性的归纳与总结。如仲可在《漫谈旧剧(一)》“以戏剧为职业,专供人之观赏者,不知起于何时,但以旧时称剧人为优伶,则必滥觞于俳优无疑。”[7]对先秦到元代戏曲的流变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除此之外,对旧剧的排场、砌末、流派等问题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总结与分析。最具戏剧史价值的一点是对旧剧的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如“戏剧以歌声代语言,以姿态表动作,故精神上之能缜密,而物质上之布置,转多忽略不备。扬鞭则为骑,累桌则为山,出宅入户则奉作踏浪之势……此皆亟待改良者也。”[8]认为中国传统旧剧过度的强调写意,应该尽快的学习新戏的舞台布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旧剧的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第二,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讨论。戏剧与现实的关系从“五四”以来,一直成为众多戏剧理论家讨论的一大话题。作为宁夏大后方重要的宣传阵地,《宁夏民国日报》之中所刊载的戏剧理论也大多直面于当时的国情,强调戏剧艺术的时代特征。苗青在《戏剧的时代性》一文中指出“一切艺术都是受着时代的决定与否定的,在某一个时代,必定会产生与某个时代相吻合的艺术。”[9]这说明,这一时期众多的戏剧理论家们都已经受到了文学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强调文学的时代性。作者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时代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就拿我们抗战以前来说,那时我们还是一种被压迫的敢怒不敢言的时代,我们的戏剧艺术里,也就充满了和那个时代同样色彩的内容,如《夜光杯》《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放下你的鞭子》《烙痕》等,都是当时忍气吞声的产物,但是里面却都已经明暗的显示出反抗的色素了,这就是戏剧已经抓住了时代的趋向,而吻合了那不可避免的反抗了。”[10]接着作者将戏剧的抗战联系起来,强调“‘七七’的民族抗战正式揭开以后,戏剧也就跟着时代的突变,毫没迟疑的立刻参加了抗战的队伍……因之沉溺在战前的浪漫主义戏剧,也就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被遗弃。”[11]因而作者反复强调戏剧艺术的时代特征,并且鼓励戏剧创作者创作出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戏剧作品,只有如此才能够符合时代精神。并且作者反复强调戏剧所具有的宣传现实功用“现在我们是在抗战时期,也是正需要戏剧艺术发挥它力量的时期,我们必须对艺术与宣传的关系,得到一个明晰的认识,而后,才不致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所迷惑,而削弱戏剧伟大的宣传力量。”[12]这也为当时宁夏地区大后方的文化抗战指明了道路与方向。
第三,关于戏剧创作研究。戏剧创作是《宁夏民国日报》之中着重探讨的一大内容。纵观其中所刊载的戏剧理论文章不难发现,既有涉及到剧本创作的内容,也有涉及表演、舞美等内容的文章。在剧本创作方面,主要的交代了剧本创作的基本理论。如《剧本中的伏线》一文,对小说与戏剧两者创作的差异作了细致的分析。“剧本需要明白诉说其中的情节,不应向观众保留一丝一毫的秘密,一篇小说可以把一个人物的性格留到最后才点明,但是剧本就不可以。”[13]这就直接突出了剧本创作之中人物性格典型的意义。此外,强调在剧本创作之中,运用道具必须要合乎时宜。“如果一部剧中的关键有一个道具,这道具必须要观众事先知道他的存在,否则,到了高潮时,观众就不会以全力去注意他的人物与动作,而为道具所分心了。”[14]除了剧本之外,《宁夏民国日报》之中也有不少文章是涉及到演员表演的。针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一位优秀的演员在进行表演的时候必须要做到“服从”与“研究”两大基本要求,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服从而不研究,那还是等于有了肉体而没有灵魂,所以我们除了信仰导演,服从导演,接受导演的纠正外,我们还要研究……除了研究导演给你的以外,你更要深切的去观察人生。”[15]这些戏剧创作、表演理论为当时宁夏地区戏剧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第四,戏剧形式内容的归纳。除了上述三大基本内容之外,《宁夏民国日报》之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是对戏剧形式内容的总结与归纳,如对悲剧、喜剧的基本特征的总结,对戏剧形式的分类归纳总结,都已经成体系化,为当时宁夏地区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报刊业的迅猛发展,为宁夏本土戏剧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平台。抗战时期《宁夏民国日报》上所刊载的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文章都以当时抗战现实活动为出发点,是宁夏本土戏剧理论的建构的最初尝试。这些理论对促进戏剧理论观念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融合,提升演员们的舞台表演艺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抗战时期宁夏戏剧的审查制度与教育功能
抗战时期,宁夏作为大后方,本地区的社会教育相较于之前有了迅猛的发展,本地区的社教基础与社教建设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对于开启民智,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当时民国政府所推行的战时社会教育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便提出“教育部为适应战时需要,使各级社会教育机关,得以充分发挥效能起见,特于二十六年九月订定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通饬遵行”。[16]正式拉开了战时社会教育工作的大幕。进入到全面抗战之后,民国政府更加认识到社会教育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抗战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民众教育是和政治,经济以及民族的发展生存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定的教育方式之下,常常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而这种社会意义就支配着整个民族的活力。”[17]进而,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社教举措,来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如对社教机构进行调整、成立多所社教学校、推行战时民教等。受到民国政府这些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宁夏大后方地区的社教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成立了省社教委员会。省社教委员会成立后,大力开展社教活动,如在各县成立社教分班,进行社教活动,创办了专门的社教壁报,加强社教宣传。这些政策,对于发挥抗战社教工作的开展作用显著,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则是对于战时戏剧社教作用的运用。
戏剧的教育作用在清末民初已经开始凸显。三爱在《论戏曲》一文中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18]随后蔡元培等人继承发扬了戏剧的这种社会教化的作用,突出强调戏剧的美育价值。进入到全民族抗战后,戏剧教育的作用开始被进一步的凸显出来。“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战时戏剧社会教育功能高度认同,制定了与戏剧相关的社会教育规划方案并积极实施。”[19]宁夏作为大后方,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本地区戏剧事业的发展,成为当时宁夏大后方一种针砭社会治理的艺术武器。
(一)审查与出版:战时剧本创作的常态化
进入到全面抗战时期后,为了尽可能的发挥戏剧的社会教育的作用,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戏剧出版演出审查条例,这些条例成为战时戏剧出版与演出的重要准则。1940年国民政府文化部门颁布了《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其中乙类涉及到当时抗战剧本的内容审核要求。“ 一、为敌人及傀儡伪组织或汉奸宣传者;二、描摹社会反动心理(悲观与消极),或夸大敌人优势,足以削减抗战必胜之信心者;三、同情或宽恕汉奸之际遇与活动,足以妨碍国人肃清汉奸之决心者;四、鼓吹不合抗战要求之异说,足以削减抗战情绪,影响抗战前途者;五、描摹军事上之弱点,足以影响战事之进展者;六、描摹伤兵失检行为或表现军民龃龉情况,足以离间军民合作之情感者;七、描摹战时社会畸形动态,足以懈怠抗战情绪,影响抗战前途者。”[20]在进行剧本的审查的时候,必须要仔细审核剧本情节是否触犯了上述几点要求,这也成为战时各省市戏剧剧本审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宁夏作为抗战大后方,在进行剧本审查的时候,也尽可能的与当时战时民国政府的要求相契合,因而出台了一系列剧本审查条例。为了适应宁夏地区抗战戏剧创作的要求,宁夏戏剧改良委员会根据民国政府剧本创作的要求,制定了本地区秦腔剧本创作规定。1941年4月23日,《宁夏民国日报》刊载了《宁夏戏剧改良委员会征集秦腔剧本》一文,其中规定了剧本创作的七条基本要求“一、本省为扩大抗战建国宣传,改良秦腔戏剧起见,特征集秦腔剧本;二、本会添设剧本编审部,专习征集剧本事宜;三、编审部设主任1人,专习编辑2人,特约编剧若干人、书记1人,专门编辑及书记薪俸另定之;四、凡本会编审部人员或外会人士创作剧本,经全体编辑审查,认为及格者,由本会呈请省政府发给润笔费,每本戏200元。若经排演,获得社会人士之好评者,另由本会呈请省政府酌给奖金,并由觉民学社提拔每次公演票价收入之3成,共3次,作为酬劳;五、凡有以我国历史作为材料,发挥适合抗战建国之意义,创作、编辑5本或10个戏曲者,除每本照前条之规定请奖外,并呈请省政府另检特别奖金;六、剧本词句以通俗文字、官话占全部为文,白话占三分之二、唱词占三分之一为宜;七、剧本内容以阐扬民族精神,鼓励抗战情绪为主旨,其有故意暴露国家、民族之弱点,诋毁政府之政策,作反动宣传者,概禁止排演。兹分下列数种:(1)抗战戏曲:凡描写抗日将领英勇牺牲、爱国民众深深纡怀之事实,足以动员民众抗战者。(2)社会戏曲:凡足以劝导民众本新生活信条,提倡“四维八德”之社会伦理者。(3)家庭戏曲:凡描写我国家庭情形,喻示观众,慈孝友恭者(4)历史戏曲:凡就我国历史上忠孝节义以及政治得失等,足以鼓励民众抗战情绪者。”[21]这一条例的颁布,为宁夏地区剧本创作指明了方向。战时戏剧审查出版制度的确立,成为当时宁夏地区社会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其对战时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宣传与启迪:抗战戏剧与社会教育
有研究者指出“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动员民众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戏剧。”[22]抗战期间宁夏全省有70余万人口。1941年该省总人口为73万,而此前一年全省所有国内专门以上的学校毕业生仅34人,肄业者17人,急需通过加强社会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如前所述,抗战时期,宁夏地区成立了多个社教团体组织,这些社教团体组织,为了能够充分动员大后方民众,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与斗志,选择借用戏剧这一艺术样式,来进行抗战宣传。社教团充分发挥战时戏剧的教育宣传作用,通过多种措施来动员大后方的民众。
其一,鼓励剧本创演。社教团为了尽可能的发挥战时戏剧的宣传教化作用,采取多种措施来鼓励宁夏大后方进行戏剧创作。如设立剧本创作奖,对创作优秀剧本的作者进行褒奖。社教团为了丰富宁夏边区大后方民众的娱乐生活,鼓励当地剧团、剧社从全国各地采购剧本,并逐次在宁夏各地区进行演出。如“觉民学社,新由西安购来大批剧本,计有:颐和园、复朝鲜记、大婚姻谈、侠凤奇缘、优孟衣冠、吕四娘、一字狱、桃花泪、青天白日、水淹下邳、阿毛传、文君当垆、自由恨、一拜缘等二十三种。闻上述剧本,多系勉励国人,精诚图结,一致对外,及国家民族之责任。”[23]这些剧本,大多以鼓舞民众为出发点,在宁夏各地演出后,起到了重要的动员民众的作用,效果十分显著。
其二,扶持本地区戏剧运动。为了能够充分的发挥戏剧的教育作用,宁夏地区社教团多政策扶持本地区戏剧运动。学校是宁夏地区戏剧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为了能够发挥各地区学校在抗战戏剧运动之中的作用,宁夏各地区的学校所开展的戏剧运动进行扶持。“本省省立宁夏中学为欢送本年夏季毕业同学,特定于本月(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时,假省府礼堂公演《黑字廿八》三幕名剧一节。本报顷悉该校以演出费困难,特呈请省党部予以补助,省党部为推广及鼓励各级学校之戏剧宣传起见,已准予补助该校,此次公演津贴三百元云。”[24]这一措施大大鼓励了宁夏地区各级学校的戏剧运动,从此之后,各级学校更加如火如荼的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培养了众多剧运人才,为宁夏地区戏剧运动进行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宁夏地区社教团还创办组织戏剧节活动的开展。戏剧节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戏剧活动。戏剧节的创办,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戏剧节第一重大意义,是在于使得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互相观摩,互为参考,并且藉以有一个友谊的比赛的机会……第二个重大意义是戏剧的总检阅日……第三重大意义是告慰亡灵,鼓励生者。”[25]宁夏地区戏剧节的开展,大大发挥了戏剧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作用,社教团通过多种形式的戏剧演出,发挥了抗战戏剧的教化作用,对当时宁夏本地区的戏剧运动起到了重要的辅助性功效。除此之外,宁夏戏剧节为宁夏地区培养了众多专业的戏剧人才。“戏剧人才的造就,这是我们当务之急。戏剧界的同志们应当很担忧地负起戏剧教育的重担。”[26]。而戏剧节的举办,为戏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契机,涌现出不少优秀专业的戏剧人才,为戏剧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地方路径作为近期中国现代文艺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其旨在将研究视线对准以往未受到充分关注的地方文艺现象,充分考察带有显著特殊性的地方文艺与文学的建构演变过程,由此挖掘出不同于以往文学史观下的现代文学发展经验。以抗战前后的戏剧史料为基础,本文比较详尽完整地揭示了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以“戏剧”为中心的宁夏抗战文艺建构过程,并且从中能够窥见该时期宁夏文学建设的整体风貌。抗战时期的宁夏戏剧界始终处在同民族革命这一时代任务的纠缠过程,并且透过包含建立社团、官方文艺政策等多种手段,强化宁夏戏剧艺术所肩负的社会历史责任。相信这种将地方路径、文学制度与文学史料三者相统一的研究思路能够有效和多元充分地完成针对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的阐释过程,而这也有机会顺应了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