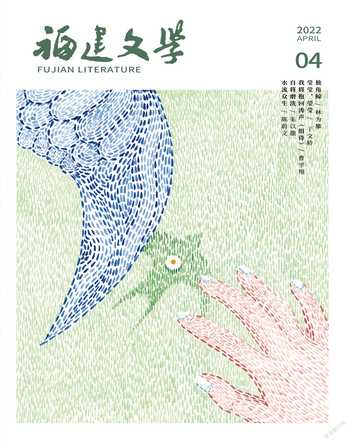有朋自远方来
2022-04-12茅草
茅草
1.敲门声
敲门声像一粒粒珠子,甚至听得出比较圆润,落在门扉上,像落在玉盘里,发出清脆的、空灵的回响。
你从书房里跑出来,对着门大声喊:我来啦。生怕外面的人听不见,又提高嗓门:稍等,我来啦。
经过卧室门口,来到客厅里,敲门声停止了片刻,又响起来:咚咚——咚咚——
你站在客厅里,没有立即去开门,离门大约一米五远,欣赏着这敲门声的美妙:不轻,不重;不急,不躁;不想打搅你,又要让你听到,每一个音符的音值、振幅都相等,好像是贝多芬在弹奏《月光》……
在岗位上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谈工作、谈心、谈感情、谈相同点……在办公室里已经谈得够多了,还不够,到家里来谈更贴近。有时,很晚了,有些累了,脱掉衣服准备睡觉,电话却响了,邀你到江边去喝酒:天上有月亮,水里有月亮,酒里也有月亮,委实浪漫。可是,你不想活得那么累、那么烦琐,一听到敲门声就头皮发麻,假装没有听到,让热忱的敲门声最终凋谢。
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敲门声和电话振铃声也随着急剧地退下来,就像夏季跳过秋季直接进入冬季。冬季是寒冷的,少有走动,一个人关在家里深陷寂寞、孤独,恨不得原来的敲门声重新繁茂起来。
咚咚——咚咚——
你闻着敲门声走到门后,将门扯开一条缝,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年轻小伙子站在门口,脸瘦而黑,漫无表情,但你觉得他英俊,讨人喜欢,好像他还特意对着你微笑。他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你的寂寞中,以敲门的方式打破你生活的平静,给你带来了友谊和希望。
您的快递:亲切、悦耳的声音。
你赶紧伸出去一双手,接过来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裹:牛皮纸包的,包得细心、讲究:面上平展,边角见棱,透明胶黏得整整齐齐,像一个吉祥的艺术品。
2.文学启蒙
你们这一代人,好多人都怀有文学梦想,准确地说,是跟文学结下了不解情缘。你与文学的情缘带有传奇色彩。
那天下午,你在村里晃荡:大人们在田里、地里忙庄稼,小孩们在山上忙砍柴、在水里忙打鱼摸虾,你啥也不会干,一如既往地在村里闲荡。荡到一间茅房门口,内急,拐进去,一阵噼里啪啦之后,找纸擦屁股,脚旁边出现一本书。这一本书的出现纯属偶然,更偶然的是你没有拿它擦屁股,而是把它带回了家。原来它是茅盾先生早期小说三部曲中的一部:《蚀》。你看着封面上写着“蚀”“茅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而内容却很上瘾:静女士、慧女士,上海的年轻女人,那么美丽、多情,一下子就照亮了你的眼,让你进入她们的气息中,同时进入无限的文学生活空间里去。
接下来,你受着一种文学魔力的支配,把凡是跟《蚀》一类有人物、有故事、有爱情的书全部找来,一口气读完了《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铁火金刚》《前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等几十部书,还用手里的零花钱买到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连心锁》。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读书人”。
无心插柳柳成荫:高考恢复了。村里除了你,没有谁肚子里装有那么多书作为底气,也就没有人敢报考,只有你早早起床,一口气赶到县城里去报考,偷偷地准备了两个月,一考就考上了大学。穿着绿衣服的邮差把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你手里,村里人,包括你父母都一脸的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3.文学观念
你们这一代人基本上走了相同的路:从文学开始进入生活,不知不觉地提升文化水平和综合素养,或登堂入室进入文学艺术机构和文学艺术队伍;或通过几年的大学中文系深造,再分配到文学艺术单位或新闻单位。这成了很多热爱文学、追求文学的人的梦想。在老家时,你就跟地方文化局、文化馆、广播站、文工团有着亲密的联系,觊觎着它们招人;大学分配时,你做了很大的努力,差一点就进入了专业的文学创作机构。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告别文坛踏上谋生的路,文学就成了一个谋生的工具甚至道具:这些人多半在办公室从事文秘性质的工作。这并不等于说不在文坛就忘记文学,更不可能背叛文学,而是一如既往地对文学孜孜眷恋,总是在业余时间关注文学、谈论文学,有的人继续保持阅读甚至写作的习惯,向报纸杂志投稿,成为一个业余作家。你就是后一种。办公室里,你柜子里总是放有一些文学书籍;家里的房间分配,你从来就没有忘记留一间当书房;出差时,行李箱里放有文学书籍;开会时,偶遇灵感,在会议记录本上记下几行诗或几个人物、故事框架。现在,你告别了自身不属于文学的历史,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终于回归到文学身上,也算是第二次开始你的“第一生命”。
從岗位上退下来重回文学的感觉,就像是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退下来,突然躲进了一片深山老林,精力和灵感就是王维的山水诗句:“清泉石上流。”两个月不到,十几首诗和几个短篇小说的构思就长出血肉来,成为完整的“作品”。你拿着这些“作品”兴冲冲地来找已然是专业作家的大学同学,请他提修改意见。在学校时,你跟他的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他在报纸杂志上发一个短篇小说,你也在报纸杂志上发一篇散文,稿费不相上下;现在,他著作等身,全国知名,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默默无闻的工薪族。
作家同学开始看得很仔细,越到后面越快,像是不用看、不必看、不值得看。你开始忐忑,自信心受到威胁或伤害。作家同学放下打印稿,望着你,目光含笑,却不知是真笑还是假笑,欢笑还是嘲笑。你如芒在背,额头上沁出了热汗。
写作的基本能力还是在的……作家开口了:但语言和表达还是我们读大学时的那种状态,现在都不这么写了。
那……怎么办?你帮我改一改?
作家同学笑:改是改不出来的,得你自己转型,然后再写。你看,李瑛、王蒙为什么能成为文坛的常青树?除了不竭的生活动力、创作灵感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保持文学观念与时代共呼吸。
你的意思是……我的写法过时了?
确实。巴特尔的《写作的零度》你看过没有?
你摇头。
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你看过没有?
你又摇头。
那你要系统地读一读这些书籍。
作家同学说得对:这些年,你就没有系统地读过文学作品,更不用说文学理论,而文学在你为生活操劳、奔波期间,它并没有停止向前行走的步伐。你走出大学校门、走进单位大门,文学已经把你甩掉了38年。你要缩短被它甩掉的距离,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系统地补课。
4.读书使观念进步
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剪开,取出一本书,像从子宫里取出一个婴儿。乔国强、薛春霞合著的《什么是新批评》,也是你新结识的“朋友”。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它求助,它永远不会背弃你。”工作了半辈子,你交了不少物质上的好朋友,现在,这些朋友都帮不上你了,你也帮不上他们了,也就相忘于江湖,最缺少的就是臧克家所言的“读了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新批评“是指20世纪初肇始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并于20世纪40—50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占主导地位的新批评派”。它对文学的核心意义或影响是唤醒了文学自身的独立、自为意识。虽然只活跃了40年,但作为一种“相对的经验”,对后来以至当前的文学观念和写作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什么是新批评》只是一本内容简要的书,罗列式介绍了一些“新批评”的主要观点、人物和典籍。你沿着它勾勒出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镜与灯》《阿克瑟尔的城堡》《新批评》《批评的剖析》《结构主义诗学》《新批评之后》《语象叙事研究》等。通过阅读,自“二战”以来的文学观念和各种文体的写作与变化,在你的头脑里慢慢地显示出轮廓:诗歌已从“主观抒情”转变到“客观叙事”;小说叙事已从注重“讲述”转变到注重“展示”;散文已从一个笼统的体裁细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随笔、杂感等,各种文体的不同写法随之明显地区别开来,而“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巴特尔《写作的零度》所阐述的主要观点,也都体现在这些变化之中。
再看你的“作品”,就很难说是作品了,多半是缺乏时代感、写作方法陈旧的“废品”。“意义”在胡塞尔那里,被陈述为“表达式”,而在你的写作中,依然是在一大堆客观的记述之后,再推演出一个深刻的“主题”,被称之为作品的“灵魂”,“灵魂”凌驾于“表达式”之上,也臣服所有的文学要素。这种写作或表达的方法,容易走向程式化、概念化的极端,使作品的意义和形象系列产生明显的裂缝,其实就是“讲述”,而非“展示”。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强调到“文学能力”:现在的读者群的综合文化素质大部分已提高到高中或大学水平,其阅读的姿态已不满足于“表达清晰”“主题鲜明”的“讲述”程式,而希望“展示”给他们更多的悬念和回味。意义的“含混”或“朦胧”比“清晰”“鲜明”更合他们的胃口。这就要求写作者把“讲述”意义的冲动转化为对一系列“表象”的描述,追求整体的意义、构思、结构之类的元素,都要一一拆解开来,朝着德里达的“异延”方向化解为具有更大、更多诱惑力的碎片。
5.意外的收获
全世界70亿人,通过一个熟人找到另一个熟人,一个一个地找下去,最终都可以成为熟人或朋友。有趣的是,谷歌通过计算机算出全世界有1亿2900多万册图书,从一本书里面发现另一本书,最终也能把所有的书都找到。用这样的方法,你找到了你想阅读的名著,也偶遇到你意想不到的“朋友”,比如鼎鼎大名的威廉·燕卜逊所著《朦胧的七种类型》。
你们这一代人,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朦胧诗”再熟悉不过了。当时,《诗刊》刊登了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引发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随后,就把北岛那一代诗人写的“象征诗”称之为“朦胧诗”。燕卜逊所说的“朦胧”跟这个“朦胧诗”有关联吗?这是阅读的局限推迟了40多年的“兴趣”。
从时间上看,章明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930年《朦胧的七种类型》在英国出版,66年后,即1996年才由周邦宪、王作虹、邓鹏合译,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朦胧诗选》和《朦胧诗精编》于1986年分别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朦胧诗”借用于燕卜逊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是直接从章明的文章中套用的“朦胧”二字。从词义上看,两个“朦胧”的词义是一致的,都表示“含混、不确定、歧义、难懂”的意思,然而,前者是从正面肯定的,认为“一切白话陈述都可以说是朦胧的”,“伟大的诗歌在描写具体的事物时,总是表达出一种普通的情感,总是吸引人们探索人类经验深处的奥妙,这种奥妙越是不可名状,其存在就越不可否认”;而后者则抱有质疑、否定的态度,认为诗歌越是明白、易懂越好。
《朦胧的七种类型》从孔夫子二手书店所购,出版的年代太久,又经人看过,形象很不雅观。可是,没有新书来替代它。它就像是一个衣冠不整的“朋友”,一直坐在客厅里等你,却不受待见。书跟人一样,老不接触、不了解、不沟通,就有一种隔膜感、陌生感,而一旦接触起来,尤其是合得来的,就会建立起感情,带来意外的收获。你从接触到文字和表达开始,就力求“言简意赅”,尤其是意义越鲜明越好,可是,燕卜逊的观点恰好相反。细细品味当下流行或被热捧的诗歌、散文、小说,其主题似乎都在契合燕卜逊的观念。有趣的是,当年以魏尔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一个个像吃了药似的迷恋于“象征诗”的写作时,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法朗士在一旁也像我们的章明一样对“象征诗”不满,说文学作品是需要人阅读和理解的,你们写出这样叫人理解不透的作品,不可能有未来。很多人都相信法朗士的判斷,然而事到今天,法朗士错了。“象征诗”在从它诞生之日起的100多年内,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不少人还在写。不能不说,这跟燕卜逊对“朦胧”观念的鼓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人不可貌相,书也不可貌相。《朦胧的七种类型》纸张陈旧,但意义没有陈旧。它被你摆放到了最重要的一类书籍中,书中的内容就像作家同学对你说过的话,一直亲切地回响在你的脑海里。
6.不亦说乎
门又被敲响了。又有一位“益友”来到。在你家里,天天都有“朋友”聚会:一些“朋友”坐在书架上,一些“朋友”匍匐在书桌上,一些“朋友”与你执手交谈,还有一些“朋友”正在路上,加快步伐朝你这儿赶。你找“朋友”的手段基本上不再到实物书店,而都是在网上,就跟找网友一样。首先是满足于当当网上的电子书,这个不用花钱,可以免费“悦读”,或者花少量的钱就可以买到电子书;没有电子书就网购纸质书,新书没有,孔夫子旧书网上基本上都有。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朋友”在路上往你这儿赶。你每天都要上网查看物流进度,看它们已经到了哪里。你很感谢物流运输在网上的设计,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你渴望到达的对象,每时每刻正身在何处。等待的过程,就是希望的过程,它充实了你的生活在流逝中的寂寞与虚妄。
说到孔夫子,《论语》开篇就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多数版本直接引用原文,没有解释或翻译“朋友”二字,而金良年先生的译本与众不同,不仅翻译了,而且比较准确:“有共同见解的人。”避免了作一般意义的“友谊”解。你与金先生也达成“共同见解”:“有共同见解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有什么样的朋友比书更具有“共同见解”的呢?
7.朋友亦书
上次带着手稿去见了作家同学之后,你就不打算再去麻烦他了,尤其是有了这么多书做“朋友”之后,还有什么必要去麻烦他人呢?作家同学也明确地说过,看人家写的东西,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意思是,不管写得好不好,人家都认为自己写得最好,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有谁觉得自己生下来的孩子不好呢?要是真写得好倒也无所谓,说几句好听的话都高兴,可大多都是写得不怎么好,说好就是违心,说不好人家又不高兴,有时意见说得越多,人家越不高兴,实属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可是,你又觉得到火候了:让老同学说你好、不再为难的条件已然成熟,决定还是去见他一次。
作家同学打开门,见是你,那表情好像在说:你又来了?是的,又来了,搞写作的人就是这么难缠。你从背后拿出一包酥糖,作家同学吃了一惊:怎么?不是看稿子?你笑:这是我刚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你最爱吃的。作家同学拿过酥糖去,拆开一块就往嘴里塞。先给他一点甜头尝尝。
嗯,好!半个小时后,作家同学终于眉开眼笑,开始夸赞起来:真没想到你能转过来……
你还没退休的时候,也拿过作品来找过他,他就劝过你转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候你极需要发几篇作品来衬托你自己,帮衬你晋升。可是,作家同学没有成全你的好事,你也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帮得上就帮,帮不上就不帮,还转什么型!其实,作家同学也没有因此怪你。他也劝过其他很多业余作者,都跟你一样的态度,他深知,不仅是功利因素的影响,本身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一个观念与另一个观念,要实现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主体对于自我的认同一向都非常顽强,正如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先驱边沁所言:“错误从来没有像当它扎根在语言中那样的难被消除。”你似乎也感觉到作家同学对你已怀有偏见,所以,以怀疑的眼神望着他:是真的吗?
作家同学朗诵起来:
中 转 站
路的枢纽。路在这里碰头
然后交换,分散,再次走向四面八方
人各怀有目的地
路却不能一次性抵达
需要改变方向,再次改变方向
人坐在车上
车的方向改变了,人的方向随之改变
也有的车改变了方向
而人的方向改变不了
事实上,车的方向、路的方向
都是人的方向
作家同学接着说,这首抒情诗改变了你一向擅长的直抒胸臆的角度,而是从叙事出发;诗中没有通常所见的抒情主体“我”,“我”退让成一个隐性叙述者,还原给诗自身或语言自身在场。按照艾略特的说法:情感找到“客观对应物”,你的“客观对应物”就是“中转站”,通过“中转站”的隐喻,把你要抒发的感情和思想立场都客观化在你所描写的客体中,也就是诗意的“表达式”。你是在单纯写中转站吗?还是在写来来往往、相互转换的车辆?或是在写车与人的社会关系?不确定,交给读者去联想,而这就是比较理想的阅读效果。虽然作品还不见得十分成熟,但至少你已经转过来了,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写作。真的,很好。
为了庆贺此事,大家相聚在江边28层楼的旋转餐厅。应邀的同学、作家都来了。黄昏时分,天边的晚霞洒在宽阔的江面上,十分壮观。你坐下来,不知是自己在转动,还是周围的城市、江水在轉动。杯子举起来,大家一起碰杯,作家同学说出今晚的主题,大家一起向你道贺。每个人的脸都是诚挚的,每个人的话语都像书里的语言一样流畅、合乎语法,尤其是作家同学的表情和话语,就像是他新杀青的又一篇散文或小说。
有朋友真好,好朋友也是有益的书。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