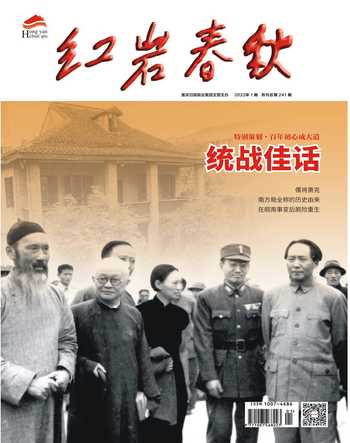我和志愿军战友 在朝鲜亲历反细菌战
2022-04-12康绍禹胡婷颜波
康绍禹 胡婷 颜波



康绍禹,生于1935年6月15日。1951年入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卫生处防疫队防疫员。1961年,任第七军医大学外科军医。1992年,任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副教授。曾参与编写《临床外科治疗手册》《烧伤治疗学》。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抗美援朝那段峥嵘岁月,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历经战火硝烟,我幸存下来,但我的很多战友却长眠在白山黑水间。回忆往昔,我总会想:那时,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们前仆后继、出生入死?
山河已无恙,铁血今犹在。那些逝去的日子,终将成为伟大历史的生动注脚,成为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
写血书申请入朝作战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父亲去世早,我们一群孩子跟随母亲四处讨吃求穿,日子十分凄惶。
1946年4月,哈尔滨迎来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和饱经日伪铁蹄蹂躏之苦的所有同胞一样,我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赴朝鲜战场是那时候的年轻人最大的渴望。
1951年1月25日,不到16岁、个头不足1米5的我,从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防疫学校的一名娃娃兵学员。
参军不久,我所在的部队就要入朝。母亲舍不得我走,我的鞋子坏了,她故意没给我换。但我下定了决心。报名时,我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那天早晨,我连饭也没吃就悄悄走了。可就在我们即将出发前往辽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的时刻,母亲赶到火车站,匆忙间只顾上塞了一双鞋给我。离别时,我一直没有回头,不忍心再看她那焦虑不舍的眼神,我也知道一回头,留给她的将是更多的牵挂和担忧。
从安东出发,队伍徒步行军,一路高歌“我们是志愿兵,年轻又英勇。伟大的祖国,号召我们去打美国强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中,我们过了鸭绿江,来到朝鲜新义州。
没想到,我们刚离开祖国的土地就进入了战场。当时敌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对新义州火车站进行猛烈轰炸。我们距新义州火车站大概有七八里的路程,只感到大地在颤抖,远处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第一次亲临战场,我和战友们心里都不免一阵恐惧。
由于敌机持续轰炸,公路上到处都是弹坑,而我们距离目的地还很远,所以只能每天步行几十里山路。白天要躲避敌机轰炸,我们多半只能在夜间行军。记得有几天遇到下雨,我们衣服全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后来雨总算停了,但害怕暴露目标,我们不敢生火,也没有多余的干衣服替换。一路上,我们累了就靠着松树打个盹,稍作休息;饿了就喝点凉水,吃点炒米、炒面。虽然条件艰苦,但同志们斗志不减。
第十天,我们终于到达了阳德郡——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所在地,没有一人掉队。
积极投身反细菌战
作为一名防疫员,我亲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
我清楚记得,那天是1952年3月8日,部队组织了文艺节目,其余战友都看表演去了,只有我和李占臣在战地值班。
虽是开春季节,山林里仍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俩在野外巡逻探查时,发现在一片几平方米的雪地上,密密麻麻有很多苍蝇,其中不少苍蝇在一米左右的高度嗡嗡乱飞。
此前,我们接到过通报,美军飞机多次出现在朝鲜铁原郡金谷里和平康郡下甲里等多处志愿军驻地上空,之后驻地就出现了大量苍蝇、跳蚤等昆虫。其后不久,这些地区的部分朝鲜民众和志愿军战士就感染了霍乱等传染病。
想到这里,我立刻戴上手套,拿瓶子采集苍蝇标本。由于手里没有其他工具,我便用鞋子滚出几个雪球,将苍蝇裹在雪球里冻死,然后掩埋,防止病毒扩散。
由于后勤部二分部没有检测条件,我立即上报,将标本紧急送往位于成川郡的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防疫大队检验。检验结果证实,这些苍蝇确实带有霍乱弧菌、大肠杆菌等病毒。
志愿军各级指战员迅速展开反细菌战动员教育和疫情防控知识普及,介绍反细菌战的基本知识和医疗技术,要求战士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我和防疫队的战友们立即将收集到的可疑标本送去防疫大队检验。
即便這样,各种感染性疾病仍在阳德郡区域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志愿军战士的生命安全。
一天,志愿军工兵第10团的一位通讯员突然呼吸困难,不停咳嗽,还咳出了带有黑色的血块。检验后发现,他感染了炭疽杆菌。这是一种通过接触感染的病菌,可引起人体皮肤及肺部损伤,病毒已经侵入他的肺脏。
我负责照顾他,他咳出来的血常常喷在我的口罩上、脸上和身上。虽然室内外进行了彻底消毒,但我们的防护装备非常简陋,稍有不慎,炭疽病还可能致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居然一点都不害怕,反倒为这位战友的病情揪心不已。
他的肺部感染严重,大部分组织已经坏死,加之我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也缺乏医疗器材和设备,最后,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在自己面前牺牲。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到这里,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流下来。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志愿军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在防疫委员会领导下,志愿军各级均建立了防疫组织和防疫力量。
为尽快打赢细菌战,阳德郡地区的志愿军对阵地、山沟、小河等地进行了疫区封锁,不准进出。每天吃过早饭,服用一片抗菌素后,我就背着20多斤的消毒水,进行不少于6个小时的疫区消杀,有时忙到连喝水、吃饭都没有时间。
除了霍乱、炭疽等病毒外,在阳德郡等地,我们还发现了鼠疫。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完成房屋、阵地和道路的消杀工作后,我们还要捕杀老鼠,每天从早忙到晚。从1952年3月到6月,我在阳德郡的四个疫区进行过防疫工作。
经过中朝军民的英勇斗争,美军的细菌战阴谋逐步被瓦解,反细菌战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生死之战上甘岭
1952年10月,我军已经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局势,10月14日,“联合国军”先后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防守的约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发起持续进攻。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我与二分部卫生处八个战友,上前线紧急支援志愿军野战医院。我们到达时,敌机正不断对上甘岭阵地进行轰炸,加上美军的地面炮火,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火光和巨大的黑烟。
入朝参战一年多,面对敌机和警报,我和战友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了当初刚踏上朝鲜土地时的紧张和恐惧,在何种险境中,都能照常工作。
当时,我在野战医院主要负责伤员接收、伤情检查和信息登记。
上甘岭战役期间正值严冬,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摄氏度。有些伤员头部受伤不能包扎,否则一旦结冰,换药时纱布就取不下来。有一个伤员脸上被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嘴周围全是冰溜子,一夜都不化。我给他喂饭时,面条要一根一根送到他嘴里,喂一顿饭要花上两个小时。还有一个伤员脚受伤,手术后裹着纱布,无法穿鞋,冻得直哆嗦。在往后方运送途中,我解开自己的大衣,把他的脚放在我怀里取暖。后来影视作品中出现过类似的情节,是真实的写照。
我在野战医院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实在太累了,就和战友背靠背打个盹。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这场残酷的战争早日结束,希望我们的将士不再负伤牺牲。
上甘岭战役开始后,我在前线待了两个多月,直到志愿军守住阵地,取得了胜利。
之后,我还支援参加了金城战役,参与清点和往前线运送炮弹。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我见证了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争结束后,回国的志愿军战友们都想去一次北京,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影,纪念这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实现医学梦想
抗美援朝期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医学梦想也就此深耕于心。
回国后,我考入第二军医大学,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七军医大学。1962年,我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医疗救护工作。
做实习医生时,我不仅做到及时诊断,还为危在旦夕的肠梗阻病人办理住院手续,和时间赛跑,挽救其生命;为患血吸虫病的聋哑小女孩检查化验单,开具住院证,保证她及时手术。
成為医生后,我兢兢业业,守护在脑外伤病人床前120多天,直至其康复;徒步走10多里路,将不能行走的骨癌晚期患者背送回家;把和妻子共同省下来的500多斤粮票,送给家境贫寒的病人。
自1963年起,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野战外科研究所工作。野战外科研究所搬到重庆后,准备培养一些烧伤研究方面的人才。由于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实际战地医疗经验,加上对医学的执着追求,我被选中培养。此后,我开始从事烧伤方面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
从1968年开始,我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西南医院)的烧伤研究所一直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当年,面对战友牺牲时的无力感,让我不断坚定信念,对自己医术的要求也精益求精。
1970年4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烧荒引发严重的森林火灾,有200多例烧伤伤员。其中71例重伤员被飞机送到哈尔滨抢救,分到5个医院进行治疗。野战外科研究所派出4人医疗小组赶赴哈尔滨,参加第五医院的抢救工作。我们共处理了2例吸入性损伤和9例双手重度烧伤者。在第五医院病房,我看到救火受伤人员的手已经收缩变形,皮肤烧伤严重,需要及时手术。
烧伤后的三到五天是做手术的最好时机,我在三天两夜里连续做了9个病人共18只手的早期切痂植皮手术。最后,他们的手基本恢复了正常功能,11位伤员也全都康复。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效果也实属罕见。
后来,我还先后赴贵州遵义,重庆南桐、綦江等地煤矿,抢救因瓦斯爆炸大面积严重烧伤的病人。每次面对十几位烧伤病人,我都是连续几天甚至一周多坚守在手术台上,把危重病人抢救过来。
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多年的医学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一直激励和支撑着我,贯彻在我每一次的救治工作中,落实到每一位病人身上。
1987年,四川省云阳县(今属重庆)一硫铁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数名工人不同程度烧伤。我带领市急救中心烧伤专家临危受命,火速前往救治。一个多月后,云阳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欢送我们,云阳县委书记特地为每位医护人员准备了200个土鸡蛋。我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说“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1992年12月2日,贵州有机化工总厂在研制新产品的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10余位同志负伤,其中几位同志严重烧伤,生命危在旦夕。西南医院闻讯后,立即派我和另一位烧伤治疗专家赵阳兵赴黔参加抢救。从9日开始,我主刀,与赵阳兵、贵阳医学院和贵州省人民医院的同志一起,一连几天不下手术台,一次次把垂危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93年,一天晚上快下班时,医院送来一个脸色苍白的病人,当时他已经出现了点头样呼吸,处于极度衰竭状态,奄奄一息。
经过现场紧急诊断发现,该病人是胸部高压电击伤并多发伤,情况十分危急。我马上带领医护人员把他抬进手术室。
该病人的肝脏组织存在烧伤,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救治方案,更谈不上治疗经验。我无暇他顾,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病人救活。于是,我在他的肝脏、膈肌和肺脏上进行创造性植皮,终于成功把他救活。
该病例是全世界首例,我因为成功救治该病例,获得了1993年第三军医大学医疗成果一等奖。
此外,我还做了新生儿深度烧伤早期切痂植皮手术,这在当时也是全球首创。
从医几十年,我成功救治了一大批烧伤病人,其中烧伤面积达50%以上的有30多人,面积达80%以上的有9人。还成功救治3名多器官功能衰竭,并且烧伤面积达75%的病人。救治烧伤并发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亦获成功。我还赴四川成都、广元,贵州遵义等地抢救40余次,均获得好的效果。
1993年,为了表彰我为国家的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特给我发放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荣誉证书。
退休后,我的孩子们,包括家属院的孩子们,都听我讲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我的孙子对我说,他以后也要学医。我说要想当医生,首先要正直、善良,能做到不忘初心和坚守信仰,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伤病员服务。
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我从事医疗事业,更让我感恩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希望自己和仍健在的战友们都能健康长寿,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