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皆重获”解*
2022-04-10常广宇
常广宇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中,记载了晋国的逢大夫为了挽救战败逃跑的晋国大夫赵旃而舍弃两个儿子生命的事件: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叟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
关于这段话中的“皆重获在木下”,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主要的聚讼集中在“重”和“获”上,也涉及“皆”的词义理解问题。
1.历代聚讼
杜预注:“兄弟累尸而死。”《正义》:“获者,被杀之名。并皆被杀,唯当言皆获耳,欲见尸相重累之皆获,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即《传》之‘重’也。”(孔颖达等,2013:397)
杜预以“兄弟累尸而死”注释“皆重获在木下”,用“累”训释“重”。关于“获”的词义,《正义》认为杜预把此处的“获”释为“死”,为了维护杜注,进而把“获”训为“被杀之名”。实际上,杜注并没有训释“获”,《正义》之训颇有些一厢情愿(详见下文)。
林尧叟:“兄弟累尸而死,故重获于木下。”(《左传杜林合注》卷十九)
林尧叟注同杜注,用“累”训释“重”,“获”未训。杜注和林注都未对“获”作训释,即二人都认为此处的“获”当为其常用义“获得”。竹添光鸿(2008:901-902):
获者,被杀之名也,并皆被杀,唯当言皆获耳,欲见尸相重累之皆获,故杜云“兄弟累尸而死”,“累”即传之“重”也。……重,平声。
竹添认同的正是《正义》的说法。焦循(2016:48):
获之言得也,谓二子皆寻得在所表木下,加一“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获在木下”,古人属文之奥也。《正义》以“获”为“被杀之名”,未是。
焦循驳斥了《正义》的意见,申明了杜预和林尧叟的观点,认为“获”的意义就是常用义“获得”;“重”义为“重叠”。杨伯峻(2016:810):
获之言得也,谓其尸两皆得之于其树也。说见焦循《补疏》。
关于“获”的意义,杨伯峻赞同焦循的看法,认为“获”义为“获得”。杨伯峻未提及“重”的意义。
可见,杜预、林尧叟两人默认“获”义为“获得”,焦循和杨伯峻明确指出此处的“获”当为“获得”;《正义》、竹添等认为“获”为“被杀之名”。关于“重”,以上诸家均无歧解,“重”义为“重累、重叠”。
此外,吴柱(2016)认为,“获”义为“杀”,“‘重获’之‘重’当读作‘轻重’之‘重’,去声,用作副词,表程度之深重,《广韵》读‘柱用切’”。
通过梳理可知,故训对“重”和“获”的意义均有歧解(详见表1)。

表1 “重”和“获”相关训释
以上观点,总结起来,可分为三类:
(一)“重”义为“重累、重叠”;“获”义为“被杀”。《正义》、竹添持此说。
(二)“重”义为“重累、重叠”;“获”义为“得”。杜预、林尧叟、焦循、杨伯峻持此说。
(三)“重”义为“深重”;“获”义为“杀”。吴柱持此说。
欲判别三种观点孰对孰错,需进一步探析“皆”的词义问题。
2.“重”的意义问题
关于“重”的词义,除吴文认为表程度“深重”外,历代注释家均认为表“重叠”。吴文之所以把“重”解释为“深重”,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语法证据,即“重”若为“重叠”义,则与“皆”矛盾,于语法不通;另一个证据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陆德明《经典释文》‘重获’下注云:‘重,直陇反。’可知陆德明亦读‘重’为去声,而非‘重叠’之‘重’。”实际上,这两个证据都有问题,第一个证据我们放在下文探讨,我们先看吴文的第二个证据。
现在通行的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所附的《经典释文》对此处的注释的确是“重,直陇反”,折合成今音也的确读zhòng,意义也正是“深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上声·肿韵》:“重,直陇反,不轻。”但是,《释文》此处实为讹误。据查,此处“重”的注音,所有单刊本的《释文》均为“直龙反”;与《春秋经传集解》合刊的《释文》或作“直龙切”或径注“平声”A国图藏宋刻《春秋经传集解》作“直龙切”,明刻本径注“平声”。,日本所见版本多如《会笺》径注“平声”;与《注疏》合刊的《释文》则以“直陇反”为常见B国图藏元刻明修本、闽刻本、明万历监本、毛氏汲古阁本和阮刻本此处均为“直陇反”。。此外,从《释文》内部体例看,“直龙反”常见, 仅在与《注疏》合刊的《释文》中有此一例“直陇反”,相应的上声陆德明通常用“直勇反”。种种迹象表明,此处的“直陇反”本当为“直龙反”,“直陇反”是与注疏合刊《释文》的误刻,不能作为论证“重”为“深重”义的证据。吴文用的是阮刻本,恰恰用到了不可靠的材料。所以,吴文的这一条证据不能支持“重”义为“深重”。厘清《释文》的问题后可知,“重,直龙反”应该是《释文》的真实面貌,而这也佐证了历代训诂家的意见,即“重”的意义为“重叠、重累”。
3.“皆”的意义问题
吴文认为:“若将‘重获’理解为尸体相重叠,则其前不能有‘皆’字。若云‘兄弟二人皆尸体相重叠’,于语法不通。” 这是吴文反驳“重”在此处为“重叠”义的第二个证据。可见,吴文把“皆”理解为一个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并且认为,在“皆”为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重”义为重叠的前提下,“皆重获在木下”在语法上是不通的。确实,如吴文所言前提下,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古人对此也早有察觉,所以《正义》有“唯当言”云云,焦循则归因于“古人属文之奥”。吴文未对此进一步论证,我们这里略加讨论。
“皆”作为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其范围指向表示所指向的对象(主语、宾语或名词谓语) 为复数,语义一般指向谓语, 对谓语起修饰作用,强调和突出谓语, 使主语具有谓语所显示出的特点或发出相应的动作。
基于“皆”作为副词的上述特点,“皆+V(代表谓语)+P(范围指向对象,语义上为复数)”这类句子可以作如下变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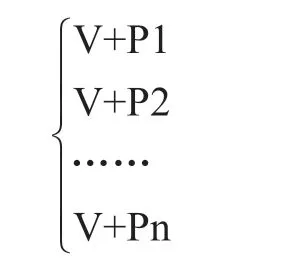
我们以《左传》中的相关句子为例说明。如:
(1)比及宋,手足皆见。(《庄公十二年》)
(2)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庄公二十八年》)
(3)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隐公元年》)
(1)中“皆”的范围指向对象为“手”和“足”,语义指向“见”。句子可以变换为:

(2)中“皆”的范围指向对象为“群公子”,语义指向“鄙”。句子可以变换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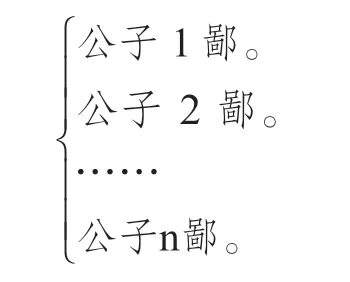
(3)中“皆”的范围指向对象为宾语“食”,语义指向“尝”。句子可以变换为:
根据以上规律,“(兄弟之尸)A此处主语据文义补充。皆重获在木下”这句话中,只有主语“兄弟之尸”为复数,自然,“皆”的范围指向对象只能是“兄弟之尸”,语义指向谓语“重获”,“在木下”是地点状语。这句话可以变换为:
“重”不是一个对象的状态,而是多个对象的关系状态,要满足“重”的语义结构,有两个办法:复数或者两个论元。《鲁颂·閟宫》“二矛重弓”,《郑风·清人》“二矛重英”,《周礼·天官冢宰·掌次》“重帟、重案”,《左传·哀公元年》“居不重席”等,这里的“弓”“英”“帟”“案”“席”都是复数。《左传·昭公五年》:“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楚辞·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重之以睦”“重之以修能”是两个论元的情况,一个论元用代词“之”替代,一个论元用介词“以”介引。“重”和英语中的overlap 非常像,overlap 语义上也要求有多个对象,其手段也是复数或者两个论元。复数的如:The generations overlapped because the Binns were an enormous family.(Simpson, John Andrew and Weiner, Edmund,1989:1097)generations 是复数。两个论元的如:As a brazier would overlap the edge of a tin pipe, for boys to blow peas with.(Simpson, John Andrew and Weiner, Edmund,1989:1097)两个论元是brazier 和edge。显然变换后单独一个“兄尸”或者“弟尸”不能满足复数或者两个论元的要求。所以,把“重”理解为“重累、重叠”的话,A 句和B 句语义上就不合法,因此,“重”不应该为“重累、重叠”义。
前文已申说“重”为“重叠”义。那么,欲使“皆重获在木下”合于语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皆”为范围副词,不与“重”搭配,“皆”与“重”都只修饰“获”;二是“皆”并非范围副词。
如周丽颖(2007)、潘国英(2010)研究所论,现代汉语中,当谓词既有范围状语又有情状状语时,情状状语一定比范围状语更靠近谓词。这一点古代汉语也是一样的Ahttps: //www.ling.sinica.edu.tw/.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的中古、上古、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中,(DA)表示范围副词,(DH)表示方式副词。我们以范围副词“皆”为例,测查了“皆”右侧第一个词和左侧第一个词的属性,“皆”右侧为(DH)的情况常见,但是不存在“皆”左侧为(DH)的情况。。换言之,在汉语体系中,当一个谓词既有范围特征,又有情状特征时,范围修饰的一定是带有情状的谓词。具体到“皆重获”,“皆”是范围副词,“重”是情状副词,“皆”不可能不修饰“重”而只修饰“获”,如此,又回到了“皆”和“重”矛盾的悖论,所以第一种可能应该排除。
剩下的一种可能,即“皆”在这里并非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
《说文·白部》:“皆,俱词也。从比从白。”甲骨文中“皆”字作(《合集》25228),或省作(《合集》31182)、(《合集》28096)、(《合集》29311)等形(刘钊等编纂,2014:231),《说文》所谓的“从比从白”的形体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刘钊,2011:190-192)。其基础形体上部从两个,下从口,虽整字构意不明,但是上部所从两个的构意是明确的,即表示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从构意来看,“皆”早期的意义当专言两个对象,而非多个。事实上,“皆”的早期用例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如:
(5)其皆取(?)二山,有大雨。(《合集》30453)
(6)豚眔羊皆用A“眔”为连词,连接两个并列的成分。。(《合集》31182)
(7)辛子(巳)卜:王其奠元眔永,皆才(在)盂奠,王弗卯(?)羊。大吉。(屯南1092)
(4)中是“二田”,(5)中是“二山”,(6)中是“豚”和“羊”,(7)中是“元”和“永”:都是两个对象。“皆”用于谓词性词语之前,表示两个对象同谓词之间的关系,既可以表示两个对象一起与谓词发生关系,也可以表示两个对象都与谓词发生关系。前者具有[+同时]的语义特征,后者则不具备。“皆”具备[+同时]这个特征的意义,后世由其同源分化字“偕”承担。《诗经·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卫风·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这些“偕”指的都是双方。值得注意的是,“偕”还有动词用法,表示在一起,如《魏风·陟岵》:“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左传·文公十七年》:“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皆”则承担了不具备[+同时]这个特征的义项,并由早期专指两个对象都与谓词发生关系而扩展至多个对象,进而发展成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王凤阳(2011:598)谓“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叫‘偕’”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偕”是“皆”的分化字,“皆”最初表示“两个对象一起”,这个义项后来由“偕”记录。“皆”也可以表示“多个对象都”,这是词义演变的结果。既然“皆”和“偕”是同源词,“偕”又是“皆”的分化字,那么,二者自然可以通用。如《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孟子》有版本或引此句作“偕亡”B《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校勘记》:“闽、监、毛三本皆作偕。”。《魏风·陟岵》“夙夜必偕”、《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中的“偕”在安大简中都作“皆”。
梳理完“皆”的相关问题,再回到《左传》看《正义》的注释。《正义》:“获者,被杀之名。并皆被杀,唯当言皆获耳,欲见尸相重累之皆获,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即《传》之‘重’也。”《正义》用“并皆”注释“皆”,是在揭示“皆”的词义。《说文·竝部》:“竝,併也。从二立。”《人部》:“併,並也。从人幷声。”《从部》:“幷,相从也。从从幵声。一曰从持二为幷。”竝和幷小篆分别作、,字形上也都是两个相同构件并列,蕴含着“一起”之义。这与“皆”上部所从的两个的构意是一致的。从文献用例上看,“并”也确实有表示“一起”的意义,如:
(8)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尚书·费誓》)
(9)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诗经·齐风·还》)
(10)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这些“并”都有[+同时]的特征,相当于“偕”。同时,“并”也有表示总括范围的用法,此时不具备[+同时]的特征。如:
(11)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世说新语·德性》)
(12)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世说新语·识鉴》)
(13)芦菔,根实粗大,其角及根、叶,并可生食,非芜菁也。(《齐民要术·蔓菁》)
这些“并”均无“一起”义,而是表示总括,相当于“皆”。“并”和“皆”有相同的构意,也有相似的引申脉络,都经历了由表示一起到表示总括的意义演变过程。《左传正义》中“并皆”被用为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如《春秋序》正义:“先儒所说并皆辟谬。”《哀公元年》正义:“后伐四国,并皆不书,非独鲁与鲜虞不书也。”显然,《正义》中的“并皆”其实是一个表示总括的联合词。据前文可知,焦循、杨伯峻、竹添所理解的“皆”正与《正义》相一致;杜预、林尧叟未对“皆”进行注释,显见他们也认为“皆”用的是其表总括之常用义。我们前已论证“皆”并非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从这一点来看,他们都未能准确地揭示“皆”的意义。吴文虽然注意到了“皆”和“重”之间搭配的问题,但是由于对“重”的意义理解不正确,自然也没能正确理解“皆”的意义。既然“皆”不是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那么,吴文反驳“重”为重叠之义的说法是立不住的。
我们认为,“皆”是“偕”的同源通用字,“皆重获在木下”即“偕,重获在木下”。“偕”与“重获在木下”构成一种结构上并列、语义上递进的关系。“偕”是说二者在一起,“重获在木下”是对其在一起的状态和地点的进一步描述。
4.“获”的意义及“疏不破注”思想下的弄巧成拙
关于“获”的意义,主要有两种观点。《正义》、竹添、吴柱等认为“获”为“被杀之名”,“获”义为被杀。杜预、林尧叟、焦循等认为“获”义为获得。
《正义》虽然说“获”为“被杀之名”,但并没有给相关证据。竹添在继承这种观点的同时,给出了一些证据。《宣公二年》:“倒戟而出之,获狂狡。”竹添(2008:817):“获,犹杀也。十二年‘皆重获在木下’,又曰‘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是也。盖狂狡倒持其戟,以援出郑人,郑人因夺其戟,反刺狂狡而杀之也。”竹添认为“获,犹杀也”,并且举“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和“获狂狡”为例,这两处的“获”似乎都可以替换成“杀”而文义不变。竹添这里有两处错误:其一,从文义上看,“皆重获在木下”中的“获”似乎可以理解为“被杀”,而竹添所举两例“获”都只能解释为“杀”,这种主动和被动的区分是不能随意抹杀的;即使证明了彼二处的“获”义为“杀”,也不能证明此处的“获”就是“被杀”,这不符合词义规律,也不符合论证逻辑。其二,古代典籍中,“获”绝不训“杀”或者“被杀”。《说文·犬部》:“获,猎所获也。从犬蒦声。”“获”与“蒦”是同源的,都是“隻”的分化字。“隻”甲骨文象以手持隹之形,会“猎获、捕获”之义,分化出“获”字。“获”又引申为“获得”义,也是其常用义。可见,“获”的词义系统,是很难引申出“杀”义的,况且也缺乏文献用例支持。实际上,竹添所举的两个例子中的“获”其词义也是“获得”,文义也只是言“获得”这种结果,并不涉及所获的对象的生死与否,只不过此二处的对象恰好是死人,使得“获”看起来似乎有“杀”的意义。综上,竹添的论证不能成立。总之,“获”不当有“杀”义,也不是“被杀之名”。既然“获”不是“被杀之名”,结合相关上下文,此处只能是其常用义“获得”。既然“获”是“获得”,则“重”自然不应为“深重”,只能是“重叠、重累”,而这又反证了“皆”不可能是表总括的范围副词。可见,对于文本解读而言,“获”的意义决定了“重”和“皆”的意义解读。
“皆重获在木下”杜注“兄弟累尸而死”。实际上,此处杜预并未对“获”字进行注释,只是在串讲中用“累”对“重”做了注释。杜预对“获”的意义有着精准的认识,如《宣公二年》“获乐吕”,杜注:“‘获’,生死通名。”《正义》误解了杜预注,认为“死”是杜预对“获”的注释,又遵循着“疏不破注”的原则迂曲释之,以致给出了错误的解释。恰恰是《正义》的“疏不破注”,让疏破了注。
总之,“获”就是获得义,不当如《正义》所云为“被杀之名”。
5.小结
“皆重获在木下”,“皆”即“偕”的同源通用字,义为“两个对象在一起”;“重”读直龙反,折合今音读chóng,义为“重叠、叠累”;“获”义为“获得”,文义当为“发现、找到”。“表而尸之,偕,重获在木下”,整句话是说按照逢大夫标记的地方为兄弟二人收尸,二者果然在一起,重叠着被发现于树下。
厘清了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对文本有准确而更深入的理解。赵旃弃车逃跑,虽然逢大夫已经察觉到赵旃在后面,但是如果要救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儿子(古代战车很逼仄)。所以,他认为如果没有其他人知道,他就可以不救赵旃,并且以不知道赵旃的存在为托词。为了保险起见,他还特意嘱咐两个儿子不要回头看,但是事与愿违,两个儿子偏偏按捺不住好奇心,回头一看恰好跟赵旃对视,双方都确定了对方已知道己方的存在。这个时候,逢大夫不得不让儿子下车,盛怒中指着路边的树,用恨铁不成钢又无奈的语气痛骂儿子:“尸女于是!”然后让赵旃上车,赵旃得免。第二天,两个儿子的尸体果然在一起,重叠着被发现于树下。“皆重获在木下”正是对“尸女于是”的验证与回答,是对逢大夫“毋谓言之不预”的肯定。逢大夫的预料和判断来自他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洞悉和观察。当时的晋国,赵氏集团炙手可热。邲之战的领导集体中,赵氏一派就占了十三人中的七位。晋灵公为赵穿所弑(《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晋成公是由赵氏集团拥立的(《左传·宣公二年》:“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国君尚可由赵氏废立,更何况一逢大夫?此时的赵旃,正在力求名列正卿之时(《左传·宣公十二年》:“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逢大夫深知,一旦惹到赵旃,后果绝非两个儿子丧命这么简单。逢大夫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权衡利弊的无奈之举。寥寥数言,逢大夫的形象刻画得如此立体、饱满,恰如王孙满、蹇叔那种洞察世事的智者,但是又增添了重无奈的悲凉。竹添:“世卿气焰,使人顿割父子之情而不顾。”权力的斗争不单单是势力集团的互相冲突,更可怕、可怜的是交织在层层冲突中的个人,把原有的伦理不断突破,变作可以商榷、考虑的选择,甚至是最基本的父子亲情都成了选项,春秋乱世中人伦精神的坍塌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