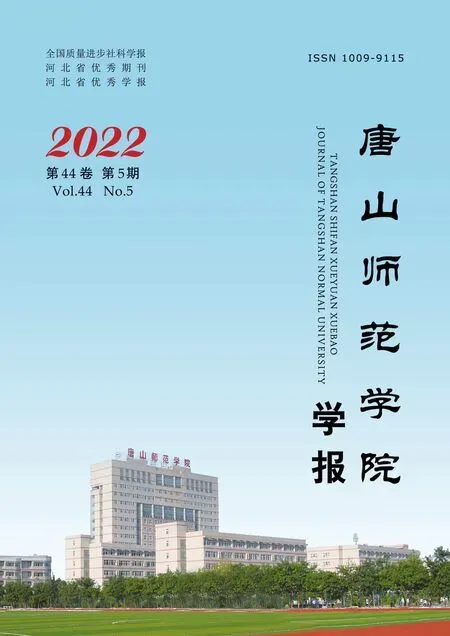论《黄帝四经》对范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22-04-08葛永辉
葛永辉
论《黄帝四经》对范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葛永辉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重要著作,继承了范蠡“天时”“盈溢”“德”的思想,所提出的“民时”“否定盈”“先德后刑”“刑德对立”等是对范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前期道家思想更加系统。
范蠡;《黄帝四经》;天时;盈溢;德
帛书《黄帝四经》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家又一部重要著作,范蠡是前期道家思想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范蠡思想与《黄帝四经》形成的先后顺序一直为历代学者所讨论,以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黄帝四经》因袭范蠡思想。基于对《国语·越语下》中范蠡的言论和帛书《黄帝四经》的阅读与研究,笔者同意此类观点。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言:“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看来,便可见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之学先河。”[1]7从范蠡到《黄帝四经》,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前期道家思想传承的概况。《黄帝四经》对范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天时”“盈溢”“德”三个方面。
一、对“天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黄帝四经》继承并发展了范蠡的“天时”思想。范蠡认为,“时”既指人行事所需的时机,亦指具有先后顺序的时节,二者皆由上天所授予,故称之为“天时”。如白奚所言:“在《黄帝四经》中,四时教令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被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此即所谓‘敬授民时’;一是被用来指导政治活动,此即所谓‘因天时’。”[2]这里的“敬授民时”便指向范蠡思想中的“时节”,“因天时”则指向范蠡思想中的“时机”。《黄帝四经》在继承范蠡“时命”观的同时,也继承了其对不同阶段的天时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时”和“困不择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范蠡的“时命”观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
如晁福林在讨论孔子天命观时所言“无论是时命也好,天时也好,其思想的出发原点都是‘天命,是‘天命’决定了人的时运,决定了人的机遇”[3],范蠡亦认为,时机由上天所授予,人的命运依循于时机。
(1)《国语·越语下》:“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4]15
(2)《国语·越语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4]22
(3)《黄帝四经·经法·君正》:“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1]65
(4)《黄帝四经·十大经·观》:“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229
范蠡与《黄帝四经》皆认为“时”由天授。例(1)将“时”视为“天地之恒制”的一个组成要素,且认为正确把握“时”方可“有天下之成利”。例(2)将“得时”视为“天予”,这意味着人的祸福由上天所决定。可见范蠡强调时机是由上天授予的,人的时运、机遇皆依循于天时。例(3)中“天有死生之时”便意在说明生死取决于天时。例(4)将“断”视为听命于“天时”的具体行为,“当天时”便是对天命的依循。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时命”观的继承。
(二)范蠡对不同阶段的天时的认知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
二者皆认为天时未至须待时;天时已至须及时把握天时;错失天时则会“反为之灾”。
1. 范蠡“待时”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
具体表现为“待天时至”和“待天时返”两种情况。这里的“时”在范蠡思想中主要指时机,而在《黄帝四经》中则既指时机,也指时节。
(5)《国语·越语下》:“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4]15
(6)《国语·越语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4]17
(7)《黄帝四经·经法·君正》:“知地宜,须时而树。”[1]67
(8)《黄帝四经·称》:“积者积而居,胥时而用,观主树以知与治,合积化以知时;□□□正贵□存亡。”[1]388
(9)《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智)以辩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寺(待)之时。”[1]310
(10)《黄帝四经·称》:“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若未可,涂其门,毋见其端。”[1]362
(11)《黄帝四经·十大经·观》:“圣人不巧,时反是守。优未爱民,与天同道。”[1]229
(12)《黄帝四经·十大经·姓争》:“明明至微,时反(返)以为几(机)。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1]267
一方面,由例(5)、例(7)、例(8)、例(9)和例(10)可见范蠡“待天时至”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例(5)中“时不至,不可强生”从侧面体现了范蠡的“待时”思想,“待其来者”亦强调要等待时机。例(7)中的“须时”和例8中的“胥时”皆指“待时”,前者指等待适宜的时节,而后者则指等待适当的时机。例(9)中“柔身以待之时”意在说明即便卑屈自己也要待时,可见其强调了“待时”的重要性。从例(10)可见,“时若未可”则须“涂其门,毋见其端”,这亦是对“待时”的强调。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待天时至”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由例(1)、例(6)、例(11)、例(12)可见范蠡“待天时返”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在范蠡思想和《黄帝四经》中,天时的运转并非一去不返的“射线形”运动轨迹,而是回还往复的运动轨迹,因此“待时”亦指“待天时返”。例(1)“时将有反”和“时无反”便可见范蠡对天时运动变化的认识,“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这里的“须”亦指“待”,体现了范蠡“待天时返”的思想。例(6)与例(11)中的“时反是守”亦强调“天时返”是行事的必要条件。例(12)中“时返以为机”可见天时具有“返”的特点,这亦是对范蠡“待天时返”思想的继承。
2. 范蠡“及时把握天时”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
天时已至,则应及时地从时、因时,进而用时。这里的“时”主要指时机,之所以强调“及时”,是因为时机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而把握天时则不仅指因循天时,还指利用天时。
(13)《国语·越语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4]21
(14)《国语·越语下》:“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4]12
(15)《国语·越语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弗成,天有还形。”[4]24
(16)《黄帝四经·经法·四度》:“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1]119
(17)《黄帝四经·十大经·兵戎》:“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280
(18)《黄帝四经·十大经·兵戎》:“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1]280
(19)《黄帝四经·称》:“积者积而居,胥时而用。”[1]388
首先,范蠡与《黄帝四经》皆认为把握天时要“及时”。例(2)中范蠡言“得时无怠”,《说文解字》:“怠,慢也。”[5]220这意在说明不可怠慢天时,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要及時把握时机。例(10)中“亟”是立刻的意思,“亟应勿言”则强调要及时把握时机。例(13)在强调“从时”的同时还强调了“及时”,范蠡将“从时”比作救火、追亡人,并以“蹶而趋之,唯恐弗及”进一步强调要及时把握时机。由例(2)、例(10)、例(13)可见《黄帝四经》继承了范蠡“及时把握天时”的思想。
其次,范蠡“因循天时”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范蠡因循天时的思想表现为“从时”和“因时”,而《黄帝四经》则主要表现为“因时”。“从时”指跟随时机,如韦昭所言“时行则行,时止则止”[4]12。“因时”则更强调主动靠近时机,《说文解字》:“因,就也。”[7]125“就,就高也。”[5]106例(13)范蠡将“从时”比作救火、追亡人,其强调了“从时”的重要性。例(14)中“随时以行”亦是强调“从时”,《说文解字》:“随,从也。”[5]33这里的“随时”便是指“从时”。例(5)“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则体现了范蠡的“因时”思想,其意在说明行事要因循天时。例(4)中的“当天时”等同于例(17)中的“因天时”,例(16)至例(18)中的“因时”皆指因循天时。由此可见,范蠡“因循天时”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再次,范蠡“利用天时”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例(15)中“圣人之功,时为之庸”,韦昭注曰:“庸,用也,因天时以为功用。”[4]24可见范蠡认为不仅要因循天时,还要对其加以利用。例(18)中的“圣人之功,时为之庸”便是对范蠡“用时”思想的直接继承。例(19)“胥时而用”中的“用”不仅指用“积者”,还指用“天时”,这亦是“利用天时”的表现。
范蠡“反为天时灾”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得以继承。范蠡认为错过天时是“逆天”的表现,将会“反为之灾”。
(20)《国语·越语下》:“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㳅走死亡。”[4]17
(21)《黄帝四经·十大经·五正》:“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功。”[1]236
(22)《黄帝四经·称》:“取予当,立为圣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有环刑,反受其殃。”[1]362
例(2)中“天予不取,反为之灾”、例(15)中“得时弗成,天有还形”、例(20)中“得时不成,反受其殃”皆可见范蠡认为错失时机将会“反为之灾”。例(4)中“当断”意味着“得天时”,而“当断不断”则意味着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把握好时机便会带来“反受其乱”的后果。例(21)中“不争者亦无功”,陈鼓应先生将其理解为“而错过天赐良机的人也绝不会成就事功德”[1]238。例(22)则是对例(15)和例(20)的直接继承。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反为天时灾”思想的继承。
(三)《黄帝四经》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范蠡的“天时”思想,提出了“民时”和“困不择时”
(23)《国语·越语下》:“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稑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4]16
(24)《黄帝四经·经法·君正》:“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1]73
(25)《黄帝四经·称》:“居不犯凶,困不择时。”[1]353
范蠡多将天、地、人三者并论,并将“民功”与“天时”相联系,但其所言的“时”皆指“天时”,并未直接提出“民时”。《黄帝四经》在“不乱民功,不逆天时”的基础上提出“毋夺民时”,这一定程度上使“民”在国家治理层面得到更多的关注。此外,范蠡多强调待时、从时和因时,而《黄帝四经》则提出“困不择时”,陈鼓应先生言:“‘择’当读为‘释’。”[1]354“困不择时”即“困不释时”,其意在说明在困境中不能放弃机会的道理。这便是《黄帝四经》对范蠡“天时”思想的发展。
二、对“盈溢”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黄帝四经》继承并发展了范蠡的“盈溢”思想。陈小华在论及范蠡治国思想时提出:“君主在国家兴盛时,要按照持盈之道‘不矜其功’,不居功自傲,这就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否则就会肇开溢骄之端,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盛衰之变。”[6]可见范蠡将“盈溢”与“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范蠡认为,“盈”与“溢”皆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状态,人的行为只能顺应盈缩变化的天道自然。《黄帝四经》在继承范蠡“盈缩转化”“盈而不溢”思想的同时,其“否定盈”的思想已经开始萌生,具体表现如下:
(一)《黄帝四经》对范蠡“盈溢”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盈缩转化”和“盈而不溢”
1. 二者皆认为事物发展遵循“盈缩转化”的规律
“盈”不仅可以理解为满,亦可以理解为进、长,“盈缩”即进退、消长。正如陈鼓应所言“‘赢’同‘盈’(《四经》‘赢’‘盈’混用不别)”[1]153“‘赢绌’犹‘赢缩’,又作‘盈缩’,谓进退也”[1]220。
(26)《国语·越语下》:“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4]22
(27)《国语·越语下》:“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4]22
(28)《国语·越语下》:“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4]22
(29)《黄帝四经·十大经·观》:“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而盈[绌]无匡。”[1]217
(30)《黄帝四经·称》:“籍(藉)贼兵,裹盗量(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㐌(施)。”[1]378
由例(26)至例(30)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赢缩转化”思想的继承。范蠡所言“赢缩”“盈匡”即《黄帝四经》所言之“盈绌”“赢绌”。“赢缩转化”意在强调事物发展须遵循“由盈而缩”“由缩而盈”的变化规律。例(26)中“赢缩转化”韦昭注曰:“赢缩,进退也。转化,变易也。”[4]22赢缩之变易如同天节之转化,这正是例(27)中
范蠡所言之“常”。例(28)中“月盈而匡”韦昭注曰:“匡,亏也。”[4]22范蠡借月亮由盈而亏的自然现象,说明事物运行遵循“由盈而亏”的变化规律。例(29)中“盈绌无匡”强调事物发展必须遵循“盈缩变化”的规律,肯定了事物运行处于进退、动静的变化之中。例(30)中“赢绌变化,后将反施”是对范蠡“赢缩转化,后将悔之”的直接继承。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盈缩转化”思想的全面继承。
2.《黄帝四经》继承了范蠡“盈而不溢”的思想
“盈”和“溢”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状态,人的行为需要顺应天道自然中的“盈”“溢”状态,“盈”意味着兴盛,“溢”则意味着消亡,“盈而不溢”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
(31)《国语·越语下》:“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4]12
(32)《国语·越语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4]23
(33)《黄帝四经·经法·亡论》:“赢极必静,动举必正。赢极而不静,是胃(谓)失天。”[1]152
(34)《黄帝四经·经法·四度》:“声洫(溢)于实,是胃(谓)灭名。”[1]109
(35)《黄帝四经·经法·亡论》:“上洫(溢)者死,下洫(溢)者刑。”[1]147
(36)《黄帝四经·经法·论约》:“功洫(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1]169
(37)《黄帝四经·十大经·行守》:“骄洫(溢)好争,阴谋不祥,刑于雄节,危于死亡。”[1]320
例(31)中“盈而不溢,盛而不骄”是范蠡“盈溢”思想的直接体现,范蠡以“天道盈而不溢”劝谏勾践不可溢、骄,意在告诫勾践“未盈而溢”必将“妨于国家”,这体现了范蠡的“盈而不溢”思想。例(32)范蠡所言“尽其阳节、盈吾阴节”意在强调对“盈”的把握和利用,亦体现了范蠡的“盈而不溢”思想。《黄帝四经》对此加以继承,并表现出对“溢”的否定。例(33)中“赢极必静”意在说明达到“盈”的状态就要“静”下来,这便是范蠡所言的“盈而不溢”。例(34)至例(37)中《黄帝四经》将“溢”分别与“灭名”“死”“刑”等相联系,可见《黄帝四经》对“溢”的否定。范蠡认为“未盈而溢”是逆于天的表现,《黄帝四经》不但认为“赢极不静”是失天的表现,而且表现出对“溢”的否定,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盈而不溢”思想的继承。
(二)《黄帝四经》对范蠡“盈溢”思想的发展表现为对“盈”的否定
范蠡“盈溢”思想的本质是把握“盈而不溢”的状态,范蠡认为“盈而不溢”如同“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是一种可以把握并加以利用的状态,因此范蠡并不否定“盈”。而《黄帝四经》则认为达到“盈”的状态后一定会“溢”,因此“否定盈”的思想开始萌生。
(38)《黄帝四经·经法·名理》:“有物始[生],建于地而洫(溢)于天,莫见其刑(形),大盈冬(终)天地之间而莫知其名。莫能见知,故有逆成。”[1]180
(39)《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吾]将因其事,盈其寺,軵其力,而投之代。”[1]253
(40)《黄帝四经·称》:“不士(仕)于盛盈之国,不嫁子于盛盈之家,不友[骄倨慢]易之[人]。”[1]353
例(38)中,“道”产生之时“溢于天”“盈终天地之间”,其带来的结果便是“有逆成”,可见《黄帝四经》对“盈”“溢”两种状态的否定。例(39)中“其”指蚩尤,“盈其寺”指满足蚩尤的欲望,陈鼓应将该句理解为“我将借着蚩尤所行的逆事,满足他的欲望,勉励他尽力作坏事”[1]254。可见“盈其寺”已经成为“投之代”的重要因素之一,并成为《黄帝四经》所否定的对象。例(40)则用“不仕”“不嫁”来否定“盛盈之国”和“盛盈之家”,这实质上就是对“盛盈”这种状态的否定。《黄帝四经》认为无法通过约束个人行为以达到“持盈”的目的,一旦达到“盈”的状态,其必将“溢”,必将消亡。由此可见,“否定盈”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已经开始萌生。
三、对“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黄帝四经》继承并发展了范蠡关于“德”的思想。一方面,《黄帝四经》不仅继承了范蠡的“刑德”思想,还继承了范蠡的“殃德”观、“逆德”观;另一方面,《黄帝四经》又进一步阐释了范蠡的“刑德”思想。
(一)《黄帝四经》继承了范蠡关于“德”的思想
1.《黄帝四经》继承了范蠡“刑德并用”的思想
“刑德”是用于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思想,“刑”指以刑罚、法令为主要内容的强制性政治措施,其核心特点是“刚”;而“德”则指以劝赏、教化为主要内容的温和性政治措施,其核心特点是“柔”。范蠡所言之“虐”即《黄帝四经》所言之“刑”,其与“德”相对,指以“刚”为核心的强制性政治措施。范蠡与《黄帝四经》皆认为在国家治理中需将“德”与“刑(虐)”相结合,如马静所言:“刑为阴,德为阳,刑德相互配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7]
(41)《国语·越语下》:“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4]16
(42)《黄帝四经·十大经·观》:“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顺无纪,德疟(虐)无刑,静作无时,先后无名。今吾欲得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以为天下正,静作之时,因而勒之,为之若何。”[1]205
(43)《黄帝四经·十大经·观》:“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而盈[绌]无匡。”[1]217
(44)《黄帝四经·十大经·果童》:“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1]241
由例(41)至例(44)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刑(虐)德并用”思想的继承。例(41)中范蠡所言“德虐之行”,韦昭注曰:“德,有所怀柔及爵赏也。虐,谓有所斩伐及黜夺也。”[4]16范蠡认为治理国家之“常”在于将“德”与“虐(刑)”相结合。例(42)将“德虐无刑”和“德虐之刑”形成对比,意在强调治理国家需得“逆顺之纪,德虐之刑,静作之时”,“德虐之刑”则体现《黄帝四经》对“刑德并用”思想的赞同与继承。例(43)中“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强调将“刑”与“德”相结合,方可达到“极”的状态,“刑德皇皇”则意在说明唯有“刑德并用”方可“无匡”。例(44)“德虐相成”亦说明“刑”与“德”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刑德并用”思想的继承。
2.《黄帝四经》继承了范蠡的“殃德”观
个人与国家所积累的“殃”或“德”是预测其取得“祸”或“福”的重要依据,也决定着其未来的衰亡与昌盛。这里的“德”与“殃”相对,“失德”“散德”“积殃”意味着凶险与衰亡,“绔德”“积德”则意味着吉祥与昌盛。
(45)《国语·越语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㳅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4]17
(46)《黄帝四经·十大经·雌雄节》:“夫雄节而数得,是胃(谓)积英(殃);凶忧重至,几于死亡。雌节而数亡,是胃(谓)积德;慎戒毋法,大禄将极。”[1]271
(47)《黄帝四经·十大经·雌雄节》:“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胃(谓)凶节,是胃(谓)散德……厥身则[寿,子孙则殖。是谓吉]节,是胃(谓)绔德。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乡(向)。”[1]277
例(45)中范蠡所言“受殃”与“失德”皆是“王早图吴”这一件事所带来的的后果,其意味着灭名与死亡。例(46)与例(47)中,“积殃”与“散德”带来的是凶忧、死亡,“积德”与“绔德”带来的是福禄、昌盛,故言“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向”。可见《黄帝四经》将“殃”与“德”视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并将“祸”与“福”与之紧密联系,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殃德”观的继承。
3.《黄帝四经》继承了范蠡的“逆德”观
范蠡与《黄帝四经》皆否定“逆德”,“逆德”涵盖了以“攻伐”为核心的“勇”“兵”“争”等具体内容,其与“好德”相对。范蠡与《黄帝四经》对“逆德”观的否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期道家思想的“德政”意识。
(48)《国语·越语下》:“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4]12
(49)《黄帝四经·经法·亡论》:“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此胃(谓)[三凶]。”[1]159
(50)《黄帝四经·十大经·顺道》:“刑于女节,所生乃柔。□□□正德,好德不争。”[1]329
(51)《黄帝四经·称》:“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进,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1]394
例(48)-(51)可见《黄帝四经》与范蠡对“逆德”的否定。例(48)中,越王即位三年欲伐吴,范蠡提出“阴谋逆德”以劝诫越王,范蠡所言之“勇”“兵”“争”皆指向“攻伐”一事,在范蠡看来此举属于“逆德”,与“凶器”“事之末”并列,由此可见范蠡对“逆德”的否定。例(49)在论及君主德行时,将“行逆德”与“好凶器”“纵心欲”并称为“三凶”,用以警戒君主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将“逆德”与“凶器”“心欲”并列,可见《黄帝四经》对“逆德”的否定。例(50)在论及雌节时言“好德不争”,可见好德的核心特征为“不争”,其与“逆德”相对,《黄帝四经》对“好德”的肯定体现了其对“逆德”的否定。例(51)所言“地之德”的特点为“安徐正静”和“善予不争”,这与例(50)所言之“好德”一致,体现其对“逆德”的否定。
(二)《黄帝四经》发展了范蠡“德”的思想
主要表现为对“刑德”思想的进一步阐释,范蠡虽然提出“德虐之行,因以为常”,但是其并未对“刑”“德”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详细阐释。《黄帝四经》在继承范蠡“刑德并用”思想的同时,不但明确了“刑”与“德”的先后顺序,而且阐释了“刑”与“德”相互对立的关系。
(52)《黄帝四经·经法·君正》:“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从其俗,则知民则。二年用[其德],民则力。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四年发号令,则民敬畏。五年以刑正,则民不幸。六年[民敬畏,则知刑罚]。七年而可以正(征),则朕(胜)强敌。”[1]53
(53)《黄帝四经·十大经·观》:“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1]217
(54)《黄帝四经·十大经·姓争》:“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彰)。”[1]265
一方面,《黄帝四经》直接提出“先德后刑”,明确了德与刑在实施过程中的先后顺序。例(52)在论及治国策略时指出先用“德”使“民则力”,后用“刑”使“民不幸”,最后方可“胜强敌”,这便强调了“先德后刑”的治国主张。例(53)不但强调了“刑德”的重要性,而且以“先春夏,后秋冬”的时节顺序为依据,明确提出“先德后刑”。由例(54)可见,《黄帝四经》在继承范蠡“刑德并用”思想的同时,通过“晦”与“明”、“阴”与“阳”、“微”与“彰”三组对立关系,将“刑与德”的对立关系呈现出来。由此可见《黄帝四经》对范蠡“刑德”思想的发展。
四、结语
《黄帝四经》对范蠡思想的继承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天时、盈溢和德三个方面。作为前期道家思想传承的重要人物,范蠡对《黄帝四经》以及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语·越语下》是研究范蠡思想的重要材料,帛书《黄帝四经》则是现存较早的黄老作品,从范蠡到《黄帝四经》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前期道家思想传承的概况。
[1]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 白奚.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J].文史哲,2021,71(2):28-38.
[3] 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对于《诗·兔爰》的评析看孔子的天命观[J].孔子研究,2007,22(3):4-11.
[4] 韦昭.宋本国语:四[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5]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 陈小华.范蠡的治国思想及其与《老子》的关系[J].浙江学刊,2013,51(3):36-41.
[7] 马静.《黄帝四经》的刑德体系探究[J].文化学刊,2018, 93(7):13-236.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anli’s Thought in
GE Yong-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learning about the Emperor Huang and Lao Tzu. It inherits Fan Li’s thought of “the order of nature”, “overflowing” and “virtue” and puts forward the thought of “farming season”, “denial of overflowing”, “benevolent rule before punish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benevolent rule and punishment”, which i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an Li’s thought and makes the early Taoist thought more systematic.
Fan Li;; the order of nature; overflowing; virtue
B223.9
A
1009-9115(2022)05-0060-07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5.01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51)
2022-03-15
2022-07-15
葛永辉(1997-),男,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献。
(责任编辑、校对:马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