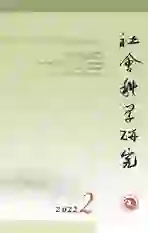克里奇利解构主义伦理学刍议
2022-04-08陆扬
〔摘要〕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25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将西蒙·克里奇利视为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并非没有缘由。伦理学关注道德、法律、责任和义务,这同解构主义的反传统势态显得格格不入。但克里奇利认为解构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必然性。伦理学并不在例外。由是观之,他的《哲学家死亡书》并不仅仅是调侃哲学的威权,而毋宁说是他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一次实践。针对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克里奇利提出一种强调即时即景的伦理经验的“他律伦理”,其中悲剧剧场是为一个典型情境。他的《无信仰者的信仰》,这样来看,一定程度亦可视为延续和彰显了解构批评伦理学转向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中回归保罗书信的倡议,最终是揭示了解构主义伦理学名可名,非常名的“谦卑”之道。
〔关键词〕 克里奇利;《解构的伦理学》;《哲学家死亡书》;他律伦理;《无信仰者的信仰》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2-0195-06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1960—)未必是一以贯之的正统解构主义者,但是美国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在他《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25周年纪念版序言中,言及解构主义的伦理学后续,专门引了西蒙·克里奇利《交错:列维纳斯、德里达与解构的伦理要求》一文中的一段话:“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统治着解构的必然性来自整个儿的他者,命数女神阿南刻,在她面前,我断无拒绝,凡我自由心愿,皆为正义抛弃。作如是言,我相信我是追随德里达了。”①这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解构主义,解构无所不在就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别无选择。解构主义伦理学,由此就体现了一种势所必然的必然性。
西蒙·克里奇利1960年出生在英国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88年,他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克里奇利于199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解构伦理学:德里达与利维纳斯》。1989年開始,他任教于埃塞克斯大学,担任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开始在纽约新学院任哲学教授,并多年担任哲学系主任。其他著作主要有《很少……几乎没有:死亡、哲学、文学》(1997)、《论幽默》(2002)、《无尽的索求:承诺伦理学、抵抗政治学》(2007)、《哲学家死亡书》(2008)、《无信仰者的信仰》(2012)和《悲剧、希腊人、我们》(2019)等。
克里奇利一直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坚定辩护人,发表过《解构与实用主义》等许多相关文章,并主编过文集《解构的主体性》(1996)等。但是解构主义伦理学这个命题本身叫人迷惑。它是要来解构伦理学本身呢,还是运用解构主义方法来开拓出一块新的伦理学天地?凡言解构,我们总会觉得它摧枯拉朽攻伐既定价值,拥抱不辨善恶的尼采传统,跟伦理学似乎最不相干。伦理学本身,以及同她关牵紧密的法律、责任、义务等观念,似乎都是解构主义攻城略地的目标所向,同解构主义应是格格不入。如今言说解构主义伦理学,是不是意味着另辟蹊径来开启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伦理、新的法律、新的义务?《论解构》在2007年出了25周年纪念版,卡勒专门写了一个长达14页,却没有标注页码的《25周年版序言》。诚如该序言中卡勒所追问的那样,这里运行的是哪一种必然、哪一种义务或承诺?是伦理学的抑或不是?卡勒的回答是,就解构主义而言,伦理学问题直达其方法论的核心所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ah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伦理学为什么关心解构主义?由是观之,西蒙·克里奇利应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一、解构主义伦理学的源起
解构主义伦理学的缘起之一,可以上溯到克里奇利1992年出版的《解构的伦理学:德里达与列维纳斯》,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出版的时候,正是德里达遭遇左翼右翼两面夹击的时光。德里达被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指责为沉溺于形而上学文字游戏,鼓吹价值虚无主义,而不愿意直面世界的苦难与不公。克里奇利针锋相对指出,德里达不是虚无主义者,他的思想当中有一个伦理观念,而这个伦理观必须联系列维纳斯的“他者”,以此来质疑自我和自我意识问题,才能见出端倪。7年之后,克里奇利在给《解构的伦理学》写的再版序言中又说,“我读了德里达1992年之后出版的著作,更对解构主义的政治可能性确信无疑,尤其是马克思的阅读,以及友谊、民主和政治决策的叙述,一并糅合其中了。”[Simon Critchley, Ethic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Levinas, West Lafayett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xii.]德里达1992年发表《赠与的伦理》,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1994年出版《友爱政治学》。德里达被认为是斯芬克斯开言,终于走出文字游戏,开始直面世界的苦难,由此完成的“政治学转向”或者说“伦理学转向”,正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叶。克里奇利《解构的伦理学》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为解构操心?为什么要读解构主义的文字?为什么要用解构的视野来读文本?为什么解构是必须的,甚至且至为重要的?《解构的伦理学》据克里奇利的交代,便是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伦理学的回答。
克里奇利本人2008年出版的《哲学家死亡书》,可以视为他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畅销书尝试。这次尝试是效法安贝托·艾柯写小说《玫瑰的名字》,一路行销之后欲罢不能的学院派畅销书路线。克里奇利的这部死亡哲学的大众读物版,主要是把道听途说的哲学家死亡故事收罗起来,娓娓而谈跟读者集中转述一遍,在不动声色的幽默之间,普及他的死亡伦理学。全书的宗旨也浅显明白,如他引用的苏格拉底的话:学习迎接死亡;以及,笑着死亡。所以这本书不是供人念诵经文以求灵魂超度,如《埃及度亡经》和《西藏度亡经》一类,而是在通俗读物的层面上,重申从苏格拉底、西塞罗到蒙田以降的西方哲学的不怕死传统。该书《导论》中作者介绍说,他这本书缘起于一个简单的假设:此时此刻这个星球角落上人类生命的定义,不仅缘起于死亡的恐惧,更害怕的是一切化为乌有。这使我们期望在宗教里得到拯救,也让巧舌如簧的术士畅行其道。因为我们追求的,要么就是此生的一时安慰,要么就是不可思议的来世救赎。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克里奇利强调他的这部《哲学家死亡书》写的不是哲学的历史,而是哲学家的历史。即是说,他写的是一系列的有着血肉之躯、有着种种局限的凡人,如何面临他们的最后时刻,无论是视死如归还是神志迷乱、是尊严高贵还是噩梦盗汗。所以他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将哲学史视为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以西方当代哲学为其一路发展过来的最高峰。所以哲学史几凡是西方的,就是最好的,至于哲学家生平鸡零狗碎的日常琐事,同它了无相干。哲学史的唯一功效,便是举起一面镜子,来镜鉴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世界。克里奇利指出,他的观念是恰恰相反,希望表明他叙述的这许多哲学家们的生生死死,能切断通向“绝对精神”的道路,来对哲学本身提出一点疑问。在他看来,哲学对于哲学家的生生死死不但长久忽视,而且态度傲慢甚至于狂妄。一如海德格尔1924年一次谈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上所言,哲学家的生平,其意义仅仅在于:他生于什么时候,他工作,他死了。这一倨傲姿态,克里奇利指出,是忽略了哲学家首先也是活生生的人,是暴露在一切疾病祸害面前的肉体的人。
克里奇利引西塞罗的名言: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怎样去死。又转述蒙田《随笔集》里渲染的埃及人风俗:在宴饮高潮中,主人经常会抬出一具死人骨架,一边有人高声嚷道,尽情喝吧,等你死了,就是这个模样。他并引蒙田的感想:于是我形成了跟死亡作伴的习惯,不光是在我想象世界里,而且在我嘴里。即是说,不妨多多念叨,时时念叨死亡。唯其如此,克里奇利发现,对于虚无的恐惧,或者可以稍有缓解。他自称这也是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以他选取哲学史上从公元前6世纪的泰勒斯开始,直到最后开一个玩笑把他自己包括在内的190位哲学家,每个人平均页许篇幅,交代他们的生平和死亡故事。如泰勒斯就是年迈之际,在看竞技比赛的时候热死渴死的。材料来源应是他引述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两句诗:
泰勒斯節日里看体育竞技
酷日难当可怜他一命归西。
即便像传奇人物如毕达哥拉斯,克里奇利认同学界当前的共识,那就是很可能这个人物压根就没有存在过,是意大利南部后来叫作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那一群人,给他们的信仰发明了这么一位“创始人”。但是这没有妨碍他根据传说,排列出毕达哥拉斯的多种死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所写的德里达篇章,克里奇利一如既往给予德里达以崇高评价。他指出,德里达博闻强记,是最好的哲学读者,其阅读非常耐心,而且细致、开放,并且质疑,充满了无尽的创意。德里达的著作总是给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当初他阴差阳错命名的“解构”,如今也成为阅读和写作的一种气质。德里达篇章的结语是:
虽然德里达拒绝古典死亡观,即哲学思考就是学习怎样死亡,但1994年出版的《友爱政治学》的题记中,西塞罗终究露了一面。德里达援引了他的话:“……更不好说的是,死者活着”(et quod difficilius dictu est, mortui vivunt)。这是说,死去的人依然活着,他们活在我们中间,骚扰着我们的自鸣得意,同时在警策我们,邀请我们进一步来思索他们。我们可以说,几凡哲学家有人来读,他或她就没有故去。倘若你有意同死者交流,那就读书吧。[Simon Critchley,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p.243.]
这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德里达当年的预言,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解构主义者。至少西蒙·克里奇利,是不耻于这个名号的。《哲学家死亡书》这样来看,当亦不失为作者“解构的伦理学”的一次成功普及性试水。
二、无信仰者的信仰
克里奇利2012年出版的《无信仰者的信仰》,副标题是《政治神学实验》,该书出版后为多方关注,应是作者解构主义伦理学路线上的一站重镇。谈无信仰者的信仰是一个悖论,它涉及宗教问题。但克里奇利并不是基督徒,他呼吁从政治角度来重拾信仰,在美学和信仰之间,建树一种政治哲学的信仰伦理。本着这一宗旨,克里奇利在《无信仰者的信仰》中分别阐述了卢梭、巴迪欧、圣保罗、海德格尔等人的信仰观,并反驳了齐泽克的批评,坚持了自己的非暴力主义立场。
该书《导论》中,克里奇利首先给读者讲了一则王尔德的故事。那是奥斯卡·王尔德1897年因猥亵罪坐牢两年之后释放出狱,同一天他最后一次告别英国,去了法国。在那里他遇到老友罗伯特·罗斯,交给他一部密密麻麻写了80页的手稿,计洋洋洒洒达5万言。手稿是写给他出尔反尔的情人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的,1905年出版,根据《诗篇》第130篇语“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题名为《自深深处》。克里奇利说,王尔德这封长信的宗教意味,特别是写信人对基督形象的阐释,使他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王尔德的这个文本再精彩不过阐示了政治与信仰之间的二难选择,而这也是他这本书的写作线索。
克里奇利指出,王尔德虽然身败名裂,杰出的才华毁于一旦,可是这个文本平静坚毅,作者没有屈服于某个至高无上神的外在掌控,反之将苦难视为反躬自省的良机。对此,克里奇利评论说,这样一种自我实现的行为,在王尔德看来既不是宗教,也不是道德可以相助的,因为它们都需要外部的中介。道德对于王尔德来说只是外部强加的法律,必须拒绝。理性让他意识到将他定罪的法律不公正。但是要把握自己遇难的究竟,王尔德在理性上又无法将这一切都简单归咎于外在的强制不公。是以他不得不从内心来开释苦情,这就是理性无能为力,唯有求诸艺术了。是以王尔德将监狱里的种种苦难转化为一种心路历程的叙述,完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的激情“升华”。
克里奇利认为这就是王尔德的宗教观,它涉及政治和信仰的主题。别人的信仰是目不可见、至高无上、为知识不可企达的,但是王尔德的信仰具有美学意味,是可以触摸、可以看见的,是一种感性的宗教。他特别看重王尔德的这句话:万物为真者必成宗教。所以不信教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可以有信仰和宗教。王尔德的原话如下: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当我思及宗教,我感到似乎想给那些无法信仰的人创立一种秩序:我们或者可以叫它无信仰者协会,那里的祭坛上没有蜡烛燃烧,那里的牧师内心并无宁静,他可能用未经祝福过的面包和空空的酒杯来赞美。万物为真者必成宗教。不可知论应当具有自己的仪式,它并不逊色于信仰。[Oscar Wilde, De Profundis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54, p.154. See Simon Critchley, 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 London: Verso, 2012, p.3.]
这就是无信仰者的信仰。它相较虔诚教徒的信仰并不逊色。克里奇利认为无信仰者的信仰这个概念,有助于走出政治和信仰的二难困境。一方面无信仰者似乎依然是需要一种信仰经验,另一方面这信仰经验又非传统宗教所能提供。如果说政治生活的目的即是避免犬儒主义,那么因地制宜树立信仰,也就是当务之急。一如王尔德是在监狱里面,阐示了他的无信仰者的信仰。至此,什么是无信仰者的信仰,就很清楚了。克里奇利说:
这一无信仰者的信仰,其对象不能是任何外在于自我或主体的东西、任何外在的神圣律令、任何超验的真实。诚如王尔德所言,“无论它是信仰也好,不可知论也好,它必不能外在于自我。它的符号必是我自己的创作。”[Simon Critchley, 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 London: Verso, 2012, p.4.]
克里奇利认为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万物为真者必成宗教,要不然信仰缺失权威性;另一方面这权威性的作者不可能是任何外人,只能是我们自己。故而无信仰者的信仰,便必然是一部集体自我创作的大著,我们的灵魂只能由自己来加以铸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里奇利赞赏王尔德1891年文章《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中,称基督为“具有奇妙灵魂的乞丐”“具有神圣灵魂的麻风病人”,是“在痛苦中实现了他的完善”。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如何重拾宗教,如何重建信仰,特别是当神学冲突里不断有政治动因溢出,哲学家的伦理关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引用的《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的台词,来“重整乾坤”?克里奇利以王尔德为例的以上阐述,一定程度上言,可以视为延续和彰显了解构批评伦理学转向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那么,信仰的本质又是什么?克里奇利据保罗的例子,分析了复活与置换两种策略。他认为说明何为信仰根本,有必要回归保罗书信,从圣保罗说起。虽然回归保罗对于当今的基督教会来说,不见得是好消息。但是保罗革故鼎新,在克里奇利看来,正可比肩克尔凯郭尔、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鲁道尔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在现代神学革新中的地位。甚至,其振聋发聩不下于以反基督而著称的尼采。对此,克里奇利表示,他赞同阿甘本的说法,那就是尼采重估传统价值,是出于妒忌当年保罗重估犹太教传统观念,也就是保罗的戏仿。他援引了20世纪奥地利宗教哲学家雅各·陶布斯(Jabob Taubes)讲座文集《保罗政治神学》中的名言:“保罗对尼采影响之深,直达最隐秘处。”[Jacob Taubes,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Paul, trans. D. Hallander,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3. See Simon Critchley, 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 London: Verso, 2012, p.156.]
回归保罗是回归保罗的书信。克里奇利指出,保罗书信的写作具有强烈的迫切性,具体说它们是在公元51年至62年这大体十年之内完成的。历来影响之大,不但表现在广为传布,而且表现在历经了最离谱的阐释、歪曲和简单化。其中传布最广的误读,便是认为“保罗创立了基督教”。但是读过保罗的读者都会知道,保罗从来没有使用过“基督徒”和“基督教”这两个语词。保罗爱说的是“基督”和“在基督里”。如《迦拉太书》:“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2:17)以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2:19)克里奇利指出,虽然后代基督教教义多倾向于将保罗改造为圣彼得那样的基督教奠基人,但是保罗自己,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任何一种宗教组织的创始人,不管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更不用说英国的圣公会了。
那么保罗的信仰又是什么?克里奇利指出,保罗不过是宣告弥撒亚的到来。这位弥撒亚的名字是耶稣,也就是历史上的约瑟家的耶稣。是以保罗的信仰既不是抽象的上帝信仰,也不是狂热的弥撒亚信仰,而是耶稣的信仰,而耶稣信仰的核心是复活:
作为救世主或弥撒亚的耶稣信仰,是通过复活实现的。复活千真万确的确定性,读几页保罗便见分晓。若无复活,一切信仰都是空谈。这并非像巴迪欧那样,视其为“寓言”就轻易打发过去。反之保罗是要以他的复活信仰,来创建社群,用他自己的话说,它们就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罗马书》,11:5)诚如陶布斯表明的那样,保罗完全是立足于爱的律令,建构了一种否定的政治神学,既不符合犹太人,也不符合罗马人口味。[Simon Critchley, 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 p.158.]
“否定神学”是典型的德里达解构主义术语,“否定的政治神学”,则可视为解构主义与陶布斯政治神学的联姻。克里奇利进而指出,保罗书信是写给公元1世纪罗马人统治下的非法地下社团的,这个贱民阶层,就是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书名意指的对象。所以保罗主义不是追求普遍性的康德主义。这里的核心部分不过是一种剩余政治学,是在人文主义的下脚料上,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连接。
克里奇利发现保罗的身份也值得重视。保罗是谁?保罗叫保罗是因为大家叫他保罗。可是在那以前,他的名字是扫罗。扫罗可是王族名姓。诚如《腓立比书》中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3:5)保罗又说,“就法律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3:7)而一旦大家叫他保罗,他也就一钱不值了,变成了垃圾。比起罗马的自由公民扫罗这个光辉名字,保罗显得微不足道。对此克里奇利还特地引了阿甘本《剩余的时间:〈罗马书〉评注》中的话,说明拉丁语里paulus这个词,意思就是“渺小,不足一道”。[Giorgio Agamben,The Time that Remai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of the Romans, trans. P. Dail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See Simon Critchley, 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 p.158.]《羅马书》开篇保罗便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主人和仆人的身份,顿时颠倒过来。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假如我們没有忘记乔纳森·卡勒《论解构》中阐述他的解构批评,如何反复强调解构主义的基本策略首先是颠倒自然/文化、言语/文字这一类二元对立,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克里奇利这里阐发他的解构主义伦理学,就像《无信仰者的信仰》书名所示,同样是热衷在二元对立中彰示真义。扫罗和保罗的置换是为一例。耶稣极度羸弱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通过复活变得无比刚强。这也是弱和强的转化,一如他引证的《哥林多后书》中圣保罗的话:“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12:10)换句话说,基督的刚强,也就是没有刚强的刚强。这与从康德到德里达的“没有宗教的宗教”命题可谓是如出一辙,最终可以说是揭示了解构主义伦理学名可名,非常名的“谦卑”之道。
三、两个核心概念
“他律伦理”和“悲剧伦理观”,可视为克里奇利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我的学生王曦博士2016年在纽约新学院读联合培养项目期间,曾经给克里奇利做过一个题为《西蒙·克里奇利谈“他律伦理”:悲剧剧场、爱与哀悼》的访谈。[王曦、西蒙·克里奇利:《西蒙·克里奇利谈“他律伦理”:悲剧剧场、爱与哀悼》,《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6期。]所谓“他律伦理”(heteronomous ethics),是克里奇利针对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提出的概念,它倡导一种伦理学维度的主体性,强调重视当下的伦理经验,主张在剧场,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的剧场中,以及“爱”等等具体的伦理场景中,来探讨人与他人关系展开之际的各种道德情感。进而,探讨伦理主体的自我生成。对于“他律伦理”,克里奇利的解释是,他试图描述的伦理的他律性是内在于主体的。17世纪以来,自律的原则似乎成为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形式。但这一传统值得质疑,是以他尝试在审美、政治、伦理等领域重新思考他律维度的意义。关于自律性,从历史上来说是政府、国王在公民身上施加强制性的影响,然后把这种外在的强制宣称为一种内化于公民的自律。这也是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运作于欧洲政治领域的主导逻辑,它的确是有效的。克里奇利表示,他并不主张抛弃自律的维度,而是说人际交往中的他律性关系,是个体自律的基础,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考虑自身的要求与选择。在康德和后康德的谱系中,自律性似乎就是政治德行中毋庸置疑的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故而在他《无尽的求索》一书中,克里奇利强调,他论证的出发点便是反对康德伦理学。对康德而言,自律和理性是伦理学的两项基本原则,二者相互关联,自律是理性的运用。但是对他克里奇利而言,伦理学应该是一种情感性关系,它起始于与他人展开关系时产生的道德情感。它可以被合理化,但合理化是后续的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克里奇利认为我们与世界展开关系的最基本方式是情感性的,伦理必须通过情绪和感受传达。所以对这些情绪本身的表达,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
关于“悲剧伦理观”,西蒙·克里奇利有过一个专门阐释。在克里奇利看来,悲剧剧场提供了一种伦理情境,在这个情境里,同“悲剧意识”密切相关的他律维度得以反复展开,成为悲剧剧场的构成性原则。悲剧剧场就这样提供了一个我们和自身拉开一段距离,由此来观察和审读自身的场景。悲剧最无法预测的,便是观众会从剧场场景中能有多大收益。对此,克里奇利作了一个词源学的追溯:“观众”在古希腊语中是theoros, 从这个词衍生出theoria即“理论”。而“理论”又和动词“观看”(theorein)关联,指在剧院即theatron中发生的观看行为。故而倘若如亚里士多德所示,将悲剧定义为对行动和实践的模仿,那么它就是从理论的视角看到的东西,即便行动本身究竟是什么,依然也还叫人迷惑。换言之,正是在剧场里,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问题被揭示出来。理论与实践的断裂,也首先在剧场中被演绎出来。我们就是正在展开的这出戏剧的观众。在剧场空间中,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到我们的行动,看到人类的实践如何从内部分裂开来,被理论引入质疑地位。由此观众在悲剧剧场中能够隔开一段距离,观看舞台展开的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而隔开的这段距离,确切地说,也是旁观者的距离、理论的距离。悲剧剧场故而是展示了一种典型的剧场政治,演员们的表演,正是在演练对待政治生活的方式。故而与其说悲剧是一种艺术形式,不如说它更接近一种社会实践。如克里奇利所言:
悲剧为何有趣?为何具备政治教义?这基于悲剧并非是个人性的叙事,悲剧真正的主角首先是城邦,政治空间才是悲剧表现的主体。它是古希腊城邦中公共机制的关键一环,城邦的社会政治制度正是在剧场中以景观的形式自我展演。我尤其关注作为一种城邦创制实践的悲剧,如何将城邦展演为自我分裂的,具有污染与乱伦根底的,它如何揭示了暴力、战争的奠基性力量。[王曦、西蒙·克里奇利:《西蒙·克里奇利谈“他律伦理”:悲剧剧场、爱与哀悼》。]
这是说,悲剧完全打破了透明的、自律的主体观念,展现的正是在自身内部拉开一定距离的伦理主体。克里奇利进而指出,西方古典政治学中主体观念,几无例外大都是孔武阳刚、敢作敢当的男性主体。唯有此种这种政治主体,方有资质来做出裁决判断。而在古希腊悲剧中,怜悯与哀悼的情感泛滥,这被认为是女里女气,暗示指向一种脆弱的、依附性的主体形象。在这一背景之下,哀悼情感的主体就显得羸弱无力,成为处在依附关系中而倍遭质疑的主体。而倘若代之以相互依存的、有限的、脆弱的主体观念来重建我们的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克里奇利认为,这其实也是女性主义和情感理论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可以说,同时也体现了传统伦理学的解构潜质。
(责任编辑:潘纯琳)
〔作者简介〕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
①Simon Critchley, “The Chiasmus: Levinas, Derrida, and the Ethical Demand for Deconstruction,” Textual Practice 3, no.1, 1989.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