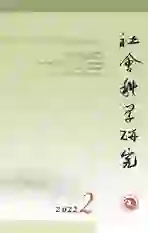朝向一种积极的启蒙
2022-04-08王德志
〔摘要〕 “启蒙辩证法”的两个命题,“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分别表达了对启蒙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二个命题上,则会得出阿多诺、霍克海默全然抛弃启蒙事业的结论,而对该辩证法的完整理解告诉我们, “启蒙辩证法”正是要将启蒙从它的“盲目统治”的扭曲形式中拯救出来,最终给出一个积极的、救赎性的启蒙概念。由此出发,文章最终将阿多诺、尼采一并解释为康德式启蒙事业的同盟军。
〔关键词〕 尼采;康德;启蒙辩证法;工具理性批判;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B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2-0037-06
写作于二战期间,出版于冷战初期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现代经典,其思想主旨正如它的两个作者阿多诺、霍克海默在导言一开始所宣称的,“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①启蒙理性本来是将人类从自然的盲目支配中解放出来,现代社会占主宰地位的理性形式却将人类引向一个自我摧毁的过程;启蒙事业非但没有实现它的承诺,反而导向“一个全盘控制的社会”,导向“奥斯维辛”。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的作者看来,奥斯维辛不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其内在逻辑极端化之后的历史产物。这就是阿多诺、霍克海默所讲述的西方文明如何由“启蒙蜕变为神话”的故事。
“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两个命题需要结合起来理解。如果我们将第二个命题当成整个故事的全部,则很容易得出结论说,阿多诺、霍克海默是启蒙的彻底否定者。这种解读显然是对启蒙辩证法思想主旨的误解。实际上,第一个命题告诉我们说,阿多诺、霍克海默对于启蒙的批判是一种救赎性批判,他们对启蒙的立场并非全然是消极的。
下文的第一部分将重点放在第二个命题上,第二部分进而论述“启蒙辩证法”是如何在康德道德思想中体现出来的,第三部分将阿多诺、尼采均解释为第一个命题的支持者,也就是,将他们的思想解释为对启蒙事业的承续与发展,最后希望由此得出一个对启蒙辩证法的完整理解。
一、启蒙与神话的辩证纠缠
哈贝马斯曾指出,“尼采的知识批判和道德批判也预设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工具理性批判形式所阐述的思想:在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理想和真实性背后,在普遍主义道德的禁欲理想和正确性要求背后,潜藏着自我持存和统治的绝对命令。”[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哈贝马斯本人并不认同对两者所代表的现代性批判立场,故亦未就此论断展开解说,尽管如此,哈贝马斯此处却正确地指出尼采对普遍主义道德、禁欲主义理念的批判是阿多诺、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即揭示启蒙如何蜕变为神话)的思想雏形。
启蒙与神话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渗透,辩证纠缠在一起的。一方面,神话已经是一种启蒙。启蒙的纲领是要以科学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然而,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神话试图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阐述、确定和解释本原:在记载和收集神话的过程中,这种倾向不断得到加强。神话早就在叙述中成为说教。……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力。”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5页。]启蒙与神话一开始就辩证地纠缠在一起,人们常常说,启蒙是现代思维,神话是前现代思维,阿多诺却认为神话从起源上已经蕴含着一种启蒙思维,古代、现代并非代表两个截然分离的时期。神话思维本身就是要赋予世界以某种可理解性的启蒙思维。远古时代的自然对人们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对文明而言,作为他者的自然存在构成了潜在威胁。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将自然视为凌驾一切的、不可测度的存在,从而对其满怀尊崇与恐惧。这个时候人们本能地倾向于用已知的范畴来同化未知的范畴,用相对确定的东西来解释、界定莫可名状的东西,为的是要消除对未知之物的恐惧。驱逐对神秘事物的恐惧的冲动,构成神话与启蒙的共同基础。
另一方面,现代的科学事业本身有可能是一种排他性的、盲目的“形而上学信仰”,也就是说,工具理性主宰之下的启蒙思维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现代人常想当然地认为科学与信仰之间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然而,在尼采看来,科学的追随者们仍然是基于信仰原则,这实际上是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引用了尼采《快乐的科学》中的一段话,以阐明启蒙对真理的神话式信仰:“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还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我们,当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从那个古老信仰、亦即从基督徒的和柏拉图的信仰所点燃的千年火堆中取自己之火的,认为上帝即真理,真理是神圣的。” [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正因为这样,尼采在《善恶的彼岸》第一部分“论哲学家的成见”中主张,应当把康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何以是可能的”置换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这类判断的信仰是必要的”。[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第129—130页。]如朗佩特所指出的,尼采让我们看到了培根式哲学统治的种种后果,因为他在作品中极为明白地道出了现时代的诸特征:我们的进步史观、我们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我们凭极端方法对科学之确定性所做的虚构……在尼采看来,现时代怀抱着一个全面的美妙神话。[参见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根、笛卡尔与尼采》,李致遠、彭磊、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94—295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的本质就在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抉择,亦即人类必须在臣服于自然与支配自然二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通过卓有成效的自我管理与控制,人类得以摆脱自然界的魔咒并达成自己的目标,即实现对外在自然界随心所欲的掌控。正如尼采所言,只有通过成功地抗拒自然,亦即通过非自然因素,人们才能够迫使自然交出自己的秘密。[参见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1页。]因此,在《启蒙辩证法》的阐释框架中,启蒙始终与对“双重自然”[“自然”(Natur)一词本身兼具“自然界”和“(人的)自然天性”两种含义。]的控制紧密关联,人类将自然客体对象化,以便按照预设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在逻辑与范畴的建构中,人类强加给混沌各种各样的规律性和形式(亦即“图式化”过程),在操控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推理逻辑在概念领域内的支配作用。[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10页。]概念范畴乃是出于操控自然的目的,将自然转化为可计算之物的手段。沿循这一尼采式批判思路,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进一步将康德与培根、笛卡尔并列为启蒙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如他们所说,支配自然的范围正是纯粹理性批判所约束的思想范围。[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20页。]内在性的抽象过程致力于抹消事物质的属性,从而将其变为可计量之物,“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这表明,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4页。]在去神话化过程中变得日益精确的形式化的概念思维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神话。
对尼采而言,人类生活中那些被称颂的一切美德都有一个动物式自我持存的来源,正义、明智、节制、勇敢,总之,“一切我们所谓的苏格拉底美德,其起源都是动物性的,都是促使我们寻找食物和躲避敌人的同一种本能的产物。”[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同样地,逻辑及抽象概念本质上植根于自我保存的需要,“逻辑规律的排他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功能意义中,最终在自我持存的强制本性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23页。]《启蒙辩证法》的论证脉络几乎严格地遵循尼采的上述思路,它描述了启蒙思想如何成为既可以把握事实又可以帮助个体最有效地支配自然的知识形式,启蒙如何通过诸如文明、理性、进步等堂皇的口号来掩盖“自我保存”的原始本能。人类的理性就是自我持存的理性,而不成熟指的是不具备维持自我持存的能力。康德的理性概念同样是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由于康德把自我保存界定为理性的基本原则[参见Kant,Gesammelte Schriften(AA),XVI,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9, p.371.],为了取得对外在自然的控制,启蒙理性舍弃了原本的终极诉求而终沦为工具理性,并通过计算与谋划,使得自然界臣服于人类并为人类所支配利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宣告:“今天,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行动来支配自然这一培根式乌托邦的时候,我们才能揭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本身。”[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34页。]
在社会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暴力下,世界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被彻底启蒙的文明在现实当中却又一次退回到了野蛮状态,被工具理性所彻底接管的现代科学技术所采用的、由支配决定的对象化形式不仅没有成功满足自我持存的需要,反而表现出了灭绝人类的倾向: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极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参见齐格蒙·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二、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启蒙辩证法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考察“神话与启蒙的辩证纠缠”这一命题如何在康德道德学说中隐含地体现出来,或者说,考察“启蒙辩证法”是如何在康德道德思想中得到贯彻的。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尼采对康德对自律伦理学的批判表现出同样的旨趣,在思路上也高度一致。
首先,康德哲学中世俗元素与神学元素是交织在一起的。阿多诺将康德道德哲学解释成世俗化的系统努力,它体现出一个根本冲动,即把人类从自身罪孽的幼稚中解放出来的世俗化的冲动,旨在祛除人类道德观念中的神学残余,“如果你们在康德的法则概念的压制规定中没有感受到这一动机的共同跃动,那么,你们实际上就没有正确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极其复杂和多样的构成”。[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3页。]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自律伦理学,是要对自我决断的个体生活予以道德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奠基,因此,在任何意义上它似乎都是现代的。然而,康德道德体系仍然有着隐蔽的基督教神学假定。在《判断力批判》当中,康德进一步论证了道德律令与自然合目的性的一致性:自然的合目的性把自然看作与道德协调一致的整体,并以实现至善为其终极目的。对康德而言,哲学的真正使命不仅仅是构建概念的理性知识的体系,与此同时也在于探索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由于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粹理性所具有的建构性作用只有在实践领域里才得以真正发挥,而普遍且必然有效的“绝对律令”却无法在经验世界中推导得出;因此,按照纯粹实践理性的内在要求,一种朝向“至善”的无限进步必然有“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的公设作为前提。[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而此二者作为德性与幸福一致的可能性根据,更加明确地体现了康德道德体系所内含的隐蔽的基督教神学假定——换言之,历经启蒙理性洗礼的“道德神学”仍未彻底摆脱其独断成分。
其次,康德自律的道德律令的内核是社会他律。在尼采看来,康德苦心孤诣构筑的道德大厦并不具备坚固的地基:“人们已经看出,欧洲人的意识不是‘物自体和现象的对象,因为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足以能下如此判断的程度。”[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345页。]由于这一看似十分严谨的体系实际上并未真正自我确证,从而也就注定了“绝对律令”内在固有的任意性和独断性——“理性变成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因如此,它可以统率一切目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東、曹卫东译,第77页。]康德哲学体系的形式化与空洞性把整个生活组织展现为一个“丧失了一切现实目标的世界”[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77页。],尼采从中辨识出“专制地、无顾忌地和无情地实施权力的要求”[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第139页。],认为康德诉诸给定的道德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做法,这一行为是在意识到道德无从推导得出后得以实施的。将一切感性因素排除在外的道德律则仍旧未能成功摆脱盲目性:那些只从康德尊重单纯规律形式的动机出发就放弃利益的市民阶层并未被真正启蒙,而仍然十分迷信[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74页。],纯粹形式化的道德律令实际上是康德所谓“自律”之中的他律因素的体现。[参见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第93页。]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与之相对,尼采提出主张,每个人为自己发明自己的德性、自己的绝对命令。在尼采看来,康德将“道德律令”普遍化的尝试根本上是抑制性的,这种试图抹平个人意志的做法无非意味着生命力的衰退,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日渐丧失对人类自身的敬畏,而这一倾向正是尼采所深感忧虑的。同样地,在《快乐的科学》第335则“向物理学欢呼致敬”中,尼采在对康德的“绝对律令”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之后大声疾呼:“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新颖、独特、无可比拟、自我立法、创造自我的人!”[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310页。]
最后,康德绝对主义的道德观实际上是一套充满残酷与压迫的道德体系。工具理性的抽象化效用凭借同一性原则(即《启蒙辩证法》中的“内在性原则”)施加于自然物,形式化的道德律则赋予专断独行的工具理性以合法性证明,同一性、强制性的道德法则由此成了尼采对康德道德哲学批评的重点所在,“只有在全人类拥有一个普遍承认的共同目标时,我们才有可能向别人建议:‘应如此这般去做。然而,至少在目前,这样一种目标还不存在。”[尼采:《朝霞》,田立年译,第144页。 ]由此出发,尼采对人类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绝对主义的道德价值观进行了一番鞭辟入里的批驳:“那个道德概念世界根本上就从未失去过血腥和迫害的气味?(甚至老康德也不例外,他的‘绝对命令就散发着残酷的味道……)”[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第41页。]诸如“罪孽”“良心”“责任”等道德性范畴概念的萌芽“完全是用鲜血长时间浇灌而促成”。“这种残酷性在不断地精神化和‘神圣化,并且贯穿了全部高等文明史(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说,它甚至构成了高等文明史)”。[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第41页。]
对隐藏在道德背后的残酷的压制性原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着深刻的体认,“个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個人与他人身体之间的关系充分说明,非理性和不公正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216页。]由此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阴郁作家们关于残酷的理论,充分认识到了这个因素的重要意义;尼采(以及萨德)通过展现启蒙道德的非道德性而将康德所代表的启蒙原则推向了极端。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尼采本人和他所批判的对象一样依然深陷于启蒙辩证法当中,尼采“并没有揭露原来意义上的不公,反而粉饰了这种不公。”[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217页。]归根结底,尼采是从个人主观愿望出发来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这一原则中所包含的任意性导致了尼采略显装腔作势的语言里隐藏着实际上的软弱无力:“权力意志”和“永恒复归”终究也未能逃脱沦为另一种“神话”的命运,尼采树立的“超人”理想与他本人乐此不疲所抨击的压抑性原则又何其相似。[参见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第194—197页。]尼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体现出了“纯粹意志”本身内在的空洞性。[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尼采的批评似乎并不全然符合尼采的原意。究其实质,尼采的议论本是针对自由主义社会建制中文化庸俗化倾向以及人的精神日趋渺小化与平面化的现象而发,亦即渴望经由现代性批判而重建一种精神等级的文化。尼采非但没有一味歌颂强权,在其著作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对于弱者更加富于精神性的称赞之词。]
康德伦理学之所以被阿多诺、霍克海默解读成为充满残酷与压迫的他律的伦理学,很大程度上跟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极权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体验相关,他们见证了20世纪人类文明的深重灾难,切身的体验与经历让他们看清了这一事实:在现存的权力机制下,形式化的、空洞的伦理学最终难免让非理性主义的东西乘虚而入,自律的道德哲学最终沦为他律的意识形态遁词。
三、结语:通过批判启蒙来推进启蒙
应该承认,尽管尼采对康德哲学的批评不乏切中肯綮的地方,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当偏激和片面化的,尼采针对康德的批判往往只是对其中一个侧面的攻击,而并未抓住康德思想的全貌。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在分歧之下其实潜藏着更大的相似性,在看似猛烈的抨击背后,尼采恰恰推进了康德的思想,“茱丽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一文的结尾处揭示了尼采的“超人”理想与启蒙主体性之间的同构性:“康德的原则——‘在意志准则基础上所做的一切,同时也是通过普遍规定把自身作为一种对象的行为——也是超人的秘密。”[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100页。]
如上文所述,尽管尼采贬斥启蒙式进步观念,“超人”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沾染了历史进步主义的色彩,而并未彻底摆脱启蒙主体性的范式。此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著名哲人”的谴责(“你们为民众和民众的迷信效命,而不为真理效命”)同样体现出了尼采以真理反对迷信的启蒙倾向。由此可见,尽管对启蒙大张挞伐,尼采在本质上仍然是启蒙精神的体现。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如果我们回想尼采对流传下来的但未经过检验的价值的不断攻击,对通过权威而固定和通过个人自己的愚昧而得到保护的偏见的不断攻击[参见尼采:《朝霞》,田立年译,第19页。 ],我们就会从中看到康德“敢于认识(sapere aude)!”这一口号的绝佳体现。尽管存在诸多显著差异,尼采构想的“超道德个体”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作对康德自律原则的极端化——两者都意欲填补上帝缺位所留出的空白,亦即在“后启蒙”的道德哲学中构建绝对有效性的规范原则:“事实上,萨德和尼釆比逻辑实证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坚守着理性,它潜在地从(包含在康德理性概念以及每一个伟大哲学之中的)乌托邦的隐身之处解放出来,而这一乌托邦则是人性的乌托邦。”[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103页。 ]
正是基于两者间的这一共通性,在指明其内在缺陷的同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尼采的批判精神也表达了由衷的赞赏:“尼釆正是在否定中拯救了人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在仅仅为了寻求抚慰的各种形式的保证中,日益遭到了破坏。”[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103页。] 并且,与尼采对康德的负面评价不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反思康德哲学的同时亦指明其积极意义:“如果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确认支配规则的层面上,那么,它就必然会比那些仅仅论证了既定事物的思想显得更有普遍性和权威性。”[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221页。 ]
这就告诉我们,《启蒙辩证法》不遗余力地对潜藏于启蒙背后的隐秘权力机制的揭露决非意味着对启蒙原则的简单否认,而是旨在推进启蒙的自我反思,从而将启蒙从自我毁灭的倾向当中拯救出来,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解——只有在摒弃了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第33—34页。]正如康德是通过批判理性从而为理性划出界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见证了启蒙理性总体性追求的徒劳无功。从这一角度看,《启蒙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试图扭转冷酷而目标坚定的进步精神”实际上是在另一层面上贯彻了启蒙理性的终极关怀,即人类对于自由的不懈追求。
阿多诺、霍克海默提醒我们注意“启蒙辩证法”的两个侧面:第二个命题提醒我们,启蒙理性可能是一股自我摧毁的力量,而第一个命题告诉我们说,对于人类而言,启蒙之外并无别的可选项;对“启蒙辩证法”的完整理解,意味着建构一个积极性的启蒙概念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并非像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那样全然抛弃了理性自身,所反对的是在启蒙理性与工具性理性形式之间画上等号。工具理性在现代生活中取得的宰制地位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在这个过程中,该单维度的理性自身与传统、神话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被掩盖起来。实证性的、形式化的理性形式有其蒙昧无知的一面,对其消极面的反思本身就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启蒙辩证法”正是要试图将启蒙从它的“盲目统治”的扭曲形式中拯救出来,最终给出一个积极的、救赎性的启蒙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尼采成了康德式启蒙事业的真正的同路人。
(责任编辑:颜 冲)
〔作者简介〕王德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6。
①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2—3页。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