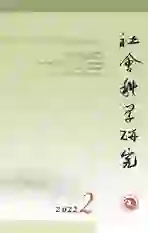处境定义与框架分析
2022-04-08赵锋
〔摘要〕 行动者总是处于各种处境中。在客观的处境中,他们又总是根据自己对处境的主观界定来采取行动。许多学者从托马斯的“处境定义”理论出发,错误地把行动者对处境的界定看作他们自身经验的产物。戈夫曼则指出,行动者对其所处客观处境的主观界定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其内化的特定文化-历史-社会的框架造成的。本文从互动处境的理论出发,一方面借鉴贝特森的框架理论和皮亚杰的图式概念,厘清了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另一方面提出运用萨特发展出的存在论现象学,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地构造出特定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下互动处境中类型化的行动者的互动框架。本文还以一个文本例子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应用。
〔关键词〕 处境定义;框架分析;互动处境;存在论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2-0079-12
一、导言
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看,他们总是处于各种处境中。①这些处境总是客观的。因为,个体行动者总是在他们的处境中从事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且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作用于处境中的对象,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此外,处境对于个体行动者而言,又总是限制和可能的双重行动条件。个体行动者只有努力克服处境中物和人的种种势力,或者顺着整个处境的趋势,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另一方面,处境又总是主观的。因为,个体行动者似乎总是以自己界定为“真实的”处境作为其行动选择或行动取向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的名言——“如果人们确定其处境为真,他们的界定就确实会产生相应的后果”②——所表达的意思。个体行动者所处处境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总是依凭自己的主观认识来引导自己的行动选择或行动取向,而较少根据客观的形势在处境中行动。所以,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看,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构成了其行动的重要一环。
个体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主观认识是仅同自身的历史经验的积累,以及处境中经验对象的呈现和他对经验对象的关注有关吗?在过去的文献中,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和具有心理学倾向的社会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Argyle, Michael, Adrian Furnham and Jean Ann Graham, Social Situ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 MacHugh, Peter, Defining the Situation: the Organisation of Mean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8, p.4; Park, Dongseop and Yuji Moro, “Dynamics of Situation Definition,”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vol.13,no.2, 2006, pp.101-129; Stebbins, Robert, “A Theory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 vol.4,no.3, 1967,pp.148-164; Ball, Donald W., “‘The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aking W. I. Thomas Seriously,”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2,no.1, 1972, pp.61-82.] 這些研究者没能像戈夫曼(一位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互动秩序的研究者)一样认识到,个体行动者对处境中的经验对象的认识,依赖于他们自身具有的框架或图式。[Denzin, Norman K. and Charles M. Keller, “Frame Analysis Reconsidered,”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10, no.1 , 1981, pp.52-60;Gonos, George, “〈Situation〉 versus 〈Frame〉: The 〈Interactionist〉 and the 〈Structuralist〉 Analyses of Everyday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2,no.6, 1977, pp.854-867.] 戈夫曼认为,“也许,(人们)总是能够发现‘对处境的定义,但是处于特定处境中的人,通常并不创造定义,即便(有人会说)这是社会创造的;一般而言,人们所做的无非是正确地估计对他们而言处境应当是怎样的,然后据此而行动。”[Goffman, Erving, “The Neglected Situ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66, no.6, 1964, pp.133-136.]据此,戈夫曼进而确定,那个给予人们对处境做出正确评估的事物,就是具有结构属性的框架。基于上述认识,戈夫曼从互动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个体行动者用以判定其互动处境的框架理论,及用以分析这一框架的方法学基础和相应的分析路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以互动处境作为基本理论框架,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以及框架分析的方法学基础,再用一个实例来展示这一理论和分析工具对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构建的可能前景。
二、互动处境的简单概念
为了明确互动处境的理论框架,作者首先将以更清晰的方式界定互动处境的概念。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首先是处境的概念。一般而言,处境是社会行动者以自身的意图,通过符号性的和工具性的实践活动,区划出的一个行动得以发生的世界,即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
这里的世界指什么?在此,我们要借用波普三个世界的概念。[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Boyd, Brian, “Popper 's World 3: Origins, Progress, and Import,”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46,no.3, 2016, pp.221-241;Hedstrm, Peter, Richard Swedberg and Lars Udéhn, “Popper 's Situational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28, no.3, 1998, pp.339-64.] 波普认为,从理论上说,可以区分出三个世界: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以及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我们可以稍微变通一下,把这三个世界改成:自然世界、人工世界和符号世界。[波普的原文是,“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我们就可以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见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第114页。波普认为,他提出的世界三(third world)同其他两个世界一样的“实在(reality)”。他对此给出了两个思想实验。实验一和实验二分别是,“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书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包括我们关于机器和工具以及怎样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显然,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的世界会再次运转”,“像上面一样,机器和工具被毁坏了,并且我们的主观知识,包括我们关于机器和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也被毁坏了;但这一次是所有的图书馆也都被毁坏了,以至于我们从书籍中学习的能力也没有用了”。见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第116页。]在此,我们不预备对这三个世界加以说明和论证,而是把它们当作前提,直接应用。有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于是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所有实践活动都是发生在这三个世界之中。
其次要区分的是环境和处境。正是实践活动的意图把三个世界联系起来,并通过符号性和工具性的活动实现了环境和处境的分割。意图是通过行动者们的意向,把第三世界的内容投射到一个局部的自然世界上的精神活动。这里的意图是具有条件共同性的行动者意识到的。同时,它总是非个人的,但也未必就是集体的;但我们似乎可以说,有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整体意图,它从所有行动参与者的意图中突生出来,把各个参与者的独立情况联合成他们的当下处境。由于意图总是精神活动,所以它就必须通过实际的符号行动和工具行动把整个的时空条件标定出来,把可能的行动世界变成现实的行动时空条件。
再次,这个标定出来的时空条件内的所有事物,就同时成为行动者实现其意图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行动者的客观处境。从三个世界的理论出发,行动者的客观处境当然也由三部分组成,即自然对象、人的工具以及各种各样的符号载体。这些事物既成为行动者(复数或单数)实现其整体意图可资利用的促进要素,也成为妨碍整体意图实现的阻碍要素。
最后,处境虽然总是客观的[对于“处境是客观的”这一命题,我們还缺少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只有一定的直观观照。不过,依照我们现有的简单想法,我们认为处境的客观性具有三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文化层次。三个世界的划分不是先天的,而是长期文化发展的产物。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层次。这尤其表现在当下行动条件的历史性中,特别是人工世界、行动的工具和符号的历史性。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层次。处境的社会客观性表现在行动者意图的交互性和整体性之中。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行动者对于处境的认识,而非处境本身的构造,所以我们暂时假定“处境是客观的”这一命题是成立的,而不深究它何以成立的根由。希望这样做并不会根本地影响我们对框架分析的论证。],但是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却并非总是客观的,或者可以说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总是主观的。这种主观性的来源可能有:(1)处境中各行动参与者的分化、独立和对立;(2)由于行动参与者的基本不一致,导致各自具体目标选择的不一致或对立;(3)由于各自目标的不一致或对立造成自身情感上的波动;(4)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上的缺陷;(5)在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中对其他行动者的行动的依赖。由于上述诸项因素的存在,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又总是主观的和带有情感特征的。于是,我们把处境中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的主观认识称作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定义,简称为情境。
依据卢曼对社会类型的划分,我们可以把社会行动者的处境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空尺度,即互动、组织和社会。按照卢曼的界定,“社会是所有相互可能联络的沟通行为的全体系统。”[Luhmann, Nikl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 Stephen Holmesand and Charles Larmo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70-76.] 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实际上指所有地球上的人类可能形成的总沟通系统。由社会所区划的处境就是人类总的客观条件,超出这个条件之外,就无所谓人类了。如果说社会是全尺度的,或宏观尺度的处境主体,那么组织就是中观尺度的处境主体,因为组织是由组织的成员之间可能的沟通形成的系统。组织的关键是边界形成和自我选择。由组织所区划的处境,称作组织处境。最后,由个体的同时在场,并以面对面的形式展现的可能沟通,就称作互动沟通。由个体间的互动沟通所区划出的处境,就是互动处境。互动处境总是个体间的、当下的和即时的处境。它具有倏忽而生、倏忽而灭的特点;同时,它可能受互动者之间历史交往习惯(通常所说的关系)之影响,也可能进而增强、削弱,甚至破坏或颠倒交往者之间的关系,但它本身不是关系,不具有持存和连续的特征。互动处境是微观的且自成一类的。[Kemper, Theodore D. and Randall Collins, “Dimensions of Micro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6,no.1, 1990, pp.32-68;Maiwald, Kai-Olaf and Inken Suerig, Microsociology: A Tool Kit for Interaction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0, pp.1-13.]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戈夫曼倾力研究的正是各种类型的互动处境。他指出,“当两个或多个个体发现对方即时在场时,一个社会处境就出现了。同时,这一处境会一直持续到倒数第二个人的离去。身在处境中的人们可能被他人称作聚在一起,即聚集。虽然,他们之间可能是分开的、沉默不语的或者距离较远,抑或仅仅片刻同在,聚集在一起的参与者总是表现出聚在一起的样子。”[Goffman, Erving, “The Neglected Situation,”pp.133-136.] 在这种当下的、即时的、面对面的聚集状态中,既有的文化规范和规则调节着聚集者之间的相互行为。因此,戈夫曼认为,互动处境具有其自生的内在秩序,即他所谓的“互动秩序”[Goffman, Erv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82 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no.1, 1983, pp.1-17.];进而,他认为对“互动秩序”的理论探索需要有独特的方法论和方法,也就是微观分析,而经由微观分析获得的理论成果,即构成了互动处境的理论。他的框架分析概念,就是用于分析互动处境中行动者如何认识或定义自身处境的方法工具。
三、框架的概念
戈夫曼框架概念一方面来自乔治·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特别是贝特森关于“游戏和幻想的理论”[Bateson, Gregory,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Man 's Understanding of Himself,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8, pp.177-193.],另一方面框架的概念同皮亚杰的图式概念又异曲同工。
1.贝特森与皮亚杰的贡献
贝特森发现动物之间通过信号沟通,从而使得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游戏的特征。比如,两个小动物之间能够游戏般地撕咬,而不是真正的争斗。把游戏和争斗区别开的信号,其中主要信息是“这是游戏”。贝特森把包含有信息“这是游戏”的信号沟通,称作“元沟通(metacommunication)”。贝特森还指出,建立在游戏、威胁、表演、欺诈基础上的符号沟通,是高度复杂的现象。
元沟通是框架行为,因为在“这是游戏”的范围之内,所有的行动都不再具有原来的实际效果,只剩余有其象征的意义。同时,框架是一种心理上的结构,同画作的画框或数学集合有相似之处。例如,画作的画框把审美者的注意力引向框内,从而把框外的一切都当作背景因素和干扰因素。与画作的画框或数学集合不同的地方在于,心理上的框架是看不到的,是生成意识的结构,而非意识本身。此外,心理学上的框架所屏蔽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功能,因为正是那整个的被屏蔽的区域使得框架之内的经验具有意义和秩序。
皮亚杰的认知图式概念也是心理学上的结构物,同贝特森的框架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重要的区别。
皮亚杰[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45页。]认为,人的认知首先从感知-运动发展起来,即在婴儿期的早期,由于婴儿的生物学基础和外在环境的经常刺激,使得他们发展出复杂的“动作-图式(action-schemes)”体系,能够按照空间-时间的结构和因果的结构组织起他们身边的事物,成功地解决许多动作上的问题(如伸手取得远处的或隐藏的物品)。
感知-运动图式经由同化作用最后发展成一种动作的逻辑,包括各种关系和对应(事物间的转换函数)的建立以及图式的分类(基于动作的分类,而不是逻辑的分类),并为日后的思维运算奠定基础。随着婴儿的成长,大约在1岁半至2岁期间,他们开始发展出另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功能,即“符号功能(semiotic function)”,从而使其知觉和动作的对象变成符号化的事物(认知图式开始发展起来)。皮亚杰[让·皮亚杰:《儿童的道德判断》,傅统先、陆有铨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122页。]还发现,儿童的游戏化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从“自我中心”阶段到“协作游戏”阶段的飞跃。在自我中心阶段,儿童虽然已经能够模仿范例,发展了共同游戏的兴趣,但他依然沉溺在自己的乐趣和想象中,同时,他认为规则是神圣不可触犯的,是成人生产的,是永存不变的,而且任何对规则的更改都被他认作犯罪。在协作游戏阶段,儿童们会协商出共同遵循的玩法,在同他人的共同的游戏中获得快乐,会尊重玩伴和游戏本身,会根据比较抽象的公平观点来协商和改变规则。可以说,儿童的协作游戏说明,儿童的认知图式不仅是心理学的、更重要的它还必须发展成社会-规则的。
简单地综合一下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我们可以说,首先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的结构物,无论称它为框架,还是图式,它都能够使得人们符号性地组织起自身的动作和经验;在人而言,这种框架或图式的发展,不仅是心理学的和元沟通的,还是文化的(以语言为基础)和社会的(规则协商和规则遵从)。
2.戈夫曼的框架概念
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无疑直接来源于贝特森[Goffman, Erving, Frame A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7.],但是这一概念在戈夫曼的手中,主要用于解决个体行动者在其互动处境中,明确自身处于何种境地以及在此境地中应当如何反应的问题,即情境的问题。戈夫曼假设,“当个体加入到当下的(互动)处境中时,他们总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接下来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事?当个体处于困惑和疑惑的状况时,这一问题是明确的,而当个体处于通常熟悉的状况下,这个问题则是不自觉的。对此一问题的回答,将会引导个体对手头事物的态度。”[Goffman, 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p.8.] 進而,戈夫曼借用贝特森的概念假设,互动处境中的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定义(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是随意的,而是受框架的制约和引导的。这一个体心理学上的具有元沟通功能的结构物,是社会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出发,对互动处境的处境定义的研究,就不能顺着托马斯的研究路径(处境定义或情境分析),过分集中在个体的社会经历和经验对其具体情境的影响,也不能随着舒茨的研究路径,经由对普通人的常识的反思性观看来做理论的构想。于是,戈夫曼的目标就是,“分离出在我们的社会用于界定事件的基本理解框架,并分析这些参照框架的特殊的脆弱性。”[Goffman, 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p.10.]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在戈夫曼的框架概念中,具有第一位置的是首要框架(primary frameworks)。首要框架是行动者对特定事件的基本认识或分类,而且这些基本分类不依于任何一个更加在先的或更原始的解释过程。另外,如果没有了这些基本的解释过程,景象中的无意义的方面就会渗透进景象中的意义整体。戈夫曼指出,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有两类广泛的首要框架:自然和社会。自然框架包括所有无目的的、无导向性的、无生命的“纯粹身体性”的事件或者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事件;而社会框架则包含所有有意志、有目标和有智力的生命行为,特别是人的活动。比如,当一个验尸官问一具尸体的死亡原因时,他实际在问死亡的生理过程,也就是用自然框架来探寻和组织各种经验事实;而当他问死者的死亡方式时,他实际问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也就是用社会框架来想象死者过去的经历。
首要框架是关键,是基础。首要框架的基础性,依赖于对首要框架的变换。变换意味着赋予个体的整个互动处境以完全不同的意义或意味,比如打斗的动作仍然还是打斗的动作,但是在游戏的处境下,打斗的动作却不再具有打斗的现实性,而成为一个带有试探、威胁或逗弄意味的虚拟的打斗。
戈夫曼指出,对首要框架有两种基本的变换方式,一种调式变换(key and keying),另一种是捏造(desings and fabrications);还有一种舞台框架(Theatrical Frame),它是前两种基本变换的结合。
调式变换指互动处境的参与者通过一组约定整个地赋予他们的活动与首要框架不同的意义。例如,把实际的、严肃的和辛劳的农业劳动,通过调式的变换,变成一处关于农业劳动的表演型庆会活动,或者用夸张的工作表现出农作的辛劳,或者用欢快的歌舞表现出丰收的喜悦。捏造变换相当于互动一方对另一方的欺瞒,即一方努力模拟和造成一种使得对方“信以为真”的场景,从而引导或诱导对方的处境定义。舞台框架是调式变换同捏造变换的结合,它关键在于一方是表演方,一方是观众方。双方都知道表演方所造成的处境和角色为布置,为虚构,与此同时,双方都还必须努力地参与到那个虚构的处境和角色之中。
3.互动处境中的框架
至此,我们可以对框架的概念稍加厘定,从而为后续的框架揭示奠定一个简明的基础:
(1)我们假定:对于任何成人间(经历了社会化的且正常的行动者)的互动处境而言,文化共享的和社会专门的,具有元沟通功能的心理学上的框架之存在,是有序互动的基本条件(要素)。
(2)框架作为一种心理学上的结构物,其功能在于产生对处境的定义,即对互动处境中的个体行动者而言理解自己在何种处境下;在这种情境下,哪些事情将要或可能会发生;以及在这种情境下,自己应当和需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或做出怎样的反应。
(3)个体行动者之所以能够参与到互动处境中,端赖于他们既具有首要框架,又具有框架变换的能力(调式变换和捏造变换),甚至是具有多层次的框架结构(首要框架、框架的一阶变换和二阶变换或多阶变换)。
(4)在具体的互动处境中,个体行动者对互动处境的定义是可感可知的,甚至他们可以通过元沟通(比如“让我们来模拟法庭活动”)的方式来变换框架,但是框架本身是不可见的。
如果借用勒温(Kurt Lewin)[Kurt Lewin, 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Selected Papers, trans. Donald K. Adams and Karl E.Zener,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l, 1935, p.73.]对于个体行为的著名定义:B=f(PE)(其中B是个体的行为,P是个体的个性或人格,E是个体的环境,f是P和E之间的函数关系),我们也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形式化上述概念。
(a)DS(0)=Pf(A,S),其中A是个体行动者,S是他的互动处境,Pf是首要框架,DS是界定了的处境,0表示最初的或现实的情境。
(b)DS(1)=Tf1(A,S),其中A、S和DS与上同,Tf表示框架的变换,1表示一阶变换,依次类推还可以有二阶变换或多阶变换。
对于我们这些现实的分析者而言,我们不能止步于框架的概念,而是要进一步揭示出个体行动者在互动处境中应用的框架,或者说如何分析性地構造出特定的实际互动处境(以具体的历史社会现实为背景)中,个体行动者(类型化的行动者)可能有的首要框架。下面,我们将以本部分的框架概念为基础,阐述框架揭示的方法论基础。
四、框架分析的方法学基础
我们的目标是:分析地构造出特定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下互动处境中的类型化的行动者之互动框架。那么这种分析的构造如何可能呢?它的方法论基础在何处呢?在此,我们沿着戈夫曼的足迹,提出存在论的现象学是分析者从事互动处境之框架分析的可供选择的基础。这里所谓存在论的现象学[Lyman, Stanford M. and Marvin B. Scott,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General Hall, 1989, p.3.],我们指的主要是萨特在其哲学和文学的创造性工作中所展示出的东西。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此提纲挈领地说明同框架分析相关的存在论的现象学的要旨。
1.现象学态度与存在论立场
在此,我们不可能深入现象学的底层和众多分支中,只能表面地指出现象学路径中最明显的教导。
海德格尔曾明确地指出,现象学“既不是某种‘立场也不是某个‘流派,而且也不可能成为这类东西。‘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是从关乎实事的方面来描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5页。] 在这里,我们认为,现象学是一种通过彻底地质疑人们通常看待事物的方式来使被遮蔽的事物得以显现的方法,即“朝向事情本身”的方法。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现象学方法的关键,在于从自然态度转向现象学态度。所谓自然态度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或专业人士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应对各种环境和事物的习惯性取向。首先,自然态度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长期成功地应对其环境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态度;其次,对文化共同体的任一个体而言,自然态度是他从出生之日起即习得的东西的结晶;再次,自然态度是一种事务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遵循自然态度的行动者始终把自己限制在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及将要发生的事务之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用传统的方法来“应对”新的变化,甚至把自己的环境改造得能够适应传统的方法。持有自然态度的行动者不一定只是普通人,还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专家学者、政治家或企业家,虽然他们具有各种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拥有超过普通人的反思能力,但他们可能依旧陷于自身的行当和事务之中。现象学态度的转变是一种彻底的质疑,它是对一切自然态度的质疑,并通过对自然态度的质疑,发现新的可能性。
仅具有现象学态度并不足以成就任何方法,现象学是一种观察和描述的实践。不过,现象学不是普通人的观察,甚至也不是专家的观察,而是针对自我的反应方式的观察,即反观式审视。反观式审视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反思或反省。反思或反省是人们事后用一定的标准(善恶、真假、美丑)来评判自己行为的内容。例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反观式审视则不同。其一,它并不要求事后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是事中的行为,即身在其中而观在其外。举例来说,反观类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五庄观面对清风和明月的责骂时,使用的分身术,把假身留在“当场”,抽出真身做其他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孙悟空的分身术,所以我们只能把身体化的基本反应留在“当场”,而抽出我们的观察力去看。其二,反观式审视重在审视,不在评判。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请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全体共同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再说一遍,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7页。] 现象学的观察与维特根斯坦所要求的“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相似。反观式审视要求我们去观察事情是怎样发展的,要求我们专注地去看,要求我们仔细地且无遗漏地去看。其三,反观式审视所观察的不是“我的反应内容”,而是“我的反应方式”。例如,我在听相声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笑了。对此,反观式审视观察的不是我在笑“什么”,而是观察“什么东西触发了我的笑”“我是怎样不由自主地笑的”“这种笑的方式有何特别之处”,诸如此类。至此,我们可以说,反观式审视是对“我”面对事物的过程中的“自发”反应方式的观察和审问。分析的描述是现象学方法的完成,一方面这是因为描述是观察的自然成果,另一方面描述与观察相辅相成。观察为了描述,而描述终结观察。分析的描述旨在清晰地呈现“我”面对事物的过程中是如何“自发”地反应的。
再让我们看一下存在论。存在论的态度或立场可能有许多种[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23页。],在此我们选择萨特式的存在论态度作为方法论的基础之一。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态度有哪些主要方面呢?
首先,在萨特看来,人是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被不自主地“抛入”到这个他在其中存在的世界之中的。[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当个人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中,他就不得不依赖既有的世界,不得不接受既有的宗教、习俗、法律,既有的伦理道德和是非标准,以及生活在他人对自己的评判之下,并受到社会和他人的驱策而作为。萨特认为,这种“自在”的存在并无本质可言,而本质是一个人自己赋予自己的意义,本质是自我选择的过程和结果。
其次,萨特认为,个人无论在何种极端的处境中都有可能自由地选择。与其他“自由选择论”者不同的是,萨特反对“无意识”的托词,认为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是有意识的谋划,但许多人是按照他人和社会的意识和意义来谋划自己的生活,而“自为”的人是按照自己赋予的意义来谋划自己的生活。
最后,萨特承认,“每个人的处境和集体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只有在改变集体处境的同时才能改变个人的处境”[萨特:《提倡一种处境剧》,施康強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4—455页。],所以,他特别宣扬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7卷,第95—116页。] 萨特的“介入”主要指,通过文学的揭露功能来暴露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暴露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压迫,暴露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殖民,暴露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从而唤起人们的反抗意图和变革意图。
2.存在论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
经由上述说明,我们可知,存在论的现象学,以萨特式的存在论态度为分析者的态度,并遵从现象学的教导,反观地审视和分析地描述自我在处境中的种种状况,以及自我在处境中的种种反应方式。在此,我们可以用萨特的小说《恶心》,简要地说明这种方法论的主要技术。
(1)处境的虚无化
在萨特的小说中,恶心指的不是一种面对某些令人作呕的事物产生的应激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持久的、弥散性的情绪反应方式。当人们处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处境中,突然发觉日常的、平凡的和习惯的事物和行为都消失了其往日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时,他们就被一种恶心的情绪抓住了。
应当说,当萨特的主人公(实际上是萨特自己)被恶心的情绪反应抓住后,他就实际地既处于自己的处境中,但又不“在”(不能按照平常所规定的那样投入其中)自己的处境中,也就是从日常的自然态度中走了出来,进入到一种特定的现象学态度之中。主人公的日记就是主人公自身对自己的情绪反应方式的反思式审视和文学的描述。主人公通过他的反思式审视使得其处境中那些被“遮蔽”的事物和行为都显现出来。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2)人的物化
在萨特的现象学观察下,属于人的事物不再具有通常的属性,而是被当作物一样的东西加以描述。例如,萨特笔下的主人公观察到,“纸牌旋转着落在呢绒桌布上,然后几只戴着戒指的手拾起它们,指甲刮着桌布。手在桌布上构成白色的斑点,显得鼓胀,灰尘扑扑。纸牌不停地落下,手也来来回回地动。多么古怪,既不像游戏,也不像仪式,也不像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填满时间。但时间太大了,无法填满。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變得松弛。譬如这只红手,它踉踉跄跄地拾牌,这个动作太松弛无力,应该把它拆散、压缩”。[萨特:《恶心》,桂裕芳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人的行为本来是富于社会意义的,但是萨特把手的动作同人所赋予它的意义分割开来,于是只剩下手、纸牌两者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与其说充满意义和具有价值,不如说是机械性的、随机的、无目的的和散漫的重复。正是透过这一现象学观察,时间从隐蔽处显现出来,因为对人来说时间(生命本身的展现)总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但是此刻却被手和纸牌的联合运动所扼杀。
(3)物的人化
另一项相关的现象学观察技术是物的人化。物的人化不是对物进行拟人的描述,而是把物视作能动的主体,来看“我”在这一主体面前的反应。例如,萨特写道:“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萨特:《恶心》,桂裕芳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1卷,第15页。] 正是透过物的人化,观察者才能看到物本身的运作,看到物和物之间的联合以及物对人的主动关系。
(4)整体的印象化
处境中的个体,往往只看到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东西,而看不到自己所立身的较大的处境整体及其边界,那么如何使得这一较大的整体及其边界显现出来呢?这时,萨特的技术是整体的印象化,即去观察处境中那些能够显示其一致性和普遍性,以及其边界性的东西,并通过对这些事物的描述,呈现整体。例如,萨特笔下的主人公身处礼拜日的中产阶级人流中,就发现“我比正反方向的人流高出整整一头,我看见许多帽子,帽子的海洋。大多数帽子都是黑色的硬帽。有时一顶帽子被一只手臂举起来,微微发亮的脑勺露了出来,然后,几秒钟后,帽子又沉沉地落下来”。[萨特:《恶心》,桂裕芳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1卷,第54—55页。] 显然,主人公置身于其中的处境的整体性和边界是由“帽子的海洋”所界定的,同样也正是这一“帽子的海洋”将这一处境同其环境区别开来。
(5)差别的显微化
处境中的个体不仅会忽略整体处境,还会忽略处境中的差别。处境中的个体很容易把相似的行为视作意义相同的行为,而看不到处境中行动者之间的抽象区别(诸如阶级、地位、权力、声望这类抽象物)。如何使得行动者之间的抽象差别显现出来呢?萨特使用的是区别的显微化技术。例如,“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位先生拢着妻子的手臂,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微笑了起来。她立刻小心翼翼地收起奶油色面孔上的一切表情,像盲人一样走了几步。这是明确的信号:他们要打招呼了。果然,片刻以后,这位先生便举起了手。当他的手指接近毡帽时,它们稍稍犹豫,然后才轻巧地落在帽子上。他轻轻提起帽子,一面配合性地稍稍低头,此时他妻子脸上突然堆出年轻的微笑。一个人影点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那种孪生的笑容并没有立刻消失。出于一种顽磁现象,它们还在嘴唇上停留了一会儿。当这位先生和夫人和我迎面相遇时,他们恢复了冷漠的神气,但嘴边还留有几分愉快。”[萨特:《恶心》,桂裕芳译,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1卷,第56页。] 通过主人公对“打招呼”行为的显微观察,处境中三个行动者之间的阶级差别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即阶级差别这一抽象物并不一定表现在宏大的事物或景观中,而是时刻存在于最细微的面部变化、手的动作,以及身体的其他细微变化之中。
这里我们所说的存在论的现象学,是一种直面日常生活本身的方法论。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可能性的积极向往来探查日常生活中权能关系的无所不在,并揭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对权能关系的熟视无睹和俯首帖耳。
在此,我们并不准备把这种方法论直接拿来去看实际的互动处境,去揭示具体互动处境中的框架。这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可能不是实际的互动处境中行动者所应用和呈现的框架,而是作为观察者和分析者的“我”所带有的框架。所以,我们将像戈夫曼一样,把存在论的现象学用来分析有关互动处境的文本(戈夫曼分析的材料包括新闻、卡通、喜剧、小说、电影、舞台剧)。[Goffman, 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p.15.] 这样一来,各种形式的文本首先就不再只是虚构的娱乐产品,而可以成为具有揭示框架作用的数据。分析者据此可以揭示和构建出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行动者在某类互动处境中可能具有和应用的首要框架的模式。
五、框架分析示例
这部分,我们将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反思式解读,来构造特定时期中一群特定的行动者对某类互动处境可能具有的框架,从而展示框架分析的实例。
在此,被选中的文本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篇短篇小说写于1979年,那个充满了斗争和转折的时期。它既是“改革文学”的先声,也是“改革文学”的经典名篇。它既是写实的(用作者的话说,“写完自己的感觉是心里很畅快,几年来积压的所思所虑一泄而出。”[蒋子龙:《春江水暖鸭先知——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记忆》,《光明日报》2019年8月9日,https://news.gmw.cn/2019-08/09/content_33065050.htm,2021年10月9日。]),也是虚构的(任何叙事都是对“现实”的虚构)。这篇小说甫一问世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时代产儿的“小说”,反成了时代的推手。然而,令人讶异的是,这样一部同时代紧密相连的作品,在40年后,依然具有相当强烈的抓人的力量。为什么呢?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是要分析这部小说艺术创作的技巧和它的艺术价值,而是把它当做某类现实的调式转换,从而构造特定互动处境类型中行动者的框架。这里,我们的预设是:正是小说中所隐含的东西,既表现又扭曲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中较为深层的结构性的事物,才使得它具有相当持久的感染力量。于是,循着小说给予我们的感染力量,通过存在论的现象学反观,分析者试着去揭示和构造行动者的首要框架。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乔厂长上任记》的整个文本由“出山”“上任”和“主角”三个部分组成。这里,我们不预备分析整个小说,而仅针对“出山”中的“党委扩大会”,即揭示和构建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处于经济发展中心位置上的中层干部在“党委扩大会”这一互动处境中的框架模式。
1.“党委扩大会”
小说的正文,以“党委扩大会一上来就卡了壳……”[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5页。],这样的布局开篇,极其醒目地點明了整个互动处境的形式——“党委扩大会”。如果我们撇开作者的写作技巧不谈,而只反观我们作为读者自身的感受,会发现自己立即被这样一个卡了壳的“党委扩大会”吸引了进去,就像被某个有很大吸力的漩涡或某场很抓人眼球的游戏一样,没有任何“预备的”阶段,一下子就被带了进去。问题是:为什么读者会出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抓了进去,而我们又对之毫无反抗,坦然接受?显然,读者的反应不是源自那个外在的、纸面上的、虚构的东西,而是读者自身对这一虚构的“党委扩大会”的认知和想象。这就是说,读者不是被抓进去的,而是迫不及待地主动地走入其中的;即便是不能参与其事,也要能侧目旁观。何以如此呢?想一想,我们是如何被各种各样的探险所吸引的。探险包括了什么样的结构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似乎有两点:一是,探险总是对秘密(并非是完全无知的领域,而是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的领域)领域的搜索;二是,探险者知道这一秘密的领域中有某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存在。“党委扩大会”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具有相似的特征,它既是秘密的,又有其内在的价值。至此,作为读者的分析者,可能会对“党委扩大会”这一事物有所领悟。它确实是秘密的,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会议都具有不透明性,它从不向众人敞开,始终在事先就确定了所有参与其事的行动者的资格,甚至在开会之前就有一个翔实的名录,明确地规定了具体参与者,并将所有不在其中的参与者排除于其外。与这种会议参与者的资格性或指定性相伴随的,是它总是要做出一定的决定,从而引起涉及众人的某些事态的重要变化。会议之外的人,既没有参与的资格,也没有提供议题的资格,更无决定事态变化方向的资格,也无从知晓所谓的决策过程。会议之外的人只知道他们的生活总是被这一互动处境所决定,但是他们既不知道其生活路径将被向哪个方向所指引,也不知道是何种力量导致其生活方向的变化。因此,在读者看来,这种类型的会议,就是由一群有限的资格参与者进行的,通过某种无资格的人所不知晓的筛选过程,把众人生活中的某些事态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再经由某种不为无资格的人所了解的决策理由和决策过程,最终做出能够导致事态重大变化的决定。简单地说,这类会议具有把众人生活中的事态括置起来并加以改变的能力,而这种括置和改变的方式又具有严格的资格限定。正是它的资格限定,以及它的括置和改变能力,造成它对读者的吸引力。
理解了这类会议对读者的吸引力的来源,分析者也就看到作者在何处进行了调式转换。首先,作者把没有参与其事资格的读者变成了一位有资格的观察者,带着读者径直地走了进去;其次,作者还告诉读者,他将把讨论的议题和决策的过程清晰且有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至此,分析者对此类会议参与者的首要框架可能会有如下认识:(1)资格感;(2)封闭感;(3)能力感。这三种基本的感受相互连接,共同构成此类会议参与者的基本框架。资格感和封闭感构造会议的空间性质,而这种由所有参与者构成的空间,具有把“事物”围在其中的效力;与此同时,只有进入到这一空间中的人、事和物才是具有意义的东西,这空间之外的东西则没有意义。能力感始终针对的是众人的事态和事态变化。这种能力感首先决定了众人事态的值,即它区分出众人事态中那些有意义的、值得讨论的东西,甚至还进一步区分出事态的价值等级;其次,它还赋予那些被讨论事态的可变性和方向性。由资格感和封闭感造成的空间,其作用恰在于参与者能够把某些事态从空间的外部带入进来,再把事态即将改变的决定输出到空间之外。所以说,这一空间是能力秘密发挥作用的空间,而这一能力又在于引起空间之外事态的变化。
2.戏剧性张力的来源之一:事态的性质
当读者随着作者进入会议,立即感受到某种戏剧性的张力——会议的沉闷气氛,“但今天的沉闷似乎不是那种干燥的、令人沮丧的寂静,而是一种大雨前的闷热、雷电前的沉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第5页。] 对会议气氛的描写,无疑是作者用以吸引读者的写作手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考虑会议是沉闷的,还是热烈的,即不考虑会议气氛的具体情况,那么会议总是被某种气氛笼罩着。假如会议的气氛是所有会议参与者处境定义的结果,那么造成会议气氛的原因就应该能够反映会议参与者的框架。是什么产生了会议的气氛呢?“算算吧,‘四人帮倒台两年了,1978年又过去了六个月,电机厂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完成任务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全局都快被它拖垮了。必须彻底解决,派硬手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第5页。] 紧随着会议气氛的烘托,作者直接告诉读者造成会议气氛的缘由——事态是严峻的。因此,对于事态性质的认识和判断,即那种可以被称作“事态感”的东西,显然是会议参与者的框架的组成部分。对于分析者而言,问题是如何可能理解和构建那样一个历史特定时期具有特定位置的行动者的事态感?因为,分析者作为读者,在40年后已经很难理解“‘四人帮倒台两年了”“1978年又过去了六个月”“电机厂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完成任务了”这样的话语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意义了。读者能够体会到事态是严肃的和紧迫的,但问题是那些可能的历史-社会中具体的行动者是怎样理解和认识事态的性质的呢?“四人帮”的倒台显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国家层面整体政治运作方式的某种转变。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上层的政治变动在经过了两年之后,它的效应并没有反映在基层工作的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体现在电机厂计划任务的完成上。因此,在作者的描述中,事态的性质首先是同它的政治属性相关的。作者在此突出和放大的是事态的政治意义,所以对会议的参与者而言,事态的严肃性和紧迫性也是用它的政治意义加以度量的。换言之,对当时的行动者而言,事态的政治感产生了他们对事态性质的基本判断。此外,在引入事态的政治感的同时,作者还引入了时间这一维度。作为读者,我们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事态的时间属性了,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时间的规制,例如,上班的时间、工作的长短,是否在某个时间节点前完成了工作任务,等等。但是,对当时的行动者而言,时间可能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赋予它的精确性和压迫性,或者,至少不像当下的行动者处处用时间规划和衡量自己的行动,并时刻感受着时刻、时期和时代的变动。至此,分析者大概可以说,当时历史-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似乎同时具有两种面对事态性质的框架:事态的政治感和时间感。这两种事态意义的组织框架也许比较纯粹地体现在不同类型的行动者身上,也许以不同比例混合在同一行动者身上,但是,这两种框架总是有张力的,而正是两种框架的紧张造成了小说的戏剧性张力。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3.戏剧性张力的来源之二:我,位置、利益和理想
在使得读者明了事态的严肃性和紧迫性之后,作者随之展开了对会议参加者互动的描写。其中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场面由以下因素构成:(1)机电局局长霍大道的不动声色,“他透彻人肺腑的目光,时而收拢,合目沉思,时而又放纵开来,轻轻扫过每一个人的脸”。[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第5页。](2)小说主角的情绪压制,“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第5页。](3)副局长及众人对主角的戏谑,“得啦,光朴,你又不吸,这不是白白糟蹋吗。要不一开会抽烟的人都躲你远远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第6页。] (4)小说主角的主动请缨和决心态度,“别人不说我先说,请局党委考虑,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我愿立军令状”。[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2卷,第6页。] 此处,分析者需要追问,这几项要素何以会产生戏剧性张力,或者说,为何读者会被小说中各种角色的行为所感染,或者受其引导,或者为之激动,或者为之不屑?在此,分析者必须反观自身情感的变化,并以此为线索找出自身何以能够进入到作者设置的情节中。当分析者反观自身对情节描述的反应时,首先会看到“我”的对象化,即分析者的“我”不再是旁观者,“我”似乎被角色的行为所吸收,变成了角色本身。这时角色的行为和表现就成了分析者的“我”的行为和表现,同时,角色之所见和所感成了“我”之所见和所感。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对象化了的“我”怎样像角色一样去看?
首先,“我”可能像角色一样感受着自己在整个处境中的位置。这一位置不是“我”在空间上的位置,而是更加抽象和微妙的,“我”同处境中的他人在阶序(是否平等)、立场(是否一致),乃至心理距离(亲近与隔膜)和道德评判(高视与鄙夷)造成的综合感受。正是这种综合的位置感,首先规划了“我”的看的行为。“我”可能像“局长霍大道”一样自如地带有审视味道的方式来巡视处境中的每个人,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能够”这样巡视的位置上,因为在场的是“我”的部下,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因为“我”的巡视可以鼓励和安抚“我”所亲近的人,还可以向那些立场同“我”不同的人表示不满。简单地说,巡视和审视恰恰表明了“我”对自己优势地位的自信。
其次,“我”还能像角色一样感受到自己同事态的现实关系,即“我”的利益感。对“事态”的现状和“事态”可能变化的认知,其中不可或缺地包含有“事态”对“我”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间接的,或者是无关的。因为“我”总是能够在事态或事态的可能变化中看到它对“我”的吸引和排斥,虽然被吸引或被排斥的是“我”,但“我”是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吸引或排斥。如果“事态”或“事态”的变化同“我”没有关系,就是说“我”被排斥于事态之外,那么无疑“我”虽在处境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位旁观者(当然“我”既可能作为积极的旁观者,也可能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置身于“事态”之外。如果“事态”的可能变化同“我”有关,或“我”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吸引,那么“我”就不得不进入“事态”之中,看看它对“我”影响的方向、大小和远近。不仅如此,“我”还要深入到“事态”的各种可能变化之中,并在其中发现对“我”有利的变化和不利的变化。最后,“我”必须对“事态”的可能变化根据常识的理由(在小说中,常识的理由是把工作岗位分成“肥缺”“美缺”“瘦缺”和“苦缺”的理论)做出自己的选择。
最后,“我”还能像角色一样感受到自己的理想我在事态上的投射,即“我”的事业感。每个行动者都可能具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最佳可能状况的想象和向往,并期待自己的想象和向往能够得到他人的承认,这些就构成了行动者的一个理想我。这一理想我是超处境的,因为它是我的构成物,而非处境的要素。这一理想我可能是模糊的且未被自我所强烈感受到的,也可能是清晰的并被自己强烈感受到的。因此,这一处境以外的理想我,可能位于整体经验框架的边缘,也可能位于整体经验框架的中心。如果它始终处于“我”的经验框架的中心,那么在“我”所置身的各种处境中,“我”都是通过理想我来看待事态同我的关系的。“我”积极地在每一个事态中寻找实现理想我的可能性(理想我的时机)。于是,任何同实现理想我的可能性无关的事态,无论其中包含多少常识所认可和期待的利益,它也是同“我”无关的事态;那些同实现理想我的可能性有关的事态,“我”都努力将其把握成时机,并据此来想象和规划“我”的可能行动。这就是“我”的事业感。当“我”在事态中看到了较大的时机或关键的时机之际,疑虑和兴奋可能同时袭来,抓住时机的渴望和小心谨慎的谋划也可能同时行进。
4.戏剧性张力的来源之三:力量的对抗
小说中,作者赋予作品的另一处戏剧性张力,是通过分别引入主人公的搭档石敢和主人公的阻力冀申来实现的。作者既通过主人公对石敢的说服,描绘了石敢的外表冷漠和内在热诚,也通过副局长徐进亭和局长霍大道的对话,描绘了冀申的谋人、谋位而不谋事的行事习惯,从而为后续故事的展开埋下了伏笔。虽然就会议处境而言,作者完全可以不引入任何参会者之外的行动者,可以用其他的情节来引入对立的线索。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作者对两位行动者的引入又是极其自然的,不引入反而变得不现实了。那么为什么读者会被作者的两组对话吸引,并感受到两组行事之间的张力呢?当分析者反观他作为读者所受到的吸引时,他会发现这是他期待发生的东西。这就是说,读者自己在小说中寻找一种对抗,力量之间的对抗,以及力量结合方式之间的对抗,所以他才能够立即感受到力量对抗之间的张力带来的吸引力。小说促进读者继续阅读下去的动力似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读者对力量对抗的期待,另一个是读者对力量对抗方式的未知,而作者正是通过力量对抗的曲折展现,一方面满足读者的期待,另一方面满足读者的未知。这种力量对抗似乎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力量团块的辨识,即读者总能够区别出各种对抗性力量的整体属性,或者像在象棋或围棋等棋类游戏中那样,给不同的力量涂上不同的颜色;另一个层次是力量的部分与部分的结合和对峙,即同一力量团块内部的行動者之间的协作或利用,不同力量团块内部的行动者之间的阻挠、反对或压制,甚至还有一力量团块内部的行动者转变成另一力量团块内部的行动者。因此,分析者似乎可以推论,现实中的行动者的首要框架也应当具有相似的力量对抗感,区别则在于现实中行动者的力量对抗感可能有不同的类型,亦即,现实中行动者对其力量对抗的目标和方法可能有不同的领悟。分析者,也就是现实行动者首要框架的构建者,当然可以顺着小说的情节和故事的展开,具体地构建出现实中行动者的力量对抗感的类型,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
在此,我們显示出的分析可能还很初步,很粗糙,也还很主观。然而,我们对这里展示出的分析对象和方法取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它们具有可观的分析前景和应用前景,而且任何方法上的初步性和主观性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探索(比如扩大相关文本的范围、扩大感受者的范围或扩大分析者的范围)来改进。
六、结语
在最后一部分,对前面的论述做一简明的概括:
1.行动者们在处境中行事。他们的处境,可以根据卢曼的社会类型理论,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空尺度,即互动处境、组织处境和社会处境。
2.互动处境中的个体行动者通过界定其处境(处境定义或情境形成)来引导其行事。然而,他们的情境形成不是随意的,而是由他们自身具有的处境认知框架产生的。
3.互动处境中个体行动者的认知框架,是文化共享的和社会专门的,且具有元沟通功能的心理学上的结构物。特定互动处境的行动者所以能够参与到互动处境中,端赖于他们既具有首要框架,又具有框架变换的能力。
4.对互动处境的研究要求分析者能够分析地构造出特定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下互动处境中的类型化的行动者之互动框架。
5.存在论的现象学可以作为分析者从事互动处境之框架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6.框架分析的目的是:以存在论的现象学作为方法论的基础,试图通过对各种具体时代和文化-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情境文本(对具体互动处境的描述,它的形式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声音的或影视的)的分析,来构建具体时代和文化-社会中的行动者在特定互动处境中可能具有的框架类型。分析者可以通过自身对文本的阅读感受的反观来辨识文本作者的括置和框架转换的具体方式,进而揭示现实中行动者可能具有的首要框架。
(责任编辑:何 频)
〔作者简介〕赵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①Dixon, John E., Rhys Dogan and Alan Sanderson, The Situational Logic of Social Action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p.2.
②Thomas, William Isaac, Child in America, New York: A. A. Knopf, 1928, p.572.23AA1D49-635F-42E1-BCAB-17FF3645FC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