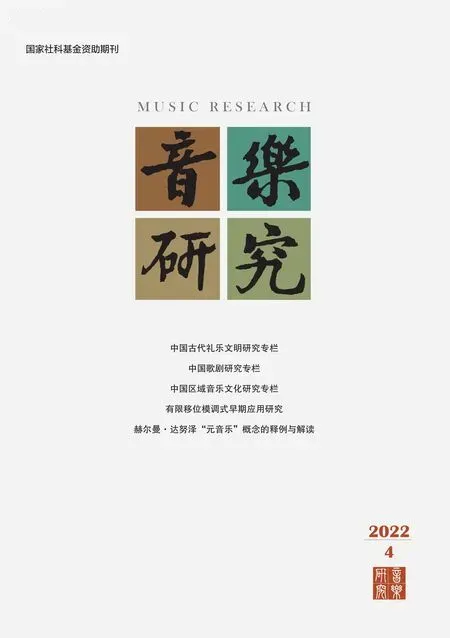论张若谷歌剧观的历史价值
2022-04-07满新颖
文◎满新颖
回首一个世纪的中国歌剧史,论及20世纪20 年代对尚处于发育期的中国歌剧有过重大影响和建树者,张若谷的贡献是不可逾越的。近年,学界对张若谷的研究不断深入,促使笔者思考: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为何能在1928 年前对歌剧本质就有了比同代人,甚至比后世很多留学东西洋的专业学者更深入的认识?身处唯美主义、西风鼓噪的环境,又在国剧派、民粹派、民族主义文艺和国民乐派鼓吹者杂处的多种文艺思潮变奏影响之下,他为何有如此清醒的辨识力?最“离奇”的是,在两三年时间内,他好像一下子学会了能以跨文化、跨时代的国际眼光来反观中国本土初生的歌剧,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他自修的?尽管张若谷的某些艺术观至今仍有可商榷之处,但是他对当代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的研究,依然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启示。
年轻时期的张若谷精力旺盛,笔锋也相当犀利。他曾或多或少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同时还对西方先进文艺思潮和生活品味公开表示过兴趣。当时很多不公正的评价,淹没了他在歌剧理论与评论方面的真正历史功绩,这是他的艺术思想至今鲜有人所关注的重要原因。
目前所见,有关张若谷在音乐和歌剧评论方面的文献,大都集中于他1932 年出国前和1935 年回国后这短短几年间。他与冼星海等音乐家有过交谊,也曾发表过不少涉及音乐领域的文章,如1935 年10 月他发表在《文化建设》上的《中国的国歌》;1939 年又为法国大革命150 周年纪念邮票的发行而详细撰写过《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产生》。总体上看,我们也仅能确认其前半生的早期阶段,短短三年就形成自己的歌剧观,然后遁出了歌剧理论和评论领域。这种艺术趣味转移的原因,是值得学界去思考的。
1925 年,意大利贡萨莱兹家族歌剧团来上海驻场演出,《申报》破天荒地予以全面的跟踪报道。主持《申报》“艺术界”栏目的朱应鹏,聘张若谷译介剧团要上演的剧目,以吸引更多的中国观众。在整个11和12 月,张若谷(笔名“若谷”)频换各种笔名,如“虚怀”、“马哥”、“孛罗”(疑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之意)等,接连发表了大量歌剧知识介绍文章。从演出前后《申报》所刊文章的内容和比例看,此前《申报》“艺术界”专栏所刊文论多为美术、音乐、话剧等艺术种类,但当该团来沪演出时,则是集中版面史无前例地关注歌剧。
在11 月3、6 日的《申报》上,张若谷先为演出写了《歌剧〈浮士德〉略说》和《再说歌剧〈浮士德〉》;11 月22、23、26 日,《申报》又三次连载他的《西洋乐式剖要——为出席西洋音乐会诸君作》,介绍欣赏欧洲音乐常识。特别是在“丙”(歌剧)部分,张若谷特意引用了尚在德国留学的王光祈所著《西洋音乐与戏剧》一书对歌剧四种样式的划分法。11 月24 日,《申报》发表了“马哥”《俄人歌舞团之表演》一文,对前天“白俄”歌舞团的《快乐寡妇》歌剧演出情况和轻歌剧体裁做了简单解说。此后,他以“孛罗”为名,发表了《歌剧〈乡村武士〉略说》(今译《乡村骑士》,11 月26 日);此外,还以“虚怀”为名,发表了《歌剧〈里哥雷多〉略说》(11 月27 日);随后再以“孛罗”为名,发表了《歌剧〈灰陶剌〉略说》(《费多拉》,12 月3 日)等,总计11 篇。
由此,张若谷不仅创下了《申报》歌剧报道史之最,也成为外国歌剧在华传播史上中国人新闻报道之最。当时他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歌剧评论、歌剧知识介绍,显然比其他同类文章显得更有深度。
一、张若谷对20 世纪20 年代初我国歌剧本土生态的分析和研判
20 世纪20 年代,在东亚大都市上海,对西洋歌剧感兴趣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而能靠文章谈出具有专业水平的歌剧见解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张若谷除了几本很有限的中外文歌剧知识手册外,他对歌剧的研究也仅靠观看俄罗斯和意大利巡回歌剧团的演出,再就是不失时机地去看早期的电影歌舞片、上海音乐会中的歌剧片段而已。然而,“足不出沪”的张若谷,却能对西方歌剧的认识充满了睿见,达到了一时竟无人可及的地步。在当时戏曲与话剧矛盾对立的大文化环境下,面对我国文艺界对歌剧不正确的认知,他的分析与研判就显得既客观又冷静。
张若谷所著的《歌剧ABC》①张若谷《歌剧ABC》,世界书局1928 年版。有一个很集中的写作目标,即什么才是真歌剧。在他看来,歌剧就是歌剧,既不能是“话剧加唱”,也不能是改良后的“国剧”和旧戏曲。在该书绪论中,张若谷以艺术评论家的独到眼光和犀利的笔锋,真切地概括和分析了上海的音乐教育和歌剧普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1)在当时的学校中,教音乐的留日教师水平很有限,只有普通音乐教育知识。(2)艺术在上海正在成为“热门货”。(3)无论是欣赏市政厅春、秋、冬三季的每周音乐会,还是看一年一度来华演出的意大利歌剧团,本土观众很少,“二等的座位也找不到半个中国人的影子”。(4)文化界有两类群体混淆了歌剧的本质:第一种是“卖野人头”者(实指黎锦晖等人的歌舞团体),他们把“歌剧”一词当成商业性儿童歌舞剧炒作的卖点;第二种是搞戏剧的文人,也像日本人对待歌舞伎那样,拿戏曲与歌剧做皮相的表面化比较,“说什么‘京剧性质纯是欧洲歌剧体裁’”。
张若谷认为,这些话剧人的最大弱点是不懂音乐。他这里所说的音乐,不再是中国传统音乐,而是今天这种已调和了中西方现代音乐概念的新音乐。虽然他认为研究西方音乐者也“未必要一定排斥中国的旧剧”,但是对国粹主义却一向持鲜明的嘲讽态度,②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艺术三家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7 年版,第305 页。这无疑与傅彦长接触较多的大同乐会代表人物郑觐文的论点格格不入。在他看来,研究话剧,留学美、日等国的那一部分“海归”人士,将旧戏曲当歌剧,同样带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看自己的传统文化:仅靠视觉的表层审视舞台表演,而不在音乐所需要的听觉上真正理解歌剧和戏曲两者的本质差异;崇古、泥古的戏曲思维和“话剧加唱”思维,这两类论断在对歌剧本质的表述问题上会误导歌剧本土化,不利于其健康发展。他阐述这个观点,并不是真的要排斥戏曲。
作为上海的著名文艺记者,张若谷后来也曾与梅兰芳有过交流和接触,想必也读过鲁迅对梅的一些看法。但对于歌剧,则是要一码归一码,不能简单地以本国戏曲的思维定式和重叠的文化印象对歌剧进行概念上的混淆。搞歌剧艺术要有世界眼光,遵循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如何真正跳脱歌剧初识期国人自设的框架,学会以西方歌剧本体论的眼睛反观正在发育中的中国歌剧,这才是他当时所持有的个人学术立场。
张若谷对歌剧的定义是:“集成声乐与器乐大成及综合其他姊妹艺术——绘画、建筑、舞蹈、文学——的一个总表演。”这当是20 世纪上半叶国人对歌剧最为生动、准确的概括。张若谷援引闻一多对话剧中社会问题剧批评的观点,指出不懂音乐的这些人是怎样故意矮化歌剧价值:“戏剧是沾了思想的光侥幸混进中国来的。不过艺术不能这样没有身份。你没有诚意请他,他也就同你开玩笑了”③参见夕夕(闻一多)《戏剧的歧途》,《晨报副镌·剧刊》1926 年第2 期(6 月24 日)。。虽然张若谷也坦陈当时的旧戏早就没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他却不能苟同余上沅、宋春舫、徐志摩等“许多从欧美各国的戏剧者”那种坚持要把戏曲当歌剧进行改良的低端意见,这无异于让新出生的歌剧去自生自灭。张若谷要竭力捍卫的是歌剧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无可替代的价值,概念上首先就不得含混。20 世纪20 年代初,作为“舶来品”的歌剧在当时的确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社会文化处境和艺术生态。相对而言,赵太侔虽然要比余上沅等人更能意识到新音乐对于建立中国歌剧的决定性价值,但是他同样对国人的音乐创作能力持绝望态度:“谈旧剧改革,音乐是当头最大最难的一个问题。这件工作,不能不属于我们将来的瓦格奈(瓦格纳),不是开一个委员会,定出一部计划书来,就可以改革了的。”④赵太侔《国剧运动》,新月出版社1927 年版。
“国剧运动”闹得最火的时间,是1925—1928 年,随后基本宣告破产。恰在这时,张若谷却在潜心研究歌剧如何才能在中国文化生态中安身立命,所以他自然要密切关注国剧阵营的反应。面对要走投机、搞改良、用拼合和刻意回避新音乐的民族化道路,“国剧”派希望在旧歌剧(戏曲)和话剧之间能尽快地调和出与西方歌剧有对话可能的“国剧”来,这显然属于少部分人对歌剧绝望后的那种心有不甘:一面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瓦格纳乐剧崇拜之风带来了国人歌剧梦的“恐高症”;另一面则是“国剧派”对如何搞出真正的歌剧不敢有奢望,更重要的是,不懂现代西方音乐的那种无奈——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新音乐文化不自信”在起副作用。对此,张若谷自己也不免对歌剧的本土化发展前景感到悲观绝望,他甚至认为,照当时一切音乐文学艺术如此饥荒,又如此孱弱地走下去,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歌剧。⑤同注①,第11 页。这种表达,实际上透出了他对中国发展歌剧艰难程度的担忧,流露了他内心的自我矛盾。
张若谷写书时才20 岁出头,在文字表述上不免存在前后概念外延不准确之处,一些话在当年许多从事话剧、戏曲之人听起来很是刺耳的。他居然还像舒曼那样,仅把自己和傅彦长、朱应鹏、曾朴等少数“异国情调”小圈子视为同盟,当然有故步自封的局限,他当时也没把努力探求歌舞剧五、六年之久的黎锦晖看作中国歌剧的一线希望。对经典西方歌剧的高度认同和对本土歌剧发展质量低迷的担忧,让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试想,一个看过如此多西洋经典歌剧又为之日夜奔波的孤寂中人,又怎能不为中国歌剧的发展心焦和感慨?
《歌剧ABC》成书之后,张若谷就再也没能集中精力去专门研究歌剧,而是转向更擅长的文学批评领域。如果仔细端详当时他曾积极思考的几个基本观点,就不得不感慨其中这些思考的深刻性。
二、张若谷的歌剧本性视角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前人相比,张若谷既不是什么话剧和歌剧专家,也不像王光祈那样,以音乐学为专业游学欧洲,但张若谷对歌剧本性的认识却远在前人和同代人之上。这是因为他与绝大多数触及歌剧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完全不相同的家庭、学校教育背景: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喜以现代白话文写作,会拉丁、英、法三门外语,更接触过大量西方文化和原文话剧,同时,也有一点较初级的作曲知识和演奏能力。应该说,他在艺术感性素质和跨文化领悟能力上是超常的。
《歌剧ABC》远比王光祈的《西洋音乐与戏剧》说理论证更明确,歌剧和各种组成要素的定义和概念更清晰,对剧本故事的介绍更能抓住戏剧性的音乐结构要害。简明扼要,其中也透露出他个人的深切体会和理性认知。
“歌剧的灵魂为音乐,其他一切舞台上的背景与动作都是歌剧的肢体”。张若谷用“灵魂”和“肢体”作比,来揭示歌剧的本质为音乐,目的是为分清歌剧与戏曲的界限。他认为,歌剧不同于本国旧剧,而新剧(指话剧)不但存在“音乐的许多缺陷,不足以表现人生繁复的意境与情绪;而且简直都是没有戏剧作家的内在灵魂”。把音乐作为“内在灵魂”论的观念,到底是受谁的影响所致,其思想的源头至今尚无定论。但笔者认为,这当与他从小所接受的天主教音乐观念、洋式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作为歌剧理论逻辑的起点,歌剧音乐“灵魂”论的合理性,也并不能当成是他歌剧观念的奠基石,固然其中包含了他对歌剧音乐创作重要性的认识,但从戏剧内容和音乐创作形式上看,他显然是为了以此排除戏曲改良为歌剧,所以才引用当时较新锐的文化进化论来为歌剧本性论找到逻辑论证的起点。这种观念至今仍在中外歌剧和音乐剧理论表述中大量存在。
三、张若谷歌剧进化论视角的理论来源
牧歌剧长期被西方学界作为歌剧起源的直接推动力之一,歌剧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副产品。“近代的歌剧,就是音乐发展的最纯全的结晶”,张若谷的这种论观,显然是从欧洲音乐戏剧进化论看戏剧。这种影响的最直接和显著的表现,是他所在意的王光祈带来的,此外还来自对傅彦长、萧友梅等人的一些现代音乐观的接受,甚至还杂有日本歌剧推动者小林爱雄(1881—1945)的影响。
张若谷认为,不论中国戏曲、古希腊戏剧、印度“南提阿”,还是日本的能乐等戏剧形式,都是旧时代遗物,它们“只能当作雏形歌剧的骨(古)董题材,都不能与欧洲近代的纯歌剧相比拟”。他目标明确,就是要在文化现代性、艺术专业性和自身规律性的多重视角上,去讨论歌剧的本性问题,以说明戏曲音乐与歌剧音乐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不同”与“不及的不同”。这当然是条难以跨越的鸿沟,至于具体的缺陷在何处,他没能进一步阐释,只是从音乐进化论把歌剧看成是超越以往任何戏剧形式的一个新剧种而已,以此表明歌剧音乐与其他所有的戏剧音乐形式相比存在差别,具有必然性。可见,其潜意识中仍带有挥之不去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痕迹。他的这种歌剧进化论观,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性文化思潮的影响所致。最终的原因可能是,外国音乐家和少数中国文化精英,出于对瓦格纳及其乐剧的崇拜而得出的结论。他的观念中的进化论因素,至少还应从如下几方面予以审视。
(1)严复所译的《天演论》(1897)早就在国内知识界传播。
(2)梁启超“文界革命”思想(1898)或“小说革命”(1902),以及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1904)中,都透出现代美学思想,也已为知识界所接受。相对而言,尽管这几位前辈学者都把进化论视为现代文化启蒙和救亡兴国的利器,但是梁启超却没像王国维那样,把进化论作为其治学的方法论,自觉地运用于本土戏曲的研究并从中得出“一代有一代之戏曲”的认识。
(3)依前两项进一步推测,由于张若谷与曾朴父子交往甚密,彼此都崇敬陈季同(严复福州船政局的学友),又都懂法文,崇法国文艺。而陈季同法文版《中国人的戏剧》中所带有的戏剧进化论思想,也有可能成为张若谷歌剧观念的来源之一。从张若谷的某些评价语感上看,他对一些问题的表述(尤其是其在第一章“歌剧之定义”上),就非常接近陈季同当年那种法国式论证和表达方式。陈季同是现代中国文艺批评中最早表现出进化论思想的学人之一,其理性批判思维在《中国人的戏剧》“前言”中就表现得很突出:“这是一个中国人在向莫里哀致敬,如果他的大胆想法能被原谅的话,他愿意称自己是莫里哀的弟子”⑥陈季同著,李华川、凌敏译《中国人的戏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 页。。张若谷对待瓦格纳的态度,与陈季同对莫里哀的崇敬十分相似。陈季同认为中国戏与欧洲戏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⑦如《中国人的戏剧》载:“如果欧洲戏如我们一样唱的角色的话,那就更接近了。和中国戏最像的是喜歌剧。喜歌剧包括演唱的场景,是最为迷人的一种法国艺术”。参见注⑥,第72 页。他把带对白的西方喜歌剧等同于本土戏曲,可是,这二者毕竟存在本质差异。陈季同在出书前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戏剧中是否有演唱这种表面性特征而已,他并没注意到在演唱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音乐,或者说具有真正原创性、多声性与交响性等更多制约因素的歌剧音乐作用。陈的这种看法,与至今绝大多数还没有认真分辨过歌剧和戏曲差异的普通民众并无二致。可是,张若谷的书中则已显现出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表达。
作为中国第一代歌剧评论家,张若谷显现出了与王国维治戏曲学探求艺术本质一样的那种自觉意识。他非但没因崇拜陈季同的造诣而苟同其说——中国戏曲相似于法国的喜歌剧,也没因与曾家父子两代之谊而盲从了陈的这种表层文化比较的观念。同样,张若谷也没有认同他尊敬的留洋音乐学博士萧友梅,或正在德国留学的王光祈的观点。
萧友梅认为戏曲就等于西方歌剧,这种观念的传递,是否是他受留日背景,抑或是陈季同和严复、王国维的影响,都值得深究。但是,张若谷并不因为自己是后学和非专业而盲从于他,他当时也不可能读到萧友梅的博士论文,他也不通德文。《歌剧ABC》全书之中,也仅有引用萧著《普通乐学》(1912)对歌剧所作的一个名词解释而已:“歌剧以歌唱及表演为主体,内容包含民歌与音乐会各种歌曲,有宗教性质的歌剧,并且兼用赞美式歌曲”。很显然,萧友梅的这个定义,现在看来很是笼统又不得歌剧要领的,显然远不及张若谷所给出的有价值。
王光祈并没像张若谷那样,整天泡在剧院里,用当今的话说,王光祈欠缺大量真正的田野调查,而即便是其博士导师霍恩波斯特尔和萨克斯也不可能真正看得出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之间的巨大差异。1886年,清政府外交官陈季同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了《中国人的戏剧》一书,而王光祈来德国已是37 年之后了。陈、王二人历时性地抱有民族主义的爱国文化情怀,而在二人之前,清朝首位以音乐为业留日的曾志忞亦是如此。毋庸置疑的是,王光祈在运用音乐比较学论进化论的某些方面,相对这两代学人有所进步,其根深蒂固的“戏曲即歌剧观”,与陈季同、萧友梅等人的观念,是不自觉地走入了思想史的怪圈。
必须指出,从陈季同、曾志忞、萧友梅到王光祈这四位重要先学,一概未能对张若谷独立的歌剧观念构成负面影响。更有甚者,在做记者和写书的这段时间中,张若谷几乎每周都处于他的同事朋友——“民族主义乐派”(也有研究称“国民乐派”)倡导人傅彦长的耳濡目染之中。虽然同样也有爱国救亡之心,在接受歌剧作为音乐戏剧进化论上,张若谷却带有清醒的独立思想和批判意识。他扬弃了几乎所有的前辈、同代好友和名家所持的那些歌剧观念,力避把戏曲与歌剧混为一谈。
张若谷走出了这个“怪圈”,跳出了这种文化思维定式的漩涡。这对任何一个学者而言都绝非易事,年轻的张若谷之所以堪称一奇,本身就说明了他才是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人。概言之,他当时就认为,要发展歌剧,必须使这种戏剧进化为一种原创性音乐。认识上的结构性差异,显然使他能立足于歌剧综合美感的本体特性之中。
四、“叙情剧”的角度与“剧诗”说的先声
歌剧的生命本质,在于其为叙情剧。这是张若谷在阐明歌剧特殊性时着重指出的一点。张若谷为何用“叙情”,而偏不用“抒情”?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歌剧史中,仅有他一人这样说。现代汉语中,叙情与抒情,似乎并无二致。但他却力避“抒情”二字。笔者认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歌剧音乐与一般音乐的不同。
歌剧是用音乐展开并讲述故事的。音乐首先承担的是戏剧的任务,而绝非一般音乐的抒情。张若谷这样“咬文嚼字”,实际上就等于把话剧界“甲寅中兴”(1914 年)以来探索用“话剧加唱”以称“歌剧”的做法,与真正的歌剧创作划清了界限——歌剧音乐主要靠作曲,而且,这同样也与过去通过戏曲音乐衍化出“歌剧”的某些通行做法(如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划出了界位。在他看来,歌剧中的声乐和器乐,都是为了“叙情”(有生动感情的戏剧情节)而作。他从音乐能表达人类最深刻的情感这种特殊审美功能的视角,揭示出歌剧是以高于人类话语为表达方式的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普通戏剧所表现的,是只靠着文学言语表现出剧中的情绪”,认为歌剧直接用音乐向观众表达“生命心灵的深坎”。道理有两方面:首先,管弦乐加深了戏剧情绪的强度;其次,歌唱和舞蹈也使鉴赏者得到了共鸣的快感,因为歌唱作为表达人类情感有着其他任何艺术样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即歌剧以叙情为主,属“叙情剧”或“叙情戏曲”的范畴。他认为歌剧的命脉在于歌剧表演、剧作家和作曲家,但作曲家的地位更高:“假如要使优伶演唱出美妙的歌曲,一定需要有诗味丰富的词句,要创作出叙情诗脉的戏曲,一定须得音乐作曲的辅助”⑧同注①,第20 页。
尽管张若谷尽可能回避使用戏曲的概念判断来类比歌剧,但是为了能让中国读者通俗易懂地认识歌剧本质,他又不得不借用大家熟悉的“戏曲”作比喻,这实在是他当时写作时的一种窘迫。
直到1942 年,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以《今日之中国戏剧》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焦菊隐,前后连续在国内发表了《论新歌剧》和《旧剧新诂》。这两篇论文一并指出,歌剧、戏曲及“话剧加唱”完全不同,凡以文字为主体工具者为话剧,而以音乐为主体构成戏剧的,“用声音而不用文字来写剧情、写剧中人物个性、写戏剧环境的发展者,都是歌剧”;“歌剧是一篇用音乐写成的戏,用歌词来帮助发挥人物个性及情感,包括音乐、歌唱和宣诵(宣叙调,笔者注),借姿态色彩来演出,有时也参加些舞蹈,不过舞蹈不是必需的。歌剧通篇是音乐,即便是宣诵,也得跟着音乐,即使是没有歌词的地方,动作也得跟随着音乐的抒写而去解释音乐”;“歌剧纯粹以组成它的音乐作为存在的条件”。焦菊隐提出,要歌剧成立,得能同时满足三个必要前提:一是要有戏剧意识,二是戏剧叙述的机能要具备,三是音乐要有足够的力量。⑨焦菊隐《焦菊隐文集》第二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12 页。
尽管焦菊隐与张若谷的人生可能并没有交集,但焦菊隐后来的这些论点却极有力地支持了张若谷过去所持的看法。对比当年未曾出国,又没读过音乐或戏剧专业博士的张若谷,我们如今已能明显地感受到其过人之思。焦菊隐以一种穿越时空的逻辑,论述着过去曾被很多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混淆和误读的概念。张、焦二人的共同点是,都坚持认为歌剧是以原创性音乐为主体的戏剧形式,旧戏曲和改良后的戏曲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歌剧。笔者也曾指出,张若谷的这种学术观点在1928 年是极为罕见的,对于那些想从本土戏曲上嫁接西方歌剧的话剧家所主张的“国剧运动”来说,无疑是进行了彻底的否决。⑩满新颖《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歌剧遗存的历史问题》,《戏剧艺术》2009 年第4 期。甚至可以说,张若谷提前60 年就有了相对明确的“歌剧思维”,而当代作曲家金湘1987 年提出歌剧思维,可看作是对张若谷歌剧观念的历史回响。
《歌剧ABC》中最能表现张若谷对歌剧相关问题和层次研究深度的内容还有两点。(1)他对神剧(今译“清唱剧”)与歌剧的区分,体现出他对二者的内在区别看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较简单,在此就不必多叙。(2)他对于如何创作中国的歌剧剧本及作词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和思考,提出了要在学习瓦格纳戏剧诗歌化的同时,剧作家还要能以音乐作曲的积极意识表现叙情的旨趣,要注重其中的“人间味”和“叙情风”;针对辞句和韵律过雅,既不能过分地强调古雅,也不可过度追求“散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其所谓“人间味”,就是指作品要能“接地气”,做到雅俗共赏。这说明,他当时思考的就是歌剧的中国本土化发展问题。
为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张若谷密切关注“国剧运动”大讨论中的留美博士杨振声的《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⑪杨振声《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载余上沅编《国剧运动》,新月书店(上海)1927 年版,第115 页。从而使他透出自己对中国歌剧剧本文学创作审美导向的期待:“最好能采用近代文学的文语,或文学化的白话,反可以容易收得听众了悟的效果”。他的这种歌剧文学,既要具备现代性,又得兼顾诗性的观点,这表明了他对西方歌剧剧本文学有着比较深的认识。中国歌剧文学为表现自己的文化现代性身份,须坚守这个立足点。事实上,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在歌词写作上,也是自觉地与时代需要相适应的,完全符合张若谷的这种理念。
进而,他更强调作曲家拥有这种能力的重要意义:“人间只有不懂纯粹音乐的诗人,却很少有不解诗歌的音乐作曲家”。认为作曲要更为使用“集中力”,才能化出歌剧真正需要的音乐来。对于歌剧编剧和作词这两个并不一定同属一人创作的行当,张若谷也明确地提出了歌剧诗人(歌剧的剧诗作家)在音乐素养和时代感等素养上的重要性。
1943 年,因有感于当时秧歌剧创作不够专业、艺术性欠缺等问题,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于是提出了“剧诗”说:剧诗是与音乐结合而成,因此写戏就要充分重视诗自身的格式和节奏有音乐性在其中。⑫转引自朱颖辉《张庚的“剧诗”说》,《文艺研究》1984 第1 期。如果从历史的逻辑比较,上述张若谷对歌剧文学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业已成为张庚“剧诗”说的先声,这也就意味着,张若谷对于中国歌剧文学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问题,具有了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
结 语
在《歌剧ABC》这本仅有一百多页的一小开本歌剧入门级书中,张若谷分别从艺术形式进化论和音乐感情表达优势论两方面,阐述了歌剧的本性,力图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作历史的和逻辑的严整契合。张若谷的歌剧观,对人们正确理解歌剧作为本质的音乐戏剧很有帮助,从美学意义上基本廓清了歌剧与戏曲等戏剧形式的本质区别,这在20 世纪20 年代末的中国文艺学领域,尤其在歌剧美学领域,还几乎无人能比肩。
张若谷对歌剧的定义和各综合歌剧元素在歌剧中的个性与共性,一一做了详细论述,然后梳理出西方歌剧进化的历史脉络,最后再分别简要介绍了歌剧本事。从总体看,他的这部著作融知识和思想于一体,较完整地从理性和感性层面剖析了歌剧的本质。他所提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构成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及文化现代性的多层次上如何理解西方歌剧的诸多问题;同时,对歧路探索中的中国歌舞剧雏形,给予了密切关注和专业性的审视与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资源匮乏的时代,他所参考的中外戏剧文献达到30种之多,而英文书、日本人的相关歌剧论文论著亦有很多种,所涉及的歌剧作曲家近32 位,剧目上百部。这对于一个从20岁出头就敢于皓首穷经、不畏绠短汲深的青年评论家而言,不仅显示出他对歌剧的意往神驰,也表现出上下求索的才学和勇气,最终使《歌剧ABC》一举成为“民国”歌剧史上最为重要的大众理论读物。这实在值得当代歌剧爱好者深思。他那坚持独立探索,敏于发现,又敢于表达的精神气,也让我们对当时人的认识和世界视野有了更多的体会。因此,从感性素质和理性审美的实际需要出发,重新认识张若谷的成长和成就,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戏剧批评事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