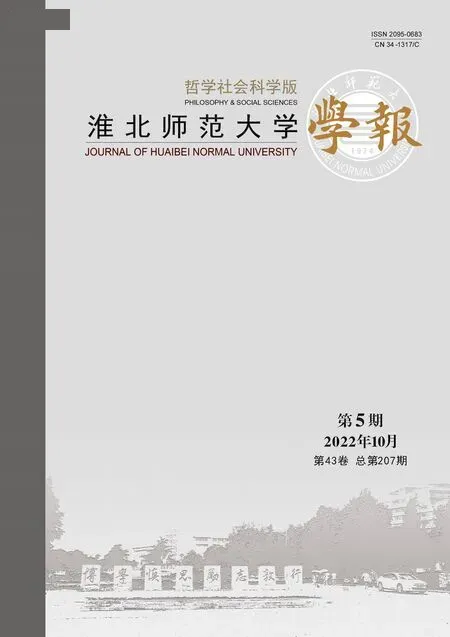祝尧“古赋”观念在清代的流变
2022-04-07王飞阳
王飞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古赋”一词早见江淹《学梁王菟园赋》,其序云:“或重古轻今者。仆曰:何为其然哉?无知音,则已矣。聊为古赋,以奋枚叔之制焉。”[1]338但江氏所说的“古赋”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并无太深的内涵。而在唐宋的赋学观念中,“古赋”是用以区别律赋,更多的是指一种赋类名称。直至元代祝尧《古赋辩体》问世,才对“古赋”作出系统性的阐述,构建了古赋多维尺度的理论内涵,对后世产生久远的影响,于此任竞泽、何诗海已有详论。①参看任竞泽:《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何诗海:《<古赋辩体>与明代辨体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明人对祝尧赋论的承袭和推崇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学赋者,必考于此,而后体制不谬”[2]620,而“唐无赋”的说法也是对祝尧“祖骚而宗汉”的间接化用。但《古赋辩体》之于清代“古赋观”的影响,尚未见学者予以发覆。关于清代“古赋观”,何易展认为其内涵十分复杂,一是包含时间上的“古”,二是包含了体例上的“散”,“古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赋文体”。[3]308-309孙福轩也提出“对于‘古体赋’的内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类分”[4]2。其实,清代“古赋”观念是在《古赋辩体》的基础上衍生的,并由此完善深化、拓展重塑,呈现古律并尊的整体趋向。梳理这一脉络,有益于加深对古赋的认识,并进一步体认古代赋论的本质及其价值。
一、时间、经义、体制:祝尧“古赋”体系的多维尺度
祝尧《古赋辩体》被称为“最具理论体系的文体学著作”[5],就赋学而言,祝氏论赋不仅系统全面,而且新见频出,其所谓“古赋”绝非简单的时间概念,或单纯的赋类名称,而是统摄时间、经义、体制多维尺度的理论内涵。祝氏“两汉体”序云:
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今故于此备论古今之体制,而发明扬子丽则、丽淫之旨,庶不失古赋之本义云。[6]143
这可以说是《古赋辩体》全书的纲领性宣言,直白地道出古赋应以多维尺度评判。以楚骚两汉
收稿日期:2022-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49)
作者简介:王飞阳(1991— ),男,安徽铜陵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为古,是时间尺度;备论古今赋体,是体制尺度;本诸丽则之旨,是经义尺度。其中时间尺度是根本性的,换言之祝尧所认为的古赋即楚骚汉赋,所谓“作赋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之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6]112。而体制尺度和经义尺度是辅助性的,是用以解释说明为何楚骚汉赋为古赋。
在论“三国六朝体”俳赋时,认为“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是因为“为俳者必拘于对之必的,为律者则必拘于律之必协”[6]266-267;在论“唐体”律赋时,认为“是以唐之一代,古赋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少异于律尔”[6]354-355;在论“宋体”文赋时,认为“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其有辩其失者”[6]418。凡此,皆是以体制尺度衡量古赋,也就是说祝尧认为古体异于俳体、律体、文体,楚骚汉赋之所以为古赋,是因为不拘骈对声律,亦不以文体为赋。除体制外,祝尧视楚骚汉赋为古赋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符合古诗之义,其云:
是以三百五篇之诗,二十五篇之骚,莫非发乎情者,为赋为比为兴而见于风雅颂之体,此情之形乎辞者,然其辞莫不具是理,为风为雅为颂而兼于赋比兴之义,此辞之合于理者。……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如《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眩矅,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6]140-142
这是以经义尺度衡量古赋,在祝尧看来古赋应归于讽谏,折以法度,应本诸美刺,合乎风雅颂之义,这无疑是班固“雅颂之亚”、扬雄“丽则之旨”的隔代响应。而且祝尧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情、辞、理三者的关系,认为古赋应“情形于辞而其意思高远,辞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长”[[6]29,凡合乎此才有古赋之义,否则“有辞无情,义亡体失”[6]267。虽然祝尧认为自三国迄于两宋,去古愈远,但其中仍有可取的赋作,如王粲《登楼》、陆机《叹逝》、潘岳《秋兴》、鲍照《芜城》、韩柳古体赋、苏辙《屈原庙赋》,而原因均在于合乎“六义之旨”。可以说,经义尺度是《古赋辩体》中的一条主线,较之体制尺度则更为关键。
祝尧统摄时间、经义、体制三大尺度,构建“古赋”的理论内涵,这是十分明显的。当然祝尧这么做,是有现实考量的。“近年选场以古赋取士,昔者无用,今则有用矣。……其意实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裁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庶几可以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云。”[7]1009可以说《古赋辩体》的宗旨即在于此,是为指导赋的创作,为举子树立应试模范,从而“以复古之体”。科场考古赋是一方面,而从另一面讲,祝尧宗“古赋”是因为在其看来骈律之赋丧失了赋的价值,所谓“雕虫道丧,颓波横流,光芒气焰,埋铲晦蚀,风俗不古,风骚不今……孰肯学古哉?”[6]354祝尧从某个程度上讲,是承接韩愈“复古”的旗帜,变宗“古文”为宗“古赋”,这才是“以复古之体”的根本途径。
虽然祝尧以楚骚汉赋为古,推尊古赋,但却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客观态度。如前所述,古赋之外并不是全不足观,就古赋来说,祝尧也认为有高下之别。如比较屈宋,而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审此,则宋赋已不如屈,而为词人之赋矣”[6]112;就汉之赋家,极推贾谊,“自原之后,作者继起,独贾生以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6]141。而就贾谊的作品,也是客观而论,“然《吊屈原赋》用比义,《鵩赋》全用赋体……若较之《吊屈》,于比义中发咏歌嗟叹之情,反复抑扬,殊觉有味”[6]145,并非一味推崇。这种客观的态度,也应是祝尧古赋理论的一部分,均为清人所借鉴,对清代的“古赋”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重力流管道中分水口流量越大,末端关阀引起的流速改变量越大,导致的水锤危害也最大。管道沿线5个分水口,分水流量见表1,其中 5#分水口桩号26+470处的分水流量最大,4#分水口桩号19+950处的分水流量第2大。
二、古律并尊、融律于古:清代“古赋”观念的重塑
诚然,“《古赋辩体》不但是赋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也是文体批评史上有卓越建树的著作”[8],其对明代的影响学者已有详述,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明代辨体批评的兴盛,同时在赋学认识上,明人亦受祝尧沾溉颇深。如吴讷几乎全部承袭,而徐师曾将赋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类,也是直接受其启发。而郎瑛盛赞《古赋辩体》“辨之精矣,予不赘焉”[9]314,许学夷也认为祝尧“其论甚确,当是赋家一善知识”[10]360,足见明人对祝尧赋学观点的认可。逮至清代,《古赋辩体》并未因时代久远而丧失影响力,相反愈演愈烈,或甚于从前。这于四库群臣的评价之中,最见一斑。
其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谓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6]24-25
因祝尧“言之最确”,故《古赋辩体》在清代十分盛行。这一方面体现在藏书情况,很多私人藏家都有收录,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另一方面,清人谈文论艺多借鉴《古赋辩体》,如陈鸿墀《全唐文纪事》、李调元《赋话》、孙梅《四六丛话》都频繁引用。梁章钜云祝尧“作《古赋辩体》,言之颇详”[11]499,这和四库群臣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和明人的态度非常接近。所以祝尧的古赋观念自然多被清人借鉴,如马积高先生所云:“至清代各家所作《赋话》,于辞赋源流,更多取资于此书。”[12]194-195当然清人在借鉴的同时也有重塑,表达出和祝尧不一样的看法。
从时间尺度来看,较之祝尧视楚骚汉赋为古,清人则有不同。清人所认为的古赋或以六朝为限,如程琰云“变古为律,自鲍照、江淹、吴均、沈约开其先,而庾子山为之枢纽”[13]40册10;或以唐代为界,商衍鎏云“及唐用诗赋取士,则用从前之体制者为古赋,而以应试之赋曰律赋”[14]287。无论哪种标准,较之祝尧以楚汉为古则范围更广。无疑,清人拓宽了古赋的外延。其实以唐为界,是因为至唐始有古律之名;而以六朝为限,则因为至六朝已有变律之实。由此可见,时间尺度往往夹缠着体制之分。
从体制尺度来看,清人则承袭祝尧,整体看法基本一致,即俳、律句式大幅出现,则古赋变矣。如来裕恂云“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体变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四声八韵,专事骈偶,其法愈密,其体愈变”[15]916。同样,清人也认为赋用文体亦为古赋之变。如侯心斋云“宋元之文赋,又律赋之变体,不可训也”[15]767。但较之祝尧,清人对体制的体认愈发全面精细。如孙濩孙看到了古赋用韵的不同,“古人用韵最宽……又古赋间有数行不用韵者”[13]29册14-16;汤稼堂对古赋句式有更具体的认识,“元人场屋更用古赋,罕有作隔句对者”[15]612;邱先德亦云“卢骆王杨每于俳体之中,错以七言诗句,与夫四六长联,谓之古赋,其去汉魏远矣”[13]58册30;徐昂则意识到古赋“平仄之配置不求尽调”[15]928。概言之,清人认为古赋的体制应不拘骈对,尤以隔句对为忌,不夹诗句,不用文体,用韵自由。
从经义尺度来看,清人亦以“古诗之义”衡量古赋。如鲁琢云“刘勰曰,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古赋之纲领也”[13]48册127。王之绩论赋“其体不一,而必以古为归”,其所谓“古”乃“必首律之以六义,如得风、雅、颂、赋、比、兴之意则为正,反是则为变”[15]876。凡此,皆是以经义衡量古赋,不合六义之旨即为古赋之变体。当然以经论赋,源自汉人,“赋者古诗之流”的论断可谓衣被赋家,非一代也。清人和祝尧,都是沿袭其说。但清人的转变之处在于颂扬意识愈发强烈,这于清人的赋选、赋作、赋论中随处可见,清人写赋或是论赋已没有那么强的讽谏欲望,因为皇权加强、政治施压,清代文人噤若寒蝉,惟有夸颂才符合时代形势。另一方面,也是出自谋身之阶的考量,清代以律赋取才,文人往往因一篇赋平步青云,自然对试赋政策进行宣扬,对浩大皇恩进行歌颂。
除以三大尺度衡量古赋外,祝尧的客观态度也被清人所发扬。虽然祝尧对具体赋家客观评断,但其赋论核心仍是推尊古赋,所谓“祖骚而宗汉”,认为古赋以下的俳赋、律赋、文赋都不足法,而清人对此实现了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古律并尊。于此,陆葇所言最为公正,兹录如下:
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也。律赋自元和、长庆而来,欲化密为疏,不觉其趋于薄;欲去华就实,不觉其入于俚。故韩苏诸公,皆由此获高第,而自以俳优鄙之。此人之为,非赋之咎也。扬子云《甘泉》《羽猎》自夸文似相如,而谓其追悔雕虫,乃后人假托之词耳。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古赋之有。[13]25册47-48
清人虽然古律并尊,但在律赋创作上却主张融律于古,这是超越的第二个方面。其中鲍桂星所云,最为客观。
夫赋有古有律,为古而不求之古,无以为法也;为律而不求之古,犹无以为法也。为古而过于高简,或矜炫奇奥,以自怡悦则可,以之应试颠矣。为律而不求之古,徒事取青妃白,弊且至于庞杂窒塞,其于律何有焉?[13]69册3
鲍氏所言,旨在树立古赋、律赋创作的准则,而这都需要“求之于古”。其所谓“古”并非以古为尊,而是以法为尊。过于古、过于律皆违背法则,不可用之应试。这种态度反映了“过犹不及”的中庸思维。中庸之道是儒家传统哲学,代表了一种适度的思辨智慧。其渗入到古代文论,亦屡见不鲜。蒋寅先生论述古代文论的独创性概念,就新故、生熟、生新阐发古代文论的中庸特色,认为这是一种认知方式,赋予文论丰富的意蕴和阐释空间。①参看蒋寅:《新故·生熟·生新——中国古代文论有关独创性的概念》,《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1期。而就赋论而言,鲍桂星的观念也体现了这个层面,古、律是赋体两端,越过“度”的界限,都会适得其反。这较之元明赋论一味求古,不得不说高明得多。
融律于古除了主张以法为尊,还推崇循律溯古。李云度论赋“汉魏六朝之古体,源也;唐宋及今之律体,流也”,而主张“当以循流溯源为得其序也”[13]128册3-6。任何文体都会有发展演变,但常见的是“源流代降”之说,即一代不如一代,如祝尧论赋所言“以至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6]263-264,因源胜于流,故多主张“握源而治”,即本诸古赋之旨,以古统律,究其本质还是尊古贬律。而循流溯源,反其道而行之,则表现为一种更客观的尊体意识,即古律并尊。可以说,古律并尊和融律于古,是清人论赋的整体趋向,而这一起构成了清代“古赋”观念的新特色。
由上可知,清人也是以时间、经义、体制多维尺度衡量古赋,而这是直接取法《古赋辩体》的理论体系。但不同祝尧的是,清人破除独尊古赋的局囿,主张古律并尊,“或又言唐后无能为赋者,果定论欤”[17]83,则打破了明人“唐无赋”的赋学偏见。而在具体创作上则提倡融律入古,以法为尊,循律溯古,从而在祝尧的基础上实现“古赋”观念的重塑。
三、考赋与作赋:古赋理论的现实考量与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赋论的主旋律,是围绕着考赋和作赋来构建的。早在汉代献赋之时,赋家就已关注如何作赋,如司马相如“赋心”“赋迹”之说,扬雄“读千赋而后晓赋”之论,虽然汉代赋论的主轴是以“经”论赋,但仍落实到具体创作之中,即赋家作赋要本诸美刺之旨,以达到“雅颂之亚”的效果。降至魏晋六朝,整体呈现“由赋用论向赋体论演进”[18]263,跳脱汉人单一的经学思维,关注赋体本身,赋论的重心更落实到作赋上,“征实”“体物”之说出现,刘勰《诠赋》则是指导作赋的系统论述。而到了唐代,以赋取士,考赋制度正式形成,从此赋论主要是围绕着“古律之争”进行,元代考古赋,清代考律赋,无论是考古赋还是考律赋,都是进身之阶,元清两代士人在考赋的层面上,面临的现实是相似的。
祝尧《古赋辩体》实为指导作赋的教科书,以应对考古赋的现实需要。清代虽不考古赋,但清人构建“古赋观”则是借古言律,是为了指导律赋创作,树立新规。在清人看来,“律赋一道在前代为程式之篇,本严声病,在今曰储馆课之用,尤其雅驯”[19]139-140,要突破唐律赋的局限,使律赋归于雅驯,则必然需要融律于古。于此王芑孙倡导“力宗汉魏,下取唐贤,其体既纯,斯文乃贵”[20]4,这是最为辩证的认识,反映了一种追求适度的思辨智慧。前人面对古律,要么极力崇古,要么过于崇律,只有清人尝试融合古律,而在具体创作上,主张取法诸家,“文成而法随”[21]12957,通变是宜。所以清人的“古赋”观念不再独尊古赋,而是古律并尊,这是清人超越祝尧和明人的根本所在。
如果进一步思考,祝尧之所以崇“古”,不只是因为“古赋所以可贵者,诚以本心之情有为,而发六义之体,随寓而形”[6]355,还在于祝尧认为“古”是一种价值判断,“古”代表着规范、理想,甚至是一种正统的观念。而清人则视“古”为一种程度判断,“古”并非等同于“好”,“古”变成了具有弹性的概念。所以清人才会消解“古、律”之别,才会有“古赋律赋,其揆则一”的认识,彰显一种可贵的思辨性。当然,清人古律并尊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古颂今,为本朝律赋之盛夸扬,展示“超唐轹宋”的气度,从而树立新的律赋准则。无疑,清人拓宽了律赋创作及古赋阐释的双重空间。
祝尧以时间、经义、体制三大尺度衡量古赋,赋予古赋理论内涵,清人在此基础上完善重塑,这启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古赋”的界定,古赋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概念,或是单纯的赋类名称。相反,“古赋”是一个相当通变的概念,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祝尧以楚汉为古,徐师曾以三国以上为古,清人或以唐以前为古,或以六朝以前为古,“古”的界限难以一定。而今天的学者对“古赋”的看法,依旧聚讼纷纭。孙福轩先生“不依于时代,不据于内容,凡是探讨骚体、文体、骈体的赋论都是属于古体赋史的范畴”[4]3;李曰刚先生以汉赋为古赋,“古赋者,后世论文家加于汉赋之徽号也”[22]88;学者陈守玺将古赋视作律赋以外的赋[23]。可见,重新思考“古赋”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界定“古赋”可实现赋体分类的融通。目前学界对赋体的分类,标准不定。其中分赋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是较为通行的说法。但如果将古赋界定为“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如孙福轩先生将骚赋、文赋、骈赋纳入古赋范畴,或是将律赋之外的赋全部纳入,那么是否消解掉骚赋、骈赋、文赋类别存在的意义?其实清人早有这样的看法,如林联桂云“古赋之体有三,一曰文赋体,一曰骚赋体,一曰骈赋体”[13]193册532-535,以古赋统摄骚赋、骈赋、文赋。侯心斋更是直言“赋有古律二题”[15]767,将骚赋纳入古赋,而将骈赋、文赋纳入律赋,换言之赋类只分古律,无所谓骚赋、骈赋、文赋。但如果保持骚赋、俳赋、文赋类别的存在意义,那么古赋就不能以唐为界,而是只能指代“汉赋”,用以区别骚赋、俳赋、文赋。虽然“古赋”是一个通变的概念,各个时代评断古赋的标准不一,但从广义上来说,“古赋”是指律赋之外的赋;而从狭义上来看,“古赋”则专指“汉赋”。惟此,才能实现赋体分类的融通。
其次,界定“古赋”可加深古代赋论的体认。“古赋”一词的诞生,从根本上来说是和科举考赋息息相关的。至迟在中唐,“古赋”就已被用来区分律赋。宋代考律赋,元代考古赋,清代复而考律赋,从功用上来讲“古赋”都是用来区分律赋的。而在诗文领域,也有“古诗”“律诗”之别,“古文”“骈文”之分。诗、文、赋的骈律化都是起于魏晋六朝,其中诗和赋都在中唐达到骈律化的顶峰,用以科举取士,律诗和律赋得以规范化,直至清代仍是应试程文。骈文盛于六朝,然中唐“古文运动”发难,施以散行之气,骈文发生变异。两宋推“古文”而广之,“古文”大盛,骈文走衰,逮及元明,遂坠低谷,迟至明末才又复兴。虽然诗、文、赋骈律化几乎同时,但发展历程却不尽同。律诗、律赋因科举的推行,故能获得士子的青睐。①明末骈文复兴,主因也出自科举需求。参看郭英德:《明末六朝文的流播与文风丕变》,《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祝尧的《古赋辩体》是为科举考赋树立准则,同样清人古律并尊也是为试赋提供津梁,虽然一考古赋、一考律赋,但本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换言之,古代赋论不是空谈泛论,而是从实际创作经验中提炼概括理论,并用这种理论指导创作。祝尧的古赋理论“祖骚而宗汉”,以古论古,相对宏观。而清代的“古赋”观念则注重落实到创作中,融律于古,所谓“古今流传,唐赋居半,虽尚声律而拘对偶,未免古赋少而律赋多。然朝廷以此抡才,虽韩柳大家尚屈其高迈之才,以俯就绳尺,要其寓驰骤于绳检之中,复骚汉于排律之外,纵横变化,气盛而高下皆宜,好古之儒所宜奉为不祧俎豆也”[13]58册29,疏解唐宋以来帖括之作拘于四六隔句对,文气板滞之病,赋予律赋新貌。稍览清人律赋之作,不乏多用散语、大赋句式,而且架构上多假设问对,令人眼前一亮,而这离不开清人“古赋观”的深化,即古律并尊,融律入古。认识这一点,对于当代赋学有着理论和创作的双重借鉴意义。
最后,界定“古赋”可打破赋学的古律壁垒。自汉迄清,赋体发展绵延千年,其中主流观念一直是崇古抑律,虽然清人整体呈现古律并尊的趋向,但也有“俳律类优”的说法,如符保森云“陆机遣词,渐开江左。自兹以降,古义浸湮。或习新声,或长艳体。下逮俳调,争涂金粉。……他如李唐试士,应制所传,只博一名,无关赋手。”[24]18296这种声音无疑是“唐无赋”说的嗣响,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研究汉赋者多嗤鄙唐赋,而钻研唐赋者又往往“矫枉过正”,许唐赋为最盛。二者均非客观。其实通过界定“古赋”,可知古律是赋体两端,彼此难分,没有律赋何谈古赋,没有古赋又焉有律赋?古律是赋体演变的内在规律,律是古之变,较之古为新,和诗一样,无须强加轩轾。“古,故也”[25]123,“故”的反面即“新”,无论新还是故,过度推崇都不好。所以清人古律并尊的态度,诚为难得,这警醒赋学研究的前提是客观公正,而非妄分高下。无论由源及流,还是循流溯源,关注的应该是赋体本身。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破赋学的古律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