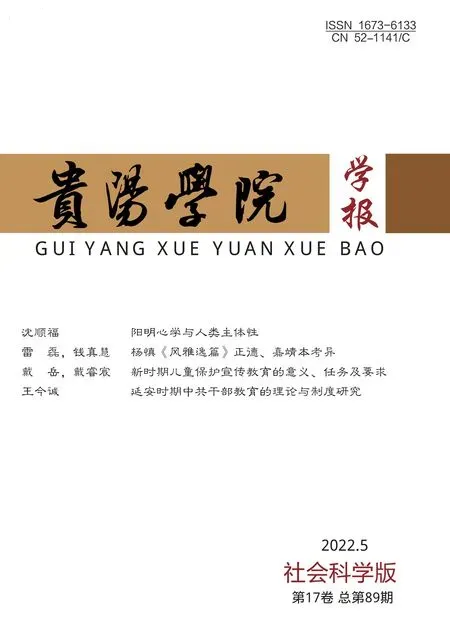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党支部与生产运动
2022-04-07张杰
张 杰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抗战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从1939 年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以实现自给自足为最终目标的生产自救运动。为了保证生产运动的有效进行,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介入群众的生产活动中。作为党在乡村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基层组织,农村党支部在推动生产运动“走深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支部的研究多是从党建的角度出发,对其加强自身建设的路径、特点以及经验启示进行分析和归纳,而对农村党支部与生产运动的关系则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将利用已刊档案、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资料,全面考察农村支部在边区生产运动中的具体作为,揭示二者“互相形塑”的关系,以期丰富现有的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党支部的认知。
一、边区生产运动的展开与农村党支部中心工作的确立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中共要在这样一个地瘠民贫的地方站稳脚跟,绝非易事。全面抗战初期,依靠着相对充足的外援,边区在财政上并不感到紧张。但自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明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意识到单靠外援终非长久之计,遂萌生“靠自己动手”的想法。1938 年12 月1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20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随即发表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的社论。经过前期酝酿,边区政府于1939 年2 月2 日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向边区各界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2月6 日至8 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及各县县长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制定了1939 年边区经济建设计划,边区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下,1939 年的生产热潮很高,原定全年开垦60 万亩荒地的计划,在该年的9 月份即告提前完成,并建立了难民工厂、农具工厂、制药厂、制革厂、造纸厂、肥皂厂、制鞋厂、铁器厂等小型工业[1]。但是,1939 年的生产运动主要局限在部队、机关、学校等“公家”领域,而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发动起来。
为了“造成更热烈的广泛的群众生产运动”[2],边区党委、政府在1940 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要实现广泛的组织动员,“应做到党、政、军、民、学各组织的一致动员,不让自己组织中有一个应参加生产的而不参加”[2]。经过大半年的发展,边区政府在该年9 月份检讨工作时发现边区的经济建设仍然“多为官办,而没有真正地发动民众来参加,一切问题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3]。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一条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河滨的封锁线,企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边区多地也出现了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内外环境的恶化要求边区的生产运动必须突破狭隘的“公家”领域,向更高层次迈进。为了找出化解财政经济困境的办法,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如朱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等人深入边区各地,开展实地调查,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4]。在此基础上,边区中央局于11 月12 日做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5]193,“这首先就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5]193。而“党的使边区经济能够自力更生、完全自给自足的计划,是只有依靠全边区二百万人民才能实现的,没有全边区二百万人民(主要是农民)的积极拥护和执行,不论什么开荒、植树、种棉、畜牧都不能实现”[5]494-495。那么,如何才能将边区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造成群众生产的热潮呢?在中共看来,支部是直接联系群众最基层的党组织;“党的一切策略路线、任务、决议、决定,都是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执行的”[6];而对于“经济建设”这个“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支部更加不能“置身事外”。“乡村支部与乡政府的任务是异常重大的,特别是乡村支部更要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保证党的决议实现”[5]495,“支部与乡政府执行党与政府关于经济建设决议的好坏,就决定边区经济建设的胜利或失败”[5]495。但要使农村支部担负起领导群众生产的任务,却并非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支部工作的干部,对于领导生产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7],认为“生产老百姓懂得,用不着咱们宣传”,“种地是老百姓的事,何必咱们操心”[7],于是,“不宣传、不解释、不研究,也不组织,任其自流”[7]。“另一个使农村支部忽视生产的原因,是一般地提出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这个不恰当的口号影响了农村支部领导生产的工作,影响到对干部、党员的政策。”[7]因为担心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所以“支部只注意了干部、党员在动员工作中的模范,按时的到会、交费,而没有注意到干部、党员在生产中的积极性”[7]。一些党员还因为终日辛勤耕作而不能经常参加支部会议,结果“受到嘲笑,责备以致开除”[7]。此外,边区的党员干部中间还普遍存在着轻视生产的错误观念,认为做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是光荣的,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影响下,农村支部在边区的生产运动中处于几乎“隐身”的状态。据1941 年延安、延川、靖边、甘泉、鄜县、志丹等县报送给西北局的材料显示:“经济建设工作在分区、县上抓得还紧,到区级以下都放松了,尤其到乡上力量就更弱了。”[8]
如何打破干部头脑中漠视、轻视生产工作的错误认识,并使农村支部成为群众生产的积极领导者?这一问题在1942年10 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下简称西北局高干会)上得到了解决。会议在讨论党今后在边区的中心任务时,确立了“生产第一”的原则,并对干部中间“轻视生产”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在会上的长篇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研究生产问题应成为每个在农村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9]。任弼时在会上也明确指出,“今后的农村支部与乡政府,都要以如何领导农村生产事业为它的中心工作”[10]297,“支部大会不要开得太多,不必要的可以不开,甚至一年只需要开四次支部大会,就是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征收公粮时)之前各举行一次,决定一些进行这些工作的好办法,或者还可以少开一些,平时可以利用时间,举行小组会,其内容也要很好地和农村生产事业、生产组织相结合”[10]298。高干会闭幕后,边区各县如绥德、清涧、吴堡、葭县等又相继召开了传达和学习高干会决议的干部会议,“会后最明显之表现,则为对目前发展生产任务之重视,布置春耕、开展纺织业、筹划植棉种树、开办合作社、修筑水利及总结检查减租交租工作,各县均积极推行中”[11]。在延属分区,“高干会‘生产第一’的思想贯彻到极大多数党政军民的干部党员中去,他们对生产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克服了某些干部对春耕领导的‘自发’论调”[12]。1943 年1 月25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领导生产应成为农村支部的首要职责》的社论,再次强调了高干会关于支部领导生产的决议。自此,领导生产好坏就成为判断支部工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在这个“指挥棒”下,支部的领导者和广大党员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领导群众生产上,而边区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亦由此徐徐展开。
二、农村支部在边区生产运动中的具体作为
1943 年2 月8 日,刚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因为善于领导群众发展生产而受到表彰的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支部怎样领导生产》的文章。王丕年根据延安县的经验将支部领导生产的工作分为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制订全乡的生产计划、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组织劳动力、改造二流子等五项,为边区农村支部领导群众生产提供了一套“工作指南”。各地农村支部围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地推动了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
(一)积极推动生产互助
西北局高干会后,生产成为边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把农业生产搞好,首先就要将边区农村的劳动力更好地组织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实行劳动互助。在边区农村中,变工、札工等劳动互助组织久已存在,“不过这种原来的民间组织,多半是自发的,限于亲朋邻舍的狭小圈子里,它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13]。而农村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这些传统的劳动互助组织“加以组织领导,普遍提倡,使它的作用更大,流行更广”[13]。
在组织生产互助时,支部首先是动员党员积极参加,并以此来带动和影响周围群众。如盐池县四区四乡支部在组织变工队时,一些群众不了解,不愿参加;该支部就动员党员先参加。党员田从魁先将自己家门兄弟3 人组织在一块变工,在他们的影响下,附近村庄的13 人也组织了起来;在支委各干事推动下,全乡组织了30 个组222 人参加变工,其中120 人组成长期变工队,全支部17个党员有15 人参加变工,并由7 个党员担任小组长[14]。子长县南区三乡支部的党员,除了2 位妇女、6 位有病的老汉、1 位小学校的伙夫、1 位长脚伕不能参加变札工外,其余一切党员全部参加了。“全体党员参加变札工的结果,推动了全乡172 个劳动力中有122 个劳动力参加了;在全部9 个札工、5 个变工队中,党员负责领导的就有8个札工、4 个变工。”[15]柳林区四乡支部是延安县农村支部与生产相结合的典范。该乡24 个党员中,除一个老汉、四个妇女及乡长外,其他18 个党员全部参加了变札工队,而且每个党员都“表现了大公无私、以身示范的作用”[16]。1943 年,安塞全县2122 名党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参加了变札工,并且由党员直接参加领导的变札工就占到全县变札工总数的45.7%[17]207。延川县参加变札工的2340人中,党员计有803 人,占了1/3 以上,其中领导札工及变工的党员又占其半数[18]。由此可见,在支部的积极推动下,边区农村的党员大都成为劳动互助的积极参加者,有的就是劳动互助的直接领导人;在他们的模范作用影响下,边区的劳动互助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1943 年时,全边区大约1/4 的劳动力被纳入劳动互助中,而到1944 年时,延属、陇东、关中、绥德(三边分区缺)4 个分区参加变工组织的劳动力占到总劳动力的51%[19]。
(二)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共历来看重“榜样的力量”。领导生产成为中心任务后,支部不仅要求每个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生产在前,影响普通群众,而且要求党员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西北局高干会后,是否积极参加生产成为衡量农村党员优秀与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在支部的推动和新标尺的“牵引”下,边区的农村党员表现出了极大的奉献精神,成为生产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吴旗县一区第三支部自确定以领导和帮助群众生产为中心任务后,支部委员均分工领导一个党的小组。通过党员分工推动农户生产,农村党员均能亲自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如某党员供给某家豌豆籽1 斗6 升,某党员借给某家草150斤、粮1 斗[20]。该县三区二乡支部书记申学川吃苦耐劳,对待工作不怕麻烦;在他的领导之下,很多党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员李英才想出了以党员家庭做模范去影响普通农户的办法,他把全家能劳动的两个哥哥、六个侄子、三个嫂嫂、六个侄媳,连同他自己的老婆等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家庭生产动员会议”,实行劳动分工,订出制度,按体力强弱各人轮流做饭、看娃娃、拦牲口、锄草,并在会议上宣布,秋后给每个妇女发毛巾1 条,袜子1 双,生产好的另加奖励[21]。其结果,三区二乡纷纷学习李英才的办法,动员全家生产,创造劳动家庭。党员申学旺在支部领导下,自动给贫苦农民调剂牛2 头、木犁上用的跑圈1 个、铧1 页;继申学旺而起的,有8 个党员自动调剂租牛2 头、借牛3 头、铧3 页、麦籽9 斗5升、豌豆3 升、燕麦9 升[21]。子长南区三乡支部为了真正使每个人有荒地开,有粮食吃,全乡321亩土地的调剂,都是经过党员解决的[15]。延川县清延区四乡张家湾荒地不多,故在接到乡政府布置下的开荒任务后,群众对完成任务信心不高;该乡支书李兴江便召集张家湾党小组的8 个党员开会,决定先由全体党员组成变工队开荒;结果在党小组的带动下,全村人民开荒120 亩,超过乡政府给他们的任务3 倍[22]。安塞四区三乡支部不仅动员党员努力生产,而且规定每个党员至少要联系三四户群众,经常进行教育督促,如汤家河党员贺某,他联系了8 家群众,经常进行宣传,早上起得很早,督促他们生产。像这样积极参加与领导生产的党员占全支部的44.2%,表现一般的占46.5%,不能起作用的只占9.3%[23]。合水县在开荒运作中出现了不少模范干部、党员。五区三乡支书王戕德自己开荒20 亩;三区五乡3 个支部委员和乡长4 人共开荒75 亩,其中支部书记王建基一人开荒40 亩;四区三乡支书李仲海开荒15亩。在这些党员和干部的影响下,“全体群众皆卷入了开荒热潮中,尤以六区一乡群众梁桂荣开荒60 亩的事实,更引起全县人民的注意”[24]。在执行开荒任务中,华池白马区四乡支部党员上山早,开得多,且全部参加了变工队,这样使全乡高涨起开荒热潮,结果全乡565 亩的荒地计划,完成了2057 亩,超过将近3/4[25]。“人无头不起,鸟无翼不飞”,农村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仅推动了边区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成为掀起群众生产热潮的关键所在。
(三)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
“二流子”是指农村中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他们自己不生产,并且说怪话,破坏别人的生产情绪,一般农民是痛恨他们的。”[26]但中共认为“二流子”与旧日的流氓已大不相同,“除了个别的坏蛋以外,毕竟不是铁石心肠,他们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而养成好吃懒做的,我们既然解决了土地问题,只要能够耐心地规劝他们好好生产,多打粮食,过好光景,是会有效验的”[27],而且“在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时,农民的劳动热忱是会大大地提高”[27]。基于上述认识,边区亦将改造二流子作为农村支部领导生产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宁县五区四乡支部在领导生产时对教育改造“二流子”颇为重视,支部委员作了具体的分工。如支书杜树玉负责领导袁生才,村主任张生邦负责领导乐生义;在改造“二流子”过程中,他们更多地采用了循循善诱和及时宣传的办法,并发动“二流子”与老户及干部订立生产竞赛,以提高他们的生产情绪。如袁生才和张月禄、乐生义和张生邦都订立了春耕生产竞赛,结果都完成了生产任务;杜树玉对袁生才的领导,还采取了不断谈话和检查工作的办法,在四月内共谈了18 次话,有时走到袁的家中去谈,有时把袁叫到家里,一边吃饭一变询问袁的生产情况;所以他对袁的影响很深,袁感动地说:“杜指导员真像我的父亲一样。”[28]志丹县一区一乡支部也是由5 个支干分工领导该乡的8 个“二流子”,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订出生产计划,动员他们参加变工队,并经常检查。组干韩纪成首先帮助高尚斌调剂锄1 把,支书姬海潮借给刘纪有牛草100 多斤,宣干苗有帮他们租了1 条牛。在支干和党员的帮助下,8 个“二流子”有5 个彻底转变,参加了变工队;刘纪有转变后当了变工队的工头,孟采堂转变后拴了1 头牛与他哥哥合伙种了20 多垧地,有个“二流子”在转变后买了1头牛,今年开了7 垧荒地[29]。安塞六区二乡支部动员群众帮助“二流子”解决了生产中的缺粮问题,“但给二流子调剂的,并没有全部交给他们,集中起来存在乡政府,规定他们按月向乡政府领取一定的粮。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他们胡吃浪用,甚至偷卖掉;二则可以用陆续借粮的方式使他们坚持下去,直至参加变工锄草”[30]。志丹三区二乡支部在春耕期间用帮助解决困难、说服教育、督促变工的办法,改造了4 个“二流子”,使他们都参加了生产。二流子的改造更加激励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许多人都说:‘二流子生产得美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赶过了。’”[31]
(四)组织生产竞赛
开展生产竞赛是中共用于提高群众劳动热情,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式。1943 年2 月24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向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发起挑战,进行生产竞赛。吴满有不仅宣布应战,而且提议把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军队和群众中去。以此为契机,朱德于3 月1 日电令边区所有部队响应这一生产大竞赛;西北局组织部亦于3 日下发了“关于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给边区各地农村支部的一封信”,号召农村支部行动起来,组织群众进行生产竞赛,并将领导生产竞赛运动好不好作为评判支部工作好坏的测量标尺。边区有领导、有组织、群众性的生产竞赛运动由此发端。
自西北局发出开展生产竞赛的指示后,志丹县积极响应。在该县一区支部的组织下,生产竞赛先在示范村中热烈展开。“在一区示范村村民会议上,除以村庄为单位的三个生产小组,由组长提出竞赛外,并展开个人间的竞赛;全村居民互相比赛者十对,举行三角比赛者三起。”[32]延川城市区六乡支部则是组织赵家沟、张家湾两个村开展生产竞赛。在春耕下种时,两村提出了具体的竞赛条件,如种得好、种得早、选籽好、锄得多又好、不荒一亩地、每垧土地上肥8~10 袋、收的成绩好等。他们为了便利起见,将两村的29 个劳力都组成变工队,从春耕开始到秋收,进行生产突击。由于两村竞赛的热忱与领导抓得紧,过去对生产不热忱的人都被竞赛带动起来了。竞赛的结果,赵家沟原本计划植棉45 亩,实际完成60 亩,共收到熟花1000 斤,可得洋125 万元[33]。延川永胜区六乡在支部书记樊古银的动员下与延安川口区六乡支部发起生产竞赛,为增加粮食产量,该乡群众提出了掏崖、溜畔和蓄肥、增肥的口号,在3 个月中全乡耕地面积增加了2600 亩[34]。再如甘泉县三区五乡模范支书顾应红向四区四乡劳动英雄及模范支书甄士英发起生产挑战。甄士英在接到顾应红的挑战书后,即以提高了的条件向他应战,并向全乡各支部书记挑战。在县委工作团的帮助下,甄士英将全村100%的男女劳动力和畜力组织了起来,进而又将全乡90%的劳动力也组织起来:“男耕女织,小孩老人也都各有任务……全乡充满蓬勃气象。”[35]再如子长县,在各支部的组织下,“此间各乡生产竞赛已广泛展开”[36];五乡杜家窑向三乡张家山提出竞赛,要做到全村不留一块荒地、深耕、多锄草,在春耕期间组织变工,不使一牛闲下,不浪费一个人工,夏耘秋收时全村札工。边区各地农村支部通过组织乡与乡、村与村、个人与个人间的生产竞赛,极大地刺激了群众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劳动效率,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运动的开展。
将领导生产作为农村支部的中心任务,凸显出中共组织理念的变化,“那就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一”[37]92。而这样的安排亦收到了明显效果。1945 年,西北局组织部在提及边区农村支部的作用时,特别指出“农村支部在生产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里有党员,那里支部工作搞得好,那里的生产也就同样搞得好”[17]206。根据西北局组织部的研究,凡是在“领导生产”这项工作上表现出色的支部都具备以下几个优良特点:一是有领导核心,支书、支干在党员中有信仰,能把公事提到第一位;二是支部会议经常讨论生产,并且能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支部能注意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坏毛病的党员,则抓得更紧;四是支部对群众的领导方式好,能按照每个党员的特长和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来分配每一党员的工作[17]208。正是凭借农村支部深入细致的工作,生产工作才突破了狭窄的公家领域,真正成为覆盖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三、生产运动对支部的影响
西北局高干会后,农村支部与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已成大势所趋。毋庸置疑,支部的深度参与极大地改变了生产运动的走向和规模。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支部在“改变”生产运动的同时,亦经历了一个“被改变”的过程,二者在紧密结合中形成了互相影响、互相形塑的关系。
(一)生产运动的开展重塑了农村支部与群众的关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边区的征粮、扩军等动员工作中,农村支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的工作制度没有建立,“有些支部干部以行政面目出现,去做动员工作,影响到党与群众的正常关系”[38]。在看到党的人出头向他们要人、要钱、要粮草后,有些群众就说,“尔个不比过去了,共产党变了”[39]。在日常工作中,不少农村党员简单地认为“比群众出得多”就是起模范作用,并没有切实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如耕牛、农具、粮食的互助,农忙时的札工变工等;再加上在农村支部中,“还有少数的干部、党员,包庇、耍私情看面子,甚至贪污腐化,成了党霸,干出种种脱离群众的事情”[39]。所有这些都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群众对支部的不满。因此,重塑农村支部与群众的关系,把支部变成党在农村中的坚强堡垒,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重塑支部与群众的关系?生活在农民群众中的农村支部,“若果对农民的生活十分关心,经常领导群众搞生产,改善生活,那么,这种支部也就一定是和群众连接得很紧,受到群众的爱戴、在群众中生了根的”[7]。而生产运动的开展恰恰为改善支部与群众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后,农村支部开始积极介入群众的生产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从而打破了隔阂,拉近了距离。如靖边长城区二乡支部,以前也是和一般的支部一样,只有动员工作搞得很起劲,对于领导群众生产就不大注意,和群众关系很差。但是,自从支部工作转变到领导群众修水地、搞水漫地,并且有了成绩以后,支部的面貌马上改变,群众兴奋地说:“共产党这样诚心给咱们办事,咱们还有什么说的!”[7]延安川口区六乡支部在春耕期间,全支部的每个党员都分工领导本村的几家农户,“在制订农户计划时,帮助他们提出计划,在他们发生困难了的时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小组会上每次都要检查每个党员的生产情形和他们所领导农户的生产情形”[40]。在六乡有不少这样好的小组和好的党员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和政府依靠他们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了解了群众的要求和情绪,完成了每年的生产任务。志丹县一区一乡支部自1943年5 月工作开始转变,“主要的表现在亲自动手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因此使支部团结了广大群众”[29]。“支部能够持续地领导群众的生产,它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41]支部在领导生产中提高了威信,团结了群众,也改造了自身(一些坏的、不参加互助或逃避工作的都清洗了),真正成为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
(二)生产运动的开展实现了党员教育的转向
党员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基层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边区党对农村党员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开办流动训练班的形式进行的。教员是从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党员中抽调的,教材则是《党员须知》《党员课本》等,内容主要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这些流动训练班对于农村党员思想意识的改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主要的缺点“在于严重的教条主义的毛病”[42]。《党员须知》和《党员课本》等教材内容,“与各地方党的工作,党员思想意识中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联系”[42],而且对于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农村党员来说,理解这些教材中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这种形式的训练班大都收效不大,“党员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枯燥无味,教员也觉得教不出什么名堂”[17]。为此,1942 年10 月30 日,《解放日报》还专门刊发了一篇题为《党员教育应有彻底转变》的社论。该文观点鲜明地指出“脱离了党员实际生活,只是背诵条文的教育,引不起党员的兴趣,对于他们思想改造与工作改进,不能起应有的作用,是没有什么奇怪的”[42]。因此,党员教育必须要与党员实际生活相联系,其目的是要改造农村党员头脑中的太平观念、自私自利的思想和封建迷信的意识。
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后,生产成为边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而这也正是农村党员实际生活中最感兴趣的问题。于是乎,党员教育围绕生产来进行就成为一件“公私两便”的事情。这既是生产运动向纵深推进的逻辑结果,也是党员教育突破瓶颈的必然选择。据西北局组织部的调查,1942年高干会后,党员教育中那种照本宣读《党员须知》《党员课本》的情况“比较少了”[17],多数地方都能联系党员日常工作及本地实际问题开展党员教育。如镇原庙渠区在开展党员教育时,授课内容都是像教育党员努力生产、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制订农家计划、进行反对“二流子”的斗争等与农村党员生活有密切联系的问题[43]。吴旗县农村党员流动训练班用实际发生的事例来进行教育,收效颇大。如四区一乡支书在夏季住训后,即在本乡召开流训班,当时组织变工问题正发生障碍,流训班就抓紧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解决了实际存在的许多分歧;同时表现在实际行动上,推动了全乡的变工[44]。一区二乡在上一年春耕时,有许多群众缺喂牛草,流训班在提出讨论春耕中存在的困难时,有3 个党员愿抽出120 斤草去帮助群众。二区一乡党员苏士明有存粮,当夏季有个别农户缺粮吃时,他说,他宁愿把粮倒进羊圈也不借出,因此引起群众的不满。后来提到小组会上讨论,苏士明的思想得到了提高,“认识了一个党员不仅自己有吃有穿,还要帮助大家发展才对”[44]。吴旗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子岐根据吴旗进行流训班和小组会的经验,认为采用实际例子进行教育“是改造党员思想的最好方法,而收效的大小,又以联系实际的紧密为测量标准”[44]。以生产运动的开展为契机,边区党员教育实现了“实践化”的转向,也充分体现了党在党员教育工作中的灵活性。
四、结语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兴起的生产运动最初只是局限在部队、机关、学校等“公家”领域;为了掀起群众生产的热潮,实现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的目标,边区赋予农村支部领导生产的重任。以发展生产为契机,中共找到了群众与党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找到了一条支部建设的新路径。农村支部的积极介入使原本处于“自流状态”的群众生产驶入了有组织、有规划的航道,从而扩充了生产运动的范围。在领导生产的过程中,农村支部重塑了与群众的关系,真正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党员教育也纠正了空疏、教条的倾向,实现了“实践化”的转向。但对于共产主义政党而言,加强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当以生产为中心的政治动员成为支部工作的全部内容时,如何使党员了解党的主张与行动纲领、遵守组织纪律就成为支部组织生活缺少的内容[37]92。如何使农村支部建立起自己的日常工作,仍然是中共在组织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