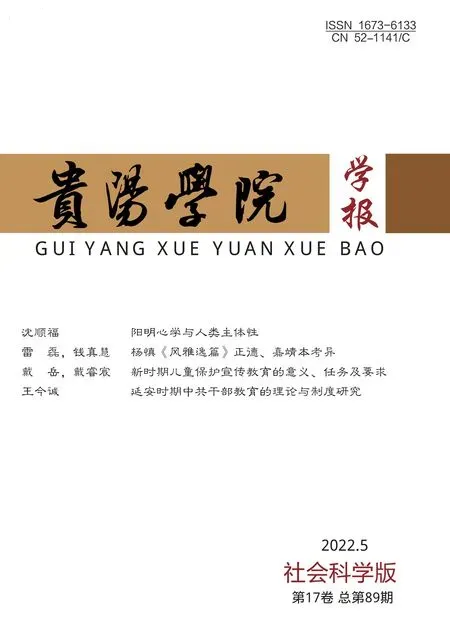论焦循对“以意逆志”的诠释及其当代意义
2022-04-07刘继平李长绪
刘继平,李长绪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以意逆志”向来被视为孟子读《诗》的方法,后世学者进一步将其理解为一种读书乃至经学研究的经典诠释方法。在这种思想拓展下,“以意逆志”获得了普遍认可,即凡是谈到读书法,或经典诠释法,人们都会引其进行解说。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以意逆志”中的“意”字,比较契合个人在读书或学术研究中的自我体会或“己之意”这类的意思。而在焦循这里,对“以意逆志”的解读则与他人不同,其体现出了乾嘉汉学的理解视角,而且解读的方法也十分具有汉学特点。
一、诠释“以意逆志”的二重向度
在考察焦循对“以意逆志”的诠释之前,首先考察三位学者对“意”字的解读,以及在这种解读下“意”字暗含的诠释学内涵。汉代赵歧说:“‘意’,学者之心意也。”[1]740南宋朱熹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2]当代语言学家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译“以意逆志”为“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3]。以上三人都将“意”视为“己之意”。从经典诠释法的视角看,这种“己之意”确保了以人为核心诠释主体在理解与阐释文本时的主体性意义。这可以说明,在诠释活动中,主体可将自己具有历史经验的个人体会,或与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话语,融入进对古代文本的理解与阐释中。所以,“己之意”则带有历史性解释的特点。
但是,“以意逆志”依然具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意”可以不解读为“己之意”,而可以解读为文本之意,或指《孟子》文本语境中的《诗》之意。从《孟子》文本看,孟子讲“以意逆志”是为了回答咸丘蒙的问题①咸丘蒙问:“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万章上》)。咸丘蒙之诗,引自《诗经·小雅·北山》。,他说: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的误解,指出读《诗》不可只凭借单纯的文、辞去理解,而应当“以意逆志”。孟子意指咸丘蒙没有理解到《北山》一诗的原义,而是断章取义。此处的“原义”是针对《北山》一诗的语境与其作者的心境讲的,即作者作诗是为了指责周王役使不均,而无法赡养父母,故而作此诗发泄牢骚。由此,“以意逆志”的“意”可以理解为,通过作诗者之“志”而指涉的整体诗文之“意”,即“意”是对《诗》讲的,并非对读《诗》的人讲的。这种解读就与“己之意”有实质不同。上述援引赵、朱、杨的解读,是为引出焦循对“以意逆志”的诠释。因为,焦循的解读同样是将“意”解为诗文文本之“意”,而非“己之意”之义,这与赵、朱、杨的解读完全不同,同时其解读方式更是大相径庭。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大量引用训诂材料,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到“以意逆志”的文本中,将此话语真正地当作历史性的书面文字材料来看待与理解。这一点,在他对“不以文害辞”中“文”字的解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这也是其诠释“以意逆志”的开端。他认为:“《说文·文部》云:‘文,错画也’。《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1]740按此,“文”是凭借着取象、作画的方式而塑造的象形图像,故“画”就是“文”。又说:“宣公十五年《左传》云:‘故文反正为乏’。《国语·晋语》云:‘夫文虫皿为蛊’。”[1]740引《左传》,指从文字造型看,“正”字的小篆体反过来就是“乏”字的小篆体。引《国语》,指“蛊”字的构造方式是通过表形的“文”“虫”而形成。以上皆从形训的角度说明文字本身具有图像属性。最后,焦循讲,“是文即字也”[1]740,认为这种具有图像属性的“文”便是“字”。从现代视野看,这种“文”“字”是一种由“画”而形成的,可以用来表形、表意的语言表象符号②王宁先生认为:“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参见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第35 页。,这种对“文”“字”的语言认知观念,在焦循随后的字词的辨析中体现得同样明显。
焦循对“文”的语言学解读,并非只局限于此字上,也就是,包括“以意逆志”在内的整本《孟子》,对他来讲都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解读《孟子》必然不能离开具有语言符号特点的文字本身。在这种思维下,其诠释“以意逆志”就展现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风貌。而随后他对于“意”字的解读,也消解掉了将其视为“己之意”的含义,反而更重视“意”字本身作为纯粹的语言文字的意义。总之,这种语言学解释思路乃是一种文本性解释的方法,所关注的只聚集在文本中的语言文字上。但是,在焦循的诠释中,也不乏有类似于“己之意”的历史性解释。故而,焦循对“以意逆志”的诠释体现出区别于他人的诠释特点,即其展现出了诠释的二重向度,一是具有训诂学、语言学色彩的文本性解释,二是具有历史时间色彩的历史性解释。
二、文本性解释:诠释中的语言学路径
文本性解释,是对焦循从语言学进路解释“以意逆志”的说明。在解释中,焦循以词义单位为基准,首先援引《段注》对“词”“辞”“意”三字进行诠解,他说:
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1]740
《段注》区分了“词”“意”“言”三者,以及三者与字音、义、形的关系。它以“意内而言外”释“词”,指其是字形、字音、字义的结合体。需要说明的是,“文”“字”是取象造字而成的符号,“意”既然为“文字之义”,那便是造字之初的构意。当构意与所造文字结合时,“意”就是文字本身的语义内涵,它代表文字本义。对“意”讲,它是“词”意义结构中的一部分。“意”与“言”共同构成“词”的意义内容,也正由于“意”的参与,才使得“词”具有语义内涵。
接下来,是对“词”与“辞”的辨析:
《段注》释“辞”为“篇章”义,又讲“篇章”之“辞”具有“文”的特点。这样,“辞”便是一种语言符号的集合体,它并不具有由“意”带来的语义内涵。接着,又认为“词”同样属于文字,但它有“意”的加持,有语义内涵,而且“词”也可以构成“辞”。由此可知,《段注》区分了两种“辞”,一是语言符号集合体之“辞”,二是既有语言符号又有语义内涵之“辞”,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即后者有“词”赋予的语义内涵,并且,后者也是由语言符号领域进入语义领域的象征,它为意义的被理解开辟了途径。故而,《段注》又引孔子“言以足志”之说,说明能够通达“志”的只有“言”,而“言”就是“词”①《段注》讲:“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词之谓也;‘文以足言’,辞之谓也”。参见焦循:《孟子正义》,刘建臻点校,广陵书社,2016,第740 页。。
按焦循引《段注》之意,是为了阐明“词”与“辞”的不同,以及说明通“志”的只有“词”,并非“辞”。所以,将作为无语义内容的“文”“辞”视为直接通“志”的渠道是不合理的,这才是孟子讲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义。焦循此论,核心之处在于阐明“意”字之含义。他在这里揭示出一个隐喻,指“以意逆志”是通过具有语义内涵的“词”而“逆志”,人们只有阅读文本,了解语言文字之语义,进而才可以领会整体篇章之文义,这才能够通达作者心志。反之,如果“以‘辞’逆志”,通达的只是一堆语言符号,何谈有通达心志之说?
当我们反观焦循的诠释理路时,他依靠语言学知识对“词”“辞”“意”的解释,实则将“以意逆志”这一命题变为自己语言学解释方法的代名词,使诠释活动不能偏离语言文字之路。这样,“以意逆志”作为被解释的命题,其本身就是解释的方法。他对“以意逆志”进行文本性解释的同时,也赋予其文本性解释的属性,即“以意逆志”这一命题代表了文本性解释本身。
三、历史性解释:诠释中的历史性原则
如果按照赵、朱、杨的解读,“意”为自己心中的私意,那么解释者的主体意志则能在“以意逆志”的命题中体现出来。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视角看,这种具有主体意志的“意”,则为经学诠释活动提供了进行历史理解的基础,增强了理解的条件和阐释上的多样性,即诠释者可将自己具有历史时间意义的“前理解”,融入进“共时性”的诠释活动中,进而构成“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现象。但是在焦循这里,“以意逆志”不具有通过“己之意”进行诠释的可能,即其不具有诠释者主体意志的参与。
焦循并非没有注意到通过主体意志进行历史解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诠释活动依从文本文字、语义固然重要,但是诠释的历史性存在于文本解释之前。在《孟子正义》中,他援引顾镇在《虞东学诗·以意逆志说》中的论述,用以说明自己对“以意逆志”的另一层看法: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诏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日谓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故必论世知人,而后以意逆志之说可用之。[1]740
按其论述,《孟子》“以意逆志”之论应与“知人论世”之说系联。只有“知人论世”,融入历史性解释,“以意逆志”才可用,这才能通达作者之“志”。焦循援引此句,是为“以意逆志”提供历史理解与阐释的主体性基础,指出诠释者主体意志之所在,弥补自己诠解“以意逆志”的不足。这种用以突出主体性的历史性解释思维,是其“性灵”思想的体现,强调的是用自己的主体意志契合古圣贤的心志[4],“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5]246。在焦循这里,只有凭借“知人论世”,“己之性灵”才可以贯通“古圣之性灵”,使“吾之意有所措”,做到“以意逆志”,进而实现对文本语义的理解、阐释。这种方式既保证了历史性解释的自觉性,使诠释不离主体性,又能够依从文本性解释的规范意义,以杜绝像咸丘蒙那样,在文本解释中脱离文本原意,随意揣摩,断章取义。当然,焦循对“知人论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
四、“知人论世”的诠释学义蕴
从以上焦循对“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关系的安置看,历史性解释是文本性解释的前提,二者是一种线性逻辑关系。但是,通过细究文本性解释的规范意义便可发现其作用,即其自身可以使诠释活动不离文本内容,以及遵从文本内容的解释应走语言学路径。由此,两种解释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就演变为圆环式的解释循环逻辑关系。在循环关系中,二者均能够发挥出各自的不同作用,即诠释者凭借主观意志进行阐释的同时,文本性解释能够克服掉主观阐释的任意性。这一点在焦循对“知人论世”的解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按《孟子》,“知人论世”是指要想与古人进行沟通、交流,就要“颂其诗,读其书”,如还不了解他们,那就进一步了解古人的历史境遇,即“论其世”①孟子说:“以友天下之善事为未足,又尚论故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按焦循的解读,认为只有读书才是知晓古人历史境遇的途径②焦循说:“故必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惟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见焦循:《孟子正义》,刘建臻点校,广陵书社,2016,第838 页。)。这种思路其实将“知人论世”限定在文本性解释中了。那么,为什么只有读书才能够做到“知人论世”呢?这体现在焦循对“颂”“读”二字的字义分析上。他首先引用《周礼·春官·大师注》,认为“颂”与“诵”同义,“颂之言诵也”,即“颂其诗”就是“诵其诗”。其次,又援引《段注》,认为:
讽,诵也。诵,讽也。读,籀书也。《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1]838-839
“讽”“诵”二字互训,故同义。“讽”字,“倍文曰讽”,“讽”则代表着不“读”文本语义,而只“讽”其“文”。“诵”,既有“讽”义,同时又指出声吟诵。总之,“讽”“诵”二字具有相同的特点,二者只限于看文本文字与发声朗诵,不具有体会语义的作用。对“读”,《段注》“读,籀书也”。焦循援引《段注》说明“读”义:
《竹部》:“籀,读书也。”《鄘风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盖籀、抽古通用。《史记》:“紬史记石屋金匮之书。”字亦作“紬”,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1]839
“籀”“读”二字互训,都指“读书”。而“读”又有“抽”义。《段注》引《史记》,释“抽”为“抽绎其义蕴”,指“读书”可获取文本中的语义内容。至此可发现“颂”“读”的差异,前者是对文、辞讲的,后者是对文本语义讲的。只有通过“读”,才能够获取到文本语义内涵。随后,《段注》从事理上解释“读”,援引司马迁《史记》中的语句,如“余读高祖侯功臣”“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太史公读秦、楚之际”等等,皆用以说明“读”具有着获取语义内涵的作用,指司马迁通过阅读文本中古人事迹,进而有所体会,并加以评价总结,故《段注》说:“(太史公)皆谓䌷其事以作《表》。”[1]839
焦循之意,是想阐明两种读书现象:一是只关注“文”而不得语义;二是读书可以深入到文本语义中,获取其中内涵。“讽诵止得其文词,读乃得其义蕴。”[1]839在他看来,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之法,是能达到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论其世”“知其人”。而之所以达不到,“不知其人”,是因为没有深入到文本语义中,对文本内容没有深入了解。如果真能通晓文本语义,便能像司马迁一样“绎其事以作《表》”,对历史人物、故事进行主观分析、判断,并构绎成文章。
焦循对“知人论世”的解读,与对“以意逆志”的解读如出一辙,皆注重文本性解释的必要。尽管“知人论世”具有着历史性解释的功能,以及内在的“性灵”思想,但其依然要基于文本性解释,依然要立足于语言文字和文本语义,或者说,解经要立足于经典。这种思维,是对经典文本自身存在意义的彰显。在焦循这里,经典文本本身的意义,通过语言学路径而被揭示,其自身建立在语言方法论之上。而且,从焦循的诠释理路中可以看出,语言学路径并非指向对语言现象的语法式分析,因为这无关于义理阐发,而是直接通过语义学进路阐释义理。从语义学层面进入到经典诠释,这依然是“以意逆志”的思路。这样,解释方法与对象都指向了经典文本本身,都在强调经典本身在诠释活动中的意义。
在这种格外强调经典文本的思想指导下,“知人论世”本身所具有的可进行历史解释的“性灵”主体意志,已然陷入到与文本性解释的循环中。那么,在这种思维下,诠释活动中的主体意志在何种意义上还可以独立彰显?焦循认为,历史性解释的主体意志是从对“时间”的认同中获得:“古人各生一时,则其言各有所当。惟论其世,乃不执泥于言语,亦不鄙弃其言,斯为能上友古人。孟子学孔子之时,得尧、舜通变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论古之法也。”[1]839-840诠释者存在于时间视域中。“论其世”便是承认“时间”带给人们的一切,对不同时间段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有其各自存在的历史时间视域。焦循正是发现这一点,故才认为要认识古人,唯有“论其世”。在理解古人时,不能拘泥于文本中的片面言语,也不能摒弃这些言语,要因时、因人、因历史环境而识人,这才可以在文本性解释中体现主体意志的存在,将自己的个人体会融入于对语义的理解中。承认时间的存在,是使历史性解释寻获解释灵活性与开放性的重要基础,也是阐发文本语义的重要客观条件。时间是使文本性解释与历史性解释贯通在一起的依据,也是诠释者进行理解与阐释的条件,以及经典文本自身得以存在的本体论根基。
五、“经典文本本位”的当代意义
从焦循对“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诠释看,尽管其论述中有着注重“性灵”主体性的思想,但在诠释活动中,他始终依从语言学、语义学路径与经典文本内容。这皆体现出其经学诠释思想中的一种重要理念,即经典文本本位。这种理念固然与乾嘉汉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但它对我们当下的学术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赵、朱、杨三人将“以意逆志”的“意”视为“己之意”,这种阐发在经典诠释的历史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它足以说明诠释活动可融入历史经验。周光庆先生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认为“意”应该是解释者心中“先在的‘意’”。他将“以意逆志”称之为“心理解释”,其核心在于“以心揆心”[6]。按此说,诠释者通过自己的内心去理解对象并进行阐释,这其中就含有心理活动的过程,此过程也是使自身精神世界与周围历史视域、生活经验、理解对象进行“视域融合”的过程。具体到哲学研究中,诠释经典无非运用经典中的文化资源来解读生活世界。经典只是哲学思辨古典思想的中介[7],它只是诠释者手中的工具。这种经典诠释的思维模式,与赵、朱、杨三人的思路有相同性,都在强调诠释活动中以诠释者为本的主体性地位,并将其放置于本体论的高度。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探索,在注重对诠释者主体性建构的同时,也应该突出经典文本的主体性意义,这在焦循这里足以说明。从焦循对“以意逆志”的诠释看,解经应当立足经典,从经典中来。经典文本制约着诠释者对经典的诠释,使诠释者需要走语言学、语义学路径,这反而突出文本性解释的重要地位,即作为被理解、阐释的文本,亦有其自身存在的主体价值与精神。
经典文本有其内在意义,包括其中记录的人物、事件,承载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等等。解读经典是对这些意义不断揭示与阐释的活动,这呈现为不同的解经者对经典之义有着区别于他人的阐释。在经典诠释的历史长河中,解经者之间关于阐释经义问题的对话,便是诠释的历史事件。经典诠释的历史,就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这种事件包含有解经者之间的对话活动,同时也包含解经群体运用语言工具与经典本身不断交流的活动。在交流中,语言学、语义学路径则将我们的关注点转向经典文本本身。
当解经群体通过“己之意”,并运用语言工具与经典文本进行交流时,文本本位的主体性意义必然会凸显,就是说,解经群体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会受到文本自身的牵引与制约,这样会缩小解经群体的历史视域。因为,他们最终所得出的结果是从文本中获取的。保罗·利柯认为:“语言经验只能起媒介的作用,因为对话双方都在所谈事物面前削弱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对话就是由所谈事物来引导的。”[8]当把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治经通“道”的方法论时,经典文本便是引导解经群体的诠释活动主体,其自身的主体性精神才得以彰显。在这种情境下,解经群体中的个人主体意志运用,则由经典文本赋予。经典文本自身中的意义,将引导着解经群体通过语言学、语义学路径,与他们自身的主体意志结合,使他们在诠释活动中能够展现,活化经典的思维与技能。而经典文本的这种行动,皆体现在对解经群体的制约与规范中。
焦循将“意”字释为“文字之义”,将“颂其诗”“读其书”视为不能摒弃的“论古”途径,都在体现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经典文本,对诠释活动的引导作用与对解经群体主体意志的宰制现象。同时,经典文本本位的主体性地位,也体现在焦循所赋予的义理内涵中,即他认为“经”本身就有着可变的本体论意义,“经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未有不变通而能久者。……故变而后不失常,权而后经正”[5]176-177。“常”“久”“变”是“经”的本体论内涵,也是其可被解经群体进行不断阐释的形而上基础。由此,焦循给后人以启发,即对经典文本本位的诠释学研究,应当属于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研究中的一个方向。中国古代经典有其内在的本体论义蕴,而不能够只关注到以解经者为核心的诠释学问题,或者说,不能够只对“己之意”进行研究与发挥,而忽略经典文本和文本中的语言文字所应有的本体论意义。当然,这种启发是由语言学方法而引申的。方法论在作为方法的同时,其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与思维范式,本体论研究应建立在这种方法论之上[9]。经典文本本位的研究,应囊括与之相应的语言学、语义学,即对训诂学进行学科交叉研究。这是乾嘉汉学“由训诂通义理”哲学方法的当代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