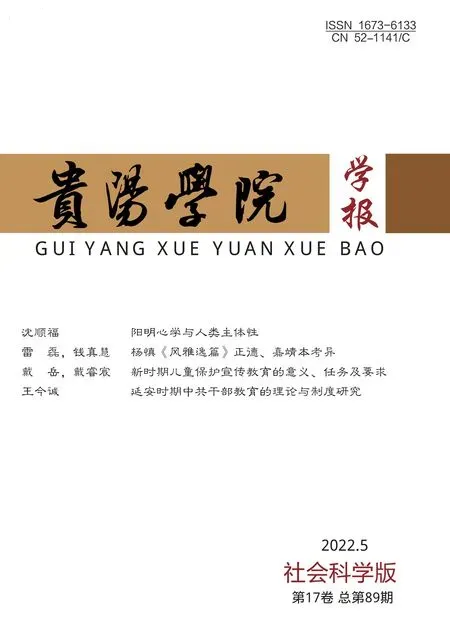唐君毅以“感通”释“仁”的心学意蕴
2022-04-07张倩
张 倩
(华南理工大学 哲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1)
现代新儒学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一本性的根基所在①由唐君毅执笔,发表于1958 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提出:“今人如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则决不容许任何人视中国文化,为只重外在的现实的人与人之关系之调整,而无内在之精神生活,及宗教性、形上性的超越感情之说。而当知在此心性学下,人之外在的行为,实无不为依据,亦兼成就人内在的精神生活,亦无不兼为上达天德,而赞天地之化育者。此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唐君毅等:《中国文化与世界》,载《唐君毅全集》(第九卷),九州出版社,2016,第21 页)。为了说明心性之学的统贯意义,唐君毅把心性之学的起点追溯到孔子之“仁”,认为“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1]。为说明这一问题,唐君毅以“感通”为核心,整合中国哲学史上对“仁”的多种解读。“感通”即是《周易·系辞上》中用来表达“易”变化无穷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2]的内容。唐君毅用“感通”来说明人的心灵活动的历程和规模,以此说明“仁”的动态活动,兼及“仁”的工夫论意义,从心学的立场,说明了中国人文传统的特质在于“伦理的人文主义”,彰显中国人对于主体的独特理解模式。
一、对“仁”上溯性解释的心学基调
“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一贯性的内核。唐君毅在梳理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认为“仁”对诸德的统贯,是孔子开启的义理结构。他说:“以仁为一德,与忠信礼敬智勇等相对,自古有之,而以仁统贯诸德,则自孔子始。以仁与他德相对,则以爱说仁,最源远流长……孔子而后,以爱言仁者,其旨亦最切近易见。”[3]39具体来说,“以爱言仁,要在即人之爱人之情,以及于施仁爱之事,言求仁之道。以爱言仁,其旨自切近易见;爱人之效,亦至为广远”[3]39。在唐君毅看来,“爱”最能体现“仁”的含义;在追问仁爱的根原、仁爱的施行、仁爱的效验中,后世儒学接续“仁”的传统,不断丰富和发展“仁”的内容,扩展“仁”的范围。
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唐君毅把孔子以后“仁”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四次阶段性变化。第一次是董仲舒“谓人之仁原于天之仁,亦言人当法天以爱人……更言以仁治人,以义正我,则重仁义与阴阳、人我之不同的客观关系”[3]39-40,其具体内容是“自仁之宇宙根原,天与人、人与人之客观关系言仁”,不同于“先秦以前诸子之直接即人之爱以说人之仁”[3]40。第二次变化,体现在宋明儒学中,“宋明儒大皆以人果能知得此仁之内在之本原在心,为心之性,亦即同时知其本原之亦在天”[3]40。第三次变化则在清代儒学,表现为“除承程朱陆王之学者之外,大约趣向在就仁之表现于人之事功上者言仁,而近乎宋之永康永嘉学派之论”[3]40-41。第四次变化,则发生在民国以后。此时的学者们讨论孔子仁论时,“恒趣向在对孔子之仁之概念,求一解说”[3]41。这种寻求概念界定的方式,是“对中国思想史中之孔子思想有一客观的理解,与昔之学者之言仁者,皆兼意在教人体仁而行仁者,其态度皆有不同”[3]41。唐君毅对“仁”论阶段性变化的归纳,把中国哲学史上论“仁”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研究方法清晰地呈现出来,成为他对“仁”进行上溯性研究的哲学史基础。
从内容研究上来分析,唐君毅论孔子之“仁”时,区分了孔子回答学生之问的内容和未明确记载问答对象的内容。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仁”,分别是孔子对樊迟问仁和颜渊问仁的回答①《论语·颜渊》记载着相关的对话。一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二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爱人”和“克己复礼”在孔子以前就被作为“仁”的内容来讨论。唐君毅非常重视《论语》中未明确记载问答对象的部分。他认为:“《论语》所记孔子之言仁之语,更有未明载其为答弟子之问者。此或为孔子答诸弟子之问仁时所说之语,或孔子之无问而自说之语。吾观孔子言仁之语,则以此一类之言,其义最为深远,而亦大皆唯是就人之内在之心志,及仁者之表见于外之气象态度,与其内心之境界而说。”[3]65最终,唐君毅概括了孔子言仁的主旨,认为“孔子之言仁,本在言为仁由己。仁者之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而己之生命与他人生命相感通,乃一‘次第由内以及于外,而未尝离其一己之仁之流行’之一历程”[3]156,把孔子言仁的核心和深意,归纳为“人内在心志”,最初并没有外在的表现。这也区别于以“爱人”和“克己复礼”来讨论仁,是孔子仁论不同于春秋时代仁论的内容。
就中国文化史而言,唐君毅认为孔子继承并转化了周代的人文思想,提出自己的仁论。他说,“孔子教人以仁,亦即教人直接法天之使四时行百物生之德,而使人皆有同于王者同于天之德。此乃孔子之由继往而下开万世之真精神所在”[4]34。从人皆具有“同于天之德”,并以此为教人之起点来进行审视,唐君毅判定宋明理学最贴近孔子的思想。他说:“唯宋明理学之精神,为能由清明之智之极,觉内心之仁义礼智之理,以复见天地之心;而教人由智上觉悟,致知涵养并进之工夫,以希贤希圣,而以讲学教天下人皆有此觉悟,此实同于孔子之使王官之学布于民间。然其所不同者,在孔子仍是先有意于政治,且孔子是以一人为天下之木铎;而宋明理学家之精神,则几全用于教化,而以一群人,共负起复兴学术、作育人才之大业也。”[4]49
具体而言,唐君毅认为明道《识仁篇》中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5]16的说法,最合孔子之意。唐君毅把明道这种思路,概括为“天人不二无间,然天人亦自是二名。此见天地之用即我之用”[6]109,表现于“明道之善观万物之自得,天地之生意,以成其乐”[6]109。在这里,唐君毅把“浑然与物同体”首先理解为在人与物的感通中不断呈现的历程,是从存在论和生成论的角度进行的解释。进而,唐君毅还指出,此“浑然与物同体”之亲近心境,只能由人与物相接触的活动、生活来“体会”。[7]41-42这种“体会”,发生在自己与他人生命相感通的历程中。
唐君毅非常认可明道“由疾痛相感说”的说法,认为其“最为亲切。此乃顺孟子之恻隐之心之意说仁,亦顺孔子以生命之感通之意说仁”[6]104。唐君毅就明道“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5]15的说明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这段话旨在说明“吾人能于所感知之天地万物,皆不只向外以视为客观之所对,而反之于身,以使之真实化、内在化于吾人之生命心灵中,则天地万物之生成,即我之生成,天地万物之化育,即我之化育,天地万物之生几洋溢,即我之生几洋溢。”[6]108在以“感通”论仁的思路下,学者之工夫,“要在于此己与人物气不相贯不相感处,随处使一己之气与之相感通,而随处见此仁所贯注之体,于吾人之生命心灵之中。此即明道言仁之体之本旨。”[6]105在这一思路下,“仁”一方面根源于“心”,是心之发动处,另一方面关联于他人与物,通过“气”的流行而具体展开。如何在气化流行中保持心的主宰义,便可以延伸到工夫论的讨论之中。
在传统心学中,王阳明在《大学问》中也有“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8]的说法,影响颇大。冯友兰解释说:“这并不是说王守仁抄程颢,这只是说有那么一个客观的道理,二人对于这个道理都有所见。程颢是道学中心学的开创者,王守仁是心学的完成者,他们所见到这个道理,是心学的一贯的中心思想。不过,程颢没有把这个中心思想和《大学》的三纲领结合起来。王守仁这样做了,这就使这个中心思想更加有了一个在经典上的理论根据。”[9]唐君毅把“与物同体”的内容直接上溯到孔子是在宋明心学的起点处和完成处进行的进一步整合。把宋明心学中“仁”的实在论、生成论、工夫论、境界论整合在一起,并上溯到孔子思想之中,以说明“中国思想之所重,在言人性人事人文,而人性人事人文之本,毕竟在于人心”[7]59的结论,从而确立“心”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体地位,在人文世界的展开中把握“心”的功用。
在唐君毅的思路中,心灵最初的存在状态就是“在一无我与非我之分别之境中,以我之生命存在与非我之生命存在同情共感”[10]134。这种“同情共感”是“人之生命心灵中之原始性情”,是“心灵自超出其限制与封闭”,“以成此感通之善” 的基础和动力。为了说明如何随处体认个体与人、物的贯通,唐君毅援引了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说法,来说明“仁”的历程,感通的过程、工夫内在其中。
具体而言,“仁”的历程的第一步是“志于道”“志于仁”,这是“要在吾人一己之向往于与他人或天下之感通,而有对人之爱,与求天下有道之志”[3]100。第二步则是“于志道之外,求实有据于德,以依仁而行道”[3]100。依仁行道的过程,即是一个修德的过程,“修德之本在恕,由恕以有忠信,而极于对人之礼敬”[3]100。修德的过程中,除了顺着恕忠信礼敬而成德之外,还要“由人之辨别于道与非道之间,德与不德之间,能不惑于非道与不德,而后成之德”[3]100,这需要“智”来成就。“智”成就人的不惑,能够“兼通于知人、知外,与知己、知内之二面”[3]100,是修德的另外一层内容。而“仁”的最高层次,在于“知天命”,这也是仁的工夫的最后一步,是“仁”与“智”的统一。“知天命,则见仁者之生命与天命或天之感通,亦仁者之智之极”[3]101。通观整个修德过程,个体在经历了修己、安人之后,又回到了仁者之内在的感通上,与天命合一。
用“感通”解释“仁”,把“感通”的根据和动力追溯到“心”,体现了唐君毅“仁”论的心学基调。通过对“仁”贯通天人的德性内涵和工夫修养的解释,唐君毅把心学的基点上溯到孔子思想。孔子的“仁”论,又是对周代人文思想的继承。经过唐君毅的一系列上溯性解释,心性之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性和贯通性便确立起来。
二、以“感通”确立仁道的规模
以“感通”为动力的行为,可以是积极辅助他人的行为,也可以只是包容的态度和同情的心境。唐君毅指出:“依儒家义,人最初对人之仁,可不表现为有所事之积极之爱,而只表现为浑然与人无间隔之温纯朴厚,或恻隐不忍之心情。……在此本能中,已直觉有他人之自我或精神之存在。”[11]407这种说明,强调了“仁”最初的状态,并其内在的、自发的生长倾向和趋势。个体面对现实境遇而有的心灵感受和现实行为,都是感通内容;感通的活动历程和范围,即是仁道的实现和规模。
围绕着个体、他人、天道相贯通的感通活动,唐君毅区分个体内部的仁义礼智、个体对他人的仁义礼智,并从仁义礼智的流行中,透视中国天道、天命思想。唐君毅说:“此感通即兼具一己之生命心灵之‘前后之度向’中之感通,人我生命心灵之‘内外之度向’中之感通,及人与天命鬼神之‘上下之度向’中之感通。”[3]9其中,“一己之生命之内在的感通,见一内在之深度;己与人之生命之通达,则见一横面的感通之广度;而己之生命之上达于天,则见一纵面的感通之高度”[3]70。仁道中“对己”的内容,体现在“志于道”之中,即实现心之所向者皆为仁,是人对己的根本要求。仁道中“对人”的内容中,最接近人的日用常行者,则在于事功和爱人。仁道中“对天命”的内容,则通过形上追问和礼乐祭祀来涵养。对己、对人、对天命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即是中国心性之学的整体内容。
首先,唐君毅以“感通”说明事功的心性论意义。他说:“孔子言仁之义,其最切近易解,而在义理之层面上最低者,为即人之事功,而连于仁与其所关联之德而言者。于此说求仁之道,则求仁虽不同于求有事功,然求仁者必志于道,亦志在事功,而事功亦当以爱人之德为本。”[3]45“功业”是人们在现实生活总最容易把握的“仁”,亦可由“功业”来说明仁道的整体。唐君毅说:“人亦必先有成功业之志,然后能乐见他人之功业之成,合于其志之所向而称之,亦乐见人之才艺之足以成功业而美之,乃可暂不问其是否皆依于其人内心之仁德。此方为仁之至也。”[3]46人内心真正认同和追求的理想,是认同并欣赏他人的依据,也是人与人互相配合而成就事功的基础。从最外在的事功中追溯到人之“志”,进而说明从“志”到“功业”的展开,从“仁”的最切近之处来向内、向上贯通仁道的整体规模,成为唐君毅说明仁道的主要内容。
进而,唐君毅以“感通”说明仁、义、礼、智的流行架构,从人如何实现自身内部的感通、如何安顿人与人之间关系、成就事功的角度,申论了仁道的规模。从人与万物的“同情共感”中区分出人自身,“要肯定人之独立自主性,正应从人之可不属于自然系统,亦可不属于神之系统,而孤悬于天地间,以面对虚无处开始去认取”[12]53。在这一“孤悬天地间”和“面向虚无处”的体认,是人只面对人的自身的阶段,仁义礼智都是以自身为对象的活动,进而才有对于他人的“仁义礼智”。在唐君毅看来,“仁”是“自己之求成就自己”,“义”是“自己裁制自己,为另一自己留地位”,“礼”是“自己对将来自己之活动之尊重”,“智”是“自己之保清明理性,以判断自己”[11]406。在此过程中,人形成好善恶恶的道德原则,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形成“浑然与人同体又直觉他人”的道德主体意识。这也是一个对于人与我的分别逐渐清晰的过程。
人对自然万物的“同情共感”,经过了人对于自己的“仁义礼智”所确立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之后,再次面对他人与天地万物,便会形成更加真实的“亲切感”和“同情共感”,成为“仁”不断外化的基点。随着自身与他者差别的逐渐凸显,以“同情共感”之仁为基础的义、礼、智便随之产生,超越自己的局限来欣赏、成就他人。其中,“义”主要指“人之承认人我之别、人我之分际分位,即表现于人无事时皆有之毋欲害人毋欲穿窬之一种自然的自制。此种自制,乃原于吾人之原始的浑然与人无间隔之仁心”[11]409,通过限制自己的私意来承认他人,没有主观上的偏斜。“礼”则是“原始之辞让”,是“一种在接触他人自我或精神时之一种自他人所赐或人与我可共享之足欲之物超拔,而‘以我之自我或精神,托载他人之精神或自我自身’之一种意识”[11]410,是对他人的真实认可,而自居辅助地位的表现。“智”是“原始之道德上之是非之心,乃依原始之辞让之心而起。是非之心所进于辞让之心者,在此中人不仅有自尊其道德自我,尊人之道德自我之意识;且有对于‘违于人与我之道德自我之实际行为’之否定,及‘顺于人与我之道德自我之实际行为’之肯定”[11]412,真正肯定自己与他人的共生、共存、共享。仁、义、礼、智在对己与对人之间连续生起,说明了人的道德活动的连续性,无一刻停止,指向未来的自己和他人,共同成就一个天人物我共生共存的社会。
从工夫论的层面看,唐君毅区分对己、对人的“仁义礼智”,是对阳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进一步说明,强调“仁”在向外推扩。这建立在唐君毅对传统心学的弊端有清醒认知的基础上,即尽心知性立命的心性工夫,虽然有简易、高明之处,但容易流于内倾、空疏,陷于一己的道德意识而难以超越。他说:“吾人亦当知人之只恃此内心之工夫,亦有工夫难就处。收摄过紧而离外务,亦足致此灵觉之自陷于其虚静之中,以成一高等之自己沉没;而由其外以养其内之工夫,亦不可忽。”[10]156唐君毅区分内在的德性架构与人与人之间的德性架构的差异,以进一步明确:只有在人与人的真实交往中,人才能真正把握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联,进而实现人文化成的文化意义。
最后,唐君毅还以“感通”为线索,回应了“孝悌”与“仁”的关系。从“感通”的角度,更容易说明“仁”超越血缘和家庭限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人之仁心仁性,初原无局限其表现于家庭中人之意义,而原为遍覆一切人者”[11]67,是一个对天地“生生不息”之德的体验和践行。从人与家人的感通,到人与陌生人的感通与欣赏,是以家庭生活为基础,逐步向社会生活过渡的结果。打破血缘壁垒,从更加整体的角度说明“生生不息”的连贯性与动态性,扩大“感通”的范围,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和生活土壤。
唐君毅一方面指出“孝”在陶养“对人”感通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关注“孝”对于“仁”的遮蔽。他说:“孝弟者人之生命与父母兄弟生命之感通,即人之生命与他人之生命之感通之始也。”[3]47通过孝悌来涵养人与人的情义,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唐君毅坚信“人之情义必先在一定之个人与个人之伦理关系中,互相反映,以成恩义,然后此情义得其养。既得其养,而至于深挚笃厚,然后可言普施博爱”[10]139。“孝”作为情感的起点,具有坚实的生命基调。但在传统思想中,以家人之爱为基础的“仁”,难以产生对于陌生人的“爱”。唐君毅承认墨家对“孝”和“爱有差等”的批评,认为:“中国先秦之儒家之言孝弟,因表面上有自血统关系上言之嫌,故来墨家之责难。墨家谓儒家单自血统关系上言仁爱,必至对无血统关系之人即无仁。其说实是。”[11]67-68如何破除这种遮蔽,是现代新儒学发展中必须要回应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扩充生命的厚度和心灵的广度,产生对他人的亲切感,保持心灵的感通能力,是唐君毅给出的思路。
三、以“感通”说明中国人文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源远流长,以《周易·贲卦·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经典概括。“人文”与“天文”相对照、相贯通式的“天人合一”,表达出天人相通、天人相类的理念,具有非常多维的解释空间。唐君毅乃至现代新儒学的基本解释思路是,将“天”视为一个价值性范畴,将“人”视为道德性存在,人的道德性即是“天命”所赋。通过人的个人修养、对外在事物的认知、社会文化活动的陶养来实现“天命”与“自命”合一,是人文世界的理想形态。唐君毅把中国的人文主义概括为“伦理的人文主义”[13],追求的是天人、物我、群己的动态平衡。“伦理的人文主义”的实现,既需要道德理性的纵向贯通,也需要伦理生活、认知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横向拓展。全面的“感通”如何实现,是说明这种理想的人文主义如何实现的核心问题。
唐君毅认为,人面对自身时的“人内在的感通”是“心之生”的结果,会形成的最初级的道德意识,体现人最初之“自命”;这种“自命”中,又包含着“天命”的贯注。他说:“吾人须知此心之生,可表现为主宰此身之行为,亦可只表现为心之自超越于其已成之自己,而更有所自命之事。当此自命为一依普遍之道德理想而有之自命时,由此理想之可伸展至无穷,即可见此自命之可开拓至无穷,亦可见得此自命之有一无穷之原泉,如自此原泉而流出,以由隐而显。为此自命之泉原者,即天命,而此自命,即为此天命之所贯注”[14]64。
“心”与天道的贯通,是一个通过体认来确认的内容,包含着主体生命的直觉和情感。唐君毅用“人皆可由其心之依道德上之普遍理想而自命,而有其心之生、心之性之表现时,当下得一亲切之体证,便不同于先客观的说”[14]64来概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思维模式。这也奠定了中国人文活动的基调,把人的自我成长的能力和潜质,作为道德最坚实的基础,并强调其自然而然的性质。当面对他人与外物时,“仁”作为道德的起点,且是对自己的“仁义礼智”的综合,也就成为人类文化生活的起点和动力。这也正如有论者指出:“就承天地之生(性)与命而言,人天然地禀赋了道德的潜能。甚至在董仲舒的表述中,这是人之为人的道德使命。就人与万物的区别而言,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安善循理之行,使人成为超拔于万物之上的独特存在,得以组织起一种文明的生活”。[15]
首先,唐君毅延续着《周易》中“人文化成”的思路,提出“我们所谓人文,乃应取中国古代所谓人文化成之本义”[16]6;在先秦儒学中,荀子思想最能体现“人文化成”之义。“荀子之学自谓承孔子,而恒将孔子与周公并称,盖特有取于周之人文,故不同于孟子之承孔子而恒称尧舜之始创人伦之道者。”[3]340其中,“人文”是内容,“化”是过程,“成”是结果。“人文化成”即是用“礼乐”对民众生活的价值引导和提升,使自然世界成为人文世界,人的道德情感、伦理生活、社会历史和谐共生。
在唐君毅看来,人文主义思想除了有人生思想,重人与自然物之辨以外,还需要“承认人之主体性、整全性,及承认个人与社会人群及历史文化生命之通感性,或进至承认人之自本自根性”[12]31-32。他重视“人内在的感通”,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强调。此外,唐君毅还认为,“人文之世界,在人之自然生命与其心所知之其他自然物之间,亦在己与人间,同时为通贯古今,而自有其历史者”[3]342。“感通”既是天地生生不已的过程,也是心灵活动的过程。“感通”是自然与人文、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历史的贯通。
唐君毅专门结合《周易》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说明。他说:“在无思无为之世界中之天地万物,与此《易》之为书及吾人之心,即皆同在一寂然不动之境。然当卦爻既定,则《易》之为书显出其彖象之辞,亦显出其辞所象之天地万物中之若干类之物,与物与物所结成之若干之事;而我即可由此若干之物象、事象以定吉凶,而知我之若干进退行止之道,亦降至于有若干之思与为之境。是即可称为《易》之为书之‘感而遂通’,亦我心之‘感而遂通’。此中同时即有原为我心所虚涵虚载之天地万物之全体中之若干之事物,自‘寂然不动’之境出现,而亦‘感而遂通’。”[14]117在唐君毅看来,易学系统用卦、爻、象、辞来说明自然事物与现象,并判定吉凶祸福,无时无刻不包含着人对自身的理解和把握。天地万物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与心灵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同一的,心灵的活动也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也显示了唐君毅哲学的易学基础。
接下来,唐君毅认为,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观念来看天、人、物、我,可以实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贯通。从“感通”中看天人物我,“即见一切天地万物,皆由寂而感,由无形而有形,由形而上,而形而下。即见一切形而下之有为,而可思者,皆如自一无思无为之世界中流出,而生而成。知此,即可以入于《易传》之形上学之门矣。然此形而上学之门,则正为可由人将此《易》之为书作卜筮之用时,再反省此书之能由‘寂然’而‘感通’,人心之能由‘寂然’而‘感通’,与天地万物之能由‘寂然’而‘感通’,而可直下契悟得者也”[14]117。对于“感通”的契悟,即是对宇宙从“无”中生“有”的过程的体悟,亦是对宇宙、人心由“寂”而“动”的反思,是对“道”的活动历程的把握。唐君毅通过对“感通”活动的描述,说明心与境(物)的互相敞开,用现代哲学的思路和表达阐发中国传统心学的核心内容。
就“心”的本性而言,“心”活动的范围可直至“天下”;就“心”的实践而言,“心”的作用范围局限在具体生活之中。因而,唐君毅非常强调具体生活对于人心之仁的现实影响。他说:“儒者之仁心,虽无不爱,而足涵四海万民而无遗,然此心之落实,则只在于当前之我与人相感应之具体生活。”[7]75“心”之发动必指向于“物”,在感物的过程中,“心”一直保持着的主体性和理想性,与物互动,保持能动性。这也就是唐君毅所指出的,“此德性心,在其自悦自安,而无间充达之历程中,乃永不能化为对象者”[7]76。
在“感通”活动中,心、性、理的一体性也呈现出来。唐君毅指出:“自理之有一定内容上看,即明似与心有所不同。盖心之与物感通,既变动不居,此心之自身,即如只为一能觉,而无一定内容者。此能觉之感物,既感此,而又能舍此,以更感他,即见其虚灵而不昧;而心之自身,唯是一虚灵之明觉,便无一定之内容;其内容,皆当是此心之与物感通,而有所发用时,所表现之性理上言者。”[6]255-256宇宙本体之生生不已,根本上是一种广大、自由的创造原则,人直下承担这种创造原则,日新己德,保证宇宙之“生生不已”能够不间断,是真正的与天地合流的大德,心、性、理根本上通而为一。
最后,唐君毅通过中西人文思想的比较,说明以“感通”理解个人、理解个体与他人关系的长处。他认为,“孔、孟虽尊个人,然其尊个人即尊个人之能及一切人,而通于一切人之仁性仁心”[4]40,个体的存在始终要在个体、他人、天道相贯通来确证,在天人物我的共存共在、动态平衡中彰显个体的主体性。在中西人文思想的比较中,唐君毅提出:“在西方之思想中,原有视自然物由原子组成,社会以个人为原子,及人各为一独立自足之个体之个人主义等种种之说。”[3]89从个人观的差异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唐君毅紧紧地抓住了中西近代文化的核心问题。儒学的价值形态在个体自由、权利方面的薄弱与缺失,成为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势发展开来的内在生长点。但是,在个体自由与权利确立之后,如何强化群体意识、合作精神、规范意识,以限制资本、市场所刺激的占有型个体主义,以及精致利己、价值虚无等问题,成为一个全世界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唐君毅认为,西方现代文化要继续发展,需要重新找到发展方向和动力,重新审视人的超越性,以解决西方文化发展中所遇到共同体和责任弱化等一系列问题。他说,“近代西方思想之发展,至少其中有一条线,是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而下降至重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16]6-7,这种发展轨迹,是一种下降,是对人的理解片面化。西方人文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建设中需要关注的,“因为他们之问题所在的地方,即我们能贡献我们的智慧的地方,使我们能自觉我们之传统的人文思想之价值的地方。亦即我们能用我们之智慧,来开拓我们之传统的人文思想的地方”[12]27。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都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有关,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需要从传统人文思想中寻求资源。
与西方绝对的个体观念不同,中国源于“感通”的伦理人文主义,是从个人责任和伦理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的个体。唐君毅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与孔子思想中,则原无此视个人为一原子或个人主义之说,而自始即以吾人之一己,乃一存在于‘人伦关系中,及与天地万物之关系中’之‘一己’。吾人之一己,原是一能与其他人物相感通,而此其他人物,亦原为可由此感通,以内在于我之生命之存在中者。依此思想,则一人之为一个体,即原为通于外,而涵外于其内之一超个体的个体,亦即一‘内无不可破之个体之硬核,或绝对秘密,亦无内在之自我封闭’之个体。故中国之思想,亦不缘此以视天为一‘超越于一切人物之上,其知、其意、其情皆非人之所能测,而有其绝对秘密或神秘’之个体人格神。”[3]89在这种思路中,个体自身所具有的超越现实内容,是中国人文思想中不可磨灭的价值。
就唐君毅的思想而言,证成心性本体的动力性、理想性和一贯性,以及中国人文思想的独立传统和优长,是其核心问题。景海峰指出,“儒家人文主义之辨析,不仅是唐君毅诠释儒家思想的主要话题,也是他以‘非人文—人文—超人文’之架构,来调和中西、证成儒家文化之优越性的基本范式”[17]。唐君毅用“感通”解释“仁”,并把传统心学与孔子“仁”论密切结合起来,并从对己、对人、对天道三个维度拓展心性之学、人文论的维度,说明中国人文传统的特质在于“伦理的人文主义”,彰显中国人的对于主体的独特理解模式,以及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