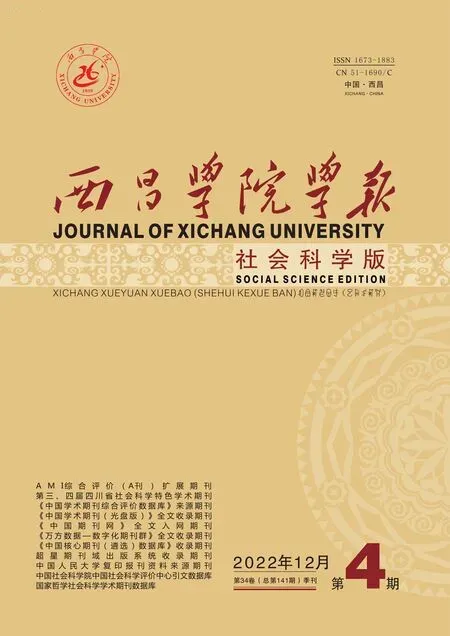明朝巴蜀诗人对前后七子复古诗论的反拨
2022-04-07郭浩南
郭浩南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100)
明中期以杨慎为代表的巴蜀诗人跻身全国诗坛,他们对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想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在诗歌的本质、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审美等方面进行了反拨。
一、对前后七子诗歌本质观的反拨
诗歌的抒情本质直到陆机《文赋》 “诗缘情而绮靡”[1],才逐渐为大家所认识,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宋代,诗歌的抒情本质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出现了所谓 “性气诗” “性理诗” ,通篇理语,毫无诗味可言,这种诗风直接影响到明初诗坛。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以复古自命,重申了诗歌的抒情性本质特征,但矫枉过正,陷入了另一个极端,认为 “宋无诗”[2]666,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代的巴蜀诗人没有盲从,阐述了诗歌创作需情理兼顾的理论主张。
(一)针对轻视诗理,重视诗理的表达
前后七子出于对诗歌抒情本质的维护,何景明提出 “宋无诗” 的口号。李梦阳为余存修诗集《缶音》所序道: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3]477此处的 “理” 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泛指一般的事理;另一层则专指理学之语,即指以理学之论入诗的倾向。相比于对理学之语入诗的严拒态度,前后七子虽对一般事理入诗较宽容,但一般事理须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进入诗歌,因为他们认为诗歌自身已包孕着 “理” ,不需要专门的理语来阐释。而承载理学之语的 “理” ,在前后七子看来,不应让此出现在诗中。
在以理入诗问题上,巴蜀诗人展现出了较前后七子更加理性的态度。他们坚持诗歌是以情为本,自觉维护诗歌的抒情本质,兼重义理,以一种较包容的态度允许理学之语入诗,但其前提是不伤害诗歌抒情本质。前后七子排斥以理入诗的做法为明代文坛滥情化进一步扫除了思想上的阻碍,明中后期市民经济繁荣更是为这股滥情之风席卷诗坛提供了经济基础,巴蜀诗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故提出了以情为本,兼顾义理的主张,来遏制这股滥情之风。如安磐在评价友人张茂先的《励志》时批评道: “张茂先《励志》……《三百篇》后能以义理形之声韵以自振者,才见此耳。”[4]肯定并赞扬诗歌表现和蕴含义理。安磐在以理入诗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巧妙寓理。如其反驳陈公甫、庄孔阳等人的诗作时,认为杜甫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 微妙流转,而孔阳 “溪边鸟共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 全不成语”[4]。 “微妙” 即表意须含蓄深刻, “流转” 为音韵和谐、形象生动之意。此论中,安磐表达了对于杜诗词工理浅之论和理语直接入诗的不赞同。安磐借为杜诗正名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即要巧妙寓理,要凭借蛱蝶穿花、蜻蜓点水来委婉表达鸢飞鱼跃、天机活泼的哲理,更要通过 “深深” “款款” 之类的词语来进一步丰富其含蓄意味,使诗歌显得 “微妙流转” 。
(二)针对一味追求人情之真,倡导 “真情” 的规范表达
针对宋元以来诗歌流弊的多重困境,前七子将重振诗歌抒情本质作为了破解当下困局的关键,如李梦阳《鸣春集序》表示: “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3]473康海《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指出: “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5]他们都认为诗因情而生,诗歌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自然呈现。明中期以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异军突起,并在文坛了产生重大影响。在此思想背景下的前七子提出的人之真情,自然与传统儒家尤其是宋儒提倡的人情不同。前七子提倡的人之真情,是包括喜怒哀乐等在内的人的自然情感,无关正邪之分,而传统儒家提倡的人情是有度有量和有正无邪的人之真情。前七子这种真情论反映到其文学观上,表现为对于民间歌谣的推崇以及李梦阳提出的真诗在民间之论。尽管宋儒的人情论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但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文学健康发展确有裨益之处。但极力想要摆脱理学束缚的前七子们尽管注意到约情的重要性,但并未提出一个对 “情” 进行一定合理约束的理论。如李梦阳在其《空同子·论学》论道: “孟子论好勇好货好色……是言也,非浅儒之所识也。空同子曰:‘此道不明于天下,而人遂不复知理欲同行而异情之义。’……理欲同行而异情。故正则仁,否则姑息。正则义,否则苛刻。正则礼,否则拳跽。正则智,否则诈饰。”[3]606李氏此处所引的孟子论好勇好货好色出自《梁惠王上》与《告子上》两篇中,在这两篇中孟子分别通过正反两个例子论好勇好货好色,他首先于《梁惠王上》举了公刘 “好货” 为周民族繁荣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的正面例子,如 “昔者公刘好货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6],又于《告子上》举了国君为了一己之私夺民利以充实国库被冠以民贼称号的反面例子,即 “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7]。通过正反两个例子来阐释好勇好货好色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能只看到情欲好的一面而忽略了坏的那面。以好勇好货好色为代表的人欲不仅会产生坏的结果,相反它也能带来好的结果,此外孟子也承认食色代表人欲,是人的天性,不能完全抹去它,需要正视它的客观存在。李梦阳基于此而倡导 “理欲同行而异情” 来反击理学家们的 “存天理,灭人欲” 之论,将欲抬高到与理一样的地位,并进一步具体阐释道,欲与理一样源于本性,会产生好坏不同的结果。希望将真情从理学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达到为以好勇好货好色为代表的人性正名的目的,即 “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3]589李氏之论重视人正当的情欲,但是对于如何不溺于情欲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仅给出了 “超乎此而不离乎此,谓之不溺”[3]590这个模糊的答案,即不溺于情欲全靠自身自觉,这对于自我约束力较高者不失为一良策,而对于自控力不强之人是否也能不溺于情欲则有待商榷。且按李氏之论,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们应该拥有较好的自控力,应能不溺,但实际情况却是亦如自控力不足之人一样耽于声色。康海、王九思在罢归之后沉溺于声伎, “每相聚游东鄂、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8]4833。如此环境和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抒发的情感确为真情,但在这种真情支配下创作出来的诗歌内容上应是贫乏和不健康的。李氏此处的忽略正是源于其一味追求自然人的 “情” 之真,不希望这股真情被加以束缚,从而重走宋儒的老路。若一味追求情之真,而不规范表达真情,则易使人溺于情,不能及时从情感泥沼中抽身而出。且不规范表达真情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艳情甚至色情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毕竟艳情与色情也属于自然人之真情,如此便易导致诗道越发衰微和人心动荡,进一步威胁社会稳定和和谐,尽管这并不是前七子所期望得到的结果。
在情感表达上,巴蜀诗人对其一味追求 “真情” 的倾向进行了反拨。杨慎在其著作《性情论》中,首先对性与情进行了阐释。他引许慎之论: “性者,人之阳气,性善者;情者,人之阴气,有欲者。”[9]66同文又引《礼》之论: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情之欲也。天静曰性,欲动曰情。”[9]66综合来看,性是稳定的,不容易受到外界所干扰的,具有稳定性,且符合某种具体标准要求和受其约束控制,即 “性善者” ;而情则是变动的,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具有不稳定性,有时不符合某种具体标准要求和不受其约束控制。从儒家与七子们对两者关系的论述上看,两家论述均有片面性。尤其是宋儒主张对人情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和规范,甚至倡导 “灭人欲” 等极端主张从而来使人情接近于他们推崇的境界。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则片面强调追求变动的且不受具体标准约束控制的情,即反对宋儒的以性约情的片面思想主张,从一个片面走向了另一个片面。在这一问题上,杨慎对片面强调性的儒家思想和片面强调情的七子主张都给予了反拨,他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既重视性,也不轻视情。杨慎指出性与情 “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举性而遗情何如,曰死灰;触情而忘性者何如,曰禽兽”[9]66。他认为诗歌如果无情,则丧失根本,即抒情本质,必然苍白无力,近乎 “死灰” ,诗歌便可能因此灭亡;不加节制地滥情乃至纵欲,则将危及社会人心。因此杨慎强调诗歌不能因情废性,也不能因性废情,要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创作出既有感人心者的情,又有能促进社会和谐的性的优秀诗歌。
前七子的主情诗歌本质观对明中后期诗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有不以为然者,如唐宋派文人;也有在此基础上继承发扬的,如公安派等文人。唐宋派文人针对前七子重情恶理,提出了重理轻情的主张来加以反驳,以唐顺之为主要代表。一方面,唐顺之不仅极力推荐宋代著名理学诗人邵雍创作的性气诗,如其晚年在其《与王遵岩参政》一书说道: “近来有一偏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10]由此可见,唐氏丝毫不隐瞒对邵雍之诗的青睐之意,另一方面,唐顺之自身也创作了不少的性气诗,这是其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安派文人则是在前七子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个人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重要性,且这种个人情感多是远离社会现实和不太符合主流伦理道德观的,如袁宏道于《与吴敦之》之中说道: “弟常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三败兴也。”[11]在袁宏道看来,国破家亡这种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事务不足为道,只有能给人以感官上和心灵上以愉悦的风花雪月和与友人纵情山水等事务才是最有价值的事务。面对同样的境遇,以杨慎为代表的巴蜀诗人则对前七子的主情诗歌本质观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既没有像公安派文学家们一样盲从,也没有像唐宋派那样全然否定,而是认识到了其中的可取之处,如杨慎评价以陈献章为代表的 “性气诗” 时道: “效简斋、康节之渣滓,至于筋斗、样子、打乖、个里,如禅家呵佛骂祖之语,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9]496表现出了与前后七子一般对理语充斥、情味寡淡的性气诗的不满态度。同时,指出明前七子情论的不妥之处,即片面的重情舍性诗学主张,于此杨慎为代表的巴蜀诗人们提出诗要合乎性情、真情须规范表达等诗论来加以反拨。
二、诗歌创作论上的反拨
由于前后七子认为此时的明代诗坛经历了性气诗和台阁体等诗风的洗涤,诗道已经倾颓,重振诗道的大业已迫不容缓,而诗歌具体创作方法则是其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鉴于此,前后七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诗歌创作方法,如 “拟议” 和 “重诗法” 等等。而巴蜀诗人则提出了博采众长、意法彬彬、提倡诗歌的独创性等具体创作方法来反拨。
(一)针对 “诗必盛唐” ,提倡博采众长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主张学诗应 “以汉、魏、晋、盛唐为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2]。明初,林鸿、高棅正式以盛唐相号召。林鸿的《鸣盛集》专学盛唐,高棅编辑的《唐诗品汇》将盛唐诗歌列为唐诗正统。而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则倡导 “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8]4833来宣传其师法对象主张。前后七子有推崇盛唐诗歌的倾向,通过贬低宋诗来抬高唐诗地位便是一个例证。何景明在其《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论宋元诗时,有两句为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奉为 “二季之定裁” 、其评 “的然” 的著名评语: “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2]575将宋诗连同元诗,作为他诗学系统中主要批评的目标,通过排斥宋元诗来确立唐诗的诗坛正统地位。片面的师法对象观点严重地束缚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品评标准,诗歌好坏的品评标准不应该单一,应是多元的,诗法对象也是,如此方能使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前后七子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在西南一隅的巴蜀诗人们却敏锐地注意到了,提出了博采众长等诗论主张来进行反拨。
费经虞针对前后七子 “诗必盛唐” 说提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费经虞于其论诗道: “诗体有时代不同,如汉魏不同于齐梁,初盛不同于中晚,唐不同于宋,此时代不同也。有宗派不同,如梁陈好为宫体,晚唐好为西昆,江西流涪翁之派,宋初喜才调之诗,此宗派不同也……然一家有一家之体,不能备载,惟为人所效法及播于诗话者,乃具列如左,余不概录。”[19]468此处虽主要论及诗体因时因人而变,且各具特色。但也涉及到了学诗师法对象,其师法对象广泛,不拘于一时一人,有汉魏,也有晚唐两宋,有建安之曹刘,也有宋之苏黄,甚至西昆体与齐梁宫体诗在费氏看来都有师法的价值所在。凡有价值之诗皆可学,不拘泥于某一朝代或某一诗人之诗。此外,杨慎、张佳胤等人对于前后七子褒唐贬宋的诗学倾向不满,从而明确反对前后七子诗以代降的观点,而主张代代有诗,表明其诗歌应以优劣论,而不应该简单地以朝代论诗。
(二)针对轻意重法,提倡意法彬彬
意与法的关系,简单说来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前后七子在意法关系论说中,落入了轻意重法的漩涡。如王世贞评论欧苏散文时说道: “至于五代而冗极矣,欧苏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欧苏则有间焉,其流也使人畏难而好易。”[18]221首先承认欧苏二子对于扫除盘踞北宋文坛已久的五代冗极文风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认为欧苏二子的轻率任意而为的散文创作为后学者畏难好易的创作倾向树立了较坏的榜样。与其说王世贞对欧苏二子 “任意而为” 的散文创作方式不满,倒不如说是王世贞在法上具有一种特殊的执着。他的这一种执着使得他对于当时一些 “轻敏之士” 学习宋文的现象大为不满,其于《古四大家摘言序》中对这种现象批评道: “而一时轻敏之士,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群然而趣之。”[13]王世贞于此论中并没有特别指出 “轻敏之士” 在文法上有不当之处,且从其 “宋之易构” 一语中也可知晓王世贞也认为 “轻敏之士” 们学习的宋文是符合法度的,他所不满的仅仅只是他认为宋文的法度太过于简单。尽管这些文章可能合意既合法,但他还是希望当时文人应在法度上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勇于去使用更具难度的文法来进行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尽管王世贞一再强调意法兼容,但在意法关系问题上,更注重后者,注重要用有形之法去约束无方之意,即 “法” 对于 “意” 有规范作用。
在意法关系上,若重点突出法对意的规束作用,则会损害意的主体地位,更会损害意的主要构成元素——情的主体地位,以费经虞为代表的巴蜀诗人给出了较合理的主张——意法彬彬。他在《琐言》中评论后七子轻意重法时说道: “王李谓诗有一定规格,多出模仿,是犹以西施之貌,当类南威秦娥之音;宜仝王豹开后学,失尽性情之端。钟谭谓诗出自性灵,而止是以乱发垂鬟,不加膏沐,卷芦截竹,尽弃笙竽,启狂夫绝弃绳墨之渐。要之,皆偏论也。规模出之古人,意兴直抒胸臆,庶几可哉。”[19]430将王李与钟谭对比,批评王世贞、李梦阳的主流诗学 “有一定的规格” ,结果却 “多出于摹仿” ,就像自有其貌与声音个性,却欲有南威秦娥之音一样,只能 “失尽性情之端” ,即背离诗歌的抒情本质。他认为诗歌当 “规模出之古人,意兴直抒胸臆” ,即既要有一定的法的规范,又要以抒情为主,直抒胸臆。此外,与后七子交好的张佳胤也对前后七子轻意重法的做法不满,提出形式不能束缚意以及突破法度的诗歌主张,表现出了较于以复古自居,而实际叛古的前后七子等人更加理性且客观的诗论态度。
(三)针对 “拟议” ,提倡诗歌的独创性
关于 “拟议” ,李梦阳主张 “议拟以一其格”[3]476, “参伍以错其变”[3]476,何景明重申 “拟议以成其变化”[14]。何李之后 “拟议” 成了后七子一些成员为摹习古典诗文及其法度规则而主张的一重要手段,其语源自《周易》: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15]拟议是初学诗者学诗作诗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不是诗人跻身于诗坛之后抄诗的凭据。因为认识到 “拟议” 这一重要作用,后七子希望通过倡导其来帮助初学诗者于漫长诗径中寻到一条捷径。可其片面的诗学主张以及七子们自身的诗歌创作偏离了自己诗论的初衷,搜寻诗径捷径的 “拟议” 成为了泥古的 “拟议” 和抄诗的 “拟议” 。这一点同时也成为了前后七子们复古思想的反对者们抨击力度最集中的一点,如钱谦益批判李攀龙所拟乐府不乏 “影响剽贼”[16]之作,不是由更易若干字句而成,就是窃取古作为其所用,而这正是 “拟议” 意识主导下的产物。
巴蜀诗人最不满的就是这点。安磐针对前后七子的 “拟议” 主张,提倡诗歌的独创性和反对因袭模仿。他直接批评 “拟作” : “近世诗人,见古人佳句辄欲拟作,自谓得意,甚者笔之于书,以夸乎人。然而何尝得其仿佛,乾鼠为璞,蹄涔自濡。殊可笑也。”[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 “杨用修述公石论诗之旨云:‘唐之名家,自立机轴。譬犹群花各有丰韵,乃或剪彩以像生,或绘画而傍影,终非真也。’又云:‘论诗如品花,牡丹芍药,下逮苦楝刺桐,皆有天然一种风韵,今之学杜者,止芍药牡丹尔。’其说足以解颐。”[20]470“自立机轴” 便是要重视诗歌的独创性,摹仿古人再逼真,也都是假的,唯有独创性才是真的。尽管安磐对前后七子的批评稍显严苛,但并不意味着巴蜀诗人就完全否定初学诗者拟作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希望通过拟作来在诗径上寻求到属于自己本身的诗道,而不是止步于和迷失于前人的诗道之中。
在面对前后七子专尚盛唐的诗学观时,巴蜀诗人与公安派文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提出了 “代代有诗” 的诗学主张。在意法关系上,唐宋派以及公安派这些当时文坛名派选取了以偏激对抗偏激的片面诗学观点,即主张重意轻法,如唐宋派的王慎中在《与华鸿山》一文中论道: “往日游世浮迹,盛衰用舍之际,言之有可感者,虽文不为工,而其意独至矣。”[17]虽然此论中认识到之前自己的一些作品可能文学形式上有所欠缺,但是内容的独到能够弥补这种不足。而袁宏道则进一步大力倡言 “信心而出,信口而谈” 和 “信腔信口,皆成律度”[23]4,希望完全将意从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即法不能约束意的文学观点。而巴蜀诗人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像之前一样选择与唐宋派以及公安派等反复古派站在一起,而是在综合考量下选择了一种既能使诗歌之意充分表现出来,同时也兼顾诗歌法度的诗学主张,即意法彬彬。
三、诗歌审美观的反拨
孔子首次于《论语·阳货》提及了诗歌具有 “兴” 与 “群” 的审美作用。王船山对 “兴” 进行了诠释: “古人有兴起之心而《诗》作,……后人于《诗》而遇其兴起之心。”[18]1790“兴” 乃诗人受到美的召唤后将美注入诗歌的过程。 “群” 则是读者阅读诗歌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后形成某种共鸣的过程,即 “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12]1937。诗歌审美观发展到前后七子时期,提出了以 “格古调逸” 与 “雅道” 为代表的形式美。尽管前后七子是从维护诗歌抒情本质的根本目的出发,但其偏激的审美主张最终使诗歌流于形式以及使复古陷入了泥古的沼泽。巴蜀诗人不太认同前后七子其狭隘的诗学审美观,提出了包含刚柔相济和雅俗共赏在内的风格无高下之分的审美主张。
诗歌的创作之难,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云: “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3]446他将 “格古” 置于首要地位,足以见出其对诗歌格调之美的重视。王廷相在与《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将 “定格” “运意” “结篇” 以及 “炼句” 视为作诗之 “四务” 。此外他论及诗歌的格调时说道: “格者,诗之志向,贵高古而忌芜乱。”[19]将诗歌的 “格” 喻作人的志向,并强调了诗格之美在于高古,而不在于芜乱。何谓 “格” ,总结李梦阳等人的言论可以得出,即作品的体式以及体格,同时关涉作品的体制格局和由此所展现的风格特征。所谓 “高古之格” ,概括而言,一是淳正不芜,与 “芜乱” 相对立;二是古朴厚重,即富有古意且形式简朴的诗体。简单来说,契合 “高古” 标准的是七子们推崇的晋以前的汉魏诗歌之 “格” 。如徐祯卿曾指出: “古诗句格自质,然大人工。《唐风·山有枢》云‘何不日鼓瑟’,铙歌辞曰‘临高台以轩’,可以当之。”[20]“芜乱” 者,杂乱而不正也,或即如徐祯卿所鄙薄的 “莠乱而未叶” ,即不符合七子理想标准之 “格” 。尽管前七子是出于重振诗道的目的而推崇格古之美,但其在格调之美具体表现方法上的拟古主张,却最终使其复古诗学主张变成了低下的泥古主张。前七子追求的格调之美主要侧重于阳刚之美,排斥或忽略了包括阴柔之美在类的其他风格美,最终使明诗发展从一个极端发展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利于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也为最终的复古运动退出诗坛埋下了伏笔。
巴蜀诗人的诗学审美观则显示出了较包容的态度。以杨慎、费经虞为代表的巴蜀诗人提出了 “绚彩风骨,彬彬不偏” 和刚柔相济等诗歌审美观。巴蜀诗人既提倡包括壮美在类的阳刚之美,且不排斥含蓄蕴藉自然清新在类的阴柔之美。大力提倡阴柔之美的巴蜀诗人首推杨慎。六朝诗歌向来由于阴柔气盛,而阳刚不足遭到包括陈子昂在内的文人们的批评,如陈氏在其《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21]杨慎却直接称赞六朝诗: “陆谢擅缘情,沈范采余绪。”[9]179赞扬陆机、谢灵运、沈约、范云等六朝诗人擅长缘情,词采绚丽,风格清新婉丽,更是毫不讳言地表达其对阴柔之美的推崇和赞赏。杨慎大力推崇阴柔之美,但同时也非常重视阳刚之美。如其评论以恢复汉魏风骨为己任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诗时,杨慎对其诗歌中充沛的阳刚之气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如 “其辞简直,有汉魏之风,而文集不载。”[9]563即承认便赞扬以简洁直率质朴有寄托有风骨的诗歌阳刚美。其诗歌审美观上更多主张诗歌刚柔相济之美。对于六朝诗歌多绚彩而无风骨的弊端,杨慎丝毫不因为自己的偏爱之心而避讳不谈,为了改正六朝诗歌无风骨即少阳刚之美的弊端,他又主张学习汉魏富含阳刚之美的风骨之事来加以调和,从而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境地。费经虞更是进一步提出了风格无高下之分的诗歌审美主张。其《琐语》云: “诗家数甚多。清新也可,雄浑也可,古奥也可,幽细也可,只要是到家句。”[22]此所谓家数,就是运用艺术手段而形成的风格特色,体现了费经虞在内的巴蜀诗人在诗歌审美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相较于前后七子诗歌审美观开明且包容的态度。
后七子在前七子的基础上更注重雅俗之分。由于深受严羽《沧浪诗话》的学诗要先除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 “五俗” 影响,故其在诗歌雅俗美学问题上的答案倾向于严羽的以雅为美,提倡 “雅道” 的诗歌审美观。李攀龙在《三韵类押序》一文中说: “今之作者,限于其学之所不精,苟而之俚焉;屈于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险焉,而雅道遂病。然险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则用之者有善不善也。”[23]李攀龙此篇表面上虽只在围绕诗韵说事,但他实际上也给出了他在雅俗问题上的答案,那就是提倡以雅为美。因为险韵与俚语,险韵尚可有法可使其转危为安,但俚语却无计可施。更甚者,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 “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有太粗者,‘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类也。”[24]42即使是对于拥有崇高地位的《诗经》,王世贞也无所顾忌,对其中的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这样浅俚的诗句而表现出不满之意,认为其太粗而不雅。显然后七子也如前七子一样在诗歌审美观上稍显片面,巴蜀同期诗人则通过推崇雅俗共赏的美学观来加以反拨。
针对后七子提倡的 “雅道” 审美主张,以谢东山和杨慎为代表的巴蜀诗人则提出了雅俗共赏的诗歌审美主张。谢东山《周太霞北来始悉升庵翁盖棺事且悲且慰诗以记之二首》第一首中 “落日诗成还寄我,空传白雪和歌劳”[25]98二句,表明诗人与杨慎之前有过寄诗唱和的事情,而如今只能空吟 “白雪” 和 “歌劳” 了。所谓歌劳,很可能是来源于汉民歌乐府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即俗的代表,与 “白雪” 代表的雅相反。空传 “白雪” 和 “歌劳” 是作者对杨慎诗歌的赞美,赞美其既有雅之美,也有俗之美,表达了其 “雅俗共赏” 的诗歌审美观。杨慎则是从用辞方面来表现其雅俗共赏的诗歌审美观。其《升庵诗话》中点评杜诗论道: “杜诗:‘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语反拙,所谓凿混沌而画蛇足,必天性命而失卮酒也。不若李群玉乐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难急流’也。又不若《巴渝竹枝词》云:‘大河水长慢悠悠,小河水长似箭流。’词愈俗愈工,意愈浅愈深。”[26]254杨慎对于杜诗的评价有失公允,但其提出的 “词愈俗愈工,意愈浅愈深” 论诗主张却值得注意,他并不是要提倡完全以俗语作诗,而是要把握好俗与工两者之间的度,不至于重工轻俗,使诗歌晦涩难懂,也不至于重俗轻工,失却诗歌原来本色。而是要以俗为工、化俗为工,如此才是真正的工。只有诗歌与文学作品做到了真正的工即雅俗共赏,才能久远流传,以致于不朽。
与主情本质观一样,前后七子提倡的包含 “格古” 和 “雅道” 诗歌审美主张亮相诗坛之后,迅速引发了明中后期诗坛对此的广泛讨论。唐宋派的茅坤虽然不认同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但是在审美观上却无法摆脱前七子的影响,如其在《调格》中论道: “格者,譬则风骨也。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汝辈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学。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即如不能高古,至于 “典雅” 二字,决不可少。”[27]由 “风骨” 和 “磅礴” 等词可以洞见,他和前七子一样追求侧重于阳刚美的古格,推崇 “格古典雅” 之美。而公安派看到后七子 “雅道” 主张带来的弊端,提出了重俗轻雅的主张试图来加以反拨,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 “穷新极变,物无遁情。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此进之矫近代浮泛之弊也。”[28]4公安派浅俗的通病,人所批评。巴蜀诗人虽然文坛地位与影响力稍逊于前两派文人,但其主张刚柔相济和雅俗共赏的审美观较前两派具有独特以及可取之处,显示出了巴蜀诗人沉着理性、辩证对待问题的品质。
综合来看,明代巴蜀诗人主要是围绕诗歌本质论、诗歌具体创作以及诗歌美学观上等几个方面对前后七子诗论展开了反拨,在这一反拨过程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博采众长和意法彬彬等见解。但也存在有矫枉过正之处,如杨慎为反击前后七子的诗必汉唐提倡诗必六朝初唐之论。巴蜀诗人诗论主要是针对前后七子复古诗论而发,但将其放在明中后期诗坛复古与反复古运动这个大背景中看,使其与唐宋派以及公安派等这些诗坛反复古名派诗论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且在对待一些诗学具体问题上,巴蜀诗人较其更加细致周全,充分体现了巴蜀文化特立独行和海纳包容的文化精神。尽管巴蜀诗人的诗歌主张与前后七子等人的诗歌主张差异性较大,但从他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看,他们是殊途同归的,是从不同的侧面维护诗歌的独立地位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