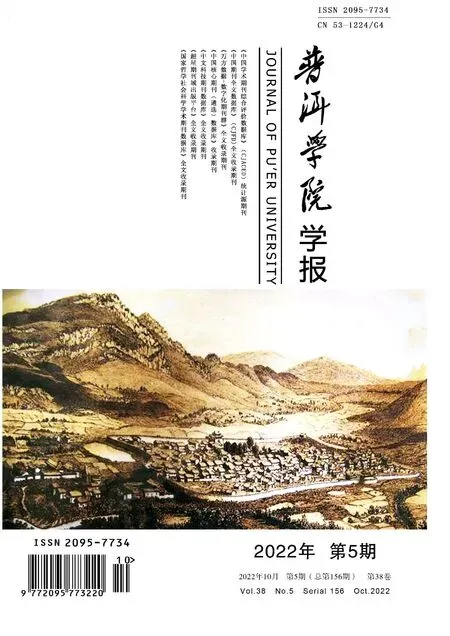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研究综述与展望
2022-04-07许媛萍
许媛萍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或者借助媒介进行的以沟通、交往为目的的传播行为,它渗透在人们的日常交往、经济建设、政治文化活动中,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民族地区的人际传播对少数民族人际交往关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等多个方面产生直接的作用与影响。因此,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际传播研究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期刊数据库“知行搜索”,分别以“人际传播”“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等作为关键词进行交叉检索,最终挑选出35 篇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呈现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轮廓。
一、研究现状
按照在人际传播活动中是否借助了除传播主体“人”之外的其它有形的物质媒介,我们可以把人际传播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人际之间面对面直接进行的人际传播,即亲身传播,比如会谈、晤面等等;第二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质媒介进行的间接的人际传播,信件往来、电话交谈、网络聊天等都属于间接人际传播的范畴[1]。
(一)口耳相传与传统媒介下的人际传播
在网络媒介时代到来前,少数民族群众的人际交往对象大多围绕“近邻”进行,人际交往网络基于血缘、地缘的纽带建立,人际交往的方式主要为人际亲身面对面交流、捎口信等。在此阶段,人际传播的范围、内容都受到限制。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民族语言、歌曲、舞蹈、服饰、宗教祭祀以及其他民俗事务在人际传播中,对少数民族人际关系的建构、情感维系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积极的意义。
龙献发现,在相对封闭的黔西北民族地区,人们与外界的交流依然具有局限性,以人为媒介的人际传播作用至今依然突出[2]。柳盈莹的研究指出,傣族的有声语言以及形成的各种歌谣与原始神话是当地人民重要的人际传播媒介[3]。刘俊妍指出,土家族的火塘公共场域,丧葬习俗活动是村民进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与信息传播场域[4]。罗婧考察了“晒坝”这一布依族传统的人际传播形式后发现,“晒坝”是人际传播的重要场域,布依族人民习惯于此聊天并交流信息,有利于增强宗族感情[5]。雪珍的研究指出,羌族在历史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口口相传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及羌文化传承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本民族的传说故事、民间古歌和祭祀活动在面对面的交往空间中得以传承[6]。卡德热依·哈力布亚指出,哈萨克族特殊的聚会形式“恰依”以及赶集方式“巴扎”是促进人际传播的重要方式,“人生礼俗”以及“丧葬嫁娶”等民俗文化活动是哈萨克族人际传播的重要内容[7]。周洁的研究发现,在西藏乡镇,广播、电视并没有完全改变当地居民的人际传播方式,过林卡、参加宗教活动和聚会、去藏式茶馆等面对面交往依然是主要的主要的传播方式[8]。
(二)以新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传播模式
媒介形态的变迁与发展,推动着人际传播模式的革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革新,少数民族人际传播可凭借的物质媒介更加丰富,人际传播的渠道发生显著性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人际交往的互动过程与行为。
1.冲击与重塑:新媒体对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
伴随着手机等新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冲击与重塑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有研究发现,手机等媒介介入云南少数民族乡村后,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交往开始突破熟人社区的局限,信息流通的范围、人际交谈的话题得到极大地延伸和扩展,但人际交往也愈加复杂化[9]。手机媒体成为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的重要辅助工具,拓展了少数民族人际交往范围,影响了人际交往行为、交往频率以及交往观念,推动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发生改变,强化了人际传播的效果[10]。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微信、QQ 等社交媒体平台对少数民族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普遍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密切、广泛、多样的人际交往模式,人际交往的形式和目的更加多元化[11]。
2.维系与发展:新媒体对传统人际关系的影响
人际传播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人际关系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与方向[12]。中国的人际传播是以“伦理本位”“关系本位”为特征的,强调人际交往中的“情”与“义”[13]。有研究者从“关系”的视角出发,将新媒体视为影响了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中介,探究新媒体对少数民族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情感的交流和维系,传统的人际关系得到进一步地建构与发展。
胡媛的研究指出,手机媒介消解了现实距离的疏离感,拉近了熟人圈层里情感联络的亲密度,围绕“血缘”“地缘”和“业缘”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深化和巩固,但手机媒介取代“第三人角色”也使人情往来出现了冲突[14]。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是传统人际交往的特征。罗江琴认为,新媒体进入鹤庆县逢密白族村后,熟人社会的“人情味”交往并没有消失,由传统的血缘、地缘联结的人际关系依然在少数民族乡村社区的人际交往中占据着主体地位[15]。有研究考察了微信对哈萨克族人际传播中情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微信程序可以拉近好友情感、亲子情感、隔代间的情感[16]。也有研究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关注移动媒介对康巴藏区居民代际关系的影响,研究指出,移动媒介超越时空帮助乡村家庭中的祖辈、父辈与子辈三个世代成员之间建立了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其信息传递行为由此前的单向流动转向双向流动,不仅带来了平等家庭的转向,还带来子辈的社会参与和祖辈和父辈的“反向社会化”[17]。此外,有研究以强弱联系理论为视角,考察哈萨克族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强弱联系的影响。研究认为,微信使用使哈萨克族大学生与家人或熟悉的人之间在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以及亲密程度方面构成了强联系, 与陌生人或联系不够紧密的人构成了弱联系[18]。
3.博弈与转换:新媒体对人际传播中权力关系的影响
1.3 器械设备 两组手术均采用常规腹腔镜设备和普通直杆腹腔镜操作器械及Olympus主机。观察组需自制改良式经脐单孔腹腔镜器脐部固定器(自制式PORT)1枚:截取两段吸引器皮条,断端相连形成一大一小2个圆环,大环直径为8~9cm,小环直径为4~6cm,将其套合于橡胶手套袖口处,通过腹壁切口将其置于腹壁内,小环在内,大环在外,手指端连接TROCAR,形成自制式PORT,如图1。
在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村寨中、宗族里或大家庭内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往往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信息资源优势而成为“意见领袖”,他们更能集中地表达“民意”,也更能获得权威性的地位。而新传播渠道的出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获得消息的来源更加多元,“自我表达”和传播欲望也得到增强,刺激了人际传播中话语权和文化资源的博弈与转换,从而形成新的权力网络和人际交往格局。
胡媛的研究指出,手机媒介在湘西州土家族内部普及后,每个拥有手机的人都能够成为话语权实现的主体,少数民族精英话语遭到消解,形成了多个权利主体[19]。罗江琴对鹤庆县逢密白族村的研究也发现,热衷上网的年轻群体通过新媒体获得的巨大信息量逐渐成为新兴的“意见领袖”,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传统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20]。此外,有研究还考察家庭情境和代际关系中的权利变化,研究指出,智能手机成为代际交流的主要载体后,康巴藏区的子辈、父辈、祖辈的话语权发生变化,父辈和祖辈的权威受到挑战,祖辈的绝对权威演化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家庭氛围[21]。然而,也有部分学者不赞成“去中心化”的观点,例如孙信茹,赵亚净对大理白族村落进行田野考察后指出,通过对微信技术的积极运用,乡村精英在巩固象征性资源、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权威构建方式[22]。
4.发展与衰落:以新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传播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新媒体的人际传播功能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现有研究关注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在布依族苗族的民俗节日中,手机成为人际交流重要的信息载体。少数民族意见领袖通过微信群聊动员散居在各地的族人参与民俗活动,参与者与游客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转发相关视频,增加了民俗活动的曝光度对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具有积极作用[23]。有研究者发现,微信改变了传统的人际邀约方式,诸如丧葬嫁娶等民俗事务的传播通知由登门走访发送请帖的人际交往方式变为链接式或照片式的线上邀约,此方式有利于节约资源,也可扩大邀约群体的范围,突破传统民族事务传达中的信息壁垒[24]。但在叫好声中,也有研究认为新媒体人际传播会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消极影响。比如,手机媒介的使用使土家族墟场的人际传播式微,过去圩场中走亲访友,交流情感的目的也在逐渐消失。此外,手机媒介虽有效地帮助了土家族民众使用规范的普通话语言进行人际交往,但也使土家族语的人际交往功能迅速衰落[25]。
5.多样化影响与差异性需求:新媒体对特殊群体人际交往的影响
新媒体对不同群体和年龄层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研究考察了新疆 90 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交往情况,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方式新颖多样,交往内容丰富,涉及面较广[26]。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交往动机主要是维持原有人际关系、拓展人际交往范围、宣泄感情、获得信息资源等[27]。有研究指出,线上的人际交往有助于拉近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对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汉语的流利程度会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方式和质量[28]。此外,有研究者认为,微信可以打破传统的地缘及本民族间的交往模式,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扩大哈萨克族大学生社交范围,提升其沟通交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29]。
此外,有研究关注到手机媒介对土家族青年、中年、老年群体人际交往的群体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为人际交往动机和人际交往需求的不同。在人际交往的情感和精神诉求上,土家族老年群体诉求强烈更为强烈,老年群体渴望融入“玩手机”的环境,融入“年轻人”和“新鲜事”中[30]。还有研究探讨了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流动人群的人际交往的影响以及这种交往模式对于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31]。
学者们除了关注新媒体对少数民族人际传播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新媒体带来的虚拟人际传播会导致“虚拟社交依赖症”和“人际传播异化”,主要表现为在虚拟社交空间中投入的时间过多,对线下人际交往缺乏动力,线下人际交往能力的弱化以及真实的交流感被消解等。此外,网络交往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大量虚假信息得以传播,影响了传统的人际信任关系,引发信任危机。对此,研究者主要提出“理性运用社交媒体,合理安排线上社交时间”“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信息辨别能力”“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建议。
二、对现有研究的反思
(一)研究多基于微观视角,缺乏宏观面向
人际传播是社会得以传播和构建的基础。虽然人际传播具有微观的传播学取向,但人际传播并非是孤立的、封闭式的传播活动,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传播过程。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在微观场景中探讨人际传播,忽略了人际传播的社会化特征以及人际传播在影响社会方面的巨大潜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研究者较少探讨人际传播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忽略了人际传播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和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文化发展等宏观层面的影响与作用;社会作为人际传播发生的大环境,则可以通过影响人际关系的方式来影响人际间的传播[32]。现有研究在分析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发展与变化的成因时,大多仅关注媒介技术的作用,而没有将其放置在民族地区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更宏大的背景中去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导致研究浮于表面。
(二)研究思路局限,议题缺乏丰富性
现有研究的议题多偏向一隅扩展,思路较为局限。研究者的着眼点多是考察以新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传播对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忽略了人际传播的其他面向;研究关注到的媒介形态也较为单一,大多考察手机媒介和微信社交平台对某一少数民族社区或村落人际传播的范围和频率、人际交往的方式和内容以及人际交往的关系与情感亲密度的影响,研究观点同质化;关于人际传播和互动生发的场景研究,多聚焦于家庭成员间、村落邻里间,较少关注少数民族跨文化语境中的人际传播;研究多聚焦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缺乏对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离散或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等人际传播现象的关注。
(三)承袭西方理论框架,缺乏“在地性”视角
研究者多采用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框架进行理论验证或分析,缺乏“在地性”的理论视角。“在地性”强调本土化、地方性特征,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和人际交往习惯与我国的社会的现实情况有诸多的不同,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具有地方性、特殊性与复杂性等特征。此外,新媒体的普及与迅猛发展,使我国民族地区人际传播有了新的变化和走向。在研究成果中,有关民族地区新媒体人际传播议题所用的理论视野并没有超越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传统框架。这些理论脱胎于传统媒体中的人际传播实践,对于新媒体中的人际传播现象是否还具有适用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四)研究力量薄弱,缺乏系统性和跨学科对话
从研究热度上看,目前学界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媒介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的研究领域并未受到较多研究者的观照,这导致现有成果数量少,研究整体上呈碎片化形态,尚未形成较为科学与完善的研究体系。从研究质量上看,研究多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性、介绍性层面,多以某一少数民族社区或村落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内容较为泛化和零散,研究没能上升至理论的高度,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考察。从研究层次上看,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居多,缺乏能够致力于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此外,研究者学科背景单一,多局限于自身的学科背景或专业实践,缺乏跨学科思维和跨学科视角,有深度的、成体系的理论文献数量不多。
三、未来研究展望
(一)拓宽学术视阈,提升研究的观照层次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际传播研究,需要将其放置在传播发生和演化的社会宏观情境和传播环境中进行考察,既关注民族地区独特的传播“场域”,把握民族地区人际传播与不同的传播符号、传播媒介、传播形式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又关注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人际传播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做到既注重微观、静态的分析,又把握其宏观、动态的发展。这要求研究者既需要以日常关系和日常交往实践为研究的出发点,思考少数民族个体或以少数民族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对其人际交往实践、人际交往关系、人际传播范围、人际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影响,也不能忽略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环境、民族文化、信息技术水平等宏观、中观的因素对民族地区人际传播变化与发展的影响;既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渠道的变化对其社会转型、传统习俗、组织动员、文化发展以及对少数民族个人的社会化、城市融入、政治参与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和作用,又关注被技术中介化的人际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方式、组织结构、权力格局等宏观关系的影响。这样研究才能从更深层次理解与把握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的特色与规律。
(二)创新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议题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还有若干具体的研究问题有待研究者们创新研究思路,深入开拓发掘新问题、新现象、新影响,使研究的议题更加丰富多元,这至少包括以下研究议题:1.新媒体的发展使人际交往不再局限于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2.新媒体突破了物理时空中亲身交流的限制,拓展了社会交往类型,形塑了基于相同认识、同一文化背景、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价值观或共同诉求的线上的人际关系。3.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传播会对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少数民族宗教精英群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离散族群等特殊群体所产生的各种影响。4.网络空间中的跨民族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越发普遍,跨民族间人际交往范围广泛,互动性强,形成了跨民族的人际交往格局。5.快手、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越发普及,与现有研究关注到的QQ、微信等即时社交软件相比,基于短视频社交平台的人际传播所形成的特点、影响与作用。6.人际传播中蕴含着权力结构,新媒体的发展刺激了人际传播中话语权和文化资源的博弈与转换。7.新媒体的人际交往会对正在流失的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8.以新媒体为媒介的人际传播带来了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均有待研究者们作进一步地关注、思考与探索。
(三)探索建立“去西方中心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范式
社会科学解释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必然要回到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这就要面对研究中“在地性”的过程[33]。民族地区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生态,造就其纷繁复杂又具有特质性的人际传播现象,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不应该以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而应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定的情境和条件,跳出西方传播理论的窠臼,探索“去西方中心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范式,凸显本土传播特色。我国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域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原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语境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进行观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体系、传播生态中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实践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内部结构、作用机制,以此寻求新的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探索与重建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域、方法论以及理论框架,为我国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化与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推动我国人际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促进多元学科的交融对话
人际传播是人类最广泛、最重要和最复杂的社会行为之一,它在维系人际交往、形成人类社会、孕育和传承文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4],但因为人际传播具有相对的私下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难直接服务于政治、商业[35]。因此相比于大众传播研究,人际传播研究依然是传播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也造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际传播研究的巨大缺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传播研究要想获得长足发展,亟需进行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我国的新闻院校尤其是民族新闻院校在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学术研究等工作时应将少数民族人际传播议题作为重要的关注点或纳入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体系中,培养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知识积淀,双语兼通的高水平、高层次人才。此外,人际传播研究要向纵深发展有待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共同探讨、攻克和解决相关问题。
四、结语
从口耳相传到书信、广播、电话的交流再到当下各类社交媒体带来的紧密联结,随着人际传播可凭借的物质媒介的变迁与发展,人际交往的方式也正在不断革新和变化。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际传播研究越发具有价值与意义。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度也伴随着新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普及有了明显的提升,研究视角也更加多元,涉及新媒体对少数民族人际交往关系的影响、人际交往中的权力关系的变化等。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人际传播研究还处于发轫阶段,研究存在“盲点”和诸多有待深化与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