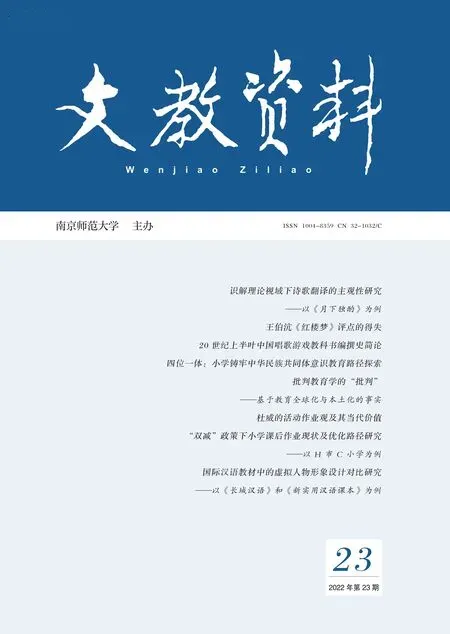浅析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角色设计
2022-04-07贾钦涵黄琳茜
贾钦涵 黄琳茜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什么是绘本?绘本是一本书,运用一组图画去表达一个故事或一个主题[1],在促进儿童情感认知、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独特效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运而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创造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引导价值,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人物是其发挥教育作用的关键,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角色形象及其设计目的,探讨其教育意义。
一、角色形象的多重类型
纵观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角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非人类角色与人类角色。
(一)非人类角色
具有自我意识的非人类角色是儿童文学,尤其是绘本中的常见形象。将动物或者玩具作为主要角色是制造距离的方式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寓言这种用动物角色来表现人类常犯的错误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儿童读物。绘本中将动物或者一些无生命的物体作为主角,让作者可以消除或者避免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与评判人物有关的因素,如年龄、性别以及社会地位。[2]简而言之,非人类角色的设计能够让读者产生与绘本角色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使读者能够更加客观地认知角色的形象、故事的情节,进而准确地领会作者想要阐发的主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多在人群间传播,绘本中的非人类角色大多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形象,如猫、狗、小鸟等,或者是与新冠肺炎疫情密切相关的无生命物体,如新冠肺炎病毒、口罩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角色在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中常常以“受助者”的形象出现。以绘本《列文是只猫》为例,故事讲述了小猫列文在主人奔赴抗疫一线后生活的变化与自身的成长。主人小静刚走后的几天,列文享受着“独自一猫”的生活,它“有车,有房,还有个好朋友”,在家中自娱自乐,过得潇洒惬意,完全没有意识到主人离开前填得满满当当的猫粮已经快要见底。渐渐地,原本整洁的家被列文弄得乱糟糟的,桌上的水杯被打翻在地上,卷纸、袜子、围巾随处可见,就连花瓶里的花也因为无人照料而枯萎了。列文这才意识到,主人已经很久没回来了,它蜷缩成一团,“有时候也有点孤独”。直到有一天,社区志愿者拎着一袋猫粮打开了房门。列文对这位陌生的来访者十分警惕,它弓起身子,钻到柜子底下,并且立志不吃“嗟来之食”,可最终还是向饿得咕咕直叫的肚子屈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列文逐渐意识到,志愿者们不厌其烦地来到家中是照顾“独自一猫”的自己,它放下了戒备,接受了志愿者的领养,并帮助他做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列文有了新家,新的朋友,和新的对手……”在这里,它结识了同样无人照顾的小狗和小男孩,在故事的最后,他们“一起等待着春天的到来”,期待着回家的那天。小猫列文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助者”形象,列文作为一只失去主人照顾的猫,生活面临着诸多挑战,好在志愿者们及时伸出援手,领养了列文,列文才得以度过这个特殊的冬天。
除此之外,动物角色还以“观察者”的形象频繁出现在绘本之中。与人类对新冠肺炎疫情居高临下地审视不同,动物对于这场属于人类社会的疫情的观察与发问,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不仅如此,这些动物“观察者”的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说《空饭盒》中的流浪狗完全在用动物的思维去观察疫情,在它的眼中疫情仅仅是一种异化了的生活状态,那么,其他几本绘本中的动物角色在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时,则多多少少带有儿童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它们是儿童的“化身”。这种现象在儿童文学中并不少见。玛丽亚·尼古拉杰娃认为,动物角色在儿童文学中的普及度也说明了小孩子与小动物有很多相同点。《下一个春天》里的黑猫是这么观察疫情的:“有些人必须在需要他们的外面……我们在家里面弹琴、看电视、读文章、玩游戏。”绘本中的“我们”显然指代的是人类,猫哪里会弹琴、看电视、读文章、玩游戏呢?毫不夸张地说,故事中的黑猫正是在从儿童的视角观察突如其来的疫情。《列文是只猫》中的列文虽然保留了动物的行为习惯,但作为一只有思想的猫,列文“桀骜不驯,宠辱不惊”,有时还会“思考猫生”,透过这些描写,我们仿佛能看到儿童的影子。尤其是在故事的最后,列文和小狗“握手言和”,相伴为志愿者送伞,这一刻,列文更是像一个在疫情中获得了心灵成长的孩子,它理解了逆行者们的付出,懂得了感恩,学会了奉献。《你为什么哭了?》中的小鸟则以孩子似的天真口吻发问,它问蝙蝠、问猎人,问天地万物,问出了儿童十分关心却无从得知的问题——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灾难究竟导致了怎样的后果?绘本创作者通过赋予动物角色类人化的思维模式,增强了绘本角色与儿童的共通感,尽可能地拉近了二者的距离。
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中,还有一类非人类角色形象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病毒。新冠肺炎病毒作为引发疫情的罪魁祸首,大多以“入侵者”这一反面形象出现在绘本、尤其是知识类绘本当中。这些病毒的形象大多被创作者描绘得肮脏丑陋,它们以侵略人类社会为最终目的,依靠空气大肆传播、蔓延,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随着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不断深入,笼罩在其身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人类揭开,切实有效的防护措施开始被提出,即便具有强大的传染性,人类也有办法将这些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拒之门外。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以最新的病毒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对病毒形象的生动刻画,向读者科普病毒的外形、来源、传播途径以及防控方法,进而传播防疫知识,最终达到科普教育的目的。
(二)人类角色
疫情主题绘本中的人类角色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医护人员、社区志愿者这些常见的“守护者”形象,即所谓的抗疫英雄。然而,绝大多数儿童读者与这些形象之间存在着隔阂,他们无法在现实中直接接触医护人员与社区志愿者,由此产生的距离感将会降低读者在阅读时对主人公(通常为儿童)的代入感。如何在丰满角色形象的同时减少读者与角色之间的距离感?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常常将“父母”与“抗疫英雄”的形象合二为一,即绘本主人公的父母拥有医护人员或社区志愿者的双重身份。并且由于第二重身份的特殊性,这些作品中的父母形象多有“英雄化”的倾向,他们往往拥有勇敢、无私的品质,在疫情蔓延之际毅然离开家庭,奔赴抗疫一线,是当之无愧的抗疫英雄。值得注意的是,英雄的光环并没有掩盖其为人父母温情的一面,这些角色往往会通过视频、电话、纸条等媒介宽慰、鼓励孩子,对主角在疫情这一特殊时期中的心灵成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沉重的疫情叙事注入了温暖和希望。绘本《爸爸,出发!》中的父亲便是父母与抗疫英雄形象合二为一的典型代表。绘本中的爸爸作为一名医生,听说外地一个城市突发传染病,医院要派人去支援,他便主动报名。“我”和妹妹满心不愿意,妹妹嚷嚷道:“不去,不去,我要爸爸天天跟我玩。”“我”也舍不得爸爸,爸爸走了,谁和“我”一起玩“坐飞机”的游戏呢?于是,“我”和妹妹使出百般解数阻止爸爸离开,把爸爸的鞋、剃须刀、眼镜偷偷藏起来,不让爸爸出门,甚至还故意站在窗口吹风,“如果家里有病人,爸爸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支援了?”可是,爸爸的申请还是被批准了。临行之前,爸爸和“我”玩了一场“火箭发射”的游戏,他说:“报告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我”忽然明白,爸爸是想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的离开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临别的那天,爸爸又和“我”重复了一遍“火箭发射”,这次,我不再阻止爸爸,而是哭着说:“出发!”告别父亲后,“我”在车上对妈妈说:“妈妈,将来我也要当医生。”绘本中的爸爸不仅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医生,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教会了孩子什么是奉献,让孩子明白了“舍小家,为大家”的意义所在。故事的最后,原本懵懂任性的“我”被父亲感动,获得了心灵的成长,立志要成为一名和爸爸一样的英雄。由此可见,双重身份的存在使得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抗疫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父母身份的加持使得儿童与这类角色之间的距离得以缩短,增强了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共通感、认同感。
二、“亲”与“子”的角色设计目的
儿童的情感经验有限,要通过什么样的知识集来唤醒儿童有限的生命体验。针对这一问题,从人物设计角度来谈,大多数绘本给出的答案都是——设计亲子关系。本文搜集了2020 年1 月至2022 年3 月的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故事类绘本共25 本,发现其中16 本绘本设置了“亲”与“子”两类不同的人物,并突出表现“亲”与“子”的关系在疫情中的变化。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绘本中会大量出现这样的人物设置模式?这与儿童的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水平有关。绘本是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一环,佩吉·惠论-莱维特(Peggy Whalen-levitt)认为,文学的阅读需要生活经验以及文学经验[3],但对于孩子来说,这两种经验都是较为匮乏的,就如牙牙学语时学习“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儿童或许能够根据生活经验理解“举头”“望”“低头”“思”一系列动作,更进一步可以通过文学经验意识到“明月”与“思念”的隐喻关系,但是为什么“思故乡”,什么是思乡,儿童或许并不能完全体会。新冠肺炎疫情中,因为缺乏生活经验,再加上儿童作为被保护的对象不能亲身参与抗疫过程,因此儿童很难直接接触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情况,并设身处地理解疫情期间中各种人的付出。如何在儿童有限的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的基础上使得儿童了解社会情况,并共情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种种值得铭记或学习的精神与情感,在绘本中有所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认为,搭建儿童容易理解并感兴趣的故事内容十分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绘本中,“子”的形象多表现为儿童或者动物(儿童的化身),大部分绘本选择以“子”的第一视角进行叙述,或是以“子”为主要叙述中心。画师在表现“子”这一类角色时,多使用圆润平滑、简单童趣的线条与饱和度高的暖色,以三到四头身的头身比为主,突出人物的童稚感。使用彩铅、水彩、马克笔为绘画工具的作品最多,如《妈妈,加油》《爷爷的14 个游戏》,营造与儿童生活经验相符合的家庭生活氛围。这些设计旨在提高儿童读者的故事参与度,以唤起其最大程度的共情。
“亲”这一类成人人物形象多围绕着“子”进行设计。多数绘本选择儿童生活的最主要参与者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等作为次要人物。这类人物是成人,多被塑造为抗疫前线人员。这样一种人物形象设计使得书中的父母、亲人同时获得了双重身份——家庭的“小我”与社会的“大我”。绘本中有在抗疫期间付出最多的医生护士,如《等爸爸回家》中的爸爸、《妈妈的秘密》中的妈妈、《空饭盒》中小姑娘的爸爸妈妈;有疫情中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志愿者,如《妈妈,加油》中的妈妈、《列文是只猫》中的社区工作人员。围绕着“子”设计这类人物,是因为与父母家人的相处是儿童现阶段最主要的生活经验之一,是帮助儿童理解“小我”与“大我”之间关系的重要桥梁。特殊的社会身份加上全民抗疫的时代背景,当社会“大我”的呼唤超越了家庭“小我”,就必定有取舍出现。这种取舍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儿童去思考探究的。因此不少作品为“亲”这类人物设计“特殊社会职业”与“家庭成员”的双重身份,借与儿童生活经验相近的家庭身份以解释他们的社会身份,帮助儿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社会情境,理解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可贵。
如《等爸爸回家》中的爸爸,作为一名医生,他需要照顾大家,作为一名父亲,他需要照顾小家,但是面临取舍时,他最终选择了以大家为重。而作为第一视角的“我”对这一选择并不理解。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称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完全从幼儿读者的视角与阅读心理出发”,绘本优先描绘“我”在挽留爸爸的过程中与爸爸的愉快相处以建立儿童读者与“我”的共情,在“我”的视角下,“我”需要爸爸完成他的家庭责任,对于“爸爸”选择优先成全自己的社会身份而非家庭身份的做法,“我”经历了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以引导绘本外的儿童读者将目光从家庭转向社会的过程。通过爸爸离开安全的家庭走入危险的医院这一行为,读者的思考将从家庭延展到社会,去关注这场疫情下的社会情景与医护人员的付出。如《妈妈,加油》中的妈妈,为了尽到自己社区志愿者的职责,不得不离开孩子,第一视角的“我”十分体谅妈妈、关心妈妈。整本绘本通过“我”对于妈妈投注的视线,详细描绘了“我”眼中妈妈忙碌的工作,来展现妈妈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作为孩子,儿童读者与“我”一样,不能直接参与抗疫,但设置妈妈这一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看妈妈的同时,看到了疫情时的社区,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在理解妈妈的辛苦是为大家付出的同时,也看到了疫情时期的社会。
新冠肺炎疫情绘本中“亲”与“子”的人物设计,为儿童读者提供了了解与思考疫情中种种人和事的空间。“子”的人物设计为儿童读者建立共情,“亲”的人物设计使得儿童读者将目光投射到疫情中的社会,思考“亲”这类人物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这种对于“小我”与社会“大我”双重身份层层深入的思考是具有呼唤力的——呼唤着作为隐含读者的孩子们去观察疫情中的社会,去思考家庭与亲情,去铭记这一次疫情付出血汗的人们。
三、想象与现实的交汇:角色设计的教育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角色设计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由此产生的教育意义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一)“入侵者”角色的科普价值
外形丑陋的“入侵者”形象往往能够凭借其夸张的外貌对认知能力尚未成熟的儿童读者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除了夸张的外形,创作者还通过生动的语言向儿童读者强调新冠肺炎病毒的危害性,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三至六岁的儿童仍处于前运算阶段,针对这一阶段的儿童所创作的绘本更加强调内容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往往通过更加具体的形象来传递信息。[4]绘本《站住!病毒怪》中,面目可怖、浑身赤红的病毒通过飞沫传播进入了一位没戴口罩的老爷爷的身体,它得意极了:“哈哈!运气不错,又找到了新家!”病毒计划得逞后的猖狂嘴脸暗含着创作者对儿童读者的警示: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防止病毒乘虚而入。
(二)“守护者”角色与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
不同于以科普为目的的知识类绘本,故事类绘本往往对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早期阅读可以促进儿童同理心、社会情感、社会交往等社会认知的发展。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儿童作为病毒的易感人群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心理健康状况的稳定性大打折扣,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在儿童群体中屡见不鲜,如何在疫情时代提高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成了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故事类绘本亟须解决的难题,角色形象的设计便是突破口之一。儿童读者在阅读绘本时常常通过代入故事角色的方式试图理解书中角色的行为意图与思想感情,进而将绘本中的社会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即所谓的社会想象。绘本描述的是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空间,包含了故事角色的语言和观点,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图像和文本的表征来构建故事的意义,与故事中的各种角色互动,不仅有助于激发儿童的社会想象力,而且能在绘本故事这种替代性社会空间里提升儿童发展中的社会认知。[5]
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中“抗疫英雄”与“父母”合二为一的角色设计对儿童读者社会认知能力发展起到的推动效果主要作用在儿童同理心与社会情感层面,具体体现为对平凡而伟大的逆行者们的崇拜以及家庭信念系统的建构。上文提到,当抗疫英雄角色被赋予了父母的身份之后,亲子关系的存在使得其与儿童读者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故事中小主人公被迫与父母分别的情节往往能够唤起儿童读者的同理心:卸下防护服的逆行者们和普通人一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同样有至亲至爱,但在灾难面前,这些抗疫英雄却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主人公身份的代入感让儿童读者能够在想象的社会空间中扮演逆行者子女的角色,同理心的存在使得他们对逆行者群体的崇拜之情不单单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还包括儿童心理深层对父母与生俱来的信任和依赖。此外,这种角色设计模式还有助于儿童读者建构家庭信念系统。家庭信念系统是家庭抗逆力的组成要素之一,稳固的家庭信念系统能够帮助家庭成员在面对危机事件时进行积极地适应和转变,将危机重新描述为一个可以理解、控制和应对的共同挑战,在困境中汲取和肯定家庭的力量有助于对抗无助感、失败感和绝望感。[6]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中,作为医护人员的父母在离开之前往往会用形象的语言告诉孩子在家应该如何做好防护措施,这就使“疫情”这个原本复杂模糊的概念在儿童脑海中变得清晰直观,具体可行的防护手段使其拥有了对抗“病毒怪兽”的信心,继而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携手抵御新冠病毒的入侵。医护人员的职业身份让父母的叮嘱更加具有说服力,家庭成员的齐心抗疫则增添了家庭的凝聚力,二者共同构成了绘本中的家庭抗逆力,并传递给绘本外的儿童读者,引导读者建构家庭信念系统,缓解疫情带来的恐慌和焦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