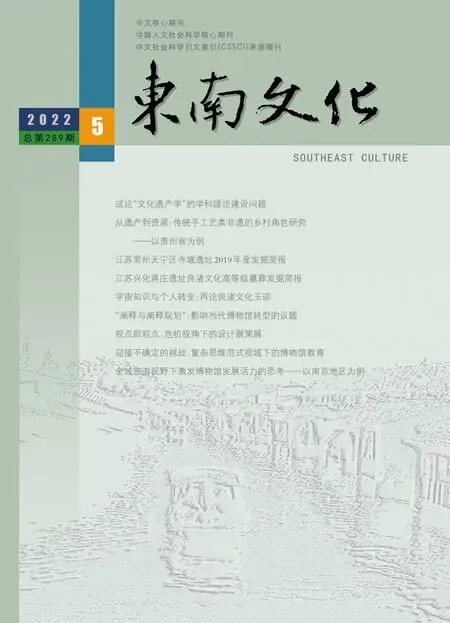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阐释与阐释规划”:影响当代博物馆转型的议题
2022-04-06周婧景
周婧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博物馆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依托博物馆物的信息传播、观众基于信息传播的实际获益。后者长期被忽视但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因此阐释学这一旨在提升信息传播中观众获益的新议题被引入博物馆领域。由于阐释学的要义是鼓励人们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上创建个人意义,所以其将成为影响我国博物馆由藏品导向向公共服务导向转型的核心议题。目前北美博物馆界已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践行。阐释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哲学诠释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我国在引入阐释学以推动博物馆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理念、技术与制度三大困境,据此提出包含主题性、舒适性、组织性、相关性、趣味性、评估性六大要素的博物馆阐释模型,进而设计阐释规划的内容框架,以期从理论和方法上探寻中国博物馆当代转型的破解之道。
博物馆说到底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依托博物馆物的信息传播、观众基于信息传播的实际获益。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是将前者视为博物馆工作的全部重心所在,不仅如此,依托博物馆物的信息传播仍主要是以机构为本的信息传播。公共博物馆诞生之初,政府预算充足,博物馆只要坐拥珍贵馆藏、亮相家底,就能过上“养尊处优”的安乐日子[1]。当时博物馆的主要职责是藏品而非观众[2],基本属于纯收藏研究机构。但自19世纪末起,博物馆在经历三次革命性运动后,逐步由纯收藏研究机构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放机构。首次革命始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至顶峰,后人将其称为“博物馆现代化运动”[3]。这场运动促使博物馆社会职能初露锋芒,但多数情况下其仍被认定是展示实物的场所。20世纪中后期,国际博物馆界又相继酝酿了两场革命,均以美国为首并席卷全球,前一次是由内向型运营形态向外向型运营形态转变[4],后一次则预示着观众的崛起以及对其的倡导[5]。此时,最大限度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成为博物馆业务的重中之重[6]。基于此,博物馆逐步摆脱窠臼,“不再仅是事实和想法的传播者,而是致力于提供机会让观众探索和塑造个人的世界观和经验”[7],实现了当代转型和范式转移。
如果说此前的博物馆理应重视依托博物馆物的信息传播,那么时至今日博物馆更应关注观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实际获益,后者经由三次革命已成为评判博物馆当代价值的重要标尺。这一背景下,旨在提升信息传播中观众获益的阐释学被引入博物馆领域,因为其要义是鼓励人们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上创建个人意义。正如山姆·哈姆(Sam Ham)所言,“阐释不是魔法,也不是一套违背逻辑的花招和噱头”[8],而是一套观众理解博物馆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尽管阐释行为如同人类的沟通一样古老[9],并且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肇兴于自然资源、娱乐和公园、休闲的研究,阐释服务和环境教育等多学科[10],但对博物馆界而言,它依然属于一个全新的议题,并将成为影响当代博物馆转型的核心议题。目前北美博物馆界在阐释和阐释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上已渐进趋热[11]。鉴此,笔者在厘清阐释及其规划的定义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破析其在推动我国当代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并提出解决之道。如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博物馆转型寻找出路,始终是当前学界和业界共同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阐释及其规划是破解该难题的关键议题,有望成为撬动我国博物馆当代转型的一个支点。
一、博物馆领域的阐释、阐释规划及其理论基础
将阐释学引入博物馆领域,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博物馆对观众及其获益的关注已从一种潜在的碎片化探索,上升至系统化的主流倡导。事实上在博物馆开展阐释研究前,教育人员、心理学家等都已开始探讨观众在博物馆信息传播中的获益问题。1889年,实践型科学家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发表《博物馆与未来》(The Museum and the Future)演讲时,主张将博物馆从收藏小古玩的“墓地”变为一个培养活跃思想的“保育室”[12]。1917—1920年,约翰·科登·达纳(John Cotton Dana)出版“新博物馆系列”(The New Museum Series)四本书,论及建立“用户中心”的博物馆,主张像吸引专业和休闲人士一样吸引蓝领工人[13]。1935年,心理学家亚瑟·梅尔顿(Arthur Melton)采用增加画廊画作数量的办法,来检测因画作数量的增加而造成的平均观看时间的变化[14],并就出口设置与观众参观时长的关系展开实验研究,提出观众的“右转倾向”[15]。可见,博物馆领域以藏品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的集中爆发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此时有关教育和观众研究的文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获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当代博物馆研究蔚为壮观的一道风景[16]。在这一趋势流变下,通过有效沟通来实现个人意义构建的阐释学,逐步进入博物馆学视域并成为富有思想冲击力的新议题。那么究竟何谓阐释、阐释规划,其是否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诸多问题亟待我们探索与解答。
(一)博物馆领域的阐释界定
博物馆领域有关阐释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呈现两大特点:从文化遗产进入博物馆领域,从其教育活动波及主要业务[17]。关于阐释的定义,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有三个。第一个由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提出:“阐释是指一种教育活动,旨在通过使用原始对象、第一手经验和解释性媒体来揭示意义和关系,而不仅仅是传达事实信息。”[18]在蒂尔登看来,阐释其实是一种沟通,目的是揭示意义和关系以帮助访客实现自我构建。该内涵的界定鞭辟入里,影响至整个文博领域日后与阐释相关研究的话语体系,并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不断得到印证。第二个权威定义由美国国家阐释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19]提出:“阐释是一个以任务为基础的沟通过程,在受众的兴趣和资源固有的意义之间建立认知和情感联系。”[20]此定义揭示出阐释的内核是让资源与受众建立联系,并明确阐释即为一种沟通方式。2013年哈姆以美国国家阐释协会的定义为蓝本,并借鉴蒂尔登的目的论,提出:“阐释是一种基于使命的沟通方式,旨在激发受众发现个人意义,并与实物、地点、人和概念建立个人联系。”[21]从该定义中可获悉,哈姆同样肯定了阐释就是一种沟通方式,同时围绕沟通问题,吸纳了美国国家阐释协会的任务构成和蒂尔登的目的主张,并增补了任务导向。尽管这些定义具备排他性的稳定要素,但主要适用于美国国家公园等自然资源机构。博物馆虽与之同属非正式学习场所,但在传播载体上有所不同,为特定空间内对物载信息的形象传播。因此,尽管两者指向的内涵趋同,但实际略有差异。笔者曾撰文指出,博物馆领域的阐释是指采用某种沟通媒介,向观众传播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过程[22]。但目前看来,该定义在突显观众主体性,特别是在参与方式和目的上稍显不足。因此,笔者主张将定义修正为:一种立足博物馆使命的沟通过程,在该过程中博物馆依托博物馆物与观众建立联系,促使其构建个人意义。此处的博物馆物既包括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中具备三度空间的实物展品和用以揭示其信息的辅助展品,也包括科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等博物馆中再现过程化现象[23](通常针对非物质信息)的设施设备。从阐释概念中不难发现,观众不再是权威事实或观点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个人意义的主动构建者,但该意义也可能是不在预期范围内的全新意义。
(二)博物馆领域的阐释规划界定
阐释规划的相关讨论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美国境内两大现象的出现而生成:公众开始重视环境并获得认知提升,联邦立法授权公众参与土地使用的规划和决策[24]。典型代表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U.S.National Park Service),其阐释规划的辉煌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25]。例如,1965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部《阐释规划手册》(Interpretive Planning Handbook)问世;1988年,强化阐释规划目标的《阐释的挑战》(The Interpretive Challenge)付梓;1996年名为《阐释规划》(Interpretive Planning)的《阐释和游客服务指南》(A Guideline for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Services)出版,提出针对公园的综合阐释规划(comprehensive interpretive plans),包括长期阐释规划(a long-range interpretive plan)、年度实施规划(annual implementation plan)和阐释数据库(interpretive database)。可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阐释规划方面独领风骚,因此数以百计的户外休闲和自然资源机构等后来者纷纷追随,相继仿效制订阐释规划。由于博物馆与此类机构性质类似,都旨在达成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所以也跃跃欲试。2005年,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组织了一场全国性博物馆阐释规划座谈会[26],会议围绕博物馆阐释规划的内容和实施展开讨论,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未出台任何官方意义的文件。随着丽莎·布罗许(Lisa Brochu)的《阐释规划:成功规划项目的5-M模型》(Interpretive Planning:The 5-M Model for Successful Planning Projects)和约翰·维佛卡(John Veverka)的《阐释总体规划》(Interpretive Master Planning)等专著的诞生,博物馆领域的阐释规划开始沿用环境教育、休闲研究和阐释服务等领域的阐释框架。
就博物馆阐释规划而言,其研究史中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无外乎2008年由《博物馆教育杂志》(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策划的《博物馆阐释规划》专刊。该杂志在第33卷第3期推出了名为“机构的各种阐释规划”(Institution Wide Interpretive Planning)专题,分别从综合和总体阐释规划、转型与阐释、整合阐释规划、阐释规划的内容、评估及资源等方面展开探究。同时相关著作接连问世,并经历了由著作的内容构成到围绕该专题著书立说、由少量提及到高度聚焦讨论的发展历程。首先是阐释规划在著作的部分章节有所涉及。如1994年首版的《博物馆手册》(The Handbook for Museums)于第10—12章讨论了一般阐释、特定对象的阐释和博物馆教育[27];2005年出版的《吸引人的博物馆:为观众的参与开发博物馆》(The Engaging Museum:Developing Museum for Visitor Involvement)一书,在第四部分《参与的规划:利用阐释发展博物馆陈列及相关服务》论述了有效阐释在博物馆展示中的作用[28];2006年面世的《博物馆文本:交流框架》(Museum Text:Communication Frameworks)探讨了文本如何通过恰当的语言选择、观点表达等与观众有效沟通;2007年编著的《原则与实践:作为学习机构的博物馆》(In Principle,In Practice: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一书的第二部分《让受众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包含有针对科学教育的阐释规划[29];同年《创造伟大的观众体验:博物馆、公园、动物园、花园和图书馆指南》(Creating Great Visitor Experience:A Guild for Museums,Parks,Zoos,Gardens,&Libraries)问世,启发我们思考博物馆如何设计受欢迎且更具价值的观众体验[30];2021年的新作《阐释遗产:规划和实践指南》(Interpreting Heritage:A Guide to Planning and Practice)在第三章专门论述了阐释规划[31]。其次,博物馆界出现聚焦阐释规划的专门出版物,如2003年苏格兰博物馆委员会(Scottish Museums Council)推出《阐释规划导论》(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Planning)、《有效阐释规划的规划》(Planning for Effective Interpretive Planning);2013年玛塞拉·威尔斯(Marcella Wells)等人的专著《博物馆的阐释规划:在决策中融合观众的视角》(Interpretive Planning for Museums:Integrating Visitor Perspectives in Decision Making)问世,主张对观众体验做出规划,同时将观众研究整合至阐释规划中[32]。
综上,阐释规划已悄然被引介至博物馆领域,并逐步在各项工作中掀起波澜,但尚未蔚然成风,主流研究和做法仍是追随环境教育、休闲研究、阐释服务等领域。那么究竟何谓阐释规划?尽管其定义远不及阐释那么明确清晰,但笔者仍试图对其进行梳理和廓清。根据出处的专业性和领域的相关性,笔者同样选择了三个较为重要的观点。一是来自美国全国阐释规划座谈会,该会将阐释规划界定为“一份书面文件,该文件概述了博物馆希望通过各种媒介(如展览、教育和出版物)传达的故事和信息。它可能包括该机构的阐释理念、教育目标和目标受众”[33]。二是出自《阐释规划:成功规划项目的5-M模型》一书,其认为阐释规划是指“将管理需求、资源,与游客的愿望和支付能力(时间、兴趣和/或金钱)结合起来考虑的决策过程,以确定向目标市场传达信息的最有效方式”[34]。三是威尔斯等在汲取先贤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博物馆阐释规划是指“一个深思熟虑、系统化的过程,用于以书面的形式思考、决定和记录教育和阐释计划,目的是为观众、学习机构和社区提供有意义和有效的体验”[35]。可见,上述观点分别将阐释规划视为一份文件或一个过程,但都旨在将受众和机构资源相结合,使其传播的信息能对观众有效和有意义,事实上它们都是机构系统规划的结果。笔者在采撷这些观点内核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境提出博物馆的阐释规划是指“一份书面文件(有时是一个过程),是博物馆基于使命的系统化决策结果,该文件思考、决定、记录如何借助各种媒介让博物馆物与观众建立联系,以促使观众理解其传播的信息并构建个人意义”。
(三)阐释及其规划的理论依据:“哲学诠释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
通过溯源可发现博物馆阐释及其规划的理论基础与多个学科相关,包括哲学、传播学、发展和认知心理学、教育学、娱乐和休闲科学[36],它们都将为该议题的探索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借鉴。
首先,与其最具相关性的是“哲学诠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脱胎于圣经注释和古典语文学,与神学、哲学、文学等学科有关的学说[37]。“诠释学”这个词出现较晚,大约在 17 世纪[38]。不过在西方历史上,诠释学的工作始终存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39],“只有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和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才能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40]。1960年,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指出,哲学诠释学探讨的问题是理解和对所理解东西正确解释的现象,而非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特殊问题[41]。所以哲学诠释学说到底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理论。尽管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使诠释学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理论,但并未超出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尚属于古典的或传统的诠释学[42]。然而海德格尔及其继承者伽达默尔却将该问题的讨论引至本体论,转而探讨“理解是什么”。伽达默尔提出“诠释学的动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43]。综上,从哲学诠释学的内涵和方法,可获得对博物馆阐释的两点认知:一是博物馆物也属于诠释学探讨的对象,因为诠释学研究对象不但包括文本或精神活动,还被扩充至对历史、艺术品和文化的处理;二是博物馆阐释的重点在于理解,涉及翻译和解释。翻译是指把不熟悉的物的语言变成熟悉的人的语言;解释是对晦涩难懂的内容的转化,使其从陌生的世界进入熟悉的世界。通过翻译和解释,结果是语言或内容被理解,即“视域融合”。
其次,与“建构主义教育学”研究内容不谋而合。每一个体都是被社会化塑造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成为解释学循环的生成力量,所以受众拥有的新想法、概念及其意义是建立在现有知识和期望的基础上,而这即为建构主义教育学所聚焦的问题。稍有不同的是建构主义教育学更侧重主体本身,而阐释学则重视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以实现资源如何更好地为主体所用。罗伯特·米尔斯·加涅(Robert Mills Gagne)和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指出外在信息和内部思维之间应建立“联结”[44]。戴维·保罗·奥苏贝尔(David Pawl Ausubel)对这种联结作了深层探讨,指出教师需要提供更为高级的陈述,关键是要在陈述者和学习者已有知识之间架起一座实现认知的“桥”[45]。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k Bartlett)创造的图式(schema)概念对理解该理论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指对个人当前知识进行组织以便为未来理解创建框架。让·皮亚杰(Jean Piaget)使用了该术语,认为图式是针对物体的某些(生理的或心理的)动作的心理表征[46],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他指出认知如同一个致力于平衡的自组织系统,主体若要同化一种新知识,必须让其思维方式顺应情境要求[47]。以上学者的观点各有建树,但同时也呈现出共同的局限,即把学习看作一种内在过程的结果[48]。与皮亚杰同时期的利维·维果斯基(Lev Vygotsky)就此进行补充,主张在社会文化框架下探究儿童的认知发展[49],外在环境因而得到重视。然而维果斯基的观点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美国心理学界关注。综上,建构主义教育的优势在于主张学习不是感官刺激在头脑里留下的印记,也并非特定环境下的反射结果,而是一种主体自主的活动。由于该优势尤其适合自由选择的学习环境,所以博物馆领域的学者先后对其展开讨论并成为其拥趸者。1995年,洛伊斯·H.西尔弗曼(Lois H.Silverman)提出“意义创造”的概念,在博物馆界引发轰动,主张应积极支持、促进和增强博物馆中可能存在的多种意义,并将人的需求纳入展览目标和机构使命[50]。而将建构主义教育学引入博物馆界的扛鼎之人是乔治·E.海因(George E.Hein),他在《建构主义博物馆》(The Constructivist Museum)一文中指出,考虑到博物馆观众的年龄跨度大,所以建构主义作为博物馆教育的基础尤为恰当。该理论要求我们将重点放在学习者身上而非学习的学科,这对博物馆而言,意味着把重点放在观众而非博物馆内容上,建构主义博物馆主张使用个性化方法为各类学习者在头脑中创造意义提供机会[51]。盖亚·莱因哈特(Gaea Leinhardt)和明达·博伦(Minda Borun)等在研究中还强调了博物馆空间及其体验有助于促进家庭等的对话,以达成学习[52]。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缺陷可能对博物馆阐释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强化认知、弱化情感,强化内在、弱化环境,强化运算、弱化情境。
二、阐释及其规划在推动中国博物馆转型中遭遇的困境
既然阐释及其规划是博物馆由藏品导向向公共服务导向转型的有力推手,同时诠释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也为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那么为何该新议题在我国博物馆界始终未迸发出强有力的生命力与冲击力,进而引发热议共鸣?笔者认为究其因,目前尚存在一些特殊困难。
(一)理念上:重视博物馆物的信息传播,而忽视观众基于信息传播的实际获益
随着国际博物馆界的理念由藏品中心向观众至上转变,博物馆不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为了公众而收藏、研究、展示”[53]。被动参与变革的中国博物馆虽也开始意识到这种转变,但仍未通过重新调试来适应由公众需求驱动的理念变革,根源在于我国“为物而物”的旧传统与“人利用物”的新需求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观众与博物馆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被人为分割,博物馆更在意的是对于物的呈现或物相关信息的输出,而非观众能否从博物馆物中获益及其获益程度。为解决该矛盾,我们应从理念上将“如何才能让人更好地理解物”置于首位。
(二)技术上:我国博物馆阐释及其规划方面的专业能力亟需提升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数量激增,展览、社会教育等各项业务规模扩大,但多数情况下博物馆对观众的受益情况不得而知。回顾“以观众为中心”理念的诞生历程,我国基本停留在公共服务和传播方式上的“以观众为中心”,还未真正企及深层,即在物及其所载信息的研究、转化和重构中奉行“以观众为中心”。因此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亟待提升,而阐释及其规划是该能力的重要构成。这种技术最早诞生在美国博物馆界,近年来美国博物馆不断厘清规划的定义,提出规划的多种视角并将其付诸实践,业已形成阐释规划的要素、框架及实施步骤。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University of Colorad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为例,该馆拥有超过400万件藏品,但三个展区没有统一的主题或使命。所以为找准定位和观众群,以明确自身使命和观众所获体验,2005年该馆开始着手制订阐释规划:首先由公共部门人员完成,再经主管验收并提交全体员工审核和批准。随着规划问世,馆方确定了资源定位、观众体验的优先顺序。在该规划被采纳一年后,公共部门又对其重新审定[54]。
(三)制度上:我国博物馆包含阐释规划在内的规划体系尚待建设
虽然制度建设会面临可能预见的利益冲突,但却能通过廓清权责、优化程序等来节约成本、提升效率、激发创新,以释放“红利”。然而当前“因物而物”的旧传统使得“翻转式”的制度创新遭遇极大障碍,同时现有管理体制也使制度创新的意识弱化、实践受挫。在制度建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规划体系建设,该体系包括使命、宗旨、长短期目标以及阐释规划。现有规划侧重于具体业务的落实安排,而非高屋建瓴的价值定位与导向。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注重展教做什么、怎么做,却忽视为什么,即重视方法论,却对认识论和本体论漠然视之。美国自然资源机构近年来在阐释规划方面成绩卓著,尤其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这方面最为突出。《阐释规划手册》《阐释的挑战》《阐释规划》等相继出版,使规划有章可依,为其创新提供持久动力,也为行动带来可靠预期。正因如此,博物馆界将其做法引入并断言:深思熟虑和系统的阐释规划必不可少[55]。
三、探究阐释及其规划以推动中国博物馆的当代转型
尽管阐释及其规划在推动我国博物馆转型中遭遇三大困境,但我们已不能再将这场“由藏品到观众”的转型视为一种超然,因为其“与社会力量所形塑的财富、知识和品味等多因素紧紧纠缠在一起”,显然已势不可挡[56]。为此,亟需在破解转型困境的基础上,为转型寻找可能的治世良方,笔者认为对阐释及其规划议题的探究便是促成转型的不二法门和有力举措。以下,笔者将从阐释模型的搭建、阐释规划内容框架的设计两方面寻求解决之道,并主张将前者贯彻至后者之中。
(一)搭建博物馆阐释的“六要素模型”
在阐释研究领域,被众多学者公认的模型是TORE。TORE是指阐释的基本要素,分别是:有主题(themetic)、经过组织(organised)、有相关性(relevant)和有趣味(enjoyable)[57]。博物馆阐释是诸多阐释现象之一,和其他现象一样都旨在鼓励人们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58]。所以此四大要素可为博物馆阐释模型所用。同时,博物馆阐释也具有普遍性之外的个殊性,最大的差异在于传播媒介的迥乎不同。所以笔者还借鉴贝弗利·瑟雷尔(Beverly Serrell)的展览评价体系(judging exhibitions: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excellence)[59],以及《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中的“教育与藏品阐释”(edu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60],提出适用于博物馆的阐释要素。之所以要参考这两大来源,是因为前者判断展览的优劣与否是建立在展览能否满足观众高质量体验的前提下,其历时约4年,经过12次反复测试[61];后者提到的“教育与藏品阐释”是博物馆工作的核心,尽管在最佳做法上较难达成一致判断,但依然能概括出卓越阐释的特征。综上,笔者认为博物馆阐释模型包含六大要素:主题性、舒适性、组织性、相关性、趣味性、评估性。
第一,主题性。主题可使博物馆阐释具备清晰的想法,为征集藏品、开展研究、策划展览、实施教育等提供取舍依据,以避免决策两难。第二,舒适性。博物馆需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至博物馆物的文化意义,若要实现该目标,首先应在身体、认知和情感上令人舒适。第三,组织性。优秀的博物馆阐释通常是经过组织的,这样受众在理解时就不会耗费过多精力,博物馆传播的信息、思路与意图也更易于被观众掌握。第四,相关性。阐释应能与观众了解的事物相关联,这在建构主义教育学中已有过详述。大卫·拉森(David Larsen)为此创造出一个名词“普遍概念”(universal concepts),认为这些概念与所有人都能产生无形或象征性联系,包括爱、恨等极端情感,生死、饥渴等生物需求,以及对悬念、宇宙等不确定性的迷恋[62]。有时并非博物馆呈现的信息不够完整,而是在于它能多大程度与多数人建立关联。第五,趣味性。博物馆的成功阐释通常是有趣的、能吸引人的。趣味性并非简单等同于阐释轻松好笑,事实上即便有些可怕且伤感的阐释也能吸引观众的注意,让观众沉浸其中。第六,评估性。博物馆的阐释成功与否,最终的衡量标准并非取决于博物馆的输出,而取决于观众的获益,获益情况通常需借助科学评估。观众研究与阐释工作息息相关,它们皆以观众为本,前者聚焦于观众行为、心理及体验效果研究,后者探讨如何帮助观众构建意义,所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
(二)设计博物馆阐释规划的内容框架
阐释规划已步入博物馆学界和业界,其说到底是主动指导博物馆进行解释的文件[63]。正如前文所述,《阐释规划》一书根据时间将综合阐释规划分为长期阐释规划、年度实施规划和阐释数据库[64]。威尔斯根据阐释深广度提出区域阐释规划、阐释总体规划和项目阐释规划三级框架[65]。波莉·麦肯纳-克雷斯(Polly Mckenna-Cress)曾将“展览大纲”称为“阐释框架”[66]。从机构层面看,上述观点基本都涉及综合阐释规划(又称“阐释总体规划”),而该规划属于布局谋篇的综合定位和整体导向,所以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此类规划。参与者通常包括博物馆管理者、展览内容策划者和形式设计师、教育人员、观众服务人员等。
威尔斯基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将综合性阐释规划的内容概括为两方面[67]:第一是规划基础,包含公园用途和意义、阐释主题、游客体验目标/游客体验声明、其他基本要素、现有条件和游客描述;第二是针对特定服务和媒体的目标和建议,特定服务和媒体包括个体服务、正规教育服务、阐释媒体、阐释设施,注重游客体验、可读性、形式外观、感知有用性。可见,阐释规划既要呈现对现有条件的系统梳理,又要将现有情况和目标建议联系起来进行逻辑分析。成功的阐释规划能提出有助于理解博物馆的合理且具体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来自对规划的目标、现状等清晰提炼与中肯剖析。
美国博物馆教育实务专家贝斯·B.施耐德(Beth B.Schneider)围绕休斯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Houston)制订的阐释总体规划,论述了其阐释规划的重点、内容和项目[68]。她指出阐释规划的重点是为观众提供进入通道,让他们能在博物馆里观察、思考、理解、欣赏和发现意义,包括明确观众、邀请其参观、欢迎观众并提供机构信息、为媒介阐释提供方向、鼓励观众重复参观并就体验作出反馈等五项内容,囊括的项目有展览、教育资源、网站、博物馆内外项目、在线聊天版块、互动空间和实践材料等。可见,施耐德将包括展教在内的几乎所有业务都纳入美术馆的阐释范围,内容主要集中在为观众提供机构信息、为阐释指明可能方向、鼓励观众前来并积极给予反馈。
综上,通过对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美术馆阐释规划的实践分析及观点借鉴,笔者认为博物馆综合阐释规划(阐释总体规划)的内容框架可由两大版块构成:规划的条件和基础、阐释项目的目标和建议。首先是规划的条件和基础。明确博物馆的使命、愿景、长短期目标、阐释主题、观众描述、目标观众、现有条件、相关规划工作和其他背景信息,其中的观众描述和目标观众可借助观众研究成果。其次是阐释项目的目标和建议。阐释项目涵盖藏品、展览、教育活动、网站、文创、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等博物馆可利用的所有方式,博物馆应规定这些项目的目标,并根据现有情况提出建议。除展览按内容阐释与形式阐释分类之外,其他项目可以观众类型为分类标准,如教育活动可分为亲子、学生、教师、老年、残障、成人等活动类型。在拟定目标和建议时,应注意将阐释模型的六要素融入展教等业务。
四、结语
虽然阐释及其规划诞生和发展于西方博物馆界,但对西方博物馆而言,其自身也正经历着“开眼”向其他学科和机构主动学习的历程,因为它们敏感地觉察到阐释及其规划的内涵和价值对博物馆当代转型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为此,我国博物馆界亟需将阐释及其阐释规划这一新议题纳入视域,对其变革中产生的客观结果作出全面性反思和本土化创新。本文在追溯阐释及其规划的定义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尝试破析目前其在我国博物馆界推行过程中所遭遇的三大特殊困难,由此提出我国博物馆阐释的模型和阐释规划的内容框架,以期为博物馆真正走下“神坛”、走向“公共化”和“世俗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69]。
观众带着各自的入门故事走进博物馆,把这些故事置于自身认知加工的背景之中,就构成了博物馆环境下建构主义学习的哲学基础。无论是展览还是教育活动,无论是实体展品还是数字展品,都会与观众构建起熟悉或不熟悉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的总体理解[70]。当前博物馆正处在“物人关系”的转型时代,阐释及其规划这一新议题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并确信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对关系的重建能力,即将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东西的能力正在增强,任务也更为紧迫。正如比尔·布朗(Bill Brown)所言,事物只有在重视它的社会才能作为对象存在[71]。研究阐释及其规划议题有助于博物馆依托物促成观众与历史、权威和偏见的公平对话。不可否认,步入博物馆的每位观众都携带着自身的认知“地平线”,这既是他们认知的全部范围,也是全部局限。博物馆试图帮助他们跨越历史的差距、文化的差距、人与人的差距,“让被认为独自存在的视域发生融合”[72]。但必须明白的是,理解始终在路上,因为理解在阐释过程中会不断被颠覆和更新。为此,阐释及其规划还应在“社会之中”,需要立足社会需求,在使命导向下不断调整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