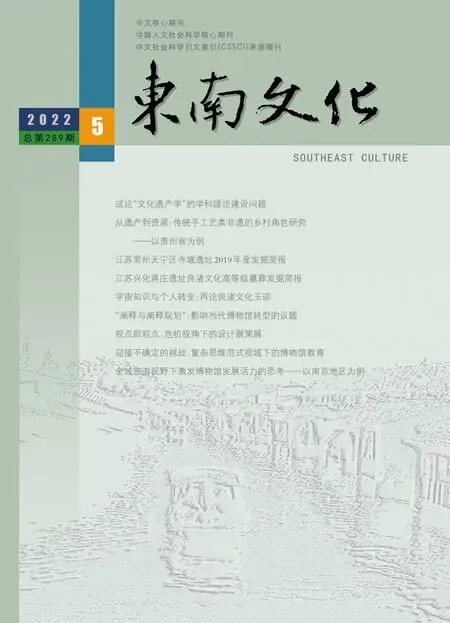浅析“特修斯之船”悖论视角下的文物
2022-04-06龚钰轩黄永冲乔成全
龚钰轩 黄永冲 乔成全 闻 豪
(1.江苏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江苏镇江 212100;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物保护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安徽合肥 230026)
内容提要:“特修斯之船”悖论及其延伸是经典的哲学问题也是古老的思想实验,这一悖论及其延伸也可以用于探讨对文物价值的认知。文物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非实用功能,对文物开展保护和修复,虽然看似如“特修斯之船”一般是对破损部件的替换,但在实际操作中,需严格遵循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理念和原则。文物的修复要在充分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保护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真实、完整地呈现和传承文物的信息与价值。
公元1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提出了著名的“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悖论[1],作为世界“十大悖论”之一,其内涵反映了人类最为古老的思想智慧。“特修斯之船”悖论描述了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名为“特修斯”的船,在不间断地维修过程中,只要一块木板腐烂,就以新的木板来替换,从而确保其能继续航行,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而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是原先的船?许多哲学家都对类似的问题作了相关探讨。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可以用描述物体的“四因说”中的“质料因”和“形式因”来解答这一问题。“质料因”是指物质的构成材料;“形式因”即物质的设计和形式,它决定了物体的形态[2]。即便“特修斯之船”的构成材料发生了变化,但船的设计和形式未改变,因此,它还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此后,英国近代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这一悖论作了延伸,他提出,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的老部件来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特修斯之船”悖论可以在多个领域被应用于探讨不同的问题。例如,在经济学上,可以用于探讨企业在经历了不断被并购和更换东家的过程之后,即便未更改名称,是否仍是原来的那家企业;在医学上,可以用于探讨人体在不间断的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之下,是否仍是原先的那个人[3]。近年来,“特修斯之船”悖论也偶见被应用于探讨文化遗产领域的相关问题。张金风和陆继财将“特修斯之船”的思辨方式引入对于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思考中,探讨了文物保护中的“可识别性”原则[4];姚东升和邵明基于“特修斯之船”悖论讨论了“同一性”问题,并将“同一性”的概念应用于历史建筑保护中[5]。而“特修斯之船”悖论及其延伸也可以用于探讨对文物价值的认知。
文物是人类从事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和遗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与“特修斯之船”相似,文物在历经了成百上千年之后,为了尽可能延长其寿命,后人需要采取适当的材料和方法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和修复。在这个过程中,常会由于保护需要对文物破损、毁坏的部分加以补缺和替换。那么文物在本体被不断修复、部件被逐渐更换之后,它还是原来的那件文物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基于对“特修斯之船”悖论的解读,厘清“特修斯之船”与文物的异同之处,并通过明晰文物的价值,辨识其身份特征。
一、“特修斯之船”悖论的意义
在哲学上,“特修斯之船”常被用于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探讨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同于其所有组成部件之和。有观点认为,所谓的“特修斯之船”,并不是指某个构件或某种状态,而是将“特修斯之船”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包含了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态,以及人们对“特修斯之船”的特殊记忆[6]。因此,“特修斯之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所代表的意义。换言之,这艘船的构件是否被替换已不再重要,而人们意识中的这艘船还是他们所认知的那艘船,无论其构件如何被更换,人们在描述它时依旧会称作“特修斯之船”。而用被替换下的旧船板和部件重新组装的船,虽然还保留了原先的结构,但它和“特修斯之船”已不具有时空连续性,因此,重新建造的船被视为另一艘船,而非人们印象中的“特修斯之船”。
“特修斯之船”悖论不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思想实验,而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事物跨时间同一性问题。这个悖论中包含了三个不同身份的“特修斯之船”:最初建造完成的“特修斯之船”;被逐渐替换了零部件的“特修斯之船”;悖论延伸中所提及的以替换下的老部件重建的“特修斯之船”。原始的“特修斯之船”其身份毋庸置疑,它必然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悖论模糊了空间概念即“特修斯之船”的状态,也模糊了事物变化的特性,即从哲学层面来看,即使不更换部件,今天的“特修斯之船”与昨天的“特修斯之船”也是有所区别的。“特修斯之船”实际上已成为后来一系列不同时空下“特修斯之船”的符号,而是否仍可以用“特修斯之船”来命名,则需要探究不同时空下这些“特修斯之船”间的本质联系。
伴随着船板的腐坏,在不间断的维修过程中,被替换下来的船板不是以船的形式,而是以“构件”的形式存在,但不断被更换了构件的“船”却一直承载着“特修斯之船”的基本属性,继续执行航行、运输货物等任务,这些便是“特修斯之船”在历史和时空中留下的印迹,这些不间断的印记维持了其时空连续性。因此,即便“特修斯之船”所有船板都被更换成新的船板,但整个船在结构、功能和属性上均未因新旧船板间的细微区别而发生改变。所以,这艘船依旧是“特修斯之船”。就如人体的新陈代谢,虽也是不断以新物质替换旧物质的过程,然而今天的“你”与昨天的“你”依旧是同一个“你”,不会因为不断发生的新陈代谢而使得“你”变成另一个人[7]。反之,被替换下的旧船板由于以单一“构件”而非一艘完整的“船”的形式存在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这些“构件”并未参与“特修斯之船”的航行、运输等活动,所以其根本不具备“特修斯之船”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被换下的构件与原先的“特修斯之船”最本质的区别。因此,重新组装而成的船已不再是人们认知中的“特修斯之船”,而是一艘由特修斯之船的原部件组装而成的“新船”。
二、“特修斯之船”与文物
悖论中的“特修斯之船”与文物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特修斯之船”是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根据人们的航海和运输需要,采用当时的材料和技术建造而成的用于航行的船只。而文物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由某个特定时代的一定人群根据当时的生产、生活等需要,运用所能得到的材料和掌握的技术制造出来的。因此,文物和“特修斯之船”在它们最初诞生的时代具有相似的意义和价值,并且都承载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但文物与“特修斯之船”也有不同之处。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特修斯之船”作为一艘航行、载货的船只,无论在哪个时代,它的价值都在于其使用价值,只要还能航行,它就依然具有存在价值;而文物则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大多已丧失了其原本的使用价值,但与使用价值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这些价值通常体现在文物的制作材料、工艺,以及使用痕迹的真实性和由这些真实性构成的完整性上。
无论是“特修斯之船”的维修还是文物的保护修复,根本目的都是延续(或保护、维护)自身价值,即“特修斯之船”维修的目的是延续其使用价值;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目的则是尽可能保留文物原有的材质、工艺、使用信息,并延续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特修斯之船”可以通过不断更换船板来延续其使用价值,而替换的新船板即使从材质到外观都与原先的船板存在差异,但只要能够确保船的航行功能,即便所有原先的船板因破损而最终被一一替换掉,它依旧是人们所认知的“特修斯之船”。而文物虽然也可以采用新的材料通过修复来补缺和更换糟朽的部件,以延长文物的寿命,但人们不禁会质疑,这种修复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减少文物的历史、科学价值?从整体上来看,文物本体材料的不断残朽将最终导致文物的失稳,甚至对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因此,多数情况下对文物进行修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修复才能让文物的诸多价值更长久地传承下去。并且,文物的修复工作还需遵循严格的修复理念和原则,确保在“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最小损伤”等基本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恢复文物原貌,并保留其信息和价值。以故宫的修缮为例,在对寿康宫室内地面进行修复时,为了遵循“不改变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避免整体拆除换新,仅对受环境因素影响和人为损坏严重的金砖采取了保护措施,针对局部缺损和开裂等病害现象,以金砖砖粉配合胶黏剂进行修复[8];在对故宫端门内残损严重的御路石进行修复时,则采用了原材料石粉进行局部修补,以确保在保留文物本体石材的同时,增强其抵抗外力侵蚀的能力,并尽可能保持文物外观色泽的一致[9]。而破损古代纺织品的修复也不例外,通常会尽可能选用与文物本体材质相同的纱线,采用传统的染料和染色工艺染出相近的颜色,进而使用对纺织品本身干预较小的针线法,将织物破损的部位精心缝制、修补。由此可见,文物的修复与“特修斯之船”的维修从目的到实际操作都存在较大差异,文物的修复工作需更为审慎和严谨。
三、基于“特修斯之船”悖论探讨文物的价值认知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因此“特修斯之船”与文物也不例外。物质材料在保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损坏,这就决定了“特修斯之船”船板的更换是一个必然过程,而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也是延长文物寿命的必然趋势。基于“特修斯之船”悖论,假设随着文物本体材料的老化、腐蚀,在不间断的保护和修复过程中,只要一部分糟朽了,就以相应的材料来修复,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最初的材料都被完全替换掉,而最终呈现的这件物品是原先的那件文物还是一件完全不同的物件?如果不是原来的文物,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是原先的文物?如果采用替换下的老部件重新制作一件“文物”,那么这两件“文物”哪件才是真正的文物?
为了辨识文物的身份,首先,可将整个部件替换的过程视为文物不间断修复的过程,每替换一个部件都等同于开展了一次文物修复工作。因此,每一次修复都需具备真实而完整的修复档案,记录所使用的材料和修复过程。从该文物经第一次修复至最后一块原部件被替换,文物便完成了修复信息记录全过程。文物都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制作而成的有形的客观存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物并非像纪念碑那样,在创造之初就具备了纪念价值。大多数文物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只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器,或是供人们欣赏娱乐的艺术品。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获得了后天赋予的价值。岁月在文物的本体材料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不论是最初的使用痕迹,还是历经沧桑后残损的痕迹,甚至是在使用过程中修补的痕迹,都见证着文物的历史价值,记录着这些器物由“生活用品”成为“文物”的历程。文物的艺术价值也不单指其具备的审美功能,或是为后人提供的美学研究资料;与历史价值相似,文物的艺术价值还包括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文物所呈现出的“古旧感”,即文物的韵味,如青铜器上的无害铜锈、古书画上的点点斑驳、古建筑上的破旧痕迹等。因此,文物原本的材料也成为体现文物真实性的身份标志,在历史进程中承载了更为重要的价值。当文物原本的旧材料被完全替换掉,而如果新的材料未历经岁月沧桑,也未留下任何历史的印记,那么这件文物就丧失了原本的价值,不能再被称为“文物”,而是一件复制品。虽然复制品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件文物,但也并非毫无用处。由于它是按照文物原先的形制、材质、纹饰等,采用传统的技法制作而成,所以在转录文物信息的同时,它可以作为文物信息的新载体,承担起传播文物信息的重任,通过展示使文物信息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发扬和传承,从而协助文物发挥其作用的永续性。
从文物的修复档案中追溯完整的修复历史便可进一步回答,这件文物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不再是原先的文物这一问题。当修复对文物造成了足够大的改变时,文物将不再是原来的文物。但这种改变的界限实际上是模糊的,并未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基于文物的“完整性”原则,并采用整体和部分相结合、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来评判。文物的“完整性”并非指其在视觉上的完整度,本质上是指文物的历史人文信息保留了多少。这些信息包括直观的“显性信息”,如文物的尺寸、结构、形制等,以及需要通过研究来获得的“隐性信息”,即文物的制作工艺、规制礼制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当人们仅从关注外表和纪念价值的角度去欣赏这件文物时,无论文物原本的材料经修复后还剩余多少,只要存在,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新修补的材料相结合,成为一件复合体文物。相较原本完整的文物,这件复合体文物仍然是原先文物的唯一继承者,并且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件复合体来了解文物的尺寸、结构、形制等显性信息,因此,它依然可被视为原来的文物。但当我们将关注点聚焦于文物的材料,以期通过研究获取文物完整的信息时,则仅能将残余的本体材料视为文物的原来部分,修补的材料只是文物本体的复制部分。而当文物本体材料已所剩无几,且丧失了时代、工艺特点等表征信息时,这件文物便不再具有原本的重要价值和真实性。综上所述,探究经修复后的文物是否还是原先那件文物,就需要了解其具备表征信息的部分究竟是在何时被完全替换掉的,使得文物逐渐丧失了其身份特征。然而,这可能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而有可能是一段时间,并且是经过了多次的修复,逐渐改变了文物的身份。因此,只有在具备全面而详实的修复档案的前提下,每一次修复才能有理可依、有据可循,从而有助于真实而有效地辨识文物的身份。
依据“特修斯之船”悖论的延伸,如果用文物替换下的老部件重新组合成一件“文物”,那么这两件物品中哪件才是真正的文物?这便涉及“最佳候选者”理论,当两件物品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权衡[10]。于“特修斯之船”而言,其被替换下来的老部件已丧失了原本的使用价值,采用老部件重新组装的这艘船也已不具备航行功能,它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特修斯之船”,而是一件纪念品。因此,重新组建的船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然而,文物则恰恰相反,如上文所说,在历经成百上千年的岁月变迁之后,文物大多已丧失使用价值,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纪念物,其所承载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信息在当前时空中远大于原本的使用价值,而文物原本的材料则成为这些信息的载体。由此,文物的材料不仅只是其本身,更是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历史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匠人创作时的艺术风格、制作时的传统技艺,在特定时期的用途和价值,甚至是历经沧桑的使用痕迹等,这些都是记录在文物材料上的独特身份符号。文物信息的本质是文物实体客观存在的各类现象,其本身并不会表述,而是由人类通过材质的研究来解释这些现象。因此,由替换下的老部件重新组合的这件器物,由于保留有原本的制作材料,它才是真正的文物,是文物价值的真实体现,有助于人们认识和解读文物的信息。这就如同将支离破碎的青铜残片、陶瓷碎片重新组合成青铜器、陶瓷器,或是将断裂、脆化的书画残片重新拼接,使其恢复原样,这种“重组”其实是对文物的修复,而经修复后“恢复原状”的这件文物,若质地、体量、形制、纹饰、使用痕迹等都与原先的文物相同,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可被视为原先的文物。
然而,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尤其是古建筑、古遗址等,“特修斯之船”悖论的解读可能会有所区别。以始建于1929年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Barcelona Pavilion)为例,它是由“现代主义四大师”之一的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建造的,于博览会结束时拆除,后为纪念这一杰作所开创的历史先河,于1986年原址重建,并严格把控建筑质量和细节。然而,建筑家、史学家和评论家对于重建后的德国馆一直争议不断。部分赞同者认为,重建赋予了德国馆二次生命,使人们能够再次体验、欣赏和感受这一建筑史上的杰作;而批判者则谴责这一建筑为“冒牌货”,认为这样一件仿冒原先德国馆的建筑根本不应存在。也有学者将“特修斯之船”悖论引入对德国馆辨伪中,认为虽然德国馆的重建与“特修斯之船”的船板替换有相似之处,但“特修斯之船”船板的逐渐更替具有时空连续性,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物质的变化,“特修斯之船”的物质形态却从未消失[11]。因此,部件被全部替换后的“特修斯之船”仍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而巴塞罗那德国馆曾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长达56年,重建后的建筑应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建筑,而非原先的德国馆。这一观点又引起新的争议,假设当德国馆被拆除时立刻重建,是否就维持了其时空连续性?而从古建保护的理念来说,需要保留的究竟是建筑的材料、形象、概念,还是其他元素?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较为赞同兰斯·霍西(Lance Hosey)的观点,他认为保护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保留其材质,更是为了延长古建筑的文化属性,延续其历史、艺术价值[12]。德国馆的重建是为了还原古建筑实物,使参观者能够再一次亲眼见到、亲身感受这一文化遗产所带来的震撼,因此,重建的德国馆其身份不应被质疑。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曾访问过原建筑的参观者的肯定,再次参观重建的德国馆使他们对该馆的认识得以加深和拓展。由此可见,文物具有“不灭性”,物质不灭性决定了即便文物实体的形状不存在,但各种组成物质并不会消失,只是转化为其他物质,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文物信息可以通过物质的不灭而达到“永续”的目的。因此,尽管德国馆消失了长达56年后重新出现在巴塞罗那,但人们对这个建筑及其附带信息的认知,依旧停留在人们意识中最初的德国馆,并且这一认知不会减少,只会加深,所以重建并未影响德国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特修斯之船”悖论的延伸来辨识古建筑的身份——倘若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拆除时将建筑材料全部保留并运往他处,重新建造一座德国馆,此德国馆是否还是原先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也做了类似的探讨。曾有学者提出,若将希腊雅典帕特农神庙(Parthenon Temple)原本的大理石柱用现代复制品逐一替换,再将替换下的这些大理石柱运往英格兰,在当地重新组建一个帕特农神庙,那么这个帕特农神庙是真正的帕特农神庙吗?[13]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物都具有特定的地点,如可移动文物有埋藏地点或收藏地点,不可移动文物有建立、建造的地点。总的来说,文物都有它存在的地点,而某些文物一旦离开了具体地点,就会直接影响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可移动文物而言,所处的地点常会伴随其实体的移动而变化,由最初的生产地点到埋藏地点,再到出土后的收藏地点,但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文物本体材料未发生改变,就依然是原来的那件文物。而不可移动文物所在的地点则通常是固定的,且被视为文物身份的标志,例如我国四川乐山大佛、山西应县木塔等,人们对这些古遗址、古建筑固有的印象便是建造在那个特定地理位置的某个文化遗产。而大多数古建筑、古遗址完整性的内涵更为宽泛,不仅包含文物本体,还包括本体周边的历史风貌、人文环境等,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印证、不可分割的关系。换言之,这些文物所承载的信息中,地理环境因素所附带的文化因子与社会情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一旦脱离了原本的自然环境,文物的完整性便遭到了破坏,部分重要信息随之丧失,该遗址、建筑便不再是原先的古遗址、古建筑。综上,无论是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还是雅典帕特农神庙,一旦离开了它原本的地理位置,就不再是原先的那个不可移动文物。
四、结论
本研究基于“特修斯之船”悖论探讨了对文物的认知。根据文物自身特点和存在形式,结合哲学理论,阐述了文物的身份特征与重要价值。然而,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有别于一般物件,是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被重新制作或建造,这使得文物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非实用功能。对文物开展保护和修复,虽然看似如“特修斯之船”一般是对破损部件的替换,但在实际操作中,需严格遵循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理念和原则。文物保护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Venice Charter)就明确提出了“最小干预原则”,再如“不改变原状”“可辨识原则”等都明确规定和规范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实践中的行为准则。因此,在面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损坏程度的文物时,应以审慎的态度,在充分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保护方案,并严格遵守相关原则和规范,确保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并将文物的信息与价值真实、完整地呈现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