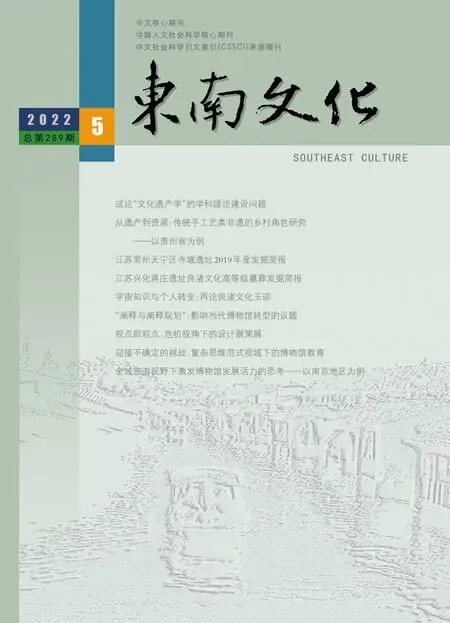试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问题
2022-04-06王刃馀
王刃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内容提要: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学科资格”及其建设是近十年来相关领域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它不仅与国家社会的文化资源管理功能直接相关,也与其作为科研行为进行管理的特殊性相关。“文化遗产”是否成“学”,首先要看是否有独立的研究视角与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文化遗产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技术“内化”关系,对遗产的界定往往源于其他基础学科的研究与判断,“文化遗产学”将全部遗产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遗产研究的核心内容应当是遗产价值的形成过程。遗产理论、遗产保护、遗产资源管理这三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涵盖我国未来建设“文化遗产学”的基本内容。
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文博、考古、人类学等领域中即开始出现关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讨论——它能否称得上一门学科,或仅仅是一种社会工作?如其能够称为学科,又应当怎样建设?曹兵武[1]、苑利[2]、孙华[3]、杨志刚[4]、贺云翱[5]、彭兆荣[6]、杭侃[7]、李菲[8]、刘禄山[9]等学者就这一话题进行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遗产研究领域自身所具有的分散性、交叉性、开放性、杂糅性、实践性等特点对其实现“独立”的学科身份似乎构成了一定的阻碍。人们关心的是,如果将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它是否能够“总括”众多已有的相关研究领域(如考古、古建筑、口述史、文保科技等),有无总括之必要,抑或只是一种基于各类已有学科而存在的“学科对话体系”与“文化资源管理机制”,因而并不必具备独立的学科立场?
直至2018年前后,仍有学者认为,如以“遗产”立“学”,那么,它只能是一种以保护遗产价值为根本目的的“保护学”[10]。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大致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从传统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来审视文化遗产研究领域,责求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另一种则希望从跨学科的角度来建构这一研究领域,而至于它是否能够独立成“学”则并不重要。事实上,在2020年前后,我国开设与文化遗产有关专业或课程的高校已经突破50个,近期又有一批工科院校增设了古建筑保护专业。如果将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类专业都计算进来,则这一数字可能会过百。在很大程度上,前述这些讨论所体现出来的仍旧是人们对“文化遗产”在知识系统性与学理建设方面的忧虑。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这场讨论恰恰说明,研究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文化遗产”能否被称为某种“学”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学科分类尝试,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的独立性与成熟度。学者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社会经济用途[11]、价值保护功能[12]、意识形态建构作用[13]、文化资源维系作用[14]、文化建设效应[15]等方面已经多有讨论,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文化遗产研究”能否成为所谓“学科”,可能并非仅仅取决于其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与技术实践工作,还要看它是否具备建构研究对象并探索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原创活力。准此,我们就必须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哪些问题才是该学科所探讨的基础问题,有无相对严密的研究范式可言?第二,它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关系如何,形成怎样的关联?第三,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其内部逻辑架构是怎样的?
一、文化遗产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及研究范式
“文化遗产”是否成“学”,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立的研究视角与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遗产研究领域中,对遗产本体及其保护技术的关注是唯一的研究旨趣[16],即研究者将遗产视为一种纯粹意义的“客观存在”,而将“人”与“社会”摆在与之完全对立的位置上看待。时过境迁,至20世纪80—90年代前后,西方哲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开始波及遗产研究领域,研究者开始着力探讨个体与遗址、地方、景观的关系问题。从这一时期开始,个体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不再被视为遗产客体的对立面,人类能动性和主观意愿在遗产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逐步被勾勒出来。“社会创造遗产并为当下所用”这一题目逐渐成为遗产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9世纪以来将遗产研究视为“保护科技研究”的单一性学科定位。“价值”也不再被视为一种遗产与生俱来的“天赋”之物。遗产研究对象形成的社会过程、社会动因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该领域新的焦点。遗产研究所关注的实践行为也不再局限于“保护”,它开始就遗产与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广泛的探讨。布里特·索力(Brit Solli)指出,能够为多数遗产学者所接受的观点是“遗产建构论”[17]——人们在对“过去”事物进行利用的过程中,不断对其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建构出服务于各类现实需要的“遗产”。哈里森将这一本体论反转过程界定为“去物质化”过程,并将其视为遗产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18]。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习惯于用“遗产”指代“过去”,“遗产”逐渐被浓缩为“过去”的标志、象征与等价物。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维度来看,遗产研究逐渐演化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如何通过建构与利用“过去”来服务当下社会所需要的学问。“遗产之用”或“过去之用”是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相关学术命题的中枢与纽带。格雷戈里·艾施沃斯(Gregory Ashworth)等学者将这一基础理论视角称为“今核范式”(the‘present-centered’paradigm)[19],其含义与中文语境下的“古为今用”相近。它是过去四十年当中西方遗产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范式,从这一范式出发建构出来的遗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20]:(1)遗产成因(社会心理诉求[21]、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22]、政治与宗教诉求[23]、社会现代性因素[24]);(2)遗产建构(遗产的物质性[25]、遗产建构行为的普遍性[26]、原真性与价值的建构过程[27]);(3)遗产利用(遗产资源的利用方式与利用过程[28]、遗产景观与地方含义[29]、认同与遗产记忆[30]);(4)遗产政治及伦理(遗产空间社会分层[31]、遗产权力与遗产政策[32]、利益相关方权利博弈[33]、遗产非物质性及情感伦理[34]);(5)遗产科技表现手段及其社会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如何利用‘过去’”逐渐成为遗产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在近四十年中,研究者对人类社会围绕“遗产”的阐释、遴选、规划、留存、保护、包装、消费、管理、破坏、注销等实践行为及相关社会机制进行了必要的阐释。研究者将社会建构“过去”与使用“过去”的能动性与主观意图作为立论基点,逐步消解了“价值天赋”等传统遗产观中的谬识。人们不再预设任何价值的先验合法性,而将其视作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行为的产物[35]。
综上,文化遗产研究在社科领域内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关键理论问题以及稳定的研究范式,其关心的主要问题有遗产价值的来源、遗产的归属、遗产使用与相关权益分配等。我们或许可以将“文化遗产学”界定为一种探索“当下”社会如何建构与利用“过去”的学问。社会既是遗产存在方式的归因,也必然受到各种遗产实践的影响。正如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所说,遗产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人们用这些“物”去“做了什么”,他们自己又在这种利用过程中“成为什么”[36]。而我们所熟知的“保护”,则仅是众多“遗产使用”行为类别中的一种而已。
二、文化遗产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如果“文化遗产学”的提法能够成立,那么,它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边界又该怎样划定?我们如何看待文化遗产与其他相关领域(考古、古建筑、景观等)缠夹不清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考古学”的构成方式,其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杂糅性或许并不亚于“遗产学”,而这也许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
时至今日,考古学已在其内部分化出各种借助自然与社会科学手段了解古代人类世界的次级学科领域。实际上,如从“通过分析物质材料了解古代人类世界”这一根本研究目标来看,考古学的属性从未改变过。我们所看到的考古学发展过程更多是考古学对其他学科的“借用”与“融合发展”,最终在其学科内部形成了稳定的话语模式——以“了解古代人类世界”这一根本目标为纽带,它已经完成了各类技术手段的学科“内化”。考古学借助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研究目标,而它与所借鉴的物理学、统计学、化学、刑侦科学、医学、材料学、建筑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仍旧保持着明确的学科界限——考古学与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统属关系。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学”的时候,仍有学者认为它应当是一种与其他相关学科具有某种统属关系的“上位”学科[37],或者担心它很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文理大综合”的状态。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
如前文所述,考古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构成一种“工具借用关系模式”。其他学科为其提供的既非研究目标,也非研究对象,而更多只是技术手段或论证模式。遗产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模式则与此不同。作为一门研究“古为今用”的学问,文化遗产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对其“过去”进行界定、遴选、管理、处置、利用的行为过程,以及这些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但是,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遗产行为对象”与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景观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存在高度的重合性。从“遗产行为对象”的含义界定与学术价值判定方面来说,多数依据源于上述相关学科领域,这种关系模式显然不同于考古学与其相关学科间的关系模式。威廉·威廉姆斯(Willem J.H.Willems)指出:“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而‘考古遗产’则关乎‘过去’在现实中的处境……之所以一个考古遗址甚至其全部景观都被称为‘遗产’,原因在于它们被赋予了价值。”[38]托马斯·F.金(Thomas F.King)则更为直接地将遗产建构过程解读为一种“认同”(recognize)过程[39]。“认同”是一系列由浅入深的重要性评判过程,包括:认知(文化含义)→认定(学术重要性)→认可(社会相关性)→认领(情感寄寓)→认养(留存保护)→利用(实现价值)。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过去的“事物”逐步被认定为属于某一群体的“事物”,亦即它们不再只是研究对象,而被赋予更为严格的社会群体性意义。遗产行为的本质是建构人群与“过去”(物质、非物质、实践)之间关联性的过程。当我们去探讨“遗产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技术“内化”关系。事实上,围绕每一类甚至每一处遗产,都存在着一系列建构活动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一个案例都会为遗产研究提供具体的遗产情境与研究素材。而对这些遗产时空载体的界定,则往往源于其他基础学科的研究与判断,如考古学研究对象为某一遗址设立的时空框架,人类学研究对象为某一古村落建构的宗族历史渊源。“文化遗产学”与各学科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实验室与培养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剧场与话剧布景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须结合每一个具体案例情境去重构遗产对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前述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工具借用关系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应当指出,将“文化遗产研究”等同于“文保研究”的看法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如前文所述,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学科,它并不将任何价值或重要性视为先验性的研究对象,相反,它看重的是价值形成的原因、过程以及影响。因此,价值建构本身即是其观察的重点对象,而保护工作是否开展、针对什么对象展开、留存到什么程度、措施实施到什么程度或利用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价值建构过程。不仅如此,各种对于“过去”的疏远、抵制、排斥、遗忘、“去价值化”现象也同样是这一研究领域所高度重视的。在遗产行为研究的天平上,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所谓“保护”。“文化遗产学”不仅要研究人们为什么要保护与利用,也要研究人们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不进行保护与利用——任何遗产态度都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感、学术认知、现实利益等诸多因素博弈与牵制的结果。如“文化遗产学”将全部遗产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就不可能只谈“保护”。简言之,“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范畴应当远大于“保护”本身。
三、文化遗产学科的“建构”问题
如欲将文化遗产研究视为一个学科,那么,应当如何建构其研究与教学内容?调查显示,从相关教材的设计方式与行业内部学术活动来看,文化遗产研究仍旧表现出一种较强的“世遗化”的态势,即在不同程度上向世界遗产权力机构的解释、表述、标准、政策趋同,遗产工作与遗产教育均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趋势。这一方面缘于世界遗产权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所建树的遗产名誉授予方地位;另一方面,各地的遗产管理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世界遗产报选机制奉为“遗产”研究对象本身。遗产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即是阐释既有价值分类、遗产分类、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及其运转规则,而非深入研究其背后的社会过程。近期高校编写的遗产学课本实际上仍旧停留在对于世界遗产体系现状的介绍与其价值取向的阐释方面。哈里森指出,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既有价值分类体系的研究上,而对于这些价值门类的形成过程却总缺少必要的关注[40]。
价值形成过程应当被视为遗产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遗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投射行为。文化遗产的形成过程本来即是一种“意义之网”[41]的编织过程。从最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伯姆(Eric Hobsbawm)与特伦斯·朗杰(Terence Ranger)等学者对社会传统发明过程[42]的研究开始,到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等学者对于遗产原真性、历史与过去的关系、遗产社会心理反思以及罗伯特·赫维森(Robert Hewison)、艾施沃斯、拉斐尔·萨穆埃尔(Raphael Samuel)、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学者对遗产利用现实动因的分析,再到史密斯对世界遗产权力结构、物质性的批评以及哈里森对于世界遗产既有二元结构视野的批评,研究者始终在寻找文化遗产最现实的社会处境以及社会创造遗产的真实动机。可以说,这一研究领域的活力主要是来自对遗产建构行为中所蕴含的能动性、情境、意义、价值等主观因素的不断揭示。
在世界遗产管理的工作领域中,在结构、内涵、标准、分类等各个方面的调整都与遗产研究领域自身的批判性与活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在社科领域的批判研究,也就不可能有遗产管理领域的任何进步。如欲将遗产研究构建为一门学科,它就不能只停留在对于分类及管理流程的介绍方面,也不能把遗产研究单纯等同于遗产保护工程或管理工作。那样,这种遗产研究即不可能获得成为一门真实学科所必须具备的辩证性与原创性。目前,我国的遗产研究工作仍旧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辨力量。在教学方面,它更多地将遗产分类、遗产管理流程与保护工程作为某种“成形”的知识体系或技能进行传习,这可能会导致遗产实践工作与社会科学理论的严重脱节。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遗产理论、遗产保护、遗产资源管理三者是遗产研究领域中的三个不同的研究方向。遗产理论研究以所有与“遗产”相关的人类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核心研究内容为价值形成过程、遗产建构与遗产利用,即在最广泛意义上探讨社会与其“过去”的关系问题。应当指出,这个研究领域并不以保护为预设目标或必然结果。其案例研究对象涉及从可移动文物到博物馆、景观、遗址、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口述史、文化传统等任何社会价值载体,所探讨的是在各种具体情境下存在的价值建构、遗产利用方式及其社会影响。遗产保护研究则主要包含社会政策、保护科技两个基础研究方向。前者主要在保护政策与规定方面进行阐发,探讨的是对不同类别遗产对象作为公共社会文化资源进行维系的社会需求与规则可行性;后者则主要是针对保护目标开展的基础研究,如土壤环境、腐蚀劣化机理、保护材料、传统技术等。遗产资源管理研究则是以具体的案例为研究与工作对象,以实现保护与管理效果为最终目标。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方向大致可以涵盖我国未来建设“文化遗产学”的基本内容。
四、结语
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中,文化遗产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建筑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都可能开设相关课程甚至专业。这反映出这个研究领域的实际分布状态和学科特点,即它目前仍旧是一门以遗产对象本身分类为专业设置依据的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类教研工作对保护技术能力培养的侧重以及在社科理论范畴中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遗产”作为社科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的出现率相对较低。换言之,将“遗产”作为一般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还不是社科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这也就意味着遗产研究的“原动力”尚未被激发出来。可以说,“遗产”在社科研究领域中的息声使现有的遗产教育在遗产思辨性培养上处于极大的困境之中,它正在逐步向应用型学科和管理型学科靠近。当我们回顾文化遗产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发现,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关键贡献主要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之中。而这中间最为重要的是被称作“去物质化”的遗产话语反转——人类社会创造遗产并为自己所用。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遗产这门学问不仅是关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门系统性学问[43]。在过去四十年里,“古为今用”逐渐成为遗产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范式,而在21世纪的今天,研究者也在进一步寻找突破这种范式的方法——如何利用遗产建设与服务未来[44]。相比于“立学”与否而言,遗产研究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息声则更令人担忧。
(近期,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其中直接以“遗产”命名的牵涉18个由大学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和4个交叉学科。值得注意的是,18个二级学科之上的一级学科几乎没有重复,涉及考古学、语言学、设计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艺术学、城乡规划、材料科学与工程等。这表明,在现在的学科设计语境中,有更多的固有研究领域开始从自身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关注“遗产”问题。4个交叉学科所涉及的一级学科情况较为单一,它们主要是来自于建筑规划研究领域。总体上,虽然教育行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遗产问题的杂糅性,但更多教育机构仍然选择在固有的一级学科框架内建构遗产研究领域。其中存在三个重要问题:(1)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领域中以“人类对其过去进行利用”的“本位范式”仍旧没有被视为既有学科建构其“遗产”领域的共同理论基础,教学内容的差异性远大于共性,实践性的受重视程度远大于理论性;(2)现有学科仍旧以研究对象的物质或非物质属性作为基础分类依据;(3)交叉学科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在本源上仍旧过于趋同,或原本即属于一个大的学科家族,教学内容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简言之,在现有学科的分类体系中,文化遗产研究本该具备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并未受到重视,对于不同研究对象的检视与相应的教学工作仍旧缺乏共同的基础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