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谋划逃离算法
2022-04-06何国胜
何国胜

視觉中国
“每个清晨都感到愧疚”,这是白领吴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想法。
工作不用坐班后,吴童起床就要花一个多小时,有时更久。而“杀”掉这些时间的,是他前一晚睡前放在枕头下的手机。
每个清晨都是这样:关掉手机闹钟后,他被多个App内容更新的红点或红色数字“抓”住。
抱着“看一下就停”的心态点进去后,投吴童所好的内容像是一个黑洞,似乎没有刷完的尽头。
愧疚就是这样产生的。每次终于扔下手机起床后,吴童都责怪自己,并决定明天不这样,但第二天,他又会重复前一天的行为,包括愧疚和下决心。
吴童隐隐觉得自己被什么绑住或监视了,好像他每次拿起手机,手机都知道他想要看什么;又或是貌似放在一边的手机,正在用一种听不到的声音呼唤他。而他每次拿起手机时,或多或少能看到新的推送和消息。然后就是一段时间被吞噬。
吴童最初没有深究这种手机对他了如指掌式吸引的缘由,后来他听到很多人说,原来那是算法的力量。
而有这样遭遇的,何止吴童一人。
“我从互联网中唯一学到的是如何千篇一律地活着。”同样作为白领的姚娟对这种被算法包围的生活体验,比起吴童更为具体。
在她有这个领悟之前,她曾乐此不疲地刷着小红书App,被里面的穿搭、用物所吸引,并想着过上跟那些博主一样的生活。
“我几乎离不开手机。”姚娟说,她的醒悟也来得突然。就是在一个晚上,她刷着小红书App,忽然就想:“我真的有必要跟随网上的博主一样生活吗?我小时候期望的长大后的人生,难道就是跟随着这些陌生人?”
姚娟说,她知道算法推荐是根据她的喜好来推荐,但很多时候她觉得这种推荐滞留在她最初喜欢的类型中。但人的喜好是会变动的,而算法一直在给她推荐很多同质化的内容。这让她越发觉得网络和算法在把人塑造成同一种模样,人们越来越不需要思考自己想要怎么样,自己能够怎么样,自己应该怎么样。而是一味地去追逐屏幕里别人的人生,最可怕之处在于,有种力量把它统一为一个固定单调的标准。
刚大学毕业的贺永宁在认识到算法和智能设备对自己造成的认知挤兑之前,也曾有过糟糕的体验。那段时间,他常刷社交媒体软件,总是难以自控地点开推荐的热点新闻。而那些新闻又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不安和暴力,评论区里也充满了戾气。
那种对新闻事件的不满和气愤蔓延到了现实生活,让贺永宁整天处在一种低沉的情绪中。有时候他不禁会想:难道社会真的是这样?
上班不久的余芳燕不担心推荐热点新闻的影响,但她害怕手机的“偷听”和预测。有一次,她跟人聊天时提到家里太干,想买个加湿器。之后,她在打开购物软件时,首页显著位置出现了多款加湿器产品。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好像被监控。还有一次,她在网上买了一双沙滩鞋,紧接着她就收到海南旅行、防晒霜、太阳镜的广告。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在经历。
面对算法的全面入侵,有些人企图反抗,却发现个体的无力。只要你连接网络,算法就无孔不入。最终大多数人选择的是逃离。
吴童自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他试过卸载那些不断给他推荐上瘾内容的App,但过段时间总会再次下载;也试过强制把自己和手机隔离开来,但再次“相遇”就会报复性地刷屏。
很多人依然在想办法。
豆瓣App的反技术依赖小组中,聚集了1.7万人,他们在进行解除手机依赖和逃离算法的尝试。小组里的成员各自被不同的东西“绑架”,有些人卸载了手机里所有的社交软件,有些人卸载了购物软件,有些人关闭了朋友圈,有些人直接把手机锁进了盒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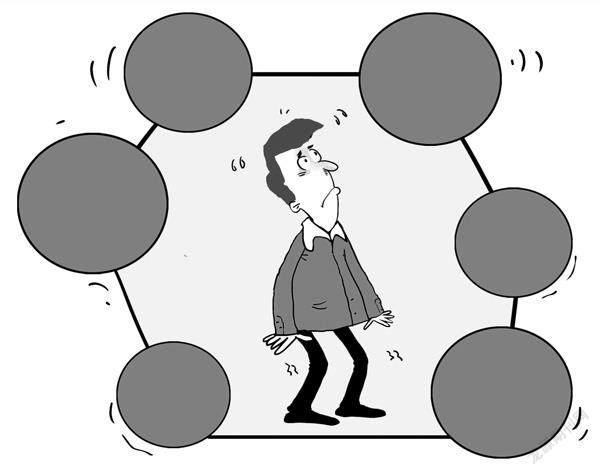
视觉中国
这个小组是网络达人左颖在2021年5月创建的。那段时间,她频繁受到一些有关智能技术和算法新闻的刺激。
这些让左颖忽然明白:“原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以为能掌握的工具,有时技术本身会反过来对我们造成压制,大家却似乎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左颖决定在豆瓣App上成立技术依赖小组。起初,她担心小组没人来,还邀请自己的豆瓣好友加入。但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里,有1.7万人加入。
这样的小组也不止左颖这一个。“互联网脱退”“断网聚集地”“远离屏幕计划”“数字极简主义者”,不少人聚集在一个个小组中,企图抵挡手机和算法对生活的全面侵入。
贺永宁和大学生郭越也在反技术依赖小组当中。贺永宁自从意识到被推荐的新闻让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变得负面后,他清除了很多新闻App。除了必要的微信外,他的手机上只剩下手机自带的软件。
郭越是在一次期末考试复习过程中,感受到手机对他时间的吞噬。于是他做了一次“技术倒退”的尝试——用了一周的老年机。当天晚上,失去智能手机的他失眠到早上,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
现在,郭越能自如地把握自己在手机上投入的时间。而且,为了不让自己被困在“信息茧房”中,他准备了另外一部手机,用来对冲算法推荐的极化。
姚娟已经不再看小红书App那些内容和刷短视频,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也强迫自己看书。
效果是有的。
姚娟说,自从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现实生活中后,所有的感受都变得真实起来,感觉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谁引导。
贺永宁觉得逃离了手机和算法后,他那种从高中毕业后消失殆尽的专注度回来了,有的时候他一周可以读完两本书。
郭越减少手机和算法依赖后,发现自己的时间变多了,也开始发现身边的美好,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可爱。
但問题也依然存在。
像姚娟所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只能尽量不去看它”。生活的在线化程度不断增强,有些手机应用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抛弃它意味着抛弃便利和增加生活成本。所以那种用回老年机的尝试,贺永宁和郭越只做过一次。
有些很容易沉迷的App,如短视频应用,卸载方法的奏效时长很难保持,因为卸载和下载同样便利。
余芳燕就是在不断的卸载和下载中反复,有的时候短视频App在一天里被她卸载三次。她说,在好友圈里,自己属于自制力不差的人,但“还是会傻傻的啥也没干刷一晚上抖音App”,里面几乎全是自己喜欢的内容。而得到的是“那种当下充实,过后觉得空虚的感觉,啥也没收获”。
吴童也不断在卸载和隔离手机的挑战中败下阵来,他一直责怪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和自制能力太差。后来他看到了一部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开始觉得这种失败不能完全归结于自己。
这部纪录片揭秘了社交媒体软件用户如何被算法和智能技术监视及操纵。其中有一点直接缓解了吴童的失败感——人们对手机或社交媒体软件上瘾,并不只是人的自控力问题,而是这些产品在设计之初就想让用户上瘾。
这些产品的开发商请了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心理学家,做了很多测试确保用户能被长久地吸引住。片中一个例子是App中收件箱的颜色应该用什么,都是经过心理学家测试的。又比如聊天软件中“对方正在输入”是为了让你不离开聊天界面。
因为上瘾能增加用户的使用时长,这正是互联网公司跟广告商谈价的基础。其中,算法负责想出该让你看什么才能留住你,进而抢夺用户注意力,而注意力才是真正的产品。
纪录片最后指出,算法和智能技术是一种天堂和地狱共存的状态。他们带来的便利和进步显而易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我们既不能指责个人意志力的薄弱,也不能指责企业赚钱的本性。
但“我们可以要求厂商设计这些产品时加入人性化元素,可以要求厂商不要把人当成可开采的资源,他们的目的可以是‘怎么让世界更美好’”。纪录片中的谷歌前伦理设计师如此希望。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