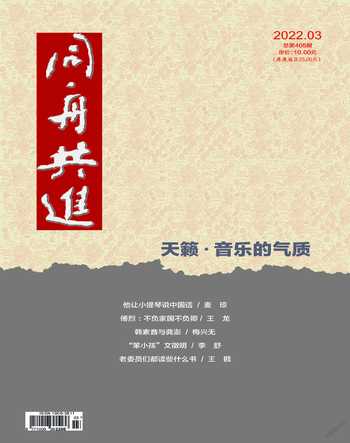蔡威廉:旧时明月映画卷
2022-04-04杨宏鹏
杨宏鹏
蔡威廉,今日多数人只知她蔡元培女儿的身份,却不知民国时她还头顶“天才女画家”的光环。她是中国现代最早向西方学艺的女画家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的高等美术教育家。她在世时,和潘玉良、何香凝等人齐名;执教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时,王肇民、沈福文、吴冠中等后来著名的美术大家都是该校学生。蔡威廉充满才情却又坎坷短暂的一生,成为那个时代一幅斑驳的水墨画卷、一抹月下转瞬即逝的暗香疏影。
蔡威廉生于1904年,是蔡元培的长女。蔡元培作为晚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当然拥有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但他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北京大学素以开明著称的老校长。1903年,蔡元培所创立的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晚清当局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因此正一边辗转躲避一边学习德语。女儿出生后,蔡元培便以德语“Wilhelm”为其命名,这也寄寓着他决定赴德求学、教育救国的愿望和决心。
1907年,已年届不惑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德国留学的生活,主要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心理学与美学;这段时间,蔡威廉随母亲在绍兴、杭州等地居住,接受了初步的中式启蒙。1913年10月,回国不足两年的蔡元培再次经上海赴法国;这一次,他带上了蔡威廉,并将她送入巴黎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不满十岁的威廉自此开始接受西式教育。1916年冬,蔡元培受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执掌北大十年历程;蔡威廉也随其一同回国,转而就读于北京孔德学校。孔德学校也是蔡元培参与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主要参照西式教育,还设有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目,蔡威廉在此时即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这段时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随着他研读德国古典哲学、执掌北大教育管理、参与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经历而逐渐成熟,并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他的这一思想也使得耳濡目染的蔡威廉逐步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3年春,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干涉北大办学的行径,蔡元培正式辞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秋天,蔡元培再度转赴欧洲,蔡威廉亦随父前往比利时。也就是在这时,蔡元培正式征询将满20岁的女儿有何志业。蔡威廉答道:自己是个沉默内向的人,总觉得用文字表达情感太过直露,不如绘画那样含蓄蕴藉——画家以情致作绘,解者自得之。蔡元培高度赞同女儿的志向,并送她进入比利时最负盛名的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这是蔡威廉正式走上绘画道路的起点。
第二年,在蔡元培的建议下,蔡威廉又转赴著名学府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继续深造油画艺术。这个“专科学校”可与今日我们的专科学历层次高校不同,它是专攻某一学科的意思;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更是一所创办于1756年的老牌美专,是当时法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美术学院之一。在这所顶级美术学府里,蔡威廉系统接受了西洋绘画从素描到油画的整套训练,并研读了大量艺术史论著作。
从里昂美专毕业后,蔡威廉又来到当时世界的美术重镇巴黎。她此时已通晓德、法、英、意等多种语言,经常前往巴黎的各大博物馆、美术展上观摩优秀画作,并出席一些高端美术沙龙。那时已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巴黎,他们也有自己的沙龙,有不少知道蔡威廉才情与造诣的师友常常劝她拿出自己的作品赴会,也露上一手;但蔡威廉不慕虚荣,总是微笑着以自己手头“只有习作尚无创作”而婉拒。
不仅在大巴黎的沙龙上甘于寂寞,蔡威廉在艺术审美取向上也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她最初就读的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深受佛兰德斯画派的影响,该画派奉17世纪著名的巴洛克美术大师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为画宗;这位大师笔下的人物以丰满的酮体和健硕的肌肉著称,色彩丰富、动感强烈,深刻影响了比利时乃至法国西北部的画风,蔡威廉的多位老师也非常推崇鲁本斯的画法。然而,蔡威廉却并不盲从,她认为鲁本斯的画“肉重于灵,华胜于实”,她更欣赏的是那种形神兼备、尤其重视揭示人物内在精神气度的古典主义画风。
循着佛兰德斯画派进一步上溯,蔡威廉找到了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佛罗伦萨画派。那一批古典主义的大师们:达·芬奇、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他们的画作真正让蔡威廉找到了艺术的认同感。尤其是达·芬奇,他笔下的女子虽也略显富态、甚至一双纤纤玉手都极尽妍态(如《抱貂的女子》《蒙娜丽莎》等),但整个人物却总是闪烁着不可思议的精神的灵光,而这正是蔡威廉想要的那种人像。达·芬奇的主张“一个画家应当描绘两件主要的东西:人和人的思想意图”,让蔡威廉进一步坚定了以人物画为主攻方向的志趣。
1927年冬,蔡威廉结束五年的欧洲游学,回到南京,与先她近两年回国、此时已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团聚。1928年初,由蔡元培提议创办的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立,由林风眠任校长、林文铮为教务长。蔡元培专程由南京至杭州参加了这所中国现代著名高等美术学府的成立仪式,并且“内举不避亲”地推荐蔡威廉担任了该校西画系教授。24岁的蔡威廉成为该校首批油画专业教师之一,正式开启了她的职业生涯。
蔡威廉很快便證明了,她能获得美院教授资质并非靠的是她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那是1929年的首届全国美展,蔡威廉以三幅肖像画和两张自画像一举震惊了当时的画坛。这次全国性的美术盛事让一批“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女画家第一次集体站到了现代美术史的聚光灯下,潘玉良、何香凝、唐蕴玉、李秋君、吴青霞都在此次美展中崭露头角。一众女画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潘玉良和蔡威廉。潘玉良的作品被推举为“本展写实最优之作品”,蔡威廉的人物画则更被推到了与艺专校长林风眠等量齐观的高度。

在全国画坛上,蔡威廉是一鸣惊人的女画家;在国立杭州艺专的讲坛上,她是认真负责的教授。欧洲高等美术教育的经历让蔡威廉深深领会到了美术学习的规律:基础扎实、循序渐进。有了稳固的造型功底和系统的美术训练后当然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甚至随意挥洒、大胆突破;但在此之前,必须老老实实练好基本功,对绘画来说,就是首先要有扎实的写实功底。蔡威廉执教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绘画正风靡世界;但蔡威廉明白,毕加索在学习绘画的初始阶段也是从写实做起的,可见想成为大师也必须经过写实绘画的训练。因此,蔡威廉经常对她的学生们说:“作画和翻译一样,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但对初学者来说,更要注重‘直译’。”
这时候艺专正好出现了另一种画风:有一个班的教师在指导素描的初级阶段即开始变形,或者说施展“技巧”,把人物的眼睛画得更大一些,鼻梁涂得更高一些,并在有些局部也加以修饰。这种类似今天“美颜”的画风在效果上的确更好看更讨喜,也引起了蔡威廉所教的学生的注意。蔡威廉遂组织学生们认真讨论、研究,并重申了她的初学重写实的主张,还举了毕加索等大师也是从写实基础练起的事例;于是学生们由羡慕、疑惑到豁然开朗,最后大家一致否定了这种画法。蔡威廉最后用一句柔和简练却又似谆谆告诫的话教导学生:“不要胡画!”
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让蔡威廉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尊重。就连日后名满天下的中国当代顶级绘画大师吴冠中此时也对蔡威廉敬若天人。吴冠中在他的回忆文章《我和朱德群》中谈到当时艺专优秀学子们心中最崇敬的老师,提了四人:“我们每天交谈上课时老师的指导,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寿等是我们心目中最最崇敬的老师,仿佛他们都来自天堂。”
蔡威廉却并不因为学生的崇敬而变得高不可攀。她尊重每一个学生,也早早留意到了吴冠中的才华,还留下了一段“以画换画”的佳话。这出自吴冠中的另一篇回忆文章《老师·掌故·怀念》:“我于课外画了大量水彩画,在全校成绩展中获了奖。蔡威廉老师赏识了我的水彩画,传话要以她的一幅油画换我的一幅水彩,我受宠若惊,便将全部水彩画送到她家中由她选……她仔细翻阅了我的作品,从中选了一幅留下,便指着墙上挂着的她的油画风景和静物,问我:你要一幅静物还是风景,或给你画一幅肖像?我立即回答愿让老师画肖像。她说好的,待找个合适时间约我到她家里画……”
她欣赏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甚至还尊重学生的选择。面对这样有才华又平易近人的教授,哪个学生能不铭记一生呢。
纵观蔡威廉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她应该是旧式文人士大夫那种类型的,尽管她主要接受的是国内的新式教育和国外的高等教育,但在那个时代也都是顶级精英才有可能;因此,蔡威廉的家世、阅历、教育决定了她非凡的见识与高卓的境界,却也铸就了她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代的深刻矛盾。
作为“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精英,蔡威廉既关注个体的成长,又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既有着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情愫,又有着悲天悯人的人间情怀。这一切,从她不同类型的美术创作中可以细细体察出来。

在蔡威廉如今已为数不多的可以考察的美术作品中,自画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画家自我意识、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西方的达·芬奇、伦勃朗、凡高等也有大量自画像存世便是旁证。对于中国的女性画家而言,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有意思的是,“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好几位中国著名女画家都喜欢画自画像。如潘玉良、关紫兰、孙多慈等,都有数目不等的自画像传世。然而,这些民国女画家们笔下的自己又不尽相同,风格迥异。就以第一届全国美展上与蔡威廉一同成为瞩目焦点的潘玉良作比,二者画笔下的“我”之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潘玉良由于其曲折的早年经历和豁达通透的性格,其笔下的自画像带有华丽的抒情性,色彩奔放、用笔大胆,画中女子眼神直视观者,丰满而夸张的酮体让人看了会有一种烧灼般的感觉。蔡威廉的自画像则是另一种气质,画中自我与现实中的她极为肖似,平静、淡然,形体概括、色调纯粹,不矫饰、不虚美,呈现一种沉默的精神力量,连眼神也并不迎合观者,仿佛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透露出一种超脱尘俗的气息。
然而蔡威廉并不会只生活在她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她也会直视人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国难当头,时局危如累卵。左翼大众文艺潮流汹涌,许多文艺作品借古喻今,意在唤起民众的警醒与奋发。具体到美术领域,大型主题性历史画创作于此时兴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徐悲鸿的著名油画《奚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这类创作往往会选取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格调高昂、场面壮观,隐含着艺术家对历史、对时代的忧愤与慨然。受这种时代氛围的感染,蔡威廉也于此时尝试作大型历史人物画;而她笔下的历史人物也往往从女性视角切入并以女性为表现主体。直到这时,我们才可以看出画家作为女性对历史的独特体察和艺术表达。她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秋瑾就义图》和《费宫人杀中贼图》。
作于1931年春的《秋瑾就义图》描绘的是辛亥革命女杰秋瑾被绑赴古轩亭口行刑的场面。蔡威廉原籍绍兴,秋瑾正是她的同乡,她应该很小就听闻过秋瑾的事迹,这时用画笔郑重地描绘了这位女英雄英勇就义的一幕:“秋瑾着白色长袍,发髻稍乱,神情沉着坚定,而又含着不能掩盖的忧郁和悲痛;四个着黑衣的兵丁簇拥着,面目呆滞而凶顽——整个调子是灰黑色的,弥漫着一种悲惨而沉重的氛围。”这幅画的真迹如今已不知去向,但通过中国美术学院校史专家郑朝的描述我们仍能感受到蔡威廉画笔下对秋瑾的崇敬与感怀。
作于1936年的《费宫人杀中贼图》则是根据清代陆次云的《费宫人传》还原的一幅历史画卷,被称为“慨于国难之严重”“以抒其悲愤”之画作。当然,在这苦难深重的人间,蔡威廉也依然不忘描绘她理想中的乐土。作于1934年前后的油画《天河会》又与前面两幅悲壮风格的历史人物画迥然不同。这幅画描绘的是一群仙女在银河里欢快沐浴的场景:淡蓝的河水、银白的浪花、隐约浮现的曼妙多姿的人体……那明快的调子、轻松的笔触以及欢悦的氛围,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怀与幻想。蔡威廉,就在这人间与天河的矛盾中用画笔挥洒着她的热血与才情。
尽管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与事业,但蔡威廉无论生前身后还总是摆脱不了“蔡元培之女”的社会标签。这也可以理解,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名气实在太大、影响太过深远。另一方面,蔡元培对自己的这位长女也的确投入了相当多的心力,寄寓了非常高的期许。他带着蔡威廉三赴欧洲,引导女儿奠定了一生的志趣。他的现代教育理念、包括“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张,乃至他忧国忧民关心中华民族文化前景的情怀,都直接影响了蔡威廉。蔡元培人生中最大的一笔私务支出——5000大洋,也是送给了蔡威廉。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讲到蔡威廉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男人——她的丈夫林文铮。
林文铮生于1903年,籍贯是近现代以来人才辈出的广东梅县。1919年的五四运动影响了刚刚中学毕业的林文铮,他也决心赴欧洲留学,寻求先进文化与救国之道。1919年底,林文铮与林风眠、李金发、蔡和森、蔡畅等百余人一同参加第十二批留法勤工俭学。1921年,一年的法语学习后,林文铮考取著名的巴黎大学,主修法国文学和西洋美术史论,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位赴欧学习美术史论的留学生。
1928年11月,林文铮和蔡威廉在杭州西湖大饭店举办了婚礼;蔡元培自然亲临,达官显贵也纷纷前来道贺,成为轰动杭城的新闻。婚礼这天还留下一段佳话:当天上午,想一睹蔡元培、蔡威廉父女风采的人们却迟迟不见二人露面;直到正午吉时新娘子才匆匆现身,手上还带着些许油彩。原来,蔡威廉执意要在出阁当天为父亲画一幅肖像,并把老父亲摁在座椅上让他配合当模特,蔡元培也就乐呵呵地照办了。蔡威廉画了整整一上午,还是没能画完;最后完成了大半,吉時已至,只好手上的油彩来不及洗净便登台亮相。如今,这幅未最终完成的画像还挂在上海的蔡元培纪念馆里,成为那个年代的见证。
蔡威廉和林文铮大婚之后,蔡元培拿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笔私务支出——5000大洋,送给女儿女婿,让他们在杭州盖房置业。林文铮又设法筹了两千余元,共花了7000余大洋,在西湖边的马岭山上盖起了一套寓所;身为美术师的蔡威廉则亲自设计了房舍格局以及围墙、铁门、窗花等细节。房舍落成,果然既功能齐备又格调雅致;蔡元培视察后非常高兴,亲题匾额“马岭山房”挂于堂上,此后每来杭州便会到此小住。
婚后的七八年间,是蔡、林二人最幸福的日子。他们一个从事美术创作,一个讲授美术理论并负责学校教务,二人互为对方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和读者,可谓琴瑟和鸣。有一段时间,为练习法语,他们约定,在家里只能用法语对话;又有一阵,为了给孩子启蒙,由林文铮挑出上口易诵的古诗,让蔡威廉配上简洁的图画,俨然组成了一套“家庭绘本生产线”。在这段时间,他们相继诞下了五个孩子。
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很快被国家的动荡打断。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淞沪会战后,日军很快逼近杭州,蔡威廉和林文铮跟随杭州艺专的师生一道内迁至湖南沅陵。1938年12月,当时的教育部下令北平国立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往昆明办学。两校合并又涉及人员重组;而此时之前与他们有隙的张道藩已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在他的暗暗授意下,林文铮和蔡威廉都未再获学校聘任。

客居昆明的一家人生活很快陷入困顿。半年坐吃山空的日子后,林文铮才终于在西南联大谋了个法语讲师的职位,战时微薄的薪水勉强够夫妇二人加上林文铮的母亲以及五个孩子糊口。没过多久,二人又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蔡威廉再次怀孕,即将临产。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蔡威廉为了省钱选择不去医院,在家生产。
1939年初夏,蔡威廉在昆明的临时家中艰难诞下一个女婴,这是她和林文铮的第六个孩子。产后数小时,虚弱的她在床侧的白墙壁上用铅笔为新生女儿画下了一幅肖像,并伤感地在旁边题上了四个字:“国难!家难!”
她仿佛有所预感。由于产后感染,她患上了急性产褥热,这显然是在家中分娩的卫生条件造成的,当时的医疗已无力回天。三天后,这位年仅35岁的天才女画家永远合上了双眼……
蔡威廉去世时,已避居香港的蔡元培并未及时得知;考虑到他业已年高体弱,家人在通信时也刻意隐瞒此事。直到近两个月后,蔡元培自己在报纸上看到昆明举行“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会特刊”的新闻,还附载《蔡威廉先生家属谢启》的消息,才知爱女已先他离开人世;他悲痛不已,写下《悼长女蔡威廉》一文,简述女儿的一生,痛寄伤怀之情。
经女儿早逝之打击,加之忧怀国事,蔡元培的身体也日渐不支。八个月后,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据其幼子蔡英多回忆,昏迷前,蔡元培还一直念叨着长姐威廉的名字。
由于早逝,加之战乱流离,存世的已没有蔡威廉的几幅真迹。如今,马岭山房的产权业已转移。旧时主人已远去,只有那块刻着“蔡元培之女蔡威廉及女婿林文铮旧居”的石碑,依然在杭州植物园的山坡树丛间静默伫立。
(作者系河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