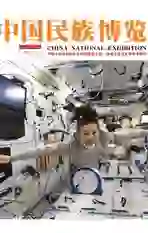知所进退陈平原
2022-04-03刘艳辉
刘艳辉

2021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了一个新职务—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他跳出潮州看潮州,强调研究要超越地域,超越文史学科思维,超越学院与社会的边界,同时“拾遗补缺”,真正连接好研究、社会与企业,更好推动潮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从成立仪式,到研讨会、恳谈会,甚至“潮人潮学”公众号文章审核,陈平原身体力行。对熟悉他的广东人来说,这并不意外。
在这位大学者身上,“潮州人”一直是张显眼标签,虽然多年在外,但他始终心系家乡的教育及文化建设。近年来,他出任潮州市文化顾问以及韩山师范学院董事,策划“韩江讲堂”,和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一举一动备受关注,颇受赞誉。又与深圳多有合作,比如出任南山区文化顾问和南山图书馆理事,粗略统计,12年间共参加学术文化活动20场。
他不需要,也从不借机自我标榜。面对媒体和公众,他再三声明,无论潮学、岭南文化还是人文湾区建设,都不是他的专业领域,敲锣打鼓可以,粉墨登场则不敢。
他自带流量,却拒绝迎风起舞,在关注现实与迎合公众之间选择前者,在采访问答的方寸之间审慎把握:“从媒体角度,话题越热闹越好;作为学者,我必须知所进退。”
陈平原曾形象地自喻为“压舱石”,对热闹、时尚保持警惕,矢志不渝地追求着学术与人生合一。30余部大大小小的著作中,他以“我手写我心”,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追寻文字、声音、图像背后的真实历史文化景观,不厌其烦地诠释着何为“有情怀的学术”以及“学者情怀”。
有境界自成高格。陈平原的学术志向与野心,通过一件往事可见一斑。1999年,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陈平原挥笔道,该中心的宗旨还有一条:研究艰难中崛起的20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大学教授,他不忘育人本色,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中更多从教育体制入手,可谓用心良苦。在他看来,所有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都必须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对陈平原的采访,本文既不是第一篇,也不是最后一篇。目前已有七八十篇采访问答,被细细整理录入《京西答客问》《阅读·大学·中文系》等书中。本文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谨供读者进一步了解陈平原的所思所想。
对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
“从书里谈到书外,长长短短、琐琐碎碎,如此扶老携幼,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
《南方》杂志:祝贺您的新书《小说史学面面观》出版。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小说史研究,中间转向学术史、教育史。能否介绍下本书写作缘起?
陈平原:刊行于1988年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我的博士论文,获得很多学术荣誉,最得意的是出版30年后,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我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著作,还有《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但这回的《小说史学面面观》不一样,属于“学术史”而不是“文学史”,那就是“中间转向了学术史、教育史”一圈的结果。在此书最后一章,我审视自己的小说史研究,辨析其中的功过得失,希望给后来者提供借鉴。
至于写作缘起,最初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大改为线上教学。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不再与学生面对面,无法交换眼神,不仅不精彩,而且容易忘词。为了备忘,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课后意犹未尽,干脆整理成文,交给《文艺争鸣》刊发,也算是对这一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
《南方》杂志:该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鲁迅、胡适等这些读者都比较熟悉的中国学者,还有普实克、夏志清、韩南等外国学者。这样的选择有何考虑?
陈平原:这就说到我希望做到的“面面观”,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描述并评价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思路及著述,目的是呈现不同的学术视野与方法。第二,选择这12位学者,不一定业绩最佳,但都别具特色,很能引发思考与讨论。换句话说,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试图凸显的是研究者的立场、趣味及方法。基于此设想,本书舍弃了很多主要贡献不在小说史学的优秀学者,即便在小说研究领域,也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选择我较为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反复敲打,希望能得出若干独特的发现。第三,我自己的解说与论述同样不拘一格,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点到为止,就像课堂讲授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同时,还得保持一定的水分与空气。如果两个小时全是实打实的干货,会让人听不下去的,必须张弛有度,灵活多样,且讲究韵律与节奏,方能维持听众的注意力。
《南方》杂志:“既学问,也人情,还文章”,是您對这本书的理想设计,也代表了您的著述风格。形成这样的风格经历了哪些过程?
陈平原:关于这本书采用何种文体,到底是论文还是随笔,我一开始很犹豫。最后选择了这么一种介于专门著作与课堂讲义之间的写作形式。有理论阐释、史料钩沉,但也穿插闲话,兼及师友逸闻。从书里谈到书外,长长短短、琐琐碎碎,如此扶老携幼,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也正因此,此书比我以往出版的诸多专业著述要好读很多。当然,这与我内心深处对过于学究气的学术论著不太满意有关。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的结果还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朋友们大都认为有见地,不怎么八股,算是别具一格吧。但这是论题本身以及生产过程决定的,不能硬套到我此前此后的所有著述。
文学教授的别有幽怀
“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叠床架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南方》杂志:无论是研究文学史,还是学术史,您都不把它单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是更多地从教育入手,有哪些用意?CEFFAA79-01E1-4DFC-B361-968BD0CCBBD1
陈平原: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一番“游历”,在我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以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体会其中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个体学者与时代氛围的关系;众多努力中,从“教育”角度切入,可以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我以为是比较稳妥且可行的。
《南方》杂志:就当下而言,落实文学教育关键在哪里?
陈平原: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我在《文学如何教育》一书中描述了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以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五书”及“学术史三部曲”为根基,力图将学院的知识考辨与社会的文化批评相勾连,在教育制度、人文养成、文学批评、学术思想的交汇处,确立“文学教育”的宗旨、功能及发展方向。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谈论文学史及文学批评,更多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叠床架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建立自己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是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
《南方》杂志:去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您的“学术史三部曲”收官之作。什么是“述学文体”,这一研究有哪些重要意义?
陈平原:一般认为,治学的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至于“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是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这里谈的不是一般的写作技巧,而是中国学者如何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建立自己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这涉及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如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南方》杂志:您的研究不限于文本,同时关注了“城市”“图像晚清”以及“有声的中国”,透过不同的媒介发现了不同的文化景观。为什么从这些角度入手?
陈平原:10年前,我发表《“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谈我为何要在主营的文学史与学术史之外,如此拓展学术疆域与视野。某种程度上,这既是自我期待,更是学术展望。关于“大学”与“图像”,我的成绩还可以,在北大出版社刊行“大学五书”,除《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我还在东方出版社推出了《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有声的中国”很有潜力,已发表了若干文章,只是尚未正式成书。有点遗憾的是都市研究,我起步很早,但效果不太理想,去年出版的《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显得有点散乱。之所以撒得这么开,除了学术野心,更重要的是为我的学生探路。放长视线,若他们在学术上有大的推进,那我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也就值得了。
对时尚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看过很多聪明人,之所以摔跟头,就因为过分看重时尚,什么热就做什么,且老想抄捷径,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南方》杂志:投身学术40年来,您共写下30多本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并获得很多学术奖励。最近四五年间又出版了七八本新作。您是如何做到的?
陈平原:人文及社科没有国家奖,最高的也就是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我获得了五次(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其中两次还是一等奖。不过,60岁以后我就主动放弃了,不再申请此奖项。因我发现,现在申请名额下放到学校和院系,你再参与,就会挤占年轻教师的发展空间。如果是校外评审,不用填表自吹自擂,那样的获奖,我很开心,比如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至于最近几年出书多,那是因为我同时做好几个题目,经过长期积累,刚好这个时候出来,像获得文津图书奖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以及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都是经营了差不多20年。
《南方》杂志: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治学方法和写作习惯,以及下一步研究重心?
陈平原:我是1977级大学生,曾下乡插队8年,学问上起步很晚。上大学后,走得比较顺畅,算是勤能补拙吧。说到研究方法,没有一定之规,跟时代背景、学术领域以及个人性情相关,关键在于学会自我反省,尽可能少走弯路。另外就是对时尚保持必要的警惕—不管誘惑多大,倘若不是你想要或你能要的,就应该不为所动。我看过很多聪明人,之所以摔跟头,就因为过分看重时尚,什么热就做什么,且老想抄捷径,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只要不太笨,以中人之资,肯下苦功,持之以恒,总能做出成绩来。至于写作习惯,那就更是因人而异了。相对于其他专业,学人文的,擅长写文章,这点很要紧。我注意到文人学者中,凡到老年还能产出好文章的,十有八九是养成经常写作的习惯,类似“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今天因为严苛的学术考核,导致某些年轻学者写得太多、太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很多教授成名后,过早地丧失学术创造力,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
我的习惯是,每年用心经营三四篇像样的大论文,另外还得有八九篇别的文章,包括一般论文、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我当然知道,一个学者真正有创见、能流传得下去的好文章,不会很多的;你不能保证写下来的,就能传得下去。不懈思考,经常动笔,长长短短,好好坏坏,除了多少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学术敏感、思维能力、写作激情以及文字管控能力。至于下一步研究重心,就不在这里啰嗦了,用我们家乡话说,“捡有猪屎呾有话”(比喻事情做好了就有话讲了),在此之前不要吹牛。(来源:人民网、《南方》杂志等)CEFFAA79-01E1-4DFC-B361-968BD0CCBB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