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实的记录”到“心灵的刻记”
2022-03-31周益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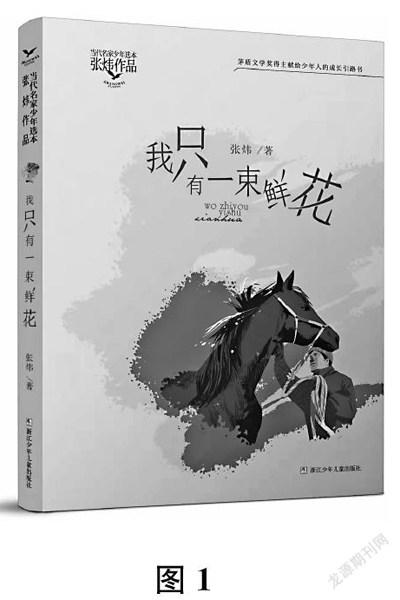
摘要:阅读张炜的散文选本《我只有一束鲜花》,在文字中捕捉到的,是一个海边少年的见闻与喜忧———感触到作家的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甚至觉察到这段经历对于作家生命成长与壮大的价值和意义。时间是一种过滤,会筛选掉某些片段与截面。过滤后的记录,往往比真实更真实。因为,这种过滤绝非刻意为之, 而是潜藏在作家的无意识之中。这些文字的本质是作家“心灵的刻记”。
关键词:张炜;散文;生命成长;《我只有一束鲜花》
张炜说过:“我一直认为,散文不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为它不是虚构,它仅是真实的记录。”①确实,阅读其散文选本《我只有一束鲜花》(书影见下页图1), 我在文字中捕捉到的,是一个海边少年的见闻与喜忧———感触到作家的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 甚至觉察到这段经历对于作家生命成长与壮大的价值和意义。
进一步追问:在作家成年后的回望中,十余年时间为何留下的是这部分“真实的记录”? 无疑,时间是一种过滤,会筛选掉某些片段与截面。这当然不是说过滤后的记录缺乏真实,恰恰相反,它比真实更真实。因为, 这种过滤绝非刻意为之,而是潜藏在作家的无意识之中。这些文字的本质是作家“心灵的刻记”。
一、“黑汉腿”:童年的自由与男孩的野性
这组散文很大一部分内容与“玩”有关, 可以想见,玩,是作者童年时代的重要生活元素。这儿的玩,并非玩“过家家”、踢毽子之类的游戏,而是洋溢着一种男孩特有的野性。
先看玩的处所。作者出生于渤海湾畔, 小岛、海滩、野地、松林,都是其天地。这些地方具有共同的特点:辽阔、神秘,对海边少年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充满了未知,如磁石般紧紧吸引着他们的心。比如:
我“们是瞒着大人偷偷坐小船去的。绕过四五道激流、三处礁石,一口气爬上小岛。真像探险一样。”
———《有个依岛》
我“们最大的享受不是在舞台上听‘鱼鼓和‘拉网号子,而是到大海边上去看真实的‘拉大网,听震天的拉网号子。”
———《大網号子》
少年的“我们”不会安心将身体束缚于室内,渴望突破眼前的空间,渴望走向大自然。
再看玩的方式:
“中午我们一头扑进水里游泳,还想逮一条大鱼,放在那个小锅上煮。”你“兴冲冲地跳下水去,扑腾得浑身泥浆……”爬“到很高的树上往下跳,赤着脚穿过荆棘丛生的灌木林……”我“一次次纵向穿过整个海滩,走到白雪皑皑的高耸沙岸上,望着没有一只帆船、没有一点人影的海面,看着海浪在沙岸上的拍击、伸缩不停的水……”
———《黑松林》
这些语句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让我们看到一群精力十足又莽撞冲动的少年。
作者在回忆这些经历时,数次提到一个外号叫“黑汉腿”的伙伴。在作者笔下,“黑汉腿”个子最高、胆子最大,几乎没有不敢干的事情。有意味的是,在成人与孩子眼中,“黑汉腿”的形象迥然不同:平“时家里大人总是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跟那个‘黑汉腿混。一些耸人听闻的坏事经常与他的恶名连在一起,其实大半都来自道听途说,只要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都会多少有点儿喜欢这家伙的。”①在成年人眼中,“黑汉腿”做的事出格, 粗蛮,是“坏事”“恶事”,而对于少年们来说, 那是力量与胆识的展示,是无穷精力的发泄, 是好奇心理的满足。“黑汉腿”正是包括“我” 在内的少年的一种自我投射,因为,在“海边上生活,勇敢是最重要的”②。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黑汉腿”的嬉玩带有典型的男性特征:崇尚力量,向往自由,充满征服者的英雄情结,更多地表现为身体的积极参与。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少年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表现。
二、“外祖母”:凝望的深情与对万物的热爱
作者笔下,有一个人物令人印象深刻,即外祖母。在这儿,“外祖母”可作为一个群体的象征,除指原本意义上的外祖母,还包括“我”的父母亲、音乐老师、岛上大婶、养马的老安等,那些“我”亲近或亲近“我”的长辈。
与“黑汉腿”不同,“外祖母”们传递出的是慈爱、柔情、宽容,正是这种“柔”,中和着少年的桀骜不驯。
“外祖母”们以自身的言行,给予“我”人性的启蒙。在得知“我”逞强打下蜂巢被蜇伤后,外祖母说:马“蜂过自己的日子,只要不招惹它们,它们就不伤人。蜂巢是它们的房子, 要花多少辛苦才建起来。你毁了它们的家……”①在得知“我”用那把剑杀死许多动物后,外祖母说:“它们有它们的日子。孩子,你想过没有,它们像人一样,只有一次生命——— 它们只活一次……”②话语朴素,充满智慧与力量。
音乐老师则是美与善的化身。“我”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时遇到了音乐老师,“我觉得她那温柔的眼睛抚慰着每一个同学,特别是投向我的时候,目光中竟然没有歧视也没有怜悯,而仅仅是一份温煦、一种滚烫烫的东西”③。一个雨天,“我”被同学欺负受伤,是她的关爱抚慰了“我”。“我”感叹老师的小屋:“我大概再也看不到比这更干净的地方了…… 屋里有阵阵香味儿:水瓶中插了一大束金黄色的花……”④从此,“我”每天都给老师带去“一大蓬颤颤的、香气四溢的鲜花”⑤。这种纯情、细腻与那个打打杀杀、充满野性的少年简直判若两人。少年在音乐老师这儿得到了尊重,得到了关切,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得到美的启蒙。那一束鲜花,是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致敬。
“外祖母”们的经历、经验与阅历也成为“我”了解生活、洞察人生的教科书。在作者笔下,父亲是寡言的,是家庭的支柱,隐忍、冷静、坚定。面对大水的威胁,他“用力挥动铁锨的样子告诉我们:绝不允许大水泡垮小屋”⑥。外祖母则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饱藏生活的智慧。她听听外面的鸟叫声,就知道会有大水。无疑,这些潜移默化地对“我”发生着影响。老安的经历更为坎坷,因而,他对人生有独到的体悟。“我觉得人和马都一样⑦, 拉一辈子车,吃一点草、草料,就这么着。”他所表现出的与马的相互依恋让“我”震撼, 让“我”开始了有关生命价值的思考。492D86EB-FC00-4CB9-948A-5D629ABF31BD
老安跟“我”说,“我和它们讲话一般不用嘴”。或许正是因为不断受到这样的影响,在少年时代,“我”就懂得了与万物对话,体察生命的丰富与细腻。这组散文中,有篇《一些美好的树》,写得十分动人。“柳树的眼神是顽皮的,白杨的神色是温暖的,槐树的眼睛是闪烁的。橡树有时严厉地看着我,让我小心翼翼地挨近它,或退开一点。”⑧这是童话吗? 这分明是少年真切的感受。“我”认为银杏树全都是女性,还爱上了一棵紫叶李,感受到来自它的痒痒的抚摸,说这是自己的“初恋”。在“我”的眼里、心中,自然万物都富有生命与情感,我们真诚地与其沟通交流,便能获得心灵感应。
三、“慧子”们:语词里的记忆和念想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语言左右思想”的观点。他指出,“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个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会获得完整的存在”①。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作者用文字表现的世界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并非等同。即便同一个生活事件,在不同作者的笔下也一定会呈现某种差异,这是由作者对客观事件的主观反映差异所决定的。
我在阅读张炜的这组作品时,留意到行文中闪现的一些特别语词。这些语词犹如密码,隐藏着作者的心之所系;又如通道,将作者的现在与过往紧密相连。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可以通过对这些语词的把玩,去领略作者的情之所牵。
这些语词带有属地性,包含着一方水土人情,闻之想之,就会浮现特定的场景、独有的意趣。“海沟”是海中的大河,燕“子似的鸟儿从水中钻出,箭一样射到远方”的叫“飞鱼”。海参怎么有营养呢? 小“孩吃了鼻子流血,大人吃了身上长蹄”。一提到“拉大网”, 就会想起夜晚海边的盛况。
这些语词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叫人过耳难忘。就说下大雨发大水吧,远远近近都在水雾中,外祖母说是“都在老天爷的大喷壶底下”“老天爷发脾气了”。为了说明水之大,村里老人说“天上的水和地底的水接起來了,两种水握了手,‘水力就大了”②。对于戏水的孩子,村里人称呼他们是“小水孩儿”。冬日漫长,妈妈说“老天爷把冬天藏在雪堆里,一点一点往外发送”。这样的话语完全胜过文人作家的语言,既充满画面感,又质朴无华。
对于“我”而言,这些语词还带有私密性, 甚至唯一性。“黑汉腿”“香香”“由由夺”,这些人对“我”的意义远远不同于其他人。于“我”而言,这些语词早已超越称呼的层面,蕴含着我的钦佩、喜悦、渴望,那是一种独属于自己的体验。最典型的,莫过于那匹叫“慧子”的灰马了。其实,灰马的名字叫“灰子”,“我”却在心里叫它“慧子”。“慧”字承载着“我”的美好情愫,寄托着“我”对灰马的深情。“我”不让旁人知晓,将它制造成一个秘密,并为之满足。
拥有这些话语,“我”便拥有了故乡,拥有了记忆。
张炜在《黑松林》一文中直抒胸臆:“我觉得这是整个海滩平原上最让人留恋的地方,它代表了我的过去,甚至是未来。比起这儿,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③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作家对故乡、对整个少年时代的告白。这些“真实的记录”其实是作家“心灵的刻记”。
(周益民,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特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① 张炜.诗性的源流[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6:自序。
①② 张炜.我只有一束鲜花[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14,23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张炜.我只有一束鲜花[M].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27,31,90,92,93,56,121, 102 。
①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1 。
②③张炜.我只有一束鲜花[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54-58,98 。492D86EB-FC00-4CB9-948A-5D629ABF31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