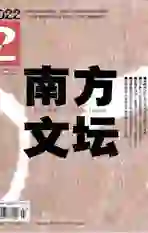探索小城镇版图边界的可能性
2022-03-30艾翔

张楚为人谦和,含蓄低调,虽然已经成绩斐然,却仍与其描写的人物相差无几。而其小说内蕴的深厚,又分明显示着这种低垂的姿态绝不意味着视野的局限。张楚的抱负在其小说的复杂呈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警惕模式化,积极寻求探索;另一方面变革本身也还是循序渐进,不急不躁。作家本人与其作品正是这样互映互证,其小说世界的建构已经蔚然大观,甚至比肉眼凡胎所見的现实表象更为纷繁,并且充满条理。
一、城镇
张楚曾在一次论坛上说出了自己真实的体验:“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似乎与我们的时代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而‘80后’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和城镇。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①的确,张楚一直以来孜孜不倦耕耘着的领域正是对小城镇的书写,所获的诸多荣誉也与此相关。
由于大量的人生经历都在小城镇,张楚贡献了丰富的相关作品。作者对他生活的地方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个我生活的小镇曾让我窒息乃至厌恶,有那么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如何逃离这里,如何与爱人、孩子在异乡怀想这里,并继续深深地厌恶这里。”②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的熟悉又令其充满了理解、体谅的温情。于是,张楚小说就提供了一幅真实可信且可感可触的小城镇风貌,既有冷静客观的描摹,又能贴近每个人物体察他们的内心。
张楚在21世纪后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到了2003年就能创作出一批十分精彩的小说,令人感叹其充溢的天赋与小镇生活的丰厚滋养。《樱桃记》讲述了一个小镇少女的残酷成长史,在校园暴力和再婚家庭暴力的环境中,樱桃见证了自己和周围同龄人的变化。原本熟悉的身体经历了逐渐陌生化的过程,情感也渐渐呈现出了朦胧萌发的态势。小城镇和少女形成了互相观看、互相陪伴的关系,这两个容易被世人忽视的角色与角落,进入了作家的视野。有意味的是,故事发生的1985年,正值少女樱桃的青春期,也恰好是改革浪潮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夹在中间的小城镇一如青春期的少女一样,一边发生变化一边遭受冷落。对少女身体成熟的陌生化,是否暗喻着对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陌生化?这是小说营造的丰富空间。小镇在工业和城市的撕扯下慢慢发展,一如少女樱桃在慌乱和厌恶中成长。其中对地图的执迷,正是文学史脉络上的熟悉环节,是小镇对城市化进程的憧憬,也是少女对成长的期待,只不过憧憬和期待中夹杂着令人畏惧与欣喜的未知。
《樱桃记》对城镇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环境描摹,难怪张楚有将其影像化的念头。还有很多作品并不担负城镇图像化的立意,虽然他对现实主义抱有很高的敬意,却并没有复刻传统现实主义的心理包袱,这是其独特性的重要体现与根源。怎样理解现实主义在作家这里的传承和调整,或许是理解其人其作的关键。他坦诚地说出了内心想法:“我承认书写现实生活时,现实主义是最可靠的主义,可是我也知道,现实主义不光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它还是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它不单单是对外部世界的还原构造,更是我们内心真正的心灵风暴。现实主义是复杂的现实主义,而不是一元的、机械的人物和故事。”③可见张楚不希望出现因为借鉴理论而束缚创作的情况,不希望过于因为注重规则令生活的再现显出僵硬感,不希望恪守“写出事物原有的样子”的训导反而丧失了事物原有的样子,不会因为现实和真实的追求而执意于肉眼可见的范围。刘卫东也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并非‘强硬’介入,以‘非虚构’方式书写现实,而是将其‘虚化’,形成带有哲学追问、悲剧意蕴的氛围。”④《关于雪的部分说法》写了城镇居民的无聊与空虚、无奈与无力,现实激烈残酷,面对现实的人却压抑着情绪。张楚不写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等现实的生存境遇,主要倾力于时隐时现的逼仄气氛,甚至连作为基本人伦的夫妻关系都显得虚与委蛇、不堪一击。米佩和颜路都是重压下扭曲的灵魂,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子里走向极端。颜路因为理想化而更极端,米佩则要承受回归日常后的欺瞒压抑,某种意义上更残忍。张楚写虚不写实,突破了表象的千差万别,直抵小镇发展和人性善恶的深处。《蜂房》在这一点有相似之处,除了引起全城关注的蜂乱事件,还有精神病症和出轨乱性,一出荒诞、无序、离奇的日常剧,甚至淡化了因果律的限定,以乱写静,主人公甚至有些享受并期待突发事件,更突显小城镇的波澜不惊。
小城镇的人与小城镇本身互为表里,环境塑造人,作为反馈,人也营造环境。《夜是怎样黑下来的》这个绝妙的标题就说出了张楚很多小说的共同主题,角落里的个体的无力感并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历史在变但情境不变,一直受到歧视,即使有一定社会职务和身份依然难以主导事情发展。这些人在激荡的年代饱受屈辱与坎坷,到了和缓的年代依然看不透历史与时代的发展原委,弄不清人和事的内在肌理,努力生活却乏善可陈,有想法却难以实施。与此同时,作者对这些不完美的人物大多抱有了很大同情。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良宵》直接出现了一个看似更加无力且还是外来者的老太太,面对被众人冷漠、被时代与世俗摒弃的男孩一家的经历,默默张开怀抱接纳无所依靠的男孩。最后设置的开放式结尾,也让原本情节链条下游并不乐观的老人与男孩的未来变得模糊,故事之外的叙事方式本身也显得充满温情。张楚笔下的世界里,总有人需要体谅,总有人会给予体谅,哪怕这些人及其所在的环境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张莉通过阅读指出:“张楚有天然的艺术感,他的内在情感充溢,即使他再克制,你依然能够感觉出小说家对世界的情感温度,他对世界的善意和爱恋。”⑤
刘涛在辨析70后作家的走向时,将张楚界定为“现实主义”,李云雷则被划入“底层文学”范畴,很坚定地予以区别对待⑥,也有论者提出张楚小说“摆脱了常见的底层书写的‘控诉’和‘揭露’”⑦。张楚关于李云雷的印象记也可视为其文艺理念的表达,虽然对底层文学的一些创作理念并不认同,但还是尊重后者作为“一起等待黎明”的知识分子及其所持部分观点:“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我觉得云雷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有些作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们俯视下的世界,只是一个麻冷的、程式化的、没有温度的扁平世界;他们俯视下的人,缺乏那种生动的、立体的、狂躁的、狂欢式的,甚至是恶毒的喊叫和抗争。”⑧理论家、批评家有自己的身份立场和思维方法,作家同样有自己的特性。从这一点看,张楚更亲近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楷模作家,一方面亲近体贴底层民众,但另一方面并不能完全纳入左翼文学的脉络。对此作家本人的表述很清晰:“作家多读些社会学、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肯定没有坏处,至少这些书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一元化。它们也可能无意识地影响我的思维,左右我对事件的判断,但不会对我的写作构成一种疑惑,这可能源自我是个过于感性的人。没有必要担心主题先行的问题,当然,能主题先行并能在小说中彻底执行,也是有趣的创造。”⑨所以《野象小姐》能称为其代表作,也正是因为鲁叶香代表了作者对于城镇普通民众的印象,他们对命运和生活没有自主决断权,难以扮演英雄或参与英雄叙事,也不夸大“积极生活”的力量,平静面对悲欢和生死,平静生活在小城镇。不仅对他们的艰难和隐忍报以同情,同时也对艰难生活下的伪饰给予理解,如同对待家人一般对待他们,平视与尊重让这些人物鲜活了起来,也让小城镇鲜活了起来。
二、都市
在一次文学活动中,石一枫回答提问时说:“北京的影响就是,这是我不能选择的。他(张楚)只能写县城,我只能写北京。你让我写县城,我也写不了。你让他写北京,当然他现在可以写了。但是我觉得,你要真是就事论事地说,我觉得北京的影响就是,北京这个地方,它永远是这个国家的风口浪尖,永远是一个风口浪尖的城市。我想写的东西恰好是这种风口浪尖,大时代大变化的东西。那么,这点在运气好,这个城市给了我一些滋养,这点是比较感谢的。”⑩从侧面可见张楚的创作在发生着变化,并且得到了优秀同行的认可。这种转变,固然与2015—2018年北京求学的经历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本身创作的故有特质的发展变化。
应该承认,张楚从城镇写到了都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是书写都市与城镇的关系。程德培指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逃离’都是其创作的重要母题,无论是从小镇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回到小镇。逃离不止是一种告别,它同时也裹挟着一种向往,于是‘逃离’便多了追寻、造访、再造的意思。向往是迷人的,但目的地尚不明晰,于是旅途中疑虑不安、犹豫彷徨便成了衍生产品。”11《金风玉露》的形式在呼应着内容,美兰相亲多次神游,既有技术上的考虑,压缩叙事长度加快叙事节奏,同时虚实配合打断主情节链的喋喋不休,更重要的是回忆中的相亲,包括与潘姓男两年前的初次见面都发生在北京,也就建立了都市和城镇的关联。再次见面后,美蘭的记忆从模糊走向清晰,但潘姓男则鉴定认为只是初识,暗含着传统的圆形时间和“现代的”线性时间的区别。当然,美兰如果没有女性的感性,其实也是被“北京化”了。两人在县城酒店里的激情,仅仅是简单的快感倾泻,感觉不到任何自我和内心,令人想到《安葬蔷薇》中的无爱、无感症,并非由情感创造的孩子的早夭让男主恢复了早年温润的记忆。《风中事》同样是关于即将不再年轻的青年寻找情侣的故事,按照极为普遍的流程顺次分手、相遇、确定关系、见父母,之后却急转直下,先是段锦失联,关鹏重新相亲认识米露,后来得知米露多次与他人开房,段锦则因代孕惨遭杀害。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与婚恋相关的如车、房、彩礼、家境、学历和职业等信息反复多次出现,情感不是被欲望裹挟,而是被更为现实的因素操控,城镇或是都市的场景反而被模糊。作者曾就“一手生活”话题说到这篇小说有个民警朋友的原型,但这个朋友看后却认为与自己无关,说明作者有清晰的构思,借“警察”这个身份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即使是警察也很难查清自己生活中的“案件”,更强化了个体自主的困境和不可知论导致的偶然性史观。题目也很值得回味,现代化的城市让具有巨大摧毁力的台风变得“日常化”,损失被降到最低,但是产生的飘摇无依的心理感受却清晰而连绵。
张楚以为年轻人的情感困局不仅仅是感情本身或人本身的事,其与城镇/都市的发展密不可分,背景不只是背景,也参与着主体建构,甚至背景之间的互渗同样有影响力。叶檀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超大城市已经是由资本逻辑支撑着运转,中小城市尚有人情关系,因此个体在不同环境下奋斗的成本和方向有差异。张楚的观察则是城镇其实已是空壳,个体被遮蔽,对感情的感知力下降,情感交流也日渐贫乏,主体趋向于机械化的物体,无论是生活、工作结婚生子甚至出轨。城镇没有“城市病”的解药,无法作为都市的“退路”,并且很大程度上已经同质化。由此,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建立起了一条诡异的理解通道:后者因为政治和时代原因导致城镇和都市无差别,情感贫瘠,个体无力。
更进一步的是《在云落》。男主从北京回到云落,能够自由地制作纪录片,还有活泼天真的妹妹和慧为伴,失眠很快痊愈,又偶识能够喝酒聊天的邻居苏恪以,一切似获得新生。但很快遭遇妹妹手术不成功、前女友仲春突然到来又突然消失、失眠复燃,还得知苏恪以一直在从事违规手术,且因女友出轨发生过激烈争执,为寻找失踪的女友消失在男主视野,又从郝大夫处得知二人皆是从小渴望关爱的地震遗孤。苏恪以找到女友时后者已失常态,接着苏恪以失踪、妹妹和慧病故、仲春确认失踪,原本为了逃避大都市来到的云落,也不再是想象中的桃花源。巧合的是,苏恪以的女友正是郝大夫的妹妹,也是因为在北京失恋,到云落散心结识了苏恪以。城镇被当作都市的休憩疗伤地,却并非纯粹是舒适自在。人们都以为大小城市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或者历史时序上的先后,希望以小城镇疗愈大都市的伤困,不料二者有相似的内面,往返大小城市之间只是徒劳甚至加固困境,毕竟云落“过不几年就能建成一座中等城市了”。
数年之后,《过香河》依然持此见。叶密在北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却偏偏好高骛远想入非非,工作漫不经心,感情也吊儿郎当,年岁增长而玩心不减,一无所成回到云落又操办起山寨感十足的歌唱选秀,受到县里大力支持,最后落得滑稽收场。接着张罗穿越网剧,再次吃了草台班子的亏。一番浮躁之后回到现实,父母还是想支持儿子,盘算着借钱,细数身边人才发现城镇普通人家依然凋敝。叶密到北京并无不适,也说明城镇与都市的趋同,城市化进程降低了直观的进入门槛,却暗中提升了安居与成功的成本。从开篇的“过香河”到结尾的“回香河”,透露着深深的无奈。都市描绘的乌托邦犹如悬在小城镇上空的一张大饼,但张楚对之不以为然,因为只要阶层依旧存在,这种乌托邦就会伤害到寄托着他的深情的城镇平民。
这篇小说还彰显了作家的新变,即大篇幅的知识性写作。作家的阅读大多很驳杂,郭洪雷就提出张楚作品中涉猎的外国作家和电影,“这些艺术资源对张楚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实质性影响,或者说,张楚在小说中对这些资源进行了怎样的创造性转化,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12。前引张楚和徐畅的交谈中,也表现出对社会学、哲学并不排斥。《过香河》多次大篇幅介绍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和思想,还有福克纳和萨特等人。粗浅判断作用有多个方面,首先是表明城镇不但在物质层面效法或山寨都市,精神追求也是亦步亦趋,当然叙述者是否真正通读甚至读懂了维特根斯坦,作者并不关心,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可能只了解最粗浅的部分,从小说细节可见,这就包含了对城镇的都市化本质的隐喻。其次是形成反差,操弄这一套哲学和思想话语的男主,虽然比叶密稍显踏实,但其实也并不能称作精英阶层。小说开始讲述维特根斯坦时提到“主动性”,相比之下叙述者“我”和外甥叶密距离这个主动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此外则是用知识性写作与部分俗文化和惰性思维进行对抗,小说中提到的一些山寨娱乐和粗制滥造的穿越网剧,同城镇及其居民的命运有深层逻辑关联。最后也是一种反差,自启蒙运动以来张扬理性主义,直至发展到计划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治理和经济制度。张楚无意于讨论大命题,但他确实看到理性在现实中的无能之处。《风中事》等作品传达的理念正是如此,用理性解决情感问题和生活问题难以奏效。
阅读张楚小说提醒了我,城镇是个大问题,其范围不仅限于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地域。平日娱乐玩手游,经常看到一些游戏水平很高的“路人王”,获得过一些国服、全国、全省和市级排名,打开仔细看还有更多的区级标,定位往往都在一些县城或者县级市。游戏战区不能随意定位,必须人在当地,至少去过。这些地方大多不是景区,因此很大可能是这些高端玩家出自小城镇,这从一些职业选手和大主播的籍贯也可见一斑。这些人可能一直在定位所在地,也更有可能定位在家,人在都市,毕竟网速更快、玩伴更多。这些人在都市游戏、工作、生活,自然也会把城镇的气质带进都市。从小城镇的角度理解都市就显得必不可少,站在这个角度,石一枫对张楚的城市书写的肯定,正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城市文学模式。张楚在小城镇的税务局工作多年,虽然这段经历本身让他感到乏味孤单,但我相信客观上会给他带来一个不同的视野,“营改增”“县改区”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会因为张楚的观察带来不同的认知,就像《梵高的火柴》等作品里的人文情怀,虽然点燃希望的物品最终被考虑用来装骨灰,但毕竟热情地闪烁过。
三、宇宙
在一次研讨会上,赵依说到很多人都在关注的现象:“《中年妇女恋爱史》补白的部分,我之前也想过,如果把这些都抽出来,比如放到最后,或者把每一部分置于年份的前面,大家的阅读效果会不会不一样?比如凤凰那一版就是把它们都删了,所以读者就会有误解。”13我庆幸的是看到了完整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且补白是放在每部分结尾处。如徐晨亮所言,这并非新事物,从张楚作品的整体样貌才能看到这部分的深刻意义。林培源提出的这个概括14,无疑已获得较大范围认可。
《七根孔雀羽毛》里的宗建明是个身无长物的混子,有命案在身,与前妻离婚后换过多个女友,后寄居在情人家里,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选取了非常贴合人物的暴躁的叙述方式。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本无“宇宙”概念,在吃饭闲聊中李浩宇提到宇宙,其实是一种自我渺小化的悲观情绪,此后再讲述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自然令小说蒙上了一层冷酷而温情的悲凉感。所谓的“刺郭”也通过当事人复述呈现出事情的真相,郭六先被滑稽化,并无“捞人”能力,宗建明最初的目标也只是钢钎戳屁股,不料失手戳进曹书娟的胸,笑的运用让小人物的英雄叙事失去了根基。之后借助蜥蜴、谍战、底层谣言等荒诞元素的插入,让原本可能成为悲剧、正剧的情节变成喜剧,写尽了小城镇无名之辈对命运的难以控制和预测。最后对宗建明而言,“宇宙恐惧论”因为命运的荒诞反而显得正经,宇宙巨大的压迫感成了他最后的精神稻草,让他说服自己无助无能乃是因为自己不过是宇宙中的细菌,而不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
从“宇宙”的角度可以将《中年妇女恋爱史》与《七根孔雀羽毛》进行对读。与宗建明不同,小说展现的茉莉从少年到中年的漫长岁月中,很难说什么时候不是在认真地生活,虽然算不上特别热烈、特别积极、特别有理想,却也对生活和情感报以希望,除了最后与蔡伟有大波折,此前与历任男友、丈夫包括身边人的感情婚姻,大多都是小插曲。茉莉的半生与很多小城镇居民毫无差别,被生活翻来覆去地摆弄,填充生命的都是些细碎之事。就在这些细碎之上,张楚放置了大事年表,有国内国际政治和地外文明两个层面。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第四卷每节正文前,摘引了长度不一的《出埃及记》,并用不同字体区分。《中年妇女恋爱史》形式上与之十分接近,却有本质的区别。《出埃及记》虽作神语,却是犹太民族历史的加工再创作,并且内容上与正文分别暗中对应,只在最后一节形成反差而造就反讽效果。《中年妇女恋爱史》大事记则是虚实结合,国内国际政治部分是事实,地外文明则是作家彻底的几乎毫无依据的虚构,正文茉莉的恋爱史恰好属于中间状态,即基于事实的虚构。吕彦霖在参与组织的研讨会上也谈到正文和大事记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二者没有关联。张楚这样写是故意的,他就是在消解这种关联。因为这种特别巨大的东西,甚至我们讲克鲁苏式的东西是有利于起到‘离间’效果的。张楚这种‘宇宙学’的写法就是在提醒我们从所谓的现实的、理性的框架里出来,他就造成了这种‘布莱希特式’的感觉,一开始就告诉你‘你看的是戏,这是假的’,让你从这种秩序中猛醒,从而真正地重新审视这个世界。”15我赞同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张楚的先锋文学起点:大二时“模仿苏童所写的一篇先锋小说”,“对词汇和结构的迷恋印证了我曾经是个技术主义者”16。后来的转变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内里几乎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先锋的内涵。从大约2010年特别是2015年开始包括《过香河》等近作,张楚愈发熟稔而自信地游走于现实主义、现代派和后现代之间。大事记的纪实部分呈现了人类现代文明中灿烂的和阴暗的两面,光鲜之下也有痛苦,虚拟部分则展示了更高端文明中的低级面向文明伪饰下的野蛮。这些与小城镇里的茉莉毫不相关,放置在一起看出张楚的蓄意,通过与世俗的小镇故事强行拉开距离,以这种叙事的真空状态蓄积反讽和先锋性,施加外力迫使读者对人物命运进行凝视、对文明及文明所庇护和遮蔽的城镇展开反省。作者在大事记里扮演的是写作的暴君,在正文里扮演的却是人间的暖灯。
与这两篇小说相比,《直到宇宙尽头》里的宇宙虽然不很狂暴,却更冷漠。女主姜欣性格里的孤僻来源于童年,叙述中没有写到与同龄小伙伴玩耍场景,倒是特别强调对科幻、科普读物的钟情。正是对宇宙的仰望和畅想中,有了参照系的人的形象和意识慢慢变得清晰,这一过程也暗合了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成年后依然对宇宙思绪万千,一方面是姜欣的性格令其未充分社会化,不似其他几个男人早已被世俗浸泡透彻;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的触感让她感觉某种清醒。巨大的仙女星系、漫长岁月形成的月球、天体間巨大的空间间隔,都是现实社会孤寂、陌生、疏离、冷漠的写照。遵循着“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宇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因为高温、辐射、引力场等因素而显得危机四伏,姜欣经历的人类社会也同样残酷而祥和。由此产生的漂泊感和不安感,也让她觉得社会中的个体如同宇宙中的星球。不过即使如此,“生活在别处”的文艺心态还是让她对宇宙充满着复杂的情感认知,毕竟个体类似星球,但还不是星球,个体直接置身宇宙反而安享静谧,作者巧妙地将多人错乱的关系并峙在一个喧闹的社交场景,之后跳出回忆,冥想宇宙,放空而得自在。为了报复前夫,姜欣与其多名好友发生关系,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复仇的利刃,但是每次复仇后她都发现对方无法了解自己内心,只不过是被“反利用”享受了“免费”的女体,复仇无疑是失败的。理论总会有预设立场,优秀的作家能突破理论的藩篱,宇宙感的营造让姜欣复仇前后的心态变得真实可触。
较早出现“宇宙”的《夏朗的望远镜》,也将其作为“空间”理解。夏朗与方雯从开始就有不能顺畅交流之处,与岳父母住在一起后,非血亲长辈又无时无刻不給他带来压迫感。因为共同的天文爱好,他与线下聚会认识的陈桂芬发生了婚外性,其实与他的宇宙观测本质相同,借以摆脱此界的焦虑、困顿、贫乏,幻想另一种生存形式。但婚外性注定难以常态化,回到家,自我连同变的幻想一起得而复失重新坠入庸常。小城镇用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气质的繁衍,生生不息。在这里,“宇宙”之于城镇是乌托邦般的存在,与“城镇”之于“都市”、“都市”之于“城镇”并无本质差别,是小城镇落寞、孤寂、无聊的精神寄托,是彼岸的城镇。但希冀是科幻片的复写,现实却是“宇宙”仍是小城镇的“宇宙”,深陷其中之人难以突破,故不可得。望远镜是夏朗通向彼岸的渡船,束之高阁后便与日常妥协,并认为理所应当,生活失去了波折和瑰丽的色彩。张楚对其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后,仍然让已经妥协的夏朗期待重新取出望远镜,保存了一线走出精神贫瘠的希望,这是作者的善良,一如《略知她一二》结尾将诗意赋予穷苦人。稍晚写出的散文中,作家说:“宇宙这么大,我偏偏生活在地球上;地球这么大,我偏偏生活在中国的第一小镇上;而小镇这么小,我偏偏拥有一条从不属于我的野河流,倒真是意外的福分了。”17与科幻中宇宙的实在性不同,张楚的宇宙观其实是提供一个归属感、一个小城镇的参照物,或者一束观察小城镇的光源。与“都市”唯一的差别是,这束光源真正在形式上而不仅仅在内核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范畴。这在《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更为显著,“宇宙”不只是“空间”,蔓延到“时间”范畴,在历史时空中强化了叙述的不稳定性,由此可见张楚技艺的精进。
纵观张楚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人,如同他眼里没有低贱的人,同样也并没有流露出对文学类型的褒贬。他的作品中不但能看到各种外国文学经典,同样不乏美剧、香港电影、武侠、侦探、谍战、喜剧特别是科幻、科普等文艺样式。甚至在《在云落》等作品中还有大量时政新闻,这正是“宇宙”的另一种形式,或《中年妇女恋爱史》的先声。在作家的诉说中,关于“地震”和“黑暗夜晚”的童年记忆,则是让后来丰富的阅历发展成“宇宙”的动力源头。同为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燕垒生也有类似经历与经验:“在经常会停电的20世纪70年代,暗夜里我拿着一盏极简易的油灯,沿着仄仄的楼梯走上去,门外的石板路上响过夜归人的跫音,而月光从紧闭的木板窗缝隙中挤进来,以致一种已被世界抛弃,这个地球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恐惧犹如利爪般抓在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的心头。在后来偶尔操觚,写一点幼稚的故事时,不知不觉地总是把未来想象成是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又总是在他们心底留下一丝善良与希望。”18物质的匮乏和转型社会的尚未到来,造就了这一代作家向星空和温情的仰望。80后一代普及了电器特别是电视,90后一代普及了网络,00后出生即是全球化和信息化,10后看世界时已满是自媒体,张楚、燕垒生等一代作家在用想象力构建世界方面确有其优势。
四、平行宇宙
在对张楚作品进行研讨时,体裁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兴趣,作家自己解释说:“《野草在歌唱》本来是作为后记,把它收录在小说里面,把我的自序变成了跋。当时也很奇怪,它其实就是非虚构的。之后晨亮他们新开的栏目《开放叙事》又把这篇散文当成小说转载。里面的《朝阳公园》其实是《山花》约我写一篇关于读书的散文,《山花》认为这是小说。就把它当小说发了,我其实是按散文体例写的,里面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隐私的人,所以小说里极少有我自己的事情,但这两个是例外,因为它们就是非虚构散文的范式。”19除了这两篇,《莱昂的火车》被收录在《梵高的火柴》,版权页印有“短篇小说集”,同时作为《关于好基友们的一切》第三部分收入散文集《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且该文第二部分也出现了“莱昂”。此外,《履历》《忆秦娥》《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等篇目都带有程度不一的散文化色彩。或许可以认定,体裁边界的模糊不只是误会或误解,与作家的先锋底色和城镇书写有深度关联。
如果规划一篇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张楚的文学观一定是理解其全部作品的基础和关键,其观念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不仅限于表层,而是渗透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忆秦娥》当然不会被误认为是散文,其跳跃突转的叙事视角不仅仅彰显着作者对叙述技巧的追求,更是为了突显父辈真情与当下粗鄙的反差。但同时运用大量散文化笔法营造“跟拍”效果,贴近人物真实内心,作者观念中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尊重、谅解和体察。《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同样是因为并不刻意强调叙事的散文化文风,让这篇带有叙事理念探讨的小说20具有很高的读者友好度,历史的偶然性和浮动其上的人物的不安定感通过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叙事娓娓道来。这些作品中的散文笔法,淡化了虚构带来的间隔感,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的孤独以及寻找同类的渴望。
可能发生误解的或许是作家在作品中的“现身”,像《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里出现了老辛的同事“张楚”,但是出镜很少,几乎缺乏刻画,并且与张楚本人有明显的差距,应该只是提供一个视角以及陌生化处理的需要。《野草在歌唱》基本都被认为是散文,其中传达的经历和思绪与作家本人高度贴合,不过也不乏小说笔法,呈现出人生与故事高度的相似性,并由此强化作品本身的气质。《朝阳公园》中的“我”不但名为“张楚”,而且很会写作文、坚持记日记,但1983年的张楚肯定还不叫“张楚”,就如同《故乡》《社戏》里的“迅哥儿”带入了鲁迅,自己却不能说就是鲁迅。除了提供儿童视角和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功能性作用外,应该还有用当下的目光审视历史,因为毕竟是后来的张楚回到了过去的时间。换句话说,作家的散文化书写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平行宇宙,站在一个相似又不同的时空看小城镇的历史。
张楚更加明确地构建平行宇宙是在2016年以后,先后创作了《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和《听他说》。张楚很多小说都在尝试处理历史议题,当下的处境或多或少都与历史发生着关联,不过从《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开始他走出了一条历史书写的新路。这篇小说涉及很多层面,包括现实的资本运作、重大历史事件、微观的家族史、城市化与环境变迁等,这些层面被作者用传统的志怪小说的方式加以演绎。《水仙》也是同一般操作,平缓轻灵且沉重的历史叙事逐渐转化为缥缈的志怪,结尾回到一个确切的公历纪年:1966年12月26日,一个普通的却连接着重大转折的日子:当年12月15日“四清”运动正式汇入一段沉痛悲怆的历史阶段,12月27日负责三线建设的彭德怀被押解回京接受批斗。传说只是一瞬,最终回到人间,但是受过历史教育的读者却知道人间即将不再平静。《听他说》将熟练的叙事技巧、厚重的历史叙事和飘忽的志怪小说融合起来,用更加清晰的神灵视角观察历史,并且因为沉浸于历史和文学而获得了人类的情感与心脏。在这样的平行宇宙下,历史中的争斗与人祸被置于一个巨大的超自然存在的观照下,曾经被固执坚持的东西显得不值一哂,小城镇特有的“平易近人的气质”,“自由的、包容的、非理性的、无戒律的,更重要的,它是温暖的”21,被放大到照亮人性深处的程度。有趣的是,不但志怪小说中的情绪及理念同小城镇若合一契,前者灵异的感官世界包括认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似乎只剩下小城镇。能从城镇上升到宇宙和平行宇宙,与作家并不执念于特定区域的书写有关,也即注重一般性而非特殊性。关于“秘密”“信仰”和“忏悔”22的诸多问题,在平行宇宙处似乎达到了预期。应该看到,正是此前作家创作向轻松幽默、去虚无方向的转变,实现了通向平行宇宙路径的达成。
张楚通过其孜孜不倦的创作,不但生动描绘出了小城镇从鲜活个体到动态整体的样貌,还生动展示了其与大都市的彼此交融,更通过宇宙和平行宇宙的高位视角,使小城镇及其背后庞大时空的陌生化成为可能。视角的抬升和下降,都是为了生活在他身边的那群熟悉又陌生的人,无论都市如何繁华、宇宙如何浩渺、平行宇宙如何奇异,张楚小说世界的地理中心与逻辑中心一直在小城镇。张楚已经为他所向往的长篇小说谨慎准备了多年,无论是艺术感知力、世界观或技术储备已经自成体系,许多人都在等待他的长篇的到来,那或许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百年中国城市化的重量级作品。不过毋庸讳言,张楚小说中的某些构思和理念已经有了当代文学史上优秀长篇的感觉,那些长篇虽然触碰到人性复杂,但对善恶仍然具备有力的刻画。张楚视界如是高(宇宙和平行宇宙),人物如是渺小,善恶也就微不足道23,也因此使小说的厚重感有所缺失,进而令史诗性与灵魂涤荡感失去了依附的基础。这样的中短篇可称优秀,长篇则显疲乏。毕竟我们看到前辈作家为人称道的长篇小说,大多具备优异的道德穿透力。
在对小城镇表达体系的探索上,如杨庆祥总结的:“张楚的写作是真正的世界语的写作,同时又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跟西方的作家们站在一起的,跟他们进行对峙或者对话,争夺对这个世界的故事的讲述和解释权,我们就能够找到世界语言的地位或者谱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用多少溢美之词来赞美张楚都是不为过的。”24通读之后,个人感觉张楚是文学的朴树,朴树是音乐的张楚,艺术上的节制精准和精神上的纯粹性与理想化,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卑微却从不放弃拼搏和希望,弱小却有行走在大地上、人世间的勇气,不讳言弱点,不羞赧于自夸美德,历经岁月磨砺终于知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张楚的理想及其作用在创作实践上的效果,让我想到一句网络流行语对话范式:“这波他在第几层?”“他在大气层!”
【注释】
①澎湃新闻:《“不惑”和“知天命”之间:一代人的文学命名》,本文为“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文学代际和经典化”2020年12月26日的报道,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291584923449835&wfr=spider&for=
pc。
②张楚:《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载《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115页。
③张楚:《我的生活与写作》,《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④刘卫东:《“退后半步”、交界与不及物——评张楚〈过香河〉》,《上海文化》2020年第11期。
⑤张莉:《有内心生活的人才完整——张楚论》,载《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第48页。
⑥刘涛:《70后六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
⑦李晓禺、张昱:《小镇·望远镜·宇宙——论张楚小说宇宙学的建构》,《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⑧张楚:《一个“沉默”的理想主义者》,载《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199页。
⑨《张楚致徐畅:时光最后剩下的东西,肯定是最沉的》,青年文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2020年8月17日推文,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901/c405057-31844629.html。
⑩张莉等:《“他们的小说里有中国人心灵的真实”——弋舟、张楚、石一枫作品研讨会实录》,《青年文学》2018年第4期。
11程德培:《要對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
12郭洪雷:《主持人语》,《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31924杨庆祥等:《“张楚的世界”——张楚作品研讨》,《西湖》2019年第1期。
14林培源:《张楚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小说的“宇宙学”》,《文艺报》2018年11月23日。
15郭洪雷等:《宇宙观照中的日常书写——张楚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及新作讨论》,《西湖》2020年第11期。
16张楚:《在南方》,载《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70页。张楚:《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自序)》,载《梵高的火柴》,花城出版社,2016,第6页。
17张楚:《夜河》,载《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69页。
18燕垒生:《燕垒生未来幻想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第1、2页。
20唐诗人:《“三心二意”与小说的挥发术——谈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21张楚:《小酒馆》,载《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44页。
22张楚:《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载《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114页。
23饶翔认为张楚小说“道德暧昧”“善恶界限模糊”,并对此进行了理解。见其《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载《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第81页。
(艾翔,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本文系天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TJZWQN1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