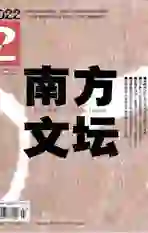论徐迟1950年代思想及创作的转变
2022-03-30李铮
引言
1949年之后,与许多进入新时代的作家一样,徐迟陷入一个艰难的思索与转型期。作家徐鲁曾这样评价徐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二三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摇摇头,自叹才尽,无法效命而停笔,过早地终止了各自的创作生命。但也有一些作家,似乎克服了‘异化,在痛苦与困惑中走出了高尔基笔下的那个萨木金式的自我天地,很快投入了新的时代当中。徐迟当属后一类作家。”①经过四年的苦闷思索,徐迟在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行后,逐渐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他的思想也因此克服“异化”,走出苦闷,投入新时代,正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五年,直到1958年下放河北怀来县劳动才告一段落。一年后,徐迟结束劳动回京,后又遭种种变故,一家人很快离京赴汉,他也因此结束了1950年代的创作,进入了另一阶段。
在这期间,徐迟先后出版了两本散文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1956.6)、《庆功宴》(1957.7),以及三本诗集《战争和平进步》(1956.8)、《美丽、神奇、丰富》(1957.4)、《共和国的歌》(1958.7)。这些作品是他在1950年代思想完成转型之后的新创作。分析梳理徐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思想的转变过程及这一阶段的创作特征,不仅对于综合理解徐迟1950年代的创作极有帮助,也有利于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更深层次地把握徐迟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演变。
一、徐迟的苦闷与失衡
1949年5月3日清晨,天还没亮,熟睡的徐迟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就在前一日,解放军来到了南浔镇上。南浔解放当晚,连日奔波的徐迟长舒一口气,心情舒畅地沉沉睡去。然而,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就有人登门邀请徐迟到镇上商会开会。睡眼惺忪的徐迟顶着困意从梦中惊醒,似乎有点生气:哪有这么天刚亮就开会的?但他转念一想,呵,现在已经是解放了呵!天不亮就应该去开会嘛!从今后,一切都要变过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徐迟匆匆起床,在朦胧的晨色中奔向了商会②。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在徐迟的脑海中却挥之不去。正如徐鲁指出的那样,一大批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的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陷入了思想与认识上“无所适从”的危机。徐迟也不例外,他极早感受到了思想与认识转变带来的矛盾。在四十年之后的回忆录中,他清楚地记下了这件事,并感慨道:“从解放的第二天早晨梦醒的时候起,我就意识到了‘自我与集体之间,个性与共性之间是存在着矛盾对立的。”③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徐迟面临着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个人认识的艰难转向,这一转变过程令他一度陷入重重苦闷。
“个人”意愿与“集体”组织之间渐渐浮现的无意识“对立”首先令徐迟倍感不适。自南浔解放的第二天起,当他怀抱着新鲜的感觉参与到集体生活中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区隔便开始撩拨起他内心的矛盾。哈耶克认为,所有集体主义制度的共同特征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对社会劳动者的精心组织”④。在这个体制中,个人要被纳入组织管理,在价值序列中为特定目标发挥出最大价值。所以,相对于之前,徐迟此刻的思想与活动已被纳入组织的“计划”之内,个人行动已开始需要服从集体需求、组织安排。这一转变显然让徐迟极为不适。
从徐迟个人经历来看,他的性格当中一直以来就有一种“我行我素”的特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从小就有不大老实的毛病,或者说,有点反传统的精神”。1931年,徐迟在东吴大学就读。国内战事爆发,危机渐起,他有意尝试一种兵营生活,便不顾学校劝阻,在校园内扎起了营盘。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七岁的徐迟不顾阻拦,与另外一个同学张宗和参加了北上援助马占山的“援马团”。行至无锡,同行的张宗和被一路寻来的母亲和姐姐态度坚决地拉了回去,只剩徐迟一人继续北上。徐母听闻此事后,亦从南浔赶到南京,找到徐迟,把他關在舅父陶俊家中。面对反复劝说,徐迟态度坚决。软禁九天后,他居然趁着早晨买烧饼,偷偷跑回了“援马团”驻地。翌日,“援马团”列队向下关火车站出发,准备继续北上。徐母和大姐开车沿着队列找到了徐迟,劝他回家。但徐迟仍不为所动,坚不让步,无奈的母亲只能眼睁睁看着徐迟离开。1934年夏,徐迟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渐渐对课程失去兴趣,“我发现上这样的学校读下这些书,实在没有多大意思”⑤。于是在当年6月的考试中,他声明弃考。学校注册处找来徐迟谈话,说如不参加考试,下学期将无法回校学习。徐迟干脆自作主张:“我本来就不想来上学了,我自动退学了吧。”⑥无论是不顾阻拦参加“援马团”,还是自作主张弃考、退学,徐迟性格中有着明显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个性”。甚至在南浔解放之后,他仍旧如此:
我提出,我想到北京去看看。在我希望我的新领导发给我一张路条时,却未想到会遭到这样的拒绝:“你不要走,这里还需要你呢。”我不假思索地自己作出了决定:我该走了!我就得走了!并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离开了当时已经在领导我的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很快一溜火星似的一走就走掉了。⑦
徐迟后来反思道:“我想,这是我第二次,对所谓我的‘组织的毫无半点儿自觉地对抗起来了的。(第一次是天刚亮就要我去开会。)”⑧
显然,这种“个人意识”突出的个性特质,让徐迟不可避免地与走向“计划集体”的新环境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冲突。当越来越多的社会与个人生活被纳入组织管理的范畴内,“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我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是如何经常地冒出头来的。……所以,当周围的一切都闪耀着无限光明、无限美好之时,我自己也曾蒙着一层荫翳,我与我生活的新环境并不能协调,自己觉得有点儿格格不入。我发现我是在作茧自缚”⑨。
在自我与集体的无意识对立之外,新形势下文学创作形态、方式的变化同样让徐迟感到难以适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徐迟赴朝采访。在那里他完成了《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与《平壤被炸目击记》。回京后,两篇稿件投给了《人民文学》。然而,第一篇文章“却被茅盾枪毙了”,只发表了第二篇,“因为这篇(第一篇)写的是北朝鲜的灾难”而“后者确实愤怒诅咒了美帝轰炸平壤罪行的,当然照发无疑”⑩。徐迟心里对此事颇有微词,他在回忆录中说: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
其实文章都是写得可以的,两个乐章构成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后来它发表于《大公报》的,可谓第一乐章:是一首哀歌,接着作了愤怒的控诉,而发表于《新观察》的为第二乐章;对轰炸的惨绝尘寰,发出愤慨之极的声讨!没有第一乐章,就没有理由写第二乐章。我对于第一乐章的被枪毙,实在觉得不合情理。11
在徐迟看来,作家不要写“应该”写的文章,而要作家只写“愿意”写的文章12。也就是说,徐迟认为作家的创作显然应是一种内在驱力为主导的行为。他之所以觉得“不合情理”,其实正是委婉表达对主题先行的不满,而强调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与自发的创作意愿。徐迟虽然能够写出形势所需的“愤慨之极的声讨”,但这种“声讨”的根本来源却是作家本人因景而生发的“愿意”,并非完全是按照设定目标而生造的感受。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文艺逐渐强化的计划性与工具性显然令外在形势先于创作者的意愿。因此,“第一乐章”被茅盾枪毙,在徐迟看来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这显然让他难以接受。
采访结束后,徐迟于1951年初回国,当年冬天分配至广西省柳州市农村体验生活,参加土地改革。这一段农村经历,让徐迟的不适感更加强烈。在土改过程中,尽管设定好的整套流程是“很了不起的一套学问,它已被说得头头是道了”13,但是在徐迟看来,实践过程却有着很大问题:
至于实践之时,应当说,是很困难的,经常是走过场,就是一切都做到了,但是都是走过场。14
徐迟对这段“土改”经历的看法并不积极,评价亦不高:
就在那时,我内心里却已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实践的这一次“土改”经验,至少在我们的三个乡里,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是煮了三锅“夹生饭”。15
这种围绕既定目的进行体验与定制,进而批量产出的“图解”式写作让徐迟难以接受。从徐迟的感受来看,这段经历没有给予他源于现实的真切触动,而更像是在机械的流水线上履行“任务”。徐迟本人并不习惯这样的创作生产方式,因此更谈不上创作的动力与激情,他曾经的创作经验让他觉得这种“图解式的作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16。但是,面对整体形势的要求,他又无能为力。因此,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徐迟只能非常悲观地否定了自己:
从我来说,我是一个最笨的人,什么也没有学到。但也不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不过带回了一点儿失败的酸味。我自知我这辈子不可能懂得农村。许多自以为完全了解农村的人,实际也并没有。中国的农民是永解不开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我从来知道我不能写农村。17
这段广西之行结束后,除上交两段日记给阳翰笙应付差事外,徐迟交了一张“白卷”,没有写出任何作品。
“个人意识”带来的冲突矛盾和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让徐迟感受到很大压力。在变化的形势中,他迟迟没有找到创作的感觉,这让他十分苦恼。在其后的四年间,徐迟陷入了相当程度的沉寂与苦闷:“事实就是如此,我被文坛冷落了。一连四年,没有作品可写,是很严峻和痛苦的事。……我在开国前写过不少东西,出过好多本书,但是一解放,即写不出文章,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了。”18
总体看来,时代的变化令徐迟面临思想精神与创作层面的双重危机。他的个性意识由于“惯性”而与时代主流有了明显错位;他的文艺创作观念似乎也与时代主流发生了抵牾。他曾借用高尔基《四十年间》的主人公来反思自身,自己似乎“游离于时代的主潮流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想着的只是他自己”19。这种状况体现出“这是一种反映了自我与社会发生了还不是尖锐的矛盾,却已有些‘异化了的精神状态”20。在浩浩汤汤的时代洪流中,徐迟对新时代抱有极大期望。然而,在张开怀抱、迈开脚步的追赶中,他却痛苦地发觉自己步履踉跄。面对克里·萨木金这面“镜子”,他觉得自己“也是掉在新中国里的一个魔影”21。在飞速前进的时代中,徐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开始痛苦地思索与转变。
二、复归的“平衡点”
1953年1月11日,徐迟响应号召来到了鞍鋼。初到建设工地,徐迟仍有些苦闷,“因为我真是从来也来22见过那么大的场面!不知有多少人,不知他们在现场干的什么,实在太突然了!”23但很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便深深感染了他。在工地上,徐迟见到了各式各样新奇的设备和壮观的场面。火炉加温设备激起的水蒸气,像云雾一般翻腾滚滚,壮观异常。工人的施工技术,令他惊叹:烧红的铆钉一扬手便飞到了十余米的高空,上面的人轻巧地接住,熟练地铆在了钢梁的开孔中。徐迟被这个场面深深地震惊了,“多么高超的技术呵!真使我在惊骇中倾倒,不胜钦佩之至”24。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宏伟气势,及从未接触过的崭新经验与经历,令徐迟兴奋异常。他迷失已久的创作动力和文学感觉,在这里似乎出现了:
总算我遵照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到了部队、农村和建设工地的火热的斗争中。兵、农和工,三处都跑到,发现我写兵士和农民不行,我不能理解他们,而写工地上的人似乎可以。国家和大规模建设正在开始,我愿意努力,为计划经济,为基本建设服务,似乎这件事是有点儿可能做到的。25
短暂的接触与适应过后,徐迟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鞍山钢铁工程基本概况和相应技术知识。一个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宏大框架和重大意义在脑海中逐渐建构成形,他很快便提笔写出了第一篇特写《难忘的一夜》。按照徐迟自己的说法,“这是我第一篇解放后的新作”26。这篇新作增强了他对创作的信心:
我开始展望到中国的未来。这可谓是我的极成功的一次创作上的探索性旅行。它是我一生中的文学生涯的新起点,是最难忘的重要的日子。现在,兵、农、工三个方面,我都已经接触过了。从此,我选定了以基本建设作为我后半生的永恒的主题了!27
在工地上,徐迟如鱼得水,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工程建设的恢宏气势,现代化的远大未来,工地上日新月异的进展和英雄人物异彩纷呈的故事,让他内心深受震撼,也找到了创作的动力与激情。按照单位的安排,徐迟在鞍山一共待了三个月。这段时间,对已经如鱼得水的徐迟来说,显然很不够:“和国家建设的恢宏气势相比较,我们编辑部也是太没有远见,给我的时间,是太少也太短了。”28但即便只有三个月,等他离开鞍山的时候,他冰封多年的内心世界,也如东北大地一样,在已经到来的四月春天中开始融化和苏醒。徐迟创作的激情和活力渐渐复归,异化感觉也因此得到了改善: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
我忽然发现我的异化感觉,一从鞍钢归来,就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已经和我那不协调的周围环境,协调得非常美满了。先前我有的那一种感觉,如同:呵哟,不好了,我一无所有了;我只能从零开始了;我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了。所有的悲惨心理,现已宣告结束。从我一到北京,参加革命的四年时间里,我的失魂落魄心理,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现在我已经充满了信心。感觉到我已经积累了许多的人们尚未注意到的新经验,特别是拥有了一些新经济的基本建设的知识。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建设气氛和一片烂漫前景,在召唤着我的激动的心,向它奔去,我在内心里作了决定:我要做社会主义建设工地的代言人。29
自此以后,徐迟将创作方向转移到了工业领域,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地上。这段路程虽遭曲折,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围绕着工业与科技的道路,徐迟的创作最终走向了科学,迎来了创作的又一高峰。
徐迟的遭遇在同代作家中并非个案,一批作家与他一样,在变化的时代形势中,或此或彼地陷入了个性意识冲突、文艺观念变迁带来的苦闷。在1940年代中期,身在延安的萧军已经流露出对文艺观念变化的不适。在稍后的1949年,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亦开始察觉到“个性”与“集体”的冲突:“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30对此,贺桂梅进一步指出:“这种独自一人游离于社会、时代,甚至日常生活之外的感觉,成为沈从文在1949年感觉到的最可怕的梦魇。”31无独有偶,姚雪垠在此阶段也陷入了观念变迁带来的创作危机:“由于我的创作道路和文艺思想同‘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我原来认为自己作为一個作家所具有的比较好的条件,不但不能发挥,反而被别人看成了长在我身上的‘封、资包袱。”32按照贺桂梅的看法,在1940年代后期,强调文学‘独立性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群体开始遭到打击和压抑33。而在“50年代之后,他们34逐渐认识到无法保持原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必须经历‘思想改造成为脱胎换骨的新人,才能成为新社会的合格成员”35。徐迟以及同代作家流露出的苦闷情绪,正与这段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相对于众多同时代作家,徐迟虽然深陷苦闷,但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却较为顺畅。这种“转变”虽看似“突兀”,但当我们综合把握徐迟前后遭遇时,却可以合逻辑地理解其特殊性及合理性。
徐迟的苦闷直接来源于他与变动环境之间的“错位”。在集体逐渐通过各种“计划”“组织”对个体进行“收编”的过程中,徐迟的个性意识、创作思想等方面显然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在内心深处,徐迟本人对新社会抱有极大期望与信心,并不排斥外在新环境的改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徐迟渴望拥抱新社会,但当他面对“错位”产生的矛盾和对立时,却并不能完全放弃“旧我”。他的内心深处,仍旧潜藏着一些难以名状的疑惑。
比如在广西,国家号召作家下乡体验生活书写“土改”成就,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体验所要求的“图解”式写作,又是违背徐迟创作直觉的——他认为不应当高度压缩作家的自主性,而是要从作家自身的创作意愿出发。一个公认正确的“前提”怎样导向了一个在徐迟看来并不正确的“结果”呢?这中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徐迟初到鞍山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段标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当时的感觉十分耐人寻味:
这字样,我不理解。左思右想,好像是对的,好像不太对,不过不知道怎么的不对。36
一定程度上,徐迟的感觉,正是他这一阶段内心疑惑的集中反映。当宏观层面的“导向”与具体问题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个人该如何是好呢?
或许,否定自己,全“新”融入是一种最迅速的解决方式。然而,徐迟却似乎走上了另一条充满挣扎的路——他不怀疑时代的大趋势,但他却也不否认自己直觉的提示。两相矛盾中,他找不到同时解答两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愿通过“排除法”来得到回答。
在四年间,这无言的矛盾如芒在背。徐迟晚年在回忆录中表明了这种矛盾和困惑状态:“我没有发现周围有过哪一个,曾为此而极其困惑过的。”37他自身顽强保留的直觉与意识像一根根冰冷的钢针,时时在刺痛着他。
然而,1953年初的这次鞍山之行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徐迟一直认为,作家的创作要从个人的体验与感受出发。而在朝鲜经历的不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军事题材与国际政治的紧密联系,政治形势的需求,显然要大过于作家本人的感受。正因于此,当时徐迟的第一篇文章才会被否,而第二篇文章却可照发不误。而在鞍山,大规模工业建设不仅对徐迟,而且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与体验。投入大量精力去探索、感受,是此时极为必要的过程。与此同时,出于宣传“一五”计划的目的,在工地上进行体验与感受的行为本身就是宣传的重要内容。这在客观上也为徐迟提供一个充分感受、体验的空间,满足了他对个人体验的重视,这无疑更让他如鱼得水。
此外,在充分体验的基础上,徐迟还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徐迟向来不喜欢按照外在的预设框架写作。广西的“土改”之行,在他看来就是围绕预设结构、结果来组织的体验、书写。从体验到写作,整个过程展现出步步紧扣的高度“程式化”。这一过程“实在是非常之腻烦的,即‘腻人‘烦人的”38。这对于徐迟来说,无疑极大地压抑作家个人的创作自主性以及积极性。而来到鞍山之后,工业建设的书写却令徐迟耳目一新。尽管这些报道与书写,在宏观上也难以脱离“图解”范畴,但相对来说却赋予了作家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广大空间。作为启蒙运动以来科技成果结晶的现代工业,其蕴含的知识密度和书写空间极为广大。相对于土地改革相关书写所承载的信息量,仅仅一项工程中的一个车间、一条生产线,就有非常丰富的开掘空间。它包含的科学背景与施工技术,应用场景与未来发展,连带其中的人与事,历史、现实与未来,横向与纵向的空间能够探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重领域,而且几乎可以无限延伸。这一切对于刚刚接触工业题材的徐迟来说,几乎是一个可以无尽书写的宝藏和自由翱翔的天地。虽然仍有外在要求,但这片领域却撑起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这片空间虽然有限,但徐迟期望的自主性却像得到了水的鱼儿,再次活动了起来。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
在这基础上,徐迟的个性意愿也与集体的要求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正如上文所说,徐迟内心的苦闷一定程度上在于外在的强大力量极度压缩了创作自主性。而在工业建设领域,徐迟却意外找到了一个留存的空间。工业本身是现代化的标志,工业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也代表了国家现代化未来的方向。工业建设这些特质以及“一五”计划的蓬勃推进,提供了一个空间,打开了徐迟被压抑的热情与热忱。整体来看,鞍山之行让他找到了自我“意愿”与集体“要求”的结合点,打通了个人情感生发与外在要求之间的通道。在鞍山,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新的工厂建成了》。在这首诗中,他展现了巨大的热情,激动地宣告:“社会主义的头胎婴儿,诞生了!”这种激动的心情,现在看来不仅仅是源自工地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克服了自己持续三四年的苦闷状况,完成了转变的过程:
而我自己可是十分认真地通过了三四年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它。最后费尽了心血,终于使我的个人与社会、个性和共性,越来越靠近,直至后来两者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大体上达到了统一,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活力,取得了稍稍的心安理得和较好的成效。39
当然,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徐迟的转变,与其说是“转变”不如说他在尽力的“适应”过程中,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他的矛盾与困惑并没有如他所愿,有了根本性的解答,而是被封存在了徐迟个人与集体的接合处。他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心态,接纳了这种平衡态,不再对其进行深究,直到其晚年。从徐迟晚年来看,环境的变化打破了这种平衡态,封存在结合点的矛盾与困惑,再度暴露出来,这种异化感觉又重新回来了。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三、现实性与抒情性:徐迟创作的新变
1949年之后,經过几年的适应与探索,徐迟从最初的苦闷中逐渐走出,克服了思想的“异化”。转变之后,徐迟积极融入了1950年代的时代大潮,他的创作此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了很多新变化。
在这期间,徐迟响应号召,在全国各处奔走,他创作的现实性因此显著增强。如他自己所说:
解放以前,我是一个在书堆里生活的人,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弄一点美学,也翻译一点,写一点诗——那是诉说自己的狭小心灵的诗。我所缺少的是实际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斗争。40
徐迟创作的现实转变在1950年代出版的两本散文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和《庆功宴》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两部作品集中反映了1953年以来“一五”计划的实施情况。徐迟围绕着工业化建设和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丰富的书写。
为了反映工业化建设的成就,徐迟先后奔赴各地,行程万余里,采访水利交通工程工地、工业建设、矿业开采。这些作品充分关注现实,写出了建设的火热现场以及人们的建设热情,充分反映了现实的巨大变迁。
在鞍山钢铁的建设基地,徐迟写下了《在高炉上》一文,具体介绍了鞍钢“三大工程”之一,我国第一座自动化高炉——八号高炉的建设情况,以点带面地反映了“一五”计划在钢铁领域的建设成就。在内蒙古草原,他深入地质资源勘探队,写出了《草原上的钻机》,反映了资源勘探队为西北工业建设勘探布局,为国家重工业建设勘探资源的辛劳与奉献,同样在侧面烘托了重工业建设在全国的计划与布局。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现场,他写下了《汉水桥头》,反映了建设者们攻坚克难、打通天堑的昂扬斗志,以长江大桥的建设,反映新时代人们“驯服”自然、改天换地的斗志。此外,他还探访水利工程规划建设的实况,写下了《三门峡通讯》,反映了三门峡水电站库址勘测活动,侧面描绘了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改善未来生产生活状况的美好图景。围绕着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探访河北饶阳县五公村的农业合作化改造,还写下了反映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的《真迹》和《滨湖来的人》。前者书写了珍古阁裘姓资本家清产核资进行改造的一个片段,后者则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反映了一个维修打字机的手工匠人接受改造的过程。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徐迟走出书斋走入现实,打开了书斋之外的宏大视野。他在《我们这时代的人》后记当中说:“我想我怎么能不充当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员呢?并且,我又怎么能不发为歌唱呢?”41在《庆功宴》后记中,他同样说道:“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深刻地感到了我们这时代的速度,它大踏步前进的响声,使我简直不能在屋子里坐下来了。”42因此,跟随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时代现场,徐迟充分贴近现实,真切记录了那个变动的时代。
在现实性之外,徐迟还充分展现出他的抒情特质。在1950年代这些贴近现实的书写中,他不再抒发个人的“狭小心灵”情感,而是围绕着时代的建设成就,用昂扬的声调和绚丽的色彩,以熊熊烈火般的激情,热忱歌颂。在文章中,他常常用诗化的语言直抒胸臆。在特写《汽车厂速写》中,徐迟用豪迈的语言介绍了汽车厂的建设:“听吧!凌驾于一切之上,一个雄伟的大合唱在歌颂着祖国,‘从今走入繁荣富强,庄严、嘹亮而雄壮。”并用人物的口吻进一步说道:“1952年,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开工了。”在结尾,徐迟更是热情歌颂道:
建设新中国,今天已经是一个现实。在这个汽车厂工地上,在这个汽车城中,怎么能不感觉到这个呢?五年计划的巨大蓝图,已经在地上矗立起来了!新中国这样日夜沸腾的建设生活,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这个生活的脉搏啊!43
在《三门峡通讯》一文中,他同样不断用抒情的口吻歌颂了克服困难施工的队员:“看,这些年轻人是如何战胜陡岛、寒冷和削壁的啊!”44这些书写事实上与文本内容并不直接相关,而是作者主观介入,以带有强烈听觉特质的书写,直接抒发着炽烈的情感。
在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中,徐迟这种热烈抒情体现得更为明显。为了反映鞍山无缝钢管厂的落成,他用《新的工厂建成了》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工厂建成了,欢呼着第一根无缝钢管的诞生。社会主义的头胎婴儿诞生了。”45在内蒙古他写出《在白云下》,歌颂即将建成的工业基地“你是祖国富强的基地”46。同样,他在青海写下《青海基地》:“婴孩将成长为英雄,青海基地是我们新的骄傲。”47在《春雷》中,他高唱:“新中国的春天已经来临,跟着要来到全人类之春。”48在这些文本中,徐迟大量运用动词和抒情式语气词、感叹词,加之情感丰沛的形容词直抒胸臆,如“看”“听”和“啊”“呢”“吧”等,情感的调值十分高扬。此外,徐迟将带有象征色彩的词语和句式结合使用,鲜艳的色彩、寥廓的景象,充分展现出一幅宏广的画面和时代进步的昂扬势头。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
总而言之,徐迟在找到自身与时代融合的平衡点后,积极走入时代与现实,较为成功地将个人创作激情与时代的建设发展融为一体。徐迟对时代新变化、新发展的现实书写与热情歌颂,构成了他1950年代创作的主色调。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创作虽然贴近现实,激情澎湃,但仍无法掩盖自身的诸多问题。文本突出的现实性一定程度上淹没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性。徐迟响应时代召唤,走入工厂与工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飞速进步与现代化建设的一日千里。激情澎湃的建设场面诚然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无比振奋,歌颂与弘扬自然也会成为感情的重心、写作的重点。徐迟这一阶段的创作,正因于此而集中贴近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感受的多面性,极易滑落回“图解”写作的窠臼。同时,这种极强的现实性,压缩了徐迟对个体的关注与展现。突出现实性将写作的准星瞄向了建设的“成就”。而徐迟本人试图秉承的创作动因,则在无形中受到了影响。抽象的“成就”成为写作的目标,而具体的人与事,反而成为“手段”,沦为了模糊的背景,这显然有本末倒置之嫌。
此外,文本突出的抒情性压倒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近乎千篇一律的抒情与歌颂,很快形成了规范的模式与套路,淹没了丰富的现实与情感,很多感情与人物也因此变得空洞、抽象与平面化。徐迟这一阶段对建设成就的书写,虽然看起来气魄宏大、感情充沛,但在不断的重复中,也不免越来越流于刻板与空洞。同时,这种抒情性还带来过度强烈的主观介入性。作者的主观理念淹没了艺术形象,基本阻断了读者与形象世界的联系。徐迟这一阶段的许多作品主观介入非常明显,口号与观念压倒了对客观现实的准确描摹、展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意味的寡淡。
结语
徐迟在1950年代完成了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在思想上,他逐步抛弃了所谓的“个人意识”而开始适应了新时期的“集体生活”。在创作上,他体验了“兵、农、工”的生活,找到了适应个人创作的工业题材,并迅速写出了一系列紧贴现实、风格昂扬激越的特写与诗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看似迅速,但很大程度上沒有真正解决徐迟思想层面的深层疑惑——思想与创作的矛盾仍旧封存在精神深处。他虽然投身时代积极创作,找到了一个足够翩然起舞、思绪飞扬的“缝隙”来安放自身,却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特质——时时露头的“个人思想”常常令他饱受批评。而随着历史时代环境的变化,隐身在深处的困惑仍旧时时浮起,不断在叩问着徐迟的内心。
尽管如此,对于徐迟来说,1950年代仍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如果我们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视为徐迟一生的创作顶峰,那么,1950年代徐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无疑是通向顶峰的一个重要关口。无论是从诗歌转向散文,还是从“书斋”走向“现实”,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极富矛盾也极有意义的一段时期。
【注释】
①徐鲁:《徐迟和〈江南小镇〉》,《中华读书报》2010年09月01日。
②③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6373839徐迟:《徐迟文集第十卷·江南小镇(下)》,作家出版社,2014,第121、121、121、121、122-123、123、135-136、136、141、141、137、141、141、147、122、122、122、146、146、147、147、150、150、164、146、122、138、122页。
④[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冯兴元、毛寿龙、王明毅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80页。
⑤⑥徐迟:《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作家出版社,2014,第131、131页。
22原文如此,疑为“未”。
30沈从文1949年9月20日给张兆和的信,收入《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沈虎雏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163页。
313335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97、8、6页。
32姚雪垠:《姚雪垠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第58页。
34此处指“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亦包括作家群体。
40徐迟:《徐迟文集第八卷·杂文》,作家出版社,2014,第133页。
414344徐迟:《我们这时代的人》,作家出版社,1956,第198、66、126页。
42徐迟:《庆功宴》,作家出版社,1957,第162页。
45464748徐迟:《徐迟文集第一卷·诗歌》,作家出版社,2014,第165、169、237、168页。
(李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