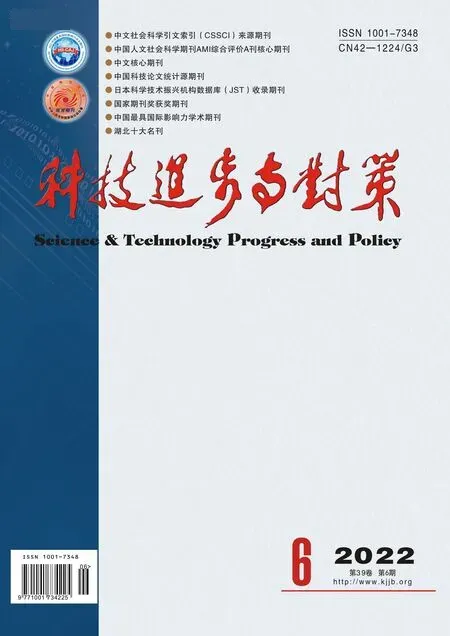助推力还是绊脚石?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双刃剑”影响
2022-03-28刘平青刘园园刘东旭刘淑桢
刘平青,刘园园,刘东旭,刘淑桢
(1.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2.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高质量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创新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创新行为的推动,不仅需要提高整个组织的创新水平,而且,企业中自下而上由员工驱动的创新行为也不容忽视[1]。员工创新行为不仅包括创新思想、想法等的产生,也包括创造性行为、产品等结果的实现[2]。学术界和管理者越来越关注如何激发和保持企业员工创新行为。学者们普遍认为,有效的互动[3-4]、积极的氛围[5]、积极的领导力[6-8]等支持性、稳定性因素是激发创新行为重要方面。然而,随着组织外部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组织合并重组、裁员、临时或短期雇用合同等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就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安全感所替代,成为一个常见的职场心理问题[9]。工作不安全感是指个体对工作本身或重要工作特征(如职位、薪酬等)未来可能会失去或丧失的担忧[10]。因此,在工作不安全感日益普遍的时代,如何管理和激发组织创新行为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由于研究视角差异,学术界关于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些学者采用压力或社会交换视角,将工作不安全感理解为一种阻碍性压力源或雇员与雇主之间交换关系的不平衡[11],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阻力”和“绊脚石”,会对创新行为产生负面影响[12-13];另一些学者从工作保留动机或主动应对视角出发,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正面的刺激即“动力”和“助推力”,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达到保留工作的目的,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反而有利于创造力提升[14-15]。由于研究视角差异,造成组织管理实践中两难的局面,那么,究竟是完全避免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还是引入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并购重组等竞争机制(即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不安全感)更有利于激发员工创新行为?
过分安逸的环境也容易滋生懈怠情绪,而来自外界的压力并不一定总是坏的。压力交互理论(Transactional Theory of Stress)指出了压力的两面性,来自外界的压力并不一定总是坏的。该理论认为,由于评估过程的差异,压力会被个体评价为阻碍性压力或挑战性压力,相应产生消极回避或主动应对两种不同行为策略,即阻碍性压力消耗内在资源,而挑战性压力激发个体采取主动应对策略。同时,元分析表明调节焦点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对员工行为具有独特解释力,促进型焦点和防御型焦点的差异揭示了个体对事物产生不同感知的内在原因及相应行为策略[16]。因此,本文引入压力交互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构建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双刃剑”作用模型,尝试回答中国情景下工作不安全感产生的“边界困境”问题,从而为在中国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解决工作不安全感问题,以及从权变角度激发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压力交互理论
压力普遍存在于工作场所之中且不可避免[17],在过去的研究中,工作场所压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情景,因为它超出了个人的能力或资源范围,并且会对个体造成一定的负担[18]。尽管压力通常被认为具有负面影响,但压力交互理论表明,压力可以分为挑战性压力(促进个人成长和实现成就的压力,如工作量、时间压力、工作范围、高度责任等)和阻碍性压力(限制个人发展或阻碍取得工作成就的压力,如组织政治、繁文缛节、角色模糊等),不同的压力类型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19]。
压力交互理论指出,刺激本身并不是个体作出反应的直接诱因,而是取决于如何评估这些刺激的意义。也就是说,对情境的评价(初级评估)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价(次级评估)在压力应对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其是将压力与结果联系起来的重要心理机制[20]。基于压力交互理论,当面临工作本身或工作特征丧失的压力时,个体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策略离不开对内外部资源的评估,一方面是基于对外界组织成本的评估,另一方面是基于对自身风险预防能力的评估。
1.2 挑战性压力的中介作用
如果个体认为工作中的变革、未来的愿景描绘有助于获得奖励(如认可和表扬)和个人成长,并且认为这种要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应对这种情境),他们就会对工作不安全感作出挑战性的评估,将其视为挑战性压力[21]。从压力交互理论来看,如果工作场所中的压力被评估为潜在挑战性的情境,那么就会产生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积极应对方式,比如增加努力以满足情境要求。挑战性压力包括较高的工作期望、紧急的时间压力、宽工作范围和高度责任感,并被视为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成长[22-23]。当个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有积极的感觉时,他们往往会有积极的情绪,感受到对组织的义务[24],表现出更高承诺、敬业度和组织忠诚度,并以有利于组织的方式行事[25-27]。通过激励个体努力工作[28],挑战性压力可以使个人体验到活力感和学习感,从而在工作中茁壮成长[29]。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挑战性压力可能激发内在创造性行为[30-31]。
综上,基于压力交互理论,工作不安全感应对是情境要求与处理这种要求的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情境要求很高,且个体认为这种要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则会对情境作出积极评价,进而激发主动应对策略,做出更多被组织所看重的创新行为,提升自我积极形象和把控未来的能力,以此降低未来遭受损失的几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挑战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个体创新行为关系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1.3 阻碍性压力的中介作用
如果个体意识到自身工作不安全感的威胁很严重(比如妨碍职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威胁个人收益和幸福等),而且自己处理这种要求的能力不足,个体就会对工作不安全感作出阻碍性评估,将其视为阻碍性压力[32]。大量研究表明,阻碍性压力会降低个体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产生更多反生产行为和退缩行为。元分析也表明,感知到阻碍性压力的个体认为压力阻碍个人成长和成就[33],导致心理安全水平较低[34]。因此,个人将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减少从事超出工作职责以外的任务,避免做出可能不被认可的创新性行为,以降低受到惩罚或误解的风险。当员工在工作场所遭受阻碍性压力时,往往倾向于将工作环境视为贡献与回报不一致的地方,于是,减弱为组织创造利益的动机,减少有助于组织绩效改善的创新行为[35]。
综上,如果情境要求很高,而个体觉察到自己能力不足,则会作出退缩放弃评价。进一步,如果个体在经历工作不安全感时知觉到无法获得上级满意或认可等,则会评估工作不安全感具有阻碍性,并且认为消耗更多资源从事角色外行为(如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创新行为)是无用的,来自未来不确定性威胁的压力将会阻碍个体采取主动应对策略。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阻碍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个体创新行为关系中发挥负向中介作用。
1.4 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个人特质影响个体如何看待压力,因此,需要深入研究人格特质与压力间如何相互作用。工作不安全感代表对潜在威胁事件的适应性反应,该适应性反应是一种回避性的保守行为还是一种创造性的开发行为,取决于个人具有更强烈的促进型焦点还是防御型焦点。Higgins[36]认为,在人们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认知与行为差异,并据此提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享乐自我调节系统,一个被称为促进型调节焦点,另一个被称为防御型调节焦点。当以促进型焦点为中心时,人们会受到成长和发展需求的激励,试图使自己的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保持一致。当以防御型焦点为中心时,人们更注重安全需求,试图将自己的实际自我与应该自我(现实中应该承担的职责和责任)相匹配。
不同的调节焦点会产生不同的期望目标,也需要采取不同的目标实现策略。研究表明,有很强促进型焦点的个体对积极结果的存在/不存在很敏感,对机会也很警觉,一般采用接近、迫切的策略实现目标。相比之下,具有强烈防御型焦点的人强调安全和避免损失,对负面结果的存在/不存在更加敏感,更关注可能存在的威胁,采用避免、警惕策略实现目标[37]。本文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对未来事件而非当前情境中已经存在事件的感知,以促进型焦点为导向的个体通常将工作中出现的不安全感看成一种挑战性压力,期望通过自己的主动努力克服“无获得”的未来情景,由此激发个体的未来提升策略,即渴望策略。这种渴望成功的策略促使个体抓住机会[38],针对情境需求展示出更多不同解决方案,无形中促进创造力提升。相反,具有较强防御倾向的个体对“损失”结果更敏感,在感知到工作中存在不安全感时,更多地产生消极心理体验,更倾向于将工作不安全感看成阻碍性压力。由于其对不利线索的接受能力有限,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将使个体更多使用预防策略,即采用更为回避、警惕的方法。这些人将采用众所周知的、经过检验的方法,导致更保守、更缺乏创造性的反应。
在面对工作不安全感时,以促进型焦点为中心的个人更倾向于将其视作挑战性压力,不仅有更多解决方案,而且更有可能选择具有新意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相反,以防御型焦点为中心的个人更倾向于将工作不安全感视作阻碍性压力,不仅解决方案更少,而且倾向于更安全、创造性更小的解决方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促进型焦点在工作不安全感影响挑战性压力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促进型焦点水平较高时,工作不安全感对挑战性压力的正向影响更强。
H4:促进型焦点调节工作不安全感通过挑战性压力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即当促进型焦点水平较高时,工作不安全感通过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更强。
H5:防御型焦点在工作不安全感影响阻碍性压力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防御型焦点水平较高时,工作不安全感对阻碍性压力的正向影响更强。
H6:防御型焦点调节工作不安全感通过阻碍性压力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即防御型焦点水平较高时,工作不安全感通过阻碍性压力负向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更强。
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双刃剑”影响模型Fig.1 "Double-edged sword" model of job insecurity to innovative behavior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程序及样本
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两阶段直接领导—员工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包括两种:直接领导问卷和员工问卷。员工主要汇报自己在工作场所中的不安全感知、调节焦点类型、压力感知类型,由直接领导在一个月后对员工创新行为进行评价。为了保证问卷效度,主要采用现场调查和回收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选取河南省12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调查对象,其主要从事五金电子、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研究和开发。对每个团队的员工进行编号,作答时每个员工需要在问卷上填写自己的编号,直接领导在填答时也在问卷上填写自己团队员工的编号,通过员工编号进行配对。本次调查共向62个团队发放450份问卷,回收438份,剔除填写不完整、有明显作答规律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最终保留60个团队有效问卷414份,有效回收率92%。
从性别结构看,员工样本中男性较多,有251人,占60.63%,女性163人,占39.37%;从婚姻状况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已婚,有235人,占56.76%,未婚160人,占38.6%;从年龄结构看,调查样本主要集中在25~45岁之间,占61.60%,其次分别为45~55岁、25岁及以下、55岁以上,分别占17.87%、13.53%和7.00%;从教育背景看,被调查者主要学历是本科以上,其中,本科、研究生分别占45.65%和28.99%,大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分别占23.19%和2.17%;从工作年限看,主要是3~5年和5~8年,分别占31.40%和36.96%,其次是9~11年,占19.08%,此外还有少部分2年及以下和11年以上,分别占8.70%和3.86%。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测量量表均来自国际知名期刊,且这些量表在中国情景下得到广泛应用并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和适配性。为了确保题项在语义上的完整性,根据Brislin(1986)提出的量表“翻译—回译”法进行检验。量表均采用Likert-5点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比较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采用Hellgren等[39]开发的量表测量工作不安全感,共7个题项,包括数量工作不安全感和质量工作不安全感两个方面。数量工作不安全感包括3个题项,如“我担心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会失业”;质量工作不安全感包括4个题项,如“我现在的职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采用Shin[40]开发的量表测量调节焦点,该量表是根据Neubert等(2008)的工作调节焦点量表(Work Regulatory Focus Scale,WRF))改编而来,共6个题项,包括促进型焦点(Promotion Focus)和防御型焦点(Prevention Focus)两个方面。促进型焦点包括3个题项,如“成长的机会对我来说是找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防御型焦点包括3个题项,如“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避免工作失败上”。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采用Cavanaugh等[41]的量表测量挑战性压力(Challenge Stress)和阻碍性压力(Hindrance Stress),共11个题项。其中,挑战性压力包括6个题项,从工作任务量、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责任量等6个方面衡量个体感受到的挑战性压力水平;阻碍性压力包括5个题项,从组织内部关系对组织决策的影响程度、无法清楚地了解工作对我的期望等5个方面衡量个体感受到的阻碍性压力水平。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采用Zhou等[42]编制的创新行为量表并经过改编,测量创新行为,共13个题项,如“提出实现目标的新方法”等。该量表由团队直接领导作答,对每个成员的创新行为作出评价。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工作不安全感、创新行为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年限等的影响。因此,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年限设置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一方面,采用领导和下属配对数据并在不同时间点采集,对研究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共得到6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未经旋转的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56%(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以继续进行深入分析。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六因子模型与其它5个竞争模型的拟合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六因子拟合效果最好(χ2/df=2.45,RMSEA=0.05,CFI=0.93,NFI=0.94,TLI=0.93,IFI=0.94),说明本模型的主要变量间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之间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工作不安全感与挑战性压力显著正相关(r=0.23,p<0.01),工作不安全感与阻碍性压力显著正相关(r=0.19,p<0.01),挑战性压力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0.48,p<0.01),阻碍性压力与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r=-0.26,p<0.01)。以上分析结果为研究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也为后续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1 六因子模型与竞争模型拟合情况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fitting between six factor model and competition model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3.4 假设检验
3.4.1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程序检验。采用样本自助抽样法对模型中估计参数进行重新抽样和置信区间估计,基于5 000次重复抽样模型,利用SPSS软件的Process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果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成立。
假设H1提出,挑战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个体创新行为关系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首先,在SPSS软件的Process程序中,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年限)、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中介变量(挑战性压力)、因变量(创新行为)依次引入;然后,选择模型4,样本量选择5 000次,置信区间选择95%,Bootstrap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挑战性压力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中介效应值为0.13,95%置信区间为[0.066,0.203],不包含0,表明挑战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因此,假设H1得到支持。

表3 挑战性压力中介效应的Bootstrap分析结果Tab.3 Bootstrap analysis results on mediating effect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假设H2提出,阻碍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个体创新行为关系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首先,在SPSS软件的Process程序中,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年限)、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中介变量(阻碍性压力)、因变量(创新行为)依次引入;然后,选择模型4,样本量选择5 000次,置信区间选择95%,Bootstrap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阻碍性压力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中介效应值为-0.06,95%置信区间为[-0.122,-0.017],不包含0,表明阻碍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因此,假设H2得到支持。

表4 阻碍性压力中介效应的Bootstrap分析结果Tab.4 Bootstrap analysis results on mediating effect of hindrance stressors
为了进一步检验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的中介效应,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部分中介模型(模型1)、完全中介模型(模型2)和无中介模型(模型3),通过比较各模型的拟合指数确定哪个模型更加适合。由表5可知,部分中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明显优于完全中介模型((1)=20.97,p<0.01)和无中介模型((1)=31.93,p<0.01),说明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为了进一步分析路径系数,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两个嵌套模型进行对比(模型4和模型5)。由表5-表7可知,模型4((1)=246.73,p<0.01)、模型5((1)=135.76,p<0.01)与基本模型(模型1)的差异均显著,表明基本模型(部分中介模型)为最优拟合模型。因此,嵌套模型4和模型5均被拒绝。
根据模型对比分析结果可知,模型1所表达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合适,即挑战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阻碍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模型的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31,p<0.01),工作不安全感与挑战性压力显著正相关(β=0.22,p<0.01),挑战性压力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β=0.33,p<0.01),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部分通过挑战性压力产生作用。工作不安全感与阻碍性压力显著正相关(β=0.30,p<0.01),阻碍性压力与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β=-0.19,p<0.01),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部分通过阻碍性压力产生作用。因此,假设H1和H2进一步得到支持。

表5 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比较Tab.5 Comparison of fitting indexe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图2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结果Fig.2 Path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hallenging-hindrance stressors
3.4.2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在构建工作不安全感与促进型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与防御型焦点交互项时,预先将工作不安全感、促进型焦点、防御型焦点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模型2中工作不安全感与促进型焦点的交互项对挑战性压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p<0.01),模型4中工作不安全感与防御型焦点的交互项对阻碍性压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5,p<0.01)。因此,假设H3和H5得到初步支持。

表6 层次回归结果Tab.6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根据simple slope检验结果,绘制不同水平(±SD)调节焦点下工作不安全感对挑战性压力或阻碍性压力的不同影响。如图3所示,与促进型焦点较低的员工相比(simple slope=0.08,p<0.05),对于促进型焦点水平较高的员工来说,工作不安全感对挑战性压力的正向影响更强(simple slope=0.52,p<0.01)。因此,促进型焦点在工作不安全感对挑战性压力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假设H3得到支持。如图4所示,对于防御型焦点水平较高的员工来说,工作不安全感对阻碍性压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imple slope=0.35,p<0.01);对于防御型焦点水平较低的员工来说,工作不安全感与阻碍性压力之间的关系不显著(simple slope=0.05,n.s.)。因此,防御型焦点在工作不安全感对阻碍性压力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假设H5得到支持。
参照Preacher等(2015)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模型,采用SPSS中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在高促进型焦点水平下,工作不安全感通过挑战性压力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显著(效应值r=0.31,S.E.=0.05),置信区间为[0.216,0.417],不包括0;而在低促进型焦点水平下,工作不安全感通过挑战性压力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不显著(效应值r=0.05,S.E.=0.03),置信区间为[-0.018,0.118],包括0;高促进型焦点水平和低促进型焦点水平两种情景下的中介作用效果有显著差异(差异值r=0.26,S.E.=0.06),置信区间为[0.168,0.373],不包括0。因此,假设H4得到支持。
在高防御型焦点水平下,工作不安全感通过阻碍性压力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显著(效应值r=-0.06,S.E.=0.02),置信区间为[-0.108,-0.019],不包括0;在低防御型焦点水平下,工作不安全感通过阻碍性压力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不显著(效应值r=-0.02,S.E.=0.02),置信区间为[-0.055,0.011],包括0;高防御型焦点水平和低防御型焦点水平两种情景下的中介作用效果有显著差异(差异值r=-0.04,S.E.=0.02),置信区间为[-0.084,-0.002],不包括0。因此,假设H6得到支持。

图3 促进型焦点的调节作用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moting focus

图4 防御型焦点的调节作用Fig.4 Moderating effect of prevention focus

表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Tab.7 Testing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4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
根据压力交互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本文构建以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为中介变量、促进型焦点和防御型焦点为调节变量的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双刃剑”影响理论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个体由于认知评估过程和自我调节系统不同而对工作不安全感产生的不同认知和行为方式。选取河南省12家高新技术企业60个团队414份领导和员工的配对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1)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这契合了刘淑桢等[43]、周浩等[14]的研究结果。工作不安全感对挑战性压力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挑战性压力源在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创新行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工作不安全感通过挑战性压力源的认知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这种积极效应受到个体调节焦点的影响,即促进型焦点在工作不安全感与挑战性压力源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当个体处于高促进型焦点水平时,工作不安全感与挑战性压力源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本文还证实促进型焦点具有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促进型调节焦点能够强化挑战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工作不安全感会通过挑战性压力认知和促进型焦点的调节导向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个体创新行为的“动力”和“助推力”。
(2)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这与大多数工作不安全感作用效果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44-46]。工作不安全感对阻碍性压力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阻碍性压力源在工作不安全感影响个体创新行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工作不安全感会通过阻碍性压力源认知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而且,这种消极作用受到个体调节焦点的影响,即防御型焦点在工作不安全感与阻碍性压力源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当个体处于高防御型焦点水平时,工作不安全感与阻碍性压力源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本文还证实防御型焦点具有被调节的中介作用:防御型调节焦点能够强化阻碍性压力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工作不安全感会通过阻碍性压力的认知和防御型焦点的调节导向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成为个体创新行为的“负担”和“绊脚石”。
4.2 理论意义
(1)基于压力交互理论,构建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双刃剑”模型,丰富了工作不安全感作用机制相关研究。自工作不安全感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已从压力、社会交换、工作保留动机等多个角度探究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作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研究视角差异,现有研究对于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间关系存在一定分歧,产生了“管理困境”,在组织中究竟是应该消除工作不安全感还是引入一定的竞争因素呢?以往的理论对揭示工作不安全感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压力交互理论,认为人们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其工作环境,是将工作不安全感概念化为实现理想和收益的机会,还是将其视为需要避免损失和履行各项义务与职责。若是前者,那么他们的反应更有可能是创造性的;若是后者,那么他们的行动不太可能具有创造性。本研究借鉴压力交互理论将工作不安全感产生的积极和消极效应纳入同一个框架中,从而更全面地阐释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扩展关于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
(2)基于调节焦点理论,本文提出促进型焦点和防御型焦点对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的调节机制,拓展了工作不安全感作用边界相关研究。现实中企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同员工在面对相同工作不安全感水平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反应和绩效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员工在高压面前表现出积极心态,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激发工作动力;而有些员工会焦虑不安、心不在焉、无心工作,严重影响自身工作任务的完成。那么,一定存在某些个体差异变量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反应。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研究以促进型焦点和防御型焦点为调节变量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这一思路也验证了Tu等[47]的研究,个体对工作不安全感的态度、决策、行为等受到个体自我调节系统的影响,调节系统不同,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和行为取向也会不用。促进型焦点的个体在面临高工作不安全感时,会产生期望继续留任组织、获得就业持续性收益的想法,为了获得未来收益和提高绩效,他们会被激励改变工作的各个方面,也会采取更多能够产生高绩效的创新行为。而防御型焦点的个体在高风险低收益和自我保护模式下,会为了避免错误更加关注责任和义务,毕竟创新行为具有一定风险性,这与他们避免失去的自我控制系统不相符,因此,防御型焦点的个体更不愿意从事创新行为。
4.3 管理启示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组织灵活度的提高,工作不安全感成为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对个体心理、状态、行为、家庭和团队产出、团队有效性等产生重要影响,有效管理工作不安全感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根据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工作场所中的不安全感进行管理,以便最大程度激发员工创新行为。
(1)合理管理工作场所中不安全感。工作不安全感可以成为激发创新行为的“动力”,因此,企业可以引入工作不安全感,设置以动力为导向的工作不安全感激励机制。例如,将短期雇佣模式打造成相互投资型的雇佣关系;调整薪酬结构,采用多元化的绩效奖励方式;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实现职位可上可下、可进可退;设置挑战性工作任务,确保及时反馈奖励机制落实。同时,工作不安全感也可能成为“阻力”,因此,组织在适度营造不安全感时,也要采取措施避免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影响。比如主动向员工传递信息,帮助成员了解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给予员工更多关爱和支持,营造良好人际氛围,增强组织与成员间联结,促使员工从内心接受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降低对工作不确定性的担忧。
(2)提高挑战性压力应对能力并及时疏导阻碍性压力。工作不安全感会通过挑战性压力对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通过阻碍性压力对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一方面组织应增强个体应对挑战性压力的能力和信念。比如,帮助个体树立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理念,提升对任务要求的解决能力、处理能力;帮助员工建立包括家庭、同事、领导、专业医师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另一方面,应及时疏导阻碍性压力。比如,个体做好时间规划和管理、劳逸结合参加运动等帮助恢复工作精力;组织营造容错试错、接纳失败的和谐工作氛围,鼓励员工勇于尝试,降低心理压力和负担。
(3)针对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和团队采取不同管理方式。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不同作用效果受到调节焦点的影响,为了提高创新水平,针对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和团队应该采取不同管理方式。调节焦点按照形成方式的不同分为长期型和情境型,前者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长期人格特质,具有一定稳定性;后者是受工作状态、情境环境等影响的短期激励取向,具有一定可塑性。因此,根据调节焦点的两种形成方式,从选拔、培训、日常管理、绩效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4个环节出发,建议在选拔阶段,挑选具有长期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在内部培训时,有针对性地培养员工的促进型调节意识;在日常管理中,注重激发员工的情境型促进型焦点;在绩效考核时,针对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和团队采取不同考核与评价方式。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1)本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均为横截面数据,而横截面数据在解释变量间因果关系上具有一定局限性。调节焦点的测量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虽然这种测量方式在相关研究中也被广泛使用,但有学者指出实验法能够更加有效地发现个体调节倾向。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问卷调查与实验法相结合的形式,进一步对研究模型的有效性和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2)本研究探讨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未来可以采用更加融合的跨学科视角,将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人力资源管理以外的领域,如创新创业领域。随着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和支持,加上便利的互联网大环境也促使很多人尝试创业活动。如王蒙蒙[48]研究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全职/兼职创业意向的影响,发现在职职工容易产生兼职创业意愿。未来可深入挖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进一步体现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3)从结构维度看,有学者将工作不安全感划分为不同维度(如数量工作不安全感和质量不安全感、认知工作不安全感和情感工作不安全感),但大多数研究都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对个体心理、行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将工作不安全感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对个体、团队创新行为的不同影响,而最近学者们开始进行更精细化的研究,对工作不安全感进行分维度探讨,发现工作不安全感不同维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比如,Tu等[47]探讨了数量和质量工作不安全感在预测员工压力症状(身体和行为压力症状)和动机状态(工作投入)方面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数量工作不安全感和质量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压力和动力有不同影响,数量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身体、行为压力更相关,而质量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工作投入更相关。Blomqvist等[49]发现情感性工作不安全感与精神药物、抗抑郁药及抗焦虑药的购买有关,而认知工作不安全感仅与抗抑郁药购买有关。这些研究说明区分不同类型工作不安全感很重要,未来可以对工作不安全感进行分维度研究,进一步探讨工作不安全感作用效果差异是否由工作不安全感的不同维度引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