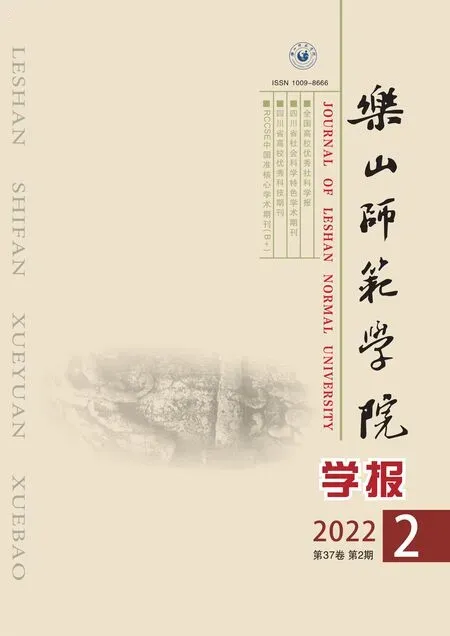只有无何真我里
——析苏轼对《庄子》“无何有之乡”的接受
2022-03-25李菁
李 菁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 天津 滨海 300450)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曲折坎坷。在这苦难、波折的生活境遇下,有着文豪这一身份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睿智思考能力的他,无不促使他对现实人生作出深邃精微的思考,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这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评价言:“苏轼算不得擅长抽象思辨的哲学家,但他通过诗词文所表达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几位前贤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来,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1]苏轼一生深受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影响。在苏轼的诗词里,《庄子》“无何有之乡”这个典故至少出现了七次,这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既有的研究较少从典故的角度深入解析苏轼诗词中的“无何”。陶慧认为苏轼追寻的是存在于心灵之上的逍遥自适的“无何有之乡”。[2]宁雯也论述了“无何有之乡”是苏轼内心保有的终极归宿。[3]两位学者都是认为苏轼的“无何”是心灵向往的境界,这对此文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以上学术成果并没有过多揭示苏轼诗词“无何”的丰富含义,以及其与《庄子》“无何”之间的密切关系。苏轼诗词创作多次引用《庄子》的“无何有之乡”,这绝非文字符号的简单重复,另有深意。苏轼自幼与庄子有着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4]因此,本文以苏轼诗词的“无何”典故为研究对象,探析苏轼对《庄子》“无何有之乡”的接受。
一、概说《庄子》“无何有之乡”的双重含义
《庄子》的语言充满了诗学的韵味,多以寓言说理,言简意赅却又意境深远。“无何有之乡”虽字句简短,而蕴含的含义实则有表层与深层之分。
(一)表层含义:一处广莫无垠、空无虚幻的天国
“无何有之乡”的表层含义,是指它字面上的综合意思。“无何有之乡”在《庄子》一书中,总共出现了四次。成玄英为《庄子》作疏,将其解释为:“无何有,犹无有也。莫,无也。谓宽旷无人之处,不问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乡也。”陆德明《释文》:“‘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谓寂绝无为之地也。”[5]今人陈鼓应则解释为“虚寂的乡土”。[6]39根据各家的注疏与解释来看,“无何有之乡”指一处广莫无垠、空无虚幻的天国,这是它字面上的表层含义。
(二)深层含义:逍遥自适的精神乐园或人逍遥自得、自然纯真的生命状态
“无何有之乡”的深层含义,是指它在寓言情景下所含有的意思。成玄英等人只对“无何有之乡”这一词做出了个别对象的解释,他并没揭示“无何”的深层含义。要把握“无何”的深层意义,必须将其放在更为广大的能包容该物存在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解释。正如马克·昂热诺学者在《问题与观点》中,表达了他对个别解释对象的看法相类似,他说:“个别对象一般没有解释的必要,只有当它们在某个既定的背景中产生问题时,解释活动才介入。所以解释所涉及的背景是意义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7]“无何有之乡”应当放在《庄子》篇目中所在的寓言进行阐释,以期有助于我们把握“无何”深层的含义。
在《逍遥游》里,“无何有之乡”是在庄子和惠子讨论大樗有无用的寓言之内。惠子代表了一般世人的社会现实意义的价值取向,只关注能为我所用的一面、即实用性。而庄子眼里,大樗虽是至大无用但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不在现实世界里体现,应当是种植在“无何有之乡”这个广莫无垠、无性命杀害的地方里。在“无何有之乡”里,大樗不会受到斧头等象征有害事物的伤害,体现出因它的无用而带来的无害与自由,不但保全了它原本的样貌,还保存了它的自然本性和生命本真存在的价值意义。大樗在“无何有之乡”里是可以逍遥无待,自由而无害。即,“无何”是个自由无害的世界。
在《应帝王》,“无何有之乡”出自无名人这个寓言人物之口。《庄子》寓言人物的名字是富有深义的。王博先生是从寓言人物的名字寓意来解读文本,他说:“单纯从名字上来论,日中始和无名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对子。当日中始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支配他人的乐趣时,无名人却在无何有之乡游历。”[8]134可见,无名人是不受权力支配的人,他不追求权力以及不以权力为乐。他是“与造物者为人”,即他与大道为友。他是一个已经领悟“道”的意义的人。他的处世态度就是拒绝权力威胁与逼迫,顺应万物自然,听任心灵自由。而与无名人相对的日中始,他代表着这一类人——利用手中的强权去威逼百姓服从的人。按照王博教授的话来理解就是:他们“以人从己,很明显地把自己摆在了如太阳般‘中心'的角色。”[8]133《应帝王》的题解,主要是阐释庄子的政治哲学。那么,通过日中始和无名人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略窥庄子所向往的理想政治王国。他的理想政治王国是君主不以权力威逼百姓遵守与服从,不强权自我私意与他人。对庄子个人而言,在“无何有之乡”里,他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不受到任何的胁迫,能顺心自由、顺物自然。
在《知北游》里,“无何有之官(乡)”是在东郭子问“道”这个寓言里,庄子回答“道”是无处不在。庄子还邀请东郭子一起游“无何有之乡”,并且一起顺应自然无为(自由无拘束地遨游)。他们的心境是“恬淡而安静,漠然而清虚,调和而悠闲”[6]663。这般心境是何等安然自适与逍遥自由!在这个寓言中,“无何有之乡”是庄子和东郭子体“道”的地方,他们认识到“道”:在空间上是无穷尽,在时间上是无始终;“道”本身无界限,无聚散,并且遍布在天地万物之中。换言之,人遨游于“无何有之乡”这个地方时,心情不仅悠闲舒畅,人们还能够在此消解时空之困。
在《列御寇》里,“无何有之乡”是在朱泙漫技成而无所用其巧的寓言里。这寓言批评凡夫的心智时刻关注着应酬交际或是一些劳弊精神的浅陋事情,因此他们无法引导众物达到太一形虚的境界。只有至人的精神是归向于“无何有之乡”,因为“至人无己”。徐复观先生曾说:“庄子的‘无己',让自己的精神,从形骸中突破出来,而上升到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9]“无何有之乡”在此寓言中是一个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是一个太一形虚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人的精神是自适逍遥的。
在《庄子》寓言故事里,无论是植物大樗,还是寓言人物如无名人、庄子等,他们在“无何有之乡”里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纯真生命的存在个体,他们能够保持着原始生命的自然与自适的逍遥状态,他们就是自我个体生命的主宰者。其次,在“无何有之乡”里,他们能“齐一”看待事物,破除“有用”与“无用”的价值衡量标准。最后,他们在“无何有之乡”里能消解因尘俗社会习染而来的功利心,以及现实世界中的精神困扰。在“无何有之乡”之前,庄子多是冠以“游”字。王中江教授对“游”字的实质做出解说:“庄子的‘游'是‘神游',是在‘精神世界'中‘无限'的漫游和逍遥。”[10]
总结以上所述,“无何有之乡”是这样的一个境界——逍遥自适的精神家园,可引申为人逍遥自得、自然纯真的生命状态。因此,“无何”典故的深层含义有两层:一是指逍遥自适的精神乐园,二是指人逍遥自得、自然纯真的生命状态。
二、苏轼对《庄子》“无何有之乡”的接受
庄子漫游于“无何有之乡”,就是“让自我真正回到精神的家,使自我‘诗意'的‘栖居'、自由的存在”[10]。他的这种做法,历代受挫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仿效,旷世文豪苏轼也不例外。
(一)引用“无何”典故创作诗词
典故是指诗词等作品中引用古代的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无何”是“无何有之乡”的简称,“无何”一词出自于《庄子》。潘万木在《汉语典故的文化阐释》中还以使用频率为条件对“典故”做出界定,他认为:“典故是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出现的,并不断地重复使用,才有资格成为典故。”[11]“无何”一词自先秦庄子首次运用后,它在后代文人创作中也是不断地被重复使用。唐代白居易的《读庄子》云:“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12]宋代苏轼《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云:“广陵阳羡何足较,只有无何真我里。”[13]1293东坡词也有引用“无何”一词,如《满庭芳·归去来兮,清溪无底》:“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14]出自于《庄子》的“无何”一词,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重复使用,成为沉淀着历史记忆的典故。
苏轼的诗词里,《庄子》的“无何”典故出现多达七次。以纣、王编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和孔礼凡点较的《苏轼诗集》为底本,本文辑出苏轼诗词里出现“无何”的篇目如表1:

表1 苏轼诗词中的“无何”篇目
由表1 可以看出,苏轼在熙宁八年外任密州官职时首次引用“无何”典故,而在元丰年间,他引用“无何”的次数最多,直到他谪迁到儋州,仍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苏轼总是在他外任或贬谪的时候引用《庄子》的“无何”。这表明,苏轼引用“无何”典故与他仕途谪迁的人生经历有关。其次,苏轼在不同的时间以及不同的地点引用“无何”,暗示了他创作诗词时引用“无何”的主观情感是不同的,那么“无何”在特定作品中的意蕴也是不同的。这与上文提及《庄子》“无何”的双重含义也是密切相关。
苏轼在不同的诗词,不同的时间以及不同的地点引用“无何”典故。他这种的用典方式就是同典异用。同典异用就是利用典故的多义性,在不同诗词中使用同一典故[15]。但典故的意义往往产生于继承和革新的张力关系中[11]。运用者在创作时因受到主观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对典故的使用也会产生细微的差别。那么,典故在具体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意蕴也不尽相同。
1.广莫无垠、空无虚幻的天国
熙宁八年(1075)正月,苏轼写下《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一诗,此时他在密州任职。在密州,苏轼经常受困于病魔,导致他疏于政务,但他得到了乔太博等人的帮助。因此,苏轼故作此诗寄答乔太博,旨在表达对乔叙和段绎的感恩以及颂赞之情。但是诗篇的笔墨,更多是侧重于苏轼慨叹自己年老多病且非才。诗歌云:“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须臾便堪知,万事风雨散。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逝将游无何,岂暇读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13]613苏轼不仅受困于病魔,还感觉自己被命运之神捉弄,始终无法违拗命运的戏弄。他开始认识到世间万事都如风雨一般飘散无常。人生短暂的悲哀之感与世事无常的虚幻之感,也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于是,他唱出了“逝将游无何”的心声。“无何有之乡”作为一处广袤无垠、空无虚幻的天国,正是此刻对人生感到虚幻无从的苏轼所向往的地方。他内心深处也有无力于时命囿限的一丝丝悲哀。在这首诗里,苏轼以追寻空无虚幻的“无何有之乡”,来展开他对虚幻人生的思考。
2.逍遥自得、自由不羁的生命状态
《十拍子·暮秋》写于元丰六年(1083)九月,此时是苏轼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上阕的黄花凋谢零落,暗示了重阳佳节已经过去,可苏轼饮酒的闲情逸趣却不减。“不得签署公事”的挂名官职,时常让他倍感“日月长”。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低落,他仍旧新开九酝畅饮美酒。他虽酒意浓浓,醉后却吐出“身外傥来都似梦”的人生哲理。“傥来”邹同庆等人笺注为“身外不意忽来之物”[14]477,即富贵、荣誉、名利等是不受人意志掌控的外在事物。经过“乌台诗案”后,苏轼醒悟到:功名等身外之物就像是梦一样变幻无常,令人捉摸不定,执着这些事物会劳役人的身心,戕害个体生命。于是,他以醉态进入逍遥的“无何有之乡”,渴望自由无拘束地遨游于此,获得身心的逍遥自适。苏轼逍遥自适的心态,下阙的“玉粉旋烹茶乳,金薤新捣橙香”[14]477能体现出来。他悠闲自娱地以烹饪美食为乐,沉浸在美食生活的快乐之中。他不仅逍遥自适,更是以四个“狂”字表现出他的狂傲不羁。“醉里无何即是乡”展现了苏轼在空间存在中追寻逍遥自得、自由不羁的生命状态。
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居到儋州,其《午窗坐睡》:“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13]2286苏轼在梦乡中进入“无何有之乡”,他对此地有着似曾相识的感受,这是他惬意、逍遥的生命状况的反映。苏轼将庄子“无何”所体现出来的逍遥自得生命状态,实践到在他的贬谪生活中,甚至是以此作为人生的理想生活状态,不断地追寻着。
3.逍遥自适的现实家园
元丰七年(1084),苏轼得知王巩南迁归来,写下唱和诗《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王巩与苏轼关系密切,他也是因“乌台诗案”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之一,他也不幸难免于贬谪。苏轼以议论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看法,诗云:“君知先竭是甘井,我愿得全如苦李。”[13]1293因“乌台诗案”,苏轼受到了牢狱和贬谪的双重沉重打击。此时,他愿意将自己比作为无用的苦李,就像是“无何有之乡”里的大樗。大樗因它的无用得以保全自身,且能在“无何有之乡”里逍遥地活出本真的自我。苏轼也渴望保全自身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他也渴望逍遥地活出本真的自我。因此,对他来说,无论是广陵还是阳羡,这两个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过美好回忆的地方,都比不上“无何有之乡”这个逍遥无害的家园。他在心里坚定:“只有无何真我里”。这是苏轼对待保全本真生命的看法,是他对生命实质、人生归宿的思考,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
但是,在“广陵阳羡”句下,苏轼自注着:“余买田阳羡,来诗以为不如广陵。”[13]1293在现实生活中,苏轼也如常人一般心系着在阳羡买田建筑心怡的居室,颐养自我珍贵的生命。“广陵阳羡何足较,只有无何真我里。”[13]1293这两句诗中,前者是苏轼调养躯体,颐养天年的地方——自然惬意地生活,后者则是他追寻生命本质——逍遥本真地存在。《菩萨蛮·买田阳羡吾》也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13]1293苏轼是希望在阳羡自然美好风光的浸润之下,自然惬意地生活,从而在造化浪潮中实现自然逍遥地活着的目的。这首诗的“无何”是带有现实意味的逍遥自得的境界,而非“无何”深层含义中纯粹精神性的理想家园。“只有无何真我里”是属于现实的逍遥自适的家园,即阳羡。
4.人生归宿的精神家园
《满芳庭·归去来兮,清溪无底》是苏轼承蒙宋神宗的恩准,返回常州时所写的。上阕主要是表达他对神宗的感激之情,以及他返归阳羡的欣喜心情。苏轼以神话寓言的创作模式来写下阙。词中的天女就像是《庄子· 逍遥游》里藐姑射山的仙女。天女仿佛代表“无何”世界里的众神仙向苏轼发出责问:为什么长久在政治官场的是非之中周旋、徘徊?苏轼以天女的责问与群仙的讥笑,来表达他对官场是非与宦海风云的批判态度,以及抒发自己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深沉感慨。人间的政治是非、官场利害冲突劳累着人们的身心,戕害人的本性。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苏轼不得不发出苦闷的质疑:“无何,何处有?”[13]527尽管风光美好的阳羡是苏轼的理想居住地,而此时久戏人间仍一事无成的他,又一次促使他思考生命的终极归宿。苏轼以反问的句式表达了他对人生终极归宿的肯定追求,这也是他对“吾生如寄”的人生思考做出的回答。
绍圣三年,苏轼前往儋州的路上,创作了《和陶擬古九首》,其一记叙了苏轼接待到访客人一事。苏轼与客人座谈古今杂史时也曾表达了自己对“人来自哪里”的哲学思考,诗句云:“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13]2260苏轼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出处就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这样一个纯理想的精神境地。无论是人生的出处还是人生的归宿,苏轼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来无何有”,即从“无何有之乡”来,最终回到“无何有之乡”,也就是下文所提及的“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
元符三年,苏轼已在儋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宦海浮沉,漂泊不定的他,除了追寻他一直以来都在探索的人生归宿,还需要化解心中的“归乡”情结。在儋州,苏轼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还和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苏轼表面上是在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实际上创作的却是一篇“归不得兮辞”。[16]他在《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引》对“归”做出了铿锵的回答,云:“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13]2560“未尝不归”以双重否定方式表示肯定的态度:虽在海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就是“归”。这个“归”字实现了苏轼在地域上和精神上的“归家”。他以儋州为地域的“归乡”,以“无何有之乡”为他人生终极处所的“归家”。但是,此时的“归”更多地意味着对安心之处的寻找与向往。[3]苏轼的安心之处就是“无何”这个逍遥自适的精神家园。只有精神家园,才是一切变化和流转中根本的家园以及不变的家园。
序中的“无何”不仅表现为它的深层含义——苏轼以逍遥自适的精神家园为寄托,“无何”还继承了《庄子》“齐物”的思想。《庄子》“无何有之乡”的“齐物”思想体现在惠施与庄子讨论大樗有无用的对话中。庄子建议把大樗种植在无何有之乡里,表层原因是大樗能因无用得到性命的保全;深层原因是庄子但愿大樗在无何有之乡里消解“有用”与“无用”的对立,即是以“齐一”的观点对待自然万物。苏轼“无何”的“齐物”思想体现在他从地域上消解了“差别”。《试笔自书》云:“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17]2549天地、九州和中国的三者关系是:天地包裹着九州,九州包裹着中原。但是这三者都是被水域包裹着的,当然,苏轼贬谪所到的儋州也是被水域包围着的。苏轼以“齐物”的观念认识天下的各个区域,在儋州也实现了他躯壳的“归家”。
(二)继承“无何”的人生哲思来展开人生的思考
《庄子》的“无何有之乡”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学内涵。苏轼在诗词创作中多次引用“无何”典故,就是将《庄子》“无何”的人生哲思融入自己的创作与生活之中,实则是以艺术的形式继承《庄子》人生哲学的深刻思想。
《庄子》“无何有之乡”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哲学的思想内涵有:首先,“齐一”地认识万物。他“齐一”地对待每一个生命,以此尊重和敬爱生命。尽管是因“大而无用”的大樗面临着被丢弃的困境时,庄子建议“树之无何有之乡”,“齐一”地破除惠施所代表众人的“无用”成见,从而保全了大樗生命。其次,他否定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世俗价值追求(强权、利禄等),而肯定个体生命(人)逍遥自得、自然纯真的状态。以《庄子》的寓言人物举例,庄子否定日中始享受手中的强权而威逼他人的做法,而肯定无名人遨游于“无何有之乡”所呈现出逍遥自得的生命状态。最后,“无何有之乡”是庄子对险恶的人世间彻底失望后,基于超越现实的“道”而构建起来的精神乌托邦,“旨在寻找一种应然生活与精神之路”。[18]“无何有之乡”的思想意蕴具有悖论性质,它不仅体现为对现实社会的沉痛批判,还应含有对理想家园的美好期许以及生命主体(人)内在觉醒的价值意义。
葛兆光先生认为:“典故中包含了古往今来人类共同关心与忧虑的‘原型',比如生命、爱情、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因为它们才最具有‘震撼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力量。”[19]苏轼心领神会地把握住了《庄子》“无何有之乡”所蕴含的人生哲思,并且结合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的经历,在诗词创作时顺手拈来“无何”二字,“从客观物,事‘他'的角度来表达主观之‘我'的情感与观点。”[11]苏轼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表现为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1]顺境与逆境的交替更迭,荣辱得失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他咀嚼尝尽人生百态的况味,让他倍感人生无常和世事虚幻,也促使他积极思考人生和努力探索“吾生如寄”的答案。这也就是苏轼总是在外任或贬谪的时候引用《庄子》“无何”的原因,可谓是借他人酒杯以浇心中块垒。
在密州时,苏轼以追寻空无虚幻的“无何有之乡”,来展开他对虚幻人生的思考。在元丰年间,苏轼把逍遥自得的“无何有之乡”与险恶烦杂的现实人间相比照,他更是清醒地认识到纷扰争斗的社会是多么的血腥。这就促使了苏轼更加积极地去思考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逍遥自适的生命状态;以及寻求安顿自然本真生命的处所——“只有无何真我里”。在儋州,苏轼不仅继承“无何”的“齐物”观,在精神上实现了地域的“归乡”愿望,消解了思乡的困苦;还以“无何有之乡”作为人生终极归宿的精神家园,对“吾生如寄”的思考做出了回答。
苏轼继承《庄子》“无何”的人生哲思,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以时间为纵向维度和以地域空间为横向维度,来展开他的人生思考。苏轼诗词的“无何”融入了苏轼的生命轨迹与人生经历。因此,同是引用《庄子》的“无何”典故,唐代的白居易与宋代的葛仲胜、刘一止等人,它们诗词中的“无何”,却少去了对“吾生如寄”的思考韵味。
(三)超越《庄子》“无何”的情感意蕴
苏轼引用“无何”典故,在继承“无何”双重含义的基础上,也对“无何”的含义进行了丰富与扩展,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意味的“无何”。无论《庄子》的“无何”表现为表层含义——“空漠虚幻”的境界,还是表现为深层含义——“逍遥自得”的精神乌托邦,《庄子》的“无何”都具有形而上的特点。庄子是基于形而上、作为万物终极根源的“道”,建构出来的理想家园。苏轼以“无何”作为内心保有的人生终极归宿,这是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但是,一生都在奔走或是在奔走路上的苏轼,频繁的地点更换,强烈而又浓厚的思乡之情也是始终困扰着他。尤其是他谪迁到儋州的时候,他以“无何有之乡”里蕴含的“齐物”观念来消解地域间的“差别”。“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这里的“无何”也含有指儋州的浅淡意味。当苏轼接到“任便居住”的诏命后,他打算北归阳羡,在此地养老。《与孙叔静》云:“度岭过赣,归阳羡,或归颖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17]1776“只有无何真我里”中的“无何”就是他理想的养老之地,即阳羡。
庄子以“无何有之乡”建构自我的精神乌托邦,虽然这是他基于“道”追求自然本真的生命价值的做法。但是,他这样的做法,暗示着:他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失望,只寻求精神上虚幻的“无何有之乡”为理想的家园。这不免带有消极悲观的情感分子。而苏轼仅以“无何”的人生哲思来展开对人生的思考,他扬弃了《庄子》“无何”的悲哀情绪。苏轼在引用“无何”典故时,他对人生思考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意蕴为:悲哀—苦闷—旷达。在儋州,他实现了在地域上和精神上的“归家”,这正是他超迈旷达的人格精神体现。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是异常沉重的,但并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对政治的退避'变而为‘对社会的退避'。他在吸收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苦难'—‘醒悟'—‘超越'的思路。”[1]
三、结语
苏轼与庄子有着精神上的共鸣,他心领神会于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不仅含义丰富,也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思。苏轼诗词里多处出现“无何”典故,实则是他以艺术的方式,即是文学创作的形式来继承《庄子》“无何有之乡”所涵盖的人生哲思。苏轼仅以“无何”的人生哲思来展开对人生的思考,摒弃掉《庄子》“无何”的消极情感。从而,苏轼化解了思乡的困苦,也解决了“人生如寄”的困惑,最终以豪迈、旷达的形象神化在我们每一个读者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