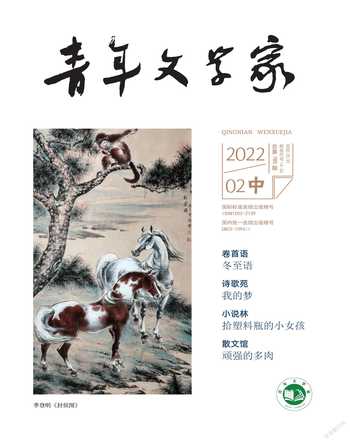简论李铁小说《手工》的叙事策略
2022-03-25李嘉懿
李嘉懿


小说中的情节、人物性格及其发展一定会基于某一特殊的社会背景,而叙事策略的运用恰恰就是社会现实与小说联结起来的纽带。由于拥有独特的发展优势,东北地区一直是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重镇,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创作工业题材小说的优秀作家。辽宁作为中国建设时期重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与其有关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曾给辽宁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近些年来,辽宁作家李铁的创作一直被看作是持续关注和书写辽宁工人形象的典型,其作品多从社会现实入手,从中展现出工人们的真实情感。《手工》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荆吉与西门亮两位手艺高超的钳工在经历了工作变动之后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手艺的钻研和坚守,并从中展现出他们身上可贵的工匠精神。在这篇小说中,李铁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基础上,以多元化的叙事策略与贴近时代的精神思考来建构文本,并力图从中凸显出工人们身上所蕴含的宝贵精神。
一、叙事视角的交叉运用
叙事视角对文学作品审美功能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英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的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路伯克的观察点就是所谓的叙事视角。在文学创作中,叙事视角的转变有助于帮助作者把话语权充分交给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拉近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增强文本可读性的同时,力图展示出人物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在《手工》这篇小说中,李铁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对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进行叙述,通过流动的视点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从中反映出故事叙述者对人物经历所持的情感態度,力图在叙述中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与此同时,《手工》这篇小说打乱了叙事的时间顺序,通过回忆与现实的交叠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二元对立,达到了小说中“虚构”与“现实”的和谐统一。
《手工》这篇小说打破了李铁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单一视角叙事的常态,通过“巩兰讲的荆吉的故事”“叶峰讲的荆吉的故事”“巩兰接着讲荆吉的故事”“郭拔讲故事”“叶峰接着讲荆吉的故事”这种小说人物讲故事的方式来切换叙事视角。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没有以荆吉的视角来直接叙述他离开工厂之后的经历与见闻,而是通过巩兰、叶峰、郭拔、辜丹等人的叙述,以拼接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叙述者的身份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也可能是事件的旁观者,但他们对所叙述的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在巩兰讲荆吉的故事时,面对辜丹的再次出现,作者以简短而又精确的话语表达了巩兰对辜丹复杂的情感态度,当巩兰讲她与荆吉这些年的生活时,巩兰也发出了一个中年女人对生活深切的感慨,也正是在这些充斥着真情实感的话语中,巩兰的形象也变得愈加清晰。在叶峰讲荆吉的故事时,当得知光洞镇上的工厂老板要缩减他与荆吉的工资后,叶峰情绪上的不满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不定内聚焦视角与非聚焦视角交叉运用的叙事策略,使得作品摆脱了非聚焦视角下除主人公之外其他人物内心世界的失语状态,人物情感得以充分抒发,人物形象也愈加真实完整。
二、具有跳跃性的叙事时序
叙事时序是文本中事件所开始的先后顺序,为了丰富作品的叙述层次,作家往往会通过改变事件时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效果。纵观李铁以往的工业题材小说,大都是由连贯的叙事时间构成,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线性结构。而在《手工》中,李铁打破了以往的线性叙事结构,将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巧妙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富有跳跃性的叙事时距使得空间不再只是作为简单的故事背景而存在,并使空间同时成为一样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手工》中,李铁多以回忆的方式来穿插叙述,使现在与过去相互交错,并以此来制造情节的呼应与延伸。从整体上看,事件的起因是“我随一个作家采风团去北方机械集团参观”,而这个集团的副总恰恰是“我”的好友郭拔。在与郭拔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知郭拔要搞一个钳工擂台赛,并希望“我”能为集团写一篇关于“工匠大师”的纪实文章。当考虑到谁参赛最能展现钳工技术风采时,“我”与郭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荆吉和西门亮。他们二人早已离厂多年,郭拔希望能通过“我”找到他们回来参赛,故事便从“我”寻找荆吉与西门亮开始了。在寻找荆吉和西门亮之前,作者安排了一段“我”的回忆,通过荆吉与西门亮的“大把”之争和厂里举办的技术比武来凸显出二人高超的钳工技术,期间还穿插着二人的感情经历。虽然这段回忆在“我”调离红星机械厂之后戛然而止,却起到了前情提要、梳理人物关系的作用,也为下文“我”寻找荆吉与西门亮提供了线索。这时,小说的时序从对过去的追忆回归现在,“我”找到了荆吉的妻子巩兰,并通过巩兰的回忆了解了荆吉离厂后的经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叙事时序时又多次发生了变化,“我”遇到了不同的人,他们的回忆把“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带回过去,当“我”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叙事时序又自觉地拉回到现在。也正是在这种反复切换的时序之中,作者打破了时间的界限,使过去与现在有了更替重叠的可能,不同的信息相互串联,在建构一个完整故事的同时增加了小说的层次感。跳跃性的叙事时距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类似,它使得作者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对不同的故事进行描写,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对照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在某一特定的情节引导之下展开,并将人物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互交错,正是这种跳跃性的叙事时距使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人物命运的不同之处也就此显现。
三、生动形象的叙事语言
读者对于文学创作的印象首先来自其中的情节,其次是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但如果就写作这一层面来说,小说中的叙事语言就成了作家要考虑的主要方向。在李铁的小说中,有关工业生产的术语比比皆是,这与李铁早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但在小说中,李铁并没有对这些术语做简单的罗列,而是借用了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将这些术语融入其间,使作品达到了文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手工》中,李铁对小说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实现了生动形象与平实质朴的统一,这不仅凸显出了现实主义手法的创作特色,更凸显出了小说的主题,达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实现了叙事语言与效果之间的平衡。
文学创作的素材源自生活,还要回归到生活中去,成为人们的记忆。“小说的叙事语言不仅作为媒介确切地重塑了作家心目中的形象体系,而且还在高低、起伏、轻重、长短的语调中不无模糊地涌动着作家的情绪、态度、心境。与之相应,人们从一个个方块字组成的句子中也不仅接受了清晰可见的形象本身,而且还从长短错落的语句中进入一种语言氛围。难言的感受,拂过的情绪,心照不宣的默契,微妙的弦外之音,甚至一个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某些片段—这一切都像沼泽地上的雾气一样无声无息地升起弥漫。”在文学创作中,作品的语言是作家精神的体现,从作品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的创作精神与创作风格,李铁笔下的工厂并不仅仅是由单一的机器与复杂多样的零件构成,在对工厂与工人的描写中,李铁倾注了自己对工厂的情感,并力图通过生动形象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来对工业生产的场景进行描述。对从未接触过工业生产的读者来说,李铁对这些工业术语的运用无疑为读者揭开了工业生产的神秘面纱。在《手工》中,荆吉和西门亮都想成为工厂的“大把”,工人们之间比较手艺高低并打上赌注的方式被称为“赌比”,还有打手锤、做四方套、刮瓦,等等。在描写荆吉与西门亮比赛刮瓦的场面时,荆吉刮瓦用的是燕子阵,“一条小巧的铁屑飞出去,瓦轴上留下一只展翅飞翔的小燕子”,西门亮用的是小鱼阵,“一刀下去挑出一条小鱼来”。在描写荆吉与西门亮比赛做不锈钢玫瑰时,荆吉的玫瑰精致逼真,正是盛开的状态,西门亮的玫瑰含苞待放,既有露珠,又有绒毛点缀。一块小巧的不锈钢,在两位匠人的手中变成了娇艳欲滴的鲜花,瓦轴上的铁屑也似小鱼与展翅飞翔的燕子一般,李铁正是用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为读者展现出了工业生产中的艺术,并从中体现出李铁对工厂深切的情感。
四、多元化的叙事对象
李铁的目光独到、敏锐,在《手工》这篇小说中,他对叙事对象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工厂这一个层面,而是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手工》这篇小说中,对工人群体的普遍思考并不是李铁小说中的主要書写对象,与之相反的是个体化书写占据了文章的中心。李铁选择了几个在工人群落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是早已调离岗位的“我”,二是坚守工人身份的荆吉,三是坦然接受职业转变的西门亮。小说中的这三个人虽然师出同门,但最终的选择却不尽相同,这种对人物个体命运、精神际遇、价值追寻的书写,拓宽了小说写作的维度,同时赋予小说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开篇讲故事的人是“我”,“我”作为一个早就脱离生产一线转为文职的人,再见到曾经工作过的工厂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伴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李铁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在书写个体情感变化的同时把个人情感融入时代变迁之中,借人物之口表达对时代变迁的感慨。在“我”之后出场的就是荆吉,对手艺的坚守可谓是他的精神所在。荆吉从始至终都没有荒废他的手艺,即便是在监狱里,听到西门亮在“练功”之后,他也马上开始练习,这种对手艺的痴迷和坚守近乎成了荆吉生活中的全部。可即便荆吉是一个坚守者,但他也不得不向生活妥协,当面对光洞镇上的工厂老板降低他的工资标准时,一向有骨气的荆吉也说出了毫无骨气的“接受”二字。不仅荆吉如此,西门亮也是如此,在最后“手工的紫禁之巅”比赛中,西门亮却并没有到场,当“我”打电话问其原因的时候,西门亮解释说是因为公司有一场重要的直播,公司不容许他推脱。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或是为了生存,人们往往会改变自己的初心,借西门亮的抉择,李铁也从侧面展示出了当个体的精神追求浸满了生存的无奈之时,人们内心的挣扎与困苦。
从整体上看,《手工》这部小说选取的大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为了生存奔波,坚守着自己的手艺与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与生活作着顽强的斗争。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中,李铁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并从中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整体关照。除此之外,李铁并没有吝惜笔墨对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细致的描写,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洞察与历经沉淀之后的人生体悟,使得《手工》这部小说也带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工匠精神的引导,小说创作同样也需要工匠精神。李铁作为辽宁工业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家,近年来一直以其对现实的温热眼光践行着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坚守。时代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机遇与挑战并存,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都无法避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催促着文学创作方式的革新,这也就意味着作家要不断实现自我的突破。从《手工》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铁对工人生存状态的书写也不再限于工厂这一特定范围,而是开始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正如李铁所说:“开始写这类小说的时候,我所描述的场景大部分是工厂内的,但写到现在,我的这类小说里工厂内的场景越来越少,这绝不是我在渐渐脱离工厂,恰恰是更接近了生活的真实。”无论是叙事手法还是叙事内容,《手工》这篇小说相较李铁之前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带有一定的创新色彩。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透过《手工》这篇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描摹,我们可以看到李铁作为一名作家深切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能看到李铁为实现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多元融合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