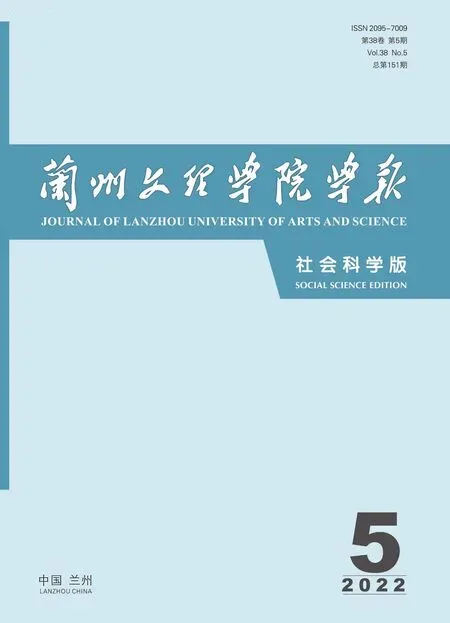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差异即对话”:作为全球化理论的本体观
——以金惠敏《差异即对话》为中心的阅读
2022-03-24肖明华
肖 明 华
(江西师范大学 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2)
毋庸讳言,全球化这一语词及其所表征的理论话语越来越难以形塑人们的想象空间了。这也难怪,毕竟我们对全球化的言说已逾数十年!就以文艺学专业为例,大概在2000年前后,话语场域中的极佳位置才由全球化所占据。当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学学科反思、文化研究、强制阐释论、别现代主义等话语兴起后,全球化理论就逐渐式微。此后,即使全球化这一语词偶有出现,但人们往往也对它熟视无睹了。
然而,于我而言,全球化却一直是一个“适我无非新”的学术词语。如果要作简要分析,那么其原因可以简述为几点:其一,全球化理论虽然绵延几十年,但这一理论话语自出现以来,就一直作为一种“过程哲学”,其阐释力远未耗尽。这恐怕得益于全球化迄今都是“现实一种”,尚为一种可感知的现象。在现代性仍是一项工程的今天,言说全球化,无疑能够参与到当下的生活世界,并实现知识的公共使用这一目标。其二,将全球化讨论引入到现有的学科知识生产体制中去,既可以推进这一理论自身的研究,又有可能改造我们的学科框架,影响和推动当今学科知识生产的新发展。比如,将全球化视角引入到世界文学的讨论中,就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不无助益。其三,全球化还是一种有形而上深度的哲学。诸如同一与差异、一般与特殊等都是与其有关的认识论、价值论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智识水准,我们还可以深入到其本体论的腹地。如此具有哲学意味,也就很可能常说常新!
最近,当阅读到金惠敏的新作《差异即对话》一书时,我更加坚定了上述想法。通过延伸阅读金惠敏的相关著述后,我发现作为“国际新比较学派文库”之一的《差异即对话》一书,可以认为是他所建构的“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的系列著作之一。金惠敏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可谓持之以恒,围绕着全球对话主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然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实绩。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化因为金惠敏的研究而更具“社会学的想象力”!那么,金惠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主要以其《差异即对话》一书予以简要分析。
一
《差异即对话》一书对全球化作了哲学的阐发。在金惠敏看来,与全球化理论关联最为紧密的问题恐怕就是如何理解差异的问题。差异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文化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认识论问题。差异的问题是一个“元问题”[1]。理解好了差异的问题,才有可能处理好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也就有望对全球化理论进行一种新的建构。
基于这样的识见,金惠敏首先对差异进行了思想史的追溯。依其之见,中国自古就有“差异的文化政治学”,但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差异的理论问题主要表现为了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去认知中西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先前的“夷夏之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还是晚近的西方文论霸权说,都一仍其旧地表现出了“中西二元对立思维”[1]4。这意味着,在中国思想史上,大家对差异的理解尚是一种朴素认知的状态,其表现往往是要么对差异抵制,要么以差异自居,至于为何抵制因何自居,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直接的利益诉求和朴素的认识论,而非依据某种深刻而自觉的学理,更遑论达致本体论哲学的深度。
在西方,对差异的思考倒是很深刻也很自觉,但是他们却又存在“惧怕差异”的思想传统[2]。其表现就是,自巴门尼德以降,哲学家一直在寻找世界的本体。无论是将本体作为本原来理解,还是将本体作为实体来看待,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是孜孜以求地试图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去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既而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同时也希望找到这个本体。但几千年来的认识论探索,它达到的效果却是宣告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永远找不到这样的本体。可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黑格尔之前的西方思想史几乎不承认这一事实。这种寻找也因此绵延不绝几千年。其最终的思想效果就是让差异的世界不被真正的承认,大家还是梦想那同一的本体。对此,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这种对本体世界的同一性认知追求恰恰是对存在的遗忘[3]。
鉴于中西思想史对差异的理解所存在的问题,金惠敏因此非常重视差异的研究。这恐怕可以从他主编名为“差异”的辑刊和出版的《媒介的后果》《消费他者》《全球对话主义》等著述中见出一二。当然,最能见出其对差异的重视,恐怕还是《差异即对话》一书所做的专题研讨。金惠敏是如何继续展开自己的差异研究呢?他又持怎样的差异观呢?
金惠敏认为要重视20世纪思想史中的差异论。在对法国后结构主义、英美后殖民主义、德国主体间性等话语中的差异思想资源进行了充分吸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差异观:“差异即对话”说[1]3。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差异即对话”的本体观分别表明了差异和对话的本体意味。不妨分述如下:
其一,差异是本体论的。这就意味着世界是差异的存在。其具体表现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前,我们无法寻找到一个同一的世界,因为没有这样纯粹的认知主体,也无法证明思维的主客体统一状态就是绝对正确的统一状态。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的不透明这一特点就会使得我们根本无法用某一纯粹的语言去陈述一个实体意义的存在。同时,意义的确定受语言的横组合纵聚合关系的影响也使得这个世界的真理即使有,但也恐怕是“意见式真理”[4]。为此之故,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本然状态就是差异的,这是需要我们承认的。但承认差异不是为了阻隔人们通往本体的世界。相反,正是因为有差异,我们才需要追寻那个本体的世界,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追寻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差异世界。
其二,对话是本体论的。对话是一种人们追寻并和本体世界相沟通的方式。说对话是追寻和沟通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对话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对话乃是因为世界是差异的存在,因而才需要对话去倾听差异。这种对话因而是本体论意义的。对话不是为了什么,对话就是世界的存在状态。没有对话,这个差异的世界就不会存在,或者说就不会有好的差异。大概因此,金惠敏才说“差异在本质上就是对话”[1]3。
基于上述对差异和对话的本体论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差异和对话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体论的。那么二者的本体论关系是怎样有机接合的呢?不妨也分两点来理解:
其一,本体论的差异观和对话观本身就导致了二者的关系必定是本体论的。具体而言,差异是本体论的,但差异不是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差异无论是“强者”的,还是“弱者”的,都可能把自己的差异作为唯一的存在,从而拒绝对话。一种拒绝对话的差异,不可能是真正的差异,更不可能是好的差异。本体论意义的差异,因而有内在的对话诉求。有差异就要对话,只有对话才能让差异的世界继续更好地存在。没有对话,差异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为此之故,金惠敏说:“不是用差异拒绝对话,而是将差异作为对话的起点。”[1]17
其二,作为本体论关系的差异和对话,二者不是工具和目的的关系。我们言说这个本来就是差异的世界,不是为了“放弃差异”。金惠敏指出,“言说差异就是将差异带入对话,差异性话语就是渴望对话的话语”[1]17。换言之,对话不是为了消灭差异,消灭了差异就不是真正的对话,通过这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对话,其目的是为了把差异的世界带入更好的差异状态。当然,对话也会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共识的出现也不意味着差异的彻底消除。或者说,共识并不是比差异更高一级的存在。按金惠敏的说法,共识的图式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星丛性的[1]18,作为星丛性的共识,它照亮差异,让差异更本真。总之,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对话,却也因为对话所以才允诺了差异的更好存在。有了这种理解,我们才可以将差异和对话二者的关系表述成本体论的句式:“差异即对话”!
《差异即对话》一书能够深入到本体论的层次去言说差异,这无疑表明了它据有了一块哲学的高地。虽然这种“差异即对话”的观念看似不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到本体论的层次去理解,恐怕很难感受到其深度和魅力。这就好比我们如果不能以道观之,便体会不到“道可道非常道”的深度和魅力一样。非常值得肯定的是,金惠敏在筑就了这一“差异即对话”的哲学高地后,并没有停下来,慢慢欣赏!更没有因此陷入到理论的口头禅之中而不可自拔。接下来,他将这一哲学高地用于其差异的文化政治学建构了。
二
差异的文化政治学主要处理的就是全球化问题。全球化问题集中表现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具体到中国则主要就是中西关系的问题。
金惠敏对目前的全球化理论状况了然于胸,并删繁就简地梳理出了两种全球化的知识型。一种是现代性的,一种是后现代性的。前者主张全球化就是全球通往同一,后者看到了全球化的效果其实是差异的凸显。金惠敏认为,这两种全球化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简而言之,就是缺乏“差异即对话”的本体论观念[5]。因为缺乏这种观念,现代性的全球化对差异缺乏基本的认同,而后现代性的全球化则忽视了差异即对话,从而过度地强调了差异。为此之故,金惠敏倡导“差异即对话”的本体观念,并以此作为其全球化理论的新本体观。基于这种本体观,金惠敏的全球化理论综合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种知识型的全球化理论。在他看来,“全球化内在地同时就是现代性的与后现代性的,即是说,它同时超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因而可成一新的哲学概念”[6]。有了“差异即对话”本体观的全球化,其具体理念和基于这种理念的文化政治学,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就思维方式而言,金惠敏主张去除中西二元对立思维,主张用“价值星丛”的理论来处理全球化进程中所遇见的中西二元对立思维问题。“价值星丛”理论受启发于阿多诺、本雅明,同时也归属于“差异即对话”的本体观。其意是说,中西双方的文化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二者的关系是星丛式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照亮对方的特殊性。换言之,他者的存在可以让自身的存在更有差异。他者和自我因此是对话的关系,通过对话互相发现各自的特殊性,也就是成全各自的真正差异。他者和自我同处于一个世界,双方共同营造一种关系场,在这种关系场中自我和他者各自找到最好的自己。因此,真正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不是文化帝国主义,不是对民族差异的抹去,相反,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展开对话。通过对话,目的是使得民族的差异凸显,而非为了压抑乃至消灭某一民族性。而且,他者的民族性一旦遭遇压抑乃至消灭,自身的民族性也将暗淡无光。任何民族都是一颗星星,都是构成“星丛”的一盏星火。对此,金惠敏写道:“在此星丛之中,民族价值符号所指涉的利益仍然存在,只是不再是自以为的独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各种利益的共同存在,是互惠互利,是‘利益’的古老意义的复归……它原本上就意味着相互依存,从对方的存在之中取得自身的存在。”[1]25这也就是说,超越了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全球化并不“无视民族利益”,更不反对任何民族的差异存在。它深知没有民族,没有有差异的民族,就没有真正的“世界主义”意义上的全球化。世界主义的全球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戕害,它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让强势民族孤芳自赏,但终究顾影自怜,要么会使得弱势民族最终更弱甚至退出人类文明而自行衰败。因此,金惠敏坚决去除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反对自我和他者的非此即彼关系,也就是主张“星丛”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这样就较好地处理了全球化进程中较为棘手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
金惠敏还特别联系我国的文化政治观念来言说。据他观察,我们存在“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之下的思维在处理中西关系问题时往往“强调二元对立、强调自己的差异性”[1]49。这就导致了我们无法真正地受惠于全球化,甚至延误我们的现代性进程。原因是,当我们一味地抵制西方,就会把自己本质主义化,从而让自己的差异得不到对话后的优化,长此以往,终究会受这种思维方式之苦。事实上,作为后发现代性的中国,的确有也应该有自己的差异,但“差异即对话”,通过对话,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发展自己更好的差异。对此,金惠敏指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将中华文化仅仅限制在特殊性层次上的思维,而不知道既往的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即是说,不知道中华文化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是自我矮化的思维,不仅妨碍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作用的发挥,也阻碍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不断对之加以创新的当代文化对全球文化的建构。”[1]43窃以为,这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位有中西二元对立的后殖民情结的人阅读。当然,我们相信,因为差异和对话乃本体论的诉求,差异和对话的关系也是本体论的,因此它并不会因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完全阻挡。
其二,再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有“差异即对话”观念的全球化理论,力求去除民族主义,彰显世界主义。
全球化当然不是要去除民族差异,但全球化不能认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的文化认同必定是值得警惕的。它和金惠敏所主张的全球化观念完全不符。民族主义虽然主张身份的差异,但它是对差异的绝对认同,从而拒绝对话,这就走向了差异的本质主义,而遗忘本体论的“差异即对话”观。金惠敏为此写道:“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孤立的存在,没有绝对的本质,一切都为关系所界定,一切都在关系中构型。”[1]43~44
金惠敏所主张的全球化也警惕对民族价值完全忽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他看来,民族价值和世界价值的关系是星丛式的。彰显世界价值不是对民族价值的否认,不是不加选择地把民族之外的某种价值设定为更高的价值。在金惠敏看来,“没有涵括一切民族价值的超级价值,世界主义只是意味着一种‘价值星丛’,在此星丛之中,民族主义价值不是要臣服于一个‘最高原则’的宰制,而是进入与其他价值的一种对话性关系”[1]25。不同民族价值之间进行对话,通过对话可能产生共识,但共识不是更高的价值,而是一种照亮民族差异的关系、氛围,凭借它将差异带入更好的状态。
金惠敏的全球对话是要建构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他说:“真正的世界主义是一种境界、气度、胸怀,是对他者的尊重、关切,甚至是自我牺牲和奉献。”[1]23看得出来,世界主义不是我们想象的高一级别的帝国,毋宁说,世界主义才能让每一个民族价值发挥到最大,才能让每一个民族差异都放大,才能让每一个民族都免于帝国之苦但又有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世界。金惠敏还联系文学翻译问题来言说这种世界主义认同。他说:“汉语翻译文学没有用汉语文学取代西方文学,而是将西方文学置于与中国文学的连接之中,从而催生了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1]28毫无疑问,金惠敏说出了一个事实!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就可以得知,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一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水准的提高,对于创造中国文学的高峰,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批批国外文学作品的传入,并没有湮灭中国文学的差异,相反,因为跨文化的有效交流,中国文学才有了自己更好的差异!才能够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被人看见。毋庸讳言,我们还应该继续在这种世界主义的全球化观念下努力发展我们的中国文学。
差异的文化政治学建构不能说就很精细完美,但是,它已然是一个具有较大识别度和较大阐释力的理论。我们也已然从上述对文化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有所体认。
三
毫无疑问,作为全球化本体观念的“差异即对话”说,对于当前文化建设以及学科发展无疑有较大的价值。为何?原因之一乃与我们的现代性有关。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无论是否持后发说,都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我们的现代性发生和西方有关。这就使得中西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和全球化有关联。全球化和西方现代性有关。我们如何处理由西方现代性所驱动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效果,因此就摆在了我们面前。简而言之,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遭遇全球化问题。只要我们的现代性尚未完成,对全球化的思考就不会没意义。金惠敏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必定会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就其已然建构的“差异即对话”的全球化本体观而言,我们不妨说,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它对全球化理论史作了很好的赓续和创构,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由此彰显。对全球化作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能够自觉吸收此前研究成果,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并落实到文化政治学层面者其实并不多见,而且,金惠敏还敢于立论,提出了有本体论支撑的全球对话主义。这使得他的研究有标示性和能见度,而且得到了中西学者的关注和回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惠敏甚至凭此形塑和夯实了其作为国际学者的美好形象。美国、德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家的不少学者参与讨论其设置的学术话题,并且评论之研究之[7]。同时,金惠敏有学术积淀,又有思想史意识,已然主持主编了好几套介入当下社会文化的前沿学术丛书,诸如“文化研究丛书”“视像·媒介·文化权力丛书”“国际美学前沿译丛”“国际新比较学派文库”等。可以说,其学术眼光之敏锐是达到了“世界主义”的层级,其学术立场的全球对话主义也可以见之于这些丛书。在我国“学术思想欠发达”的当下[8],金惠敏较好地实现了当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目标。这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学术事件。
其二,它有助于我们建构当前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内在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诉求,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因此有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话语的出现。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特色、民族性和同一、全球性之间的关系处理已然成为了一个问题。不妨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差异即对话”观念的全球化理论中获得较好的启发。简而言之,在这种全球化理论的观照下,我们可以这样处理二者的关系,即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强调自己的特色,要凸显民族本位,但另一方面,特色、民族本位不能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对话主义的。通过对话,把特色、民族性带入到全球,从而建构更好的特色、民族性。对此,金惠敏写道,我们要“以‘解决人类问题问题’为鹄的,这当然不是要扬弃自己的传统,不是摆脱自己的现实,而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胸怀世界、宇宙、人类,将我们中国人特殊的经验汇入人类经验的辽阔海洋,实现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过渡,让‘中国史’成为马克思所谓‘世界史’的一个部分,让‘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部分”[1]38。这种世界主义的全球化,或者说这种“差异即对话”的全球化理论无疑很好地处理了当前中国价值观建构的问题。有了这种世界主义的观念,我们才有可能在世界文化场域中有较好占位,才有可能建构“文化引领权”[9],才有可能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去。顺便说一下,金惠敏的“差异即对话”观以及基于这一观念的文化政治学对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沟通我国主流话语如文明互鉴等也是有积极效应的。这也是金惠敏理论建构的文化自觉。他曾写道:“‘差异即对话’命题,一方面意在反对某些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之固执于绝对的不可言说、绝对的他者,以文化差异和特色拒绝异质文化的进入,拒绝文明互鉴、文明对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构价值观上的西方霸权主义,将西方价值地方化、语境化、文化化,而最终目标则是期以形成‘价值星丛’或‘文化星丛’。”[1]2
其三,“差异即对话”的全球化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它对于体制化较为严重的学科知识生产也有较大意义。仅以美学为例。《差异即对话》一书虽然没有专门对美学学科的发展进行研讨,但是他删繁就简地对美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两点很值得践行的意见。其中一点是,美学要文化化,不要体制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杂美学”的观念[10]。也就是说,美学不要把自身的学科差异本质主义化,而要持“差异即对话”观。通过对话,让自身的差异被照亮,从而进入更好的差异状态。对此,金惠敏写道:“今后一种美学如果仍是自怡于作为传统形而上学宫殿的侧厅,不去了解最新的和最激进的艺术事件,不积极参与跨界文化交往,将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1]186在打破学术体制方面,金惠敏的“述学文体”都有值得肯定之处,他的著述虽不能说就一定达到了有学者所谓“毕达哥拉斯文体”[11],但的确有“不循常规,自出机抒”之感。另一点是,美学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它同时是全世界的,也即是“球域的”。“差异即对话”的全球化理论告诉我们,既要美学的民族特色,但同时又要有世界美学的眼光。当民族和世界二者产生了良性互动而拥有了美好的张力时,美学就有了未来[1]191。
四
“差异即对话”的观念,作为全球化理论的本体观念,它还具有较大的“引申意义”。这是因为,这种本体观可以作为“元叙事”,具有较大的生产性,能支撑诸多的知识生产。这里仅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为例。
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需要凸显,实际上也成为独立的知识生产领域,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有族群差异。然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不是排斥其他民族文学的理由,更不能因此拒绝和主体民族文学的交往。相反,少数民族文学要和其他民族文学交流。这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有和其他民族文学进行对话交往的内在诉求。这种交流不是要改变,更不是要否弃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而是要通过交流对话,来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带入新境,也就是获得自身的更好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构成,它可以也应该努力参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建构,它本来也就在这种参与和建构之中。这种参与和建构是“本体论”的,也即是说这种参与和建构是不能改变的“存在”。为此,我们有必要树立与这种“本体论”相应的“认识论”,也就是我们要努力去践行参与,多和其他民族文学乃至国族文学对话,而不要人为地、主观地去阻碍这种参与。套用一句话来说,少数民族文学要具有这样的“差异即对话”观,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
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在实际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就要更为自觉地去改变一些做法。比如,少数民族文学并非只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才能研究,相反,我们要欢迎甚至要主动邀请非少数民族身份的人来参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比如,少数民族文学史当然可以单独书写,但也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之中。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构成。少数民族文学不能被圈定在因族属身份所产生的差异之中,而忽视自身对话的本体需要。
当然,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改变中国文学的观念。就民族构成而言,中国文学是复数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多民族文学”,而不是“单民族文学”。只要在文学史上有独特性的作家作品、文学样式、文学思潮、文学社团等都可以也应该作为中国文学的构成,而无需特意地以民族身份论处,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是文学的,同时,也才能做到有多民族性。藉此,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也才能更好地甚至是真正地呈现。有了这种观念之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就要对任何民族的文学有考察和鉴别,而后选定有历史意义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纳入到文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并非不重要!比如,从文学样式看,中国文学除了有诗词歌赋、小说散文外,本来就还有“史诗”,还有“阿肯弹唱、好来宝、约隆歌、克智论辩、目瑙纵歌等特有的文学形式”[12]。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在言说中国文学样式时特意地突出这些文学样式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这是因为它们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但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我们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要有这种文学史观念的自觉。
回到现实看,少数民族文学更多的还是拘囿于少数民族文学圈,大体上还是存在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历史中。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并没有真正的凸显,倒还可能成为“奇观”文学。在需要少数民族文学“显影”时,它才可能作为对象呈现,但遗憾的是,这种呈现很有可能还是作为他者,被凝视。比如,我们常常习惯于凸显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当我们在讨论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时,便强调乌热尔图写鄂温克人的《马的故事》,彝族吉狄马加写的《我,雪豹……》、满族胡冬林的《青羊消息》等。凸显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族属身份是有必要的,但这种凸显有可能就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中国乃至世界。较好的做法恐怕是,作家的族属身份差异,藉文学的独特价值来彰显。我们要把族属身份的差异隐藏在文学的差异之中。如果族属身份的差异过于彰显,就很可能忽视其文学自身的差异,甚至也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下的发展。有学者为此指出,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过于强调“民族的族群标志和文化符号”,这就不利于文学的现代发展。依其之见,“民族文学需要从中国当下的现场经验中不断地挖掘出新的审美资源,表现处在现在时态中的、正在行进着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从这种文学书写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的现代变迁,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新的变化,表现民族文化在时代潮流中所产生的新质”[13]。窃以为,这种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考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如果我们太重视族属差异,并且将这种差异本质主义化,那就很可能是在主动将自身他者化,从而压抑其差异本有的对话之维,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变成凝视的对象,而不能进入文学的历史。这无论如何,是需要逐渐加以改变的文学景观。这种改变的理念,则可以生成于 “差异即对话”的本体观。
非常值得肯定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其实也早在改变之中了,并且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如,新时期以来的张承志、王朔、霍达、扎西达娃、阿来、关仁山、陈村、鬼子等众多知名作家的文学创作,一方面保有一定的族属差异,但另一方面,其少数民族的身份却并未刻意彰显。很多人也可能并不太在意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而更多的是从他们的文学中去体会差异。少数民族文学是有差异的,对待这种差异,我们要警惕以不可改变的族属身份差异来掩盖他们的文学本来就有“差异即对话”的本体诉求,也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要强调少数民族文学而拒绝必要的文学乃至文化对话。不妨说,他们的文学是,而且本来就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他们也可以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吸取有助于生成更好自我的营养。从文学样式说,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就在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之外,增添了“三大史诗”和以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为主要类型的南方史诗群;增添了阿肯弹唱、好来宝、约隆歌、克智论辩、目瑙纵歌等特有的文学形式。
晚近,学者刘大先专门讨论了世界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原来“单面的”世界文学是不合理的,甚至会对少数民族文学构成伤害,比如“为了向‘世界’靠拢,会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看齐,甚至为了便于译介传播,在手法、技巧和语言上寻求‘可译性’”[14]。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刘大先认为要重新发现世界文学。所谓重新发现世界文学,意思是要改变我们的世界文学观念,世界文学并不是西欧和北美文学,世界文学不是以牺牲差异为代价的,当然,也不是固守差异来成就的。他写道:“随着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样性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重新发现‘世界文学’的多样谱系已经成为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基于其内部的多样性,反而可以联结起更为宽阔的世界文学地理。”[14]不妨说,刘大先的观念,和“差异即对话”的全球化本体观是契合的。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处理好差异的问题。差异是对话的差异,对话是差异的对话。差异本身就有对话的诉求,对话也是基于差异才有必要和可能。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差异。少数民族文学是差异的存在,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在世界文学中,它就是世界文学的构成,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和其他文学的对话,不是要消除自身的差异,而是要将自身的差异带入新境,从而获得更好的差异。
总之,《差异即对话》一书以“差异即对话”为本体,建构了金惠敏的全球化理论新观念,而且这种新观念已然达到了本体论的深度。同时,在这种理论建构中,金惠敏又处理和把握好了全球化问题所存在的比如差异与同一、民族和世界等之间的张力。基于这种本体论的新观念,金惠敏还践行了有关全球化问题的文化政治学研究。在存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风险的当下[15],在后理论持续地对理论进行“清算和反对”的“氛围”中[16],金惠敏的研究无疑有非常积极的理论效果、现实价值和“引申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金惠敏就完成了全球化的研究进程。套用一下他的“差异即对话”,我们恐怕也可以说,作为一种哲学的全球化,一定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同时也就会生成对话的内在诉求。我也相信,对话才能保证我们对全球化的言说常说常新!非常期待金惠敏能够一如既往地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积极对话,继续把中国学术和文学文化的差异带入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