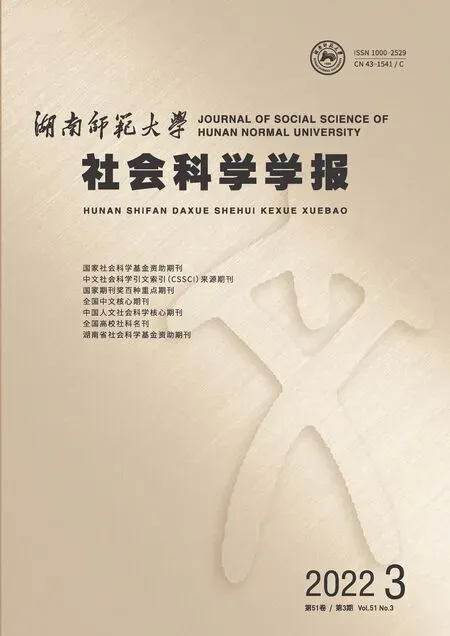论唐宋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
2022-03-24张利国
钟 涛,张利国
喜雨赋是以“喜雨”为题材的赋体文学,产生于晋宋时期,多用于干旱时节祈雨成功后向上天以及参与祈雨的皇帝或地方官员表达感谢与歌颂。这类作品最明显的标志是在赋题中直接标示“喜雨赋”字样①。唐宋喜雨赋共存9篇,与同时期喜雨诗、喜雨文以及祈雨文相比,有着独特的文体特征、主题内容和书写方式。唐宋两代,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也存在较大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相对于同时代喜雨诗而言,学界对唐宋喜雨赋关注不够。目前所见论著,或将喜雨赋简单归为祈雨文进行整体考察,或将喜雨赋作为写“雨”题材的赋体文学进行意象的探析,或以喜雨赋为史料进行祈雨礼制、祈雨风俗以及祈雨文化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对唐宋喜雨赋有了初步的观照,但大都只是整体提及,未加深析,专题、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付之阙如。本文拟以唐宋喜雨赋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系统地考察其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探究其主题内容、言说策略与文化意蕴。
一、“有志乎民”与唐宋喜雨赋主题生成
现存完整的喜雨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傅咸《喜雨赋》及南朝宋傅亮的《喜雨赋》。这两篇喜雨赋与后来的盛唐开元时期玄宗皇帝李隆基、张说、韩休、贾登、徐安贞与李宙等6人创作的6篇喜雨赋一样,都是宫廷应制之作。这些作品都以中央(皇帝)为中心,且以大型祈雨仪式为背景,其主题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在具体言说过程中也往往会提及统治者对黎民百姓的关心与体恤,即“有志乎民”。降及南宋,王炎、张侃、王柏等3人创作的3篇喜雨赋标志着喜雨赋的书写发生了变化:创作中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创作主体主要是地方官僚、士人,歌功颂德的主题有所淡化,“有志乎民”的主题内容则更加鲜明突出。
喜雨赋虽有唐宋之变,但主题内容依然是歌功颂德与“有志乎民”,只是侧重点与书写方式有所不同。唐宋喜雨赋这两个主题是怎么形成的呢?显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值得探索。
“喜雨”一词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僖公三年》,是传者对经文“六月,雨”的解释:“‘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春秋》经文未见“喜雨”“有志乎民”之意,传者却为何对僖公三年六月的这场雨作如此解读呢?众所周知,《春秋谷梁传》主要是用来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的,显然这是传者对孔子“微言大义”的阐释与发挥。
关于降雨情况,《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年至三年记载有以下几处:
(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郑。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夏,四月,不雨。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
由此可知,从鲁僖公二年十月至三年五月都没有降雨,《春秋谷梁传》传文或曰“不雨者,勤雨也”,或曰“不雨者,闵雨也”。“勤雨”,杨士勋疏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1]可见国君盼雨之心,恤民之意;“闵雨”,杨士勋疏云:“经一时辄言不雨,忧民之至。闵,忧也。”[1]可见国君忧民之心。到僖公三年四月依然不雨,《春秋谷梁传》传文曰:“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连续不雨,国君忧民之心愈发深切。传者此处进一步回答了国君之所以闵雨,是因为心中有百姓。同年六月降雨,《春秋谷梁传》也作出了“有志乎民”的解读。一“喜雨”,一“闵雨”,皆曰“有志乎民者也”,可见在《春秋谷梁传》作者眼里,鲁僖公是与民同忧喜的。这是对鲁僖公的赞扬。
结合《左传》僖公三年的传文:“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2]我们可知,从十月到次年五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降雨,但是没有形成干旱灾害,所以经文只说不雨,并未云“旱”。另据《春秋》所用历法“周历”,这段时间正是农作物播种与生长的季节(笔者按,周历以十二月为岁首正月,因此这段时间相当于夏历三年正月至四月),天不降雨就会对作物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干旱灾害,因此言国君“闵雨”是害怕成灾;而僖公三年六月(即夏历四月)正值小麦即将成熟的季节,这场“及时雨”满足了农作物的需要,消除了灾害发生的隐患,因此言国君“喜雨”。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对此有详细解释:“闵雨与民同其忧,喜雨与民同其乐,此君国子民之道也。观此义则知春秋有惧天灾恤民隐之意。遇天灾而不惧,视民隐而不恤,自乐其乐,而不与民同也,国之亡无日矣。”[3]另《左传》孔疏曰:“文二年传曰:‘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言僖有忧民之志,故每时一书;文无忧民之志,是以历时总书。”[2]两处“有志乎民”的解释都反映了国君体恤人民、与民同喜同忧的情怀。《春秋谷梁传》的解读就为“喜雨”附加“有志乎民”的政治评价意义,即对文公“无志乎民”与僖公“有志乎民”的比较,而作出历史的价值评价。也可以说,在传者看来,“有志乎民”是僖公“喜雨”的原因。
综上,“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即体现统治者体恤人民、与民同忧乐的情怀。朴素的“喜雨”情感经过儒家经典(《春秋谷梁传》等)的解读与阐释而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意义,成了儒家学者对统治者进行价值评判的依据,也成为唐宋喜雨赋歌功颂德与“有志乎民”之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的深刻文化渊源。
与喜雨赋几乎同时,直接以“喜雨”名篇的文学作品是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喜雨诗。目前可见最早的喜雨诗是曹植的《喜雨诗》,而后有南朝宋谢庄《喜雨诗》、谢惠连《喜雨诗》、鲍照《喜雨诗》、南朝齐谢朓《赛敬亭山庙喜雨诗》、南朝梁庾肩吾《从驾喜雨诗》、北朝齐魏收《喜雨诗》以及北周庾信《奉和赵王喜雨诗》和《和李司录喜雨诗》等。《全唐诗》有三十多首喜雨诗,与魏晋南北朝一样,这些喜雨诗的主题内容大多表达的是诗人对天降甘霖的喜悦之情,也蕴含着对天下丰收的期待心理。
喜雨赋与喜雨诗相比有独特的主题内容与书写策略。喜雨诗偏重抒情,主题比较多元,或抒一时之趣,或描一处之景,或用于唱和交游,或用作独抒性灵。而喜雨赋更注重宏大叙事,主题内容主要集中于歌功颂德,润色鸿业,大多具有政治功能与礼制内涵。《全唐诗》收录的三十多首喜雨诗,其主题主要是表达个人情感,即便在朝堂创作的喜雨诗也多是君臣之间的唱和娱乐而已,并没有喜雨赋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二、唐宋喜雨赋主题内容与书写方式的承与变
唐宋喜雨赋继承了晋宋时期傅咸、傅亮赋作的基本体制,并且有所发展,也更加趋向成熟。因历史文化语境不同,唐宋喜雨赋主题内容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特色。唐代喜雨赋以歌功颂德为主要主题,也在客观上体现着“有志乎民”;而南宋喜雨赋歌功颂德色彩有所淡化,“有志乎民”主题更加明确与直接。
目前流传下来的6篇唐代喜雨赋,是唐玄宗李隆基与五位大臣在一次大型祈雨仪式结束后同场集体唱和之作。据《玉海》唐玄宗《喜雨赋》条载“张说等和者五人……贾登赋十有六年”[4],可知这次集体创作发生于开元十六年(728)。在内容上,这些喜雨赋主要书写祈雨成功后的喜悦之情,并表达对上天降雨的感谢以及对皇帝德行配天、恩泽万民之精神的歌颂,也在客观上展现了国家的盛世气象,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与礼制文化内涵。
按照创作主体,还可以将唐代喜雨赋细分为两类,其一是帝王所作,这里指的是玄宗皇帝;其二是统治集团高层核心人员所作,主要是指应制作赋的五位大臣。
唐玄宗李隆基的《喜雨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第一篇由帝王创作的完整的喜雨赋作品。皇帝作为祈雨仪式的参与者,同大臣一起向上天祈雨。祈雨有应后,又与诸位大臣集体作赋进行庆祝。赋开头“仰重华于齐政,步文命之彝伦。何天道之云远?亦明征之在人……恐岁凶之及人,宁天谴于我身”[5],表现了玄宗皇帝担忧旱灾殃及百姓、宁愿天谴己身的责任担当。接下来该赋简单回顾祈雨过程,又用骈俪化的语言详细刻画了雨的形状、声音、节奏、意境之美,俨然一幅有声有色的喜雨图,字里行间也能够使人感受到被甘霖滋润的盛世大地的美好。前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玄宗皇帝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仿佛感受到了上天对其政绩的肯定,自然十分喜悦。他在赞美这场雨泽披天下的美德的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希望迎来丰年,希望百姓知礼节,国家消除边患与内乱,安定富强,从而实现垂拱而治的美政。他也可以像鲁僖公一样,被历史学家列为“有志乎民”的贤圣君主之列。
参与奉和圣制的五位大臣是张说(667-731)、韩休(672-740)、贾登(?-?)、徐安贞(?-743)与李宙(751-815)。这五位大臣当时都是朝廷重臣,从事的工作也大都与国家礼制有关。根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开元十六年)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6]张说在当时是集贤殿学士。根据《旧唐书·韩休传》:“(韩休)出为虢州刺史……岁余,以母艰去职,固陈诚乞终礼,制许之。服阕,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诰,迁尚书右丞。”[7]韩休在当时担任知制诰,尚书右丞。据陶敏辑校《集贤注记》:“登,开元十五年预撰《初学记》,又预修《开元礼》……十六年和玄宗《喜雨赋》。”[8]贾登此时为起居舍人,当时正在参与修撰《大唐开元礼》。按照《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徐安贞)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9]徐安贞是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常常参与皇帝起草诏书。又据陶敏辑校《集贤注记》:“张说、徐安贞、贾登、李宙、徐浩均集贤院中学士、修撰,故此次唱和活动当为院中活动之一。”[8]李宙在当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修撰。五位喜雨赋作者当时身处朝廷要职,又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盛世,在天子身边,正是人生风光得意之时。这样的政治身份与处境,再加上他们言说对象是皇帝,这些就决定了他们创作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功能主要是歌功颂德、润色鸿业。
贾登《奉和圣制喜雨赋》(以下几篇赋作题目均为“奉和圣制喜雨赋”,为叙述方便,仅列作者姓名):“天昭厥诚,神降之吉;霈然为雨,不俟终日”“非圣德之兼济,何以臻于此焉?”“铄皇篇兮熙帝谱,于胥德兮振万古。”[10]张说:“虽欲谈天而窥管,孰知尧德之为大。”[11]韩休:“乾道兮下济,湛恩兮汪濊,四三皇兮六五帝,于胥乐兮万千岁。”[12]李宙:“愿依稀兮其奚多,虽三五而可越。”[10]徐安贞:“仰宸仪之法度,闻天韵之宫征,大舜之庆云已发,武帝之秋风莫比,钦丰岁之余裕,赜先天之至理。”[10]五位大臣一致认为,之所以能够祈雨成功主要是皇帝的圣德动天。而且,他们也认为玄宗皇帝的德行堪与上古圣王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帝之所以值得歌颂,主要在于皇帝厚生爱民。因此,五位大臣的歌颂集中在一点,即“有志乎民”。贾登:“恐二气之相迫,于兆人而不臧。”[10]张说:“恐降灾兮此下民,罄虔祈兮我仁主。”[11]这是君臣同时同场的一次集体言说与对话。虽然旨在歌颂“仁主”,但关注点主要在于玄宗皇帝的仁圣爱民。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开元)十六年,东都、河南、宋亳等州旱。”[13]而且到此时全国已经是连续三年亢旱。这场雨真可谓“久旱逢甘霖”,焉能不令人喜悦,皇帝为民祈雨成功,焉能不歌功颂德。
综上所述,唐代的6篇喜雨赋的体制与主题内容继承晋宋时期,并在此基础上走向成熟,书写更加充满恢弘气象,这是盛唐的气象。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这是前人对赋体文学特色与功能的概括,也正体现在唐代喜雨赋主题内容之中。
如前言所述,喜雨诗重视抒情,在礼赞盛业方面相比喜雨赋不具有优势。且以张说《奉和同刘晃喜雨应制》诗为例试作比较。诗曰:“青气合春雨,知从岱岳来。行云避师出,洒雨待军回。厌浥尘清道,空濛柳映台。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开。”[11]这首诗与上述张说《(奉和)喜雨赋应制》一样同是应制之作,但显然诗更加简洁,只描写了降雨的场面,主要是君臣喜悦心情的诗意书写,更多是游宴的性质,充满闲情雅致,与其赋作详细铺陈和再现祈雨礼制活动过程的恢弘气象有很大不同。
总的来说,喜雨诗侧重瞬间情感的摹写,注重抒情,注重诗情画意的雅致,因而淡化了仪式性,强化了文学形象性;而喜雨赋与之相反,目的是体国经野、歌功颂德,因此更加重视仪式性与政治性,其书写方式与祈雨礼制活动有一定的同构性。
较之唐代,南宋的喜雨赋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创作主体由皇帝与中央核心官员转变为地方官员或一般士人。其二,创作场合也由中央转移至地方。这一变化也就导致了喜雨赋主题内容及书写方式的变化,具体体现在歌功颂德的色彩有所减轻,“有志乎民”主题内容的书写更加鲜明与直接。同时,个人化书写的色彩逐渐增强。宋代共有3篇喜雨赋,都创作在南宋时期。作者王炎(1137—1218)时任鄂州崇阳薄[14]。作者张侃(1189—1259)此时身份不明。作者王柏(1197—1274)此时是一般的士人,未入仕途。
王炎的《喜雨赋》是为赞颂武昌崇阳宰吴侯祈雨成功而作,作于淳熙三年(1176)②。赋序云:
丙申夏四月,武昌阖郡不雨。越五月三日,崇阳宰吴侯以诚祷,雨获优渥。按《春秋》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说者曰:“书不雨者,闵雨也。书雨者,喜雨也。喜雨者有意于民也。”今吴侯祷雨以诚,不崇朝而雨随之,可谓有志于民矣,作《喜雨赋》。[15]
该序详细叙说了作赋之缘由。作者直接引用《春秋谷梁传》关于“喜雨”之“有志乎民”的解读,借此称许吴侯“有志乎民”的责任担当。赋后歌曰:
“霢霂兮涵濡,污邪兮满车。其饟兮有黍,稻粳兮可炊。岂弟之泽,民肥不臞。我字我抚,公留勿归。均此大惠,公归勿徐。”[15]
描绘了雨润苍生的丰收图景,再次表达对吴侯惠及一方之功业的赞许。而吴侯的谦虚回答颇有意味:
吴侯闻而哂之曰:“父老之言何美之溢也?向也民忧而忧,此吏责也。今也民喜而喜,吏不敢以为德也。然旱而祷,祷而雨,如重负之获释也。”[15]
为民祈雨虽然是地方官的法定职责,但吴侯“民忧而忧,民喜而喜”的爱民情怀,却也配得上这“溢美之词”。这让我们不由地想起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16]的伟大情怀。不仅如此,往深处言,这显然是王炎等有宋一代士大夫对这种“有志乎民”精神的自觉传承。
王柏的《喜雨赋》也是献给地方太守,表达赞颂之意的。该赋开头陈述旱情:“农人告予曰:‘两月不雨,骄阳盛炽,伤禾稼之就槁,竭陂塘而莫溉,沟浍眢涸,草木病瘁。渺一饱之未期,敛双眉而堕泪。’”[17]面对如此严峻的旱情,作者不禁为之愀然同情。接下来该赋书写了祈雨、降雨的过程,表达祈雨有应的喜悦之情:“化雕瘵而丰裕,消愁叹而欢忻,一点一谷,如坻如京。”[17]最后,“童子不识秋事之可庆,但喜得新凉于户庭也。长啸于是诵孟氏‘勃兴’之语,赓诗人‘有年’之篇,献于太守。太守不有,归乎天子。天子谦谦,功不敢专,让于皇天。天冥冥不得而名,本大德之好生也欤”[17]。把这场喜雨归功于太守,太守不居功,归为天子,天子归为上天,最后归为天之大德好生。可以说,此处“大德好生”之于皇天、皇帝、太守是一致的,都是“有志乎民”。另外,此赋还映射了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把天旱涝不定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充满对王安石变法辛辣的讽刺意味,“长啸愀然,归而与客曰:‘四海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非王金陵之诗乎?想新法之纷张,瞻青苗而色沮,泽民之事业如是乎?金陵之所谓霖雨,犹今春之淫潦,所以基后日之祸也”[17]。其观点或可商榷,但作者“有志乎民”的情怀则溢于字里行间。
与王炎、王柏二赋相比,张侃的《夏喜雨赋》有着更明显的个人化倾向。该赋序“张子病暑,无以涤炎酷,效六一翁赋之。今得一雨,嫩凉入骨,向者日之虐,今为雨之赐”[18],交代了作赋之缘由。这篇赋与以上所述喜雨赋截然不同,可以说是打破了之前的体制,完全剥离了歌功颂德的政治意义与礼制内涵,而主要书写作者个人的人生境界。这里对降雨的喜悦之情的书写完全是一种审美性的,没有政治说教色彩。正如刘培所说,该赋“体现出理一分殊的感悟和透脱洒落的仁者襟怀,洋溢着人间气息、生活气息。这不同于陶渊明笔下的结庐人境而心远地偏的出世,更不同于王维的空山不见人般的孤寂,而是表现着人与万物、我与外物的共存共生和谐相处,这不是濠、濮之乐,而是曾点之境”[19]。这当然也是儒家士人在现实生活之上追求的更高一层的理想境界了。
三、唐宋喜雨赋的言说策略及文化意蕴
唐宋喜雨赋的重要文化价值不仅在于表达为苍生祈得甘霖的喜悦之情,也不止于歌功颂德的空洞叙事,也不重在对神灵的感恩戴德,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现实目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示、教化与统治秩序的稳定乃至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与弘扬。
如上所述,唐代喜雨赋是祈雨成功后对上天及皇帝表示谢恩的华美颂歌。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在这里,“有志乎民”显然不只是喜雨赋重要的主题内容,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一种政治言说策略。一方面表征玄宗皇帝德行高美、顺天应人,理应受到万民拥护。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一种儒家的集体意识,即合格的皇帝当重民恤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实现统治秩序稳定。关于喜雨赋这种言说策略,笔者主要从以下三点进行论述:
首先是以礼制言说。喜雨赋是祈雨成功之后的歌颂,虽并非礼制仪式所必需,但本身与祈雨礼制有直接关系,其创作程式也体现了与祈雨仪式的同构性。不妨说,喜雨赋的书写也是对祈雨礼制的一种言说,通过祈雨仪式,强调祈雨礼制,宣示国家意识形态教化,这是喜雨赋的一种政治言说策略。
关于唐代祈雨礼制,颁布于玄宗开元年间的《大唐开元礼》有明确的规定:
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并同小祀……若雩祀之典,有殊古法,《传》曰:“龙见而雩。”自周以来,岁星差度,今之龙见,乃在仲夏之初,以祈甘雨,遂为晚矣。[20]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唐代把国家祭祀礼制分为大祀、中祀、小祀,而祈雨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到了德宗时期,祈雨祭礼已从小祀升格为中祀。德宗李适《拜风师雨师诏》:“风雨等师,升为中祀,有烈祖成命,况在风雨,事切苍生……朕当屈己再拜,以申子育万姓之意。”[5]这份诏书体现了德宗皇帝对“事切苍生”祈雨祭祀的更加重视。重要的祈雨祭祀活动,皇帝还要亲自主持祈雨仪式。所谓“礼别异”,祈雨礼制对祈雨主体等级的严格规定,在深层意义上体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
唐代贾登等人创作喜雨赋时正值编纂《大唐开元礼》,作为主要参与者,他们更是对礼制建设的政治目的有更深刻的体会与自觉的意识,这势必体现在作品中。如贾登“直以万乘之贵,躬亲三日之祠”[10],韩休“设槱燎,奠椒醑”[12],还有玄宗皇帝“尔乃洁斋坛墠,五精是祠,暴立炎赫,三日为期”[5]。这些都是对祈雨仪式的书写,体现了皇帝躬行祈雨的光辉德行。
荀子《天论》云:“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天旱而雩……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21]“荀子的议论深刻而富哲理,天旱而雩,其实是君王、地方官关心农业,作为政治文饰手段罢了。要之,在‘时灾系政,人患由君’的政治理念下,皇帝、地方官员通过祈雨活动强化了君权神授、等级秩序的思想。祈雨也成为一种象征,凸显皇帝君临天下、子育万物的身份”[22],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礼制的言说,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对皇帝德行与威严的言说。
如本文前言所述,有学者将喜雨赋归入祈雨文,并统而言之,认为喜雨赋体现的也是对祈雨礼制的强调,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问题。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喜雨赋与祈雨文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祈雨文是祈雨礼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祈雨活动的一个物质环节,而喜雨赋并非祈雨活动所必备,只是对祈雨礼制的一种诗意化的言说,是一首华丽的颂歌。
其次是以神道设教言说。《文心雕龙·原道》云:“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23]刘勰指出“神理设教”是中国古代文章一种古老而重要的书写策略与言说方式。喜雨赋的创作也对此有所继承。喜雨赋与祈雨活动有关,是祈雨成功之后对上天神灵与帝王的感谢与盛赞。在行文中简短地描写神灵,充满了神话色彩。这里表面上是一种对神的言说,其最终目的显然也是对人的言说,神灵不过是用来点缀与衬托人间帝王德行功业的一面镜子,这显然是一种高明的言说策略。
又如,唐玄宗《喜雨赋》“尔乃洁斋坛墠,五精是祠,暴立炎赫,三日为期”[5],描写了祭祀“五精”之神而祈得喜雨的过程。贾登“王言既出,圣心惟一;天昭厥诚,神降之吉;霈然为雨,不俟终日”[10],指出了皇帝至诚之心感动上天神灵,祈得喜雨。张说“是月也,朱明渐半,紫油未吐,恐降灾兮此下民,罄虔祈兮我仁主。退象龙之礼祷,斥持鹭之貌舞,屏翳惭其废职,祝融悔其迁怒。山泱漭而出云,天滂沱而下雨。速一言而感应,克二日而周溥”[11],指出皇帝的震怒使得神灵感到悔恨而降雨,显示了皇帝的威力。
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24]。天子在世间的行为要受到上天的监视。天子在人间行为的好坏,是否遵循天道,是否恩泽万民,都会得到上天在人间的祥瑞或灾异的反应。唐人陈子昂也有同样的观念:“天人相感,阴阳相和。”[25]古代的重大祈雨仪式,一般皇帝要亲自参与,代表万民与天进行对话。这种行为本身就表征着皇帝受命于天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而在大旱之年,祈得喜雨正说明了皇帝德行的光明,更强化了这种神圣性与合法性。一方面,唐代五位大臣的喜雨赋代表君王向天下百姓言说,使其拥护天子的权威与维持统治的秩序,从而实现政治教化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高一层次的言说者(作为儒家道统传承人的士人)也借助天的感应来教育君主,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合乎儒家明君的标准。这样就逐渐形成天-君-臣-民同构的较为稳定的意识形态教化体系。正如李春青说:“这种言说方式的创造者与运用者只能是政治上属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们,是在特殊语境中产生的特殊话语,所以言说本身就是对言说者特权地位的肯定与强化。”[26]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有志乎民”的体现,不过是更高意义上的体现。而且,在喜雨赋的书写中,皇帝不仅德行符合上天的要求,而且感动了上天,甚至战胜了上天,还可以驱使各路风神雨师为皇帝效力。
最后是以民本话语言说。如上文所言,“有志乎民”成为评判统治者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唐宋喜雨赋在言说中处处体现着“重民”“利民”的观念。开元十六年,玄宗君臣同作喜雨赋,是一种集体言说。玄宗“恐岁凶之及人,宁天谴于我身”[5],贾登“恐二气之相迫,于兆人而不臧”[10],张说“请言瑞雨之可喜也。协气交泰,嘉生是赖,湛覃而不溺,衍溢而不害”[11],虽说是为了歌功颂德,但也体现了对黎民的重视。毕竟“覆舟之喻”萦绕心中。可以说,这种与民同喜同忧的思想成为统治者以及儒家知识分子的潜意识。
这种民本思想在宋代的喜雨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直接,因为言说主体是士大夫,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力,直接参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民同乐是孟子以来儒家士人自觉追求的一个政治理想,这时候的言说者是儒家民本话语的制定者,即一代代儒家学者。他们落实的不只是唐代喜雨赋表现的对百姓的教化与控制,而是自我审视、自我说服,以及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
如上,王炎的《喜雨赋》直接道出了“有志乎民”“与民同忧同喜”的文化内涵。该赋不仅表达了对崇阳吴侯功业的赞美,表彰其爱民情怀,其实也能反映出作者自己同样的爱民情怀。王炎是南宋新安理学的重要人物,与理学家朱熹、张栻交往甚厚,受朱张二人民本思想的影响较大。朱熹鲜明地提出了“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与共之,犹虑有不获者,况皆不恤,而惟自丰殖,则民安得不困极乎”[27]。同时,他还奉劝封建统治者要重视农业生产,提出“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28]。而张栻主张“德者,所以为民极也”[29]“夫人主之职,莫大于保民”[30]“与民同其乐者,固乐之本也。诚能存是心,扩而充之,则人将被其泽,归往之惟恐后,而有不王者乎”[30]。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王炎受到这些当时流行的民本思想主张的影响。张栻“惟吾忧民之忧,故民亦忧吾之忧。忧乐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理之公也”[30],显然对王炎创作此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王柏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在思想上也同样受到朱熹的影响。其《喜雨赋》中对两月不雨引发的旱情深感愀然,与太守一起为民祈雨,终于天降甘霖。作者将降雨的功劳归于太守及天子的厚生爱民之德行。
此外,本文第二部分提到南宋张侃《夏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以上喜雨赋有所不同。该赋的言说主体是独立个体,书写了与天地造化为一的人生境界,这是一种完全基于审美意义的道的言说。作者把天地万物都视作是齐同的,就连天上的神仙也可以“延以佳宾,酌以醲醇”,与“我”促膝而谈,最后达到一种“商羊起舞”的天人和谐的境界。这是一种“曾点之境”(刘培语),亦即历代儒家学者所向往的与仁道自然融合的更高社会人生理想。这显然是“有志乎民”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的另一种补充与升华。
正如理学家张栻所说:“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31]王炎、王柏的喜雨赋在表达“有志乎民”的同时,也是以士人的身份在强调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人生追求。
综上所述,喜雨赋的创作从唐至宋经历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创作场合、创作主体与书写方式方面。这是盛唐与南宋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喜雨赋创作方面的体现。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盛世,疆域辽阔、军力强盛、经济繁荣,士人们充满高度文化自信。唐玄宗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重新巩固李唐江山的政权,再加上他执政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可谓万民拥护、景仰的有为之君。而五位大臣又都居高官、处庙堂,当然要歌颂,喜雨赋的言说方式更侧重于以神道设教与以礼制言说;而到了南宋时期,大宋王朝失去了半壁江山,这皇帝当然就不好太过分去歌颂,正如刘培所言,“没有强大的王朝作依托,没有自豪开阔的胸怀,润色鸿业的颂声是唱不成调的”[32]。而且作为胸怀天下、与民同乐的宋代士大夫,他们与百姓更加亲近,也有着爱民的自觉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的喜雨赋多直接表现爱民的精神,这个时期的喜雨赋的言说策略主要是以民本话语言说,实质上也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与言说。当然也是对儒家所倡导天下秩序的强调。
结语
“喜雨”本是一种因降雨而喜悦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产生于我国古代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状况之下,体现的是古人对风调雨顺之丰年的期盼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春秋谷梁传》“有志乎民”之解读,“喜雨”附加了一种政治道德情感,成为人们对统治者体恤百姓、与民同喜同忧之精神歌颂的价值依据。“喜雨模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反复书写的一种民族文化原型。唐宋喜雨赋内含“有志乎民”这一文化精神。在表现歌功颂德与关切民生的同时,唐宋喜雨赋通过礼制言说、神道设教与民本话语这三种言说策略宣示着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实现对君、臣、民等的教化,以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以及儒家民本思想的永世传承。而这种言说策略与文化意蕴在唐宋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唐代喜雨赋更强调歌功颂德,其主要依据是统治者“有志乎民”;宋代喜雨赋则更加突出表现“有志乎民”,体现了士大夫的仁者之心和天下情怀。
注释:
① 其他如贺雨赋之类,其内容虽涉及喜雨情感,也有歌功颂德之意,但与喜雨赋有着明显不同,本文仅将此作为参考。
② 结合该赋序所言“丙申夏四月”,参考作者生卒年,对照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可知,该赋作于淳熙三年,即公元1176年。这一年前后是气候相对寒冷且干旱的时期,旱灾发生频次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