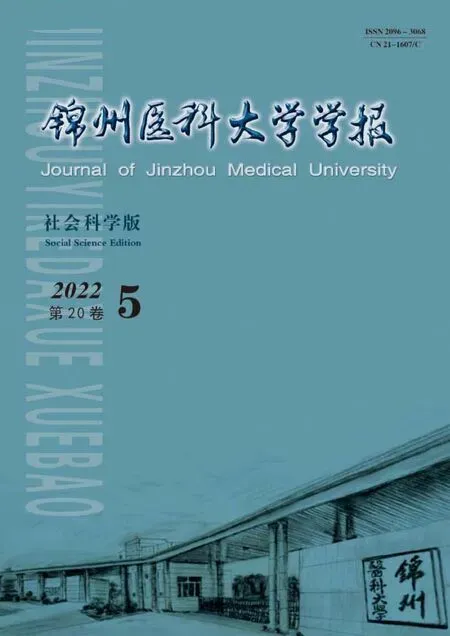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及其话语体系的跨文化建构
——以《黄帝针灸甲乙经》为例
2022-03-24杨建新吴雅萌
杨建新,吴雅萌
(河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其话语体系不仅包含中医药理论知识,还蕴含阴阳五行、气血精神等中医学说。这些内容结合了儒家和道家等诸子百家理念,包含深厚的哲学思想。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一方面可为全人类健康贡献中国智慧,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也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典籍是中医实践过程中的文字记载,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基石。如何提升中医药典籍的译介,推动中医药典籍话语在目的语文化中的跨文化构建,是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重点和难点。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黄帝内经》《黄帝针灸甲乙经》《神农百草经》《伤寒杂病论》《难经》等重要中医药典籍都被译介至海外。现有研究也已对病理类、药理类典籍外译进行了一定探讨,但对《黄帝针灸甲乙经》等针灸类典籍外译尚欠讨论。针灸典籍话语的跨文化构建,除了提升针灸的国际传播外,也可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医话语体系的了解,对中医药话语跨文化的构建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本研究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黄龙祥整理本的汉语本、Yang Shou-zhong 和Charles Chace 的英译本为案例,讨论在针灸典籍话语跨文化构建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以期推动中医药典籍话语体系的跨文化构建。
作为现存中国最早的针灸典籍,《黄帝针灸甲乙经》有三个特点。其一,《黄帝针灸甲乙经》在历代都经过修订和专业人士的重新编撰,并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完善理论。据考察,“1949 年建国后,《针灸甲乙经》多次出版、影印、校勘、注释、整理版本共计49 种”[1]。其二,《黄帝针灸甲乙经》与中国历代政治联系紧密,政治需求可影响其发展方向。例如,皇甫谧在进行编纂时曾受到皇帝追求长生不老观念的影响,险些因以自身为施针对象而丧命。其三,《黄帝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针灸学典籍,涉及知识面广、专业性强、实践难度高,并涉及来自中国哲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多学科内容。因此,在翻译《黄帝针灸甲乙经》过程中不仅面临来自源文本的挑战,还有来自同一概念下不同话语表达的挑战,译者需同时调动中医药百科知识与多学科知识进行准确、专业化翻译。
一、《黄帝针灸甲乙经》跨文化话语构建的挑战
1.话语复杂性要求翻译的跨文本可考证性。中医药典籍话语跨文化构建的首要任务是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跨文本可考证性,即中医药话语中的同一所指,在典籍译本中也实现一致;目的语读者在阅读不同典籍译本或阅读中医药汉语本时,对同一所指在不同文本中能找到统一可理解的能指。中医药典籍话语通常存在同一所指有不同能指来体现的现象,这便造成了中医药术语翻译的复杂性。该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医药话语中的同一所指在不同典籍中所用的能指不同形成了中医药术语的多样性;同一典籍存在多个版本,中医药典籍在历朝历代会经由不同的主体修订和重新编撰,同一典籍中的部分名词和概念甚至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不同版本中同一所指所用的能指也可能存在差异。下文将通过对比《黄帝针灸甲乙经》的源文本与目标文本进行具体说明。
例1
源文本:足阳明,外合于海水,内属于胃。
目标文本:The foot yang ming relates to the River Hai i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pertains to the stomach in the interior(of the body).
源文本中的“足阳明”是人体十二经脉之一,全称“足阳明胃经”,简称“胃经”,属于中医药针灸典籍中的常用话语。《针灸大成》 《足臂十一脉灸经》 《灵枢·经脉》 《圣济总录》 等都有关于“足阳明胃经”的记录。在《针灸甲乙经》中,译者将“足阳明”译为“The foot yang ming”。然而通过对国外Magic TCM 中医典籍用语网站查询发现,“足阳明”英语为“Stomach Meridian of Foot-Yangming”。这与译本所选用的《针灸甲乙经》英语译本中的译法大不相同。Yang Shou-zhong 和Charles Chace 对《针灸甲乙经》 的译法忠实于源文本字面,将“足阳明”译为“The foot yang ming”,未将“胃经”翻译出来,缺乏对“足阳明”这一能指的全称“足阳明胃经”的考察,也缺少对Magic TCM既有译法“Stomach Meridian of Foot-Yangming”的考证,使“足阳明胃经”这一术语在目的语话语中缺乏统一性,造成了读者在阅读不同中医药典籍时对跨文本考证的困难。作为承担中医药话语跨文化构建直接使命的译者,如果缺乏对术语在不同文本中的考证,以及对同一所指不同译文的考证,将会导致中医药话语无法实现跨文本可考证性,无法实现其在不同典籍译本中的跨文化建构和传播。
2.话语哲学性要求翻译的多维性。中医药典籍是中国古代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医学上的体现,典籍所记载的病理、穴位、针灸手法等无一不蕴含着中国哲学思想。可以说,中医典籍集医学和文学价值于一体,既有科技文本的特征,也融合了儒、道、佛等哲学文化[2],中医话语处处体现着分形观、整体观、辩证观等中国哲学思想。分形观体现在其对“肝”“心”“肺”“脾”“肾”等身体系统的描述。整体观是对医药典籍的体系化研究,它将人体内部机能与外在穴位、自然系统相结合,认为人体九窍、五脏、四肢十二关节等都与天地自然相应,人的生长壮老也不能脱离天地自然而存在[3]。辩证观主要表现在其对于万物状态所持的观点,中医认为一切事物并非一成不变,世界万物相生相克。然而,“因为中医药学的大部分用语在欧洲语言中都缺乏对应语,从而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4]。
例2
源文本:心为牝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角,其味酸。
目标文本:The heart is a masculine viscus,its color is red,and its season is summer.Its days are bing and ding,its sound is zhi,and its flavor is bitter.
中国古人将对自然万物的体验反映到医学典籍的编纂中,体现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例2 源文本体现出古代对于色彩、时令、时日、声音和味道的哲学式认识。撰写人皇甫谧将人的身体与天地自然紧密结合,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解释了“心”所对应的颜色、季节、次序、音、味。在翻译中,译者对“色”“时”“日”“音”“味”进行了语言的对应转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的五脏对应“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春、夏、长夏、秋、冬”五个时令、“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个时日、“角、徵、宫、商、羽”五种声音、“酸、甜、甘、辛、咸”五种味道。然而在翻译中,由于有限的篇幅和文化差异的影响,译者并未将相应的哲学观念反映在目标文本中,译文用“heart”“color”“season”“sound”“flavor”等词与源文本一一对应,译出了源文本的表层意义。译文在语言层面准确,却未将源文本中多维的哲学蕴涵完全译出,古人对天、地、人、自然的认识未得到有效体现,中医话语在跨文化背景下的多维文化意义也极大降低。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度翻译的方式[5],阐释中医药话语体系背后的中国哲学思想,多维度展现中医药话语背后的思维哲学根基,以此来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铺陈思想和认知背景,让域外受众在整体上深度把握中医药话语的脉络。
3.话语模糊性要求翻译的医学专业性。中医药典籍所涉概念纷杂多样,多为典籍撰写人在中国不同区域进行实地考察或以自身为实验所得的结论。因此,若不进行详细的背景考察撰写和书籍研读,很难准确理解词汇的意义。中医典籍话语的翻译对译者的医学知识掌握程度要求更高,需要译者具有一定的中医药知识基础,准确理解典籍所描述的症状、病理和医治方法,才能将其释译充分。
例3
源文本: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皇甫谧)
目标文本:Therefore,what are vitality(de),qi,life (sheng),essence,spirit,hun,po,the heart-mind(xin),reflection(yi),will(zhi),thought(si),wisdom(zhi),and worry(u)?
例3 源文本有多个具有高度总结性的词汇表达,部分词汇发音相同,在英语语境中容易产生歧义。目标文本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译者通过意译结合音译的策略翻译源文本中的十三个词汇。然而,使用这种策略后,目标文本存在两个相同音译术语zhi,即will(zhi)和wisdom(zhi)。对比发现,zhi 在源文本中所指是不同的。在源文本中,第一个(zhi)为“志”,指人的意志力。第二个(zhi)为“智”,是聪慧的意思。在目标文本中,译者用同样的音译方式翻译两个不同的概念,很容易导致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混乱。目标语读者既无法理解二者各自的意义,也无法进行准确区分。其二,译者对该句中多个平行词汇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即部分音译,部分不音译。对“德”“生”“心”“意”“志”“思”“智”“虑”这八个词汇,译者进行了对应词汇转换与音译并用的方式。对于“精”“神”“魂”“魄”这四个词汇却没有使用音译。“单纯的音译可能增加读者理解文本的难度,使译文产生‘支离感’,甚至有‘未译之嫌”[6],案例中的“气”“精”“神”“魂”“魄”的音译便是如此。这里的音译未译出源文本的所指,译后跟译前没有太大区别。虽然译者采取了“音释结合”的策略,但还是存在中医典籍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语义模糊问题,导致目标语读者的概念混乱。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医药典籍时,从一个中医药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准确定位话语的语境意义,诠释超出文字层面的内涵,在中医药话语跨文化转化中,力求准确,避免术语呈现给目标语读者带来语义模糊和歧义。
二、中医药典籍英译及跨文化背景下的中医话语构建传播
中医典籍的译介与相应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倡导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1.基于已有汉语中医词典推进汉英词典的转化。为有效推动中医药术语的跨文化构建,需以现有汉语中医药辞典作为基础,将已成文的中医药术语翻译并编撰成汉英对照辞典。国内市场已流通有各类中医药术语词典,如《简明汉英黄帝内经词典》 《简明中医大辞典》 《中医典籍大辞典》 《简明使用中医基础辞典》 《中国医籍大辞典》等;也有学者针对海外中医与中医文化学习者编撰出了中医名词英汉对照词典,如Wiseman &Feng Ye 的《实用中医药词典》(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李照国的《简明汉英中医词典》、原一祥等的《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及石学敏、张孟辰的《汉英双解针灸大辞典》。相比中国浩瀚的中医药文化与相关词汇表达,现有文献和词典规模仍很有限,大量中医药术语未被收入词典。此外,大多中医药词典的编纂者之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翻译标准。由于不同译者选择的源文本版本不同,或对源文本中古文的理解不同,词典录入的词汇和相应的翻译也有所不同。有鉴于此,应将中国现有的中医药辞典进行重新筛选、编撰,将其中的术语解释统一化,然后再通过建立一套具有文本可考证性、多维展现中国传统思想、专业性强的中医药汉英辞典,供相关从业者、学习者及对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群体参考、学习和使用。
2.译者与官方力量合作促进术语统一。中医典籍翻译要求译者不仅有扎实的古文阐释能力、流畅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高的文学素养,还需有相应的中医学常识。然而,独立的译者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翻译工程,当前少有译者能同时兼具语言能力、文学能力、中医学能力。因此,官方机构应提供知识、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一是知识支持。可针对译者开展相关中医典籍培训工程,提高译者对典籍中术语的理解与阐释。这点可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成立的“中医药名词术语成果转化与规范推广”专项课题,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成果跨文化转化与规范推广”项目,进行名词术语分类、撰写原则和体例,建立名词术语数据库,制定名词术语在线工作流程,进而形成汉英中医药名词术语库,供学习者进行双语学习。二是资金支持。投入资金,与中医药从业人员合作。中医药从业者既有相应的中医学知识,又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与其合作可以确保术语表达的正确性。通过与相关中医从业人员共同探究,可有效推进统一的中医典籍多语术语库的建设。三是人才支持。强化政府组织与世界针灸联合会、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世界医药机构的合作,筛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等官方文件的中医典籍,推动其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提高中医术语自身的辨识度,促进统一中医药话语的跨文化构建。
3.依托国际教育平台普及中医术语。国际中医药教育始终是中医药话语跨文化系统性普及的重要手段。中医药话语作为一套系统性的特殊行业语言,急需借助中外教育平台进行推广,增加国际受众对中医药基本概念的理解,培养域外中医药推广人才。截至2020 年,全球共有中医孔子学院7 所(亚洲、欧洲各2 所,非洲、美洲、大洋洲各1所),独立课堂2 个,下设课堂23 个。此类教育平台已成为传播与普及中医知识的重要平台,极大促进了中医话语的跨文化建构。此类学校可通过开设中医外语阐释与中医语言翻译班,开展相应教学活动,并定期对学员进行术语水平测试,使其具有基本的术语辨识与阐释技能。同时,中医孔子学院可开展国学培训。中医典籍所含话语对阅读者的国学素养具有较高的要求。若没有一定的国学知识做背景,则无法完全理解中医典籍的术语,更无法对目标文本进行甄别、判断或使用。因此,中医孔子学院等相关教育平台应大力推动国学与中医教学的结合,从教育入手,普及中医知识,促进中医话语体系的跨文化构建。
标准统一、涵盖范围广、可信度高、阐释力强的中医典籍话语体系的域外构建,对中医药的国际传播有重要意义。中医药典籍话语体系的跨文化构建中,多重能指要求跨文化话语建构的跨文本可考证性、话语哲学性要求翻译的深度性、话语模糊性要求翻译的医学专业性三个特点。因此,有必要从官方、译者、教育三方面入手:推动中医药汉英词典的建设、加强译者与官方力量合作促进术语统一、依托国际教育平台普及中医术语。只有从中医药汉英词典编撰、译者与官方合作、国际教育平台三方面入手,才能应对中医药典籍翻译的复杂性、哲学性和模糊性问题,推进中医药话语由汉语到外语的有效转化,传播中医药文化,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