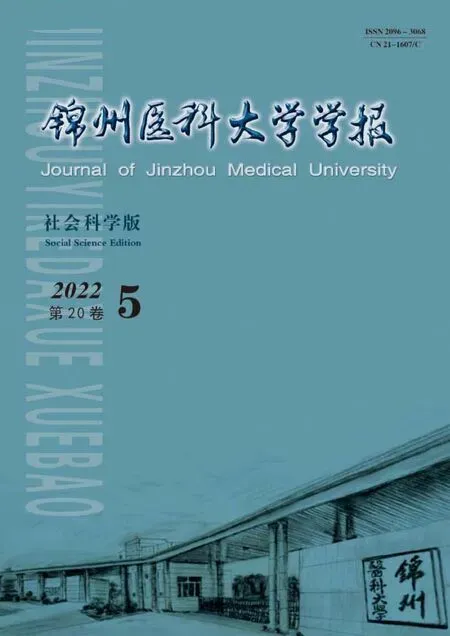过度医疗侵权法律理论的修整与补充
——基于111 份裁判文书
2022-11-09赵恒喆
赵恒喆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 年和2021 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6 年至2021 年的5 年间,我国人均卫生费用由3 351.7 元增长到5 348.1 元,截至2021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已达75 593.9 亿元,占GDP 的6.5%。我国人均卫生费用飞速增长、医疗卫生费用巨额支出现象的产生,首要原因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民众收入水平提高、对个人健康愈发关注亦是重要因素。除了这些积极方面的缘由,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严峻的问题——过度医疗,其宛如生长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机体上的一颗毒瘤,贪婪地消耗着养分——卫生事业社会资源,这不仅减损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效果,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社会福祉,还可能成为激化医患矛盾的“定时炸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治理过度医疗问题、维护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须多法并举——不仅需要行政法、刑法等公法实施制裁,而且需要侵权法律调整过度医疗侵权民事法律关系。当前,我国过度医疗侵权相关法律很不完善,司法裁判缺乏统一标准,过度医疗侵权救济困阻重重,而现有的过度医疗侵权法律理论滞后于实践发展,难以给法律修改提供优良的指导。笔者试图从权威案例切入,洞察过度医疗侵权的社会现实,进而对过度医疗侵权法律理论提出修整和补充的建议,以期为统一过度医疗侵权裁判标准、扫除权利救济障碍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方案。
一、案例来源、总体情况与问题浮现
本文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内容为“过度医疗”,设置法院层级“高级法院”,限定案由“民事案由”,共得到判决书130 份。排除明显无关的结果,最终得到判决书111 份。基于案例统计,笔者发现:
第一,过度医疗案件诉讼的当事人问题。过度医疗侵权诉讼的当事人,并非只有主流学说论及的医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与患方(患者及其家属),还包括医患关系以外的过度医疗侵权受害人(以下简称“第三人”)。在111 个案例中,仅有55 例主张过度医疗者为患方,而其余56 例主张者均为第三人——导致疾患的另案侵权人(以下简称“致患侵权人”)(41 例)、用人者(8 例)、保险公司(7 例)等,第三人主张过度医疗的动力在于,其为实际的医疗费用支付义务人,在这些案件中,第三人无一例外是向患方而非医方主张过度医疗侵权。由于缺乏立法者或学者对这一现象加以研究,第三人主张过度医疗侵权的案件缺乏统一裁判标准。
第二,过度医疗案件无法鉴定问题。肯定过度医疗存在的裁判很少,无法获得鉴定结论是主要原因。在111 个案件中,除1 例因发回重审未作明确表述外〔(2021)辽民申2192 号〕,否定过度医疗存在的高达99 例,肯定存在的仅有11 例,而无法鉴定的共74 例。医学的专业性与神秘性致使法官不敢轻易涉足,故通常会因无法鉴定而直接否定过度医疗,无法鉴定的原因有很多,直接原因包括患方拒绝鉴定〔(2021)京民申4789 号〕、患方干扰鉴定〔(2016)川民申2602 号〕、鉴定机构不予受理〔(2019)湘民申3198 号〕、第三人无权申请鉴定〔(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1672 号〕、该种疾患技术上无法鉴定〔(2019)辽民申56 号〕等,直接原因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如鉴定价格较为昂贵、鉴定机构的公信力不足、传统风俗不愿尸检等。过度医疗案件无法鉴定的问题盘根错节,在短期内恐难以解决。
二、过度医疗侵权基础理论的修整
由于第三人向患者主张过度医疗侵权案件的涌现,过度医疗侵权基础理论须加以修整。
1.过度医疗定义及侵权人的范围。笔者赞同杜治政教授的定义: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超过疾病实际需要的诊断和治疗的医疗行为或医疗过程[1]。过度医疗有“医因说”和“多因说”两种定义,之所以选择该“多因说”定义,是因为过度医疗的发生原因往往有多种,尤其是有患者的原因,如果只限定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所导致的……”则与现实不符。侵权人的范围,不应囿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还须囊括患者。从第三人的视角看,患者过度医疗的行为性质可能被理解为故意或过失扩大损失,但若把患者视作侵权人,可以认为,患者实施过度医疗行为侵犯第三人财产权。故而,过度医疗的受害人还应包括致患侵权人、用人者、保险公司等第三人。
2.过度医疗损害的范围。通说认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客观结果要件是造成患者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包括财产权的直接受损、人身损害、因人身损害引起的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害等[2],这些在案例样本中均有反映,但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第三人遭受的非因其人身或所有权等权利受侵害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即纯粹经济损失,过度医疗一旦发生,负有医疗费用支付义务的第三人就会因支付额度的实际增加而产生纯粹经济损失。
3.知情同意与违法性阻却。侵害患者身体的医疗行为得因同意而阻却违法[3],笔者认为,绝大部分医疗侵权中的知情同意可定性为“消极知情同意”,即“知情权利—说明义务—同意权利”的模式[4],医方基于患者的知情权履行说明义务,征得患者同意后始能阻却违法。在过度医疗侵权案件中,还存在一种“积极知情同意”,即患者主动要求过度医疗并获得医务人员同意。因此,在过度医疗侵权的违法性阻却问题上,有两种知情同意情形须分别讨论:对于消极的知情同意,医方充分履行说明义务,且不过度说明、夸大病情即可;对于“积极知情同意”,如果只涉及患者自身的财产权益减损或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承诺放弃的人身权益,则可阻却违法,但如果可能造成第三人权益减损等超出患者承诺权限的后果,且医方明知或应知的,即使充分对患者履行了说明义务,医方亦不能民事免责。
三、过度医疗侵害第三人权益的责任归属
当过度医疗侵害第三人权益时,患者与医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两者的责任应如何划定,值得探讨。
1.要求患者与医方担责的正当性。作为医疗服务需求方,当医疗费用的部分或全部比例无需自己承担时,患者的预算约束趋于软化而容易进行非理性医疗[5],在个案中,患者可能有故意让加害人付出代价的意图,或是试图以过度检查方式而为可能的诉讼搜集证据[6]。由于过度医疗侵权损害的发生可能有患者的过错因素,患者就其过错承担责任无可非议,这有利于遏制过度医疗。至于医务人员,其作为一类专家,需要在执业中尽高度注意义务,如此才能保护社会公众的合理信赖[7]。基于专家责任的特性,医务人员不仅应对患者负责,还应对一定范围内的第三人负责,虽然医务人员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但当其过度医疗行为造成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即产生侵权关系。
2.患者责任存在的判定标准。目前,尚缺乏医方对第三人承担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案例,但存在较多判断患者责任的裁判,其判定标准有待取舍。
第一,两种裁判标准的对立。参考表1,过度医疗患者责任的判定,实务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标准:“无必要性和合理性”标准与“恶意扩大损失”标准。前者是指若鉴定结论等客观证据表明,患者所接受的医疗行为或医疗过程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则不予支持患者对应的医疗费用。这种判定标准不考虑患者的主观过错,笔者推测,有可能是裁判者以客观不必要和不合理推定了主观过错,裁判思维或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的收款凭证、病历、诊断证明确定,赔偿义务人可以主张治疗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后者不仅要求医疗行为或医疗过程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需要患者有扩大损失的主观恶意,才能认定为过度医疗,这应是对侵权责任法一般过错侵权思维方式的继承。

表1 两种裁判标准的对立
第二,迈向“恶意扩大损失”标准。依据两标准裁判的社会效果有差别,“无必要性和合理性”标准更倾向于保护第三人权益,对患者配置了更高的注意义务——谨慎维持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正如Whitaker 诉Kruse 案(以下简称“Whitaker案”)法官所指出的,无必要性和合理性标准将置患者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能会被致患侵权人主张过度医疗;不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致患侵权人又可能主张患者未及时就医以控制损失(Whitaker v.Kruse,495 N.E.2d 223(Ind.Ct.App.1986))。进而,Whitaker 案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Whitaker 规则:患者可因致患侵权人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因医生的不当诊断和不必要的治疗导致的伤害加重得到赔偿,患者只需要证明在选择医生时秉持了合理的谨慎(reasonable care)(Sibbing v.Cave,901 N.E.2d 1155(2009))。诚然,患者因过度医疗而扩大损失的部分是致患侵权人和医方过错累积的可预见结果(Hillebrandt v.Holsum Bakeries,Inc.,267 So.2d 608(1972)),展开而言,如果第三人可以预见患者可能遭受需要接受治疗的损害,也应认识到治疗本身所涉及的过度医疗风险。
过错是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必要主观要件,在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构成过度医疗时,可以采用医疗必要性和合理性标准,因为该客观标准可以同时确定医方的主观过错[8],但不应搬用于患者过错的推定。因专业知识特别不均等、信息严重不对称,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弱势地位[9],患者通常只在选择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时有较为完全的自主权,选定之后就处于被动地位,当医方实施过度检查、治疗时,其没有足够能力识别、拒阻以保障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依据侵权法过错责任精神,结合Whitaker 规则,考虑我国存在患者选定医务人员后主动要求过度医疗的情况,笔者认为,如果患者未恶意扩大损失,即在选择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时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在选定医务人员后没有主动要求过度医疗,纵然其客观存在不必要和不合理的医疗费用,仍应因其没有过错而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3.侵害第三人权益责任归属的判断流程。如图1 所示,假设过度医疗的客观存在已被确定,若患者无恶意扩大损失行为,医方应由于过错行为而对第三人承担全部过度医疗侵权责任。那么,若患者恶意扩大损失,且医方对第三人不可预见,则由患者就损失扩大部分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医方明知或应知第三人存在,考虑是否构成医患共谋,若患者与医方由于存在某种利益一致性而形成“医患共谋”[10],则应就扩大损失部分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若不存在共谋,医方也应因对第三人有预见可能且患者超出承诺权限而不能免责,是与患者构成分别侵权,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或平均担责。

图1 过度医疗侵害第三人权益责任归属判断流程图
四、过度医疗非鉴定司法认定标准构建
当下,过度医疗侵权诉讼几乎完全依赖医疗鉴定,因而研究其法律理论不能脱离鉴定问题。唯鉴定的过度医疗诉讼,受害人胜诉率很低,鉴定程序启动难与诉讼成本增加阻碍了诉讼[11]。现有学说针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是鉴定制度本身的改进[12],实务中出现了少量非依据鉴定作出的过度医疗认定,可归纳、甄选后构建一种非鉴定司法认定标准。
1.不能完全依赖鉴定。笔者认为过度医疗的认定不能唯鉴定,除了阻碍诉讼的负面作用外,鉴定本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而非鉴定标准有一定适用范围。
第一,鉴定立足“医方标准”而忽视“患者标准”。如图2,由于立场的不同和知识、信息、经验的差别,医方和患者判断过度医疗自然有两套不同的标准,过度医疗鉴定包括医学会的鉴定和司法鉴定,均采取偏向于“医方标准”的专业标准。患者标准虽可能缺乏绝对的科学性但有时也有一定合理性,时常可以代表一般大众标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融入人民群众的常识、常情和常理,有助于实现精英智慧与群众智慧的结合[13],个案中,法官应思考患者标准是否合理并酌情采纳。

图2 过度医疗认定标准来源的设想
第二,医疗鉴定结论不是法律结论。“医”与“法”之间有一道鸿沟,正如法官不轻易刺破医学的神秘面纱,医疗鉴定一般也不会直接给予法律结论,如在(2016)新民申819 号案中,鉴定意见表述为:本案本质上属于过度医疗……神经损伤系治疗并发症之一……手术所致神经损伤如属于免责范畴,医疗过错与神经损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过错只是客观上增加了医疗成本。如不属于免责范畴,过错与神经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大小建议委托方从法律实务层面进行判断。并发症往往可以预见,其难以避免和防范但不是绝对不能,医护人员对其预见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是免责与否的考量因素[9]。笔者认为,不可预见或不可避免的治疗手段并发症本应作为免责事由,但过度医疗导致的并发症,即使不可预见或不可避免,也不应免责,因为过度医疗本身是可以预见且避免的。上述鉴定意见并没有直接给出法律上的结论,需要法官结合鉴定意见、依据法律知识才能得出结果。
第三,鉴定未必精确。鉴定本身未必能精确计算过度医疗的费用额度,据(2019)内民申3012号一案可知,确定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费用往往最终还是需要法官根据鉴定意见加以主观判断:鉴定意见认为上述费用不合理,但鉴定人明确表示,《鉴定意见书》中医疗费用合理性1-18 项,只是按照一般医学常规,判断该药物的使用或诊疗行为合不合理,但是具体诊疗行为因人而异,不能回答合理费用应是多少、不合理的费用应是多少。
第四,非鉴定认定具有正当性和一定适用范围。并非所有的过度医疗案件均需要鉴定,有些只涉及医疗法规范、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法官根据非鉴定标准即可以判定。对于需要鉴定的案件,即使当事人均配合鉴定,也可能因鉴定机构原因无法得到鉴定结果,对此法官不应拒绝审判,此时可根据非鉴定认定标准加以裁决。当案件获得了鉴定结果,亦不应完全依赖鉴定结果,法官应基于其专业保持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判断,可基于非鉴定认定标准对鉴定结论内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尽可能地审核,当鉴定结论内容是合法且合理的,法官亦通常需要参考非鉴定标准确定医疗合理费用和不合理费用的精确数额,得出最终的法律结论。
2.非鉴定认定标准探讨。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笔者初步归纳出以下非鉴定认定标准:
第一,根据医疗相关法规范。医疗行为的违法性判断须依照医疗相关法规范,包括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14],还应包括人身权侵权相关法规范等。如表2,实务中存在一些案件,法官纯粹依据医疗相关法规范,通过确定治疗终结的应然时刻,对比实际时刻判定是否构成过度医疗,划分合理费用与不合理费用。因此,在某些案件中,法官若仅依靠医疗相关法规范而不需要医学专业知识,即可排除合理怀疑、确定过度医疗存在与否以及过度医疗损害的金额,则应大胆适用。

表2 依据医疗相关法规范认定过度医疗案例表
第二,参考医疗行政部门的意见。在现实中,患者、第三人向卫生健康或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举报过度医疗,若获得行政部门的认定——如行政处罚文书,由于医疗行政部门的权威性和在医事法规与医学知识方面的专业性,患者、第三人应可以此认定作为诉讼证据。法院还可以主动咨询医疗行政部门的专业意见,由医疗行政部门按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卫生部门规章和相关检验操作规程、常规流程确立的诊疗规范,确认是否构成过度医疗〔(2017)吉民申665 号〕,实践中已出现了法院就是否存在过度检查咨询卫健部门,并以其专家讨论意见作为裁判参考的做法〔(2017)湘民申1849 号〕。
第三,依据生活经验、医学常识与公正理念。如表3,判断是否存在过度医疗事实,在有些案件中并不需要用到专业医学知识,或者只涉及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范围内的医学知识,因而出现了若干依据生活经验、医学常识与公正理念判定过度医疗的裁判。此处的“生活经验”标准要求法官依据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而不能偏听偏信当事人据其个体经验得出的结论,例如,有患者以自己和邻居病情相同花费更多为由主张医方过度医疗〔(2019)渝民申1691 号〕。

表3 依据生活经验、医学常识与公正理念认定过度医疗案例表
实践日新月异,理论需与时偕行。笔者针对过度医疗侵权法律理论进行了修整与补充两方面的工作。“修整”针对过度医疗侵权基础理论:支持了过度医疗“多因说”定义,拓宽了当事人范围,将第三人纯粹经济损失纳入损害范畴,并提出“积极知情同意”概念。至于“补充”,则包括:其一,探讨了过度医疗侵害第三人权益的责任归属,一言以蔽之,“恶意扩大损失”的患者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医方承担专家责任,两者的责任可能出现交错连带;其二,尝试构建过度医疗非鉴定司法认定标准,包含“根据医疗相关法规范”“参考医疗行政部门的认定”“依据生活经验、医学常识与公正理念”三种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