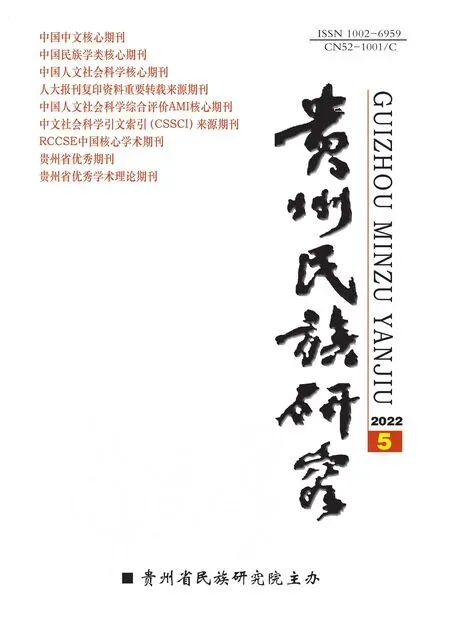跨文化传播中的解域化与再域化
——以成都武侯区民族街为例
2022-03-24昂翁绒波
邴 正 昂翁绒波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跨文化传播是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移民迁移往往引起跨文化传播现象。跨文化传播推动移民的城市化与文化适应进程,并在城市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空间。具体表现为移民的民族文化经历解域化与再域化过程,文化要素在城市中重组与更新,最终实现移民文化的创造与民族文化的转型。文章以成都武侯区民族街的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解域化与再域化理论来解释跨文化传播现象。
一、差异适应:跨文化传播与移民文化的形成
跨文化传播一词,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1959年首次提出[1]。起因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复苏,与之伴生的跨地域人口流动现象引发大众对文化差异的关注与讨论。因此,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跨文化传播也因而引发关注。不同文化群体成为研究对象,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重点也从表层差异转向更深层的文化原因。文化差异导致认同分野,跨文化传播进而介入其中。认同不仅成为不同类型的文化群体及其成员在社会中存续的主要原因,也成为与外界展开交往的重要依据[2]。
城市移民是对文化差异习以为常的群体,也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与边缘人。齐美尔认为陌生人是留在本地的外来人,会使熟人共同体面临新的关系挑战[3]。面对文化差异成为陌生人群体的生活日常,而更强调直面差异的“边缘人”理论随后出现。“边缘人”强调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新旧经历的冲突,同时生活在两种文化生活和传统之中[4]。身处文化交界处,边缘人具有跨文化理解的先天优势。在各地文化间游走的犹太人,最终成为全球文化的“混血儿”。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仍有其正向意义。边缘人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后,其跨文化传播与实践能力在事实层面得到提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结构向流动化、多元化、客观与公正的方向发展[5]。与此同时,边缘人身处跨文化的传播前沿,接触不同文化时也对自身文化产生反思与追问。因此,跨文化传播也是文化互动性与自反性并举的过程。
约翰·贝瑞强调文化适应是在不同群体间进行的双向参与过程,发生在多元族群之中[6]。金洋咏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理论,重点关注跨文化传播引起的群体内部变化。他认为跨文化传播遵循压力——适应——成长模式,指向个体内部状况与渐变过程[7]。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不得不自我调适以应对文化差异,文化因而实现内部变迁。因此,跨文化传播是包括文化适应与文化创造的复杂过程。个体拥有了“跨文化身份”,因而在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上更胜一筹。在此意义上,第三种文化作为跨文化适应的必然结果,成为其成功的重要标志[8]。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结果,第三种文化具有融合性特点。这一文化是出生地文化与东道主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其表现形式不受边界限制,是差异和融合共同驱动的结果[9]。因此,第三文化不仅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文化适应与创造的有力见证。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差异的存在,促使原有文化的适应与转型,最终都指向新文化的产生。
二、关系演变:蓉藏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变迁
汉藏交流由来已久,以文成公主入藏为标志,拉开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序幕。成都与藏区自古相邻,两地文化交流频繁。贡赐贸易的互补性经济催生了唐朝与吐蕃的“绢马互市”,促进了汉藏民族融合[10]。之后各朝发展茶马贸易,由于兼具“贡道”与“商道”身份,川藏道成为两地往来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藏族僧俗到访成都,并影响城市布局与发展。据《华阳县志》 记载:“县南十里明嘉靖中蜀王于此建坊,北人谓坊曰牌楼,当时藩府亦沿是称,故今犹呼红牌楼也”[11]。红牌楼距城十里,在此建坊有十里迎送过往成都的藏族僧俗之意。以红牌楼的建成为标志,成都成为汉藏民族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
清代成都商业发展,民族交流活动也更为密集,接待藏商与交易货物奉化馆的出现。从“大头人顶有蓝红,奉化馆前言语通。藏佛藏香兼氆氇,先来松茂道衙中”[12]的记载中可知,奉化馆已成为当时成都的藏族文化聚集地。官方朝贡与贸易活动之外,民间商贸也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燮的《锦城竹枝词》中也有“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饶钲响器回”[13]的描述。竹枝词所描绘的贸易场景虽然是片段式的,但也足以旁证藏区与成都两地跨文化传播的悠久历史。康雍两朝将康巴藏区大部分划归四川,行政上的统一管辖,客观上促进了这些藏区与省府成都的交流。清末更有“皇城南门外有巴塘人定居的地点,因此可以想象他们西藏人大概也会以此地为根据地”[14]的描述。巴塘人也是藏族人,这证明清末民初成都与藏区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已颇具规模。
民国时期,当时的政府在康藏地区设治直接推动商贸与人员往来,藏区与成都的跨文化传播进程得到更进一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解放与川藏公路通车进一步推动两地交流进程。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来大量藏族移民在成都发展,这一群体因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力。几十年来,成都武侯区民族街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内地规模最大的藏族社区与藏族文化产品集散地。此地在行政上归属成都,文化上却与千里之外的藏区联系密切。在此生活的藏族移民抓住政策与时代机遇,积极发展民族产业,拓展汉藏文化交流路径,将跨文化传播进程推向新的高度。
三、解域化:成都藏族移民的文化分化过程
文化是移民的身份印记,移民通过文化获取资源。即使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依然是移民精神层面的依凭。只有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移民才能实现在新土重建基业的目标[15]。在此过程中,文化分化成为必然,移民群体的原有文化因远离故土而改变。惯常的社会关系、例循的文化规律、实践的文化仪式都因为迁离固定文化环境而被移民重新审视与选择,移民文化也因而进入解辖域化进程。辖域是指界限明确的区域,如动物的活动领域,若有人进入域内,就会发出低吼[16]。辖域意味着固定的边界,内部同质性较高。解辖域化也称作解域化,出自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而后由德勒兹和瓜塔里拓展概念。在他们看来,解辖域化是对原有情境的脱离,是超越边界的动态过程[17]。宋怡明进而利用此概念来分析明代军户的迁移生活,着重强调其中的“脱离”特点。士兵的征调历程意味着原有社会环境的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被割裂,士兵因而面临被“解域化”的处境[18]。沿袭宋怡明的思路,成都藏族移民迁离藏地也是解域化的过程,基于地域空间展开的日常生活在迁移中改变,文化分化成为必然结果。
首先,分化表现为文化符号的抽离,由此引发习俗解域化进程。因为符号植根于社会文化环境,标示文化特色。因此,符号的抽离会导致部分文化特色的流失。藏族人打酥油茶与煨桑祈福等习俗仪式都是民族特点的体现,相较于图像文字等方便移植的抽象文化符号,这些依赖现实物质因素的传统习俗对空间等物质因素要求较高,而难以被复制与移植到城市生活中。因此,迁往城市也意味着部分传统习俗的消逝。传统藏族文化符号被分割与重组,复制性与移植性成为在新环境中选择与应用文化符号的新标准,习俗解域也因而成为文化解域的先声。其次,解域化也是移民文化认同的解域。作为地域性与社会性交织的日常生活实践结果,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与内在逻辑,是现实生活的投射。解域化表现为人类与象征形式的分解,文化结构、关系、场景和表征在此过程中部分离散[19]。迁移导致原有生活场景的改变,文化象征、关系与认同也因而改变。一方面,文化认同在藏族移民内部产生分化,在代际间表现明显;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差异导致藏族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较为曲折。对成都藏族移民而言,城市生活的逻辑、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挑战移民的文化认同,面对差异成为移民的生活日常。最后,解域化也表现为语言与文字的解域。藏族移民移居成都后,城市生活的丰富性促使藏族移民的文化选择更加多元化。文化环境的改变使得藏族移民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意愿与必要性降低,作为文化要素的语言与文字在成都藏族移民群体中开始分化与改变。
解域化是移民群体内部习俗、认同等要素解域的复杂过程。解域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也是多重性的。一方面,解域化导致文化分化,传统藏族文化部分变迁;另一方面,解域化有助于对藏族文化的清理与重建,这也是文化适应的前提。现代城市影响藏族移民的日常生活,促使移民从传统文化中抽离与移植适应城市生活的文化符号,并将其改造为移民群体的特色文化。因此,文化解域化是文化清理的过程,为移民的文化再域化奠定了基础,也为移民文化的发展塑造新的可能。
四、再域化:成都移民的文化整合过程
藏族移民在文化解域化后,在民族街的文化实践中糅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特色并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这就是文化再域化进程。再辖域化表现为经历解域化过程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组合并进入一类新关系中[20]。成都藏族移民的文化再域化进程也是如此,原有文化要素在城市中被拆分重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都被融合其中,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与生活模式。
首先,文化自觉是文化再域化的驱动内因,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民族是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民族意识与认同只有在与‘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后才能产生,这是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21]。在市场化驱动下,民族街内随处可见的藏族文化符号营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民族产业形塑出内外有别的文化边界,商品符号影响下的文化认同得以强化。当移民聚居区的民族文化发挥自身的优势时,也为新移民在陌生世界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动力,使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存于大社会之中[22]。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中,藏族移民依靠民族街的产业优势聚拢与发展文化资源,进而展现与塑造民族文化特色。对藏族移民而言,这是文化身份确立与重构的过程,文化自觉得以形成。其次,市场是文化再域化的外在动力。成都藏族移民面对文化差异时,以模仿传统文化作为应对方式。被解域化的人们为了达到心灵的平静和舒缓状态,需要借助源自故乡或带有故乡风格的大众文化产品,以及能够代表故乡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地方材料[23]。成都的民族街是藏族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方,民族文化成为市场商品并在市场流通过程中产生文化效应。这些藏族文化产品脱胎于传统,并被改造以适应城市环境。因此,市场既推动移民适应城市生活,也助力藏族文化的适应性发展。最后,科技是文化再域化的重要媒介。网络平台成为文化交流通道,抖音、快手等网络媒介是符号传递与文化价值再定义的重要工具,常见的雪山、牦牛等成为文化符号,在网络中被重新定义与传播。原有的文化含义被改写并服务于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全新诠释需求,市场反应也成为影响文化定义与传播的重要元素。传统与现代文化借助技术得以融合成新的文化并成为互联网中的景观,跨越原有的时空界限并持续产生影响。
文化再域化进程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与移植,而是藏族移民文化融合与身份重塑的过程。市场推动藏族文化符号的重构与传播,移民群体的文化形式发生改变,他们的文化特点更加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也得以被重新审视与发掘。藏族移民聚居的民族街不仅是移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挥着维系与支持群体认同与社会文化的作用。藏族移民在城市中寻找认同,积累群体所需的物质文化资源,进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出新的文化与身份。因此,文化再域化的目的是多重性的,既为了藏族移民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也着眼于民族文化的保存,还致力于跨文化传播中个人与族群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既是文化再域化的发展要求,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
五、结语: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化融合发展
文化解域化是成都移民文化的形成前提,也是跨文化传播造成的分化结果。一方面,文化解域化清理了部分文化及其符号,文化变化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文化解域化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藏族文化中适应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并成为藏族移民依凭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承性与包容性强,是文化存续的重要基础。因此,文化解域化也是文化自我更新与发展的前提过程。文化再域化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受到文化与市场力量的形塑作用。文化再域化是藏族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加速融合并得到发展机会,多元文化环境最终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