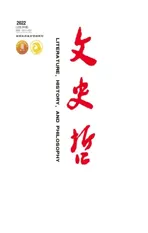《左传》“荆尸”考
2022-03-24黄杰
黄 杰
《左传》中有两例“荆尸”,见于庄公四年“四年春,王三(或作“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与宣公十二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杜预解释为楚陈兵之法,传统注家多从之。

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持异议。几位学者重申杜预注,更多学者则提出了新的看法。张君提出“荆尸”曾为楚国神主说。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引述了于豪亮的说法,但没有采纳,并说:“疑此‘荆尸’当作动词,指军事。”1996年出版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认为“荆尸”为楚国行军之祭,“尸”即木主。李学勤认为这两个“荆尸”应是组织兵员的一种方式。刘刚认为是指一种祭祀,具体是军事活动前由楚王作为主祭者的祭礼。刘信芳、王箐认为“荆尸”乃楚国尸祭。黄圣松认为“荆”读为“刑”,“荆尸”意为使陈列之兵阵符合规范,意同治兵。
由上述可见,自相关的出土文献面世之后,《左传》“荆尸”的内涵成为楚国乃至先秦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四十多年中,超过十位学者对此发表了多种意见,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待继续探讨。
笔者曾长期关注并撰有文稿讨论这一问题,但未曾发表。这里在旧作基础上,系统梳理前人意见,对这两例“荆尸”的意思再做考察,希望对厘清这一公案有所帮助。
一、原始材料及简要说明
《左传》庄公四年: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王三月”,或作“王正月”,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及《四部备要》本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王红亮梳理了有代表性的包含庄公四年传文的历代《左传》版本,指出从六朝、宋、元、明直至清乾隆年间,各本皆作“王三月”,到嘉庆年间才出现作“王正月”的版本,认为应以“王三月”为是。此从之。
宣公十二年《传》主要记载了楚人伐郑、克郑及晋楚邲之战的经过。“荆尸”见于邲之战前晋国上军主帅士会(随武子)所说的一段话中,相关《传》文如下:
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
二、前人的解释及相关的讨论、辩难
目前为止,学者们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如下六种:
第一种,解为楚陈兵之法。庄公四年《左传》杜预注:“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扬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则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宣公十二年《传》杜预注与此近似。洪亮吉、刘文淇、竹添光鸿、吴闿生、徐中舒、李宗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陈恩林、王红亮同。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与杜预之说有差别,但或多或少都有关联,附录于此。丘光庭《兼明书》认为“荆尸”是说“举其先代之军法”。胡抡《礼乐通考》云:“楚人阅兵曰荆尸。”俞樾认为,“荆”既是楚之旧号,“荆尸”亦必是楚之旧法。楚武王此年伐随仍用荆之旧法以治其行阵,故曰楚武王荆尸。章太炎将“荆尸”解为荆山之陈法,具体而言是用荆山弧父之法以立陈,《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习用弓矢……”,从文法上看,“楚武王荆尸”犹“赵武灵王胡服”。李宗侗将宣公十二年的“荆尸”解为楚王所做的政法。

需要附带提及的是,持此说的学者们对《左传》原文的断句存在差异。曾宪通、于豪亮将“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读为一句。有学者将“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读为一句。有学者将“楚武王荆尸”读为一句。
第三种,解为楚祖之神象。对于庄公四年之“荆尸”,张君从“尸”字的本义入手,根据段玉裁“凡祭祀之尸训主”“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而祭者因主之,二义实相因而生也”的意见,认为“尸”早先均以活人装扮,后来才改用木主,因此认为“荆尸”即楚祖之神象,“楚武王荆尸”是说楚武王亲扮此神象。有个别学者赞同张先生的说法。
第四种,认为是组织兵员的一种方式。李学勤从宣公十二年的传文出发,说:“品味‘荆尸而举’数句,‘荆尸’也不像是月名,而应是组织兵员的一种方式。正因行用‘荆尸’,才做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庄公四年传杜注释‘荆尸’为陈兵之法还是不中不远的。”
第五种,解为祭祀。《楚国历史文化辞典》认为“荆尸”为楚国行军之祭,具体祭仪不详。该书在引述杜预看法之后说,“荆尸”应为兵祭,“将齐”之“齐”同“斋”,指祭祀斋戒;“尸”即木主。2010年12月公布的清华简《楚居》简4-5有这样一段话:


第六种,使陈列之兵阵符合规范。黄圣松认为“荆”可读为“刑”,作动词,使对象符合规范、令其端正之意。尸释为敶,陈列之兵阵。荆尸意为使陈列之兵阵符合规范、遵守法度,意同《春秋》经传与《国语》之治兵。
第六种说法是刚刚发表的,尚无其他学者回应。对于上述前五种说法,学者们各有一些辩难。
对于第一种解释,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俞樾指出,如果是楚武王始为此法,则当写作“楚武王作荆尸”,不能仅说“楚武王荆尸”,而且此时邻国称之皆曰“楚”,楚人自称亦曰“楚”,则武王创此陈兵之法,何不说“楚尸”而说“荆尸”?张君认为,按杜注孔疏作“陈兵之法”解,于理不通。“楚武王荆尸”出现在“授师孑”之前。授孑(授兵)的对象不可能是全部征战之士、只能是少数战争骨干,且授孑及其前进行的仪式目的在于求神赐福和进行战争动员,此时言陈兵布阵太早了一点。如果强言“荆尸”为“陈兵之法”,则《传》文语序应该改成“楚武王授师孑焉,荆尸以伐随”方能说通。汤志彪、芮赵凯认为,将“荆尸”理解为军阵、阵法,在庄公四年里可以理解成名词活用为动词,而在宣公十二年中不合适,演练“军阵”可以做到“卒乘辑睦”,但与“商农工贾”无涉。这两场战争中,《左传》均未见楚国使用特别的阵法和军事组织方式的记载。

对于第三种解释,黄圣松认为,张先生未解释何以商农工贾参与荆尸而能不败其业,且他说尸由楚君或莫敖担任,无文献证据。
对于第四种解释,汤志彪、芮赵凯认为,将“荆尸”理解为一种组织兵员的方式,用在庄公四年文中尚说得通,但不能通读宣公十二年文意。组织和动员全国兵员可以做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却不能做到“卒乘辑睦”。若将“荆尸”理解为组织兵员,继而把“举”理解为“举兵”即“军力的动员”,那么“荆尸而举”就只能理解为“组织兵员而军力动员”,语义重复,且行文拖沓。
对于第五种解释,汤志彪、芮赵凯认为,宣公十二年随武子所说的那一段话中,德、刑、政、事、典、礼与下文是一一对应的。按照古代对“礼”的定义,祭祀是一种“礼”,随武子却将“荆尸而举”论述为“事”而不是放在“礼顺”的范畴中,可见此处“荆尸”不能理解为“祭祀”。从逻辑上说,“荆尸”也不能解释为兵祭。因为兵祭只与战争胜负有直接关系,而与“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不存在必然联系。古代在大规模军事活动之前常举行祭礼,但并不是说举行兵祭就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将“荆尸”理解为祭祀,那么庄公四年楚武王斋戒祭祀,结果却死于途中,这是“荆尸”“祭祀说”最好的反证。黄圣松认为,刘刚之说用来解释庄公四年《传》颇合情理,但放入宣公十二年《传》,何以商农工贾参与荆尸之祭祀而能不败其业,刘氏未予解释。言下之意,此说不能很好地解释宣公十二年《传》。
三、前人意见的辨析
上文所列的几种解释及学者们的辩难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先来看六种解释。结合前人的辨析来看,杜预提出的第一种解释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1)如俞樾所指出的,如果要表示“楚武王始更为此陈法”(宣公十二年《传》注)之义,则应当说“楚武王作荆尸”,而不能仅仅说“楚武王荆尸”。即便像汤、芮那样认为庄公四年“荆尸”名词活用为动词,那么,以杜预的解释为基础,“楚武王荆尸”的意思也应当理解为“楚武王按照楚地的方式陈兵/列阵”,而不是“楚武王始更为此陈法”。杜预在将“荆尸”训释为“楚陈兵之法”后,人为加上了谓语动词“为”,犯了增字作解的毛病。(2)按照杜预之说,宣公十二年“荆尸而举”与后文“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没有逻辑联系。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楚陈”能导致“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第二种解释存在几方面的问题:(1)如张君所指出的,庄公四年《传》文已经标明季节与月份,无须赘列楚的代月名。《左传》中还有多处某年某月楚国国君做某事的记载,都未另外标明楚之月名。(2)如李学勤所指出的,庄公四年的实际历时是建丑,“王三月”实为卯月,与“荆尸”为寅月矛盾。(3)如王红亮所指出的,曾、于二先生分别依据“王三月”“王正月”两种版本得出了“荆尸”是楚月名的相同结论,存在漏洞。在这几方面的问题中,(3)可以通过采用曾先生在《楚月名初探》一文中的论述(其论述是以“王三月”的版本为据,较详细)的方式得到解决。尽管如此,(1)(2)仍然是无法回避和解决的问题。此外,如果不采用曾、于的断句,而是将“楚武王荆尸”读为一句,那么还会面临陈恩林所说的王公名号加上月名不合文献通例的问题。
第三种解释的问题留待下文再谈。第四种解释即“组织兵员的一种方式”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的界定,或者说解释的方向,并非对“荆尸”含义的明确解释。

同时,持这种解释的学者们的意见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楚国历史文化辞典》认为“尸”即木主,不可信;第二,如汤志彪、芮赵凯和黄圣松所指出的,将宣公十二年“荆尸”解为祭祀,“荆尸而举”与“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难以讲清楚;第三,刘刚引《尔雅·释天》“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而后出,谓之宜”来与宣公十二年“荆尸而举……事不奸矣”相参照,却没有注意到宣公十二年传文本身就包含说明这个“荆尸”的含义的关键证据,《左传》中别处也还有比《尔雅》此文更直接的旁证;第四,清华简《系年》“成王屎伐商邑”之“屎”读为“尸”不符合古文字的用字习惯,不可信,“成王屎伐商邑”应读为一句,与“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没有关联。
第六种解释的问题是:将“荆”读为“刑”、解为使……符合规范,比较牵强。古书中“刑”可通“型”,表示“为……之典范”,这个意思离“使对象符合规范、令其端正”还有距离;更关键的是,将“尸”解为兵阵、阵列,不能成立。《左传》中表示阵列,一般用“陈”“行”,未见用“尸”者。总体而言,从表达的角度看,古人若要表示“使兵阵符合规范”之义,是不会说“刑尸”的。

再来看学者们对前五种解释的反驳意见。其中合理的、可资借鉴的部分,上文在指出各种解释的问题时已经基本上吸取了,这里对这些反驳意见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做一些辨析。
陈恩林用先秦文献没有用王公之谥号记月(按:即王公谥号加上月名)的例子来反驳曾、于之说,似未切中肯綮。曾、于二先生是将“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读作一句的,按他们的理解,此句的主干是“楚武王授师孑”,“荆尸”是时间状语,并不与“楚武王”搭配组成实质性的结构。因此,曾、于之说并不存在陈先生所说的用王公之谥号记月的问题。陈先生的这个反驳,只适用于将“楚武王荆尸”读作一句,且认为“荆尸”是月名的学者。另外,说楚武王是谥号,也不确切。
李学勤、黄圣松认为,将宣公十二年“荆尸”解为月名,与《传》文的时间过程会有矛盾。这一点其实不能成立。我们在下文再专门讨论这一点。
王红亮在反驳曾、于之说时提出的意见,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他说如果将宣公十二年“荆尸”作月名理解,就成了晋国人说楚地方言,于情理不通。这个意见似是而非,理由有两点:首先,上引宣公十二年传文不一定是实录。我们不否认历史上在邲之战前,晋大夫士会可能对战局发表过言论,但这些言论被一一记载下来并照录到《左传》里的可能性很小。上引传文更可能是出于《左传》作者的创作。其次,即便这些内容是实录,也不适合用“晋国人说楚地方言,于情理不通”加以否定。当时晋楚争霸,双方的卿大夫对对方国家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楚月名作为楚地流行的一套特别的记月系统,是楚地特色制度中很显眼的一部分,晋国大夫知晓、提及,不足为奇,这与“说楚地方言”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他说出土材料中的“荆尸”与《左传》中的“荆尸”有两点差别,在笔者看来,这些差别恐怕更多的是相互补充,而非矛盾冲突的关系。第三,他说《左传》中的“荆尸”毫无明显的指代时间的迹象,不符合事实,下文将会详细论述这一点。
汤志彪、芮赵凯对第四、五种解释的反驳有几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只说最主要的问题,即:他们说,“古代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活动之前常举行祭礼,即所谓的‘兵祭’,但并不是说举行‘兵祭’就一定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将‘荆尸”理解为‘祭祀’,那么庄公四年楚武王斋戒祭祀,结果却死于途中,这是‘荆尸’‘祭祀说’最好的反证”,这段话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就像他们已经指出的,并不是说举行祭祀就一定能获得战争胜利等好的结果;庄公四年《传》中最终出现楚武王死去的不好结果,不能反过来说明该处的“荆尸”不能解释为祭祀。
四、本文的解释
先看庄公四年的“荆尸”。既然将“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读为一句、将“荆尸”解为时间状语不可信,我们还是要回到“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的断句上来。杨伯峻说“荆尸”是动词,是可信的。李学勤也认可这一判断。考察这个“荆尸”的内涵,应当以此为前提。

按‘孑’,杜预引扬雄《方言》释为“戟”。据此,则“授师孑”亦即“授师兵”。西周春秋时因兵甲等军实皆出于官,故各国临战前皆有“授兵甲之仪”,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杜注:“大宫,郑祖庙,大音泰。”又按,“齐”通“斋”,“将齐”即“将斋”。古礼,出兵前必先祭祖,祭前必先斋。……“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是总括之辞,以下为细述之语。武王伐随将先祭祖庙,于祖庙发布征战令并接着举行授兵之仪,为行此仪,武王须“斋”……

至于宣公十二年的“荆尸”,我们认为,解作月名是正确的。传文本身就包含了表明这个“荆尸”是时间状语的关键证据,曾宪通早已指出:
下文随武子称此次行动为“事时”,理由是“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张君引述了曾先生的上述意见,并且补充了一条重要的材料:
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春”,楚子反求成于郑,构成与晋交兵的态势,子反过申“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五月,晋师济河……”。杜注:“奸时,礼不顺时,周四月,今二月,妨农业”。也可证明若非王三月、楚正月而举兵,便被楚人视为“奸时”。
这些论述已经点出了最关键的直接证据和间接材料。仔细领会,其实不难得出正确答案。不过,许多学者忽略了这些论述。
本文开头所引的宣公十二年《传》文非常规整。“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是总括之语,其后的文字分别对“德、刑”“政”“事”“典”“礼”进行论述,最后以“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作结。其中,“事时”与“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对应。参照“(德、刑)二者立矣”与“德立”“礼不逆”与“礼顺”的关系来看,“事时”很可能是“事不奸矣”的另一种表达。因此,“事不奸矣”应当就是“事不奸时矣”。
这一点可以从张先生提到的《左传》成公十六年的一段文字中得到佐证:
(四月)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
申叔时对子反所说的内容与宣公十二年《传》中随武子的话非常相似,关系也甚为密切。其中屡次提到“时”,“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和宣公十二年《传》“民不罢劳”“事不奸矣”对应。这可以佐证“事不奸矣”当理解为“事不奸时矣”,即举事不违背时令,“事时”是说做事符合时令(时间合适)。
确定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到“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这个长复句中,“事不奸矣”是对“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总结。“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与“卒乘辑睦”是并列关系,中间用“而”连接。“荆尸而举”与“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之间是因果关系,正因为有“荆尸而举”的行为,才有“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结果,李学勤已经指出这一点。
由此可知,“事不奸矣”“事时”表面上看是对“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总结,实际上真正的落脚点在于“荆尸而举”。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荆尸”应当视作时间状语,解作楚月名。
古代时令观念非常浓厚,从先秦到汉代,以《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管子》的《幼官》《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的《天文》与《时则》等篇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明确地说明了什么季节该做什么事,其中大多涉及国家的行为。战争为国之大事,不只关涉农事,也关涉工、商各行。春秋时战事,以“士”为主力,庶人、工、商及皂、隶、牧、圉亦从军役。举兵若不选择合适的时候,则农、工、商业都会受到影响,尤以农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传》文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其内在逻辑是:荆尸之月(夏历正月)举兵,不误农时,对工、商之业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军队中服役的农、工、商各色人等皆无他顾之忧虑,都同心协力服军役。
李学勤、黄圣松等都曾提出,将“荆尸”解为楚月名,与宣公十二年《传》文的时间过程会有矛盾,所以,这里有必要对该年《传》的时间历程再做考察,以检验究竟是否存在矛盾。
《经》《传》所载楚伐郑、克郑及晋楚邲之战的时间梗概如下:
《传》:“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
“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
《经》:“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经文有误,乙卯实为七月十三日。
《经》《传》径以“楚子围郑”开始,李学勤指出,“荆尸而举”的“举”指举兵,楚军动员启程,以至开始围郑,需要一段时间。其言有理。上述时间梗概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楚举兵-a-开始围郑-b-退兵-c-复围郑-d-克郑-e-邲之战,其中a、b、c等字母表示前后两项之间的时间间隔,已知b约为17日,d约为90天。需要指出的是,a不一定很长,因为楚人很有可能从申、息发兵,春秋时楚国常用申、息之师经营中原。申一般认为在今南阳,有学者认为在今信阳,这两个地方及息(今河南息县)距郑都(今新郑)均在300公里以内,而且地势平坦。若楚从申、息发兵,10日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郑国都,亦即a可以是10日甚至更少。c未知,从《传》文看,似乎不会很长。楚退兵后郑人必定立即修城,而楚人此次为降服郑国而来,立意攻克之,不会给其很多缓冲时间,c短至两三天都是有可能的。克郑的具体时间,《传》文没有交代,孔《疏》认为在六月。由于邲之战在七月十三日,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克郑在六月底。假设楚人举兵在“荆尸”月(周历三月)初,从三月初到六月底,约为120日,即a+b+c+d=120日。若c取3日,则a=10日。根据上文的讨论,这个时间表可以成立。可见,将“荆尸”理解为月名,与《传》文所记的时间过程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学者们认为时间过程上存在矛盾,主要是因为忽略了楚从申、息发兵的可能性。
五、小 结


对《左传》“荆尸”内涵的探讨,是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几批出土文献在“荆尸”的解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问题的探讨过程却比较复杂,讨论历时长,参与的学者多,意见很纷繁,后人对前人意见的辩难也较为充分,其中真知灼见与疏误并存。纵观讨论的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第二,这一公案的探讨过程比较曲折复杂,其中的症结在于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前提靠不住,导致研究思路发生了偏差。回过头去看,对这两个“荆尸”,各自都有学者提出了可信的解释,但并未在同一位学者那里得到统一,这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默认这两个“荆尸”是同一个意思。对于他们来说,这大概是一个不言自明、无须讨论的前提,但由本文的分析可知,这一前提不能成立。前提出了问题,就难免在强求一致时顾此失彼,无法周全。所做的论证工作,有时反而削弱了其观点的可信度。如果不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左传》“荆尸”恐怕无法获得正确的解释。这再次提醒我们,做研究要谨防先入为主的成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讨论存在前提,对其可靠性应当进行审慎核查。
第三,这一案例还暴露出相关研究中存在搜集材料不全面、对前人工作理解继承不够等问题,充分说明了利用出土材料解读传世文献的复杂性,可为以后的同类研究提供鉴戒。
在对《左传》“荆尸”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未注意到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的异文,有的学者忽视了上下文所提供的关键证据(如宣公十二年《传》“事时”),至于有关的间接材料(如与宣公十二年《传》文关系密切的成公十六年《传》文),则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提及。考虑到曾宪通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里已经明确以“事时”作为证据、张君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里已经明确提及成公十六年《传》文“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出现这些问题,就令人费解了。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轻视了利用出土材料解读传世文献的复杂性,以为有了新材料就能轻易解决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新材料上,未能多方搜集材料,从多个角度求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有的学者对前人的研究重视不够,没有仔细研读、充分理解,这导致问题的讨论不仅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反而重新跌回低点,从头开始。在以后的研究中,这都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利用出土材料解读传世文献,并不只是用某个语词在出土文献的用法来解释它在传世文献中的用例那样简单。这种研究和其他的文献学研究一样,都是综合性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细致分析,多方搜集可资利用的材料,包括研究对象本身的异文、上下文等直接材料及有关联的间接材料,综合运用校勘、训诂、分析句子结构和语法、梳理行文脉络、对比相似文例等方法,多方论证,并从是否符合古人表达习惯的角度加以验证,方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附记:本文初稿写于2011年5月,后历经多次修改,2021年12月改定。承蒙李天虹师及陈伟、陈晨等先生指正,审稿专家提供卓见,谨致谢忱!文中疏误,由作者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