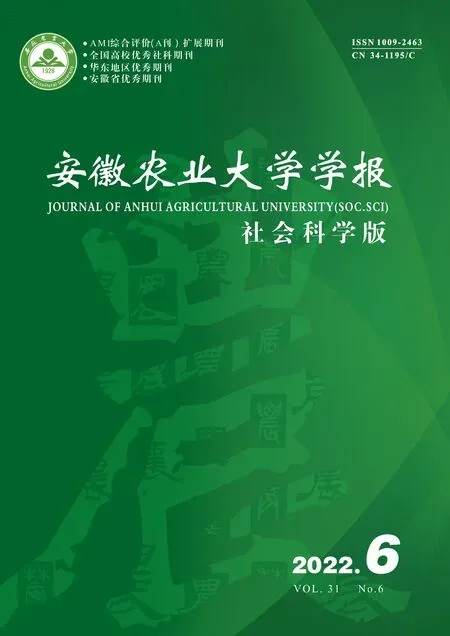从“以名取士”到“莫取有名”:论汉末魏初士人“名声”的浮沉*
2022-03-23杨霞
杨 霞
(安徽开放大学 文法与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古人向来重“名”,士人尤甚。“名, 自命也。”[1]41“名, 明也, 名实使分明也。”[2]54“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3]776从字源学角度看,“名”是通过语言形式标记和显示事物的存在规定,可彰显事物的性质和意义;从社会学角度看,“名”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是一种倾向性表达和意义指认。也因此,“名”有多重内涵,如姓名、名义、名誉、名声、名望等①,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名”更多侧重于“名声”这一概念。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名声只是一种次要之物,它只不过是成绩贡献的映像、表征、回音,并且,能够获取赞叹之物比赞叹更有价值。”[4]104可见,名声是他人或社会对某一个体或家族包括能力、素养、学识等内在价值的外部评价,且内在价值更具意义。
在古代中国,“名”是统治者取人、用人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早在春秋末期,名家学者邓析就提出了“君有三累”而“以名取士”[5]108便是其一的观点,可见,其时“以名取士”现象已经多有发生甚至成为君主的主要牵累之一。后代取士又有不同标准,秦代多以军功取士,西汉重视血缘权力家族,而“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6]827。至东汉后期,士人的名声复又成为朝廷察举人才的重要尺度,“以名取士”之风愈演愈烈。曹魏时期,统治者不再倚重士人的名声,明帝曹叡甚至下诏要求“选举莫取有名”[7]651。那么,这一时段,从“以名取士”到“莫取有名”,其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士人“名声”的浮沉?这种变化其实质又是什么?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态度的变化又会引发制度层面的何种变迁?学界对此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本文着意于此,重点对汉末魏初名士②的遭际、士人“名声”的浮沉及其成因、影响展开分析。
一、汉末“以名取士”风气的高涨
如上文所言,名声是士人能力、学识、素养等内在价值的外部评价。统治者依据名声而选用士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这些价值的重视与认可。先秦时期已有楚威王听闻庄子贤名,而“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8]2145,西汉初期贾谊“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太守“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9]2221。东汉前期有不少士人因过人的勇气、才华、学识等而为朝廷、州郡所征辟。例如,光武帝时期,陈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10]1233;章帝时期,虞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10]1152,高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10]2769;安帝时期,张衡因“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10]1897,马融也因为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10]1953。思想家王充曾分析奸佞毁谤贤士现象,言道:“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声显闻,(佞人)将恐人君召问,扶而胜己,欲故废不言,常腾誉之。荐之者众,将议欲用……”[11]525这一段话明确传达出一则信息:在王充生活的东汉前中期,“名声显闻”之士已经很容易得到“人君召问”,且“荐之者众”,更有如司空张纯“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10]1195这般依据名声选拔人才更是三公、郡守的常规操作。
到东汉后期,选士以“名”之风气愈加炽热,声名昭著者更是得到多方青睐。如韩融“少能辨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10]2063;姜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10]1749。不仅如此,东汉后期更是出现了诸多以怪异行为获取名声并因此为朝廷所用者: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以“炫”与“藏”的对立、矛盾行为引得士林和朝廷的关注,果然,“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10]2232;向栩“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其名显于外,而“公府辟,皆不到”,“后特征,到,拜赵相”[10]2693-2694;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远超过东汉服丧三年的通行做法,使得“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10]2159-2160。
由此可以想见“名声”在汉末政治领域的重要影响力,“以名取士”现象在这一时期之普遍存在。后世评价其时选才制度,言“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12]104。而到汉末,此风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为学者阎步克笔下汉末选官危机中的一种,“已成为影响选官的诸多重要因素之一”[13]76。
应该说,“以名取士”是自古即有的选士方式,但是汉末“以名取士”风气弥漫,士人奔竞逐名,唯名声为要务,则是内在、外在、长期、即时各种因素推动的结果。概言之,拥有良好“名声”的士人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和引领功能可为统治者所用,故而使“以名取士”成为可能;西汉武帝开始推行的重举荐而举荐多以名声为参考的察举制度为“以名取士”提供制度依据;东汉“尚名节”之风为汉末“以名取士”风气的高涨奠定舆论基础。而真正促使汉末“以名取士”风气达到高潮的则是以下两点原因所致。
一是浮华交结之风弥漫引发名声传播速度加快,导致名士盛行。这为汉末“以名取士”的过度膨胀提供了“名士”的基础。
历史上的东汉是士人游学、游宦异常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游学士人数量不断增长,以致“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10]1714,游宦群体也日益庞大,和、安之后更是出现了世务游宦的局面。与此同时,官僚机构能提供的职位数量有限,有一部分还向权贵子弟倾斜。普通士子仕进本就道阻且艰,而汉末朝廷卖官鬻爵盛行,戚宦政治下更是出现了“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10]1657的局面,这使得士人仕进愈发艰难。
仕途堵塞、前途暗淡之际,士人不再困守经学,相反形成了“英雄四集,志士交结”[10]2481的局面,并逐渐演变为浮华交结之风。“所谓浮华,非指生活上之浮华奢靡,而是从政治着眼,以才能互相标榜,结为朋党。”[14]35名声虽是内在价值的体现,但其最终实现,则需他人的认可和口耳相传。史书记载:“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10]2234许劭曾“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7]658。郭泰亦曾奖拔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等士人,又曾“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等六十人,并以成名”[10]2231。而这些成名者其后大多为朝廷或州郡所用。可见,士人的交结、“游谈其中”[10]2481无疑加速了士人名声的传播。浮华风气之下,清流名士涌现,同时也催生了大量好名成癖的士人。
二是士林抗击恶政而形成的婞直之风从外部给予统治者“取”士以“名”的压力。
士人大规模的求学、仕进活动对东汉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引发了资源和权力分配危机,卷起了汉末政坛的风云。从东汉士人行迹来看,大批士人游走于京城、郡国之间,先有师生、生生之学术情谊的天然维系,后又有彼此交结的有心为之,士人群落化、集团化在所难免。而当其满怀政治热情却又迟迟不得进入帝王之门时,其对体制内部的政治权贵的期待终究落空,自然很容易转向,而成为与之对抗的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这种政治势力更因时局动荡而加速形成。史书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0]2185而所谓“婞直”,刚强也、倔强也,它反映了士人驱除戚宦、政归士人的政治诉求与坚强意志。而“激扬名声”正是士人这一群体干涉朝政、掣肘戚宦腐败用人的重要方式,“以名取士”即是这一群体抗击恶政的产物。不仅如此,当“正直废放,邪枉炽结”之时,“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分别有“一世之所宗”“人之英”“以德行引人”“导人追宗”“以财救人”[10]2187的地位或能力——更是将名士的名声进一步张扬,以扩大其在士林中的影响,并波及至朝堂之上。这些“名士口中的褒贬,传达到政府时,可以在选举上起决定性的作用”[15]86。同时,这种名声已不是个体日积月累、经乡举里选而为众人所知的传统“名声”,也非来自“王朝的赐予”,“而是在士人群体的舆论评价中形成的”[13]76。正是在名士群体的强力推动之下,“以名取士”靡然成风,如陈蕃为太傅之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秉政,就致力“引用天下名士”以“连谋诛诸宦官”[10]2196。
由上可见,汉末“以名取士”之风的高涨既承袭了前代遗风,同时更是汉末这一复杂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它是士人欲有为政治而为现实所阻后的抗争与努力,是士人群体对抗恶政、激扬名声、干涉时局的必然结果。
二、魏初“莫取有名”的新动向
“以名取士”之风在汉末达到鼎盛,在曹魏时期却受到了统治阶层特别是魏氏三祖的厌弃。
曹操曾致信孙权,认为“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16]31。当朝臣建议其“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以消除时人担忧、成就忠义美名时,曹操表示“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16]19,明确指出虚名的危害以及自己决不为虚名所困的心意。更甚之,曹操还给予名声不佳者以入仕机会。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曹操指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16]22此举消弭了令名与恶名在举荐上的差别待遇,以才能选士,对“以名取士”的观念与实践而言是一次颇具颠覆意义的解构与冲击。
曹丕厌恶邀名之举,反对虚名乃至“清名”。在《典论》中,他严厉批判了汉末“要名者倾身以事势”“名定乎横巷”[16]75的现象。当成皋令沐并意欲收捕索要财物的校事刘肇时,曹丕下诏指责其“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16]53,从此细节也可看出曹丕对“清名之士”的反感。
与曹操、曹丕相比,明帝曹叡对名声的看法就更加直接与明显。就选举中书郎一事,曹叡曾下诏“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7]651,可见其对名声的厌弃。
应该说,曹操、曹丕乃至曹叡也非全然弃用名士。史书记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曹操“以陈群为酂令,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7]380。曹丕曾称赞杨彪“世著名节”[16]47而给予几杖之礼,称扬庞德“式昭果毅,蹈难成名,声溢当时”[16]55;曹叡也曾重用过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当世俊士”[7]769。但相对汉末而言,“以名取士”已不复往日热潮。这种转变自然也有其复杂的动因。
(一)汉末名声的异化、物化是“莫取有名”的内在诱因
“名的文化心理动力功能,主要是通过人们对不朽荣名的追求和对神圣名节的捍卫而展开。”[17]107孔子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8]214,屈原忧“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19]12,司马相如认为“身死无名”将“耻及父母,为天下笑”[8]3045,三者皆体现了士人对精神层面的不朽荣名的追求。同时,名又能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集中表现为名与利的紧密捆绑。“利”本就是世人的生存基础和重要目标,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8]3256。名利双收更是绝大多数士人的现世追求,特别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9]3620——可见“利”对士人行为的重要指导意义。东汉社会,政府奖励名节,重用名士,“名声”成为士人仕进的重要砝码,名与利更是连动生成。
而事实上名、利有时又很难两全。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有“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20]80的判定,以对名、利的不同态度来分小人与君子。至东汉后期,士人“好高尚义,贵于名行”[21]637的意识与行动,使得“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12]104。其背后隐藏着以名牟利的深层动因。
东汉后期,最高学府洛阳太学中,士子多“曳长裾,飞名誉”[10]2481。才华之士也以托名为要事,如赵壹上计京城期间,“以公卿中非(羊)陟无足以托名”而“日往到门”[10]2632。袁绍曾先后为母、父服丧,“凡在冢庐六年”[7]188,后世学者谓之“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22]203。各级官员也刻意营造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以致“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23]292。
才智不显、品行有亏的士人也试图通过各种异常举动、过激行为引起世人瞩目,以致名声日显,如前文提到的晋文经、黄子艾、向栩、赵宣等士人。由此也可见汉末士人的逐名之举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正是“东汉之末,士之矫伪极矣”[24]580。这种刻意塑造出来的名声经不住现实的考验:晋文经、黄子艾“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小道破义,空誉违实”而为符融所觉察,“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10]2233;向栩拜赵相后,“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任职期间更是毫无作为,且提出读《孝经》以灭贼的谬论,最后落个“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10]2694的结局;赵宣以至孝显名,最后却被查出其“五子皆服中所生”,“遂致其罪”[10]2160。
汉末士人过度逐名、以名谋利的不良风气使得“名”在这一时期逐渐被异化、物化甚至污名化。往之名声所指代的能力、才华、品行、素养等内核价值逐渐被轻视、淡化以致模糊,取而代之的则是奇谈怪论、异行所造就的虚浮、空泛、华而不实的名声。名不副实、名实相悖,自然引发了世人对“名声”的犹疑与鄙弃。
(二)汉末名声批判为“莫取有名”奠定舆论基础
“以名取士”带来的精神享受和物质利益引发了士人的逐名狂潮,而名实不符乃至严重背离的现象引发了士林的关注与思考,对士人重名、好名、逐名现象的批判也随之产生。就在东汉后期已有因征聘之士“功业皆无所采”而产生的“处士纯盗虚声”的俗论,李固认为这是“观听望深,声名太盛”引发的心理失落,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致[10]2032。其时有识之士的批判大多集中于士人结交以求名这一风气:王符集中批判了“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盛飨宾旅以求名”[25]20的不良风气;徐幹指出“古之交也为求贤,今之交也为名利而已矣”的本质差异,认为“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的“以名取士”风气造成了“民见其如此者,知富贵可以从众为也,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的追逐名利的社会心理[23]290-291;仲长统着力批判其时“交游趋富贵之门”“慕名而不知实”[21]900的不良士风,并直言“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10]1644,体现出远离仕途的决心以及对名声的淡然态度。
在这些有识之士看来,名声不再是内在价值的外部评价,反而变成了可凭借其进入仕途、获取利禄的工具。正如后世学者所总结:“士大夫交游结党,其流弊所及,则为俗士之利益结合。”[26]137而名不副实、举非其人造成恶劣后果必然引起清醒之士的反思:“它使得一批士大夫厌恶了群体认同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个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27]315同时也为曹魏“莫取有名”的用人举措奠定舆论基础。
(三)曹操务实的名声观消解了名声的政治影响力
作为汉末魏初政坛核心人物,曹操的名声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士人的用进废退。而论及曹操的名声观,首先有必要了解曹操的名声。
据史书记载,曹操乃宦官曹腾之后,其父曹嵩虽“官至太尉”,然“莫能审其生出本末”[7]1,曹操也因此被攻击为“赘阉遗丑”[21]928。同时,少年曹操“好为游侠”,曾有“抽刃劫新妇”[28]851的荒唐之举。史书记载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此,“世人未之奇也”[7]2,即未有良好且足够鼎盛的名声。待大权在握,曹操更是为政敌所攻击,特别是“挟天子令诸侯”、不愿让出实权的举动令其背负了“托名汉相,其实汉贼”[7]1261的恶名。曹操对名声的态度也因此呈现出复杂性与多面性。
不可否认,受大时代环境影响,曹操确有慕名声、慕名士之举。其《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开篇即写道:“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16]18这清晰展示了其年少求名的心境。对名士,曹操亦推崇有加。他称赞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7]353,称颂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7]650。然而,相对汉末识人、用人“必采名誉”,曹操更加注重“名声”的名实相符。这一点可从曹操对王修的态度与评价看出。史书记载:“及破南皮,阅(王)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7]347此外,曹操还曾致信王修,赞扬其“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副,过人甚远”[7]347-348。
总的来说,曹操的出身是卑贱的,名声是不佳的。在清名盛行的汉末,其诡谲、散漫的行事风格为大众所鄙视,虽然一度有邀名之举,也得到了一定的名声,然其出身一直为人诟病,其内心深处对名声的态度是:始渴求之,终怠慢之。待其有一定地位和权力,自然要不断降低甚至消除名声对政治的影响力。
而后来者曹丕、曹叡父子更是继承和发展了曹操的名声观念。魏氏三祖的名声观对政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反映于“以名取士”热潮的逐渐散去。“太祖为司空丞相,(毛)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7]375文帝时期,张登以“忠义彰著,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饔膳近任”[7]411而被封为太官令。明帝虽为卢毓“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7]651-652的一番说辞所劝服,却推行鉴别官吏优劣的考课之法。这些都说明曹魏时期选举以“名”的风气正逐渐消歇。
(四)曹魏集权统治是“莫取有名”的根本动因
如前文所言,汉末“以名取士”之风还是其时士人对抗戚宦政治的产物。士人们因“抗愤”而“横议”,并通过“品核”“题拂”“裁量”等一系列方式干预政治。这一系列举动下形成的“名声”自然也带有浓厚的干政色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言之,“以名取士”正是士人对中央集权(无论是皇权还是宦官专权)统治的一种挑战。对于汉末实际掌权的曹操集团和其后新生的曹魏政权而言,巩固和加强集权统治是首要问题,取士的标准自然也围绕此展开。而“唯才是举”“莫取有名”,正是对“以名取士”风气的矫正,说明曹魏统治者开始有意识降低、摆脱、杜绝士林舆论对朝廷用人的影响,特别是名士对朝政的影响。
“莫取有名”首先是因为有部分名士对曹魏政权持不合作态度,自然需要摒除。以名士孔融为例。孔融“幼有异才”,十岁时便得到李膺的“高明必为伟器”[10]2261的评价,十六岁时掩护党锢名士张俭逃脱,“由是显名”[10]2262。大将军何进一度有追杀孔融之心,而为宾客“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10]2263之言论所劝止。曹操亦曾因孔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而欲杀之,奈何“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10]2272,由此可见孔融的盛名与影响力。其盛名固然使上层有所忌惮,使得孔融几次免遭杀身之祸,但也正是这一盛名最终为其招来了灭门惨祸。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终于以“大逆不道”罪将孔融诛杀,并下令宣示孔融之虚名,以警世人,文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之采其虚名,失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16]16这一结局既与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有关,更是孔融“好士,喜诱益后进”的结交喜好和“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士林地位所致,更是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的具体操作[10]2273。对曹操而言,孔融有如此显赫的名声,却又是这般轻慢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挑衅,更是一种威胁。
又比如汉末名士管宁,其“清声远播,顽鄙慕仰”[16]380,先后受到了魏氏三祖的征辟:曹操拜司空时一度“辟宁”[7]354;曹丕曾“诏以宁为太中大夫”[7]356;明帝又“以宁为光禄勋”[7]356。而所有这些征召都遭到了管宁的“固辞”[7]356。在反复征召未果之际,曹叡诏问青州刺史,指责管宁“违命不至,盘桓利居,高尚其事”的不仕行为已“失考父兹恭之义”,并质疑其“澡身浴德,将以曷为?”[7]357“为守节高乎,审老疾尫顿邪?”[7]358。由此可见,名士屡征不仕,引起了朝廷对其政治立场的狐疑。由此亦可见,曹魏时期的“以名取士”也不过是曹魏统治者的驭人之术,是巩固政权、收拢民心的一种方法而已。因此,无论是“以名取士”还是“莫取有名”,一切都出自巩固政权的需要。
与曹操不同,曹丕力图以文章不朽来淡化或消解士人对政治名声的追逐。这种大力宣扬文章不朽的做法,也是对其时士人的一种提醒与规劝。关于曹丕对士人的用与察,汪春泓指出,“汉末士人起而挽救汉刘政权的命运,大肆讲政治道德和原则,自然就潜伏着冲突的危机”[29]135,也为曹魏新政权的稳固埋下隐患。因此,曹丕称赞“怀文抱质,恬惔寡欲”的徐幹有“箕山之志”[16]66,推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6]83的地位,其意在“引导士风,当他推行改朝换代的重大举措时,亦令士人无意干预时政”[29]135——将在汉末政治领域激荡许久的名声引入文章写作领域,以此来转移、消解易代之际士人的政治热情。
曹叡对浮华之士的弃用自然也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激扬名声”“以名取士”正是浮华的产物,对浮华风气的打击必然导致对名声之士的弃用。曹叡曾下诏要求“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6]91。而其“选举莫取有名”的主张也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史书记载:“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7]651此“四聪”“八达”如同汉末党锢名士中的“三君”“八俊”等名号,对统治者而言意味着又一批士人浮华交会、自我标榜、互相援引,试图再度“建立士林舆论中心,品评人物,影响朝廷的选官用人”[26]143。最后这些“驰名誉”者终以“构长浮华”之罪而“皆免官废锢”[7]76。
综上,汉末名声的异化、物化昭示其被弃绝的必然性,是内在诱因;其时有识之士的名声批判为“莫取有名”奠定舆论基础;曹操不佳的名声与其务实的名声观是“莫取有名”的原动力;而曹魏集团集权统治的需要才是朝廷“莫取有名”的根本动因。这其中既有对伪名士、假名士的“莫取”,是魏氏三祖对汉末魏初虚浮“名声”不遗余力地矫正,更是对不合作士人的攘除,显示了曹魏集团务实的名声观与强力集权之趋势。
三、曹魏时期名声走向
“以名取士”风气在汉末士人与宦官集团的对抗中逐渐高涨,体现了此期士人以舆论、名声来干涉朝政、左右时局的用世之心,同时也衍生出不少假名士、伪名士,并引发过度逐名的不良风气;“莫取有名”则是曹魏集团摒弃浮华、收拢皇权、打击名士的重要举措。曹魏时期的“有名”之士,依然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品性高洁、才华横溢和能力突出的士人,但是汉末旨在以“激扬名声”对抗弊政、颉颃政统的干政士人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成为“有名”士人中重要的、突出的一部分。即使在新的统治集团已然形成之际,这一股势力依然表达着“政归士人”的政治诉求。也正是如此,魏氏三祖执政期间对部分于政权有益、无害的名士依然礼遇之,而对执意结党、延续汉末名士之风的士人则予以重创。可以说,“莫取有名”更多是对这一批名士的仕途淘汰与政治清洗。孔融之死、魏讽之死、青龙浮华案即是明证③。
当然,这种清洗又很难彻底完成。这与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体规模、治世理念、济世情怀和抗争精神有关。就在士权与皇权的反复较量中,新的选拔人才的方式逐渐浮出水面。史书记载:“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7]619旨在肃清其时士林中人物清浊难辨之风气;而从“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30]1243的记载来看,中正之设立,正是以品评人物为要务,以备朝廷之需。史书又载“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为一时选举之本耳”[31]1058,指出士人流动引发的考察不便,故而有考察人才的中正官的出现。这当然也是九品中正制诞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学者指出九品中正制“实现了朝廷选举和名士月旦统一, 朝官保举和乡里清议统一, 人士徙移和核之乡闾统一”[32]49。而从名声沉浮角度来看,当局者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对汉末士林舆论干政的改造和利用。它依据家世、道德、才能将士人分级、定品,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种赋予士人“名声”的过程。归结之,汉末魏初盛行于世的“名声”继之以“品第”的形式存在,其赋予者由士林转为朝廷,士人的名声由此打上了清晰的、沉重的官方烙印。
注释:
①关于“名”的多重内涵,可参考苟东锋《儒家之“名”的三重内涵》,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第42—48页。
②“名士”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为其注解:“名士,不仕者。”蔡邕亦谓:“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孔颖达主张“名士”即“有名之士”(《礼记正义》卷第十五)。据此可知,“名士”有广义(有名之士)和狭义(不仕之士)之分。本文中的“名士”取其广义。此外,牟宗三在其《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指出:“名士者,有名之士也,声名洋溢,人所注目。”并强调这里的“有名之士”之“名”,“唯在因显一逸气而名”,又与本文“有名之士”不同。概言之,本文中的“名士”指因自身学识、德行、才华、能力等方面异于他人或过于常人而获得他人和社会褒扬之士,即拥有良好名声的士人。
③关于魏讽之死、青龙浮华案,可参考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中《“魏讽谋反案”析论》《“青龙浮华案”析论》两章。